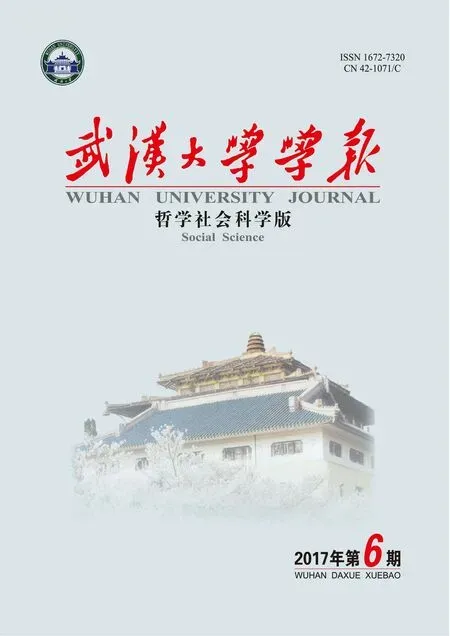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
胡锦光
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
胡锦光
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时依据两个基本法的明确规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为了保证这一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规定有权审查两个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两个基本法虽然未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法院对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具有审查权,但依据两个基本法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规定,可以推定也应当具有审查权。同时,香港地区属于英美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是毫无疑义的;澳门地区属于大陆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易造成不同法院之间对相同法律的合基本法性上的差异,需要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点,将违反基本法的判断权集中于终审法院。审查机关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其审查的依据应当是基本法的正文及附件,而不能单独依据基本法的序言及宪法进行审查。法院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必然要受到其所获得的基本法解释权授权限度的限制,且还要受到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应遵循的司法原则的限制。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一国两制; 基本法审查权; 司法审查; 基本法第158条
香港基本法第8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澳门基本法第8条规定,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第11条第2款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据此,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获得了最高法的地位。那么,由什么主体来对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审查而维护基本法的最高法地位?进而,审查的依据是什么?由审查机关的性质所决定,审查的界限在哪里?应该说,这一问题如同美国宪法相似,在两个基本法中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需要两项基本内容:一是最高法地位的确立;二是审查机关的确定。美国宪法只明确了第一项内容,而没有明确第二项内容。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开创了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联邦国会制定的法律合宪性的先例,从而弥补了美国宪法关于违宪审查制度规定的第二项内容。我国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与美国宪法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完全相同的空白。。同时,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分属两个不同的法系,但两个基本法的规定却是完全相同的。在“一国两制”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的背景下,有探讨和分析的诸多空间,限于篇幅,本文仅探讨其中的三个问题。
一、谁有基本法审查权?*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使用过多种概念,如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基本法诉讼等。笔者认为,基本法并非一个国家的宪法,只是在一个统一国家的特定区域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使用“违宪审查”并不妥当;司法审查只是基本法审查概念之下的一个子概念;“基本法诉讼”是指所有的依据基本法所进行的诉讼,其中包括依据基本法对特区法律的审查。因此,使用“基本法审查”这一概念相对更为妥当。
(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审查权
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第17条都规定,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其所属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该法律的失效,除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外,无溯及力*此外,香港基本法第160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香港地区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为同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如以后发现有的法律与本法抵触,可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在香港地区原有法律下有效的文件、证件、契约和权利义务,在不抵触本法的前提下继续有效,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承认和保护。澳门基本法第145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时,澳门地区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为同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如以后发现有的法律与本法抵触,可依照本法规定和法定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根据澳门地区原有法律取得效力的文件、证件、契约及其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在不抵触本法的前提下继续有效,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承认和保护。此两个条款也可以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的依据。。
这一条款的规定,显然是基本法制定者已经考虑到了既然两个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地位,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就有可能与基本法相抵触,有必要设定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审查机制。换言之,上述条款即是基本法制定者所设计的保障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作为最高法地位的机制。在基本法制定者看来,保障基本法地位的机关只能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为非常设机关,对香港地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日常性的审查工作是不可行的。同理,依据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亦是进行宪法监督的经常性机关。,而不能是特别行政区的某个机关。因为,第一,基本法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的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基本法律*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香港基本法第159条规定,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非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第二,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全国性法律,而非仅在特别行政区有效的地方性法律;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具有解释权;第四,中央负有维护“一国两制”及特别行政区稳定的责任。同时,在基本法制定者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交来备案的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的法律进行审查,并对不符合基本法的法律予以发回,使其失去效力,以维护基本法的最高效力,保证基本法统一秩序,是保障基本法作为特别行政区最高法的唯一机制*香港终审法院于1997年回归不久作出了吴嘉玲案判决,首次行使了司法审查权。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五位法律专家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措辞严厉地批评香港终审法院的这一做法。其基本根据是,香港基本法已经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保障基本法地位的权力,而并未赋予香港法院这一权力。。
毫无疑问,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性质和地位,基于基本法的性质,依据基本法的制度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具有审查权。而且,这一制度安排是非常妥当的。
但同时,又必须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审查的性质和方式。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审查从性质上说,属于政治审查。依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性质是最高民意代表机关的常设机关,本质上属于民意代表机关,主要的职能是制定法律,以及对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决定,在性质上属于政治机关。其并不审理具体的争讼案件,主要是从政治上审查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同时,在审查方式上,其采用的是抽象的原则审查。即对于提交备案的法律从条款字面的含义上审查其是否符合基本法,对于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的法律的理解,均是纯条款字面的意义,并不联系具体的诉讼上的争议、争议双方的利益冲突及争议双方的利益主张和理据。也正因为仅仅是从条款字面上审查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与基本法相抵触,在发现相抵触的冲突点、启动审查的动力及紧迫性等方面存在消极状态,实际进行审查的可能性并不大*香港/澳门基本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并未对特区立法机关提交备案的特区法律进行一次审查,并未发回过任何一个特区法律。。
当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基本法审查权又是非常必要的。首先,这是一种主权宣示。为国家的某个区域制定特定的法律、解释这一法律及维护这一法律的效力是一种国家主权行为。其次,掌握这一权力与是否实际行使这一权力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当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这一权力时,就可以在必要时行使这一权力,完全依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判断而定。
在殖民地时代,宗主国控制殖民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一是宗主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殖民地或者为殖民地制定专门的法律以限制殖民地的发展;二是殖民地制定的法律必须提交宗主国进行审查,即政治审查;三是宗主国掌握司法终审权,殖民地法院审理的案件最终可上诉至宗主国法院,宗主国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附带地对殖民地的法律是否符合宗主国的法律进行审查,即司法审查。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虽然完全不同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但中央通过基本法授予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这一高度自治权并非完全的自治权,特别行政区在行使高度自治权时是否符合基本法,当然有必要通过审查进行控制。
(二) 特区法院的基本法审查权
在基本法已经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审查权的前提下,还需要探讨特区法院是否具有基本法审查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起因是1997年香港回归不久,香港终审法院对吴嘉玲案的判决。在这一案件中,香港终审法院通过解释基本法并依据基本法审查了《香港入境条例》的相关规定,实际行使了基本法审查权,因而引发了极大的争议。那么,在基本法未明确授权特区法院拥有基本法审查权的情况下,特区法院是否具有基本法审查权呢?
笔者认为,从解释权与审查权的逻辑关系、从各国司法审查权的实践及经验中,是可以推导出特区法院具有基本法审查权的,换言之,特区法院具有基本法审查权是基本法“默示”的权力。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第三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澳门基本法第143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亦作出了完全相同的规定。
在各国的法律体系中,不同法律文件的效力存在位阶等级。上位法在效力上高于下位法,下位法如果与上位法存在冲突则自然无效或者当然无效。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存在冲突,而法院同时有权解释上位法和下位法时,当然有权得出下位法是否与上位法存在冲突的判断,并当然适用上位法,而排除下位法的在具体个案中的适用*在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法院如果认为法律违反宪法,只有权在个案中拒绝适用被认为违反宪法的法律,而不能直接撤销该法律或者宣布该法律无效。。
香港基本法第1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澳门基本法第11条还根据澳门的情况,明确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根据这一规定,基本法在特区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有人甚至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小宪法”*“小宪法”的称谓易于被认为基本法是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宪法”,在这一意义上,这一称谓是非常有害的。,特区的一切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很显然,这些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如果同基本法相抵触,则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当然不得适用。
通过基本法授权,特区法院获得了基本法部分条款的解释权;同时,特区法院在其司法权能中,固有地享有对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解释权。法院在审理个案中,若案件当事人或者法院自身对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基本法存在争议或者疑问时,必然需要通过对两者进行解释,以释疑解惑,寻找到恰当的裁判依据。如果法院经过解释认为,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与基本法相抵触,则在个案中不予适用。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规定了联邦宪法的最高法地位,但未明确规定违宪审查机关。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开创了联邦法院审查联邦国会法律的先例*此前,联邦法院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已有审查州法律的先例。。马歇尔首席大法官在判决书中找到的宪法根据是著名的三段论,即大前提:宪法是最高法;小前提:法官宣誓忠于宪法;结论:法院有权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该三段论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法院司法审查权的根据是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美国与我国香港、澳门地区所不同的是,美国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权是其司法权能中所固有的,而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的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授权的。,但实际上暗涵着这一根据。基本逻辑是,宪法高于法律,法官宣誓忠于宪法,而法官通过解释宪法和法律,认为法律违反宪法,即不能依据违反宪法的法律作出判决*该三段论在后世曾遇到另外三段论的挑战。有学者提出以下三段论,即大前提:宪法是最高法;小前提:总统宣誓忠于宪法;结论:总统有权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该三段论之所以没有被广泛认同,重要原因在于总统没有宪法解释权。。据此,法院实际上具有了司法审查权。
从世界各国违宪审查体制的经验与实践也可以看出,宪法解释权与违宪审查权在主体上是同一的。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虽然在功能上存在差异,宪法解释不一定是为了违宪审查,但违宪审查必须进行宪法解释则是必要的条件。因此,英美法系国家法院有宪法解释权,故同时有违宪审查权;大陆法系国家专门法院因无宪法解释权,故当然不享有违宪审查权,需要特设宪法法院解释宪法、行使违宪审查权。
1.香港特区法院的审查主体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明确授权香港特区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基本法解释权。香港基本法第81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署法庭和其他专门法庭。因此,香港特区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基本法审查权。这种审查权主体的安排属于分散性审查。行使基本法审查权的法院是在个案中审查判断特区法律是否与基本法相抵触,如果认为被审查的特区法律与基本法相抵触,只是在个案的判决中拒绝适用被认为违反基本法的特区法律,而无权宣布撤销该法律或者宣布该法律无效。从理论上说,该法律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在这种分散性审查之下,审理案件的每一个法院都有权通过解释基本法审查特区的法律,并宣布在个案中拒绝适用。那么,如何保证同一法律的同一效力呢?其所依靠的是英美法系法院内部特有的“先例约束原则/遵循先例原则”,即最高法院及上级法院所作出的判决虽然只是裁决个案的纠纷,判决的效力只及于个案的当事人,但其与先例约束原则/遵循先例原则相结合便成了判例,而判例则具有普遍约束力或一般效力,下级法院在未来的类似案件中,必须以最高法院及上级法院的判例作为判决的依据。最高法院或者上级法院如果认为某项法律规定违反宪法,则所有的法院均不得予以适用。该项法律虽然未被宣布撤销,但实际上已成为“死法”。
香港地区属于英美法系地区,法院系统内部亦实行先例约束原则/遵循先例原则。同时,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即使需要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因此,虽然基本法授权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基本法审查权,但仍然能够保证法律效力的同一性。
2.澳门特区法院的审查主体
澳门基本法第143条明确授权澳门特区所有法院均具有基本法解释权。澳门基本法第84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初级法院、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第86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行政法院。因此,澳门特区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基本法审查权。行使基本法审查权的法院亦是在个案中审查判断特区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与基本法相抵触;法院如果认为被审查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与基本法相抵触,亦是在个案的判决中拒绝适用,无权宣布撤销该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宣布该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效。
澳门地区属于大陆法系地区,法院系统内部并不存在“先例约束原则/遵循先例原则”,而又实行分散性审查体制,那么如何保证同一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同一性?
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需要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对于这一类条款,采用这一机制以保证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同一性,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对于这一类条款,审理案件的所有法院均具有解释权及审查权。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难以保证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同一性。
根据澳门地区《司法组织纲要法》规定的“统一司法见解”制度,澳门终审法院负有统一司法见解的权力,即当不同法院或者法官对同一个法律条款作出不同的解释,形成对立的判决时,终审法院可启动统一司法见解程序,对两个判决中的法律条款作出最终解释,消除分歧。终审法院的解释对以后法官的判决具有约束力,必须遵守。这一制度对于统一法院对特区法律的理解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现有的统一司法见解制度要达到统一基本法的理解,其障碍在于澳门基本法已经授权澳门所有法院均具有基本法解释权。
有学者认为,应通过建立特区内部统一的基本法解释和审查机制,保持特区司法机关内部对基本法解释的统一性。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在保留任何一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和审查的基础上,同时赋予终审法院对下级法院解释和审查基本法的意见进行复查的权力。如果特区终审法院发现下级法院对基本法条款的解释和违反基本法的审查有问题,可发回下级法院重新审理,或者由终审法院直接对基本法条款作出解释,然后下级法院按终审法院的解释重新审理案件,以确保对基本法解释的权威性及基本法条款解释的统一性(骆伟建,2007:203)。这一方案也需要修改澳门基本法才能实现。
笔者认为,最佳的方法是修改澳门基本法,根据澳门的特殊情况,只赋予澳门终审法院基本法解释权及基本法审查权。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是通过解释基本法,明确规定需要解释基本法才能够作出澳门法律违反基本法的判决的案件,最终需要由终审法院作出判决*在这一制度安排上,澳门基本法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的做法。。
二、审查的依据是什么?
香港基本法第1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澳门基本法第11条还根据澳门的情况,明确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
(一) “本法”是什么?
根据基本法的上述规定,很显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及特区法院审查的依据是“本法”。所谓“本法”,在香港,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澳门,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两个基本法的结构是相同的,由序言、正文、附件三部分构成。该三部分共同构成基本法的整体。三部分的制定主体、通过程序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三部分在法律效力上当然是完全相同的。“本法”应当包括三部分。区别只是在于,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序言和正文的修改,只能由全国人大进行,而附件的增删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需要指出的是,修改主体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法律效力上的不同。
全国人大常委会及特区法院直接依据“本法”中的正文部分和附件部分对特区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审查,应当是没有争议的。问题是,能否直接依据“本法”中的序言部分对特区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审查?
众所周知,宪法通常有序言,法律通常只有正文而没有序言。我国目前只有三部法律在正文之前列有序言,即民族区域自治法、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序言的特点是,以叙述性文字阐述以法律规范的形式难以表达的内容。内容主要是,法律制定的背景、制定的目的、制定的指导思想、制定的基本原则等。香港基本法的序言如下: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占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由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予以阐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
从上述香港基本法序言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其基本内容是,香港地区的历史、香港回归的过程、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原因及依据、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方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的依据等。
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及特区法院在行使基本法审查权,对于能否将基本法序言作为审查的直接依据时,可以参考宪法序言在各国违宪审查中的作用。1.在绝大多数国家,序言不能成为违宪审查的直接依据。其基本理由是,序言内容的表述是叙述性文字,而非严谨的规范性规定,其具体内涵难以清晰地界定;序言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表述,难以完成规范的功能。2.违宪审查机关在解释宪法正文时,应当参考序言的内容和规定。例如,序言中关于基本原则、指导思想、制定目的等规定,必须作为解释正文的参考。诸项基本原则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关系,在解释正文时必须参考诸项基本原则的规定,平衡不同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而不能仅仅根据其中一项基本原则确定正文中某项规范的含义*例如,依据法治原则,公权力机关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接受宪法审查;而依据分权原则,公权力机关内部享有一定的自律权,同时,司法机关的权力也存在一定限度,因此,国家行为可以不接受司法审查。。3.世界上仅有法国的宪法序言才可作为违宪审查的直接依据。这是由法国宪法的结构所决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通常是各国宪法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国宪法的正文中没有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这一内容是规定在宪法的序言之中*法国现行宪法即1958年宪法序言规定,1789年的人权宣言、1946年宪法序言是法国宪法的组成部分,具有宪法效力。。因此,在法国,宪法委员会如果不能直接依据宪法序言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则法国的公民基本权利将无法保障。法国宪法委员会在作出的一项违宪审查决定中明确说明,宪法序言部分的规定是进行违宪审查的直接依据*1971年7月16日宪法委员会对于“结社自由案”的裁决,明确宣布该法律的一些条款和宪法不一致,其原因则是它们与宪法序言所规定的原则相违背。。
(二) 宪法能否成为审查的依据?
宪法能否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及特区法院审查特区法律的直接依据,必须首先明确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对此,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基本法是宪法的特别法。基本法是依据宪法第31条制定的,即依据宪法的特别授权制定的。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基于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情况,仅适用基本法而不能适用宪法,基本法与宪法是平行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宪法在作出特别授权之后,特别是宪法已经在基本法中获得了体现*全国人大在通过两个基本法的同时作出决定,认为基本法符合宪法。,与基本法基本上没有关系。依据这一观点,在审查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时,当然不能直接依据宪法。
第二种,认为基本法是我国宪法的组成部分。依据“一国两制”指导思想,在设立特别行政区并实行特殊的制度和政策之后,我国的宪法应当由三部分构成,即规定“一国”的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宪法,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规定“一国”的宪法在内地和特别行政区均适用,规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宪法仅在内地适用,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仅在特别行政区适用。按照这一观点,我国现行宪法实际上规定了两部分内容,即“一国”和社会主义制度;除基本法适用于特别行政区外,现行宪法中“一国”的部分也适用于特别行政区。在审查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时,也应当适用宪法中关于“一国”的规定*实际上,我国现行宪法中关于“一国”的规定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难以区分,适用时操作性较为困难。笔者曾经专文作过探讨。。
第三种,虽然学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观点,但通说认为整部宪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而不仅仅限于宪法的第31条,宪法的效力高于基本法。对于这一点,法律上的依据应当说是非常充分的。(1)两个基本法序言均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设立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澳门地区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2)两个基本法第1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3)全国人大在通过两个基本法的同时,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决定中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香港/澳门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
在这种关系下,宪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宪法在效力位阶上高于基本法。因此,在审查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时,只能依据基本法进行审查,而不能直接依据宪法进行审查。
基本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依据宪法”的基本含义包括依据宪法的立法授权、依据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依据宪法的基本原则、依据宪法的理念精神和制宪目的、依据宪法规范的内涵等。基本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制度化。在基本法制定之后,宪法的上述内容实际隐含在基本法之中。那么,在理解基本法的内涵时,就不能仅仅从基本法自身的内容和层面上理解基本法,而必须首先从宪法层面理解基本法,如此才能将基本法的内涵理解透彻。虽然在审查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时,不能直接适用宪法作为审查依据,但在说明理由部分,必要时是可以引用宪法规定予以补强的。特别是关于“一国两制”中的“一国”部分,“一国”的含义是什么,“一国”的表现是什么,“一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些必须联系宪法的规定予以确定。
三、司法审查的界限是什么?
如前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权的主要依据是两个基本法的第17条及第8条,根据该条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的界限是:(1)不审理具体案件而只进行抽象的原则审查;(2)审查的对象为特区的所有法律;(3)审查的标准是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条款;(4)审查的程序是先征询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5)审查的效力是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除另有规定外,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无溯及力。
限于论文的篇幅,这里仅探讨特区法院审查的界限,即司法审查的界限。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其性质为非民意代表机关,无权代表民意创造规则、平衡利益,只能依据既有的规则裁判案件、解决纠纷;其工作方式是事后、被动地审理个案,作出裁判。同时,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而非独立的国家,其享有的高度自治权由中央通过基本法授权而非固有,其享有的是“高度自治权”而非主权意义上的绝对权力,必然受制于授权者。受此两方面的规定性,特区法院在行使基本法审查权时,必然地要受到约束而形成一定的权力边界。
(一) 解释权限度的限制
特区法院的基本法审查权来源于基本法解释权,因此首先必须受到其对基本法解释权限度的限制。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特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非其固有,而由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授予,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还保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依照授权理论,授权者的解释当然要高于被授权者的解释,在授权者与被授权者均作出解释的情况下,被授权者应当服从授权者的解释。
依据基本法的规定,特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包括对自治条款的完全解释权和对非自治条款的初始解释权。按照这一制度安排,特区法院如果依据基本法中的自治条款对特区法律进行审查,则有权根据自己的解释作出裁判;如果依据基本法中的非自治条款对特区法律进行审查,则有权在作出可以上诉的裁判中进行解释,但这一部分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在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审裁判之前,必须由特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作出可以上诉的裁判的法院虽然有权解释基本法中的非自治条款,但其解释若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相悖,则必须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此处的难点在于,基本法条款中哪些属于自治条款、哪些属于非自治条款难以区分;同时,判断的主体并不明确。。
香港高等法院在审理立法会议员宣誓案件过程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已进行解释的情况下,能否对基本法中的非自治条款进行解释而不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如前所述,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特区法院对于基本法中的非自治条款在作出可以上诉的裁判之前是“可以”解释基本法的,但只是“可以”,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是必须的、最终的和最高的。因此,在香港高等法院对基本法中非自治条款解释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了解释,则没有必要再作出解释,应当直接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作出裁判。此次香港高等法院在裁判中并未直接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作出裁判,应当说是非常不妥当的*香港高等法院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在立法会议员宣誓案件故意不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而又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判决,这一做法违背了基本法的规定。。
(二) 案件性(成熟性)原则的限制
作为司法机关,法院的全部任务只是审理案件、裁判纠纷。法院只能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附带地审查作为案件裁判依据的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而无权抽象地审查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因此,法院审查特区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是存在一个具体的个案。
依据案件性原则,法官不得立法,法官不得参与立法,法官不得参与行政管理,审理案件的法官才得对案件发表意见,审理案件的法官必须在合议阶段对案件发表意见。
依据案件性原则,首先必须存在一个具体的纠纷;纠纷又必须成熟为一个具体的案件,成为一个司法机关具有管辖权的案件,又必须是根据法院内部的分工,审理案件的法院具有管辖权的案件。依据国家权力分工原则,司法权所能够受理和审理的纠纷,有着一定的限度。虽然内地曾有法院院长扬言,法院可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但司法机关并不是全能的和万能的。
法官所擅长的及所能做的主要是合法性判断,法官对于合理性判断是受到限制的,法官无权对专业性、科学性问题作出判断,法官对属于其他国家机关内部的自律性问题也无权判断*在立法会议员宣誓案件中,立法会主席即认为议员宣誓是否有效问题属于立法会的自律权范畴,法院不应当具有管辖权。。
(三)当事人资格的限制
法院审查特区法律只能是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附带地进行,其审查特区法律的本质是为了确定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从而保证裁判的合法性及彻底完成解决纠纷之司法功能。因此,如果法院认为特区法律可能违反基本法,也可以直接进行审查。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法院适用了违反基本法的特区法律作为裁判的依据,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然受到侵害。作为救济手段,当事人有权在诉讼过程中,向审理案件的法院提出特区法律可能违反基本法的异议并要求进行审查。赋予案件当事人质疑特区法律违反基本法的资格,是作为当事人的救济权利而设定的,因此,其资格只限于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利害关系”应当包括与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及结果上的利害关系。按照这一标准,有资格提出异议的当事人应当包括原告、被告、有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除此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即使认为特区法律可能与基本法相抵触,也不得向法院提出异议。换言之,法院只能依据案件的当事人所提出的异议,才能对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审查。
(四)双重基准的限制
法律是民意代表机关依据严格的立法程序制定的,是民意代表机关意志的体现。法院作为行使司法权的机关,为非民意代表机关。因此,其在对民意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时应当表现出极大的尊重。
法院尊重立法机关的表现即是按照双重基准对待被审查的法律。所谓双重基准,是指除将规范表达自由的法律推定为违反基本法外,应将立法机关制定的其他法律一律推定为符合基本法。可见,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中,规范表达自由的法律属极少数,其他法律为绝大多数。
推定的意义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承担举证责任者显然负有更大的责任。规范表达自由的法律因为被推定为违反基本法,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其举证责任应当由立法机关承担。当事人指控规范表达自由的法律违反基本法,立法机关需要举证证明该法律合乎基本法,以推翻当事人的指控,否则,当事人的指控成立,该法律构成违反基本法。反之,其他法律因为被推定为合乎基本法,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举证责任应当由当事人承担。
(五) 国家行为豁免审查的限制
国家行为免受司法审查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国家行为,又称之为政治行为、统治行为、政府行为。其免受司法审查的原因主要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分权原则等。我国目前有三部法律对国家行为豁免审查作出了规定。行政诉讼法第13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原行政复议法也作出了与行政诉讼法相类似的规定,后修改时予以取消。。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第19条第2款规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应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文件,上述文件对法院有约束力。行政长官在发出证明文件前,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证明书。因此,法院不能通过审理国家行为案件而审查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
问题是,需要界定何为国家行为?在法治国家,国家机关的公权力行为均是依法作出的,均具有法律性,而同时这些行为均又是基于一定的政治考量作出的,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换言之,国家机关作出的任何一个公权力行为兼具法律性和政治性。当其法律性大于政治性时,该行为为法律行为,法院则可以依据法律进行审查;当其政治性大于法律性时,该行为为国家行为,法院则不能依据法律进行审查。是否为国家行为,判断的标准为该行为是否具有高度政治性*各国法院早期的判断标准为所作出的行为是否基于政治动机,后改为是否具有高度政治性。。
法院之所以不得审查国家行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法院缺乏审查的标准、法院无力对审查的后果承担责任、法院考虑到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等。与我国不同的是,其他国家通常对何者为国家行为未作出明确规定,而由法院在个案中进行判断。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对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对此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第2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基本法的规定看似比较明确,实则存在很大的考量空间。其焦点在于该条款中的“等”的理解。即该条款中的“等”为等内之“等”,还是等外之“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理解为等外之“等”,而香港终审法院的解释则为等内之“等”*香港终审法院于1997年回归后不久就临时立法会是否符合基本法的争议案件中,认为这一争议不属于国家行为,因为不在香港基本法对于国家行为的列举范围。。如果按照香港终审法院的解释,则国家行为仅限于基本法所列举的国防和外交两项。从各国的通例看,这一解释的范围过窄。
香港终审法院于2011年6月8日就刚果金和中国中铁(香港)有限公司等上诉人诉美国FGH公司一案下达了初步判决书,其中就该案所涉的香港基本法第13条、第19条有关款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解释请求。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的行为体现了国家主权,是涉及外交的国家行为。决定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不属于特区管理的事务或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项。香港基本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必须遵循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我国实行的国家豁免规则是,我国法院不管辖、实践中也从未处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针对外国国家财产的案件;同时,我国也不接受外国法院对以我国国家为被告或针对我国国家财产的案件享有管辖权。我国的国家豁免立场,体现在我国政府对外正式声明和实践之中,这是一个法律事实,并为国际社会广泛了解。香港原有法律中有关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的规定,如果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的上述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不一致,将与香港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规定相抵触,也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行政区域的地位,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的规定,应作出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或例外,以符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2011年8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就这一解释草案向常委会组成人员所作的说明。。
(六) 审理案件必要性的限制
法院之所以需要附带性地审查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其目的在于裁判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同时为当事人提供救济。因此,法院所审查的特区法律必须是作为所审理案件裁判依据的特区法律,而并不能是与案件无关的特区法律;同时,法院必须认为如果可以对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不进行审查,也能够作出裁判,则也没有审查的必要。换言之,基于审理案件的必要性,才可审查特区法律。如果穷尽特区法律判断即可解决案件,则不对是否符合基本法作出判断*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发生在日本的案例。某人因偷割自卫队的电线而以盗窃罪受到起诉,在审理时被告提出须先审查自卫队是否为违反宪法第9条的“武力”,而构成非法组织。法院认为,即使不作此审查也能够确定是否构成盗窃罪,故未就自卫队是否违宪进行审查。。
另一方面,法院在审查特区法律时,如果既可以作符合基本法的解释,也可以作违反基本法的解释时,基于司法的保守性及对立法机关的尊重,应当采用符合基本法的解释。即法院应当尽可能回避作出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判断。
四、结 语
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既是低于宪法的全国性的基本法律,又是在特别行政区处于最高地位的法律,其既贯彻了“一国”的指导思想,又体现了“两制”的基本精神。依据两个基本法的制度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及特别行政区法院均具有依据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审查权,通过审查,保障基本法的地位和权威,进而保证体现“一国两制”指导思想的基本法的完全贯彻实施,保证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别行政区法院均具有审查权,必然地存在一些共性要求,而又因两者在性质、地位、行使权力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在审查方式、原则、内容等方面存在区别。同时,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审查权为授予权力而非司法权能中所固有权力,在效力上要低于作为授权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此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别行政区法院均具有审查权的背景下,两者之间在行使审查权过程中的衔接、互动方面必然存在诸多需要磨合之处,甚至可能出现冲突、紧张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在基本法审查权实践及理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课题。
骆伟建(2007).论澳门法律制度中的司法审查.汤德宗、王鹏翔.2006两岸四地法律发展——违宪审查与行政诉讼: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筹备处.
ReviewPowerontheBasicLawofHongKongandItsLimits
HuJingu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Basic Law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establish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s basic law.And thus,according to these two Basic Laws,they are at the top of the hierarchy of laws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respectively.In order to ensure such legal status,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vested with the review power to judge whether the existing laws in these two regions as well as the laws enacted by the legislative bodi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s.When it comes to whether the courts in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re empowered to review the existing laws in these two regions as well as the laws enacted by the legislative bodies,it has not been clarified in these two Basic Laws.However,it can still be presumed that the courts are also vested with the review power on the ground of interpretative power of the Basic Law provided by these two Basic Laws.Meanwhile,the legal system in the Hong Kong is characterized by common law,and thus there is no doubt all the courts in this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re vested with review power.Yet,the legal system in the Macao is subjected to civil law,and all courts are vested with review power,which would lead to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ourts as to the compliance of the same law on the basis of the Basic Law.At this point,it should integrate such judgment in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given the legal speciality in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The body with the review power should carry out the review of the laws in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legal text and annex rather than only the preamble of the Basic Laws and Constitution.As far as the courts are concerned,their review on the laws of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unavoidably restricted by the authorized limits regarding their interpretative power on the Basic Laws,and by the required judicial principles as well since courts are judicial branches.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One Country Two System”; review power on the Basic Law; judicial review; article 158 of the Basic Law
10.14086/j.cnki.wujss.2017.06.006
D921.9;D676.58
A
1672-7320(2017)06-0060-11
2017-06-19
■作者地址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特别委托项目(JBF201005)
■责任编辑李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