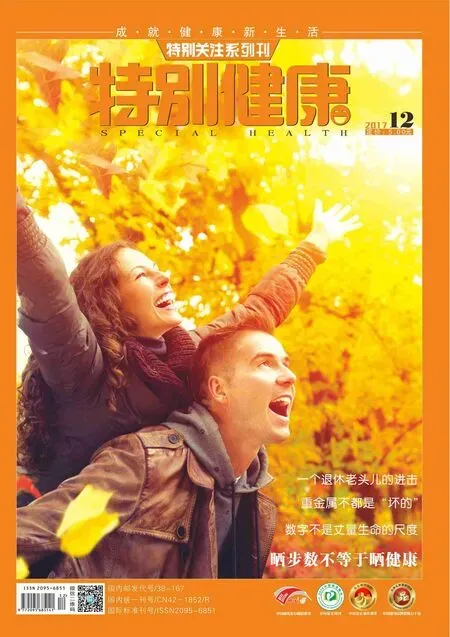分田到户了
◎王向阳

朝也盼暮也盼,终于盼到15岁,我到了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年纪。原以为能给家里挣工分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一年(1982年),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文绉绉的说法,在农民看来就是两个字:“单干”。
喜忧参半要单干
那时我爹常年在外做木工,姆妈只有5分工,家里年年缺粮,不仅要向生产队缴缺粮款,还要缴一笔不菲的公积金。这个沉重的经济压力,压得爷娘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一直想早日参加生产队劳动,虽然刚刚参加劳动的15岁小孩,做一天只有两分半工分,但多少总能为家里多挣一点,少缴一点缺粮款。
面对单干这个沧桑巨变,村民们各怀心思,表情复杂,惋惜者有之,高兴者有之,担忧者有之。
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以脾气暴躁闻名。得知要单干了,他心情郁闷,三天两头喝闷酒。喝醉了,便在家门口破口大骂,骂那些没有劳动力的人家,几十年来全靠他们养活,单干以后,只能喝西北风。他骂东骂西,指桑骂槐,分明是骂我们这样的缺粮户。我和姆妈听了,心里很是郁闷。
单干以后,我家不幸跟这个老队长成了“田邻居”。他一没有文化,二没有技术,只会死做,种的水稻产量还不如我家高。我心中不由产生疑问:在农业集体化阶段,到底是余粮户养活缺粮户,还是缺粮户养活余粮户?在人多田少的乡村,如果没有像我爹这样的能人走家串户去赚钱,然后把部分收入作为缺粮款和公积金上缴生产队,生产队拿什么给余粮户发余粮款?
也有的村民眉飞色舞,喜形于色。有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村民,坐在村口的石板上,喜笑颜开,高谈阔论:“走人民公社几十年了,我在生产队里什么干部也没有当过。如今单干了,种什么、种多少,都由我自己做主,既当队长,又当会计,还当粮食保管员。”
对于单干,我和姆妈一样,喜忧参半,心里没底。喜的是,从此以后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再也不用受人家的闲气;忧的是,我爹常年外出做木工,这辈子基本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光靠我们娘囝几个“半劳力”耕种几亩田地,能行吗?
自力更生忙种田
那一年的春天,过了谷雨节气,就开始插秧了。除了妹妹才念小学二年级无法参加劳动以外,我们全家出动,包括9分工的爹、5分工的姆妈、两分半的哥哥和从来没有参加过生产队劳动的我。姆妈郑重其事,早早到街上买来香烟、老酒和猪肉,请外公、新正伯伯和大哥(大伯伯的大儿子)来帮忙,好生招待,好像家里请手艺人一样。记得姆妈买的香烟是两毛四分钱一包的新安江,价格居于中游,比它贵的当时还有中华、大前门、利群等,比它便宜的有雄狮、大红鹰等。
种田的时候,我发现村里的那些老把式虽然不用塑料绳,照样种得笔直,像模像样,煞是好看。而我不仅速度慢,插的秧苗还东倒西歪,扭来扭去。最讨厌的是,插秧的时候,人要慢慢向后退,眼前留下两行又深又阔的脚印,如果秧苗插在脚印里,就立不牢,只有返工,速度就更慢了。好在对种田地来说,爹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三脚猫,我们几个的水平半斤八两,他对我的要求也特别宽松,慢一点不要紧,干多了就快了;歪一点也不要紧,歪田有歪谷。唯一的要求是牢靠,秧苗一次插牢,不能浮起。
插完秧苗,经过两三个月的田间管理,不知不觉就到了夏天。看着自己田里沉甸甸的稻穗,爷娘心花怒放,脸上洋溢着笑意。夏收季节,家里不再请人,摆脱依赖,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打稻的时候,姆妈和妹妹递稻,我和哥哥脱粒,爹挑谷担,五个人就撑起了以前生产队里几十个人的收割场面。
收割早稻,播种晚稻,全家人用了十来天时间就忙完了。短短半年时间,我家从请人帮忙到自力更生,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丰衣足食大反转
我家五口人,分了三亩多田。其中两亩多种植水稻,包括早稻和晚稻两熟,平均亩产800到1000斤,收了4000斤稻谷。再加上1000斤春小麦,总共5000斤粮食。稻谷和小麦加工成大米和面粉,以七成计算,就是3500斤,人均700斤,家里粮食多得放开肚子也吃不完。而在生产队里,当时每个人每年核定的口粮标准只有360斤。
在种植晚稻的时候,家里特意种了小半亩糯稻,加工成糯米以后,可以做糯米饭,也可以做甜酒酿、年糕、冻米糖、杨梅馃和麻糍,以改善伙食。短短一年时间,我家就从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
除了两亩多水稻,我家还种了一亩棉花。秋高气爽的日子,一个个棉桃里吐出了一朵朵又白又肥的棉花,不仅产量高,出皮率也高。卖给供销社以后,换回了两百多元花花绿绿的钞票,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钞票。
从集体时代的“出工一条龙,收工一阵风”,到个体时代的“半夜三更忙割稻,天早五更去车水”,农民身上沉睡已久的生产积极性得以空前激发。我家从每年向生产队上缴四五十元的缺粮款和公积金,到从农田里收获两百多元的经济作物,来了个大反转,姆妈的心里特别激动,脸上乐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