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
⊙ 文 / 李云雷
乡村医生
⊙ 文 / 李云雷
李云雷:一九七六年出生,山东冠县人,二〇〇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文艺报》。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小说集《父亲与果园》等。曾获二〇〇八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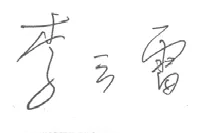
那时候我们村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顺德爷爷,一个是铁腿他爹。顺德爷爷在后街,铁腿他爹在前街。顺德爷爷年龄很大了,胡子白了,走路拄着一根拐杖,佝偻着腰。据说他也没有学过什么医,也不认识字,但他懂得很多偏方秘方,我们村里的人都很信他,什么病到他手里,他这儿看一下,那儿看一下,捏一捏脉,开一个方子,吃几服药就好了。他治跌打损伤最有效了,小孩子崴了脚,脱了臼,痛得龇牙咧嘴,嗷嗷乱叫,赶紧去叫顺德爷爷,他一来,摸摸手,摸摸脚,看准了穴位,手上猛一使劲,咔吧一声,那孩子痛得高叫一声,但很快就不叫了,活动活动手脚,才发现骨头已经复位,一点也不痛了。
我有一次就是这样,那天我爬树,不小心崴了脚,痛得很难忍受,简直像断了一样,晚饭也没有吃,我爹从地里回来,看我痛得不行,就和我姐姐轮流抱着我,跑到了顺德家。顺德爷爷正在吃饭,见我痛得乱叫,他将我接过来,放在长板凳上,一边和我爹说着话,一边捏捏我的脚,突然他手下猛一用力,痛得我啊地大叫一声,这时他已放开了我,到脸盆架那里去洗了手,接着跟我爹继续说话。我忍着剧痛活动一下脚踝,发现脚竟然慢慢就不痛了,等回家的时候,我不仅能走,而且还能跑了,我跑在我爹和姐姐的前面,欢快地回了家。还有一次,我的右脸痄腮,脸肿得像一个紫茄子,鼓鼓的,饭也吃不下,整天只能捂着腮帮子,咝咝地吸气。我娘带我去了顺德家,顺德爷爷给我娘说了一个偏方,将松柏树的叶子嚼碎,敷在右脸上,再将槐树的小树枝掰几枝,和水一起煮鸡蛋,煮好后用这水洗脸,再把鸡蛋吃了。那时候我们很少能吃到鸡蛋,我就这样连吃了几天槐枝水煮的鸡蛋,所以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爬树掰树枝也是我自己去,和平日里偷偷爬树不同,现在爬到树上,掰了树枝,就能吃到鸡蛋,这也让我很兴奋。只是可惜,痄腮很快就好了。
顺德爷爷还懂草药,会画符。有一次我牙痛,到铁腿他爹那里开了药,吃了也不管用,仍然疼痛不止。夜里很晚了,我姐姐带我到了顺德家,顺德爷爷掰开我的嘴,看了看我的牙,从他的药柜里拿出一味草药,让我放在疼痛处咀嚼,嚼了一会儿,果然就不痛了,并且那颗牙至今也没有再痛过,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药。那天晚上,顺德爷爷还拿来一张草纸,用毛笔龙飞凤舞地画了一个神秘的画符,画完后,他让我在上面哈一口气,接着划了一根火柴,将那张画符点燃了,他将草灰和水,糊在了我的腮帮子上,再加上草药的作用,我感觉牙痛一丝丝从牙缝中慢慢溜走了,也敢咀嚼东西了,想想真是奇妙。
我见过顺德爷爷治病,最神奇的一次是治魔怔。说起来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但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不过现在想起来也难以理解。我们院里一个远房姐姐,嫁到了我们村南边的一个村子。她公公年前去世了,转过年来四五月间,她突然得了魔怔;就是她突然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她的口音也变了,粗着嗓子,像是她公公在说话,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骂那个,像是她突然被她公公的鬼魂附了体,说话的口音语气都像是她老公公的。家里人又急又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没有办法,就把她放在板车上,套上一头驴,拉到了顺德家,请顺德爷爷给看病。村里人听说了,都拥到顺德家去看,我们这些小孩很好奇,也跟着去看热闹。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个姐姐被放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躺在席子上,她口中吐着白沫,正在以她老公公的口气破口大骂,骂儿子不孝顺,骂家里人不听话,骂村里多年前欠了他账的一个人,骂哪一年村里的谁偷了他家的羊,等等。围着她看的那些人远远地围成一个圈子,又惊讶,又害怕,又兴奋。她婆婆在边上又哭又号:“老头子,你死了就死了吧,又回来干啥?”她丈夫跪在顺德爷爷面前:“您老给她看看吧,这个家,是没法过了,您看看这是咋回事?”
顺德爷爷走过来,在那个姐姐边上绕了一圈,又掰开她的嘴看看,对她丈夫说:“你爹这是不放心家里,想回来看看,你家里的坟修得不好,前几天下大雨,可能漏水了,你先去修一下坟,我这里送他走。”她丈夫听了,连忙叫上几个人,扛着铁锨骑着车子,往坟地里去了。这边顺德爷爷让人摆了供桌,杀了一只鸡,将鸡血倒在一个碗里,他又画了一张符,在供桌前磕头焚烧了,将草灰也撒在碗里,接着他举着桃木剑,口中念念有词地劝导死去的那个人的鬼魂:“你看看家里,都让你搅乱了,你回来看看,家里都很高兴,可是也不能没完没了,让家里大人孩子都不安生,你的坟漏雨了,他们去给你修了,你就放心走吧,家里啥事都挺好,你别不放心,以后过年过节,家里都会给你烧纸,你就在那边好好过吧,有啥事就托梦,别再回来了……”他这么念叨着,只见那个姐姐嘴里呜呜着,像是那个鬼魂在辩解,突然顺德爷爷又提高了声音,厉声说:“该走的时候你就走吧,要不请出张天师,也够你受的,走吧走吧,快走快走!”说着他嘴里念了一道符,挥动桃木剑,将那碗鸡血泼在了她身上,只见她骨碌翻了个身,一下子清醒了过来。醒来之后,她茫然地看看周围,像从梦中惊醒一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来,顺德爷爷在我们那里名声更大了,村里人有点大病小灾,都到他那里去看,周围三里五村的,也经常慕名而来,很多地方都把他传得神乎其神。
但是对于顺德爷爷,铁腿他爹却不以为然,认为那都是封建迷信。铁腿他爹学的是西医,最初是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在生产队里拿工分,生产队解散以后,他就在我们村西头的马路边,开了一家小药铺。我们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仍习惯到他那里去拿药,他的小药铺门口有一棵大榆树,很好认。村里的小孩却很害怕到那里去,到了那里,不是打针就是吃药,没有什么好事,有的大人骗小孩去代销点买糖,小孩高高兴兴地去了,上了自行车,还没到代销点,遥遥看见那棵大榆树,小孩就哇哇吓哭了。我那时候也是这样,一听说要去铁腿他爹的小药铺,就吓得一溜烟逃跑了。不过那时候我和铁腿却是好朋友,我们读小学时在一个班,放了学之后常在一起玩,他到我家来过,我也到他家去过。从我家到铁腿家,出了我家胡同一直向西,穿过井边那个十字路口,路过我奶奶家继续向西,村西头有一个大坑,我们村里人都叫它大西坑,铁腿家就在大西坑的西岸上。那个大西坑很深,一到夏天下雨,村里的雨水就流到了这里,据说这个坑里曾经淹死过小孩,但是一到夏天,我们一伙小孩仍喜欢到这里来玩水。我们在水里扑腾,打水仗,玩得不亦乐乎,大人看到了,就拧着耳朵将我们拽到岸边。那时候大人都不让我们下水去玩,我们偷偷去坑里游泳,回到家里,大人拿手指在我们的皮肤上一划,如果有一道白印,就证明是下过水了,少不了挨一顿打。
铁腿家建在大西坑的西岸,大门正对着那个大坑,村里很多人都说风水不好,也有人问过顺德爷爷铁腿家的风水,顺德爷爷只是摇摇头,也不说话,也不知道铁腿家后来发生的那些变故,是否真的跟风水有关系。铁腿他爹可能也觉得这房子的风水有问题,就将迎门墙建在了门外,建在大西坑的西岸。我们去他家,从大西坑里爬上去,绕过迎门墙,再穿过一条路,才能进他家的大门。那时候铁腿他爹住在药铺里,偶尔才回家一趟,我去他家里,见到的就只是他娘和他妹妹,很少能够见到铁腿他爹。铁腿他爹那时候才三十多岁,在我们村的庄稼汉之间,显得很白净、清秀,算是一个异类,再加上他当医生,整天穿一身白大褂,干净利落,很显眼。他在家里很少下地干活,他家里干活的就是铁腿他娘和铁腿,只有在农忙的时候,他才脱下白大褂,到地里去忙活几天,等干完重活累活,他就什么都不管了,穿上白大褂,整天待在小药铺里。有人来看病的时候,他就过来看病,没人看病的时候,他就坐在玻璃柜台后面,捧着一本厚厚的医书在读。那时候已经时兴考大学、考中专,我们村里的人都说,铁腿他爹是想考学呢,都觉得他虽然是我们村里的人,但好像不属于我们村。那时候,铁腿他爹当医生,家里的经济条件比一般人家要好,铁腿穿的衣服、吃的东西,在我们小伙伴里是最好的,那时候我们穿衣服都是自己家织了布,找裁缝裁剪了,缝起来做成的,但是铁腿他爹却到城里给他买“成衣”——就是成套的衣裳。那成衣很漂亮,很合身,看上去跟城里人一样,其中有一套白色的西装款式,很洋气,他穿着像一个小医生,我们都觉得铁腿长大以后,会像他爹一样当医生。还有一次,铁腿他爹给他买了一双棕色的小皮鞋,他穿上,显得很神气,那时候我们穿的都是家里做的布鞋,见到铁腿的小皮鞋,亮闪闪的,我们都很羡慕。
铁腿他爹和顺德爷爷都是医生,一个在前街,一个在后街,一个是西医,一个是中医,倒也相安无事,乡里乡亲的,都有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谁也不会说对方不好。但是顺德爷爷在红火过一阵之后,在一次给人拔火罐的时候,将人家的头发烧着了,那人受了惊吓,病情加重,最后竟然死了。不少人都传说,那人是让顺德爷爷给烧死了,这一来,去顺德家看病的人越来越少,去铁腿他爹小药铺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顺德爷爷以前很少闲下来,现在经常搬个躺椅坐在门口晒太阳,看街上人来人往。街上的人问起来,顺德爷爷也对铁腿他爹没有什么抱怨,只是说自己老了,不想再看病了,有时候有人来他这里看病,他还说,去前街小药铺抓点西药吧,见效快。还有一次,他甚至带着小孙子顺德到铁腿他爹的小药铺去抓药,村里人见到了,问他,他很自然地说:“去前街拿点药。”好像他自己不会看病,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那一段时间,铁腿他爹的小药铺更加红火了,村里人来得更多了。有时候铁腿他爹回家吃饭,看病的人甚至找到家里去,铁腿他爹饭也吃不好,洗一洗手,就在家里给人看起病来,虽然很忙活,但他却很高兴,毕竟生意好了,家里的生活也好了,他出来进去,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在我们村里很风光。不过那时候,虽然大人不说,但小孩之间却也明白,顺德爷爷的孙子比我们高一个年级,他跟铁腿的关系就很不好,有一次放学后,还堵住铁腿打了他一顿。铁腿对我们说:“顺德爷爷老了,不会看病了,他倒拿我出气,我就是要穿好的、吃好的,气气他,气死他!”
铁腿他爹的小药铺红火了没有一两年,就出了事。这件事在我们村里有很多说法,引起了长久的涟漪和回响。最根本的还要从小药铺说起。铁腿他爹的小药铺盖在我们村西头,比较偏远。这是两间房子,外间是他看病的地方,摆着柜台和药柜,刷了白灰,很干净,里间是他休息的地方,有时候铁腿他爹晚上也不回家,就住在这里。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村里人发现,不止铁腿他爹住在这里,跟他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年轻女孩。关于这个年轻女孩的身份,我们村里人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她是外村一个来看病的人,时常来这里看病,天长日久,他们就产生了感情。有的说是铁腿他爹在县里参加赤脚医生培训时认识的,他们两个早就有了瓜葛。还有的说是铁腿他爹去哪个乡镇进药的时候,那家铺主的女儿看上了他,一来二去,她就跑出来找他,他们就住在了一起。那个女孩比铁腿他爹小十多岁,那时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岁。一开始她躲在小药铺的里间,几乎从来不出门,我们村里人都没有见过她;后来大约住的时间长了,她开始慢慢走出来,我们村里有人见过她在那棵大榆树下洗头,长长的黑发涂满了泡沫,在阳光下闪烁;再到后来,铁腿他爹在小药铺里也置办了一套锅碗家什,我们村里人经常看到她在药铺后面用铁锅炒菜,炒完菜她就回到里间,几乎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话。
那时候我们村里的风气很保守,这可是石破天惊的一件事,从我们村里人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伤风败俗。但那时候城里的风气已传到了我们乡村,在新的观念中,一个年轻女孩勇于追求自己喜欢的人,为此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她的大胆让人钦佩。至今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铁腿他爹和这个女孩的情感,但他们的同居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铁腿他爹最初还回到家里吃饭,时间长了,连家也不回了,天天待在小药铺里,跟这个女孩在一起。村里人也议论纷纷,对铁腿他爹既好奇,又鄙夷。铁腿家里简直乱了套,他娘也不下地干活了,整天躲在家里哭,蓬头垢面的,两个孩子也没工夫照顾。铁腿呢,铁腿以前穿得比谁都好,现在也是破衣烂衫的,跟我们差不多了。走在街上,还有不少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在我们班里本来学习成绩很好,但不到一个学期,就滑落到了最后几名。他爹也没有时间管他,他妹妹就更不用说了,整天拖着鼻涕在街上玩,也没人管。我们村里人都看不下去了,那时候衍奎大爷已不当我们村的支书了,新支书继春叔找铁腿他爹谈过。他说:“你这是犯罪,你知道吗?这是重婚罪!你赶紧把那个女的弄走,在村里也败坏民风,这算个啥事?你要是想跟那个女的好,就赶紧跟铁腿他娘离婚,离了婚你想干啥就干啥,没人管你。”铁腿他爹哭丧着脸说:“这个不走,那个一说离婚就要上吊,就要喝农药,你说该咋办?”继春叔瞪着眼说:“你狗日的问谁呢?你自己作下的孽,自己想办法处理。”铁腿他爹垂下头,再也说不出话来,他坐在小药铺里,像一个病恹恹的病人,窗外老榆树的叶子哗哗响。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那就是铁腿的娘突然死了。关于她的死因,我们村里人也有很多种说法,一种是她是被铁腿他爹生生气死了,一种是她是喝农药自杀了,还有一种说法更可怕,流传也更广,很多人都说,她其实是被铁腿他爹和那个女孩下药害死了,因为铁腿他爹是医生,懂药,知道什么药能致人死命,下药杀害她并不是没有可能。究竟是哪种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无疑后一种更有戏剧性,也更符合我们村里人想象的惯性。在我们看的那些戏里,那些奸夫淫妇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不就是这样对结发妻子下毒手的吗?事情的真相我们已经不知道了,不知道是谁报了警,这件事也惊动了公安局,但就在公安局下来调查之前,村里人发现,铁腿他爹和那个女孩突然消失了。不知道他们是畏罪潜逃,还是感觉人言可畏,总之他们突然就走了,一夜之间就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公安局的调查也没有什么结果,只能草草结案。在这个过程中,最难受的就是铁腿了,他从家庭和睦富有,一下跌落到了母亡父逃的境地,也从一个爱说爱笑的孩子,突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少年。铁腿他娘出殡那一天,我们村里的很多人都哭了,铁腿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弱小的肩头扛着白色的灵幡,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泣不成声,在街上见到人就扑通跪下磕头,一路上也不知磕了多少,那天正好下着蒙蒙细雨,他满脸都是泪水和雨水,身上湿透了,膝盖上也沾满了泥。我们村里人站在路两边,看着他单薄的身子骨在风雨中颤抖,想到这个孩子的悲惨命运,不禁纷纷摇头叹息,觉得这个孩子命太苦了,太可怜了。我们这些以前跟他一起玩的玩伴,当时并不能理解发生在铁腿身上的变故,但看到他那么小就穿着一身白,费力地扛着灵幡,在泥泞的道路上磕磕绊绊地走,心中也不禁感到万分难过,就连跟他打过架的顺德,也都流下了眼泪。

⊙ 陈 雨·波德莱尔
本期插图作者 / 陈 雨
自由职业画家,一九七五年生于广东省雷州市,二〇〇八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现居北京宋庄。
丧事办完之后,铁腿没有再回到学校,他辍学了。现在他的生活都成了问题,还要照顾他妹妹,家里没有大人,他姥娘家来人把他妹妹接走了,他寄居在他叔叔家生活,很少再回到自己的家里。有一次我和胖墩儿去找他,爬上大西坑,绕过迎门墙,进了他家的大院,发现他家的院子里长满了青草,昔日的欢声笑语早就不见了。
铁腿不再上学,我们跟他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很快我们就从村里的小学毕业,我到直隶村去读五年级,然后到城关去上初中。读初中的时候,我每天上学放学,都会骑车路过铁腿他爹以前开的那家小药铺,门口的那棵老榆树还在,依然茁壮成长着。每次路过那里,我都会想到铁腿、铁腿他爹和那个女孩,以及铁腿他娘的死。有时候夜里骑车到那里,我心里就会非常害怕,总是蹬着车子飞快地骑过去。
这个时候,我听村里人说,铁腿曾到外面去找过他爹,但是要找到他爹并不容易,根本就没有什么线索,只是模模糊糊听什么人说,他爹在哪个地方落下了脚,仍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他们又生了个孩子,当地的人问起来,他们就说是逃计划生育的。那时候“超生游击队”确实存在着,也没有人怀疑他们。但那时候城市里还会查盲流,不欢迎农村人口涌入,所以他们很难在一个地方落脚,他爹只能带着女人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不过好在他会给人看病,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铁腿只能根据这些模模糊糊的传闻,出发去寻找他爹。别人问他,你爹都不要你了,不要这个家了,你还找他做什么?铁腿说,有我爹在,就还是一个家,爹不在,这个家就没了,哪怕有一个后娘,也比啥都没有强啊。人家又问,你恨你爹不,恨那个女人不?铁腿说,我恨他做啥,他再怎么着,也是我爹啊,我找到他,把他接回来,还要给他养老送终;那个女人我也不恨,她跟了我爹就是我娘,我也会好生待她,好生待她生的弟弟妹妹,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好生在一起,多好啊!又有人问,你想你娘不?铁腿却不说话了,眼泪一颗颗滴下来。
铁腿出门去找他爹,出去了很长时间,他以我们县城为中心,不断扩展搜寻的范围,骑自行车、坐汽车、坐火车,在周围的城乡到处转悠,像大海捞针一样,只要看到一家小药铺,他都要上去看看、问问,看他爹是否在那里,问是否有人见过他爹。但是搜寻了很多天,铁腿也没有找到他爹,那次回来,他大病了一场,躺在床上都爬不起来了。有人请来了顺德爷爷,他给铁腿开了十几服中药,也没有要钱,铁腿躺在床上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抽噎。
那次病好了之后,铁腿就不在他叔叔家住了,开始自立门户,他把妹妹从姥娘家接来,把自己家院子里的草拔掉,把积满了灰尘的房子打扫干净,在厨房里烧火做饭。他从小没有做过饭,火也不会烧,第一次烧火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烟雾缭绕,呛得兄妹两人只能从厨房里逃出来,在院子里抱着头哭。后来还是铁腿又回到厨房,忍着烟熏火燎,将那顿饭做完了,两个人吃饭吃得很是凄凉。他们吃饭时又想起了他们的爹娘,不免又哭了一场,不过铁腿劝他妹妹说,没事,有哥哥在,咱还是一个家,慢慢就好了。从此以后,铁腿下地干活,养活自己,养活妹妹。每天他扛着锄头去锄草,施肥,浇水,种地,那些大人干的活儿,现在他一个人扛了起来。我们村里人看到他那么小的年纪,就扛起了一个家,既觉得他可怜,也为他高兴,在铁腿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帮他搭一把手,或者他有什么不会的活计,他们就很热心地教给他,铁腿慢慢学会了庄稼地里的各种活儿。等到农闲的时候,铁腿把他妹妹送到姥娘家或叔叔家,他又一个人踏上了寻找他爹的路程。夏天他从南走到北,冬天他从北走到南,风尘仆仆,一路走,一路问,像个流浪汉一样,四处打探着他爹的消息。但他走一路,问一路,却一直没有他爹的踪影,但铁腿毫不气馁,这次找不到,再隔半年,等收了庄稼,地里没有什么活儿了,他就又踏上了寻找他爹的旅程。
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很少回家。那一年顺德考上了一家医学院,成为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顺德爷爷和顺德全家都很高兴,在村里放了一场电影,村里人纷纷到顺德家里去祝贺,他家还特意杀了一头猪,请村里人喝酒。我们村里人都说,顺德爷爷的医术终于后继有人了,又说顺德从小看他爷爷开方抓药,潜移默化就学会了,上个医学院倒是正合适。顺德考上大学,在我们村里影响很大,我们这些读高中的就更憋了一股劲,想着也要考上大学。那时候我也是这样,学校虽然离家不远,但也是两三周才回家一趟,全力以赴奔在学习上。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正好遇到了铁腿,他拉着一辆地排车迎面走来,我跳下自行车,跟他打招呼,铁腿也停下来跟我说了几句话,我问他去做什么,他说他去城里淘粪,城里公共厕所里的粪肥没人淘,他到那里去淘了粪,厕所干净卫生,他拉回粪来,上到地里,也省了买化肥的钱,真是一举两得。他跟我说话时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怕我觉得他身上臭,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又问他最近又去找他爹了吗,有没有什么消息?他摇了摇头说,还是没有消息,他准备忙完了这一阵,到冬天闲下来,就再出去找。“只要人活着,总能找得着吧。”他这样说。那天匆匆谈了几句,我们就分手了。
考上大学之后,我开始在外地漂泊,很少再见到铁腿。有一次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娘告诉我,铁腿到我家里来,要了我的电话,可能会联系我。我想,不知道他是否要到我这个城市里来找他爹,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他仍然念念不忘,痴心不改,一心想要找到他爹,用我们村里人的话来说,他可真是个犟种!但是我一直也没有接到铁腿的电话,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时候都还没有手机,大学宿舍里也没有电话,每次接电话,都是宿管阿姨在楼道里大声喊,也可能他给我打过电话,可是我错过了。
那时候在我们村里引起轰动的一件事,就是铁腿的妹妹结婚,从铁腿他爹逃走之后,铁腿和他妹妹两个人相依为命,饥一顿饱一顿,我们村里人都是眼看着他们长大的。那时候铁腿自己还没有结婚,但是他妹妹到了年龄,他就张罗着给她办喜事,他说现在父母都不在,他这个当哥哥的就要当爹当娘,把妹妹风风光光地嫁出去。结婚那一天,敲锣打鼓的声音震耳欲聋,铁腿的妹妹痛哭不止,不愿意上轿,她说,哥呀,我走了,谁给你做饭,谁给你做鞋,谁给你做衣裳啊。铁腿也哭了,他说,妹妹你放心,我很快给你娶个嫂子,就有人管了,咱这儿也不像一个家,你到了那边,多听人家的话,别让人家说咱没有爹娘教养,有了啥委屈,你就跟哥说,哥给你出气!迎亲的喇叭呜里哇啦哇啦吹了好半天,铁腿的妹妹才上轿,她一路走,一路放声大哭,我们村里站在两边看热闹的人,也都听得一个个抹眼泪。
铁腿把妹妹的喜事办完,这么多年攒下的家底,也花得差不多了,村里人都说这个孩子真仁义,提起他来就啧啧称赞。现在家里只有铁腿一个人了,他倒更加自由了,想出去多久就出去多久,也不用再牵挂他妹妹了。这个时候,铁腿仍然在寻找他爹,他寻找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现在他不像以前那样匆匆忙忙地寻找了,家里没有了牵挂,他可以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边打工边寻找。他当过建筑队小工,在市场卖过菜,捡过破烂,有时候住在简易工棚里,有时候住在公园的躺椅上,有时候住到过桥洞里,像一个乞丐一样。不过在城市里流浪的时间长了,铁腿渐渐也摸到了门道,后来他别的都不做了,开始专门捡破烂卖。
说起来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谁也没有想到,铁腿在城里捡破烂,竟然捡出了门道,过了没有几年,他在那里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承包某个区域的垃圾处理,开始在城市里创业。那时候,他已经很少回到我们村里来了,他具体是如何创业的,我们村里人并不清楚,但我们村里人都知道,铁腿在城市里发了财,他在那里买了房,买了车,还把他妹妹妹夫也带到了城市,帮他管理公司的事情。铁腿究竟有多少家产,我们村里人也不清楚,但每当我们村里有什么大事,修桥、修路、翻建小学,继春叔找到铁腿,他总是没有二话,就给我们村里捐一大笔钱。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铁腿每次回到我们村里,车到了村口,总是停下来,让司机开车在后面跟着,他一个人步行进村,见到村里人,该叫叔叫叔,该叫大爷叫大爷,递上一根烟,拉呱一会儿,一点也没有架子;不像有的人刚有了两个钱,就张牙舞爪的,谁也不放在眼里。我们村里人都说铁腿这孩子懂事,真是我们村里的骄傲,又说起铁腿他爹,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现在铁腿这么有出息,要是他爹他娘知道了,该有多好啊!
顺德爷爷去世的时候,铁腿特意从外地赶回来,一进门他就扑在灵堂上痛哭失声,谁劝也不听,一直哭到声音沙哑了,没有力气了,众人才把他扶了起来。我们村里人从来没有见到铁腿如此难受过,以前他受苦受累受委屈,都是打落牙齿和泪吞,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流露,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顺德爷爷那么有感情,可能是顺德爷爷救过他的命,也可能是顺德爷爷让他想起了同样做过医生的他爹,让他想起了从前生活的种种难处,他既是在哭顺德爷爷,也是在哭他自己。顺德爷爷的葬礼分外隆重,这么多年,他在我们村给那么多人看过病,家家户户都对他很有感情。送葬的队伍从村里到地里,绵延了好几里地,铁腿穿着一身孝衣,在送葬的队伍中低着头默默地走着。
我最后一次见到铁腿,是前两年春节回家。那年大年初一,我和家里的人出门去拜年。那天,天上飘着小雪,我们在村里四处走,不知怎么就走到了原先的大西坑。现在的大西坑比我们小时候浅了很多,有人在坑底种上了白杨树,已经有碗口那么粗了。从大西坑南边走到西边,我正好在那里遇到铁腿。他家还是原来的样子,并没有翻新。我们两个见了面都很高兴,在大西坑他家迎门墙的边上,抽了一支烟,简单聊了聊。铁腿告诉我,他家这一片,很快就要拆了,大西坑也要填平,我们村里要建设“新农村”,要在这里盖楼。我问他,这么多年了,他还在寻找他爹吗?他说,也还在找,但这么多年没找到,希望也是越来越渺茫了,他感觉到他爹是在有意躲着他,要不这么多年了,不管好坏,总该会有个消息。他又告诉我,我们县里的一家大医院准备卖给私人,他想接手,到时候就以他爹的名字命名。他说他爹只要活着,总得叶落归根,总会有想见他的那一天,等到那时候,我们县城的这家医院的广告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爹的名字,他爹一定会高兴的……
告别铁腿,我向回走,绕到了铁腿他爹以前的小药铺。小药铺早已坍塌了,但是废墟还在,雪花越来越大,飘落在瓦砾堆上,黑白相间,分外醒目。矗立在废墟边上的那棵老榆树也还在,很多年过去了,这棵榆树显得愈加高大、挺拔,冬天的枝条上没有一片树叶,那些树枝在空中随着狂风飞舞。站在这棵树下,我看到了当年自己在这里,铁腿他爹给我包扎的场景,以及看到了铁腿他爹和那个女孩的身影,也看到了铁腿坎坷半生的经历。
我不是铁腿,不能像他一样感受到那么真切的痛楚与欢欣,但是有时候我会想,铁腿也是另一个我,他走了我可能走的另一条路,这条路他走得那么艰辛,那么心酸,但是他终于挺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将来会向哪个方向走,但是那些过往都已经深埋在我们心中,就像眼前纷纷扬扬的大雪,和这棵随风摇摆的老榆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