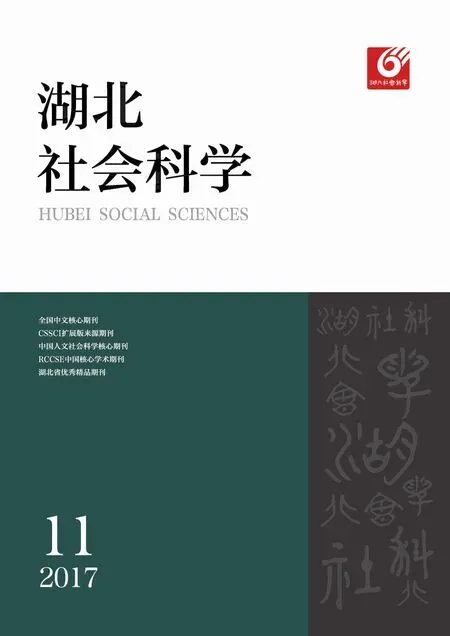“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
颜惠箭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
颜惠箭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在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批判时,学界较少重视这一批判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之间的思想谱系关系。从这一谱系关系的角度去分析,可以发现《启蒙辩证法》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现象的解码时揭示了其拜物教本质,从而彰显为一种“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一方面以资本增值为目的,在生产中消磨了文化的本真内涵及其应有功能,另一方面渗透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挥着同化功能,进一步在消费中扼杀了大众思维的能动性和多样性,从而在总体上遮蔽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秘密并生产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但是这一批判在方法上存在着趋于单一和非辩证的缺陷,需要我们辨明和反思。
《启蒙辩证法》;文化商品拜物教;资本增值;意识形态
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并延续至今日的文化工业开启了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和消费,但是这一形态内部却蕴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统治模式的内在本质,这一本质首先是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完整揭示出来的。不少学者在研究《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批判时,往往没有重视这一批判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之间的思想谱系关系。从这一谱系关系的角度去分析,可以发现,《启蒙辩证法》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现象的解码实际上展现为一种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同构的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
一、从“商品拜物教”批判到“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深入探析和揭示,继承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进行批判的观点和方法。
对于商品拜物教,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1](p89-90)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这一现象之本质的揭示为探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切入点:一方面,从产生的过程来看,商品拜物教与商品生产和交换有着必然的联系,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而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和交换才成为广泛、深刻的活动,具有普遍的社会性;另一方面,从发生作用的机制来看,商品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以商品所表现出的使用价值——物的关系公之于众,从而掩盖了商品所内含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劳动关系。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会进一步衍生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其中资本拜物教乃是商品拜物教完成形态,因而在其本质上是广义的商品拜物教。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拜物教使得资本增值仿佛是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这样资本运作的深度模式——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便在资本主义表面丰富多彩的商品流通领域消失得毫无踪影,资本的秘密、资产阶级统治的秘密被彻底掩盖住了,一般大众便不能透视资本主义的本质因而对社会整体保持无意识失语状态。如此,商品拜物教所发挥的实际上是遮蔽功能,奉行的是深度的顺从逻辑。但是马克思认为,一旦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运作机制中,“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1](p204)这就从根本上向我们展示如何通过商品生产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统治的内在本质。
综上,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启示价值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现象的客观性。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的客观现象,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就一定存在拜物教现象,这是资本主义一种独特的展现方式。第二,现象对本质的遮蔽。商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挥的是一种遮蔽性功用,它掩盖了社会真实的内在关系,隐匿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统治在历史深处的真正秘密。第三,遮蔽逻辑对人的危害性。商品拜物教的遮蔽逻辑之于大众则是“昧心”的,它让大众看不透社会的“真相”。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潜在地把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移植到了对20世纪上半叶所兴起的文化工业的批判中。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新代表之一,霍耐特在反思老师们的思想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称之为“具有拜物教性质的大众文化理论”,[2](p35)这一概括的见地性就在于以“拜物教”为线索勾连了霍阿二氏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谱系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霍阿二氏在思考中具体使用的是“文化工业”,而非霍耐特所言之“大众文化”。
在霍阿二氏看来,虽然20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战争与混乱之苦,但是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余热带来了西方文化表现形态方面的革新。新生的文化表现形态大行其道,家喻户晓的电影、广播、广告、杂志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结晶。这些文化表现形态以新的技术条件为依托,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线上的杰作,这就是“文化工业”。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是在《启蒙辩证法》中首次使用的,它的出现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用‘文化工业’这个表述代替了‘大众文化’这个说法,目的是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这种诠释:大众文化仿佛是从大众自身中自发成长起来的文化,是大众艺术的当代形态”。[3]由此可见,这种新出现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是一种特殊现象,它并非是大众土壤中的自生性文化形态。工业生产的逻辑使得文化工业的产品成为“文化商品”:“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在这个领域里,生产出来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4](p108-109)
应该注意的是,文化商品是“商品”,因而具有商品拜物教的一切普遍性质。其一,从商品拜物教的客观必然性来看,产品只要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必然带有拜物教的性质。在霍阿二氏的语境中,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商品也必然表现出拜物教的性质。其二,从商品拜物教的运演来看,拜物教所发挥的是一种现象对本质遮蔽逻辑。在霍阿二氏的语境中,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生产出的文化商品虽然以新的特殊形式展现于世,但是这种特殊形式只是表象,背后隐藏了文化商品所蕴藏的真实关系——资本增值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三,从商品拜物教的遮蔽逻辑对大众的危害来看,资本主义文化商品因其特性在消费领域对大众实施着“文化欺骗”:文化商品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线上深深地烙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正是借此来控制大众的意识、思想,进而控制社会。因此,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主导的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成其所特有的“文化商品拜物教”。
总的来说,霍阿二氏在继承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方法的基础上,根据资本主义具体境域、现象的转换,发展成一种十分深刻的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本质,即:从生产方面来看,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是商品,文化商品以交换价值和资本增值为目的,在生产中消磨了文化的本真内涵及其应有功能;从消费层面来看,丧失了文化本真内核、趋于同一化的文化商品渗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消费中发挥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化功能,扼杀了大众思维的能动性和多样性,从而谋求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总之,霍阿二氏的批判展现了对资本主义文化商品拜物教“遮蔽”的“解蔽”、“现象表象”的“本质还原”这样一幅历史角斗场的画面。
二、资本增值逻辑与文化商品的生产
商品拜物教之“遮蔽”是物的关系的凸显从而造成了对商品中所蕴含的人的关系的遮蔽,换句话说,实际上是交换过程中使用价值的凸显造成了对生产所决定的价值的遮蔽,使得人们瞩目于使用价值而看不到商品交换在本质上是由价值所决定的。价值的蕴义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是生产中劳动者无差别的劳动“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因资本所主导的大工业机器生产而变得更为社会化和普遍化。在这一语境中,“资本”、“大工业”、“机器”成为“同质性”实际上的主导因素。霍阿二氏借取并发挥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基质,用“同一性”(或统一性)替换了“同质性”的说法,用以指涉资本增值逻辑下文化商品的生产。
在霍阿二氏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商品在表现形式上的百花齐放造成了双重遮蔽:第一,文化商品看似拓展了文化内涵及其形态的自由、全面发展,即对于大众的使用价值的丰富性,实则非然;第二,文化商品看似丰富的使用价值(多样性和异质性)遮蔽了其背后决定性的价值(同一性)。他们指出:“在今天,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够取得一致”。[4](p107)这里的“一致”即是由文化生产这一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条件所决定的“同一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导下的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劳动在均质的基础上得以在量产上大幅度扩张,从而形成一个由普遍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所构造的世界。霍阿二氏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指出文化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生产技术革新的产物,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工业生产的资本增值逻辑。既然如此,分析“文化工业”的着力点就不是文化的艺术属性——使用价值,而是资本增值的运行规律——背后主导价值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因资本主导下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型技术的操持才成为可能。
在传统的文化活动中,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技术操持,文化领域的特有技术与不同文化本身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与文化的表现形态、内容共同熔铸成文化自身独特的内涵和发展规律。文化领域的特有技术本身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动力和载体,从属于文化自身发展的理念。但是霍阿二氏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发展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观:工业技术得到了空前的进步,它打破了原先专门技术(特殊的、具体的)在不同领域的特殊性和内在姻缘,以一种强力的统一性占据了各个领域的主导,甚至直接创造了新的文化艺术形态,从而促使了那个时代文化及其形态的变革。吉尔伯特·西蒙栋在《技术进化的条件》一文中耦合了霍阿二氏在此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客体已获得其在工业水平的一致性……工业技术客体迎合了各种需要,催生并塑造了文明”。[5](p180)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业技术的现实属性是资本的工具。在这一逻辑下,工业技术并不服务于文化本身发展的规律,商品化的文化表现形态已被工业利益的逻各斯原则所操控。“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文化工业的技术……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这一切……是由今天经济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4](p108)因此,“文化—技术—资本”成了文化商品拜物教三位一体的遮蔽—操控模式。在资本和技术的主导、操控下,文化及其成果都必经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的洗礼,“文化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商品。它完全遵循交换规律以至于它不再可以交换;文化被盲目地使用,以至于它再也不能使用了”。[4](p146)以现代艺术为例,霍阿二氏分析道:在当今的艺术作品中,风格和内涵已经被工业泯灭了,成了一种绝对的模仿和工业生产线上的“死物”,文化艺术的生命力在于非同一性的否定和多样性的差异,而工业生产的要求带来的是一种可悲的强制性统一。在霍阿二氏的哲学理念中,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会在风格和内涵上实现一种自我否定——打破工具理性的异在统一性藩篱,这种否定性在于对在世生活世界多样性的敏锐体验,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体验的真实性、具体性和特殊性,而这种经典是不可复制的,因而是独一无二的、非同一性的。但是在文化商品的世界中,资本对“同一性”的迫切寻求必然会导致文化商品走向失败。拙劣的作品常常依赖于一种具有替代性特征的一致性,于是,在文化商品的世界中,一切业已消失,仅仅剩下了统一的无特殊性的形式。当这种工具理性化的形式成为一切的时候,它也就丧失了一切,丧失了前进、生命体验的动力,只剩下一副僵死的工业复制原则,因为在资本增值逻辑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的效率要求是不会让“风格”独特起来的。也就是说,在文化商品的世界中,文化已不再是本初意义上的了,因为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表面现象,文化、艺术本身内在的丰富性和涵养被抛弃了、被沉沦了,只留下了赤裸裸的交换价值。在这里,霍阿二氏让马克思语境中的商品拜物教重新登场,只不过,这一次它羞答答地披上了文化的外衣:文化工业用机器化的技术形式把文化变成了商品,同时也把商品变成了“文化”,在二者之间的复杂转换中,文化商品世界表面的多样性掩饰了文化本身理念的内在多样性的消逝,文化的内涵发生了恶性质变。
总之,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内,文化商品拜物教的遮蔽逻辑表现为:文化工业使得文化与本有技术内在关联的价值合理性转换成了经济活动与工业技术合谋支配文化的外在、强迫式的同一性,从而文化商品在根本上服从于资本增值逻辑。
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文化商品的消费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商品拜物教的进一步批判时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庸俗的经济学理论试图去证明暂时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普遍化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永久合理性,从而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现实秩序(拜物教化的资本主义现实秩序)的意识形态代言人,这是商品拜物教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突出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如何进一步走向大众、统摄大众(即发挥作用的中介性机制),马克思并没有特别指明。而霍阿二氏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从文化商品的消费上去思考这一机制的现实逻辑。他们指出:以资本增值为目的,以技术操作为手段的文化商品同一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隐性暴力式的同化逻辑。
由于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对内部控制工作不够重视,使得单位不能很好地贯彻和落实国家传达的各项政策。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对国家政策中的核心的理念理解不够深入,进而在单位内部控制建设上产生消极的态度,不能很好地发挥内部控制的真正作用。
从消费层面上来看,文化商品拜物教所实行的是一种操控模式,即由文化商品的制造商们(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借助于文化商品所实行的对普通大众和整个社会的全局性意识形态渗透控制,这种控制始于生产,在消费中得以实现,霍阿二氏称之为:文化工业的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下,文化商品“遵循着固定的程式”,[4](p113)表现为一幅资本主义的“创世纪”:其一,文化商品隐匿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设计,使得文化商品内涵的扁平化和操控化;其二,在消费中,变了味的文化商品使得大众的个性与思维的多样性、差异性、特殊性潜能实际上被扼杀在文化商品的操作机制之中了,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资产阶级的观念体系:“对大众意识来说,一切也都是从制造商们的意识中来的”。[4](p112)“文化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文化化”展露出了文化之殇,但是更深刻的影响乃是大众之殇,这正是文化工业更深层面的“同一化”暴力。在这种机制下,大众只是一种被文化商品所塑造的对象,是文化商品拜物教的纯粹客体,而非自己掌握文化主动权的能动主体。文化本来是大众启蒙的土壤和营养,但是现在整个文化商品世界恰恰是一副“慢性毒药”,在里面浸泡得越久,就越丧失人所应有的本质特性和发展潜能。
在霍阿二氏看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微观政治意蕴的隐性强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施加“道德”压力。在一种“文化”垄断的条件下,统治者们总是很自然、很严厉地对大众施加道德压力,这种道德压力是一种在道德名义下对幸福生活的现代定义,即从文化商品消费中体验满足,丰富个人的文化内涵,向着更完善的人格跃升。但实际上,琳琅满目的文化商品早已不再是文化本身的佳作了,它的背后始终潜流着资本增值的欲望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最大限度地榨取大众的“思想剩余价值”。第二,制造无用之需。霍阿二氏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统治的利益,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往往在经济上把大众无情地抛向消费社会,迎合人们对无用之物的需求,让大众在消费中沉沦。这种“文化消费”和“消费文化”不断地制造着感官欲望和虚假需求,因而并不能使大众通向更合理的生存和生活秩序,反而在深层次上剥夺了人们生存和生活的权利。第三,扼杀反思潜能。以文化娱乐消费为例,霍阿二氏指出,“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投入劳动”。[4](p123)从文化娱乐中人们所期望获得的仅仅是一种感性生理或情感的满足,以便延续自己的劳动力,从而使得这种文化活动进一步服从于资本的增殖需要,而非实现和升华人们独特的存在意义。在霍阿二氏看来,资本的背后操手们也不可能让大众进入对存在的真实体验和理性反思的情景中。于是,健全的理性被萎缩和扭曲成了资本增值的片面工具,这种资本化的文化逻辑把大众应有和能有的批判思维紧紧地捆住了。这一逻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发挥有过之而无不及,克里斯·希林在借用霍阿二氏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当代的音乐,他认为:“针对音乐的用途与效应……与阿多诺关注的话题依然大有干系……在许多人看来,音乐或许已不再像柏拉图主张的那样,应当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可以肯定这是一门非常大的生意”。[6](p144)这一“生意”不仅仅关涉到人们的日常消费,从根本上来说关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自身的“塑形”。
上述逻辑导致文化商品世界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悄然无声地内侵到每一个个体的意识、行为和行动之中,个体在选择各种各样的文化商品时不是在选择不同质性的文化范畴、观念和内容,而是在选择同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象化展现。正如鲍曼所言,“这种工业以及这种生活形式相互协调一致,而且相互加强,牢牢地握住我们时代的男男女女可能现实地做出的选择”。[7](p66)这会带来进一步的恶果,即造成一种制造出来的“必然性”,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逻辑的导控之下,即使是有个性、有理性的消费者也难以阻挡这种“必然性”的控制,这是一种无处不在又难以从根本上抗拒的恶性“以太”:“消费者自身的意识被有规则地撕成了两半……他们觉得,如果不同意这种欺骗,就是说,只要他们不再沉迷于那种什么也不是的满足,他们的生活就会变成完全不可忍受的”。[3]
由此,大众在资本主义文化商品世界面前便走向了统治阶级设计好了的集体失声的境地,不可能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而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服从,成为随意的偶然性的无差别的“物”,从而无法生成真正的自我意识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就是文化商品拜物教的制高点,同时也是文化启蒙的现代悲剧。拿破仑曾说:“我发现牧师比我更有权力,因为他统治思想,而我只统治肉体”,[8](p77)而现在文化商品拜物教实现了“拿破仑”与“牧师”的合体。值得注意的是,霍阿二氏在此并没有提出消除文化商品拜物教的方法,实际上是因为在这种颇为悲观的语境下,他们也很难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
四、对“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反思
在总体继承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霍阿二氏对资本主义文化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这种批判在方法上同样也存在着单一和和非辩证的问题,需要我们辨明和反思。
其二,霍阿二氏对大众(主要是工人阶级)作为突围文化商品拜物教统摄之“主体”的不信任使得辩证法丧失了主体维度,成为“非辩证的”,从而导致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没有真正的现实意义,只是一种理论的自我安慰。“文化工业的总体后果之一就是……它使人们成为大众,进而轻视他们”。[3]霍阿二氏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总体控制之下,这种深度的文化商品拜物教是难以撼动的,它无法带来启蒙的正能量,使得大众无法摆脱强加于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只能处于被宰制的地位,而作为主体的大众只是被文化商品所创造出来的虚假“主体”,这是对大众在消极意义上的全称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霍阿二氏放弃了马克思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大众(主要是工人阶级)作为能动主体的信任和希望。对大众自身能力的过于低估,导致他们对打破文化商品拜物教统摄前景的极度悲观,这恰恰又造成了二者理论批判与现实的致命分裂,从而变相地对文化商品拜物教做了妥协,这一妥协在根本上来说依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萨米尔·阿明在对当代种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之有效性进行诊断时深刻指出了这一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已经超出了现有的资产阶级思想框架呢?问题就在这里”。[9](p149)
直至今日,在资本主义世界,霍阿二氏的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思想不断随着历史年轮的滚动而卷起理论创造的热浪,可是资本主义现实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走向更加精微控制的深处。诚然,理论批判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正—启蒙”意义,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启蒙”又如何能够面向大众呢?一般大众又如何能够作为真正的主体被唤醒乃至自我启蒙呢?即便是唤醒之后,又如何能够革除这种资本主义多重权力的统治和压抑呢?在这种条件下,批判如若不能改变其人道主义关怀的现有面貌而真正走向现实并变革现实的话,那么其命运就像不可着陆的荆棘鸟一样,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霍阿二氏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为我们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启—思”价值,但是这种批判理论的弊端同样不可为我们所忽视。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M].童建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3][德]阿多尔诺.再论文化工业[J].王凤才,译.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4][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法]吉尔伯特·西蒙栋.技术进化的条件[A].秦琳,译.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8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6][英]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M].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8][英]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M].顾肃,刘雪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M].丁开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A811
A
1003-8477(2017)11-0005-06
颜惠箭(1990—),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青马英才”厚重人才成长支持计划项目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马克思所有制思想中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研究”(17XNH06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张 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