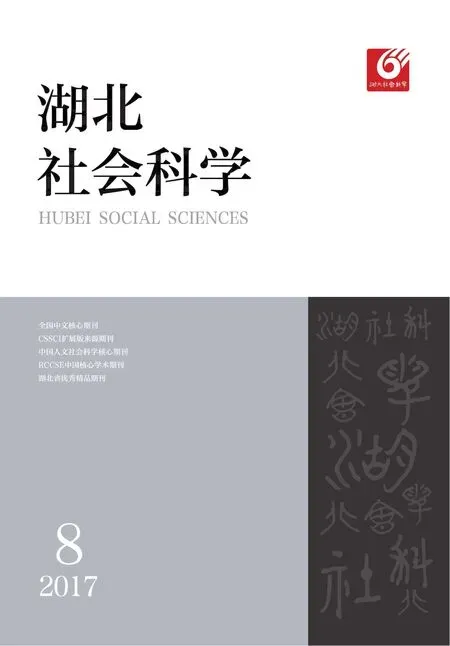文化领导权视阈下中国共产党英模精神的历史建构
孙云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文化领导权视阈下中国共产党英模精神的历史建构
孙云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中国共产党英模精神的建构和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背景下,对民众的动员和教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国家意志的确立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注重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特殊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通过学习苏联英模精神的核心内容,并对中国传统英模观念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彻底改造与继承,成功地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英模伦理体系,直接促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功。因此,必须要正确看待英模精神的历史功绩和现实价值之所在。
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英模精神;历史建构
中国共产党英模精神的建构和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背景下,对民众的动员和教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国家意志的确立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英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革命和建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精神法宝。那么,这一法宝是怎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构起来,又如何引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的。有鉴于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葛兰西对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重要性的论述出发,将其放置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长时段内,重点考察中国共产党英模精神的历史来源、建构过程及其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至关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重要性的分析和相关论述,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正式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以来,便对其进行了科学地分析和批判。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1](p72)因此,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p52)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唯有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基石,“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p214)才能取得革命的真正成功。列宁也特别重视无产阶级对思想领导权的掌控,他说:“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4](p321)“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5](p111)因而,通过外部灌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培育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必不可少的途径和教育方式。“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6](p37)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和组织者,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也在总结多年革命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集中阐发了他的核心理论,即“文化领导权”理论。①英文名称为“cultural hegemony”,又译为“文化霸权”,但笔者认为用“文化领导权”一词较少歧义。在葛兰西看来,西方的无产阶级在革命条件如此成熟的条件下,却没有像马克思判断的那样取得革命的胜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通过“文化领导权”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控制。而无产阶级要革命成功并最终实现政治目标,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新文化”,争夺并获得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他说:“创造一种新文化,……意味着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可以说是这些真理的‘社会化’,甚至使它们成为重大活动的基础,成为一个共同使命、智力与道德秩序的要素。”[7](p235)针对马克思只注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研究,葛兰西指出了其缺失,并特别强调“新文化”对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和维持是何等的重要。他认为,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和持久统治,政治的强制力与文化领导权这两个因素必不可少。而要拥有后者,就必须通过诸如政治教化,借助一切大众传媒等手段向民众宣传,制造一种“集体意识”,使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处于领导地位,并让广大的民众接受他们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他说:“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7](p38)
为了实现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手段对社会精神生活达到真正控制的目的,即葛兰西所说的“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他提出了与“政治社会”不同的“市民社会”概念,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号召他们打好“阵地战”。即要注意开展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成为统治者之前,首先做领导者。葛兰西认为,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共同组成的。在政治社会里,“强制”是一种“硬权力”,这种利用一系列专政工具,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对人民群众进行统治的做法,常常借助暴力。但在市民社会里,就应该通过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取得被统治阶级、被领导者们的“同意”。政治社会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要以市民社会的“同意”为根基。换言之,统治阶级不仅要依靠暴力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而且还要行使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研究葛兰西的学者佛朗科·里沃尔西也说,在葛兰西的理论体系里,“阶级冲突的真正战场不在别处,而在于是否有能力提出一种独立的、广为传播的世界观。而这正是‘领导权’所涉及的领域,在这里,所谓领导权就是阐发和传播具有聚合力的那样一种思想的能力,实际上就是比自己历史性的‘阶级’敌人更广、更好地传播自己思想的能力。”[8](p113)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秉承了马克思主义重视和重构意识形态的革命传统。马克思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p293)同时,他又宣称:“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说,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p53)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发展过程中,忠实地实践了这一指导原则。同时,在重构和宣传新的意识形态时,正如葛兰西所言,它尤其重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统摄。这既跟共产主义的政治文化密切相连,又和中国社会长期重道德的旧有传统有关,更与经受了“五四”大潮浸润,相信“思想文化革命”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党的核心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密不可分。新的意
二、中国共产党英模精神的历史建构
所谓英模,即是英雄和模范的简称。英雄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中,是指那些智谋、才能、勇力过人的人。汉代已大范围运用了这一概念,汉末三国时甚至出现了专门论述英雄的文章,有王粲的《英雄记》和刘劭的《人物志·英雄》等。模范,是近代以来运用较多的词语,指称那些可以成为效仿和学习的对象。将英雄和模范合并起来使用,则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主要出现在革命话语体系里,与旧概念相较,这一新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对传统英模范畴扬弃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英模伦理体系。概括地讲,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苏联英模伦理体系基本内核的影响: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
1917年10月,列宁在俄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计,这个曾经作为“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的国家,开始了向未来社会的过渡。而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就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建设蓝图的远景规划。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内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理所当然地成为苏俄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指导思想。这一意识形态,为当时的苏俄人民描绘了一幅强调实质性平等的理想图景,同时也为现有的政权提供了“来日合法性”。①所谓“来日合法性”,是指统治者在未来可以给社会带来什么。这一概念最初来自S·P·亨廷顿(美)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77页。郝宇青对此做了专门解释和说明,详细参见郝宇青:《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9页。意识形态的选择对于苏联整个国家的发展影响极大。卢卡奇说:“意识形态在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中所起的作用”,是“带决定性”的。[9](p349)1919年,列宁针对新生事物——“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通过连续撰文和演讲予以表彰,称赞它是“伟大的创举”,并将它看成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10](p17)他还专门号召全苏俄行动起来,向模范们学习,积极开展这一运动。列宁表扬工人们的这种英雄主义行动,“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10](p1)他说“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以便从这个伟大创举中得出一切由它产生的极重要的实际教训。”[10](p20)列宁甚至认为这种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的东西”,他说:“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10](p91)不难看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所倡导的革命新伦理,一言以蔽之,即是为国家为集体无私奉献和勇于牺牲自身一切利益的政治伦理。
按照马克思、列宁等人对新社会制度下无产阶级新政治人格及其价值观的相关理论论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着力铸炼这一理想人格,以期改造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新人”呢?根据列宁与斯大林等人的论述,概括而言,符合苏联革命和建设所需“新人”的标准大致有三个方面:阶级出身好,具有极强的阶级意识和高度的警惕性,随时准备开展阶级斗争;大公无私,勇于自我奉献和牺牲,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永远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不折不挠的革命品质,并始终相信党和政府,洋溢着识形态的建构和宣传,从革命的早期就已经得到足够重视,无论是具体革命实践中喊出的“劳工神圣”口号,还是左翼文化的广泛传播,其目的都是力图构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并通过知识分子的“阵地战”和宣传工具,从“文化领导权”上占据制高点。而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建立起来的新政治文化,则更加强调新革命价值观和伦理观的确立和宣传,英模精神就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和代表性理念之一。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学习苏联英模精神的核心内容,并对中国传统英模观念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彻底改造和继承的结果,不仅融入了时代元素和民族特色,更是对传统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扬弃。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苏联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着力形塑的就是这样的“新人”,这个新政治人格对民众影响很大。文学人物“保尔·柯察金”及其创作者本身,便是这一政治人格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者。源自于奥斯特洛夫斯基自传性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这一英雄人物,他强烈的阶级观和对敌斗争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对党无比的热爱和忠诚以及以全世界被压迫者获得解放为己任的共产主义理想,是苏联表彰和褒扬的英雄人格,也是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着力介绍和宣传,借以塑造自己国家新型政治人格的蓝本。这一标准革命者政治人格标本的诞生,和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的经历紧密相连,在他短暂的32年人生历程中,就有8年战斗生涯和10年与疾病抗争的病榻经历。奥氏是一个意志极为坚强的革命者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忠实的追随者,不仅体现在他前期的战斗生涯中,更体现在他与病魔抗争的后半生。“当一个外国记者问他,如果没有共产主义,他是否能生存和创作的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简短回答说:决不能。”[11](p241-242)
苏联的英模伦理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生政权影响甚大。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各工厂、机关学习苏联,实行礼拜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属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效仿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在边区工业领域开展了“赵占魁运动”。时任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委员的朱宝庭,在职工大会上演讲时就明确指出,“苏联有个斯塔哈洛夫,我们今天就有个赵占魁,苏联有斯塔哈诺夫运动,我们也要来个赵占魁运动。”[12]新中国成立后学习和开展“斯达汉洛夫运动”,更是轰轰烈烈。1956年,毛泽东提议说:“搞一个斯达汉诺夫式的运动”,全国职工由此开展了“当先进生产者、创先进班组”的大规模群众性劳动竞赛运动。[13]
除了表彰的方式学习苏联外,新中国在苏联英模文学的译介、宣传和学习方面更是不遗余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该书刚开始在苏联印行时,就有人把它介绍到中国,供当时的左翼青年学习和阅读。这本书1935年在莫斯科完整出版后,1937年,便有了段洛夫、陈非璜根据1936年的日译本转译而成,并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其后,各种版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国内开始热销。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版本则要属梅益的翻译本。该翻译本1942年初版5000多册,销路极好,此后再版,并被大连中苏友好协会和解放区的新华书店连续刊印,读者甚众。新中国成立后,其影响更加广泛,根据出版界的统计,在1949年至1966年间销量最大的文艺小说中,除了杨沫的《青春之歌》等17部小说外,其中唯一的译作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4](p37-38)另外,苏联的英模文学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就让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倍感亲切。该作品以革命行动的风暴,鼓舞着当时正处在极端险恶和艰难环境中的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他们常常把自己的行动比作“铁流”。
其二,在对中国传统英模观念进行改造和继承的基础上,使之更加具有中国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礼乐文明为基础的,尤其注重个人道德的内省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儒家经典典籍《礼记》中概括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之道,一直是中国典范政治的经典阐释。它作为帝国时期的统治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他们或者无比热爱和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危难之时总能挺身而出,或者像孟子倡导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修炼自己的品行,时刻准备着担当“大任”。这种对个人、家国和社会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和内核,它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人生座右铭。
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儒家理想政治人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全面彻底地改造,尤其注重将传统的英烈观念与革命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价值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刘少奇在论述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专门指出,共产党人要像孔子学习,完成自己的个人道德修养过程。①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出自《论语·为政》。毛泽东继承了儒家“反躬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特别强调革命者和“新人”的“内省”,要求大家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在他看来,英模具有的品质就应该像白求恩那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5](p660)但是,毕竟中国传统的英烈观念是植根于封建社会这块沃土的,它以维护封建统治和忠君为目的,有其落后的一面。鉴于此,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有目的性开始对其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944年,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就撰文对新旧英雄主义做了本质的区分。他说,旧的英雄主义是“为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而新的英雄主义,是“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主要的表现如下:“革命的英雄主义是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先革命之忧而忧,后革命之乐而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不是斤斤于作个人打算的;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革命是为群众的事业,又是群众自己的事业,而革命的英雄主义必然是群众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群众的利益;一是相信群众力量、集体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的力量只是这个伟大力量中的‘沧海一粟’。新的英雄和英雄事业是产生于广大群众的共同行动、共同斗争中,为群众所赏识,为群众所称颂,而不是自封的高高站在群众头上的。新的英雄们也知道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不轻视较自己稍微落后的人,不嫉妒较自己更为前进的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真正体现‘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就是新英雄主义和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严格区别。”[16](p115,122)与朱德对新英雄主义的解释相较,毛泽东则更加注重从哲学层面解释这种英雄伦理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他借张思德的追悼大会表达得很清楚:“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17](p1004)在毛泽东看来,英模伦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人民服务”。
由此可见,新英模伦理与旧的英雄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讲,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旧的英雄主义,不管装成怎样神圣的面孔,拆穿了说总不外是个人主义的极致而已。这种英雄主义一切以个人为出发点,为了个人的利益、荣誉和地位有时甚至不惜以千千万万的群众为牺牲品。历史上的许多所谓英雄不是从群众的血泊中爬起来,就是把群众当泥土踏在脚底下。”[18](p204)而新的英模伦理认为,一切个人的智慧和能力终是有限制的,只有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语)因此,任何“伟大的个人至多也只是一只伟大的螺丝钉。离开了群众的机器整体,就只能成为‘伟大的’废铁(严格地说,只怕连废铁还够不上,因为废铁也还可以有用,至少可以无害)。”[18](p205)他们不但一切为着群众,并且一切经过群众,他们自身也永远是群众的一员,永远与群众在一起生活,一起斗争。群众之所以称他们为英雄,只是因为他们在生活和斗争中竭尽了最大的努力,提供了最多的贡献。而对于他们自己在精神物质的享受和个人的名誉地位等方面,英模们总是处之淡然。“新的英雄所具有的却是诚恳的严肃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的提高自己,也为着牺牲自己,为着使自己能对群众作更好的服役。新的英雄随时都准备着赴汤蹈火。”[18](p207)
延安时期洋溢着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新英模伦理的产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影响甚大。经过“延安整风”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成为“文化领导权”争夺中守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忠诚勇士。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创作和宣传了大量有关英模精神的作品,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民众的精神教育和新意识形态的确立。譬如,当时以劳动英雄吴满有、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等人为榜样开展的“文化下乡”运动,实质上就是一次全方位对民众进行英模精神启蒙和培育的运动。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中国人百分之九十是农民,要在文化上唤醒他们,中国才能得救,否则一辈子也救不了国。”只有文化下乡,“文化才能真正到百分之九十的同胞中去,这样才是地道十足的大众文化。革命的文化真正大众化了,革命才有希望真正成功。”因此,“革命的文化人,有责任来给他们以思想上政治上和技巧上很好的新食粮。”[19]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将英模精神发扬光大。葛兰西说:“从一个从属阶级真正独立并取得统治地位的那一刻起,随着它要求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也就具体地产生了这样的需要: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和道德秩序,即一种新型的社会,因此也就需要整合出最普遍的概念、最精良最明确无误的意识形态武器。”[20]恩格斯也指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21](p410)新中国建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英模表彰活动,正是对该理论最好的说明。无论是前十七年间国家在各行各业树立的新榜样,抑或是“文革”中产生的英模典型,还是改革开放后大量涌现的新英模,他们本质上都是新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与体现者,也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者和捍卫者,更是新社会新人得到极大发展的集中呈现者。
三、结语
必须要指出的是,基于共产主义政治文化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由此决定了它意识形态中的新英模具有先天的理想化特点。马克思早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中就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22](p459)这种理想化和浪漫主义色彩甚浓的革命新英模理念,在中国共产党具体的革命实践中,由于革命的特殊需要,政治环境的羁绊,加之革命宣传的独特性,难免有时会出现拔高或“高大全”的宣传效应。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圣人人格”和理想人格特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政治教化和制度化的旌表活动影响下,使得广大民众更容易接纳这一特点。因此,部分英模的拔高宣传,有时成为事实上的不可避免,这种瑕不掩瑜的革命宣传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建立,从根本上促成了革命的成功和新生政治秩序的建立,其功绩巨大。但恰恰在这点上,却某种程度地给了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夸大英模宣传中的部分失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谈不上用辩证的、发展的、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英模们巨大的历史功绩和英模精神价值之所在。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列宁.列宁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6]列宁.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7][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0]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苏]拉·波·奥斯特洛夫斯卡雅.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妻子眼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M].李一柯,译.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
[12]农具工厂奖励模范工人赵占魁,各机关与群众纷送礼品[N].解放日报,1942-09-29(2).
[13]姜天明.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及其经验与教训[J].辽宁大学学报,1991(2).
[14]余敏玲.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J].新史学(台湾),2001,(12)4.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朱德.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姜振昌.野百合花——四十年代延安解放区杂文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19]陆定一.文化下乡——读“向吴满有看齐”有感[N].解放日报,1943-02-10.
[20][意]葛兰西.现代君主论[M].陈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6.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张 豫
D64
A
1003-8477(2017)08-0028-06
孙云(1976—),男,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
国家社科基金“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下的英模塑造研究”(13CZZ01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4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英模表彰制度的历史考察与创新研究”(2013M54163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