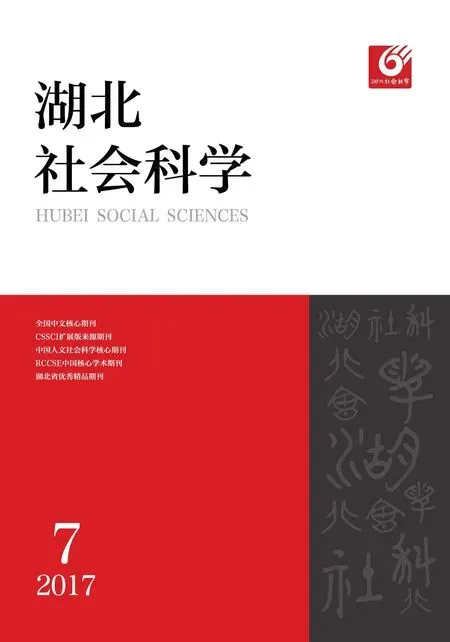“九谛九解”之争新探
——对晚明一桩学术公案的重新考察
田探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1331)
“九谛九解”之争新探
——对晚明一桩学术公案的重新考察
田探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1331)
晚明之时,围绕着心学中“无善无恶”的命题,许孚远与周汝登进行了一场反复持续的争论,史称“九谛九解”之辩。论辩围绕性体、工夫、教化三方面展开。许孚远批评“无善无恶”说不合圣人之教,周汝登则坚持心学的这一核心命题,对许孚远的批评逐一反驳。他们的争论显示出一个共同目标,就是都想用自己的体系来统一性、道、教三者,担当儒教大命,然而他们都不成功。
九谛九解;性;道;教
自王阳明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命题后,儒者们对心体善恶问题聚讼不已。1592年春夏之交,周汝登与许孚远在南京围绕着“无善无恶”的一系列辩论将此问题的争论推向了高峰。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其中,以蔡仁厚先生的《周海门“九谛九解”之辩的疏解》一文影响最大。蔡先生从本体与工夫的角度详细疏解了两人的争论,他认为,周、许二人的观点并非势成水火,而是各有所重,亦各有所失。周汝登所言为虚层,作用层;许孚远所言为实层,客观层。周汝登之失在于“以为凡言有者,即是工夫层上的有迹之有,而不知对方所谓有,乃自实有层上而言之。”[1](p245)许孚远之失在于未能契入阳明“四句教”及龙溪“四无”思想的理路,“以为凡言无者,即是无其实有层上之善,将对方自工夫上之无迹而言之无,误认为实有层上之无,故一味‘执有’而‘非无’”。[1](p245)言下之意,许孚远与周汝登对性体之善的理解并无本质的不同,他们的争论只是心学内部的各执一面而已。乃至有人认为许孚远只是个“王学修正者”。[2]
笔者认为,蔡先生将许、周二人的学术论争视为双方互不理解,是把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简单化了。许孚远的诘难集中在性体、工夫、教化三个层面,而周汝登也在这三个层面逐一反驳。“九谛九解”的问题域并非只在“无善无恶”,而是涉及到了儒学中的性、道、教三个核心问题。可以说,“九谛九解”就是以“无善无恶”为核心而展开的关于何者可以承担教化,何者为儒学正统的激烈交锋,实为理学与心学之争在晚明的正面交锋。
一、良知之有善与无善之争
王阳明提出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命题,经王畿而至周汝登,更显光大,但也更受批评。“无善无恶”之说也就成为许、周二人此次争论的焦点。蔡仁厚先生在疏解“九谛九解”时指出,“所谓‘无善无恶’,意在遮蔽善恶相对待的对待相,以指出这潜隐自存的本体不落于善恶对立之境,以凸显其超越性、尊严性、纯善性。纯善,不是与恶相对的善,而是善本身。”[1](p242)而且,“善、恶皆是名言,一用名言指述,便已限定了它,而使它成为相对的。”[1](p243)也就是说,语言无法述说良知,只有以“无”来显示其无对待的超越性。因此,蔡仁厚判定周汝登的“无善”实际是说性体在形下层面的自然流行,毫无造作,但他并不否定性体的至善之实。而许孚远所说的“有善”是强调性体至善之实,不能以“无”名之。
的确,周汝登之“无善”并不否认性体之善。周汝登在“解四”中也以“人性本善者,至善也”,[3](p432)明示“无善无恶”说与告子性无善恶说有本质不同。可见,他并不否认人性之善,但问题在于,蔡仁厚先生对实有层之善本身并没有清晰的界定,他只是依靠否定性的表述方法来反显良知之至善。这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因为,从经验层面的善、恶现象如何能必然地推论出其上有至善之体呢?如果断言有一个不落于经验的绝对善,则只能视其为宗教性的信条。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正面地解析“无善无恶”说,来揭示其真实的理论内涵。
其实,我们从他关于理气论述中可以获得启示。他说:“理、气虽有二名,总之一心。心不识不知处,便是理;才动念虑,起知、识,便是气。”[3](p452)心体可以分为理和气两个方面,其中,“不识不知”处是理,而“起知识”处便是气。换言之,只要心体进行是非判断活动,则其中必然有气的运行。然而,周汝登指出:“心虽不离见在知觉,而未可便以知觉当之”[4](p169)心体判断是非的能力是“不杂气质”、“不落知见”,是先天所有的。它是理,也是性,任何对此能力的“知”和“识”必然使气掺杂于理中,故而只能以“不识不知”言之。这也是周汝登以“知而无知,无知而知”来描述良知的原因所在。
我们由此可知,周汝登所指的“良知”实则是一种道德判断的能力,而不是具体事物的对错。当周汝登说“不虑者为良,有善而虑则不良”[3](p434)时,正表明了“良知”并不是作为道德判断之结果的“善”。思虑所知之善不是真善,而是“妄作善见”。如果求善于思辨的构造,那么一定会走向伪善。故此,真正的善是生命能够进行判断的本能,它为具体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周汝登称“仁本于知,知以成仁。”[3](p443)仁爱的实践只有奠基于生命的这种本能才有可能实现,而这种本能又是在具体的仁爱行为中开显出来的,具体说来,日用伦常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这种能力展开的真正场所。
实际上,良知的这种道德判断的本能,正是人生而具有的能好、能恶之性。周汝登说:“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无恶,岂更有善耶?”[3](p432)赤子之心尚未被外物浸染,因此保有了人最原初的好、恶性能,如“好好色,恶恶臭”之类。对于好、恶之性来讲,最重要的是涵养,让它如其所是地展现出来。周汝登以“无意”解释《大学》之“诚意”正说明,任何对良知的知性构造都会干扰好、恶之性的自然展露。而“无善无恶”说正是为了返回良知好恶的本真性。
然而,许孚远未能理解“无善无恶”说中的至善概念,也没有领会周汝登主张“无善无恶”的深意。虽然他也认为善不可有意而为,至善是“不杂气质,不落知见”,[3](p431)超越于经验的,但他所意会的善只是超越于经验之上的“物”,而不是天赋予生命的原始的好恶能力。在周汝登看来,许孚远所谓的至善来源于人为的认定,是思虑的结果。所以,当许孚远说“宇宙之内,中正者为善,偏颇者为恶,如冰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损其间”时,周汝登驳其为“曰中正、曰偏颇,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见”,[3](p430)指责其良知说依然杂于气质,落于知见。在周汝登看来,若将良知“知是知非”的能力理解为实体化的一物,则难免“以人作天,认欲作理”,[3](p435)褫夺其虚灵不昧、感应万物的本性。故而,周汝登在“解三”中诘问许孚远:“太虚之心与未发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皆以为更有一物而不与太虚同体,无感乎?”[3](p431)
综上所论,周汝登与许孚远虽然都认为性体至善,但他们对良知之善的理解却截然不同。周汝登以“无善无恶”言说善体是为了强调良知之能的非道德规定性。“无”的作用就在于消解对“良知”的某种特定规定性。许孚远未能理解“无”的作用,他所理解的良知就是一种实体化的、现成的物体。
二、道德实践工夫之争
两人对良知的异见导致了在道德实践上的工夫论的不同。许孚远认为,“人性本善,自蔽于气质,陷于物欲,而后有不善。然而已善者,原未尝泯灭。故圣人多方训迪,使反其性之初而已。”[3](p431)而周汝登俱以“无”指认心、意、知、物。若以周汝登所说,“则格致诚正工夫,俱无下手处矣。岂大学之教……不待学而能者欤?”[3](p431-432)复归性体的途径虽各不相同,但都需要具体的道德实践,许孚远担心,若以“四无”为宗旨,会使艰苦的道德实践堕落为疏略狂荡之学,陷入不待学而能的妄想,而这正是晚明一批儒者共同的担忧。
刘宗周曾将王学末流的弊端归为“情识而肆”,“玄虚而荡”两类。前者是指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之流,后者就是顺龙溪“四无”一脉而趋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评介周汝登时指出:“先生之无善无恶,即释氏之所谓空也。”[5](p854)可见,无善无恶之说确被时人指认为禅学。原因有两点:其一是认为它违背了性善说的道统,背离了儒学根本;其二是容易使修养工夫流于空疏。也正因此,许孚远在“谛六”中指出:“登高者不辞步履之难,涉川者必假舟楫之利,志道者必竭修为之力……其所谓克己复礼,闲邪存诚,洗心藏密,以至于惩忿窒欲,改过迁善之训,昭昭洋洋,不一而足也。而今皆以为不足取法,直欲顿悟无善之宗,立跻圣神之地……在高明循谨之士,着此一见,犹恐其涉于疏略而不情,而况天资鲁钝,根器浅薄者。”[3](p433)他担心,致良知的工夫若完全收摄于内心的顿悟,则必然堕入神秘主义的体验,从而忽略了现实层面的道德实践工夫。
许孚远对行道的艰难性有深刻的认识,他的诘难也的确切中时弊。然而,以此来指认周汝登“无善无恶”说不重修为,却未能契入其思想的要义。周汝登在《祁生壁语序》中说:“今天下学有二病,其一谈玄妙而忽行持;其一执涂辙而昧著察。谈玄妙而忽行持,则如人自厌户庭而梦想瀛岛,尽是悬驰。执涂辙而昧著察,则如生盲不见日月而舞蹈康庄,终成履错。盖自两者之见分则转相非而相矫而学,病矣。解之者曰:悟与修不可偏废也。悟必兼修,修必兼悟。夫使悟必兼修,则是修外有悟。修外之悟可云悟乎?是所谓悬驰而已矣。使修必兼悟,则是悟外有修,悟外之修可云修乎?是所谓履错而已矣。故真悟不必言修,真修不必言悟。彼为悟修之说者,方便之辞,而执以为真,则亦子莫之见耳。”[3](p546-547)
根据材料,周汝登并没有忽视现实的行持工夫,只是提出修持与顿悟皆不可偏。若将顿悟与渐修截然二分,其结果便是学者各执一词,相互攻讦。所以,真正的修持一定包含对良知的顿悟,而真正的顿悟也必然以现实层面的道德实践为题中应有之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学”的论述中发现。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释“学”为“效”,对此,周汝登指出:“《白虎通》曰:学者,觉也。觉悟所未知也。知学是觉,则知时习是常觉,而《集注》学之为言效也,岂不自悖?”[6](p280-281)周汝登对觉的理解是很独特的,他认为学无间歇,故而人生无处不在学,无处不在觉。他说:“子何往而不觉乎?觉寒、觉暑、觉痛、觉痒,以至于夜寐、沉寂,觉未尝少。岂待持之、使之而后觉?焉往非觉,则焉往非学矣。”曰:“此觉则人人同之矣。何以书学不学?”曰:“虽同,而不觉此觉,日用不知也。求觉此觉,明明德也。未觉,求觉;既觉,则觉之而已。觉则无觉,而况于觉?觉无觉之觉,方可为觉,故曰,始终惟觉耳。[3](p532-533)
“何往而不觉”意味着“觉”是人生最普遍的现象。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学而能的疑问。周汝登的回答表明,学和觉的含义可以分为两层:其一是感知外物的能力,凡是经验性的感知都称为觉,如对寒、暑、痛、痒的感知;其二是自我觉察,意识到自身具有感通外物的能力。而这两种能力都是良知的运作方式,所以,学和觉就是良知自身能力运作的另一种表达。其中,感通外物的能力就是良知通过好、恶之性对万物的统摄,而自我意识则是透悟本心生而具有此好恶之性,正是有此能好、能恶之性,良知乃能通达万物。然而,百姓任由声色货利牵引,本心失察,错误地认为自己没有善性,而实际上,好好、恶恶之性无法抹除,良知通达外物的能力并未缺失,只不过日用而不知而已。因此称为“无觉之觉”。鉴于这种情况,周汝登特意强调了“觉”的自向性,他说:“学问头脑只在信得自己,自己一毫无所亏欠,不必更求帮补。信不及者,向外驰求,愈求愈远,圣学之所以失其宗……曰莫不在己,曰不在外也,曰反身,曰自得,语语归根,是入门第一义谛。”[3](p516)
学问的根本不是无休止地获取外界知识,或对外部世界无穷尽的好奇心,而在于确立对自己内心道德的信心。进言之,真正的学问必定包含主体对自身内蕴道德的理解。无论我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程度和层次达到何种高度,若缺失了对本心的检查,则真学问不明。周汝登指出,只有“觉照常存”才是修养工夫的本真途径。他说:“有志于学者,但当信此一心,力自反求,随事随时,察识磨练,遇声色货利,莫随之而去,伦理上率践,性情上调理”,[3](p443)“但妄起便觉,忘了又提,不可纵容,亦不必追悔,绵绵密密,竭力做去。”[3](p603)在此途径中,道德实践是“随事随时”而展开的,换言之,真正的善一定是良知的好、恶之性在具体情境中的当下显现,每次善的显现都是良知的当下运用。因此,明悟良知并不意味着恶永远被祛除,更谈不上道德实践的完满。因此,道德实践的工夫依旧保留在周汝登的修养论中。他曾告诫陶石梁:“领略肤浅者,境缘上容易打失。此真膏盲之剂,谓朴实做去,不作过头语,犹是契紧之方。生每每与证修诸子言,皆今从家庭日用上履践,从声色货利上勘磨,若于此打不过,于此踏不实,更论何学。”[3](p600)
从这段文献看来,许孚远对周汝登工夫论中“直欲顿悟无善之宗,立跻圣神之地”的指责就不攻自破了。而蔡仁厚关于“海门更漠视为学之常义、世教之常法……未免忽视对治实践之功,而有荡越之病”的判定是有误的。我们看到,日常朴实的道德实践是周汝登悟、修之说的必然指向。那种期待回归善体的道德实践,在周汝登看来,只是以自我立名之善为善,他们“皆世所谓贤人君子者,不知本自无善,妄作善见,舍彼去此,拈一放一,谓诚意则意实不能诚,谓正心而心实不能正。”[3](p432)所以,周汝登总结他的工夫论的本旨是“不以去恶为究竟,而以无恶证本来”,[3](p432)也就是周汝登所强调的“修为无迹,斯真修为。”[3](p433)在道德实践中,让良知在自我的觉照中层层敞开,将身和心整体地托付于当下的开展中,从而使良知重新回归好好、恶恶的本真之性。
我们看到,在关于道德工夫的争论中,许孚远重在强调切实平正的道德实践;周汝登则偏重于强调对自身良知的觉察和存养。两者都是道德实践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只不过由于他们对性体的认知不同,才使他们在辩论中各执一词,未能仔细领会对方的言说意旨。
三、道统之争
如果说前两者是显性层面的辩论,那么,孰为儒家正统,孰可以承担儒家教化之任则为背后的隐性论题。在这方面,周汝登遭到了许孚远严厉的指责:“古之圣贤,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这些子秉彝之良在……惟有这秉彝之良,不可甄灭,故虽昏愚而可喻,虽强暴而可驯。移风易俗,反薄还纯,其操柄端在于此。奈何以为无善无恶,举所谓秉彝者而抹杀之?是说唱合流传,恐有病于世道非细。”[3](p432)
我们知道,教化世人是儒学最重要的使命,道统是教化之所依,它保障了儒学传承的相对一致性,是使受教者不至于沦入异端的关键。许孚远指责“无善无恶”说“有病于世道非细”,实则是说,“无善无恶”的宗旨不能承担教化的使命。换言之,“无善无恶”说不是儒学正统。这一点在“九谛九解”中可以得到映证:许孚远在“谛一”中以《周易》《尚书》《大学》《孟子》中均以善为宗旨,指出“圣学源流,历历可考而知也。今皆舍置不论,而一以无善无恶为宗,则经传皆非。”[3](p429)经传承载着儒学道统传承的重任,许氏指认“无善无恶”说乃经传所无,言下之意就是说:“无善无恶”非道统所在。
对此,周汝登回应说:“若夫四无之说,岂是凿空自创?究其渊源,实千圣所相传者:太上之无怀,《易》之何思何虑,舜之无为,禹之无事,文王之不识不知,孔子之无意无我、无可无不可,子思之不见不动、无声无臭,孟子之不学不虑,周子之无静无动,程子之无情无心,尽皆此旨,无有二义。”[3](p436)为了证明“无”在儒学史上确有渊源,①彭国翔先生在《从出土文献看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连贯性》一文中论证了“无”在孔子那里的渊源,证明“无”的确为儒家的传统,而非周汝登的杜撰。参见《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他从儒学史上选取八十六人的传记和论说,编成《圣学宗传》一书,以明“四无”乃道学正脉。然后,他指明:“自古圣人未尝有一法与人,亦无一法受于人,前无辙迹可寻,后无典要可据,[3](p478)“圣人立教,俱是因病设方。病尽方消,初无实法,言有非真,言‘无’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则何言非碍?”[3](p436)依此而言,道统传承并不筑基于一套可言说、可传达的经传系统。任何语言的述说和逻辑的分析只能是片段性的截取,拘泥于此,德性本身会固化为对象化的知识。这意味着要以思虑来把握良知,也即以气来统摄理,这不仅颠倒了理、气之间的关系,更导致了知行之间的断裂。因而,“圣圣相传,自见、自闻、自知,同归于宗,如水合水,非真有物可相授受之谓也。”[3](p478)道统传承其实是生命在自反、自省中完成的。因此,他总结:“千圣相传只传此心而已。”[3](p443)
前贤往圣的道德实践是良知之能、好恶之性的自然开展,是自我显现、充实、转化和提升的过程,它为后来的行道者垂示了一个良知所能达到的境界,在此意义上,圣贤动静语默,出处进退无不是在立教,他们的生命转化为教化场所。所以,千圣所传之法实际是圣人通过自身的进德修业而为后世展示的良知所达到的可能性。它是垂示性的,而非直接参与到后来学者的行道过程中。在周汝登看来,将道统的传承置放于当下的学者生命中,避免了使活泼泼的圣人境界抽象化,从而让教化与受教始终保持在活泼泼的生命中。由此,道统传承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经传,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每个行道者的进德修业都是在进行道统的传承,他们既在接纳前人所立之教,又在为后人确立道统。所以,道统的传承其实就是立教与行道融合在学者当下实践中的过程,而不同时空的学者则共同构筑了此道统。
由上所言,周汝登试图将前人用知识体系建构起来的道统消融在具体的感性生命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汝登对经传所代表的语言系统的放弃,而是说,语言及基于其上的知识被目为感性实践中的一个环节。他所强调的“授受不在言语,亦不离言语”[3](p435)表明语言是在实践的统摄下立教的一种方式,而非唯一路径,更不是根本途径。许、周二人对道统承传方式的争论,实际上是儒学正统之争,他们都认为自己承担着儒教的大命。
四、结论
“九谛九解”以性体(心体)之“有善”与“无善”为核心,展开了两条不同的道德实践工夫论,并最终落脚在孰能承担教化,孰为儒学正统的关键性问题上,实际牵涉到性、道、教之间的关系问题。性体是修道和教化的根基和目的,修道和教化也是性体返回自身的通道,三者是紧密相连的。许孚远与周汝登都是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统一性、道、教,从而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
许孚远严守经传所言之善,以此作为修道和教化的根基,原因在于:其一,经传作为文本,它记录了往圣前贤的言行,因而是圣贤精神的实质化体现,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它作为修道和教化确定不移的根基,保障了道统不坠;其二,经传的编撰使精神具化为知识,而知识的可言说性和可传达性为道体提供了客观的载体,使受教者的修道有法可依,不至于堕入异端。由此可见,许孚远的理路是依托于知识性的经传系统的,而这正是朱熹“道问学”的理学思路。尽管许孚远也言心言性,但是,其学术的根基和思路是理学的。周汝登则完全以个体内心道德意识的觉醒作为唯一的根基。原因在于,经传作为圣贤精神的载体,只具有引导性,是道德实践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修道与教化的目的是使性体自反,最终的落脚点是生命个体。以“无善无恶”言说性体,反显性体中本有的好善、恶恶之“良知”,并把性体的自反托付于个体的道德实践。使性、道、教三者在人自反、自知的内向察觉中得以统一。由此可见,周汝登的理路完全是王阳明“尊德性”的心学思路。许、周二人的争论乃是理学模式与心学模式的正面交锋。把他们的争论说成是心学内部的争论,是不恰当的。
许、周二人的争论并非是门户之见,而是切实洞察到对方义理系统中的漏洞及其可能导致的危险所致。许孚远以经传的权威性和确定性保证了教化的普遍性和明晰性,却容易使人陷入追逐经传所言之理的知识性活动,使对“良知”的持守异变为对外在知识的逻辑一致性的探究,造成王阳明那种“格竹”之困;换言之,由“道问学”而来的“知”之明,并不能保证“行”之善。而周汝登以“无善无恶”消解知识性建构的努力,却因其个体对“良知”的体悟缺乏知识的明晰性,而有沦为神秘主义体验的危险。更重要的是,由“尊德性”而来的个体化的体验并不能保证他立教的普遍性。由此可见,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未能完成性、道、教三者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是到了王夫之的“气论”哲学中才得以完成。
[1]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2]姚才刚.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J].中国哲学史,2008,(1).
[3]周汝登.东越证学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一六五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4]周汝登.圣学宗传[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周汝登.四书宗旨[M].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基金会,1978.
责任编辑 高思新
B248.99
A
1003-8477(2017)07-0111-05
田探(1983—),男,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哲学中心讲师。
重庆市社科规划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博士项目“周汝登心学思想与晚明儒学本体论思想变迁研究”(2014BS016)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106112015 CDJSK 47 XK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