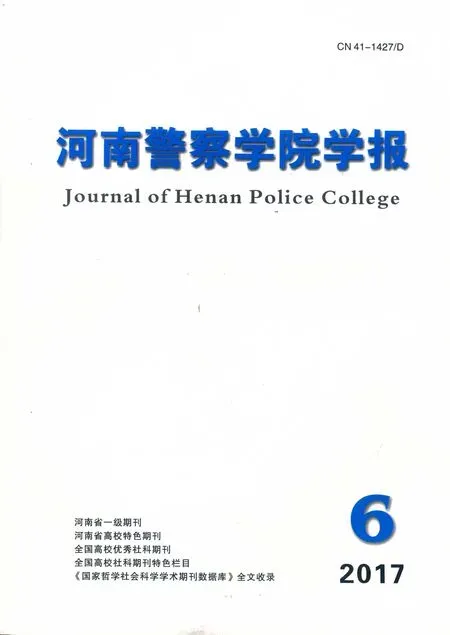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
——警察权与住宅权关系的合理重构
沈国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
——警察权与住宅权关系的合理重构
沈国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在执法实践中,经常与住宅权发生关系的公权力无疑是警察权。要合理构建警察权与住宅权之间的关系必须充分考虑警察进入公民住宅的条件、时间、程序、方式、相对人的意愿等要素,甚至对于何谓“住宅”也应做审慎的判断。完善的制度为警察执法提供合理的指引,但深入分析我国关于警察权与住宅权关系的法律制度,会发现其中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关于“住宅”的法律用语混乱,有“住所”、“住处”以及“场所”等不同的表述;警察进入住宅的法律定位不科学,出现错位的现象;警察进入公民住宅的制度设计存在重大缺失等。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在制度上进行调整与完善,最终推进警察权与住宅权之间合理关系的形成。
警察权;住宅权;搜查; 检查; 监控
法谚常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其意是指,哪怕是破陋的小屋,风可以刮进来,雨可以下进来,但是国王却不得随意进入。根据法律授权,有机会常常与住宅权相遇的是警察权,对于警察权而言,这一法谚当然适用,也更应被记住,“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技术手段的运用,这一法谚也被赋予时代的崭新意义,有待我们重新全面地认识与界定。检视我国赋权警察进入公民住宅的法律制度,不仅存在着面对警察权时对住宅权保护不周的问题,也存在着法律的不科学规定导致面对住宅权与生命权、人身安全权发生冲突时,无法发挥警察权的积极作用的问题。鉴于以上问题,有必要对警察权与住宅权的关系进行全面理性思考,重新构建警察权与住宅权之间的合理关系。
一、当前制度中警察权与住宅权的关系:混乱、错位与缺失
在我国,对警察权与住宅权关系进行规定的法律规范涉及多部,其中进行明确规定的有《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法》《刑事诉讼法》等,与这些法相呼应,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也有相关规定。除了有明确规定的法律规范之外,《反家庭暴力法》《行政强制法》中也暗含了警察权与住宅权之间的关系。综观这些法律规定,可以发现我国整个制度中关于警察权与住宅权的规定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律用语混乱的问题较为突出
“住宅权”中的“住宅”这一法律术语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是,《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范中并没有“住宅”这一术语,*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有一处使用了“住宅”,其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了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情形,“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很显然,这主要是针对个人侵入他人住宅时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而规定的,并不涉及警察权与住宅权之间的关系。而是使用了“住所”、“住处”与“场所”等名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使用的是“住所”,该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可以进行检查。……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人民警察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保持了一致,也采用了“住所”的表述。*《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对警察行为的禁止性规定之一是,“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这里使用的是“住所”一词。《刑事诉讼法》则更为独特,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述,其第一百三十四条对搜查进行规定时,使用的是“住处”,该条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但是技术侦查措施中使用的是“场所”。该法第二编第二章第八节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规定时未触及技术侦查措施的对象,但根据《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包括场所监控,*《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指由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技术侦查的部门实施的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措施。”显然住宅包含在了“场所”之中。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住所”、“住处”与“场所”三个词语的使用都试图表达对住宅权的保护,但是它们的含义却与“住宅”相去甚远。先来看看“住所”,该词的使用可以找到其明确的法律概念界定。其来自于民法。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中也有对住所的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相比,其关于住所的规定相对明确、科学,除增加了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亦为住所之外,特别强调住所是指居所,而不是指居住地。一般而言,民法上所确立的住所往往是为了确定诉讼管辖地、债务清偿地或债务履行地。宪法上规定的住宅权中的“住宅”与民法上所规定的“住所”的功能指向完全不同,范围也相差很大。民法上所规定的住所范围极为狭窄,在我国仅为登记居所和经常居所,*何谓“经常居所”,尚无明确司法解释。不过对何谓“经常居住地”有过司法解释,可视为对经常居所的理解。经常居住地就是“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规定。2013年修改之后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则规定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若以此为宪法上住宅权保护的“住宅”的范围,显然对于警察进入住宅的权力过于放纵。
“住处”的使用找不到明确的法律概念界定,也无司法解释。从字面来看,这一词简单易懂。“住处”就是指“居住的地方”,这一词大大拓展了住所的范围,不论户籍、不论有无产权、不论长住还是短住,不论多人居住还是一人居住,只要是居住的地方都可以称为“住处”。但这只是学理解释,由于没有明确的正式解释,其范围有多大在制度上并不明确。
“场所”的使用同样也找不到明确的法律概念界定,也无司法解释。只有学者解释,“将对住处、其他有关地方的搜查归类为场所搜查”[1]。这意味着,场所包含了个人的住处,也包含了公共场所。
由上观之,立法者在规定“住宅权”保护时术语使用较为混乱,导致法律之间的不统一,甚至出现法律内部的不统一,这对警察权与住宅权合理关系的形成是极为不利的。
(二)警察进入住宅的法律定位并不科学,出现错位的现象
一般来讲,警察权进入公民住宅至少有四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警察权以物理方式进行公民住宅进行刑事搜查。第二种情形是警察权通过技术手段进入公民住宅进行刑事侦查。利用技术手段对公民住宅进行监听,监控当属此类。第三种情形是警察行使行政职权对公民住宅进行检查。警察搜查以犯罪嫌疑为前提,而警察行政检查则主要以违法治安管理为前提,这是我国警察权二元构造模式所形成的独特结构。第四种情形是警察因履行救助危难的职责而进入公民住宅对公民的生命与人身安全进行保护。
就这四种情形来看,前两种均为警察实现刑事侦查的目的而与住宅权发生关系,一般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之中,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均做了相应的规定。从刑事诉讼法规定这两种类型的目的来看,它们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是恰当的。现有的制度存在法律定位不科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三种情形与第四种情形。这两种情形都规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从对警察权的定位而言此种规定是不科学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围绕惩治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而做出的规定,警察住宅检查前提也要求必须“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但是分析第四种情形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情形中警察进入公民住宅的目的是排除危险,保护住宅内人的生命与安全。诺瓦克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家公约》进行解读时也曾提到搜查之外基于救助而对公民住宅的进入,“房屋搜查不能被滥用,以至于产生超出其所要达到之特定目的的骚扰。除了房屋搜查之外,在灾难(火灾、洪水、地震得等)期间进入私人住宅也完全是允许的”[2]302。显然,在住宅内人的生命与安全遭受威胁时,警察进入公民住宅与基于对违法行为的查明而进入公民住宅的行为目的完全不同,这决定了对警察进入公民住宅的性质,进入的条件、进入的程序等规定也是完全不同的。我国笼统的把两种类型都规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二者的差异,导致在实践中一方面无法充分发挥警察的积极救助职责,另一方面未能有效制约警察进入公民住宅进行行政检查这一庞大的可能侵害相对人权利的警察权。
(三)关于警察进入公民住宅的制度设计存在重大缺失
警察搜查、技术监控或检查住宅是警察进入住宅的常见行为,其目的在于针对违法犯罪嫌疑搜集证据。对于这类警察行为,制度设计上一般会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要避免警察权滥用的问题,另一方面保证警察权能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有效率地侦破刑事案件或者查明治安违法行为。制度设计往往在这些层面展开,仔细分析我国相关的制度,可以发现为实现前述目的而设计的制度尚有重大缺失:
一是对警察权滥用的约束制度设计不足。避免警察权的滥用并非绝对禁止警察进入公民住宅,而是限制警察权的任性,减少其进入公民住宅的任意性。因此,对于警察进入公民住宅往往从正当理由、正当程序、合理的时间和期限等方面进行限制和约束。住宅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与其他场所,尤其是公共场所存在着重大区别。但是,我国制度设计中,并没有特别关注住宅与其他地方的差别,未给予其特别保护。如,《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刑事侦查时将“人的身体、物品、住处与其他有关的地方”并列起来进行规定,与其他有关的地方相比,住处并没有获得特别关注,未获得特别的保护。*在住宅内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也有类似的情况,根据《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界定,技术侦查措施包括“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措施”,场所监控包含了住宅监控,这里也未将住宅与公共场所区分开来。与《刑事诉讼法》相比,《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检查的规定有了对住宅的特别规定,这特别值得肯定。但是这主要是针对紧急情形下进入公民的住宅而言的,对于非紧急情形下的行政检查并未对“住宅”与“其他场所”进行区分。
并且,对于住宅搜查、住宅技术监控以及住宅检查制度中,正当理由的规定也是有所欠缺的,在住宅搜查中把搜查的目的等同于搜查的理由。《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搜查的目的是“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刑事诉讼法》中在规定搜查时强调其目的:“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诉讼程序规定》中对此条进行了细化,但主要谈搜查的程序,目的上仍然采用了同样的表述,“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搜查目的是统一的,抽象的,搜查理由则应是具体的,有明确针对性的。国内的研究学者在分析我国搜查制度存在的问题时即指出,“对搜查证上应具体记载哪些事项,《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都只字未提”,“对于搜查的适用条件,其规定基本等同于立案条件,侦查人员无须‘合理根据’就可请求对怀疑对象进行搜查”[3]。场所监控中存在类似的问题,其启动的理由在《刑事诉讼法》上仅仅规定为针对一些重罪,“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即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赋予了警察过多的裁量权。警察行政检查权的行使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只要是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就可以进行检查,并无检查理由的明确规定。
警察进入公民住宅进行搜查、技术监控与检查的程序规定也受到不少批判。我国的搜查与检查的程序问题在于将审查、批准的权力和执行的权力合在了一起,均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行使,缺少外部的监督力量。“通过签发搜查证启动的搜查行为是否合法并无法律监督……,这显然违反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另外对搜查证的签发存在公权力恣意的情况。在实践中只要可迅速收集证据、有利于案件侦查,便可签发搜查证,失去了侦查以审判为中心合理保障人权的宗旨,很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4]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检查证的签发、通过技术手段对场所进行监控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并无外在制约性力量介入。
二是,在无证搜查制度中缺失“同意搜查”制度,缺失无证检查制度的规定,更未关注“同意检查”制度的设计。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警察搜查的规定,未明确确立同意之下的“搜查”导致即使基于“同意”之下的无证搜查所获取的证据也处于“非法”状态,这忽视了住宅权人的意志,降低了警察搜集证据的效率,也人为封闭了警察与相对人耐心平和商讨的渠道。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无“无证检查”的规定,“同意检查”制度更未规定。其实行政检查仅仅针对治安违法行为,当事人与警察之间的对立性并不强,征询当事人“同意”进行检查既节约警察资源,也尊重了当事人意愿,在制度设计时完全可以考虑。
二、警察权与住宅权关系合理重构的理论基础
通过前述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警察权与住宅权关系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需要对警察进入公民住宅的制度进行完善,予以重构。合理重构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对警察权与住宅权恰当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住宅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对普通法的要求
我国宪法上规定了住宅权的内容,明确表明了宪法的态度,是把住宅权作为基本权利来对待的,而基本权利“具有对抗国家权力的意义,要求国家权力在做出任何立法时都必须考虑不得以不正当的理由剥夺和损害这些权利,因此,基本权利的生存是通过宪法约束各种普通法律而获得保障的”[5]。住宅权作为基本权利要获得其他普通立法的尊重,首要的一点就应当是普通立法与宪法关于“住宅”这一概念的表述应当一致,普通法在具体化宪法上的住宅权时不能擅自缩减住宅权保护的范围,不能降低住宅权保护的力度。如前文所述,我国相关的立法中关于“住宅”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混乱的,出现了对住宅的不同表述,分别有“住所”、“住处”、“场所”等概念。这些概念与“住宅”的含义并不相同,无法承担起保护住宅权这一基本权利的重任。从宪法与普通法的关系而言,当普通法的规定与宪法不一致时,应当服从宪法的规定,从宪法到普通统一使用“住宅”一词更为恰当。
宪法的“住宅权”在普通法中的具体化意味着有了具体制度的保障,但是“住宅”这一概念本身若不能清晰表达,仍然会带来诸多困惑与误解,因此住宅权中“住宅”的范围应当明确界定。要对“住宅”进行明确界定,就得探寻住宅权本身背后的价值取向。以美国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确定“住宅”范围时,住宅权背后的价值取向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随着住宅权背后个人隐私价值的确立,美国住宅权中“住宅”的范围急剧扩大。1967年,卡茨诉美国(katz v.United States)案的判决中明确提出了“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这使得住宅的范围甚至扩张至电话亭。该案判决指出,“封闭的电话亭类似于家,而非户外,处于其中的人享有宪法所保护的合理的隐私预期”。*Katz v.United States, 389 U.S.361(1967).总体来看,发展至今,在美国,基于个人隐私价值而形成的住宅范围不仅包含了自己所有或者占有的住宅以及属于住宅的附属空间;包含临时居住的地方,如旅馆;而且还包含与外界相对隔离,个人在其中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地方,如电话亭等。我国属于成文法的国家,并不具备通过判例确定概念含义的传统,不过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或者法律解释的方式推进概念的明确化、具体化。我国“住宅权”中“住宅”的范围的确定也需要探寻住宅权背后的价值。从我国宪法文本的整体内容来看,支撑住宅权的是对住宅内人的保护,而非对住宅这一“物”本身的保护,关于住宅这一私有财产“物”的意义上的保护是放在宪法第十三条关于“财产权”保护的框架之内的,这就形成了“财产权”与“住宅权”保护价值的分流,财产权保护房屋的财产价值,住宅权保护房屋之内人的安全、自由、尊严或者隐私等。我国现行宪法制定时草案修改说明对住宅权背后的价值基础交代得非常清楚,彭真同志1982年曾经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指出:“为了切实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草案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和诽谤;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侵入。”*1982年4月22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其中对住宅权的保护目的作了明确的说明。in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6/content_5001302.htm.从这一说明可以看出,“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是住宅权的价值基础,无论怎样的住处,是长期居住的,还是短期栖身的,无论是富丽堂皇的,还是破败不堪的,身居其处,其中都安放着个人的安全、个人的自由与个人的尊严。这也就意味着,住宅是给人以合理的安全、自由与个人尊严的预期的地方。这些价值基础应成为我国判断“住宅”的核心标准。另外,住宅本身“物理”上所具有的“与外界相对隔离”这一得到普遍承认的标准也是重要的判断依据。基于“个人的安全、个人的自由与个人的尊严的合理期待”以及“与外界相对隔离”这两个标准,电话亭虽未必能纳入其中,但至少以下场所可以纳入“住宅”的范围:自己所有或者自己以租住、借用等方式占用的房屋;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等;*2000年11月23日发布的《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入户抢劫”中的“户”是指“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在确立住宅范围时,这一解释能够提供极好的思考路径。用于个人生活时段的商住两用场所;个人投宿的宾馆等。
(二)住宅权的“权利”属性之于制度设计的意义
从宪法角度而言,警察进入公民的住宅必须有正当理由与正当程序。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正当理由、正当程序之外,也就是“有证进入”公民住宅之外,是否制度上也有必要设计“同意”进入这类“无证进入”公民住宅的情形。在很多国家的制度中,“同意”本身具有替代正当理由与正当程序的作用,美国联邦法院在 1921 年对 Amos v.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确立了此种观念,认为经被告同意而进行的搜查无须具备宪法第四修正案中要求的司法令状和正当理由。*Amos v.United States,255 U.S.313(1921).那么,为什么当事人的“同意”会为警察进入住宅作“合法性”背书呢?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学理上的总结,认为有三种理论上的论证,一是无合理隐私期待说;二是权利抛弃说;三是规范政府行为说。*这三种理论的立论在于:无合理隐私期待说强调相对人同意侦查机关搜查后,相对人对隐私权的合理期待已经丧失;权利抛弃说则认为相对人同意意味着对宪法第四修正案赋予的不受不合理搜查、扣押这一权利进行了处分,即抛弃了该项权利;规范政府行为说认为,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目的在于阻止政府进行不合理的搜查扣押,其目的在于防止政府的违法搜查行为侵害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而在个人同意的前提下,公民出于自愿,同意或授权警察搜查,没有伤害公民隐私或人格,所以政府的行为并非不合理的搜查,不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应当被认可。参见宋志军: 《同意搜查制度比较研究》,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这三种理论均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均具有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无合理隐私期待说”与“权利抛弃说”的理论依据基本类似,都试图从个人权利可以放弃的角度进行论证,但是个人放弃权利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赋权公权力进入公民住宅呢?这种逻辑关系并非必然;“规范政府行为说”的解释力也不足,个人的同意减少了公权力与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但无论如何都无法直接规范政府的行为。在警察进入公民住宅时建立同意制度,其实是对公民的权利的尊重,这种权利中包含了授予他人进入住宅的权利,其实是权利的授予,而非权利的抛弃。这种制度的设计是对公民自主意识的尊重,是对公民个人的合理预期的尊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警察权的合法进入是“制度预期之外个人预期的产物”,是公民对公权力的授权。
根据宪法原理,一般所涉及的“正当理由”与“正当程序”是向当事人提供基本的保障制度,通过整个制度预期实现每个个体的合理预期;在这之外,同样允许只基于个体能力而形成的“个人预期”,当理性的个人通过自己判断和分析同意警察进入公民住宅时,其应当能够预见到这种同意而带来的后果,形成个人的合理预期,其实这就等于是用自己的授权代替了有权机关的授权。这是警察权在住宅主人同意之下能够正当进入其住宅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因此形成了同意之下“无证搜查”或者“无证检查”为合法行为的制度。“无证搜查”或者“无证检查”制度不仅充分尊重相对人的自主意志,而且能够极大地提高警察行为的效率,这种制度设计对于疏解现实中警力资源不足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警察权作为特殊公权力形式与住宅权的关联性
警察权是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形式,在所有行政权中具有最强的强制力,甚至可以对个人的人身进行强制,并享有配备与使用武器的权力,这使得警察权具备利用其强制手段保护公民的生命、人身安全以及财产的能力,但同时另一方面,也带来人们对警察权滥用的极大恐惧,一旦滥用,公民的权利就可能会遭受致命的打击。因此,对其进行合理的约束与限制,保证其造福于人们而不是威胁人们的权利便成为必然。正是警察权的这些特性,使其经常与公民的住宅权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形成两种不同的类型,基于不同的类型应考虑不同的制度设计。
第一类型是警察权基于保护人的生命与安全的职责而进入公民的住宅。我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警察因此需要承担救助的职责,现实生活中需要警察救助的情形非常多,因此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进行具体分析。一旦与住宅发生关系时,警察在面对公民救助要求时就需要谨慎平衡住宅权与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以及财产权之间的关系,很显然,与住宅权相比,生命权与人身安全权的利益要远远超过住宅权,但是财产权的利益则低于住宅权。在生命与人身安全遭受巨大危险时,警察应当承担起进入住宅进行保护的职责。并且从现代社会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来看,个人的生命与人身安全获得公权力,主要是指警察权的保护已经成为公民权利的内容之一。在传统社会,虽然国家为维护社会秩序,在排除对个人生命、人身安全造成的危险因素方面享有了垄断权,但是国家并不因此而承担保护个人生命与人身安全的责任,法定的国家职责尚未被提出来,就国家而言国家职权与国家职责并不统一,因此,个人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保护尚未作为权利形式而存在,充其量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副产品而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反射利益。但是进入近代后,人们不仅关注克服庞大的国家权力侵害个人权利之虞,而且开始关注个人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保护问题,要求国家对个人生命安全、人身安全负有安全保护的职责,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保护已经成长为一种权利,而不再是一种副产品。这就意味着,当住宅内人的生命、人身安全遭受威胁时,警察进行救助成为法定职责,如果不履行该职责,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超级玛丽”案就真实地反映了这种观念。*“超级玛丽案”的具体过程如下:“超级玛丽”演唱组合是由两位女孩罗惊与韩萱组成的。2006年3月21日凌晨0时30分左右,两女孩的朋友报警两女孩可能在出租屋内煤气中毒,警察接警后不清楚出租房内的具体情况,未敢贸然强行进入房间,直至当日清晨8时许通过电话联系上房东,在房东通知下由持有钥匙的邻居打开屋门。发现屋内弥漫大量煤气,罗惊、韩萱已经昏迷,经医院诊断为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最终结果是,一人死亡,一人成为植物人。超级玛丽的家属认为警方存在违法不作为,未能对二人进行及时救助导致二人媒体中毒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向二人家属支付200万元补偿款,家属撤回了对公安机关的行政诉讼。具体参见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7/11/id/ 276239.shtml;以及http:// blog.sina.com.cn/ s/blog_492a2cb401017t30.html,访问时间2016年10月1日。总之,无论从警察机关的职责来看,还是从公民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与住宅权发生关系的优先性保护特征来看,以及从生命权以及人身安全权的权利属性来看,当住宅内人的生命与人身安全遭受危险时,警察有权也有责任进入住宅进行救助,并且由于是在紧急情形下对生命、人身安全的保护,因此,应当更多强调效率,在程序设计上不宜复杂,并尊重救助现场实施救助的警察的判断。
第二种类型是为侦破刑事案件或者查明行政案件而对住宅展开的搜查、检查或者技术监控。这种类型中,警察进入公民住宅往往是因为有违法或者犯罪嫌疑需要进一步核实、查证,虽然这里目的涉及对犯罪违法行为侦破或查明的国家利益,但是这种国家利益实现的逻辑是:警察进入住宅是建立在存在线索或者证据显示有必要进入住宅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警察的主观臆断或者任意的猜测。如果这样,个人就失去了构筑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宅的意义。如前文所言,住宅的背后包含诸多人类社会基本的价值要求,诸如个人安全、个人自由与个人尊严等。无论如何,支撑住宅权的这些价值都要求警察必须审慎地进入公民的住宅,特别要求比进入其他场所更加慎重。这种慎重的要求体现在法律上就是必须有正当的理由,正当的程序以及合理的期限。
随着高技术手段的发展,刑事案件侦破时技术手段的使用尤其值得关注。技术手段突破了传统肉眼所见不可再现的特点,其所形成的电子资料不仅可以远距离为他人当时所察看,而且还可以储存起来,不断地重复、再现,甚至可以放慢、可以定格,因此,各种细节都可被反复展现,反复收听。另外,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资料的复制和传播变得越来越简便,只要小小的一个U盘就可以把可视、可闻的资料全部传播出去。并且随着网络的普及,一旦电子资料被上传至网络空间,其传播广度和速度往往极为惊人,不受地域、距离、时间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出去,进入到网民的视野中。由此看来,住宅的技术监控与传统的住宅搜查相比,有自身的特点,并且一旦滥用会给个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因此,一方面,对于住宅的技术监控应当考虑其自身特点,形成与之相应的约束警察权滥用的制度,如监控所获取的视频或者听频资料的保存、使用等都应当有专门的规定;另一方面,正确认识技术手段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警察采用住宅监控的行为给予更为严格的控制。
三、警察权与住宅权关系合理重构的路径
针对我国当前制度中不合理的警察权和住宅权关系,应当重新调整和完善。在这之前,首先应当实现宪法与普通法中关于“住宅”名称与范围的统一, 抛弃“住所”、“住处”以及“场所”等词语的随意使用,统一使用“住宅”一词,并作出必要的解释。
在“住宅”一词使用统一的前提下对相关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这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警察履行进入住宅救助生命、人身安全救助职责的制度重构
现有制度关于警察进入住宅救助生命、人身安全的职责的明确规定出现在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其中规定的“立即检查”即包含此种情形,要求“检查公民住所的,必须有证据表明或者有群众报警公民住所内正在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事)件,或者违法存放危险物质,不立即检查可能会对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从其规定的内容及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位置来看,这里立即检查的规定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对住宅进行“立即检查”规定的具体化,明确了对住宅进行“立即检查”的法定条件。很明显,其中关于为保护个人人身安全目的而进入公民住宅的行为与住宅行政检查行为不同,这种行为并非基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或者违法嫌疑而启动的,纯粹是警察基于“救助”职责而展开的。因此,将其与行政检查行为混同在一起极易造成制度上的混淆。因此,笔者建议对于警察因保护公民生命、人身安全进入公民住宅进行救助的行为应当放在《人民警察法》中规定,而不是与其他住宅行政检查一起规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警察进入住宅进行救助是因为住宅内人员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遭受危险之时,处于紧急情形之下,因此,程序上的设置不能太过复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立即对住宅进行检查时特别强调其程序上的严格性,要求必须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这其实混淆了住宅内紧急救助与基于违法事实查明的行政检查行为之间的区别,对警察权造成了不恰当的羁绊。这种无助于警察权制约的“检查证”制度往往会延误时间,错过进入住宅救助生命的最佳时间。约束住宅内紧急救助的核心是“启动条件”的合理设置,该“启动条件”应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当事人报警或第三人报警,或者有证据表明公民住宅内正发生公民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案件或者事件;(2)第三人报警的内容或者证据显示的线索使警察获得合理的怀疑,怀疑住宅内的人正在遭受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威胁。
当事人自己报警寻求救助的情形相对较为简单,可看作是当事人对警察进入住宅的授权。
第三人报警求助情形较为复杂,警察是否有权进入公民的住宅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分析要素包括三方面,一是报警救助的对象是什么;二是报警救助者与住宅之内的人员是什么关系;三是所获得的信息是否能够使警察获得合理的怀疑,怀疑住宅内的人正在遭受生命安全或者人身安全的威胁。若涉及住宅之内人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之外的其他权益,则不能只根据求助人的求助而进入公民住宅;若涉及住宅之内人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则必须尽快查明申请者身份,弄清申请救助者与住宅之内人员的关系,分析评判相关信息能否形成合理的怀疑。为保证第三人慎重对待自己报警所涉内容的真实性,应当履行书面签署申请书的手续,申请书中写明申请人与住宅之内人员的关系,申请所依据的事实以及不实报警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第三人书面申请不仅可以保证警察进入公民住宅的理由具有正当性,保证其并非基于任意的猜想而进入公民的住宅,而且可以保证求助者慎重启动救助程序。此种情形之下其实存在着生命安全、人身安全与住宅权之间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的解决应当遵循“生命安全、人身安全优先”的原则,“救助中的情形千差万别,理论的想象永远都难以赶得上实践的丰富,但无论什么样的差别,都必须恪守生命安全第一的原则。如果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同时需要救助,则优先救助生命”[6]。
无任何人申请救助,但是有证据表明证公民住宅内正发生公民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案件或者事件的情形,则要求警察必须有充分的证据线索,并且这些证据线索不能仅仅是使人怀疑住宅内人的生命、人身安全遭受威胁,而是应当使人确信这一点。因此,对其证据的证明力要求非常高,也意味着在这种情形下,警察判断是否进入公民住宅进行救助必须特别慎重。
(二)“同意搜查住宅”、“同意检查住宅”的制度设计
在无证搜查或者无证检查制度中,相对人的同意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警察搜查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警察行政检查的规定,均未明确确立同意之下的“搜查”和同意之下的“检查”制度,导致即使基于“同意”之下的搜查或者检查所获取的证据也处于“非法”状态。很多国家刑事诉讼法之中设计了“同意搜查”的制度,*具体各国关于同意搜查制度的内容可参见宋志军: 《同意搜查制度比较研究》,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已成为警察“无证搜查”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建议,应当学习这一制度,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完善中,应当给“同意搜查住宅”、“同意检查住宅”制度一席之地。
同意之下“无证搜查住宅”或者“无证检查住宅”制度中相对人的“同意”是极为重要的,相当于相对人发去的“授权”指令,因此对于“同意”这一意识表示必须确定其明确的判断依据。对于搜查制度中同意之下的搜查,学界多有探讨,提出同意必须满足的条件,“(1)警察必须首先向预搜查者表明身份和搜查意图。(2)同意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受胁迫的,无论这种胁迫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3)公民个人的同意必须是明智的而不是受欺骗的”[7]。这基本上能够说明“同意”的核心内容,一方面,要求警方必须承担告知义务,这能够保证相对人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形下做出的决定;另一方面,要求相对人的“同意”必须是自由、自愿、自主地做出的理性判断,不是在受到公权力的“压力”、“威胁”、“欺骗”、“诱惑”等情形之下做出的。除此之外,还应当要求做出理性判断的相对人必须是有判断能力、意识到行为的意义和后果并且能够承担行为后果的理性的个体。符合这些条件,才能保证基于对相对人自主意识尊重基础上的“同意搜查”制度不违背其制度设计的本意。当然,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警察行政检查时获得相对人的同意而进行的检查行为。
当然,在“同意搜查”、“同意检查”的制度设计中,应当保持对非自愿“同意”以必要的警惕,设计出周严的制度体系,避免其沦为警察任意进入公民住宅的堂皇借口。
(三)警察以物理方式进入公民住宅进行“搜查”或者“检查”制度的完善方向
警察以物理方式进入公民住宅进行“搜查”或者“检查”时,最需要警惕的是警察的任意“搜查”或“检查”。为了避免警察的任意而为,正当理由、正当程序、合理时间都是制约警察搜查住宅或者检查住宅制度中重要的内容。我国虽然在相关制度中也涉及了这些内容,但规定仍非常粗陋,难以适应对住宅权保护的需要,因此,应在相关制度中予以完善。
从正当理由来看,我国住宅搜查制度中,把“搜查目的”等同于“搜查理由”,导致启动条件过于宽泛,达不到制约的效果。从美国、英国的发展情况来看,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美国要求启动搜查的条件是必须具有“合理的理由”,即“当官员掌握有可能合理地相信其真实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所获悉的事实和情况本身足以使有合理谨慎的人相信犯罪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实施时,合理根据就存在了”。*Carroll V.U.S., 267U.S 132, 162(1925).对于住宅搜查而言,“合理的理由”的“合理”要求更高,美国刑事诉讼法学者阿希尔·里德·阿马教授曾对此作出过解释,比如“对机场的搜查,考虑飞机的爆炸,——有时0.1%就够多了——而其他时候100%仍是不合理的。(即使政府确切地知道,诚实的亚伯的商业记录在他的卧室中,包含了一个关于贝蒂和卡罗尔之间的诉讼的记录,一项与传票相反的突袭搜查——将典型地是不合理的。)常识告诉我们,除了可能性之外,要注意发现下列问题的重要性,即:政府要寻找什么,搜查的侵扰性、搜查目标的确定性,以及达到搜查目的的其他可利用的方式,等等”[8]。可见,这种更高比例的“合理理由”要求警察在进入住宅时应进行多方面分析和判断,保证其进入住宅的理由是充分的,合理的,不过这往往赋予警察较大的裁量权。英国则收缩了警察的裁量权,针对住宅搜查确立了独特标准,“对搜查人身或车辆采用了‘合理的根据怀疑’,对住宅采用了‘合理的根据相信’。……‘怀疑’与‘相信’是对搜查理由规定了不同程度的证明标准,‘相信’比‘怀疑’证明标准高”[9]。“合理的根据怀疑”与“合理的根据相信”表现出证明标准上的极大的差别,引起怀疑与让人相信相比,二者所需要的证据信息相差较大,前者只强调警方所掌握的信息线索能让有理性的人怀疑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犯罪就可以了,而后者则要求信息线索不仅让人怀疑,而且在怀疑的基础上继续证明,直至达到说服有理性的人相信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犯罪。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机动车和人的可移动性,若要等到“合理的根据相信”才能达到搜查标准的话,机动车和人可能早已杳无踪迹。而住宅则不同,其不仅不能移动,而且其中包含了居于住宅内的人的自由、安全、尊严与隐私等价值,对其搜查必须特别地慎重,达到“合理的根据相信”的标准能够减少对住宅内的人的侵扰,同时也不必顾虑住宅移动而失去搜查的对象。
我国住宅搜查制度也应当逐步确立搜查理由制度,减少警察启动搜查的任意性。英国的制度对我国警察而言,要求过严,恐一时难以适应,学习美国的经验建立“合理的理由”制度是可以被接受的。要求警察在客观上收集到一定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使一般理性人认为可能或者大致相信,怀疑犯罪已发生或正在实施时,警察才可以进行住宅搜查。这应当是对警察进入住宅进行搜查的基本前提,否则警察凭什么理由进入住宅?
从正当程序来看,我国住宅搜查与住宅检查的程序问题在于审查、批准的权力和执行的权力合在了一起,均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行使,缺少外部的监督力量。不独住宅搜查和住宅检查存在此问题,其他类型的搜查与检查均在这方面受到批判。在程序上,学界多主张建立“司法令状”制度。这种改革思路对住宅搜查或者住宅检查尤其是重要的,由独立第三方进行事前审查、批准,这能有效减少警察权对公民住宅的随意侵入。
从住宅搜查时间或者住宅检查时间来看,很多国家对物理方式侵入公民住宅在时间方面有法律限制。有些国家直接在宪法中规定夜间住宅的特别保护,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等国家的宪法;有些国家则在刑事诉讼法中在规定搜查时明确规定对其夜间搜查住宅的限制,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夜间不得搜查住宅,要求搜查住宅必须在早 6 时之后至晚 21 时之间进行。*当然,这些国家夜晚不得进入住宅进行搜查进行是原则规定,也规定例外情况可以突破。如法国规定的例外是从白天已经开始的搜查,或从房屋内发出呼救以及法律有规定的某些特殊情况。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住宅的夜间保护问题均未置一词,没有明确的法律立场。对此问题我国的相关制度设计也应当有所考虑,设计与保护住宅内“个人的安全、个人的自由与个人的尊严”相关的搜查制度和检查制度。
(四)警察技术监控公民住宅制度的完善方向
在人类立宪之处,尚未出现侵入住宅的高技术,因此当这类技术出现并被公权力所采用时,基于宪法基本权利的要求对其进行约束和防范成为必要,国际人权研究专家曼弗雷德·诺瓦克指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家公约》第17条第1款提供的保护针对的是对住宅的任意或非法干预。“任何未经被影响的个人的同意而发生的,对可以解释为‘住宅’这一术语的范围的侵犯都属于干预。这适用于强行或者秘密的侵入以及电监视行为、监听装置、隐藏的录像机等等。”[2]301对于公民住宅的技术监控进行约束和防范需要考虑技术手段的特殊性,设置相应的制度。技术手段一旦被滥用,会给公民权利带来更大的危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一般对技术监控,尤其是针对住宅的技术监控设置更为严格的制度控制。
从各国的发展状况老看,针对住宅的技术监控启动要求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法定重罪;二是“穷尽原则”。如德国《基本法》第13条第3项规定,“根据事实怀疑有人犯法律列举规定之特定重罪,而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查明事实者,为诉追犯罪,得根据法院之命令,以科技设备对该犯罪嫌疑人的住宅进行监听”。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启动的条件,对“法定重罪”才可启动的原则予以确立。*《刑事诉讼法》区分了公安机关侦查和检察机关侦查的不同,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必须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才可启动技术侦查措施;检察机关侦查的案件必须是“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才可启动技术侦查措施。但是,“穷尽原则”并未能确立,仅仅规定“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即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这一规定受到学者的批判,被认为,“这一用语含义过于宽泛,可以理解为采取其他侦查措施无效、低效而‘需要’技术侦查时,甚至也可以理解为我国公安机关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不受最后手段原则的限制”[10]。与其他侦查措施相比,技术侦查措施带给个人的压力、恐慌、不安全感更为强烈,对住宅的技术侦查给人带来的不安与恐惧更甚,这也是各国强调“穷尽原则”的前提所在。我国针对住宅的技术监控制度的完善也有必要考虑增加“穷尽原则”,即必须穷尽了其他侦查手段仍然无效或者低效时才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至于通过程序控制警察对住宅技术监控措施的使用,则与以物理方式进入公民住宅的程序要求类似,建立独立于警察的第三方控制的方式更有助于约束警察权的滥用。
另外,考虑到进入公民住宅的监听或者监控具有不间断、可持续性特点,如长期使用则会获取被监视对象方方面面的信息。通过限制监听或者监视的时间长度来对警察权进入公民住宅进行限制成为至关重要的。从各国的规定来看,监听或者监视均有时限上的限制,但是对住宅内监听或者监视则在时限上要远低于其他场所的监听或者监视。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监听为3个月,但是对私人住宅谈话进行监听的最长期限则缩短至4个星期,当期满后,采用监听措施的情形若依然存在,虽可以申请延长,但是每次可以申请延长也不得超过4个星期。我国当前的制度仅规定,技术侦查的首次适用期限为三个月,根据侦查的需要可以多次延长,并无最长适用期限的限制,也没有公民住宅监控时限的特别规定,对于住宅内人的自由、尊严与隐私保护不够充分。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使用技术手段对公民住宅进行侦查较之以前愈来愈多,有必要及时针对住宅这一特殊的空间,规定较短的监控期限,以避免公民的住宅权遭受过度侵扰。
[1]刘方权.人身搜查和场所搜查的比较——域外法治的简单考察[J].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3):25-29.
[2][奥]曼弗雷德·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上)[M].毕小青,孙世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李超峰,邢永杰.我国搜查制度的运行现状、问题及完善[J].江西社会科学,2014(2): 158-164.
[4]王弘宁.我国搜查与扣押制度的完善——从中美搜查与扣押制度比较研究谈起[J].法学杂志,2016(7):134-140.
[5]沈国琴,田双铭.民法参照背景下宪法的根本法属性分析 [J].晋中学院学报,2016(5):54-60.
[6]程华,沈国琴.警察行政救助权的有效行使及法律规制探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95-102.
[7]刘方权.论搜查[C]//陈兴良.刑事法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10.
[8]阿希尔·里德·阿马.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M].房保国,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60.
[9]刘金友,郭华.搜查理由及其证明标准比较研究[J].法学论坛.2004(4):9-20.
[10]王东.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J].法学研究.2014(5):273-283.
(责任编辑:岳凯敏)
GiveAdmittancetoAllButthePolice——ReasonableReconstruc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olicePowerandHousingRight
SHEN Guo-qin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8, China)
It is police power that often relates with the housing right in law enforcement.When we try to set up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the police power and the housing right, we should consider the condition, time, procedure, method and the will of the relative person.It should be prudently judged what is house.The perfect system can guide the police to reasonably enforce the law.There are many imperfections about the syste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e power and the housing right.First, the terminology of house which is used in the common law is called confusedly as “domicile”, “dwelling” or “place”.Second, the nature of the conduct of the police entering the house is inaccurate.Third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the system of the police entering the civil housing.In order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e power and the housing right.
the police power;the housing right;search;inspect; monitor
2017-09-12
司法部课题“宪法规制下的警察权研究”(16SFB2012)的阶段性成果。
沈国琴(1972— ),女,山西屯留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宪法学、行政法学。
D631
A
1008-2433(2017)06-004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