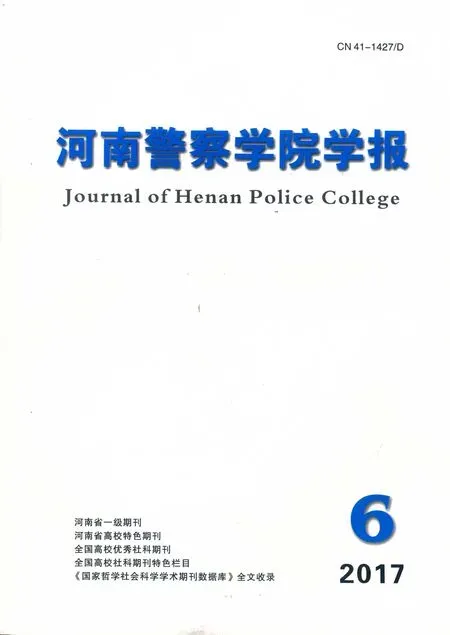我国精神病人司法处置问题与对策
张 勇,李紫阳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我国精神病人司法处置问题与对策
张 勇,李紫阳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在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注重对涉案精神病人进行事后惩罚,而忽视了事前预防制度。刑事法治的进步必然要求转变司法理念,积极应对精神病人犯罪控制和矫正预防问题,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注重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刑事法律与非刑事法律的衔接,通过调动国家司法与精神卫生两大体系的资源,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罚相结合的处置方式,实现社会预防与人权保障的统一。
精神病人;精神病人司法处置;精神病刑事责任能力
2017年2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面馆发生恶性杀人案件。胡某因每碗面一元钱的差价,与店主姚某发生争执,随后手持菜刀将姚某砍死并割下了头颅。胡某行凶后并未逃窜,被现场抓获。事后查明,胡某患有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持有“精神残疾二级证书”。该案件发生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热议,有人提出精神病人是定时炸弹,需要全部进行物理隔离,送入精神病院或其他监管机构,永远限制其自由。相反,有些人提出对于精神病人应给予更多关爱,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等方式构建完善的精神卫生医疗和监管体系,实现精神病人犯罪事前预防才是可行之道。笔者认为不能将精神病人作为实现公共安全的工具,必须站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关注犯罪人的家庭背景、社会角色、人际关系、性格、精神等方面,通过综合判断决定是否需要对犯罪人处以严苛的刑罚,或者进行从轻甚至免除处罚。
国家卫计委公布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病人人数为429.7万人,96.9%的患者病情稳定或者基本稳定,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患者高达83.6%。面对已经过亿的精神病人带来的压力[1],我国立法理念也随之出现了转变,开始反思原有事后反应式司法处置模式,逐渐重视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预防工作。然而从整体立法和司法价值取向来看,我国倾向于有效打击犯罪。下文笔者将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对精神病人司法处置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
一、我国精神病人司法处置相关立法评析
对我国精神病人司法处置的规定进行梳理之后,不难发现,有关条款呈现碎片化的特征,散见于各部门法,主要有《刑法》第十八条,《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七条、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八十四至二百八十九条等,《精神卫生法》第三十至五十三条等。除了体系化构建不足之外,立法还存在用语模糊、不易操作,未对精神病人有无服刑能力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分类等问题。具体而言,依据《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实践中对此类精神病人的司法处置,与普通犯罪人适用的程序和刑罚种类并无不同,仅仅是考虑到其认知方面存在瑕疵,选择对其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现行处置方式并没有关注到该类精神病人潜在的人身危险性,对他们没有进行区分便将其投入监狱或者看守所之中,忽略其随时可能给看守和同监人员造成伤害的危险存在。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立法上并未构建起完善的精神病人司法处置制度,立法仍以事后补救和反应式处罚为主,忽视对精神病人犯罪的事前预防和监管防控,各部门法之间的规定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一)反应式处置的刑事立法理念难以适应现实需要
根据1997年《刑法》规定,只有当精神病人造成法益侵害之后,才会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司法鉴定,如果鉴定结果显示其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在必要时,才由政府进行监管。换言之,如果精神病人并未造成实害结果,政府则可以对其放任不管,甚至虽然造成了实害结果,可以“不认为是必要的”为由将政府的监护和管理责任全部推卸给精神病人的家属或者监护人。追溯至1979年《刑法》立法时,部分领导干部便错误地认为如果不在法律之中规定应由精神病人家属或者监护人进行监管治疗,会导致某些精神病人家属以此为由,将责任推卸给政府,或者放松自己对精神病人的管教责任[2]24,政府只需要在精神病人造成实害后果时才需要介入对精神病人施以惩罚。该种错误思想延续至今。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当精神病人已经造成了实害结果,并且还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时,才会对该精神病人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庞大的精神病人数,致使事后反应式的精神病人司法处置理念早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理念的变革需求迫在眉睫。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知,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821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左右,仍仅有33616元。精神病人治疗周期长,治疗费用高的现状也迫使部分家庭只能选择放弃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无法接受有效治疗的精神病人在人群中自由生活,随时会对他人人身和财产造成侵犯。为了缓解由此带来的社会安全压力,作为利维坦式的现代政府必须主动承担起对精神病人治疗矫正和社会预防的重任,处置模式也应该由被动的事后反应向主动事前预防介入,应该积极面对与解决社会问题,做到主动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而不是回避问题和推卸责任[3]169。
(二)《刑事诉讼法》与《精神卫生法》内外部存在冲突
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刑事诉讼法》内部程序规定存在冲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加了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弥补了长期以来程序法没有对精神病人司法处置问题进行规定的立法空白。然而,该法律规定在给予公检法机关较大的操作自由度的同时,并没有对违规操作规定相应的惩戒措施。除此之外,针对诸多内部程序性规定存在的冲突,《刑事诉讼法》自身也没有给予解决方式。比如说在检察院进行审查提起公诉时,没有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或者虽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人,仍以普通诉讼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据被告人的表现及案卷材料发现应对其适用强制医疗程序。此时是否应该终止一审普通程序转为强制医疗特别程序进行审理,或者继续按照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给出可以解决该问题的答案。另外,对于检察机关是否拥有要求法院转化程序的权力,以及在法院自行转化程序时,是否具有提出异议乃至抗诉的权利,法律也未明确规定[4]17。其二是《刑事诉讼法》与《精神卫生法》等规范存在外部冲突。依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对精神病人采取自愿住院的原则,然而如果当其被认定为严重精神病人,并且具有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已经实施或者将要实施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情形时,应当对其进行强制住院治疗。精神病人或者监护人如果不认同医院的诊疗结果,可以申请重新进行诊断和鉴定,结果仍与前次相同的话,监护人必须同意对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此时,监护人如果仍采取措施阻碍精神病人住院治疗,或者精神病人主动逃避并脱离精神病院拒不接受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院对其实施强制医疗。此时,监护人依据《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公安机关的行为作出裁决。此时,法院便陷入了两难境地:究竟应该如何对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行为进行认定?“法院应按照《精神卫生法》对公安机关实施强制住院治疗的合法性进行裁决,还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作出处理?”[4]24
(三)实体和程序上双重限制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
有关精神病人司法处置的规定应同时考虑人权保障和社会预防两个方面,不能偏向其一。立法理念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如上所述,自立法之初,立法者便错误地认为对精神病的监管应由家属完成,而非政府主动担责。正是基于该考虑,在1979年制定《刑法》时,并没有专门规定“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当时,许多领导干部认为,由于医疗机构配置不足,法律如果规定由政府进行强制医疗,反而会造成工作被动[2]24。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外有关精神病医学和精神病人司法处置的知识传入中国,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专家开始关注“由政府进行强制医疗”的必要性,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对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进行预防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1988年9月的刑法修改稿第十五条第一款后增加了“必要时可以由政府强制医疗”的规定。在1988年12月25日提出的刑法修改稿中基于修辞的目的,将原句改为“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并为1997年《刑法》所采用[2]192。但是,《刑法》仍然只规定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才能实施强制医疗,选择把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排除在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此时的强制医疗程序还存在另一缺陷,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专章针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出规定,长时间内出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立法空白和司法衔接漏洞。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虽着力于填补该空白,但是却进一步限制了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范围。对《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进行解构,可以发现已经实施暴力造成公共安全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只有在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时,才能够对其进行强制医疗。这也就意味着经过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限制,导致“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具备受审能力和服刑能力的精神病犯罪人、实施非暴力性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人,另外还有未危害公共安全和未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却不能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5]77。笔者认为该种做法的合理性仍有待商榷,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过于狭窄的法律规定,会导致大量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等被关入监狱和看守所,在狱中不仅难以接受专业的精神病治疗,无法有效控制病情,甚至会对同监室的人员和看守造成侵害。
二、精神病人司法处置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即使是规定完善的法律,也需要具有高素质的司法人员在实践中予以运用和实施才能发挥作用。有关精神病人司法处置的立法规定存在程序冲突、适用范围狭窄等缺陷,更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具有高度自觉性,排除办案过程中的外在压力,按照法定程序办事,自觉追求社会预防和人权保障的统一。正是由于精神病人对自己的行为存在认知和辨认瑕疵,所以才无法准确地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此时从法理角度来看理应对其施以宽容。近些年各国也开始转变对精神病人司法处置的理念,提出了恢复性司法的口号,关注精神病人的病情控制矫正和回归社会。然而立法司法理念的转变不能一蹴而就,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的不足需要得到妥善解决。
(一)司法机关选择“从重从快”的现实原因
司法实践中,诸多压力并存会迫使公检法机关选择从重从快处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维稳的政治压力。公检法三机关呈现鲜明的利益一体化现象,即作为不同的政法机关,三机关在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结成了利益联盟[6]。遇到影响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时,在政法委的领导下,公检法司机关负责人往往会提前对案件进行讨论。面对恶性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为迅速平息舆论,政法委也多会力主从重从快处罚。实践中,精神状况的司法鉴定是处理精神病人犯罪问题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经过鉴定程序认定其为无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则必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不幸的是,由于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管理、鉴定的启动等方面存在法律漏洞,该阶段也成为最容易被操纵的环节,以至于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法官无法独立地进行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的判断,不得不受到上级领导批条及党政机关意见的影响。比如在是否启动鉴定程序,是否启动重新鉴定程序,以及是否采纳鉴定意见等问题上,法官都会或多或少地接受来自上级的倾向性指导意见。若鉴定意见会给公检法机关处理案件带来阻力,则会反复要求对精神病人进行鉴定,直至获取支持其观点的鉴定意见。南通王逸泼硫酸案件中,为了确定王逸的刑事责任能力,当地政法委召集公检法机关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三次精神病鉴定的采信问题,统一认识,消除分歧[3]133。第二,社会群众的舆论压力。小范围的精神病人犯罪案件经过媒体的传播,会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不断发生的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也一直在冲击社会公众的心理底线,让他们感觉危险就在身边。除此之外,见报的案件手段很残忍,结果较恶劣,政府如果不能及时进行心理疏导,恐慌感必然会不断蔓延。群众对该案件处理结果的关注也已经转化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朴素的正义观必然希望公检法机关对造成恶果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从重处罚,若办案机关不顾民意将精神病人放归社会,很容易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不仅难以安抚被害人及民众的情绪,而且可能被认为是工作不力或者打击犯罪无能的表现,使司法公信力遭受减损[3]134。第三,被害人家属的诉访压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应刑理念,推动被害人及其家属积极寻求办案单位对被告人处以程度基本相同的刑罚。作为受害方,他们很难接受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甚至被送往精神病院进行治疗的结果。为了追求心中的正义和引起领导的关注,他们往往会不断地进行上访和抗议。此时,公检法三机关为了照顾被害人家属的情绪,会将顺利起诉、审判作为工作目标,而选择性地忽略对犯罪嫌疑人精神状态及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
(二)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司法实践存在的不足
由于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涉及的程序较为复杂,不可能在本文中一一对应进行解剖分析,因而笔者选取其在涉及精神病人刑事案件的办案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展开论述。
首先,案件侦办过程中,公安机关羁押性强制处分使用率高,移送精神健康机构治疗的措施使用率低。公安机关在面对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的精神病人时,可以采取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其直接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然而由于公安机关日常办案工作量大,内部人力资源不足,无法时刻将精力放在对精神病人的教育和治疗上,加之公安机关内部设立的安康医院数量难以满足需求,促使公安机关多选择采取羁押措施,对移送精神健康机构治疗的措施使用率低。目前,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的单位多为公安机关内设的安康医院,然而全国目前仅18省市分布24所安康医院,能够提供的住院床位7500余张,稀少的政府系统内资源必然无法满足、应对现实需求[7]。正是精神卫生资源的匮乏与精神病人治疗和康复任务繁重之间的矛盾导致悖论的出现,本来应该为精神病人康复治疗提供便利的安康医院,为了腾出床位接收新的患者,不得不将住院时间缩短,迫使尚未得到完善康复治疗的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再次成为危险源,几乎无法起到犯罪预防与疾病矫正的作用。除公安机关内部所设立的安康医院之外,我国综合性医院精神科和专门精神病院数量也十分有限。据统计,全国精神科医生仅有2万余名,精神病的床位数仅有15万余张,其中仅有20%的医生接受过专业训练[8]。安康医院无法承担起全部精神病治疗的重任,因此综合性医院和专业精神病医院理应承担部分社会责任,接收和安置部分精神病人。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事业单位也都遵循优胜劣汰的基本竞争法则,各单位均是为了利益奔忙,其更乐于接收能够支付充足治疗费用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有时只能被迫通知家庭贫困的精神病人家属或者监护人将其带回看管。
其次,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动申请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鉴定率较低。上文已经提及政治上的压力、社会公众的舆论、被害人家属的诉访压力以及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的存在,导致在实践中往往会忽视对疑似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导致鉴定率低、起诉率高的情况出现。深入分析,其原因有二:其一,检察机关在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时,往往会在政法委调节下提前介入案件的调查,进行检警联合办案,检察机关提前掌握有关犯罪的证据材料,对犯罪嫌疑人精神状态是否存在瑕疵进行初步判断。若在审查起诉前,检察人员并未发现其精神异常,并且前后供述比较稳定,此时选择不进行精神鉴定,直接提起公诉是最为经济的选择。其二,对于部分社会影响重大,危害后果严重的故意杀人伤人案件,为了实现打击犯罪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彰显国家机关对于犯罪行为零容忍的态度,检察机关便会选择着重于审查案件事实与证据情况,对案件进行快速审查起诉,以防止长时间的拖沓增加自身办案压力给本机关带来被动。除此之外,精神病司法鉴定技术还存在不确定性,不同机构所作鉴定意见会存在差异,此种不确定的鉴定意见也会增加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理的难度。对这种极可能干扰正常的刑事诉讼进程,又可能导致后续处置困难的精神病鉴定,显然不是检察机关重点关注的做法[3]97。
最后,在审判过程中,法院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认定过分依赖精神鉴定。精神病司法鉴定是判断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前提,其本不可以对刑事责任能力有无进行直接认定,然而实践中,鉴定人员实际上在行使司法权力,刑事裁判领域内司法人员专断审判权也在逐渐遭到侵蚀。国外也出现类似情况,德国Koch法官曾说,在德国事实上裁判几乎是从法官的重心移到了医生的范围,此乃必须接受之事实。笔者认为鉴定人只有对精神病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判断的权力,而精神病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在其权限范围之内[9]。《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指出,司法鉴定的范围仅仅包括解决案件时出现的某些专门性问题,并且鉴定人应该是具有专门知识和资格证书的人。换言之,鉴定人员对于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是没有权限进行判断的,即使鉴定人在鉴定意见中对精神病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给出了倾向性意见,法官也不应该直接适用而不进行独立判断。笔者认为可以将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有关精神病人所涉及的医学专业问题,由医学鉴定人进行初步判定,并在鉴定意见中提出倾向性意见;其二是有关精神病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等法律专业问题,应由法官参考鉴定意见中的倾向性意见,并借助于对案件整体事实和证据的把握,进行终局的裁决。然而实务操作中,由于司法审判人员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导致其不敢对精神病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进行判断,以此来防止出现法律适用错误时,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由此形成了对精神鉴定的过分依赖。
三、完善精神病人司法处置的若干对策
通过以上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的讨论,大致可以勾勒出我国对待精神病人刑事司法处置方式的轮廓,即强调以事后惩罚为主的处置理念,忽略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保护。笔者认为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必须始终坚持转变处置理念,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注重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刑事法、民事法和行政法之间的衔接,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充分调动国家司法与精神卫生两大体系的资源,通过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罚相结合的处置方式,力求控制犯罪于事前,实现社会预防与人权保障的统一。
(一)转变事后补救的司法理念,减少审判工作对医学鉴定的依赖
上文述及,我国反应式的处置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预防庞大精神病人群体犯罪的需求,立法理念必须逐渐实现由惩罚到惩治结合的转变。并且注意调节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减少碎片化给司法实践带来的操作不易的压力。司法审判过程中也应注意减轻裁判人员对医学鉴定的依赖度。笔者认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属于司法审判权,不能将该权力随意转让给精神医学鉴定人员。参考国内外做法,笔者认为以下三种方式可以减少司法审判工作对精神鉴定的依赖:1.引入专家辅助人,允许被告方对鉴定意见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减轻错误鉴定意见可能给审判活动带来的不良影响,使裁判解决符合天理、国法、人情,进而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除此之外,该做法还可以防止裁判者专断独行,提高判决结果的民主性和妥适性,增强民众对判决的可接受度。2.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解决机构。比如加拿大的审查委员会。刑事审判中,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时,法院将会面临三项选择:有条件释放、绝对释放和收容于精神病院。如果要作出有条件释放和收容于精神病院的决定,则应接受专业审查委员会评价[10]。该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由副总督任命,人数至少为5人,主席应是适合的法官担任,且至少应包括一名具有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已经根据省的法律取得了从业资格的精神病医生[11]。笔者认为按照该模式组成与各级法院对应的独立第三方解决机构,可以缓解精神鉴定人员与司法审判人员之间的冲突,实践中也便于操作。3.设立精神卫生法庭或者合议庭,引入拥有精神医学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在我国,针对特殊人群设立专门业务法庭已有先例,如少年法庭。而专业精神卫生法庭的设立在国外也早已付诸实践。如美国,截至2008年,美国精神健康法庭已经超过了150个,还有更多的专业法庭在建设中[12]。笔者认为精神病人犯罪问题涉及多学科知识,法官仅依靠法学知识,并按照普通诉讼程序处理精神病人犯罪问题,会导致精神病人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受到忽视。在现行法院系统内设立精神卫生法庭,根据精神病人的病情轻重有选择地展开审判活动,可以提升裁判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拥有司法裁判权的法官本身就掌握法学和精神医学相关知识,也可以减轻对精神鉴定的依赖,保证法官敢于遵循内心确信进行判决。退而言之,若设立专门业务部门存在程序上的难题,我们仍可以在不变动现有体制的模式下,有选择性地引入拥有精神卫生医学知识的专业人才作为人民陪审员,积极推动他们参与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精神病人精神状况等问题向审判长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合议庭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出裁决。
(二)衔接民事与刑事程序法,构建民事强制住院制度
《精神卫生法》指出对具有人身危险性(危害自身或他人)的精神病人,可以对其进行强制性医疗,有学者称之为民事强制住院制度[13]1291-1305。此制度适用于精神病人已经表现出人身危险性,尚未造成实害结果的情形,然而该制度容易同刑事法律中的强制医疗程序相混淆。依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可知,目前我国民事强制住院制度采用“精神科医生决定或者鉴定+诉讼救济”的模式[13]1291-1305。笔者认为不应该授予不具有独立性的精神科医生以决定精神病人强制住院的权力,民事强制住院制度与普通病人住院治疗并不相同,其涉及精神病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更涉及国家的警察权与监护权等公权力。该项权力的行使必须掌握在独立公正裁决的人员手中,而精神科医生多依附于医院,独立性较弱,甚至会出现为了获取高额的治疗费用,作出不利于精神病人而有利于精神病院的医疗诊断。因此必须构建完善的民事强制住院制度,力求与刑事强制住院制度相接轨。笔者构想应将决定民事强制住院的权力收归于法院系统,用完善的诉讼程序保障精神病人权利。遇有紧急情形时,可以授权公安机关直接采取约束性措施,但是必须在法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对应否采取强制医疗作出裁决。而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可以按照精神病人的危险性程度等对其进行分流,一部分触法精神病人进入刑事程序,对其依照刑法定罪处罚;另一部分仅被分流至民事程序,若满足《精神卫生法》等要求,则将其移送至精神卫生机构,强制接受一定时限的治疗。
(三)加大对精神卫生的支持力度,建立社区康复服务机制
政府要实现犯罪预防的目标,应将更多关注放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上,帮助消除强势和弱势阶层的对立。单从精神病人犯罪预防角度来看,政府应增加精神卫生财政支出,加大对精神卫生医院的建设投入,努力实现公安系统安康医院与社会综合医院及专业精神卫生医院协调配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医院、家庭和社区三级联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政府应增加精神病人治疗专项资金的拨付,并且对该资金的使用进行全流程监督和控制,一旦发现贪腐行为的存在,坚决给予严厉的处罚。同时,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和城乡收入差距,应将政策适度向精神卫生建设水平低下的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其二,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建立社区康复的服务机制。现今我国对精神病人的司法处置仍以惩罚为主,一旦涉及犯罪且不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必然会被投入监狱或者看守所执行自由刑。然而,该做法无疑会使精神病人的病情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矫正,即使其未在服刑期间对看守或者同监犯人造成侵害,刑满之后复归社会也会成为隐患,如此一来,精神病人犯罪问题不仅未得到控制,甚至可能会由于看守所或者监狱里存在交叉感染等现象,使本可以通过治疗改善病情的病人的危害性增加。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西方经验,建立起专业的社区康复体系。模拟社区由志愿工作者、精神康复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创造,其主要目的是训练精神病人社会生活必备技能,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为精神病人重新回归社会奠定基础[14]。对于部分已经实施了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其接受适当的精神医疗之后,应对其病情定期进行评估,如果病情已经改善并且满足进行社区康复的条件,应该将其送入模拟社区,进行回归社会的恢复性治疗。实际上,早在2009年北京海淀区精神病防治院便已经建立了意大利模式的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居住之家——“玫瑰园”。在“玫瑰园”中,精神病人各自承担各自的工作,并定期轮换,并且充分挖掘每一名精神病人的特点,使病患者增强生活自信心[5]247。
总之,作为有认知瑕疵的特殊犯罪主体,刑事司法程序中对待精神病人应更注重对其权益的保障,通过实体和程序双重限制,防止国家公权机关恣意办案。我国立法司法过程中存在的上述缺陷,显露出现存制度存在的不足。然而,法治的发展要求政府应在该问题上转变思路,采取积极作为的姿态应对精神病人犯罪控制和矫正预防问题。关注精神病人权利保障,立法时就应尽可能构建起用语明确、可操作性强的法律体系。司法过程中减少对医学鉴定的依赖,赋予被告方平等的诉讼权利。执法时减少羁押刑适用,尽可能将精神病人送往专业机构接受治疗。当然,与之相配套,国家必须增加精神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促进精神卫生医疗系统的完善,为建立社区康复和民事住院制度奠定基础。最终要求政府在对精神病人处以刑罚的同时也关注对其病情的控制,实现人权保障和犯罪预防的有机统一。
[1]李志强.研究显示我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EB/OL].http: //news.Xinhuanet .Com / legal/2010-05/29/c_12155254.htm.
[2]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贺小军.精神病人刑事司法处遇机制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杜志淳,王永杰,郭华.强制医疗司法鉴定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5]赵春玲.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
[6]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0-240.
[7]陈卫东,程雷,孙皓.司法精神病鉴定刑事立法与实务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231.
[8]王牧.犯罪学论丛(第六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462.
[9]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304-305.
[10]Steller.Special Study on Mentally Disordered Accused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85-559-X)[EB/OL].http://www5.Statcan.Gc.ca/olc-cel/olc.action?objId=85-559-X&objType= 2&lang=en&limit=0.
[11]李娜玲.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39.
[12]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Mental Heath Courts Program[EB/OL].http://www.doc88.com /p -9139550147433.html.
[13]郝振江.论精神障碍患者强制住院的民事司法程序[J].中外法学,2015(5).
[14]陈强,黄国光.社区综合干预对重性精神病患者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影响[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08(6):971.
(责任编辑:刘芳)
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JudicialDisposalofMentalPatientsinChina
ZHANG Yong, LI Zi-ya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China)
In the course of dealing with criminal cases of mental patients, judicial department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ubsequent punishment when ignoring precaution.To develop criminal legality, the judicial departments should transform judicial philosophy, face the problem of criminal controlling and precaution actively,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dual value of fighting crime and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Besides, they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riminal substantive law an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other laws.By coordinating judicial system and mental hygiene system, they can take actions by combining the precaution and the subsequent punishment so as to unify social prevention and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
mental patients; judicial disposal of mental patients; criminal capacity of mental patients
2017-09-05
张 勇(1973— ),男,河南许昌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李紫阳(1994— ),男,河南永城人,华东政法大学2016级法律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D914
A
1008-2433(2017)06-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