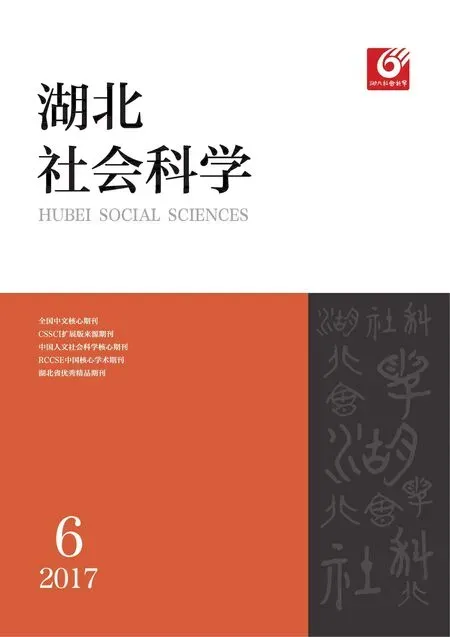九尾狐从祥瑞到妖异转变的思想内涵
——以汉唐为中心的考察
张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人文视野·文学
九尾狐从祥瑞到妖异转变的思想内涵
——以汉唐为中心的考察
张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九尾狐作为承载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其在先秦两汉时依托“长生”、“谶纬”等思想成为祥瑞的高级代表,以此宣扬统治者道德品行及政治行为合乎天意;从唐代开始,九尾狐逐渐沦为民间崇拜中的“妖神”,唐代之后进一步退化为受人贬损的“妖物”。九尾狐走下神坛,其地位发生根本改变,既是中国古代祥瑞思想变化的缩影,又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民间信仰与世俗文化发展的证明。
九尾狐;狐;祥瑞;妖化;内涵;转变
在人类意象与观念的思维发展及演变历史中,“狐文化”可以看作是人类对自然界各种存在的感知与认识、亲和与排斥等方面的一种体现。自古以来,狐在形象以及人们的观念上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和审美等方面的内涵。在史书记载及文学描绘中可见,狐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从祥瑞之兽到妖兽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九尾狐,作为一种特异性的存在,更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代表。①狐在中国古代早已超越其本身的生物性,成为思想文化中多重观念的载体和多元意义的象征。而在中国古人的意识和想象中,狐类中有一种形貌独特的“成员”,即九尾狐。九尾狐因其拥有“九条尾巴”的显著外表,成为“狐文化”中最显眼的符号。九尾狐脱胎于狐类,从九尾狐成为国家政治祥瑞到沦为妖类的演变历程中,也将“狐”背后蕴含的文化概念释放到极致,九尾狐成了“狐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范例。至今学术界关于九尾狐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李剑国的《中国狐文化》粗线条地梳理了各历史时期的狐,但并没有突出九尾狐的存在与内涵;李炳海的《从九尾狐到狐媚女妖——中国古代的狐图腾与狐意象》侧重于从图腾崇拜的角度分析九尾狐;李淼的《从瑞兽到精怪——浅析九尾狐地位更迭的原因》和蔡堂根的《九尾狐新解》立足于文学层面分析了九尾狐的演变历史。总体来说,论及九尾狐的篇幅并不多、对其的研究也不太充分。通过文献记载的考察可以发现,历史上人们对九尾狐的形象描绘以及所赋予的观念内涵方面的变化是很有代表性的,九尾狐在先秦两汉时被视为祥瑞之物,但唐代之后其形象发生重大改变,成为妖淫之物的代表。九尾狐所代表的内涵变化之大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都是罕见的,梳理这种变化的历程,也是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另类透视。
一、瑞兽——九尾狐的祥瑞化
关于九尾狐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在《南山经》中有:“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之不蛊。”[1](p4)郭璞注此兽即“九尾狐”。在《海外东经》中又有:“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1](p95)《大荒东经》也记载:“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1](p120)可见,在《山海经》中只是简单地把九尾狐当作一种野兽来记载。随着历史的发展,九尾狐在“长生”和“谶纬”等思想的“裹挟”下,登上了祥瑞的舞台。
九尾狐因其特殊的外表被注入了丰富的思想文化与观念内涵。《白虎通义》中记载“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2](p146)“九尾”被当作子孙繁息、后代昌盛的象征之意。
“九”在中国古代既代表数字的极限,又有强烈的思想文化意味。《黄帝内经》记载:“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3](p45)“九”一直被用来形容最深的程度,[4](p221)并且“九”又与“久”谐音,与皇权产生密切联系,蕴含了封建礼仪因素。九尾狐之“九”除了表示最高的数字外,逐渐蒙上了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的色彩。按中国古代象数与五行的推演,“九”也被视为最大的阳数,[4](p221)代表“极阳”之意。而“阳”在古代思想文化中多指男性,“九”、“阳”也就包含了生殖崇拜的含义。《白虎通义》中以“九尾”对应“九妃”而象征帝王子嗣绵延,皇权永故而万世昌盛。九尾狐不仅有“极阳”的生殖崇拜力,其“九尾”的形象也与古代星象之东方苍龙星的尾宿有关,“尾”本就是星宿之一,如《史记》记载的“尾为九子,”[5](p1298)“尾宿”本身即象征多子。
此外,在现已发现的汉画及石刻像中,九尾狐的形象多次出现。常有九尾狐、蟾蜍、玉兔和三足乌并伴于西王母身边的构图。西王母在西汉时期被视为长生之神,九尾狐被雕刻在其旁,[6](p151)表明当时的人们也将其纳入了长生信仰。九尾狐以其“九尾”象征子孙后代繁盛的意义,与汉墓壁画中伴于西王母身侧的画像在此形成了思想上的交汇。现世的九尾狐代表子孙绵延,往生的画像上亦有“长生”意味,九尾狐在此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当时人们对长生的追求,以及通过繁衍后代使自我生命在另外一个个体上延续,现实意义上的长生不老难以实现,只能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我生命的延长。九尾狐之“九尾”象征后代子孙繁多继而实现自我生命延续,故九尾狐能成为长生之神西王母身侧之物,或许此为原因之一。[7](p52)
九尾狐在后世成为祥瑞之物,与狐本身被视为“德兽”有关。《子夏易传》中记载:“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8](p76)其明确将“获狐”作为吉祥的征兆。后来这种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内涵被进一步发挥,先秦典籍《礼记·檀弓上》云:“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9](p124)唐代孔颖达疏曰:“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9](p124)屈原《九章·哀郢》中提到“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10](p506)唐代白行简《狐死正丘首赋》中也写道:“其心怀土,望故处以增悲;惟首正丘,聊向隅而表恋。”[11](p617)这些记述是在说明,狐狸虽死,而其依然正首向着自己的巢穴,这种行为在儒家看来是不忘本、显仁恩的象征之举。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更是将狐赋予“三德”,称:“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12](p206)析而言之,“其色中和”与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相符合,即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3](p54)故狐被儒家视为和谐之物。正像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在形象上狐狸身体纤细,狐尾多蓬松丰实,其前小尾大暗合儒家井然有序的尊卑之道。[14](p22)正是由于“狐群体”被认为具有“狐死正首丘”和“三德”等儒家道德的意味,在此背景下具有特殊形貌的九尾狐也向“道德化”和“祥瑞化”又迈进了一步。
九尾狐成为祥瑞之兽的象征,与符瑞、谶纬之说关系密切。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祥瑞思想,如《诗经·周颂·载芟》记载:“至诚感物,祥瑞必臻。”[15](p2005)这种祥瑞观与九尾狐初步结合,便有了如下的一些记述,诸如传世的《竹书纪年》记载:“(帝杼)八年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16](p11)又如《田俅子》记载:“殷汤为天子,白狐九尾。”[17](p31)还有《逸周书》记载周成王大会诸侯与四夷,青丘国贡献九尾狐之事。[18](p245)可见九尾狐被当作吉祥的象征,并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汉代谶纬思想盛行,大肆宣扬符瑞学说。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吉祥含义的九尾狐被各种谶纬书籍拿来附会,《孝经援神契》记载了“德至鸟兽则狐九尾,”[19](p701)《春秋运斗枢》言“机星得则狐九尾,”[19](p487)九尾狐俨然成为盛世到来、明君出现的吉兆,在原来的道德含义之外又增添了政治内涵。九尾狐作为政治祥祯的形象还被东汉赵晔用到了禹身上,《吴越春秋》对此作了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庬庬。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20](p96-97)在这里,九尾狐被视为明君出现的吉兆,和帝业、国家等政治元素结合在了一起。东汉的《白虎通义·封禅》有云:“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2](p144)其中明确将九尾狐作为太平盛世的吉兆和上天意志的符号表达,也是统治者道德品行及政治行为合乎天意的证明。在道德内涵和政治内涵的结合下,九尾狐的祥瑞地位达到高峰,被官方重视和宣扬,成为显示王者之兴和承天顺民的标志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而九尾狐的王道内涵却表现的越发强烈。曹植的《上九尾狐表》即云:“黄初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鄄城县北,见众狐数十首在后,大狐在中央,长七八尺,赤紫色,举头树尾,尾甚长大,林列有枝甚多。然后知九尾狐。斯诚圣王德政和气所应也。”[21](p235-236)可见人们在乱世中仍然推崇九尾狐,愿意相信九尾狐的王道色彩。而且,各方政治势力都企图以祥瑞来标榜其统治的合理和兴盛,各地为迎合统治者的意图也纷纷献瑞,所以史书中以九尾狐作祥瑞的记载层出不穷,比如:
鱼豢《魏略》记载:“文帝受禅,九尾狐见于谯都。”[22](p4030)
《宋书·符瑞中》记载:“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甲午,九尾狐见鄄城,又见谯。”[23](p803)
《魏书·灵征志》记载:
“十年三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王者六合一统则见。周文王时,东夷归之。曰,王者不倾于色则至德至,鸟兽亦至。
十一年十一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
孝静天平四年七月,光州献九尾狐。
元象元年四月,光州献九尾狐。
兴和三年五月,司州献九尾狐。”[24](p2930-2931)
根据以上从鱼豢《魏略》中因文帝受禅而现九尾狐,到《魏书·灵征志》中多次献九尾狐的记载,可见“九尾狐祥瑞化”的兴盛。一方面,曹魏初期,为显示曹丕称帝的“天命所归”,以九尾狐为代表的祥瑞之物纷纷出现,与谶纬之学在当时的兴盛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魏书·灵征志》记载的数条关于“九尾狐”的史料,和北魏拓跋政权入主中原有关。[7](p53)原本为草原游牧部落的拓跋鲜卑,在不断南迁的过程中汉化逐渐加深,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汉化更为彻底。作为“中原文化”一部分的“祥瑞”之说又被拿来附会于拓跋政权,以九尾狐为代表的“瑞狐”文化在孝文帝时期大量出现,为北魏政权在中原的统治提供支持。
除了各地献瑞外,当时的人们针对“九尾狐”也有其他论述:
萧统的《昭明文选》有载:“昔文王应九尾狐而东夷归周。”[25](p715)《宋书》卷二十八记载:“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24](p803)《太平广记》卷四四七《瑞应》记载:“九尾狐者。神兽也。其状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国。音如婴儿。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气。及蛊毒之类”;[26](p3562)《艺文类聚》卷九十九记载:“王者不倾于色则(九尾狐)至”、“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则见,”[27](p1715)这些都是认可其作为瑞兽的“历史”记述。东晋的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涉及九尾狐的地方也都加入了祥瑞思想。郭璞注《山海经·大荒东经》“青丘国九尾狐”称:“太平则出而为瑞也。”[1](p120)他所作的《山海经图赞》云:“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则见,出则衔书。作瑞周文,以標灵符。”[28](p38)明确指出九尾狐是周朝兴盛的祥瑞。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尾狐虽然继续充当祥瑞,但这时期不少志怪小说纷纷将狐当作妖类来描写,也开启了九尾狐妖异化的前奏。
九尾狐的“祥瑞化”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达到鼎盛,各种记载层出不穷。入唐以后,九尾狐随着谶纬祥瑞之说的没落也经历了巨变。唐朝时期随着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多元的思想和文化交相辉映,在当时开明的政治氛围下,整个社会呈现出的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精神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九尾狐等祥瑞之说在唐朝变得更加弱化,在国家政治领域已不占主要地位。九尾狐所象征的国家级政治意义,随着其在政治领域的淡化而减弱。于是,九尾狐走下神坛,逐渐演变成了另一个极端。
二、妖兽——九尾狐的转变
九尾狐从先秦时就是吉祥的象征,在秦汉时期谶纬祥瑞观念盛行的背景下,被提升到了神圣的地位,魏晋南北朝特殊的历史又使九尾狐频见于史书,不过这也是其最后的昙花一现。唐代之后,九尾狐走下神坛,由代表国运兴隆的瑞兽转而成为被人厌恶的妖物。
当九尾狐带着兴旺家国的光环走上祥瑞“殿堂”时,普通的狐类却已经开始了妖化的历程,狐中绝大部分被视为妖类,成为人们憎恶、惧怕的对象,与九尾狐的神圣地位相去甚远,同时也为九尾狐沦为妖类埋下伏笔。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指出:“狐,妖兽也,鬼所乘之。”[12](p206)由此,以狐为妖的观点逐渐显露。[29](p224)到魏晋南北朝时,关于狐妖的记载也多了起来。如干宝的《搜神记》中提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30](p123)郭璞的《玄中记》记载:“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盖魅,使世人迷惑失智。”[31](p492)葛洪的《抱朴子》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32](p36)如此这些,都明确指出了狐整体的妖化。《魏书·灵征志》中的京师事件、《洛阳伽蓝记》中“孙岩妻”事件和《北齐书·后主纪》中的邺城、并州事件等等,①此三则记载皆为狐妖截人发。详见《魏书·灵征志》《洛阳伽蓝记·法云寺》和《北齐书·后主纪》。也都记载了狐狸的幽冥之力。唐代传奇小说盛行,其中很大部分与狐妖有关,如《任氏传》《古冢狐》和《代州民》等篇,可见狐的妖化在彼时已经深入人心。
入唐以后,狐作为民间信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张鷟所著的《朝野佥载》记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33](p167)《广异记》也记载了开元时期河北一地的“狐神”之事,当地村民言:“此有灵袛,好偷美妇,”[34](p200)可见狐神虽被人们视为神灵,但其属于妖神,与正常神袛有很大区别。前文已述,由于狐类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以妖化和道德化并行,故唐人狐崇拜中存在妖异成分并不奇怪。
但唐代狐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天狐崇拜,”[35](p115)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诺皋记下》中记载:“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洞达阴阳。”[36](p144)对九尾狐的崇拜恰是唐代狐信仰的主要部分,上天入地、通晓阴阳的九尾天狐即是这种信仰之力的来源。九尾狐神通广大,早已超出普通狐类,当这种力量和人们希望生活稳定、富足康乐的理想结合时,九尾狐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人和九尾狐可以直接对话,即使九尾狐的定位发生变化,更潜在地改变了九尾狐的角色。九尾狐作为王业兴盛、国泰民安的象征,属于国家政治层面的庄严角色。作为祥瑞的九尾狐充满政治性、与生活相游离。对民众来说,作为民间信仰的九尾狐是植根民间、生动具体的。因此,以民间信仰形式快速流传的九尾狐,成了大众文化的共识,某种程度上也冲淡了其原生含义。
作为唐代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拜九尾狐”的行为是民间多数人都能负担得起的,②前文所引张鷟《朝野佥载》中的记载表明,唐人对狐神的供奉都是普通之物。也更能反映九尾狐信仰“民众化”和“市井化”的特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渴望与神明站在平等立足点进行交流的自信,并且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操纵”神明。民众对菩萨、仙人的信仰是建立在善和光明基础上的,对本脱胎于妖神的九尾狐信仰则能够承载欲望、利益甚至不可告人的目的,民众以善良、符合传统道德的一面祈求神灵,某些不符合传统道德却又乐于实现的诉求转而祈求九尾狐神。民间的九尾狐信仰与其他信仰互补,构成信仰体系有机整体的同时,也为九尾狐的进一步妖化打下了基础。
唐代各种传奇小说中多有普通狐类作祟人间的记载,而对九尾狐这方面的记录却很难见到。和其他狐类相比,九尾狐的妖化过程来得晚些,[35](p150)其头顶的光环在宋代人的观念中最终黯淡。宋代的不少记录已经直接将九尾狐当作可憎的妖物,如北宋田况的《儒林公议》中记有“时人目为九尾狐,言其非国祥而媚惑多歧也。”[37](p9)赵令畤的《侯鲭录》卷八中有“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38](p117)这些记载明确指出了九尾狐在宋代已经成为人们贬损的对象,而不再是原来神圣的瑞兽,反映出当时人们脑海中对九尾狐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九尾狐妖化后尤以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的苏妲己形象最为人所熟知,晚清时的小说《九尾狐》高度概括了其妖化特性,“盖狐性最淫,名之九尾,则不独更淫,而且善幻人形,工于献媚,有采阴补阳之术,比寻常之狐尤为厉害。”[39](p1)九尾狐的形象彻底堕落,完全成了妖物,其祥瑞之说不再见于记录并逐渐隐于历史中。
三、余论
在历史上,九尾狐从人间祥瑞变为民间信仰中的妖神,进而蜕变成被人憎恨的妖物,其地位更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被人为地赋予了多重含义的九尾狐,再也无法占据神圣、庄严的瑞兽地位而最终沦落入人们的憎恶中。九尾狐从瑞兽到妖兽的变化,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阐述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的文化差异比不同的宗教信仰者之间的教派差异更为深刻。那么,又如有学者所论述的那样,中国古代的九尾狐信仰与“士大夫阶层通常用以作为思想载体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40](p111)作为民间崇拜的九尾狐信仰并不属于儒家正统文化,但却能成为超社会阶层的共识,在“正统文化”占主导的古代顽强发展,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世俗文化、市井文化发展的表现。
[1]山海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班固.白虎通[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郝易整理.黄帝内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张德鑫.数里乾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朱存明.汉画像之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7]王守亮.唐前瑞狐文化的演变与兴衰[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1).
[8]卜商.子夏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1.
[9]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黄侃经文句读.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屈原.屈原集校注[M].金开诚,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11]白行简.狐死正丘首赋[A].文苑英华:卷一三四[C].北京:中华书局,2003.
[1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3]论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4]任志强.中国古代狐精故事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15]毛亨著,郑玄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音释,朱杰人、李慧玲整理.毛诗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6]竹书纪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田鸠.田俅子[A].稽瑞[C].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逸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赵在翰.七纬[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0]赵晔.吴越春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1]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2]鱼豢.魏略[A].太平预览:卷第九百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5.
[23]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5]王褒.四子讲德论[A].昭明文选:卷五十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26]孙柔之.瑞应图[A].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七[C].北京:中华书局,1986.
[27]孙柔之.瑞应图[A].艺文类聚:卷九十九[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28]郭璞.山海经图赞[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29]胡堃.中国古代狐信仰源流考[J].社会科学战线,1989,(1).
[30]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1]郭璞.玄中记[A].鲁迅全集:古小说钩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2]葛洪.抱朴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3]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4]戴孚.广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5]李剑国.中国狐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6]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7]田况.儒林公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8]赵令畤.侯鲭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9]江荫香.九尾狐[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40]范立舟.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03,(5).
责任编辑 邓 年
K203
A
1003-8477(2017)06-0125-05
张程(1989—),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