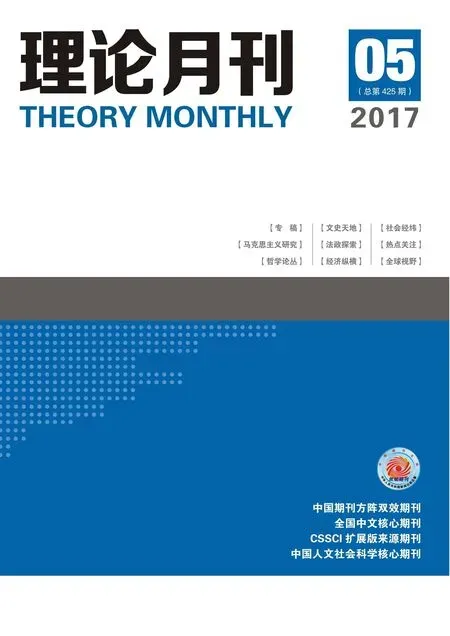从审美之“趣”到娱乐之“趣”
——晚明小说观念中的趣味化研究
□闫娜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从审美之“趣”到娱乐之“趣”
——晚明小说观念中的趣味化研究
□闫娜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在晚明特定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潮影响下,“趣”这一审美范畴逐渐失却了其原本的空灵超俗之味,沾染了不少世俗逐乐的自适之味,由审美之维滑向了娱乐之维,这个趋势在晚明的小说观念中尤为显著。晚明时期,越来越多的文人敢于正视自己的享乐需求,在此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小说评点也开始追求好玩和有趣的特点。晚明的小说序跋也集中反应了当时的小说创作者和阅读者对于小说的态度和小说功用的看法。不同于小说评点中对于趣味不加掩饰的追求,序跋的情况较为复杂一些,其对小说所具有的趣味性观念在表述上有肯定,有否定,有坦而言之,也有王顾左右而言他的。
晚明小说;审美之趣;娱乐之趣;小说趣味化
“趣”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据统计,以“趣”为基本语义衍伸的审美语汇多达上百种,如兴趣、情趣、理趣、旨趣等,这些涵义互为生发构成一个庞大的枝根交错、筋络相连的“趣”范畴。先秦两汉时,“趣”的涵义为趋向、趋附、催促、催办等,基本不涉及审美的意义。魏晋时延伸至人物品评中逐渐有了审美的意蕴,唐代开始“趣”逐渐被抽象至诗文品评的专门用语,而宋代一般被认为是“趣”作为审美范畴的成型期。至晚明时“趣”不仅频繁地出现在各类诗论、词论著作中,同时也被广泛地用于曲评曲论以及小说评点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特定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潮影响下,“趣”这一审美范畴逐渐失却了其原本的空灵超俗之味,沾染了不少世俗逐乐的自适之味,也即由审美之维滑向了娱乐之维,这个趋势在晚明的小说观念中尤为显著。当时不少文人主动介入小说的评点中,评点者既有文人、书商,也有官僚或半文半商等多重身份,使得其时的小说评点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雅文化主动向俗文化的一种渗透。这种渗透的动力就是主流文化体制近乎解体之下娱乐思想的张扬和凸显。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娱乐思想影响之下晚明的小说评点对于趣味化的追求和呈现。正如英国的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说过的:“批评界在感受着文学形式的重大变化的同时,也感受着意识形态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无不体现着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1]
1 晚明小说评点的趣味化呈现
正统文学观念中对于小说趣味化阅读呈戒备之态。“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中论·务本论》中认为“短言小说之文”与“丝竹歌谣之和”“雕琢采色之章”“辩慧切对之辞”“射御书数之巧”“俯仰折旋之容”一样都会迷惑人的情志,妨碍人追求正业,所以奉劝君王要远离这些娱乐之事[2]。这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于“玩物丧志”的戒备和警惧,所以自然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玩乐性质也抱着先天的戒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小说的娱乐功能也表示了担忧和否定,他说:“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己,则髠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3]他认为小说不仅与世无补,而且沉溺其中还会造成“德音大坏”的不良影响,也即“谬辞诋戏,无益规补”“空戏滑稽,德音大坏”[4]。由此也可知,晚明时期公然在小说评点中追求趣味和娱乐就是一种出离正统的解构和叛逆之态。晚明时通俗文化市场逐渐兴盛起来,加之意识心态的松弛以及自适自乐的“心学”思潮,越来越多的晚明文人敢于正视自己的享乐需求,文学的娱乐作用被公然提倡。在此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小说评点也开始追求好玩和有趣的特点。
晚明小说评点中对于“趣”的追求集中体现了评点者对于小说娱乐功能的肯定,而评点者对“趣”事的关注和表现也体现了他们正是以一种玩乐的态度看待小说。以李贽为例,李贽曾评点了多部通俗小说,因其在晚明的盛名,还出现了大量托名李贽的小说评点之作。他的焚书中收有其对《琵琶记》《拜月亭》《玉合记》《水浒传》《西厢记》《红拂记》《昆仑奴》等作品的评论文章。李贽专门的批评著作,如现存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卓吾先生批幽阁记》等集中体现了他的小说评点思想。这些评点具有较强的趣味性,评点者格外关注小说中的趣人趣事,并以谐谑调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李贽在小说评点中追求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活享受。他曾说过:“《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窜改得更妙。”[5]晚明的士人普遍更加关注自身的感受,追求愉悦和自适,李贽也曾坦言自己评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他曾说:“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每开看便自欢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6]李贽曾称赞过《水浒传》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施耐庵、罗贯中,真神手也!摩写鲁智深处,便是个烈丈夫模样;摩写洪教头处,便是忌嫉小人底身分。至差拨处,一怒一喜,倏忍转移。咄咄逼真,令人绝倒异哉!”[7]在李贽的评点用语中,“快心”“快活”“快乐”“绝倒”等词频繁出现,体现出李贽在阅读评点中对于快乐的执着追求。追求快乐契合了人性中趋乐避苦的天性,概观李贽的评点更是如“活神仙”一般一挥而就、酣畅淋漓。
在具体的文本评点中,评点者也对好玩、有趣的情节颇为关注,如叶昼托名李卓吾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中对其中第三十二回《平顶山功曹传信莲花洞木母逢灾》的评点。此节中有关于猪八戒对着石头自言自语的情节:“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甚么山?我若说是泥捏的,土做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哩,若讲这话,一发说呆了。”[8]一个呆呆傻傻又冒着天真可爱的猪八戒形象跃然纸上。还有猪八戒希望妖怪手里没有自己的画像,这样就抓不住自己,于是他在庙里祈祷说:“城隍,没我也便罢了。猪头三牲,清蘸二十四分。”[9]此两处叶昼都评以“趣”字。可爱萌呆的猪八戒忘了自己便顶着一个猪头,却发誓诅咒要以猪头祭祀兑现承诺,让人不由失声而笑。叶昼借用李贽的“画工”与“化工”之说,认为这里便是化工之笔,“描画孙行者顽处,猪八戒呆处,令人绝倒。化工笔也。”(第三十二回回批)八戒因了“呆”才变得有“趣”,除了“呆”八戒还“真实”,他毫不隐瞒自己的欲望和私心,这与李贽所倡之“童心”说也是契合的。“趣”这一审美范畴无论是在诗歌领域还是小说评点之中都逐渐由空灵之境走向世俗之趣,八戒之“趣”正在于他的自然欲望的真实流露以及毫不掩饰的傻气和呆气。“趣”其实就成了好玩,所以正是这种以文为娱的心态解构了原本如山中之光、水中之色的空灵超脱之“趣”。
在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水浒传》第五十三回的回评中,叶昼曾明确提出一个批评标准:文章“当以趣为第一”。他写道:“李和尚曰:有一村学究道:‘李逵太凶狠,不该杀罗真人;罗真人亦无道气,不该磨难李逵。’此言真如放屁,不知《水浒传》文字,当以此回为第一试看种种摩写处,那一事不趣,那一言不趣?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又曰:罗真人处固妙绝千古,戴院长处亦令人绝倒。每读至此,喷饭满案。”[10]此处明确指出“趣”的艺术效果要远比小说的真实性重要,“趣”是天下文章最终的评判标准,同时这里涉及了小说的“虚”“实”关系,只要小说所塑造的人物能让人觉得有趣,且不脱离“趣”所追求真实自然之境,便是好的,更不必“实有其人”了。评点者抱着求“趣”的心态发现的也是与此心态契合的“趣人”“趣事”。评点者与阅读和批评活动中也享受了“趣”所带来的畅快淋漓的快乐,以至于“喷饭满案”。晚明文人在阅读中也坦然分享这种快感,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里中有好读书者,缄嘿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异哉!卓吾老子吾师乎?’客惊问其故,曰:‘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11]
评点不仅在评点中主动求“趣”寻“乐”,而且还常以诙谐、嘲谑之口吻进行批评,这就可视为一种毫不在乎的玩世不恭之态了。原本严肃认真的事首先在批评家那里被调侃了,这种轻松娱乐的基调必然会传给阅读者,从而为阅读增添娱乐消遣的色彩。如《李卓吾先生批评古本荆钗记》第三十八出的出批这样写道:“余笑谓‘道士不宜见夫人’。客曰‘不妨,近日和尚且见太夫人矣’。相与绝倒。”[12]在《李卓吾先生批评洗纱记》的第二十三出“迎施”中,“刘泼帽”一曲所唱:“娘行聪俊还娇倩,江东万马千兵,你立功异域才堪敬”,评点者将“江东万马千兵”加以圈号,还煞有介事的评为:“要思胜万马千军的是慈东西?”[13]在第四十四出“治定”的出批中,评点者继续写道:“范大夫载此大将军而去,恐此将军以伐吴手段再伐越耳。但范大夫自身亦当保重,危哉,危哉。客曰:‘渠当再嫁之河伯耳。’余曰:‘河伯独不怕死乎?’相对一笑。”[14]评点者假设有客与之对话,共叙调侃之语,让人哑然失笑。
2 晚明小说序跋的“趣味化”追求
晚明的小说序跋也集中反应了当时的小说创作者和阅读者对于小说的态度和小说功用的看法。不同于小说评点中对于趣味的直接和不加掩饰的追求,序跋的情况较为复杂一些。因为古人实际的想法和书面的表达有时并不一致,在涉及文学趣味化追求这一有悖于正统政教文治的文学观念面前更是如此,所以对于小说所具的娱乐性和趣味性观念在表述上也是有肯定,有否定,有坦而言之,也有王顾左右而言他的。
很多晚明文人不避讳在小说阅读中体验的快感,他们更注重真实的自我感受,对人性中的趋乐避苦也不加掩饰,真是真了,但这种真实消解了他们人生中的某种需要负重和担当的东西。袁宏道曾提及:“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及举《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15]。在求真求乐的思潮影响之下,文人普遍在阅读中追求情真有趣的自适感,化名临海逸叟的晚明文人曾述及,“主人取将竣之帙于手中,一展卷皆天地间花柳也。花红柳绿,飘拂牵游,即老成端重之儒,无不快睹而欣焉。乃知老成端重,其貌尤假;风花雪月,其情最真也。人心一天地。春夏秋冬,天地之时也则首春,非春不足以宰发育收藏之妙;喜怒哀乐,人心之情则鼎喜,非喜无以胚悲愤欢畅之根。天地和调,则万物昭苏;人心悦恺,则四体睟盎。风光艳丽,不独千古同情,天地人心所不可死之性理也。夫小道可规,职此故耳。况《秋波传》《诗媒记》《红梅》《桃花》梨园盛传,幽香喷人,宇内融融,兹帙可媲而美焉者。倘谓淫邪贼正,视为污蠢之物,桑间濮上,宣尼父何不一一笔削去之,其中盖有说焉……虽然,经目者以之适情则可,以之留情则不可。”[16]
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舍德与功又何足言者!世有能言之士,上不得坐而论道,谋王断国;下不得总览人物,囊括古今,修辞赋之业,而第猥杂街谈巷语,以资杯酒谐谑之用,其言可谓不遇矣……于是使客座为悠谬之谈,鼓掌捧腹以耗磨雄心,而延永日[17]。
——许维桢
余家所蓄杂说剑客甚夥,间有慨于衷,荟撮成卷。时一展之,以摅愉其郁[18]。
——王世贞
在贤者知探其用意,用笔不肖者,只看其妖仙冶荡,是醒世之书,反为酣嬉之具矣[19]。
——戏笔主人
以下四则也是对小说娱乐性的肯定以及趣味性阅读体验的描述:
不堪复读《离骚》,计唯一笑足以自娱,于是争以笑尚,推社长龙子犹为笑宗焉[20]。
——韵社第五人
然每于岁暮之时,喜作消寒之会,良朋宴集,醉后狂谭,率以俚巷游戏之言,写世俗离奇之事,巧思绮合,妙绪环生[21]。
——小石道人
兹所谓以文为戏者非耶[22]?
——李祯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23]。
——绿天馆主人
有对小说与正统史书之阅读体验的对比,褒贬之下突出以文为娱的明确态度:
然好事者或取予书而读之,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终而博物以通志,则资读适意,较之稗官小说,此书未必无小补也[24]。
——甄伟
前此虽有陈寿一志,较之荀勖……览者终为郁抑不快。则又未有如《演义》一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拊髀扼腕,有志乘时者读之而快,据梧而壁,无情用世者读之而亦快也[25]。
——李渔
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优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今世所刻通俗列传并梓《西游》《水浒》等书,皆不过快一时之耳。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26]。
——佚名
有为小说阅读中的趣味化追求寻找合理依托的:
客有见者,问曰:“子所著忠节道义孝友之传,固美事矣,其于幽冥鬼神之类,岂非荒唐之事乎?荒唐之辞,儒者不言也,子独乐而言之,何耶?”余曰:“《春秋》所书灾异非常之事,以为万世僭逆之戒;《诗经》郑、卫之风,以示后来淫奔之警:大经之中,未尝无焉。韩、柳《送穷》《虐鬼》《乞巧》《李赤》诸文,皆寓箴规之意于其中:先贤之作,何尝泯焉。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
已[27]!
——赵弼
顾以世远人遐,事如棋局,《左》《国》之旧,文彩陆离,中间故实,若存若灭,若晦若明。有学士大夫不及详者,而稗官野史述之;有铜螭木简不及断者,而渔歌牧唱能案之。此不可执经而遗史,信史而略传也[28]。
——陈继儒
稗编小说,盖欲演正史之文,而家喻户晓之。近之野史诸书,乃捕风捉影,以眩市井耳目。孰知杜撰无稽,反乱人观听。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感[29]。
——佚名
有为将人导向身心放纵之艳情小说的强行之辨:
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人心世道者为贵。《艳史》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有裨于风化者岂鲜哉!方之宣淫等书,不啻天壤。风流小说,最忌淫亵等语以伤风雅,然平铺直叙,又失当时亲昵情景。兹编无一字淫哇,而意中妙境尽婉转逗出,作者苦心,临编自见[30]。
——隋炀帝艳史凡例
除了对小说娱乐性功能的肯定、对小说阅读之畅快体验的描述以及从史传文学角度为小说存在的合理地位立论之外,不少文人在序跋里也表达出对这种趣味性态度的贬斥和否定。
小说家千姿万态,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栋。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一切偷香窃玉之说,败俗伤风,辞虽工直,当付之祖龙耳[31]。
——滋林老人
以下这则序跋,将《金瓶梅》强行拉入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的教化功能叙事之中,并极力对该小说语涉俚俗、气含脂粉的特征予以掩饰,并打出富贵易趋淫、爱怨易致伤的人性弱点为其中的男女艳情立论。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敢正视小说的娱乐功能,试图将其纳入主流话语中,从而获得合理地位的思想观念的体现: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则曰:不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爱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慮洗心,无不小补。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富贵善良,足以动摇人心,荡其素志[32]。
——欣欣子
综观以上的序跋文集,可知在对通俗小说这种文体的看法和态度上,不少人坦率地承认小说阅读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和消遣,将小说视作一种娱乐之具,也有不少人虽然也意识到小说的消遣之用,然而却尽力将其拉入正统文用观所倡导的教化之用之下。这既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对于人类精神文化需求中娱乐消遣需求的压制,以致面对小说这一带给人愉悦和快感的文体时总是如做了错事一般。同时也因为文化导向中缺乏正视审美娱乐的观念和意识,使得人们在面对快乐或美时一方面从心理上先生戒惧,不能坦然面对,而另一方面又容易抱着沉醉其中与玩世不恭之态将美或快乐滑向纵乐或堕落。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一个用以制衡的文化观念。当时的文人或者按照儒家道德标准严格律己,或无视这种道德标准而纵欲享乐。比如晚明就是这样一个正统文化近乎解体而走向放纵和堕落的时代。也正因此本属于审美范畴的空灵通透之“趣”在世俗之乐的追求和侵染下成为一种自娱自适、追求感官快乐之“趣”。
3 趣味化追求:在审美与娱乐之间
晚明小说观念中审美之“趣”到娱乐之“趣”的变化与李贽倡导的“童心说”及当时整个追求自适快我的社会思潮都有密切的关系。李贽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深受心学思想的影响。心学将“心”也即人的主体能动性作为道德生发的起点,事亲、事君、交友、治民,都是由人心生发的,并不是靠外在的“理”去强制规范的。心学后学进而提倡心的自适与快乐,都对李贽的思想影响较大,如李贽对于本心的重视、对于文艺“快我”作用的提倡。所以他在小说的评点中也刻意追求一种快意舒畅的阅读感受,追求一种娱人娱己的趣味化评点效果。文艺的娱乐作用也随之在晚明成为一种普遍的发展态势,郑元勋在《媚幽阁文娱》的序中写道:“吾以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六经者桑麻寂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若使不期美好,则天地产衣食生民之物足矣。彼怡悦人者则何益而并育之?”[33]
就文学的功能以及带给人的阅读体验而言,审美和娱乐有时很难截然区分。文学的娱乐性是指以文学为娱乐对象,以“爱玩”的心态对待文学、从事文学活动,以满足自己的娱乐消遣之需。文学的审美性更多的偏向内心的沉醉或激荡之后的安宁,娱乐停留在心灵浅层次的快乐上,而审美则直达心灵深处的震颤。比如人听到一首歌时可能觉得很好玩一笑便过了,也可能听到一首歌觉得心被扎了一下或揪了一下,以致久久不能忘怀。孔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显然是审美而不是娱乐。依次区分标准,晚明小说评点中的趣味性追求显然是一种娱乐性追求,是与审美无关的一种文学娱乐活动。不是所有的娱乐都能提升为审美,但娱乐也不是一无所是。文学的娱乐作用在于宣泄排遣人的情感情绪,从而达到一个身心平衡的积极状态,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情绪宣泄口,每个人都有趋乐避苦的天性,所以某种意义而言娱乐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影响力比文学的审美功用要更大更广。
晚明的小说评点者追求以“趣”为美、淋漓畅快的阅读体验,坦言在评点中对消遣之乐的追寻。这在传统的提倡文学宗经征圣载道功用的社会里,正显示了人们对于小说这一通俗文学题材的态度转变,这种转变与晚明时期小说的繁荣互为因果,共同折射了当时追求自适的社会思潮以及价值取向的转变。晚明时人只想从小说的阅读和评点自娱娱人,并尽力将这种娱乐化的文学行为推向市场从中获利。创作和评点繁荣的背后体现了商业兴盛之下文学的消费化、娱乐化趋势,以及这种趋势背后文学的担当和提升作用的丧失。繁荣之时亦是文化品格滑坡之时,而追求自适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堕落,并且这种堕落是在小说自带的快乐诱导下自然而然进行的,不是说追求快乐就等于堕落,而是只追求快乐不再追求担当和审美就很容易滑向了堕落。所以稍有责任担当之士便会对此不满,如金圣叹批评叶昼的小说评语:“此篇纯以科浑成文”,他对叶昼于阅读评点中处处寻趣,插科打混、追求短暂快感的言行颇为不满。文学的娱乐趋势不再向上提升为审美或担当时便很容易沦为人们的宣泄排遣之具,甚或滑向了“堕落”之维,这也是晚明小说观念在由“审美”到“娱乐”的降格之中对于当下文学的警示意义。
[1]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4.
[2]徐干.中论[M]//纪昀.四库全书:文渊阁景印本.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493.
[3][4]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72.
[5][6]李贽.续焚书注[M].张建业,张岱,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7,34.
[7]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九回回评[M].
[8][9]叶昼托名《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第三十二回回批[M].
[10]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水浒传》第五十三回回评[M].
[11]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M]//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册[M].朱天吉,校.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2.
[12]《李卓吾先生批评古本荆钗记》第三十八出出批[M].
[13]《李卓吾先生批评洗纱记》的第二十三出出批[M].
[14]《李卓吾先生批评洗纱记》的第四十四出出批[M].
[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883,883,32,594,1300,657,668,608,774,879,901,93 5,598,863,935,953,993,1078
[33]郑元勋.媚幽阁文娱[M].上海:上海图书出版公司,1936:1.
责任编辑文嵘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5.009
I106.4
A
1004-0544(2017)05-0052-05
闫娜(1982-),山西闻喜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讲师。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