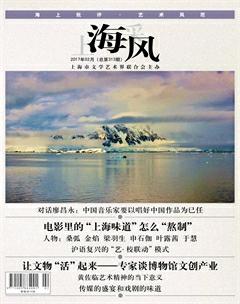我与新中国评弹

接受任务,开拓起步
我1945年参加党的地下组织工作,从那时起就一直搞新文艺工作。1948年冬天,地下党联系人约我到现在的静安公园碰头。当时那边还是外国人公墓,平时去的人很少,很冷清。我们边走边谈,他提出了领导上要我去搞戏曲的决定,我当时认为戏曲不是进步文艺,是看不起戏曲的,心里很不愿意,但这是党的决定,应该服从,只好接受。后来的工作就由刘厚生同志联系了,我和另外两位同志组成了一个小组,负责上海地区的戏曲工作。讨论分工的时候,我想自己祖籍苏州,苏州的评弹文学性高一些,也较高雅一些,就主动提出由我来搞评弹吧,其他同志就分工搞沪剧、滑稽等。
就这样,我搞起了评弹,开始跑书场收集资料,包括评弹小报、“书场陈容表”,乃至根据评弹书目改写的绣像小说、连环画等,据此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办法直接接触评弹艺人,我就考虑通过评弹小报的作者去联系评弹艺人,这是开拓工作的起步。
我首次接触评弹艺人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1949年5月28日。刘厚生同志通知我28日上午到泥城桥民营的大中华大陆电台去,那里有我们组织的特别节目,要我代表组织上去联系艺人。电台方面我们有自己人配合,特别节目除了由主持人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外,也要评弹艺人唱一点我们带去的宣传材料。第一个联系的演员是赵稼秋,赵稼秋是擅唱白话开篇的。我那时并不熟悉评弹开篇。我把我写的唱词交给他们唱,问他这你们能唱吗?他连说好唱好唱,把唱词都接过去,练了一下,结果都唱了。那天来的都是比较有名的艺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接触。
接着地下党叫我到市委组织部去报到,分配到军管会文艺处工作,联系苏南剧种,评弹也还是归我联系。
当时,根据“改人改制改戏”的戏改政策,我到评弹界去做工作,联系评弹艺人。我们主要用之前搞地下群众工作的方法,和群众交朋友,找骨干,组织他们学习,推动他们说新书。最近还听金声伯回忆,说他十七岁那会儿,有一天坐在评弹协会门口吃茶,看见一位工会干部领了我走进协会去。那是我第一次到寿宁路的老评弹协会。
在协会里我普遍接触艺人,尤其注意接触两类人,一类是年轻的,如周云瑞、张文倩等,还有一类是正派的和愿意靠近我们的人,然后从中物色可以作为骨干的人选,就这样,潘伯英成了积极分子。我们还要组织会员学习,有妇女组、青年组等,妇女组的活动地点在沧州书场,潘伯英也组织了一个小组在汇泉楼,用上午时间,每周一次,学习材料是“工人读本”,从劳动创造世界学起。有些响档上午不出来,潘伯英于是告诉我,在南京路成都路有个“大观园商场”,里面有个茶室,他们每礼拜一天,在那里唱京戏,让我那个辰光去,就能碰到他们。于是,我专拣那个时候去,也不打扰他们,等他们唱好京戏,再请他们坐下来学习,这逐漸成了常规。
那时候,我们认为评弹说的都是封建的内容,所以要推动他们说新的内容。但是评弹艺人很多,一人成一档,说一部书都要换新内容,困难很大。潘伯英向我建议,组织大家演书戏,内容为潘伯英改编的《小二黑结婚》,在南京大戏院(后改为上海音乐厅)作为劳军演出。演出由协会出面组织,当时在上海的有知名度的艺人都参加了。蒋月泉演小二黑,范雪君演小芹,刘天韵、张鉴庭、张鸿声、朱耀祥等都参与了演出,周云瑞、张鉴国等组织乐队伴奏,等于在上海的响档全亮了相,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说新书了。
遵照领导指示,老评弹协会也要进行改建。于是我和潘伯英等商量,帮助他们进行改选改建。改建大会是在军管会文艺处的大礼堂举行的,改建后称评弹改进协会。后来便是在改进协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曲艺协会的上海分会,之后又改称上海曲协。这些工作也都是我主持筹建的。这也可说是开拓工作。
进入评弹团
1950年,军管会文艺处转为上海市文化局,我便在文化局戏改处编审科当副科长,并兼任《大众戏曲》副主编(主编梅朵),和评弹的联系少了。
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我被调到文联当治淮宣传工作队副队长。1951年11月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海评弹团)成立,第二天整团被调来参加治淮,说也凑巧,便又归我领导了。
我们在漴潼河和佛子岺水库工作,与民工、工人同住同劳动三个多月。不但我们都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我和评弹团的艺人们的关系也更为亲近了。
原来文化局派的一位驻团干部是兼职的,他没有参加治淮,回沪之后也无暇兼顾团的工作,局里商量要再派一位驻团干部。一天,刘厚生同志刚好谈起派人驻团的事,我觉得坐机关不如基层剧团活络,就说,我去吧。领导同意了。于是我去了评弹团,就这样真正走进了评弹。那时,评弹是艺人当团长,正团长是刘天韵,副团长是唐耿良、蒋月泉,还有一位秘书张鸿声兼演出股长。局里派来的干部叫党代表或政委太严肃,就叫教导员。此外,还有一位搞创作的陈灵犀叫指导员。到1954年,决定艺人不当团长,团长就由我当了。我不是评弹团的首任团长,但是干部当团长我却是第一个,并且还得到了陈毅市长签名的任命书。
局里就派了我一个干部去评弹团。团里的演员都已和我很熟悉,不需要介绍了。不过当时,我和他们之间的反差还是很大。我当时二十八岁,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当了干部;他们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年纪大的已经四十多了,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社会经验丰富,从小学了说书,就在社会上接触各阶层的人物了。所以后来陈云同志说:“他们是五颜六色都见过,鉴貌辨色。吴团长啊,我替你想想,你这个团长不好当啊。”我当时也有点糊里糊涂。不过,我当时作为党员干部,他们是尊重的,和他们一起参加治淮,也建立了初步的友谊。当然后来在工作中也产生过各种矛盾和意见,但我熟悉了他们,他们也熟悉了我,觉得我不带私心,是一心一意要和他们一起搞好评弹事业,办评弹团的。三十多年来,我们建立了感情,在艺术上,他们也对我有了信任和崇仰。
然而一开始,工作上的困难还是不小的,各种矛盾和意见也时有产生。首先,评弹演出以档为主,评弹团是从来没有过的,评弹团该怎么办,从来没有一个样板,也没有地方好学。领导提出的办团宗旨是四个字“实验示范”,戏改政策是“改人改制改戏”。我们领会,要“实验”的就是对评弹艺人和书目的改革。另外,我也参考当时一些文工团的办法。评弹艺人以“档”为主,从来没有经历过集体生活的,因此也缺乏集体主义思想,评弹演员每一个人或每一档有一部书,谁的听众多就是谁的艺术好、收入多,谁也不服帖谁。到了团里要评级评薪,那就矛盾大了。别的剧团有主要演员,可是在评弹团,他们都是主要演员。分“观摩票”不能谁有谁没有,安排演出,场子大小,档子前后,都会有意见。
再举一个例子。那时,演员都住在团里,每星期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始提出要批评自我批评,就有人提出来:我不批评你们,你们也不要来批评我,我也不会自我批评的。现在听起来,这话是不对的。但那时,说这个话的还觉得理直气壮。凡演出调度,拼档拆档都会牵涉到演员的名利,也会有矛盾。如当时为了优化组合,让蒋月泉、朱慧珍拼双档。现在看来是对的,不然像《庵堂认母》这样的选回就出不来。但是牵涉到拆夫妻档,就会引起矛盾。后来有演员对我开玩笑说:“你领导的不是一个团,你领导我们三四十人(当时评弹团已扩大),领导的是三四十个团。”上海评弹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国家剧团的工资,只有民间艺人拆账的演出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而且他们的家庭负担又重,此事引起很多演员的不安,以致有人闹退团。退团当然不说是为了工资,要说些对团不满的借口。有关工资的情绪,一直到“文革”时才停止。不过我还是同情他们的,有些情绪也是人之常情。中间我曾多次向上级反映,并在上级的支持下,采取过一些改革措施,但未能解决。
然而,上海评弹团始终是巩固、团结的,应该说,参加治淮工作,深入工农,在他们思想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民间艺人时为名利、为衣食的思想,逐渐转变为要为人民服务,而党的思想教育也使他们改变了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同时,团里又进行了集体主义教育,他们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尽心尽力为国家、为社会,也为艺术、为评弹团工作和生活了。可以说,他们的认识水平和生活作风达到了国家剧团演员应有的水平,是明显不同于一般民间艺人的。
当时评弹团的办公室设在楼下,有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客堂,开全团会、排书都在里面。外面有一条很宽的走廊,一头用玻璃窗隔开,放三张写字台,便是团长办公室了。我和几位团长还有秘书张鸿声,就在里面办公。这以后的近十年里,我们正是在那里搞创新整旧,搞出了数十部长篇、中篇和短篇,整理传统书目,产生了优秀的选回还有不少开篇选曲,半个世纪来,这些书目成为了评弹书坛上经常演出的保留节目,掀起了艺术繁荣的高潮。
出人出书,传承发展
后来我听刘厚生同志说,周恩来同志在1946年和谈破裂离开上海时,曾经提出要地下党派搞文艺的作风正派的同志进入戏曲界去。刘厚生原来搞话剧的,后来进入到越剧界去了。解放前,地下党文委派我们这批文艺界的党员去搞戏曲改革,我想也是这个精神。
我又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艺的各方面都有冲击,但对旧的戏曲曲艺冲击不够,像评弹这样,传统书目,艺术可说是没有动过。解放后,要进行戏改,也是要补的这一课。还要根据党的为人民服务和推陈出新等方针进行改革,要新文艺工作者去帮助改造提高。我想,这也是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精神,是我们这批党的文艺工作者被派往戏曲界的任务,也是我去评弹团的任务。而且那时国家剧团要“实验示范”,也就是要由国家剧团负责对一个剧(曲)种的改革(今天来说,即是其传承、发展起带头和骨干作用)。
我到评弹团时,就是凭这个认识进行工作的。评弹团建立了,首先需要演出,而传统书目因为艺人提出“斩尾巴”而停演了,手上只有几部新编的历史题材长篇,很不成熟。组织上要求全团去参加治淮,真是英明。治淮回来,演员有了感受,产生了激情,自发地集体编出了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适应了当时上海人民的需求,受到欢迎,连续客满了三个多月。这样,治淮不但为演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使评弹团的书目建设有了很好的开头,取得了经验。就是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了评弹团的创新工作,明确了创作必须深入生活,到唯一的源泉里去。这样在《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之后,领导又派蒋月泉和周云瑞一起到海军去生活,创作了第二部中篇《海上英雄》;后来,编演《王孝和》,就去发电厂,并访问了忻玉英等许多关系人物;编写《冲山之围》(《芦苇青青》),我和幾位演员一同去苏州太湖生活了几个月;编演《江南春潮》,蒋月泉、杨振言等到江南造船厂深入生活。再后来,编新长篇也是这样,改编《夺印》,蒋月泉也是到上海郊区农村去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根据编排新书的经验我们建立了一套保证质量的工序,而深入生活是放在第一位的。深入生活不仅是为了收集素材,熟悉人物,而且还使创作人员和演员产生激情和灵感,而灵感和激情对创作是很重要的。
下面我就讲讲,我们建立的工序。
脚本先经艺委会讨论,由团领导批准排练,然后由艺委会定演员,交演员讨论,明确主题,人物性格等。于是由演员进行二度创作,演员称为“拽书”,有的演员还做案头工作,然后进入排练,演员俗称“立起来”,意即使平面的文本变成立体的表演。排练中,或由艺委会指定艺术指导,或由每回的上手负责(“挡舵”)。排好后,在全团进行响排,并听取意见。接下来,到听众中“试演”,这可以说,还要进行“三度创作”。评弹团的演员很重视这“三度创作”,听众的情绪、反映会启发他们激情和灵感,这演员称为“磨刀”。经过多场的演出,表演就会“出包浆”,生出光彩来,效果更好。不过,一般演了半个月就要定稿,由演员记下演出定本,把好的创造固定下来,以便复排、复演。
这样的工序,评弹团不但创作排练中篇时遵循,在排演短篇、长篇,也都采取严谨的步骤以保证演出的质量。
再有个重要工作就是整旧。评弹团建团时,艺人都已把传统书目自动停演。到1954年,学习了全国第二次文化会议的精神,考虑开放“老书”。但是认为还是要根据戏改政策对传统书目采取谨慎、严格的态度,整理后逐步推出。这样,便开始了上海评弹团的整旧工作。
现在强调对评弹,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整旧实在是一种积极的传承。只是将传统书目的文本印行出来,这只能是保留资料,算不得传承的。戏改政策对旧戏旧书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发扬其民主性的菁华”。可是一些书目的所谓“整旧”,只是做到了剔除糟粕(有时,到底是否糟粕也未能辨别清楚),却没有做到发扬民主性的菁华,更说不上艺术上的传承、发展了。
我们觉得一开始就整理长篇书目有困难,决定先从书的“关子”部分,或其菁华处整理起,由短及长。这样,1954年整旧工作先从长篇《玉蜻蜓》的“庵堂认母”,也是重点档子的重点回目开始。先由蒋月泉、王柏荫按原来的演出本,在团内演出,再由全团展开讨论,然后由我作分析报告(也参考了越剧等的整理本),最后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书目的积极性主题,人物的思想感情,书情进展的层次。再由陈灵犀执笔写出脚本,由蒋月泉、朱慧珍排练(设计唱腔等),讲行二度创作,随后在团里响排、讨论,终于第一次整旧工作就获得了成功。
《庵堂认母》成功的经验接着在全团推广,之后陆续整理了《玄都求雨》《怒碰粮船》《抛头自首》《花厅评理》等选回,后来更产生了《老地保》《三约牡丹亭》《大生堂》《厅堂夺子》等中篇。通过对重点关子书目的讨论研究,也对整个长篇了有了认识之后,就针对每部长篇召开座谈会,肯定了其菁华所在,由演员并配备创作人员进行整理。
应该说,整旧对传承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由此调动了演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表演艺术上也能得到发展(如《庵堂认母》的蒋俞调对唱,《玄都求雨》刘天韵“以哭代笑”表演等),但当时,常认为演旧书不如现代书进步,整旧工作到今天也是未能彻底完成的。不过,我还是很接受人民电台戏曲频道前艺术总监周介安的评价:“整旧工作是吴宗锡对评弹的重要的艺术实践之一,吴宗锡以其所代表的新文艺思想灌注于传统的评弹艺术,使之有了提高,而吴宗锡本人也同时在整旧中对评弹艺术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和把握。”
作为建设者,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调教演员。“调教”两个字我是从足球运动学来的,即使是大牌球星也要有教练的调教。评弹团的演员即使是响档名家,也还是要调教的。“调教”的内容除了要为人民、为社会服务和集体主义思想、团队思想外,还有文化、进步的文艺思想等。进评弹团时,有些演员小学也没有进过,他们的文化知识都是靠自学得来,对进步的文艺思想更是陌生,对于什么是主题、矛盾冲突、人物刻画以及从内容出发、从人物出发等也都不了解。我就利用一切可能向他们灌输,给他们提供各种学习的条件。如办图书室,上文化课,利用晚间纳凉读唐诗、宋词等等。
那时,上海文艺界常有观摩演出,有外国的,也有外地的,演员观摩之后,打开了眼界。我们还在团里组织讨论、开设辅导讲座。最主要的是一年一到两次的“休整学习”(那是学部队文工团的名称),再有便是通过整旧工作和排演新书等艺术实践。
我们评弹团基本上是和谐团结的,大家关系融洽,没有大的矛盾。这样,大家珍惜团的荣誉,都有“精品意识”,互帮互助。像周云瑞,还有作家陈灵犀都是有求必应,最肯辅助人的。所以,“调教”也不只是团领导的事,能者为师,成了有能力者们共同的事。当然,组织推动这个“调教”的是我。
在这种经常的“调教”之下,大家创新整旧的能力增强了,演员“二度创作”“三度创作”的能力也提高了。几次发动写新开篇、改说现代长篇、整理传统长篇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些都得力于平时对演员的“调教”。在不断的“调教”学习中,评弹团的演员提升了气质,提高了审美水平和情趣,台风也更好了,所以老听客们说“一听就能听出是不是上海评弹团的演出”。后来这种“群体风格”越加鲜明了,人们称扬这种“群体风格”。然而有人听了却说“群体风格”是“左”的,以为有了“群体风格”就要抹煞个人风格了,殊不知,个人风格是个性,和“群体风格”的共性并不矛盾。个体风格越发扬,群体风格越鲜明,这个“群体风格”还是通过“调教”打造出来的。
过去有人说,没有听众就没有评弹,所以,评弹演员十分重视听众,也十分懂得聽众。我到了评弹团界,也开始注意听众了。演出时要坐在场子里感受反映,还要开座谈会,和老听客交谈。振兴评弹出人出书,是为了要出听众。对听众要适应,要争取,也要培养。有些艺术的改革,是为了适应听众,也是听众所推动的,所以也得到了听众的支持。中篇形式的产生,就是为了解放后适应没有时间每天连续到书场听书的听众的,因此也得到了广大听众的欢迎。而中篇形式又适合及时反映新的内容,也就适应了过去不听评弹的新听众,这样的适应也争取了新听众。中、短篇这样短小精悍的形式,也便于深入工厂、农村、里弄、学校等演出。这样,评弹的听众就多起来了,有人指责说,提中篇为主不对,我们从来没有提中篇为主,长篇我们也编说的,但我们以中篇形式争取、适应了听众。评弹界很多人都效法我们,争取适应听众。原来的茶楼书场只有两百左右座位,专业书场扩大到四五百座,上海解放之后,取缔舞厅改建书场,有八九百乃至千余座,进入剧场,有二千左右座位的。1959年到1961年间,上海评弹团进入“文化广场”演出,先后演出十三场,听众排队买票,场场满座。听众少的一场六千余人,多的一场九千多。演出时,全场毕静,反映热烈。听众这样多,这样盛,显示出评弹的繁荣。评弹能在广场演出,过去是想象不到的,这是近十年评弹建设、传承发展、创新整旧的成果,也是我们适应、争取、培养听众的显著成果。
人们说评弹既有文学性又有戏剧性、音乐性,所以从事评弹建设需要懂文学、懂戏剧、懂音乐。我觉得,我从事过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协会员,又搞过戏改,是中国剧协会员,又爱好音乐,结识过音乐界的朋友,这些对我去搞评弹是不无帮助不无裨益的。不过,一定要看到新中国评弹的发展繁荣,不是某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新中国的建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切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地利是上海这个海纳百川的大都市,评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发展繁荣就是进入了上海,融入了海派文化,五六十年代评弹更得益于上海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经济繁荣的各种条件;至于人和就是当时评弹团和评弹界拥有的艺术才俊们;不仅如此,评弹还得到了广大热爱评弹的听众的支持。一门艺术的发展,要深入群众,跟上时代,这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