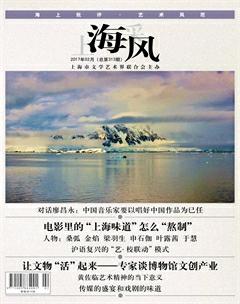沪语复兴的“艺·校联动”模式
陈雷



很多上海人都有这样的忧虑和抱怨:现在的上海小囡都不会讲“上海闲话”了!“不会讲”首先体现在“不讲”,而“不讲”的原因很复杂,比如社会、学校甚至家庭的语言环境中方言明显式微,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讲的都是普通话或者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于是,倘若你要坚持说上海话,就变成奇怪的少数、“无法交流”的另类,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地域意识亢进的傲慢,以及对尚未或不愿掌握沪语者的不够尊重。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讲沪语成为“常态”,沪语成了一门偶尔言用、点缀助兴的“本土外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嘴里也已经听不到标准的上海话,更别谈流利的、漂亮的沪语。上海人整体性失却沪语思维,大量词汇已到了非国语而不能表达的地步。当上海小囡被家长要求说几句上海话权当“表演”时,你听到的大多是发音怪异的“洋泾浜”沪语;如果规定不能夹杂国语,他甚至无法顺利地说出完整句子。
上海人方言能力的滑坡式退化,显然有城市化进程加快、流动人口加剧的因素,但无论如何终究似乎不是一种语言蜕变的正常节奏,一个时期在上海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系统、文广宣传系统被大力推行的“推普”政策,被认为是造成今天沪语在沪被严重边缘化、上海人讲不来上海话窘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幸好上海方言始终还有几块保留地,曲艺作为一种方言艺术,至少未被列入“推普”的清理范畴,一口纯正、柔糯、区分尖团音的上海话逐渐成为滑稽戏、沪剧演员的专利,美妙的“海上乡音”只能在舞台上才有机会欣赏到。
人们对一方语言之于地域文化的意义的认识,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加深。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大声疾呼“救救沪语”,国家的普通话政策也日渐宽松,从原先国语与沪语“有你无我”的对立状态,变成如今“兼容并蓄”的共生关系。于是,对语言影响最为深广的教育、文广等领域,开始有了一系列“拯救”措施,例如沪语广播、电视节目数量的显著增加,城市公交系统沪语播报的引入,以及学校开始允许甚至倡导师生在课间说上海话。
但是,即便如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看到“沪语复兴”的成果,显然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更多的方法,上海的曲艺界与教育界已经联手探索一条“艺·校联动”的有益路径——既然沪语失守从幼儿始,那么沪语复兴也当从娃娃抓起。
去年底,由上海市文联作为指导单位,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主办,上海市惠民中学承办的“学语言,从爱曲艺开始”沪语文化教育联盟校长论坛,邀请了曲艺界、教育界、媒体等各方专家、学者汇聚在修葺一新的文艺会堂,畅所欲言,共同探索传承沪语文化的新模式,为沪语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可供复制的经验。
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尤存在论坛上指出,上海市沪语文化教育联盟是社会大力倡导推广沪语文化下应运而生的机构,它把“文”和“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沪语文化教育的形式,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海派文化的熏陶,提升他们对海派文化的自信。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次全国文代会上关于“要增加文化自信,首先要从尊重自己的文化,尊重自己的民族,尊重自己的经典,尊重自己的英雄开始”的讲话精神的具体落实。
沪语保卫战从校园打响
作为沪语艺术最重要的实践者、看守者、传承者之一,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对沪语复兴的趋势从来特别敏感,对沪语推广工作始终不遗余力。
沪语文化教育联盟成立一年多来,上海曲协的艺术家们深入学校,在学生中开展了大量的沪语普及工作,如今,在“联盟”成员学校的学生之中,沪语又重新开始传播,让人看到未来复兴沪语、复兴海派文化的一线希望。
正如语文教科书上的《最后一课》所言:“一个民族的顽强生命力,首先表现在语言的坚守上。”沪语是上海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和传承好沪语,对传承并进一步发展弘扬海派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前年,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发起成立了以惠民中学牵頭的上海市沪语文化教育联盟。联盟成员中除了惠民中学,还有长宁区姚连生中学等九所学校。独脚戏和上海说唱的一些经典文本成为联盟学校“推广沪语”的最佳载体,而曲协的艺术家们则理所当然地成了孩子们的“沪语辅导员”。曲协副主席、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钱程每周都会去惠民中学给孩子上课,用沪语给孩子们讲上海滑稽戏的艺术。
惠民中学校长孙广波虽然是一位还说不好上海话的新上海人,但这些年,他对推动沪语传承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让钱程深受感动。钱程受邀在惠民中学成立了“工作室”,他说,校长专门给他准备了一间办公室,虽然他每次去学校大都直奔教室,很少去他的专属办公室,但从中可以看出学校对这件事的重视和对沪语教育的重视。
除了钱程工作室外,惠民中学还专门办了一个沪语文化展示馆,师生可以从展示馆里得到很多沪语知识,还配有视听设备。新校舍建成后,展示馆被布置成石库门风格,在里面既可以上课,又可以排练节目。
与孩子接触多了,钱程观察到,他们对沪语教学非常感兴趣,沪语对于孩子并非没有吸引力,而是因为他们鲜有机会接触沪语,他们是被硬生生地与沪语隔离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他们重新连接起来。
钱程认为,上海话里渗透着许多地域文化,上海这座城市接触西方文明相对较早,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西化程度都比较高。因而沪语里的“舶来品”特别多,与英语的关系比较密切,比如现在普通话里也通用的“麦克风”就是上海话从英文的“Microphone”直接音译过来的,又如旧上海称电话为“德律风”(Telephone),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沙发、水泥等许多词汇都是上海人贡献给《新华词典》的。从保护方言的角度讲,不仅是上海话,全国各地的方言都应该得到保护和传承。如果方言消失了,这个地方的戏曲也就消失了。大家都只说普通话,交流起来确实方便了,但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那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会随之被丢弃,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推广沪语还要政策支持
然而沪语文化教育联盟毕竟只是一个规模有限的民间组织,“入盟”是自愿,并没有教育部门的硬性规定。因而联盟有没有快速壮大的成长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校长们对沪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因此,上海曲协主席、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团长王汝刚说,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在运用民间力量推进“艺·校联动”的同时,推广沪语还是要寻求和呼吁政策支持。不仅应该明确废除校园沪语禁令,而且还要鼓励师生一起说上海话。
现在沪语文化教育联盟的行动,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加入的学校越来越多,电视台的小荧星艺术团也有老师来参加论坛,说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只要坚持不懈,肯定会越做越好。
王汝刚说,沪语教育联盟的成员学校,对上海那么多学校而言,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就算未来有很多学校想加入联盟,师资力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语言教育有它的特点,语言是每天在用,每个人在说的,你学会了,只要你坚持使用,你就成为一名播种者。所谓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只要有了沪语传播的土壤和春风,沪语复兴是可以期待的。
同时,王汝刚呼吁曲艺工作者在推广沪语时,工作面还可以有所拓宽,推广方法还可以多一些。比如,曲艺作家可以主动多写一些宣传沪语、适合传唱的作品。如果我们只是拿一些传统作品让孩子们去演,对他们来说,可能难度比较高。是否可以用沪语来唱唱学校新面貌?甚至可以动员学生创作一些新段子,不但动口讲,还可以动手写,用沪语思维编成小唱段来唱。还有是否可以依托市文联的资源,横向联合木偶剧团,搞沪语木偶剧,既避免了搬演传统滑稽戏对孩子表演上的过高要求,又迎合小朋友的兴趣点。
刚参加全国文代会回来的王汝刚说,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感触很深,体会蛮多。他说,跟我们关系最密切,就是如何增强文化自信。从文化自信的角度上讲,沪语的传承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老祖宗的语言中包含了丰富的智慧信息和文化基因,把它保存、整理、传承好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工作。好在這几年实践下来,曲艺界和教育界联动,星火传承,沪语文化的火种非但没有熄灭,而且越燃越旺。
一首评弹曲调的校歌
曲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社交能力、想象力以及思维的灵活性、创新意识、道德修养等方面有独特的功能。这次沪语文化教育联盟校长论坛就以“学语言,从爱曲艺开始”为主题,上海曲艺界除了滑稽戏外还有一支重要力量——评弹。
八年前的一天,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的俞蔚老师接到一项“任务”——组建学生评弹社团。当时对评弹一无所知的她,完全不知道如何完成这个特殊的任务。她找了许多评弹演员身着各色旗袍在聚光灯下表演的舞台照来“诱惑”孩子:学评弹,能穿着漂亮衣服在舞台上边弹边唱。好不容易,从班里连哄带骗拉来六个女孩子。来上第一堂课的是上海曲协副主席吴新伯,他换上长衫,手执折扇,表演“武松打虎”,一招一式,立马把俞蔚和孩子们镇住了。
在俞蔚看来,评弹离孩子并不遥远,只要内容得当,传播力不亚于流行歌曲,社团排练《静夜思》,几个调皮的男孩子在教室外学唱。她惊讶地发现,除了极个别吐字、音调不准,他们基本上能把曲子唱下来。在校长支持下,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给校歌谱上评弹曲调,教全校孩子唱,还租用专业录音棚录制评弹版校歌,它将成为今年学校七十周年校庆的一份特殊的贺礼。
沪语是非遗传承的宝贝
上世纪八十年代,媒体人端木复曾经写过三个“内参”,希望上海加强沪语教育,增加沪语广播,培养沪语主持人。因为他已经看到,当时全国普及普通话是采取一刀切、一面倒、一风吹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十年前,上海曲协也意识沪语没落的问题,带头搞沪语普及工作,滑稽界在这方面功不可没。近几年,上海人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大家越来越明白,我们的沪语在非遗传承中是个宝贝。
端木复认为,严格说来,不会说上海话,就没有上海人的情感。就如同生活在上海,不一定有上海的生活。端木复是北京人,1958年到上海,学的第一句上海话是“吃东西”,因为舌头转不过来,老是说成“吃袜子”,还因此被起了外号。在当时的生活环境里,不会说上海话是没法跟别人交流的。几十年操练下来,如今端木复的一口上海话已很流利。
侯宝林的相声里说上海人把“洗头”说成“打头”,让很多听众印象深刻。可见曲艺可以用诙谐幽默的方式,让人轻松地走进上海的方言。所以,端木复认为,上海曲艺应该在沪语推广方面“无孔不入”。
现在独脚戏、滑稽戏和沪剧这三个上海最主要的地方戏曲申请非遗都成功了,从非遗保护层面,这些戏曲作品中就留下了上海的历史,上海人的喜怒哀乐和思维方式。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目前还是困难重重,但在教育界的大力支持,艺术家的辛勤耕耘,全社会的关注重视,尤其是立法保护下,上海话的路会越走越好。
方言复兴不能单靠课堂
曲艺家们走进课堂,自然是为拯救日渐没落的上海方言的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著名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教授却泼了点冷水,他认为在课堂里无法从本质上拯救日渐衰亡的方言,并表示自己不会去学校里教孩子方言。
钱乃荣认为,方言之所以无法像一般的学科那样通过上课的形式传承,是由于语言必须“在用中学、在学中用”,如果没有日常使用的环境,语言一定会失去生命力。仅仅靠每周一堂或几堂45分钟的语言课,不过是让孩子们学会零星的方言词语或句子,不可能使他们像几十年前的祖辈们那样拥有真正的“乡音”。
目前由学校主导的方言教育,大多处于实验性阶段,不仅缺少教材,而且也缺少真正的方言教育工作者,很多教授孩子们方言的老师,本身是新上海人,对沪语也是现学现卖。学生们上课学几个常见词汇和日常用语,或者一两首方言的童谣,对方言是窥一斑而不见全豹。
方言教学先天不足,后天又受制于强势的应试教育。方言课不列入考试考察的范围,所以就跟体育课或者美术课一样,变成了一种“放松课”。因此,即使是在上海卢湾区土生土长的语言学家钱乃荣,也拒绝了母校向明中学请他去上方言课的邀请。
他强调,方言是不需要教的,任何语言系统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使用是对方言最好的保护。人文地理、移民、栽培植物发展史、地名、戏曲小说、民俗等文化元素,都在使用方言的过程中,得以口传心授,讲方言应当是和吃饭喝水一样寻常的事情。类似应试教育下的外语教育常常把学生们教成“哑巴英语”,要想学说方言,也不可能仅仅靠课堂。只有学而没有使用的语言,永远都是死的、没有生命力的。
“乡音不改”需要立体维护
要复兴方言和方言文化,还是要追根溯源,为什么祖祖辈辈“乡音难改”,到了经济繁荣的当代就变成“乡音难觅”了?
其实沪语衰败的责任,也不能全算到“推普”政策的头上,因为普通话虽然降低了不同地区人们的沟通成本,但这也只是方言衰败的表面原因。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成因是在近现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人口迁徙。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原来只有三五十万本地人。后来随着经济中心的形成,不仅江浙人大量移居上海,广东和山东,甚至不少外国人也不乏定居上海者。战争年代,还有大量江淮难民逃到上海。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引进人才”纷至沓来,“打工族”更是如潮水般涌入上海。由于人口迁入时间短、数量多,不会说上海话的人的比例愈來愈高,就连上海话本身的语言面貌也已经随之发生变异。
语言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也会与其他语言不断地碰撞、融合。在人口流动相对静止的时期,地域内部的方言可以比较完整地保持和延续下去,但是当这种人口迁移的平衡被打破,方言也会随之产生动荡。方言的衰败是人口迁移的副产品,即便没有普通话的强势推广,只要有大量的人口流动,方言也会或变化或淡出。
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试图保护方言,特别是在一些人口大量涌入的地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虽然不能将沪语复兴的重任完全拴在“方言进课堂”这一根绳上,但是,像上海曲协这样以艺术教育的方式带入方言推广,以幽默丰富的内容和优美风趣的形式,将方言文化带入课堂,植入孩子们幼小的艺术心田,这种尝试仍是非常值得称道和可以复制的。无论这些孩子最终是否会成为曲艺爱好者甚至工作者,至少沪语的传播、方言的传承多了一种方法,多了一种可能。
当然复兴方言,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多多营造语言环境,形成立体化的方言氛围,在普通话强势介入日常交往和沟通的同时,给方言辗转腾挪出一点空间。这样一方面作为“官话”“雅言”的普通话能够消除沟通的隔阂,而作为地方文化载体的方言也能够发挥其文化遗产的作用。
可以看到,始终保留粤语广播、电视频道的广东地区,方言的日常使用率就比全国其他地方高。目前多数人使用方言是在家庭环境或私人场合,但只有在公共空间也允许和鼓励方言的存在,方言才能得到真正的复苏。
或许,类似曲艺工作者带方言进课堂的推广方式,其最大的教育宗旨不是要在课堂上真的教会孩子们说多少句方言,而是通过曲艺的形式挖掘方言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激发孩子们对方言的兴趣。
方言里大有乾坤,承载着地域文化和远古文明,对文化艺术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滋养。保护方言的最好方式就是使用方言,既要靠曲艺工作者去上课,并且带动更多的沪语老师去推广上海话,更要呼吁给方言一点立体化的使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