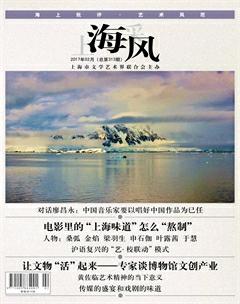对话廖昌永:中国音乐家要以唱好中国作品为已任
胡凌虹

廖昌永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国家二级教授、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现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多次在国内、国际重大声乐比赛中获大奖,特别是1996~1997年,在一年之内连续三次分别夺得“第41届图鲁兹国际声乐比赛”“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挪威宋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第一名,在世界乐坛引起强烈反响,也开启了和世界歌王多明戈的精彩合作。特别是在美国“肯尼迪中心2000演出季”,廖昌永与世界歌王多明戈在美国首度合作的威尔第歌剧《游吟诗人》的大获成功,使他被《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盛赞为“天才的歌唱家、是一块瑰宝”,“将成为跨时代的大歌唱家”。廖昌永曾主演过《塞维利亚理发》《弄臣》《唐·卡洛》《卡门》《浮士德》《茶花女》《游吟诗人》《假面舞会》等经典歌剧。在国内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宝钢高雅艺术奖”,“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配角奖”,上海首届国际艺术节“艺术之星”,“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全国德艺双馨青年艺术家”,美国百人会“杰出艺术成就奖”,纽约“杰出艺术家奖”,比利时“东方艺术骑士”勋章,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等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关于廖昌永的光辉履历,很多人耳熟能详:屡次在国内、国际顶尖声乐比赛中获得大奖,特别是在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中斩获桂冠,实现了亚洲歌唱家在此项赛事中零的突破。这是极不容易的,更不容易的是,获奖后的近二十年,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姿态:曾先后与世界著名交响乐团及世界著名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成功合作,与歌剧大师多明戈、卡雷拉斯、露丝安·斯文森等成功合作,演出了众多的歌剧和音乐会,其精彩完美的演唱确立了其“世界著名男中音”、“亚洲第一男中音”的国际乐坛地位。
凭着深厚的演唱功力,对西洋歌剧的精彩演绎,廖昌永的演出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获得国内外各种好评,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近年来开始“华丽转身”,专注于中国艺术歌曲和中国原创歌剧的创作和表演。他策划并主演了原创歌剧《一江春水》。他举办了《中国声音·致世博》《中国声音·新年问候》《中国声音·感动世界》等专场音乐会,举办了数场以“毛泽东诗词艺术歌曲”为主题的个人音乐会。同时他还做着中国艺术歌曲的整理工作,推出了《中国艺术歌曲精选》专辑。他坦言,自己已经慢慢把很多精力转到弘扬中国的音乐文化方面。除了歌唱家,廖昌永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不同的身份,也促使他用多种角度多种纬度思考中国歌剧的发展、中国艺术歌曲的弘扬以及青年人才的培养等问题。
廖昌永实在太忙了,就说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奔波于国内外各个场合:2016年9月初在G20峰会文艺演出上演唱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10月底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参演清唱剧《禹王》,11月上旬在伦敦与世界顶级的倫敦交响乐团合作录制唱片,11月30日参加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2日在天津大剧院举办歌剧讲座,平安夜在深圳大剧院举办独唱音乐会,跨年之际又参加了2016年中央电视台跨年晚会,2017年1月8日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汤显祖》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演,饰演汤显祖……好在,即使在这样繁忙的时刻,他还是挤出时间,为本刊《面对面》栏目,接受了专访。
谈中国艺术歌曲的推广
记者:前不久,你在深圳大剧院举办独唱音乐会,演唱的是“风雅颂”范曾诗词艺术歌曲,这也是“中国艺术歌曲百年经典”系列音乐会的一部分。为何独唱会上选择演唱中国艺术歌曲?
廖昌永:唱了这么多年歌剧,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唱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国外的。虽然也有中国作曲家写的一些作品,但中国人写的歌剧也大都用英文唱,所以在观众心中,歌剧的中国特点、中国特色还是不够。在学生时代,周小燕老师就对我说:中国人一定要写中国的作品。这个观念对我来说根深蒂固。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音乐家,首先要以唱好中国作品、振兴祖国文化为己任。所以近年来,我举办了不少中国艺术歌曲的独唱会,每年在国外举办的一些独唱音乐会的演唱曲目中,我至少会保留三分之一的中国本土作品。一次,我在挪威做巡回独唱音乐会时,有很多观众跟着我在城市间巡回。我很好奇,就问他们,你们今天怎么又来了?他们说,对啊,我们就跟着你走的,中国歌曲太好听了。艺术是无国界的,文化的交流非常必要。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将中国歌曲更好地传播出去,不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记者:近几年你一直在推广中国艺术歌曲,这方面你们做了哪些工作?为何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中国艺术歌曲中有哪些宝贵的财富尚未被重视?
廖昌永: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作曲家写了很多中国艺术歌曲的作品,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过程和国外的发展过程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艺术歌曲有它的一个特定范畴,如:要根据诗词进行谱曲,音乐必须要有很高的艺术性等。在中国的艺术歌曲创作过程中,我们知道有一些是民间歌曲改编的民歌,有一些是创作歌曲,有一些是根据诗词写的一些艺术歌曲,但是因为一定时间内,大家很难明确区分哪些是艺术歌曲,哪些不是艺术歌曲,因此就需要把属于艺术歌曲的划到艺术歌曲的范畴中去,哪些需要提高的,再进行提高。现在我们就在做挖掘、整理、推广、出版、发行这样的工作,正在按计划实行当中,已经做完了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收录、演唱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赵元任、黄自等这批中国艺术歌曲先驱作曲家的作品,现在准备出的第二张唱片是《风雅颂》,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的著名作曲家谱的一批诗词作品歌曲,我们在上海、西安、深圳等地,刚刚做了“风雅颂”艺术歌曲的推广活动,今年2、3月就会出这第二张唱片。今年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可能还会做一个“中国艺术歌曲百年”的专场音乐会。
之所以要做中国艺术歌曲整理推广的这项工作,是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在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有好的创新。现在我们很多作品就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曲家那样,是按照德奥艺术歌曲的标准来创作的,其实我们有着自己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修订《诗经》时,《诗经》就是由音乐来传唱的,可以说我们中国的诗歌与音乐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做中国艺术歌曲的整理工作,还有一个初衷就是希望帮助解决现在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有些作品旋律和诗词写得都很好,但是在色彩性和丰富性上往往达不到艺术歌曲的高度,通过我们的挖掘整理,希望作曲家们从中借鉴经验,使作品更加完善。现在的好作品是有不少的,但推广力度还不够,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前些年市场化走得过快,对作品的评价是看票房和赞助有多少,而这一点应该是由艺术性来引领的。
谈唱法问题和“飙高音”问题
记者:以前人们印象中,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一直是泾渭分明的,但近些年,在很多音乐晚会、歌唱比赛以及音乐选秀节目上,开始出现了融合,学美声的人唱起了流行歌,流行歌手开始运用美声唱法,引起了不少争议,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廖昌永:流行唱法、美声唱法、民族唱法,从发声技巧、唱法上讲,当然是不一样的,音色出来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要简单地分开。我觉得音乐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流行歌是否只能流行歌手唱,美声的歌曲是否只能美声演唱者唱?我不认同。流行歌也可以用美声的方式、技巧来演绎,可以演绎出不一样的音乐风格。比如《黄河怨》,大家一直认为是个美声歌曲,大家一开始约定俗成的好像就是这样来唱的,但是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听到了彭丽媛老师唱的《黄河怨》,当时给大家特别新的感觉,唱民歌居然可以把《黄河怨》唱得那么好,这给我的震撼是特别大的。用民族唱法这样的一种发声技巧,依然可以把所谓的美声歌曲唱得非常好。所以彭老师这样一个演唱,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标杆。《黄河怨》本来就是一个中国曲目,不论是美声唱法唱,还是民族唱法唱,都是我们的母语,我们都应该把它唱好。其实每种唱法都是可以把作品唱好的,就像美声就是“优美的歌唱”嘛,无论我们技巧怎样,最终目的就是把作品的内容唱好。对于我来讲,演唱的曲目上,音乐风格上,没有任何界限,不论是流行歌曲,还是美声歌曲,只要是好听的,能够触动我心弦的歌,我都愿意唱。当然演唱技巧上一定有不同,我唱出来的不可能跟孙楠一样,我唱出来的一定是廖昌永式的。
记者:你在青歌赛做了很多年评委,在你看来,青年歌手在演唱时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廖昌永:之前在青歌赛做评委时,当时我们很焦虑,有些孩子很早唱很重的曲目,嗓子唱坏了。男高音又在唱《魔笛》,又在唱《奥赛罗》,又在唱伯爵,一会儿又在唱别的,他认为只要是男高音就都可以唱,不管是不是合适。只要是花腔就唱夜后,这是不对的,夜后是非常powerful(有力量)的,是戏剧花腔女高音,不是抒情花腔女高音,后者虽然可以唱得很炫,但是人物不对,声音里面的张力不对,没有力量感。但这点,从业的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那个时候也不是非常清楚。其实声部里面也是细分的。男高音还可以细分为抒情男高音、戏剧男高音、英雄男高音等;女高音分花腔女高音、抒情女高音、戏剧女高音等,花腔里面还分有抒情花腔女高音、戏剧花腔女高音。同样是男高音,比如《奥赛罗》中是戏剧男高音,《魔笛》中是抒情男高音,戏剧男高音唱抒情男高音的曲目是不合适的,不同类型选择的曲目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不是所有的男中音声部我都可以唱,我是偏高的男中音。《费加罗的婚礼》有两个男中音声部,一个是费加罗,另外一个是伯爵。我适合唱伯爵,费加罗对我来说太低了。所以适合哪个声部是由我们的声带和腔体构成的,是天生的,我们要尊重身体的规律。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青歌赛上,只要是男高音,什么曲目都唱,幸好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很大的改善。
记者:在《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音乐类选秀节目中,不少歌手喜欢展示强悍的高音技巧,在大众心中,也有一种“唱功等于高音”的观念,以及“美声歌唱家都会飚高音”的固有观念,对此你怎么看?
廖昌永:只会飚高音并不一定就会唱歌。我们练习不是为了把音练得有多高。我們练习技巧是为了让你的声音更加有弹性。我们唱歌要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让自己的嗓子能够有更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而不是一味飙高音。有时候好像有些训练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声音能飙多高,帕瓦罗蒂能够唱High C,我能够唱High D,你声音唱得再高,没有情感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唱歌不是为了飚高音,而是为了表达情感。技巧不在于音唱得有多高,而在于你在同一个音上,从最弱唱到最强,从最强唱到最弱,声音的力量保持是一样的,这个是最难的,而不是高音。因为高音能唱多高是你的嗓音条件决定的,有些人嗓子声带短、薄,他的会厌是呈卷叶状的,他的高音就容易上去,但是有些人声带比较长,像我这种男中音,非要让我去唱High C,就强人所难了。记得有一次,有人问我,你现在在唱什么,我回答“男中音”。他说,那好好努力啊,十年以后,听你唱“男高音”。我只能一笑了之。为何声部要分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就是从人的声带的长短、宽薄、会厌的状态等生理条件决定的,是天生的。
谈青年人才的培养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音乐类的比赛,不少歌手在这些平台上脱颖而出,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对于想一直在歌剧道路上走下去的年轻后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廖昌永:从事歌剧的中国歌唱家是蛮清苦的,因为我们唱的歌剧属于西洋艺术类型。在国外,意大利人有足够多的意大利歌剧让他唱,即便唱法国歌剧也可以改成意大利的方式。德奥歌唱家有足够多的德奥的作品让他们唱。因此他们在唱本国语言的时候没有文化障碍。但是对于中国歌唱家来讲,观众会要求我们要懂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你今天唱男高音,就要被拿来跟帕瓦罗蒂、多明戈比较,这对于中国的歌唱家来讲,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以这个作为我们的目标,要咬牙坚持。
现在成名的人确实很多,最后往往是两种结局:一种是忽然红了后,开始坐享其成,然后就昙花一现了;还有一种就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继续努力,不断实践、学习。艺术家要学一个戏非常困难,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要去找语言老师、形体老师、表演老师、艺术辅导老师等等。国外歌唱家艺术生命很长,有很多女高音歌唱家已经到了七十岁声音依然很漂亮,像二三十岁的声音状态。原因是他们在唱的同时还不断地学习。但国内的艺术家成名之后再回去上课的人就比较少,慢慢地唱着唱着就偏了,越偏越远,等发现,肌肉已经养成习惯,要再纠正过来需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从事艺术还需要坚守,需要不断学习。
记者:除了艺术家的身份外,你也是一位老师,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在培养学生方面,你采用了什么方法,有什么心得?
廖昌永:长期以来,音乐学院的学院培养和剧团之间是有一定脱节的。学生都是被关在房间里面练,给他们上舞台的时间很少。等学生毕业,剧院还要经过三五年的培养,他们才能成为职业演员。如今各个音乐学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近些年上海音乐学院以及其他音乐学院都开始在制作歌剧,像上海音乐学院制作了《费加罗的婚礼》《女人心》《茶花女》《卡门》等等。在学校教学当中,我们把艺术实践这一门课程安排得非常紧,比以前增加了很多量。上海音乐学院全院艺术实践的经费也大大提高了。付诸实践之后,我们发现学生的变化非常巨大。我们前年和日本的一所大学以及一位意大利导演一起合作做了全学生的《费加罗的婚礼》,演出结束之后学生最高兴,当时一个学生在发言的时候说:经过这一部戏的排练,我觉得我成熟了,我长大了。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一个体会。记得当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到旧金山歌剧院去学习,在那儿呆了一个月,看了旧金山歌剧院排了五部戏,这一个月的时间相当于在学校里面一两年的学习时间。为什么?你可以看见它的整个制作流程,演员在舞台上怎么唱,演员在舞台上怎么放松,演员在舞台上怎么塑造人物,他应该在舞台上怎样站,动作是怎样的,音乐结构比例是怎样的,这样的实践远远比你关在琴房里面自己瞎琢磨强十倍。我认为,在我们的教学当中,我们要相信学生,给他们足够的信任,学生有很强的创造力,因此我们学院也成立了青年歌剧团,这些年青年歌剧团开始排戏。如今我们的学生到国外演出,相当出色。国内的惠民音乐会上,我们很多学生是明星,观众予以他们的掌声不比我们的小。所以我认为,人才培养要从我们的制度、要从学院里面开始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