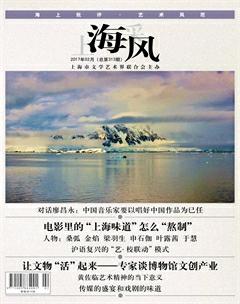电影里的“上海味道”怎么“熬制”
曾凌



魔都上海一直是电影导演喜欢拍摄的对象,尤其是“老上海”,很多中外大导演都拍过。曾经的上海已经一去不复返,岁月已经给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永远聚焦着人们好奇的目光,也给了创作者展开想象、自由抒写的空间。然而,真正能拍出上海内在精神的凤毛麟角。观众们或感叹“上海味道”不够“浓”,或抱怨上海只是影片的背景、一个华丽的虚壳,更重要的是,近些年上海题材的影片寥寥,让观众尤其是上海观众挂念。因此,近日银屏上一下子出现的两部上海黑帮题材的电影,立刻点燃了大家的兴趣。
一部是程耳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个性化的风格引发了观众的热议。影片非线性叙述的方式,让一些观众大呼看不懂,也让一部分观众认为“有个性”、“有腔调”,要去二刷甚至三刷。在最近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发布的“电影眼”新片评分榜上,对于《罗曼蒂克消亡史》的评价也呈现了两级化,影评人的打分从9分到0分不等。
另一部影片是上海导演胡雪桦执导的《上海王》,虽然尚未公映,但拿奖已经拿得手软。第12届中美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年度导演、最佳男配角三项大奖,第8届澳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音乐、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五项大奖,近日入选第74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无论是被热议的《罗曼蒂克消亡史》还是“金光灿灿”的《上海王》,都不再局限于以往很多影片中人们熟悉的上海元素:耳熟能详的上海老歌,华丽精致的旗袍,男女间的暧昧,这两部影片都有着更大的“野心”,即反映那个时代以及时代中人物的沉浮命运。最终,《罗曼蒂克消亡史》到底是一部有个性、有腔调的“奇作”,还是一部歪曲历史、杂乱无章的“伪作”?即将公映的《上海王》是否能满足观众对上海本土导演的期待?这需要时间来验证。不过,两部片子的“新气象”以及引发的争议倒可以先谈论一下。本文采访了一批电影评论家、电影导演、沪语研究专家,一起来探讨如何在电影里“熬制”上海味道……
电影里的沪语,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
《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当章子怡、闫妮等北方背景的演员以及日本演员浅野忠信说着一口上海话时,很多观众都感到新奇。尤其是上海观众,感到久违了。影院里罕见地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头发斑白的上海观众。网络上有人因此片专门撰文分析“上台面”和“不上台面”的上海话。
近二十年来,不少影片中夹杂着一些沪语,但总是寥寥几句,就像一桌菜中的小点心,犹如点缀,如今此片一下子用了大规模的沪语对白,如同上了一桌子的上海菜,不少观众自然大感过瘾,听着亲切。但也有些观众认为味道不地道,说得过于刻意,让人分分钟出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认为,《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上海话,感觉烂熟,熟透的熟。口语排练太多遍,标本感,像公交报站,听着不舒服。
导演朱枫坦言,看片时,演员们的一口上海话让他感到别扭,对影片而言反而帮了倒忙。“我觉得葛优演得最好,葛优基本不说上海话。上海话的质感,王汝刚等演本地戏的演员才能体现出来,不是光配音就好了。要复原上海的文化,上海的影像场景,上海的语言环境,人物的对白如同对电影道具的最后一道做旧工序,对了,复旧的感觉就出来了,没有对,是一口大兴话,如同非但包浆没有做好,又刷了一层新的油漆,不干不净却又崭新崭新。”
对此,沪语研究专家钱乃荣则有不同的观点。他指出:“上海话是有变化的,像唱沪剧、滑稽戏一样的上海话是戏剧上海话,现在大多数上海人讲的是交际上海话,跟戏剧上海话是两回事,不能要求太高。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上海话话剧,还拍成了电影,后来有沪语电视剧《孽债》,上海人很喜欢看,所以沪语影视剧不是新生事物,现在是恢复的问题。那么多年不讲了,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粗糙的,我觉得要一点点来。现在是先鼓励大家讲,讲语言不是制造一个产品,一定要多标准,只要大家能够交流、听得懂就行,等到电影里的上海话都讲起来了,再谈怎么更标准。”
电影《上海王》里也有不少上海话,包括主演之一胡军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在台词当中不时夹杂着上海话。朱枫认为《上海王》里的上海话处理得比《罗曼蒂克消亡史》好,“特别是曹可凡带有尖团音的很苏很糯的上海话,完全还原了上海师爷的质感。这些细节是胡雪桦作为本土导演富有的天然优势。”
导演胡雪桦向我透露,在拍片时,对里面的上海话做了精心设计,比如影片刚开始,筱月桂说的一句“我还不情愿”,就是浦东川沙话,因为筱月桂是浦东川沙人。“这里还有我的一个个人情结,我母亲就是浦东川沙人。我觉得在这个戏里面要有这种感觉,一开始是浦东话,然后说上海话,之后再说普通话、英语。她的语言的演变也反映了人物的成长和变化。”
主持人曹可凡在《上海王》中扮演了洪门师爷一角,凭借这个角色,他在12届中美电影节上斩获最佳男配角奖。除了精彩的演技,曹可凡的一口地道的民国上海话也让人印象深刻,这一点在他饰演《金陵十三钗》时,很多观众就见识了。该片中,曹可凡扮演的“孟先生”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南京底层小吏,既说英语,又说日语,还说了一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话。曹可凡虽然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并不天生就会说老上海话。“我们现在说的上海话和以前不一样了。比如现在上海人自称‘我用‘阿拉,其实这是从宁波传过去的,老上海人说‘我是‘哦呢。只有像卢燕老师这样,很早就出国了,她的乡音没有受到后来的影响,就固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所以一开口就有老上海的味道。”为了说好老上海话,曹可凡还曾虚心向老上海人程乃珊夫妇求教,把那段台词逐字逐句改成上海话的讲法,然后把每一句台词念给程乃珊的丈夫严尔纯先生听,请他纠正发音。在演《上海王》时,曹可凡的上海话依然是“民国的”,碰到吃不太准的发音,还是会打电话去问一下严尔纯先生。
电影里的“沪语”标不标准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要不要加,怎么加?在上海题材的影片中,上海话到底是必不可少的“盐”,还是增添点上海味道的“鸡精”?
“语言是电影里边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一个片子的年代感,人物的个性,剧情的烘托,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花样年华》里的孙太太是上海人潘迪华扮演的,几句台词,味道就出来了,那个年代感就出来了。《上海王》中我演的师爷是配角,《金陵十三钗》中演的人物戏份也不多,但人物有个性,语言有特色,所以人物就比较丰富。”曹可凡指出。
对于上海话,很多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听不大懂,因此也有人担心,电影中大规模使用沪语会带来地域上的局限。对此,电影学者葛颖不以为然。他举例道,他在“关灯拆电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电影同评视频,用上海话评论电影的视频的点击量远高于用普通话评论的,可见沪语市场远比我们想象中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地区多元性的崛起,必定伴随着地域文化出现。大家渐渐发现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其实现在方言电影越来越多,不少电影里用了东北话、陕西方言等,只是现在上海话的电影好像迟于其他北方语言。因此,要允许上海独特文化的生长。”
上海话能带来“上海味道”,这毋庸置疑,但是怎样放入影片也有讲究。钱乃荣就指出,上海话的运用不单单是语音,还有词汇、语序以及整个语言体系的问题。“拍上海题材影视剧时,最好先写成上海话剧本。方言词汇总是比书面语生动,而且上海话有上海话语法,有些上海话的语序跟普通话里不同,比如:普通话中是‘我吃了饭了,但是上海话里是‘我饭吃过了。像小说《繁花》中,并不都用上海话词汇,但是大家觉得上海味道比较正,用上海话读出来很亲切,就是因为他用的是上海人的表达方式、讲话习惯。所以如果只是用上海话来说普通话写的剧本,依然会缺乏沪语特色。总之,我觉得应该积极支持拍沪语电影,若希望里面的上海话标准,可以让上海演员来演,不然的话,用配音的方法,各种方法都可以。”
在影院里,每个观众的观影感受都会不同。一些观众听到上海话就感到亲切,并不在意是否足够“纯正”。但对某些观众而言,让一个北方人说一口吴侬软语的上海话,如同让一个大大咧咧的东北姑娘穿上一件精致的旗袍,举手投足间总是不着调的,那么上海演员就有着天然的优势。
“如果上海题材的电影能请上海的演员来演就更好。王志文的上海话非常好听,只是屏幕上不说而已,陈冲的上海话那是相当标准、非常纯粹,还有一些上海的青年影视演员,如胡歌、孙俪等,都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很有味道。据说王家卫要拍的电影《繁花》中会用上海演员,会说沪语,我很期待。”曹可凡说道。
在《上海王》中,曹可凡饰演的洪门师爷并不完全说沪语,他可能对这人说的是上海话,转身对另一人说起了普通话。在一些人看来,难得有一口标准的老上海话,这不是稀缺资源的浪费嘛!但胡雪桦自有想法,虽然作为上海导演,在上海话的运用上更有优势,但他讲究的不是多,而是是否到位。《上海王》中前半部分,很多人物说沪语,但是到了后半部分说得越来越少。胡雪桦解释,人物的语言也要随着人物所处的时代、環境变化而变化,譬如曹可凡饰演的师爷会面对不同的人,因此对不同背景的人就要说不同的话。“上海本来就是五方杂处的,现在在一个餐厅里,能听到上海话、外地方言、普通话、英语等各种语言,以前的上海也是这样,非常多元。”
上海题材已经不是上海独有的资源
《罗曼蒂克消亡史》这个片子完全是由非上海的导演,带领着一拨非上海的演员,在非上海的地方取景拍的一部反映旧上海众生相的影片。这也让一些影评家看到了一种新现象。
葛颖指出:“我们上海从事电影的人一直在纠结上海题材的问题,因为一直没有出现让我们非常满意的作品,但是从历史上讲,上海题材或者说上海电影又是那么的辉煌,所以这种落差,到今天还是我们的一个心结。而《罗曼蒂克消亡史》完全突破了我们对于所谓上海题材的那些固有的观念,我觉得这个创作群的突破是非常好的信号,也就是说上海题材已经不是上海独有的东西,其他地方的创作者,海外创作者都可以拍。之前我们老觉得好像别人要拍老上海的东西,非得来车墩影视基地取景,但这次程耳完全在北京搭的景,说明目前我们上海的所谓优势都被打破了,对我们这边而言也是一个挑战。从比较公允的心态上来看,上海题材真的不应该是一个地区创作群独有的资源。”
为什么具有上海味道的景可以在别的地方搭起来,某种意义上还不影响人们对上海味道的辨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探究的话题。“可能上海这个城市代表着现代历史上的某种普遍性。上海具有某种非地方性的地方性,它本身就是一个在流动中产生并且在流动中持续的城市,和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不像其他地方必须依托于一方水土一方人才能造就那种独特性。《罗曼蒂克消亡史》它不是一部地域片,也并非纯然意在怀旧。该片在上海之外搭建了‘上海,展示了上海在中国现代地景呈现上所具有的‘非地域性潜能。当然,要在北京棚里把某种上海意味的景搭出来,要拍出既抽象又富有时代感的上海味道,对摄制组是一个考验。”
《罗曼蒂克消亡史》放映后,很多观众对里面的音乐印象深刻。汤惟杰也认为该片音乐的设计颇见巧思,没有被那几首所谓海上金曲圈拘住想象力。“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五方杂处,世界各地的资源都可能汇聚于此,因此音乐元素也非常丰富,并不只有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上海老歌。所以不用纠结于非要用很多熟悉的上海元素,上海本身是变动不居的城市,很难确定哪些是纯上海因素。”
“只有上海人理解上海这座城市,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我也不太同意‘上海人对这个城市有更权威的阐释这种观点。”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指出,“从电影史看,主要形成了两种表达上海的视角:一个是外部视角,一个是内部视角。1949年以前的上海题材电影很多都是内部视角,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把抗战后上海人的生活艰辛,内心对于公平、对于光明、对于进步的呐喊刻画得淋漓尽致。最近二十年主要是外部视角,像陈凯歌、张艺谋、斯皮尔伯格等都拍过上海。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拍上海,这样是对上海丰富性的最大肯定。上海在开埠以来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拥有了巨大的包容性、开放性以及到今天所形成的异常复杂的文化特质,很难用一句话或者特定的东西来概括其丰富性,任何这样的概括都会把上海刻板化,所以我们就直面它的丰富性,从各自的角度去表现、理解它。”
《上海王》,展现一个血气方刚的上海
日前,上海电影博物馆举办了一个特别策划:“中国力量·上影制造——胡雪桦与他的朋友们”放映活动,展映胡雪桦导演的“王·三部曲”系列电影:《兰陵王》《喜玛拉雅王子》《上海王》。我去观看《上海王》的那天,正巧胡雪桦也在,放映结束后,很多观众不愿离去,围着胡雪桦合影、聊天,观众们感慨最多的就是,总算看到上海本土导演拍的很有上海味道的电影了,并希望胡导能多拍一些。的确,近二十年,眼看着诸多外地“大厨”热火朝天地烹饪出各种号称上海口味的影视大餐,而上海本地的“厨师”的灶头却冷冷清清,上海观众自然着急啊。
“胡雪桦导演的《上海王》是属于内部视角的重要收获。最近二十年的上海题材电影的内部视角比较薄弱,相对外部而言,内部这条腿要短一点,现在两条腿长齐了,这也是重要的成就。”石川说道。
胡雪桦告诉我,身为上海导演,一直有拍一部上海题材电影的情结,但是并不想草率地推出。因此《上海王》整整“熬制”了十多年。
2002年时,胡雪桦在北京碰到作家虹影。虹影聊起自己正在写的上海题材的故事,引起了胡雪桦的兴趣。经过几次的面谈、沟通、讨论后,虹影写了近万字的故事梗概,胡雪桦觉得很精彩,当即决定买下版权。虽说2003年就开始创作《上海王》的剧本,但是胡雪桦不愿速成,而是精心打磨,直到十几年后,才拿出了《上海王》,他希望展现一个与众不同的上海影像。
《上海王》讲述了洪门三代“上海王”与奇女子筱月桂之间曲折离奇、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恨情仇。很多上海题材的影片聚焦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而《上海王》中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为何选择这个时代背景呢?胡雪桦解释道:“之前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黑帮故事的电影太多了,我们拍《上海王》就要跟以往的电影不太一样。我们要营造出一个别人并不完全知道的曾经的上海。我们的故事从1905年开始,1925年结束。1900年到1925年,这是改朝换代的年代,是一个充满了激情、浪漫又非常野蛮的年代,上海的变化巨大,华洋杂处的文化状态下,各色人等,各种党派,各有诉求,鱼龙混杂。电影《上海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里讲了洪门三代‘王与筱月桂的传奇故事,讲了在这个大时代里帮会的人、革命党人、租界的人怎么在上海互相交错、相互抗争,这是之前的影视作品里几乎没有过的。”
上海黑帮故事、人物很多,为何着力于塑造一个女性的黑帮老大?胡雪桦回答道:“在我看来,上海这座城市就是一位优雅的女性。从某些程度上讲,她代表了一种现代的文明。‘上善若水,海纳百川,这就是上海的特质,就是开阔、包容、创造,同时水也代表着女性。《上海王》中,筱月桂,一个浦东大脚丫头,最后成为上海滩上的‘无冕之王,似乎是当今‘女屌丝逆袭的故事。上海这个地方就是英雄不问出处的,只要怀揣梦想,只要肯干,只要聪明,只要有机会,你就能成功,这样的故事在上海有很多。”
近日,在上戏召开的电影《上海王》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影视界专家对《上海王》在时代、人物等方面的设定给予了肯定。上海戲剧学院教授吴保和认为《上海王》在表现上海题材的电影创作当中做到了三个突破,“第一是突破了之前香港电影人给观众留下的‘上海滩的固定印象,《上海滩》背后是香港电影兄弟情仇的模式,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要突破它真的不容易,有很多电影都在这个模式里迷失了方向,胡雪桦以帮会作为背景、讲述三代上海王的设定突破了‘上海滩的叙事模式。第二个突破是在题材和电影空间上,《上海王》中,除了城市的感觉,还有租界的感觉,这在电影空间上有大大的突破,所以《上海王》给我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是:终于不是‘车敦一条街的感觉了。第三个突破就是,最近十几年,由于张爱玲的走红,上海被打上了‘小资的文化符号,但其实上海有很丰富的城市特征,《上海王》中的女性就突破了‘小资的局限。”
“上海女王的塑造就给了那些把上海男人塑造得娘娘腔的创作者一记响亮的耳光。”石川直率地说道,“很多人认为,上海是非常女性化的城市,胡雪桦的片子展现的就是血气方刚的上海。为什么不可以从这个角度体现?哪怕是女流之辈,但也是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杰。”
《上海王》虽未公映,但已参加了不少国际影展,也赢得不少外国人士的称赞。金球奖评委会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成员安德里·加蒙德先生赞叹,《上海王》中精彩的打斗场面以及复杂多变的细节,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美国电影人、学者乔纳森·巴尔曼先生给予了《上海王》高度评价:“这是部美丽壮观的史诗电影,使我更想深入地了解上海的文化和历史,也使我不禁联想起由意大利导演瑟吉欧·莱昂导演的《美国往事》。”
身为上海人的胡雪桦是否更能把握上海题材呢?胡雪桦回应,这之间有关系,但并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联。有关系是因为在上海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对这座城市自然有着真情实感。与此同时他表示,自己在国外求学、工作的经历,让他有了一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感受,让他对家乡看得更加清楚,更客观、更宏观。“走得越远,对家乡看得越清楚。这个清楚并不是距离的远近亲疏,而是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对这个城市会从比较客观、宏观的角度看,从而把握住它的本质,这是很关键的。”在胡雪桦看来,上海这座城市的本质特征是:外来文化,这迥异于北京的传统文化。“在城市的文化的融合方面,上海是首屈一指的,过去是,今天还是。因此,我们要有一个开阔的视野,上海这个城市的坐标一定要划在国际上。”
上海题材的电影如何“熬制”上海味道
对于外地和上海的艺术家而言,上海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但是是否能“熬制”出浓浓的“上海味道”,则考验着他们的功力。
曹可凡认为,要拍出“上海味道”,首先要对上海文化熟悉,否则容易造成两层皮。“虽然我们是上海人,但对民国的解读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对老上海的理解,基本上还是流于肤浅,碎片化的,大多数拍民国时期上海的电影,鲜有成功者。你要拍出上海文化的骨髓,必须沉浸在上海文化里很多年,否则对它的理解可能是有偏差的,不一定能掌握住那种调调,上海人的那种范儿。”曹可凡回忆,黄宗英曾跟他讲,赵丹过去演李时珍时,平时生活中家里头也穿着李时珍的衣服,他的理由是,必须生活中就穿着这衣服吃饭、走路、喝茶,这样到拍戏时才会很自然。“现在是 IP时代,大家都在赶时间,但是你真的要拍出一点上海味道,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读十本参考书都不够,还要跟文化进行大量对话,对城市的文化要有参悟。否则即便是一个大艺术家,若远离上海文化,很难拍出上海的真正的神韵。”
“有一些影片中的上海只是一个基本背景而已,是因为对上海不了解。要拍上海,必须要了解上海是怎样的城市,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在那个历史阶段会发生一些什么事,人们会怎么做。”胡雪桦说道。为了拍《上海王》,他研读了很多老上海的资料,并从那个年代的人物身上,感受到了宝贵的品质:情与义。“《上海王》这部电影不仅展现了清末民初的上海,还探讨了人性,与现代社会、与现代人也有关联。我们希望通过细节,折射出那个年代的风貌,展现人的情感以及一种处事规则,让现代人了解那个年代的人,并关照现在的生活,在内心里边呼唤一点丢失的东西和希冀的东西。《上海王》这部电影归根结蒂就是讲:情与义、情感与规则。这对现代人还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罗曼蒂克消亡史》讲述了1937年大动荡前夕,上海滩风云显赫的陆先生正面遭遇侵华日军施压,被卷入一场暗杀阴谋,身边朋友一一惨遭牵连,乱世当前,大佬、小弟、弱女子等往昔人物走向了不同命运的故事。影片中,小跟班间比脚的大小以及闲聊“童子鸡”等细节也引发了争议,一些观众认为情节太碎或太低俗,但这些看似跟整个剧情无关的台词,一些看似狗比倒灶的细节,恰恰是让葛颖看得欣喜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影片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把这种鸡零狗碎的东西拍出来了,把上海的黑帮老大、妓女、小马仔等边缘人物纳入到整个影片的所谓‘凝视的范畴,让他们作为主要角色出现。整个影片其实并没有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完整故事,只是有人物线索,很多都是碎片化、多线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树立了一种美学标准,我借用昆汀的片名,把它叫做‘低级趣味审美,也就是民间审美。程耳作为一个影迷,看了很多西方的作品,像昆汀的作品,那完全是一种民间的街头美学。《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用上海话,很多人只是感受到一种地域性的表达,但是我觉得更是支撑了一种民间审美。‘上海味道也是一种上海民间的味道,比如说上海有十里洋场,上海大亨杀人不像北方人那么生猛的,亲自是不动手的;他们是要有腔调的,哪怕喝黄酒也是要有吧台的;有时在杀人之前,是很关心生活里面很下作的事情的,这些都是上海的码头文化。”葛颖说道。因此,他强调,创作者千万不要怕“俗”,如果重视民生的话,就不要居高临下地把老百姓的趣味贬低为“低俗”。“这个时代,民间性正不断被强调,被重视,被尊重。所以我觉得《罗曼蒂克消亡史》在这方面有很大突破,也给我们启发。之前很多创作者习惯于主题先行,但‘上海味道在于生活中的那些人以及听说的那些人,所以创作者现在真正要补的一課是,先去了解老百姓喜欢什么。尤其是上海本地的创作群体,敢不敢把老百姓的真实趣味拍出来。”
近年来,在上海题材的影视剧中,“老上海”被很多导演眷顾,因此出镜率比较高,而“新上海”却很少露面。对此,也许有人会反驳,近些年在上海拍摄的影视剧很多啊。的确如此,但大多数情况上海在其间只沦为背景而已。“我不认为这些是上海的电影和电视剧,里面的家长里短的细节,没有真正城市的灵魂、城市人的灵魂,只是概念化的上海。我称之为‘绿幕扣像,把片子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搬到苏州、南京都一样。我觉得只有像黄蜀芹导演的《孽债》这样的作品,才真的反映了上海人的精神风貌,深入刻画了上海人的灵魂。”曹可凡说道,“当代生活是那么丰富,作为创作者对生活不能视而不见,不能没有艺术感受力。”
胡雪桦透露,他也特别想拍一部反映现代上海的电影。“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目前缺少深度的反映,这个大的时代真的需要更多影视作品来记录、展现。但是要拍的话,难度也很大,关键是剧本。剧本首先要好,现在很多人都在写,但写不深。”
上海这座城市,有老上海的想象,也有新上海的现实;有神秘莫测的黑帮史,也有风起云涌的金融史、革命史等。上海有太多的历史皱褶可以展开,这座城市中的人有太多的情感需要抒怀,如何“熬制”出一桌桌有着浓浓的“上海味道”的影视大餐,这是观众的期待,也是时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