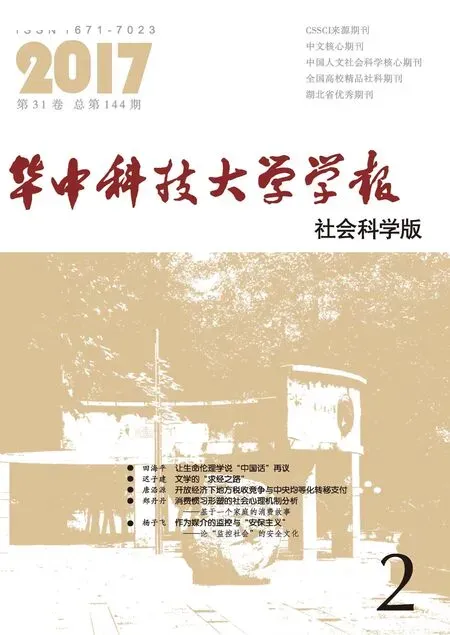神性书写与迟子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
刘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神性书写与迟子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
刘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散文化”因素或者倾向,不惟迟子建所专有,从现代白话小说伊始的鲁迅、郁达夫到沈从文、废名等人,尤其是萧红就更有典型性;对百年汉语新文学,小说的“散文化”几乎可以做连续性和谱系性的整体研究。迟子建小说中的宗教情怀、神性因素虽已为很多研究者注意,但鲜有人能够从神性书写的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做出细致的梳理分析。本文从神性书写中的风景、人性与“抒情传统”、历史与现实中拯救小说的日常生活美学、作为素材和散文化建构要素的神性书写等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迟子建神性书写对其小说散文化倾向的关键性影响。
神性书写;风景描写;诗性;抒情性;散文化倾向
鲁迅作为白话文、现代白话小说的先驱者,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他小说里的呐喊、彷徨、失望、绝望和批判等,但迟子建点评鲁迅小说,会选择《社戏》(1922),认为它“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学家骨子里的那股忧愁和浪漫的情怀”,并认为没有这样的情怀,是产生不了像《药》(1919)、《孔乙己》《风波》(1920)、《故乡》《阿Q正传》(1921)等一系列作品,在她看来,“我读到了《社戏》,读到了一首哀婉的乡间恋曲,读到了好小说所应具有的朴素而优雅的品质。从《社戏》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鲁迅,一个满含着伤怀泪水的柔情的鲁迅,其温暖的情怀跃然纸上、令人感动。《社戏》是鲁迅写给自己的一首《安魂曲》,在他的作品中,《社戏》因为没有更多的思想之核‘哽’在其中,呈现着天然、圆润、质朴、纯真的气质。现在读它,依然是那么的亲切、感人。”[1]139-140迟子建所认为的鲁迅很多小说中有“更多的思想之核”,其实也就是萧红所认为的鲁迅是“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而萧红能够以不“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的人物比我高”[2]5-6这样的小说写作态度,才会写出《呼兰河传》宛若“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704-705的小说。葛浩文在《萧红传》中曾经盛赞萧红的简洁、不雕琢、自然得像诗样美的精炼行文,而她如行云流水般的文体,被认为是她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也令萧红后期的小说,尤其是《呼兰河传》呈现出诗意、抒情性的散文化特征。而这散文化特征在彼时以及在文学史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被主流文学思潮所接纳和推崇的。但从小说的写法和体式上来看,谁又能够否认其价值呢?以《呼兰河传》为例,如果不是如“叙事诗”、抒情散文一样的笔调和写法,未必能够实现像钱理群所说的——摹写出了代表“民族的生活方式”的社会风俗画卷。正是由于对散文化倾向小说的喜爱,迟子建更加喜欢给学生去开一个郁达夫的专题,郁达夫小说中情绪、情怀的浸润、饱蘸了许多感情的自然流动的抒情结构,肯定是吸引迟子建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文学资源的汲取,东北边地的地域性因素等影响,产生了迟子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在黑龙江这片寒冷的土地上,人与生存环境抗争的时候,会产生无穷无际的幻想,再加上这片土地四季的风景变幻如同上天在展览一幅幅绚丽的油画,所以具体到作品中时,从这里走出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其小说中的‘散文化’倾向也许就悄然生成了。”[1]140-141
一、神性书写中的风景、人性与“抒情传统”
有人认为,迟子建小说创作所显示的宗教情怀,是一种综合性的对宗教的理解、认识和情感体验,其中既有基督教、犹太教、萨满教元素,又有道教、佛教的熏习濡染。不无道理,但一切的根基和主要的影响,还是原始宗教、鄂伦春、鄂温克族的原始宗教,尤其是萨满文化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奠基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之上。迟子建在《文学的“求经之路”》里讲到了民间神话和原始宗教对自己的影响,她在作品里常常写到的鄂伦春和鄂温克民族(《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两个少数民族信奉万物有灵,在他们眼里,花、石头、树木等都是有灵魂的。”
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曾经指出,迟子建能够怀有如儿童一般的赤子之心,拂去世俗矫饰,具备不为世俗和种种利益所侵扰的眼光和观察力,可以激发更多的灵感,取得他们读取世界和人生乃至人性的途径,从而能够塑造富于诗意的艺术世界。而在童心与诗心的烛照之下,作家笔端常常流露“我向思维”的特征,将周围的一切事物等同于有生命的“我”,把物和整个世界都当做有生命的或者说是情感投寄的对象来加以对待[4]147,这一特征表现在迟子建小说大量的风景描写,尤其是泛着神性的风景描写当中。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比比皆是的万物有灵的风景描写,像“顷刻间,森林已是雨雾蒸腾,一派朦胧了。雷公大约觉得这雨还不够大,它又剧烈咳嗽了一声,咳嗽出一条条金蛇似的在天边舞动着的闪电,当它消失的时候,林间回荡着‘哇——哇哇——’的声音,雨大得就像丢了魂儿似的,四处飞舞,空中出现的不是丝丝串串的雨帘,而是一条条奔腾而下的河流了”[5]57,等等。迟子建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北极村童话》可以说是她写作的出发地和回溯地,这与她早期的很多作品《秧歌》《原始风景》《东窗》一起,都有着不少这种视万物都有生命的风景描写。很难想象,如果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略去了充盈了神性光照的风景物事的描写,小说还能否成为那样富于诗性和抒情性地展现鄂温克民族几十年生活变迁的“叙事诗”。万物皆有灵的信念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有了《越过云层的晴朗》这样以动物——一条狗的视角来叙事。“狗”的视角,人作为被“狗”来观看和叙述的对象,叙述视角设置为一只狗,这可能是万物皆有灵性的最实在的一种尝试方式,一种视万物皆有生命的观察事物的感知角度和看待事物的立场与态度。
只有具备了超越时代潮流和世俗化写作的诗心,才能够有这样的诗性思维和创造性想象,才能够在风景描写当中达到一种物我不分、物我两忘的境界,就像沈约《郊居赋》中所说的:“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达到作家主体与创作对象的客体浑然为一而兼忘的境界。能够突破或者超越外物为物和只是物的限制,打通人的各种感觉、知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萧红的后期小说哪怕是纪念性文字《回忆鲁迅先生》当中,就有很多突破物的限制、打通人的感觉、知觉能力的描写,但并不像迟子建这样鲜明的神性书写和神性光照下的各种感觉、知觉能力的打通。迟子建有一段描写月光的文字,理应得到足够重视:“我曾经在一篇童话作品中抒发过我的一种奇想。我背着一个白色的桦皮篓去冰面上拾月光。冰面上月光浓厚,我用一只小铲子去铲,月光就像奶油那样堆卷在一起,然后我把它们拾起来装在桦皮篓中,背回去用它来当柴烧。月光燃烧得无声无息,火焰温存,它散发的春意持之永恒。你听到这也许会发笑吧,可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有这样的幻想。我生于一个月光稠密的地方,它是我的生命之火,我的脚掌上永远洗刷不掉月光的本色,我是踏着月光走来的人,月光像良药一样早已注入我的双脚,这使我在今后的道路上被荆棘划破脚掌后不至于太痛苦。”[6]204月光的生命感、富有诗意,“我”与月光之间毫无间隔,月光几乎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它很典型,谕示着迟子建能够自如打通物我的界限、持物我同一之感。这段文字对于迟子建的写作来说,又几乎是一种象征和隐喻;“月光”的象征和隐喻,也一直贯穿在迟子建的小说当中。在迟子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树下》中,七斗与米三样婚礼的前夜,有着反复出现的对月光的描写,月光俨然已经与七斗的心灵和一举一动交织相融、绾合在了一起……“月光满满荡荡地从天空泻下来,在雪地上映出了许多美丽的光影”(依然没有从姨妈、姨父托梦的梦境中走出),七斗漫无目的地在房屋的周围散步,“月光下的山脊呈现出清亮的奶白色,就像涂了一层蛋清一样”,“一路上她不停地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映在雪地上的月光,比较着哪一种光晕她更喜欢”,结论是她更喜欢月光了。看到鄂伦春人的马站在树下,她知道鄂伦春人来喝喜酒了,“她没有走进米家,因为她很清楚走进去意味着什么”,她走回自己的木屋,月光与她的心情交织在了一起,那样地了无间距:“她没有点灯,她就坐在黑暗中,月光透过窗户,只给窗台附近的地面和墙壁留下一些乳白的光影,而其他地方它却爱莫能助。七斗喜欢这种半明半暗的氛围。她坐在暗处,越发体会到窗外月光的明亮。”而七斗估计鄂伦春人的马队就要离开时,她披着棉大衣走到外面:“这时月亮因为释放了一夜的光芒而显得十分苍白疲倦,它形象淡泊地映在西边天上,就像一片薄纸一样,似乎稍微来一股风就会把它吹散。”[7]224-227月亮和月光也读得懂七斗的寂寂心境。
无论是万物皆有灵性的风景描写,还是打通了人与物的界限、能够物我不分和物我两忘,这样的风景描写,既有神性、灵性,又令迟子建的小说不是以故事性强和浓烈的小说质感取胜,而是铺展着诗意化、散文化的小说质地。五四运动以来,风景在作家笔下慢慢具有了现代性的精神表征,小说家笔下的风景描写,作为主体的小说家常常是跟作为描写对象的客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主客体拉开距离后,作家和外部事物的关系,更多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借用柄谷行人的话来说,“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写风景的人“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8]12-15。解放区文学的经典之作里有大量的风景描写,其中,有非常客观性、不带情感色彩的风景描写,带明显愉悦和欣赏的正面情感的风景描写,也依然视风景为客体和“他者”。当代作家能够不把风景当“客体”和“他者”来写的,也比较难得。迟子建没有把风景看做与自己拉开距离、仅供自我观照的“他者”,而是打通了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知觉,把自己和景物融为一体。迟子建的风景描写,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很多作家那种视风景为“他者”与“客体”的一种自觉反拨。在有的研究者看来,当代小说难以找到好的、传神的风景描写,其实就和作家叙事耐心的丧失有很大的关系。“诗性产生抒情性,而抒情性的获得和一个作家的叙事耐心有关”;“当代的小说显得单调,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现实世界越来越没有感觉,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没有了声音、色彩、气味的世界,正是心灵世界日渐贫乏的象征”[9]177。迟子建小说里泛着神性光辉的风景描写,还原了世界本来的声音、色彩与气味,而且,往往比对话、心理描写更加能够衬托和反映出人物内心情感和情绪的流动与复杂况味。
不止是风景描写里内蕴的神性色彩,迟子建很多小说里神性书写还氤氲出人性的诗性和抒情性。《逝川》里的泪鱼,是有灵性和神性的,捕捉泪鱼更是有着神性谕示般的仪式。泪鱼每年九月底或者十月初从逝川上游哭着下来了,阿甲渔村的渔民再累也要打上几条泪鱼,才算对得起老婆、孩子和一年的收获。渔妇们则赶紧把丈夫捕到的泪鱼放到硕大的木盆中,一遍遍地祈祷般安慰它们,它们果然就不哭了,然后次日再放生它们。老吉喜要为年轻时的恋人胡会的儿媳接生,错过了捕捉泪鱼,当她终于能够赶到逝川捕捉泪鱼,却一无所获;许多渔民开始将捕到的泪鱼放回逝川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木盆的清水里竟游着十几条美丽的蓝色泪鱼。泪鱼是有神性的,而为了接生错过捕捉泪鱼,也隐喻了当年吉喜在胡会另娶后一直孤身的人生,可吉喜还要为胡会的儿媳接生,这种人生的哀伤、无助、凄凉和泪鱼那神性意味的蕴藉,让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腾挪出诗性和抒情性的空间,这种散文化的笔调,是那种被经济和商业意识形态影响的写作所不可能拥有的。《白雪的墓园》中父亲死了,变成一颗红豆藏在母亲的眼睛里,直到母亲去墓园看过他的坟茔,他才安心留在那里,这时母亲眼睛里那颗红豆消失了。母亲眼中红豆的在与消失,成了一种神性的隐喻;《亲亲土豆》中妻子要离开丈夫的坟,坟顶一只土豆滚落,一直滚到妻子脚边,是“仿佛一个受宠惯了的小孩子在乞求母亲那至爱的亲昵”般的“跟脚”,生命逝去、无限悲伤当中的神性书写,成为慰藉人心的一种力量。哪怕是首部长篇《树下》中姨夫强奸了少年的七斗,迟子建也为被人行凶全家暴毙的姨夫一家人寻觅到了灵魂安妥的家园、另外的世界,七斗还在梦境里数次与他们不失人间温暖地重逢。《额尔古纳河右岸》《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群山之巅》里,太多由神性书写所带来的人性的诗性和抒情性,它们影响形成了迟子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但迟子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并没有给作家带来如期而至的热闹喧嚣和荣光。跟当年后期发生写作转向的萧红在文学史里一度所遭遇的情况相似,迟子建是少有的没有进入当代文学史叙述谱系的重要作家,以致于会被认为在别人收稻的时候,她却在捡拾弃置在收获的田野上的稗子。当年的先锋文学姑且不论,对于关注现实人生的小说家,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是一味屈服于事实,只在事象层面描绘并求证生活真相,还是也呈现事实背后的心灵轨迹和心灵跋涉?“价值想象力的获得,首先就要求小说家必须脱离就事论事的困局,要扎根于诗性、梦想,寻找灵魂中还未被充分认知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力量和可能性,有了这种精神腾跃的空间,小说就不仅是描摹、发现,它还是创造。小说不单要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它还要告诉我们生活可能是怎样的。”[9]177
近几十年,沈从文、陈世骧、普实克已经先后提出并创造了“抒情传统”的语境,加上唐君毅、徐复观、胡兰成、高友工等人的论述,抒情传统的再发现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场重要事件。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1961)中指出生命的发展,“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形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英文稿首发于1972年,提出了“抒情传统”的概念。而到了高友工,他已经将起自文体的“抒情传统”,扩展为整个文化史上某一些人的“意识形态”,包括他们的“价值”、“理想”,以及他们具体表现这种“意识”的方式……并因此以“抒情美典”名之。普实克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演变呈现了由抒情的(诗歌)过渡到史诗(叙事)的过程。王德威本人则是把对抒情传统的讨论延伸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但主要是以启蒙与革命等话语作为参照系来理解抒情传统的现代传承[10]6-63。在这种情形下,有研究者已经在考察“70后”作家在小说写作上对抒情传统的赓续和扩展[9]176。先前就有研究者在讲到迟子建是没有进入文学史叙述谱系的重要作家的时候,就睿智地提出迟子建的写作,是自有谱系的。而笔者要进一步说,若要考察当代文学与抒情传统之间的关系,迟子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例证,迟子建的写作,令抒情传统有了非常动人的一个当代传承。
二、神性书写中的日常生活美学
巴赫金认为,在作家长篇小说所营构的“世界”中,“目力所及和已经认识把握了的、真实可靠的东西,仅仅是地球空间里的一个孤立的小碎块,也只是从真实时间中分割出来的同样不大的一个片段;其余的一切都影影绰绰地消失在迷雾中,与彼岸世界,与孤立的、理想的、幻想的、乌托邦世界纠结交织在一起。问题不仅在于彼岸和幻想的东西填补了贫乏的现实,把现实的碎片组合、充实而成为一个神话的整体”,更为重要的是,“彼岸的未来,脱离了地球空间和时间的水平线,作为彼岸的垂直线扶摇直上到达真实的时间流。这时,彼岸的未来使得真实的未来以及作为这一真实未来活动的舞台的地球空间变得虚无空洞,使一切都披上了一层象征的意义,凡是不能作为象征理解的,则全都失去了价值而被弃置脑后。”[11]254巴赫金言称“凡是不能作为象征理解的,则全都失去了价值而被弃置脑后”,这句话固然有点绝对化,但是,他的这段话,明确了作家的长篇小说不能只局限于目力所及已经认识把握了的、真实可靠的东西,强调彼岸和幻想的东西对作家长篇写作的重要性。而如果能够藉由彼岸的未来——作为通过彼岸的垂直线扶摇直上而到达了真实的时间流,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多么重要,迟子建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在这个此岸到彼岸的垂直线上,神性书写,便托举着迟子建从现实世界来到了文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题材,迟子建的神性书写,都恢复了历史与现实当中日常生活的审美性和复杂性。迟子建在一种历史与现实的“伤怀之美”当中,承续和恢复了文学的抒情传统。
面对历史题材,迟子建自言:“我们读惯了某一类描写历史的‘大’作品,把他们奉为了‘经典’,可能接受《伪满洲国》就会艰难。我觉得一部作品,如果呈现的是教科书的‘历史’,不管人物如何鲜活,都是失败的。我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只愿意沿循着文学的路。这样的路,在我心目中才是正路。”[12]60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其实就是一部关于神灵的史诗:“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迟子建自己,基本把《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解读放在行将消逝的文明的挽歌之上。而我倾向于《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关于神灵的史诗。”[13]101“十七年文学”的历史书写,采用的是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方式,也就是迟子建所说的描写历史的“大”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以及由其催生或者陆续出现的其他“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小说,能够提供一种“复线的历史”(杜赞奇语),对于纠偏或者说补充“十七年文学”中“红旗谱”和“创业史”两种基本类型的那种宏大的民族国家单线历史叙事,是有价值和意义的。《红高粱》《古船》《活着》《白鹿原》《长恨歌》《尘埃落地》《丰乳肥臀》等小说的出版,令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叙述模式,“村庄史”、“家族史”、“民间野史”、“个人史”等对应“民族国家史”的“小历史”,也不断成为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评价这类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小说的常用研究视角。但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并加以反思,小说作为历史建构的一种方式提供了远远比历史研究丰富的日常生活审美,而且“复线的历史”似乎并不必然地带来文学审美的丰富性,一种极端的倾向,是忽视人在历史中的复杂性,甚至将暧昧、幽暗、矛盾的人历史符号化。所以,像迟子建新世纪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群山之巅》,虽然所涉及的题材都已经在中国当代文学被许多作家做成了“民族志”和“村庄史”。研究者考虑的却是,迟子建怎样舍弃建构“复线的历史”的努力,转而将自己融入人间万象,和小说人物结成天然的同盟,形成共同的担当,“从历史拯救文学”,进而逐步建立以“伤怀之美”为核心的文学和日常生活的美学[14]15-16。“迟子建的兴趣不在建构‘复线的历史’,她别出新径,从历史中拯救小说。如果一定要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题,我觉得最切近的是迟子建自己说的‘现实和梦想’。”[14]17-18在历史书写当中恢复和建立日常生活的美学,所有的神性书写也都是与日常生活交融,并且令“伤怀之美”为核心的日常生活之美学特征得以凸显。不惟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的日常尤其跳神,是神性的又是日常的。就是“我们”部族的一切活动、日常,也都有着与神灵、与自然之神浑然一体的意味,神性色彩的文学书写令小说的日常生活呈现一种诗性、抒情性。达西与鹰的故事,母亲和尼都萨满的故事,等等,无不如此。妮浩萨满在成为萨满的时候,就得到了神的谕示——每救一个人,她就失去一个自己的孩子,可她还是要去跳神,去救人。在迟子建看来,妮浩萨满本身就是神灵,但其神性,又是与鄂温克部族生活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迟子建自己都说:“如果把萨满请下山,让他在哈尔滨给一个人做法,他一定做不了,因为这里不接天不接地,没有气场,没有灵性。可是在大自然里面,在青山绿水当中,神灵就会显现。”[12]61-62也就是说,这神性是与自然和鄂温克人的日常生活浑然一体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中出现多次的部族男女情爱书写也是藉由自然界的“风声”来呈现,有着人与自然浑融一体的生活美学意味:“深夜,希楞柱外常有风声传来。冬日的风中往往夹杂着野兽的叫声,而夏日的风中常有猫头鹰的叫声和蛙鸣。希楞柱里也有风声,风声中夹杂着父亲的喘息和母亲的呢喃,这种特别的风声是母亲达玛拉和父亲林克制造的……”[5]8(省略号为笔者所加)《白雪乌鸦》写作准备阶段,迟子建查阅了大量资料,但是她没有陷入宏大历史叙事的套路,也没有让自己的小说成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复线的历史”,散落其中的宗教情怀和神性书写,是与当时人的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呈现一种日常生活美学。
“事件、细节只是文学世界构成的现实元素,是真实性幻觉得以维持的物质基础;它们要想获得生机,还需要一盏放置在内心深处的‘台灯’的照临;而宗教情怀——慈悲、伤怀、哀愁,正是这样的‘台灯’,它打通了迟子建的心灵,使她的‘世界’有了光,飘出了特有的气味。”[15]33如果是惯常那种描写历史的“大”作品,写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会使真实作者尽可能不去侵犯“叙述者”和“隐含作者”;而且,自现代以来,中国小说获得成熟现代小说经验的问题上,亟须进益的是限制叙事和限制视角的采用。但迟子建的文学书写,都不能用这样的文学观念去规训和“定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小说,可以说是“作者”无所不在介入到写作中的文本,“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和小说中的人物确实存在着无法分离的混合性。迟子建在写作过程中,自己其实已经是文本的一个有机部分,就像她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小说所弥漫的那股自然而浪漫的气息已经不知不觉间深入到我心灵中了。”[14]21无怪乎苏童会这样说:“迟子建的小说构想几乎不依赖于故事,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个人的内心感受折叠而来。”[14]25如果没有这种作者主体生命和情感与文本的浑然一体,也就没有小说文本的诗意化、抒情性和散文化倾向。
历史题材,迟子建是沿循着文学的路,而现实题材的小说,要挣脱事象层面的束缚、不是一味求证生活真相,并不容易——且不说近年流行过的“非虚构”写作,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的“新写实”,一些作家俨然已经踩在了从虚构文学前往纪实文学的门槛上。在“新写实”们“本色”的“生活流”书写中,有研究者已经表达了其忧虑:文学“它的本质精神是在与现实的抗衡中升华出来的,因此才有虚构另一个现实物质世界以外的世界的必要性”;“在现实上面,有精神的天空;在现实下面,有精神的深渊。天空高扬希望,深渊传达绝望。谴责‘新写实’的文章说这些作品使人看不到希望,倡扬‘新写实’的文章说这些作品并不让人绝望。我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也不知道‘绝望’在哪里,我从大多数的‘新写实’作品中感受到的是无可奈何的情绪。”[16]107很多小说其实是在过度拘泥于现实中丢失着小说作为艺术品的品性。迟子建小说中的神性书写,是她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恢复和重建一种日常生活美学的重要一翼,使她的小说在一种散文化韵致当中呈现一种诗性与抒情性。《逝川》《亲亲土豆》《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晚安玫瑰》《群山之巅》,等等,莫不如是。
三、神性书写中的小说素材与故事性向抒情性的转化
同样是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在神性书写上面,迟子建与萧红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却是秉持不同的取径和价值判断。萧红对跳大神等活动,是冷眼旁观,采取限制性叙事和视角也是意在呈示其背后的人性之恶,她认为这是一种作假的行为——跳神不止没有救得了小团圆媳妇的命,反而是加速或者说促成了她的殒命。在迟子建这里,她和她小说的隐含作者,不止相信萨满是通灵的,对自然神性也满怀敬畏。神性书写,成了迟子建小说中常见的笔调,甚至直接启发她的构思和成为她小说的写作素材。前面举例的迟子建的一些小说,都是如此。
以中篇小说《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为例,这个小说故事性并不强,如果真要找出它的“故事核”的话,就是迟子建自述的:“前年飘雪季节,我在故乡,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山上一个林场派出所的警察,抓到一个贼,擅自把他放了。因为警察到案犯家调查时,发现他家一贫如洗,面临断炊的窘况。而这个贼,偷的不过是用以果腹的一袋米。这个警察不仅把贼放了,还买了粮食和豆油,送到案犯家。”“这个故事看似‘暖’,其实背后是‘冷’的。我要探究的是,这‘冷’缘何而来?来自民间的‘暖’,能不能抵御人间种种的‘冷’呢?”“在我熟悉的鄂伦春人中,他们人性中的‘暖’,也是存在的。不过,少数民族人性中的‘暖’,往往是与他们信奉的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宗教,总脱离不了神话的色彩。于是,云娘这个形象悄然出现了。”[17]26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迟子建小说构思与神性书写之间的密切关联。而神性书写成为小说素材和情节,尤其表现在这个中篇所设置的那对提着红鱼去为儿子结阴婚的夫妇的故事和情节上面。没有神性的慰藉,这对老夫妇怎样面对孤苦的人生?而云娘的狗嘎乌最后以衰老的身躯越过铁轨,用死亡阻止了快速列车的前行,让老夫妇终于能够因为火车的暂停而踏上了快速列车。“小说中的顺吉,在结尾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样有神的夜晚,以后再也不会有了!’而我是多么希望这样有神的夜晚,以后仍然存在啊。因为有神的夜晚,即使再黑暗,我们的心里,也会有丝丝缕缕的光明!”[17]26到了《群山之巅》里面,仍然有绣娘、安雪儿这些神性的人物以及相关的故事与情节。神性书写,在迟子建这里,已经化身为小说的素材、故事和情节,就像迟子建将她的心灵与小说文本合而为一一样。
在迟子建这里,神性书写,甚至影响了小说的故事性,让小说不是以故事性和情节性较强取胜,而是向一种抒情性的散文化结构和笔调转化。比如处女作长篇《树下》,《树下》可以说是七斗的女性成长叙事。少女的七斗被姨妈苛待,又遭到姨夫强奸,但姨夫一家被邻人枪击射杀全家暴毙后,七斗没有心怀怨恨,反而是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怀原谅和宽宥了他们。如果我没有数错,小说先后设置了四次梦境(第221-223、257-258、311-314、338页)——让七斗在梦里与姨妈姨夫相遇,在梦里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忏悔[6]。而七斗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仇恨在里头。在此岸与彼岸的垂直线上面,哀愁和伤怀之美化解了所有的戾气和仇恨。
宗教、神性,影响了小说故事性,导致小说故事性和情节性并不强的一个最为典型的小说文本,应该说是《晚安玫瑰》。我很想把迟子建的《晚安玫瑰》与乔叶的《认罪书》作一个对比研究,都是女性成长叙事和复仇叙事的文本,却有着明显不同的小说气质。《认罪书》中的金金,是母亲与邻人哑巴所生,这种不伦的出身,是一种“创伤性体验”,但金金并没有向生父复仇,而是选择了另外的复仇对象。复仇的缘起,是由于金金被“始乱终弃”这样一种女性的情感仇怨,后来才转向对梁家家族罪恶和历史之恶、普通个体身上“平庸的恶”的揭示和反省,而这一切,经历了一个叙事逻辑的转换,就是对恶的揭示,让位于一种复仇叙事。小说以金金为主线进行的叙事,偏重的是对复仇行为、复仇过程和复仇结局的展现。小说故事性和情节性是很强的,当金金的复仇目标达成后,小说也以善必胜恶和因果报应而较为仓促地结尾。《认罪书》的复仇叙事,更多体现中国复仇之作所惯常的“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愉悦感”和因果报应的善恶伦理。所以《认罪书》的故事和情节是很吸引人的,是典型的小说文本。而《晚安玫瑰》中的赵小娥,是当年母亲在上坟时被人强奸致孕,这种与金金类似的“创伤性体验”,让赵小娥将复仇的目标对准了生父。但生父的出现是意外的,赵小娥的杀人,也缺乏预谋性和长期缜密的谋划,几乎是仓促的,是一种“冲动式”、单纯为母亲报仇式的杀人行为。而与赵小娥有着相近的“弑父”经历的犹太老妇人吉莲娜(年轻时杀了设计害自己失身日本人的继父),所持的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神性色彩,消解了小说复仇叙事的强度与烈度。《晚安玫瑰》就犹如一篇散文,谁又能够否认,不是小说的神性书写维度和迟子建的宗教情怀,将复仇本该有的处处心机和人心诡诡,复仇叙事小说本该有的较强的故事性和情节性,加以疏解和淡化的呢?更不要说像写作复仇叙事小说《安慰书》北村那样的男作家,几乎是在一种层层悬疑和推理当中,以很强的故事性和情节性结构而成小说文本,并且小说情节和故事,几乎是在一种善与恶的近乎“天人交战”的方式和状态当中纠结着往前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讲,神性书写,不止浸润到了迟子建小说的字里行间,是她小说离不开的素材要件,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她对小说的构思,让迟子建的小说,从小说惯常所具有的故事性、情节性强向抒情性较浓的散文化倾向转化,具备抵达人心的“伤怀之美”。
[1]迟子建:《与迟子建对谈:鲁迅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5年第3期。
[2]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季红真编选:《萧萧落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茅盾:《〈呼兰河传〉序》,载《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4]刘艳:《童心与诗心的女性书写——萧红、迟子建创作品格论》,载《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
[5]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6]迟子建:《迟子建文集(2)·秧歌·自序》,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7]迟子建:《迟子建文集(4)·树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8](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9]谢有顺:《“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载《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10]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11](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载《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2]迟子建:《现代文明的伤怀者》,载迟子建、郭力对话笔记:《迟子建与新时期文学·现代文明的伤怀者》,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13]何平:《重提作为“风俗史”的小说——对迟子建小说的抽样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4期。
[14]何平:《从历史拯救小说——论〈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群山之巅〉》,载《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1期。
[15]郭洪雷:《论迟子建小说创作中的宗教情怀——由其长篇处女作〈树下〉说开去》,载《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1期。
[16]刘纳:《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也谈“新写实”》,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17]迟子建:《创作谈:这样有神的夜晚还会有吗》,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8年第10期。
责任编辑 吴兰丽
栏目特约编辑 梅兰
Divinity Writing and the Prose-style Tendency in the Novels of Chi Zi-jian
LIU Yan
(ResearchInstituteofLiteratur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Prose-style” factors or tendencies in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are not specifically held by Chi Zi-jian because they can be found in the initial modern novels of Lu Xun, Yu Da-fu, Shen Cong-wen, Fei Ming and other writers, among whom Xiao Hong is a typical example. For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with a history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prose-style novels can almost be studied successively and genealogically. Although the religious and divine factors in Chi’s novels have been noticed by many researchers, it is rare to see any detailed analysis on her prose-style tend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inity writing. The elaboration has three points. The first is the lyricism of human nature which is rich in the animistic landscape description and divinity writing. The second is the history writing from the tiny clues along the literary road and the revival of the aesthetic and complex value in the daily life. The third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lot and story to the lyric material for the divinity writing. In this way, the thesis expounds how Chi’s divinity writing crucially affects his prose-style tendency.
divinity writing; landscape description; poetic features; lyric features; prose-style tendency
刘艳,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副编审,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
2017-01-10
I207.4
A
1671-7023(2017)02-0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