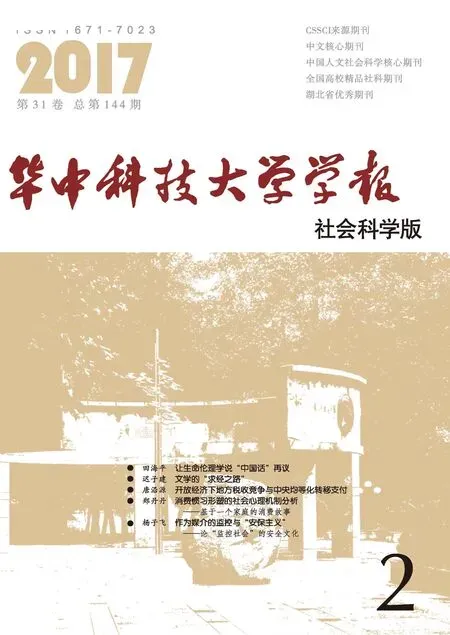论迟子建的自然写作
王均江,
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论迟子建的自然写作
王均江,
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对大自然与人性自然的热情讴歌,是迟子建的写作主题。但迟子建的写作中存在着过于自然化的倾向,甚至追求自然的奇观化。这对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思想深度、故事结构、题材选择、叙述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不利影响。如能兼顾自然与文化两翼,迟子建的创作将会取得更大成就。
自然写作;奇观化;自然与文化;迟子建
迟子建的自然写作,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道美丽风景线。然而,她的写作模式也存在着某些困境。本文拟主要通过对以下三部作品(兼顾其他)的考察,分析她的自然写作之路上的成败得失。这三部作品是:《树下》(1991年)、《穿过云层的晴朗》(2003年,后文简称《晴朗》)、《群山之巅》(2015年,后文简称《群山》)。它们都以当代小镇生活为题材,时间上又恰好分属迟子建长篇写作的最初、中间与最新,在她的创作生涯中非常具有代表性。
一、聚焦于自然的写作
称迟子建的写作为“自然写作”,首先是因为外在的大自然在她的小说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经常有人称赞迟子建的小说写得美,像五彩斑斓的油画一样。但从总体而言,其小说更像国画中的山水画卷:散点透视,山水自然占据整个画面,也有人物,甚至人物众多,但不以人物为中心,也没有中心人物,人物只是闲散、潇洒地星散在画卷的各个部分,他们经常是各行其是,甚至毫不相关,但所有人物都与自然息息相通。这种状况在《树下》《晴朗》中非常突出。这两部小说都属“移步换景”式结构,即根据时间、地点的推移划分章节,但分处于不同地点,分属不同章节的人物基本上是毫无关联的,如《树下》惠集小镇上的人们就与后文林场中、江轮上、农场中的人物没有关系,他们只是因为在主人公李七斗的生活经历中出现过而聚集到一本书中。这种作法显然是违反长篇小说写作常规的。当年大文豪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只因列文与伏伦斯基两条人物线索没有明显的关联,就引起一干评论家的讨伐,托尔斯泰也不得不对此做出解释。迟子建小说中的这种反常现象,如果从她的自然写作的角度,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即她强烈渴望直接描绘各种样式的大自然以及人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状态。也可理解为她下意识中已把自然作为她的小说主人公,不同的自然环境就是自然这一主人公的个性的不同方面。
在一般小说中,自然描写作为外在环境描写,通常是闲笔,起显示季节变换、暗喻人物的情感、烘托渲染气氛等作用。但在迟子建小说中,环境描写远远不是如此简单。首先自然是人格化的,有各自的性情脾气;其次它与人物一样,直接参与到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以《群山》为例。大自然是失意之人的天然庇护者。在仇日的社会氛围中因娶了日本老婆而一辈子无法抬头的辛开溜,“他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山林,也将自己的屈辱交付给山林,在风雪人间,不知不觉走到了熄灯时刻。”[1]294犯了罪的唐眉则把大自然当做自己的囚禁之所。大自然也是孤单之人的天然盟友。辛开溜就靠着它在晚年以游戏的心态打赢了一生中惟一让他扬眉吐气的一仗:他与山林联手让辛欣来安然躲避了一年的时光,不是为了包庇罪犯,他想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而非逃兵(这当然不可能证明)。大自然还是人类的永恒情人,年轻时的绣娘曾是一个出色的舞者,她认为“好舞蹈应该跳给月亮看,跳给河流看,跳给野花看,跳给心爱的马和心爱的男人看”[1]68。大自然也是永恒的启示者与安慰者。安雪儿被强暴后,绣娘与安平都曾骑马带刀进山搜索辛欣来,尽管没有搜到,但他们渴望复仇的心在自然的怀抱中都得到了某种净化或者说是软化,比如安平注意到“万物之间也有残杀和凌辱,不过这一切都静悄悄地发生着,有的甚至以美好的名义。”[1]104安雪儿在法庭上不指证辛欣来的强奸罪,而是用给孩子取名、为辛开溜刻墓碑等一系列动作纪念辛欣来的这些反常行为,也只有联系到她的自然精灵安小仙的身份,她的自然思维方式才可以得到理解。
这也就是将迟子建的创作命名为“自然写作”的第二个原因:她小说中的理想人物总是自然化的。譬如《树下》中骑着白马的鄂伦春小伙子,《晴朗》中自由美丽、任性放纵的小花巾,《群山》中的绣娘(鄂伦春族)、安雪儿、辛七杂等。这些人生命力健旺,性格坚韧,甚至赋有自然不可知的神秘,是庸常暗淡生活中的闪光点。而那些与政治、与文化相关的人物,恰恰是自然的反面,或面目阴森可怕(如《树下》“穿制服”的朱大有),或生命力孱弱(如《树下》自杀未遂的画家),或生活刻板乏味(如《群山》中的安玉顺)……背离自然是不折不扣的灾难,必然导致人性残缺。这一点,在《群山》中得到了群像式的表现:与自然保持着亲密关系的第一代(以绣娘与辛开溜为代表)、第二代(以安平与辛七杂为代表)人的生活是稳定甚至诗意浪漫的(想想绣娘的白马月光,辛七杂的悠然自得的太阳烟儿),但脱离了自然的年青一代无论在爱情、婚姻、事业还是在心态等各方面都处于一种恓恓惶惶、没有着落的状态。辛欣来自不必说,陈媛被唐眉下毒成为弱智,单夏在母亲逼迫下连续复读没考上大学后精神上出了问题,安大营单纯而懦弱、随波逐流,林大花以8万元价格向于师长出卖童贞并在间接害死安大营后无地自容,唐眉一再犯罪又一再自惩 ……
将迟子建的创作命名为“自然写作”的第三个原因是:她对于历史与社会事件的书写,所取的也是自然的视角。在《晴朗》的后记中,她表示这部小说的写作目的之一,是表达对“文革”的“日常”理解:“其实‘伤痕’完全可以不必‘声嘶力竭’地来呐喊和展览才能显示其‘痛楚’,它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当然,我并不是想抹杀历史的沉重和压抑,不想让很多人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文革’在我的笔下悄然隐去其残酷性。我只是想说,如果把每一个‘不平’的历史事件当做对生命的一种‘考验’来理解,我们会获得生命上的真正‘涅槃’。”[2]267把社会的不平,只当做对个人的考验,即是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而脱离了社会关系的“日常”的个人,当然也就是人化的自然或人的自然化。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迟子建的很多作品的写作特点。比如《树下》,作者就立定宗旨只写人的自然性,而把人的社会性因素(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极力排除在视野之外,即便要写,也会采取一种简化、变形的方式。比如枪杀姨妈一家的邻居朱大有,其身份是警察(小说中表述为“穿制服”的),他是村里人春节期间唱红色样板戏间隙偷偷唱黄色二人转的告密者,他杀人的动机是他觉得“惠集小镇所有人的眼光都不正常”[3]122,而姨妈一家尤其“不正常”,让他忍无可忍。显然他是社会的监视者,但小说中把他处理成一个疯子。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最终跳车自杀的江轮上的船长,他被此前的政治运动迫害得家破人亡,运动结束后才出来工作,小说同样也把他处理为一个疯子。这是迟子建表现社会问题时喜欢采用的手法:或者偶尔露峥嵘的暗示(另如短篇小说《花瓣饭》),或者把社会的悲剧(政治问题)转化成个人的悲剧(精神疾病),把一种必然性改写为一种偶然性。再如《晴朗》,我们只能透过狗眼(叙述者为狗)看到孤零零的梅红(上海知青)鬼鬼祟祟地替人生孩子以维生兼自赎,同样孤零零的文医生一个人在大烟坡替人易容、熬大烟膏。我们当然被作者告知:看,这些人就是“文革”的害人者和受害者!且不说这些奇异的行为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组织化、阶级斗争化的社会是否可能,易容的外科手术在荒郊野外的简陋住所里是否可能,我们只问:这样的写法与人们对“文革”的理解有丝毫的帮助吗?显然,严肃而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在这里只是被奇观化了,如同迟子建小说中的一个个其他自然奇观。
自然化的极致就是奇观化。自然中的奇山丽水、巨木繁花是现代人眼中的奇观,鄂温克人或鄂伦春人在山林中的生活方式是奇观,能断人生死的安小仙是奇观,有着“文革”痛苦经历的许达宽、梅红、文医生们,如果没有被放到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恰如其分的刻画,也不过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奇观而已。在信息化网络中日益枯焦、日益肤浅也日益胆怯的现代人,没有见识过真正的大自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历史事件,生命中空空荡荡就像一张白纸,因而对此类自然化、奇观化读着轻松舒服又不会产生任何思想困惑的艺术类消费品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超好胃口。无疑,这是迟子建小说在读者中大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自然化写作的困境
自然化、奇观化,作为迟子建创作的核心特征,对迟子建小说创作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下面将依次阐释它们对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思想深度、故事结构、死亡题材、叙述方式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人的自然化,在小说创作中会造成人物思想的简单化,形象的扁平化、类型化等一系列问题。长篇小说之长,在于它可以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提供足够的空间,但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在这一点上有些辜负长篇的容量。此外,迟子建小说中知识分子很少,即使偶尔出现,也或者是刻板沉闷的书呆子(如《热鸟》中赵雷的爸爸),或者与社会其他阶层的人物毫无二致(如《晨钟响彻黄昏》中的大学教师宋加文),思想深刻复杂、激烈冲突的思想者类型是绝对不可能有的。显然,迟子建看重的人格是陶渊明式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自然潇洒,“多虑”乃是多余,一切随顺自然即可。因而,单纯的少男、少女,天真的少妇,看淡世间一切的老头、老太太,是迟子建小说中最常见的人物形象。如果还不够,智力有缺陷的儿童就会登场了,如《树下》的大欢、二熳,《雾月牛栏》中的宝坠,《采浆果的人》中的大鲁、二鲁等。正如亚当、夏娃只适合待在有上帝保护的伊甸园里,迟子建的理想化人物也只适合在山林里讨生活的少数民族和民风淳朴的山村等。《额尔古纳河右岸》使迟子建获得茅盾文学奖并不是偶然的:作者找到了最适合她的题材,那个题材也找到了最合适的作者,二者交相辉映,相互成就。但这些人物如果出现在现代都市中,就会显得不伦不类,非常不“自然”。比如迟子建迄今为止惟一一部写现代都市生活的长篇《晨钟响彻黄昏》(1994年)中的女贼刘凤梨(绰号菠萝),她“只是喜欢一个人在这世上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4]310-311,在黄昏的梦中会梦到飘荡在空中的早晨的钟声。很明显作者是把她当做一个葆有自然野性的理想人物来写的,但是在城市的环境中,就显得恶俗和做作。很难设想她在不断地行窃、被抓的恐惧、为逃脱惩罚而不惜以性行贿的仓促生活中,如何体会那种“自由自在”并保持和表达那种浪漫想象。另外,迟子建也显得并不擅长写现代都市生活。她的想象力只有在写到大自然或人的自然性的时候才会妙笔生花,而城市生活中有太多让她本能地觉得乏味的复杂关系需要精确刻画,稍不小心就会做成夹生饭,显得简单幼稚。一个精神病院的院长再加一个暴虐成性的老医生结成的联盟,会在一天之内被一个新来的医生与一个记者联手推翻,无论如何都是天方夜谭。同样,《热鸟》中的赵雷在村子里的作为与那四个光屁股小孩对温泉服务业的影响都是只能写给小孩看的。
因而,迟子建的小说很难凝聚起真正的“问题”意识,也难以引起读者对社会与历史的深刻思考。即便在她的笔下或明或暗地写到“文革”(《晴朗》),写到“三年自然灾害”(《额尔古纳河右岸》),写到“强拆”(《起舞》),都被她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了。就像在《群山》中一样,里面写到了地委副书记陈金谷家族、于师长、汪团长们的受贿、腐化、欺骗,但这些问题仍然不能在小说中得到有效聚焦,因为作者只是或从侧面、或以时间跨度很大的补叙、或以街谈巷议的方式顺便写到这些,呈现于文本正面的主要还是云淡风轻、充满诗意地对日常生活细节、自然风景与民俗风情的描绘,给读者带来的最多也不过是“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春月秋风”的江湖看客们的一种“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苍凉美感罢了。
同样,《伪满洲国》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也不能令人满意,尽管许多评论家对它盛赞不已。真正的历史小说必须要体现历史性,而历史性一定是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历史人物与历史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举步维艰的抉择中体现出来的,而迟子建擅长的却只是写个体的人、自然的人,在复杂社会关系之外的人。姑且不说小说中绝大部分篇幅都给了那些稍加改头换面就完全可以放在任一时空中间的非历史性小人物,就是那些历史人物(比如溥仪、杨靖宇)也多是孤立的,而不是放在复杂社会关系予以表现的。小说以某某年为章标题,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共分十五章,这样纪年性的历史写法却不配合以真正历史性的事件,历史就成为一种戏说了。当然,这部小说如果不取“伪满洲国”这样一个端着严肃的历史面孔的名字,作者不宣称这是一部写历史的小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人物的自然化也会给小说的结构带来重大问题。因为一般而言,小说的主体就是故事情节,而情节是由人物的渴望、障碍、行动三者构成因果关系的序列向前推进的。但迟子建笔下的人物,因其自然化,一般都没有明确的渴望,即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只为活着而活着,并且也以单纯活着而满足,因而也就无所谓障碍与行动了。那么,迟子建的小说如何结构成篇呢?解铃还须系铃人,由自然惹起的问题,只有交给自然来解决。无论如何,时间“自然”是要流逝的,于是以时间作为章标题(《伪满洲国》);人或物“自然”会去到不同的地方的,于是以地名为标题(《树下》《晴朗》)。这样必然付出小说结构松散、没有悬念、吸引力大大降低等代价。如此“自然”而随意的结构在艺术形式上当然是一个缺憾。
不得不说,迟子建自写《额尔古纳河右岸》开始,在小说的结构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非常松散。像《白雪乌鸦》(2010年)和《群山》,20万字左右的篇幅,需要20个左右的章标题,大几十个人物,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得已,因为迟子建式的故事没有情节或情节极简,很难写长,不得不增加人物,多分章节,频繁转换写作重心。事实上,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是非常容易分成若干中篇和短篇的。这就像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评价: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迟子建对死亡叙事的特别依赖。这在《树下》与《晴朗》中看得特别清楚。七斗从惠集小镇到斯洛古小镇,再到林场,到江轮上工作,最终到农场,基本上都是由一场接一场的死亡促成的。《晴朗》中的狗在6个主人之间的交接,也是一样。人物成了完全被作者操纵的道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死),很少有自身的主动性。
当然,死亡叙事在迟子建那里还不仅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需要这么简单。因为她小说中的死亡实在是太密集了。迟子建在《白雪乌鸦》后记中说,因为写鼠疫不断死人,而感受到“心理无法承受的重压。这在我的写作中,是从未有过的。”[5]288这只能说多年的世事沧桑使迟子建的心理承受能力变弱了。因为她的长篇处女作中就已有了那么多的死亡,并且很多还是莫名其妙的:七斗少女时代的同学兼好友火塘参军走向了外部世界,在小说的结尾传来的是他死亡的消息。农场的客人,那个画家,也来自外部世界据说还是高干子弟,他的女友自杀了,他选择在黑龙江源头自杀。他在遗书中说:“我一生中最想干的事就是杀死自己,如今在这里我找到了勇气。”[3]235就连七斗梦中的理想人物,那个骑小白马的英俊小伙子,七斗在送儿子去城市医病的途中也目睹了他的葬礼(死于狩猎),与此同时她的儿子死于她的怀抱中。这个四岁的神秘的孩子一直对死有着浓厚的兴趣。倒是早已死去的姨妈、姨夫一直活在七斗的梦中,不断地跟她交流阴阳两界的信息。
自杀、他杀、病死、老死……迟子建热衷于死亡叙事,这或许因为死亡是人性的自然(按弗洛伊德的术语叫“死本能”),是人的宿命,也是对人性的自然来说最大的神秘。从万物有灵的角度,人死之后灵魂才可以出窍,才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好地表演来自大自然的神秘。迟子建喜欢在血缘关系问题上做文章,其原因也在于此。血缘亦是人性的自然,其中有诸多人所不能克服的神秘性存在。当然,血缘关系只有在与非血缘关系的对照中才能得到更有效的显现。就《树下》而言,七斗被过继给姨妈,七斗的妈妈也有一个后妈,七斗的老公总是怀疑儿子并非亲生,等等,都属此一题材。此外,情欲,尤其是与亲情纠结在一起的乱伦(姨父对七斗的强暴)、作为社会禁忌的情欲如婚外情(《逆行精灵》中的鹅颈女人),等等,这些自然性命题,也都是迟子建的小说中最重要也最常见的题材。作为这一切的升级版,情欲加血缘加仇杀,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也屡见不鲜,如《岸上的美奴》《晚安玫瑰》等。
除了人物类型、故事结构、写作题材之外,自然写作也深深决定了迟子建的叙述方式。而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容易看出一个作家的成长。《树下》的叙述方式是第三人称,但与第一人称几无二致,因为叙述者的视点、声音甚至词语声音都是主人公七斗的,因此把文中的“七斗”换成“我”,不会对原文有太大影响。这说明了作者在创作初期叙事技巧的不成熟,因为第三人称原本有更广阔的视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晴朗》采用狗的视角,用一条狗来做叙述者,因而是第一人称叙事。据作家说这是为了表现“万事万物皆有灵性”[2]267。如果这是采用狗作为叙述者的惟一理由的话,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完全是得不偿失。因为狗的视点太低了,有太多的东西它看不到,看到了也不能理解。这还不算作者为了表现狗视角,不停地加上一些诸如超过10以上的数字作为狗的“我”就不能理解之类的废话。而到了《群山》,作者的成熟从第一句话就表露出来了:“龙盏镇的牲畜见着屠夫辛七杂,知道那是它们的末日太阳,都怕,虽说他腰上别着的不是屠刀,而是心爱的烟斗。”[1]1这才是真正的第三人称视角,这一视角拉开了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却拉近了与受述者之间的关系,取得了对受述者施加各种影响的充分主动性。与此同时,万物有灵的观念也轻松地得到了传达。
但是,即便是在《群山》中,作者的叙述方式还是过于传统与简单了,只是这一方式与作者的自然写作非常适合罢了。换句话说,作者如果想在叙述技巧方面得到进一步提高,比如想尝试一下作者极少涉足的隐蔽叙述、反讽叙述、不可靠叙述等,必须同时打破这种自然写作的观念,给予故事中的人物更多自我表现的机会,同时在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进行更多复杂而有趣的交流与游戏。但作者醉心的环境描写,以及作者为了在较小篇幅内交代更多人的故事而使用过多的时间性概述,都是公开叙述的最基本形式。公开叙述越多,作者对人物的限定就越大,即作者有更多的机会说服读者接受他的观点,而不是让人物在读者面前自由表演,自我呈现,活出自我。
结 语
人类从走出自然的那天起,就一直面临着自然与文化的冲突。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同时也是叙事学的鼻祖之一列维·施特劳斯就把自然与文化的冲突建构为人类学的核心二元对立。他也曾描述人类与自然撕裂的痛苦:“对于心灵和精神来说,好像没有任何情形再比这种人与其他生物共存,与它们分享一块土地,却又不能与其交流的情形更令人伤心、更令人气愤的了。”[6]176但这是人作为人、人要成为人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并且,也只有站在文化亦即超越自然的层面上,人类才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自然的美。没有走出自然的原始人在自然面前,就如同一个被抛弃在自然里的孩子,所感觉到的只有恐怖与神秘;事实上,一个吃苦受累的农民,对于自然美与农业劳作之美的感受,也不会像迟子建这样的作家感受的那么多。从这个意义上,自然与人的自然性之美,首先是作家的虚构或者说创造。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但问题是自然性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人的文化性或者说社会性才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如马克思的经典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 135。
迟子建聚焦于自然美的创造,满足了现代社会的文化饥渴,这是她的作品取得成功的原因。然而过于自然化,就会使写作成为自然奇观的展览,会给作品带来一系列问题。诚然,从《树下》到《群山》,迟子建作品中人物的社会性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但过于自然化的倾向仍然很明显。迟子建如果要突破自我,就必须打破这种独重自然的单翼模式,自觉地把自然与文化作为写作的双翼,才能在人类文学的天空中飞得更高、更远。
[1]迟子建:《群山之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迟子建:《越过云层的晴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3] 迟子建:《树下》,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4] 迟子建:《晨钟响彻黄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5] 迟子建:《白雪乌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6](法)迪迪埃·埃里蓬:《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传》,袁文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责任编辑 吴兰丽
栏目特约编辑 梅兰
On the Nature Writing of Chi Zi-jian
WANG Jun-jia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ResearchCenterforContemporaryChineseWriting,HUST,Wuhan430074,China)
To eulogize the nature and the human nature is the theme of Chi Zi-jian. However, the tendency of excessive naturalization or even the quest for the natural spectacle can be found in her writing, which, more or less, adversely affects the image of characters, the depth of thoughts, the structure of plots, the choice of subjects, the way of narration and so on. If Chi Zi-jian takes both nature and culture into account, her creative work would attain more achievements.
nature writing; spectacle; nature and culture; Chi Zi-jian
王均江,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2017-01-10
I207.4
A
1671-7023(2017)02-0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