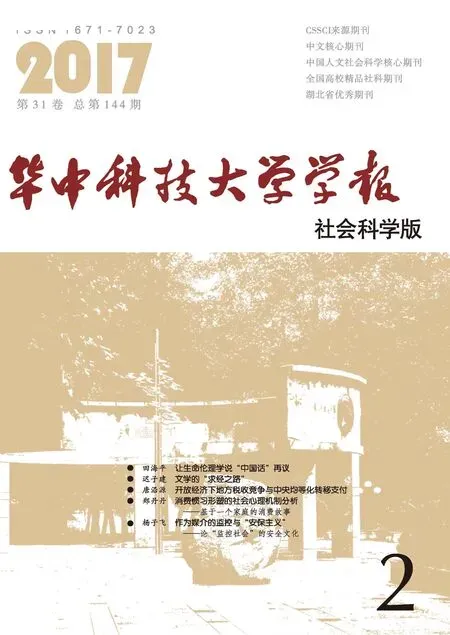作为媒介的监控与“安保主义”
——论“监控社会”的安全文化
杨子飞,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作为媒介的监控与“安保主义”
——论“监控社会”的安全文化
杨子飞,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全世界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全面监控的社会形态,作为媒介的监控塑造了一种适合监控扩张需要的安全文化理念,即安保主义,从而实现了监控社会的自我再生产。一方面,“作为媒介的监控”放大了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催生了对监控的渴望;另一方面,“作为媒介的监控”又虚构了一个可以通过全面监控来实现的“安全乌托邦”,促使人们非但可以忍受被监控而且还享受被监控。然而,要在一个“最不安全的时代”里通过监控来建设一个“最大安全社会”,这注定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悲剧。
安保主义;监控社会;不安全感;安全乌托邦
一、 引言——“监控社会”的来临与观察视角的转换
自从斯诺登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丑闻之后,形形色色的监控开始褪去层层神秘的外衣,并逐渐走进普通公众的视野之中。但是,棱镜计划只是庞大监控网络的一小部分,美国也只是众多实施监控计划的国家中的一个,电话和网络监控也只是众多监控手段当中的一种。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全面监控”的时代[1]135-149,我们甚至可以说监控已经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2]259-273。从生产到消费,从小区到广场,从街头到商场,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一张监控的天罗地网正在越织越密,越铺越广。
伴随着监控的日益普及,一个新的词汇被创造出来,那就是“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这一概念(通常认为“监控社会”这一术语产生于Gary Marx的研究成果[3]21-26)。“监控社会”不是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描述,而是对一种特定形态的社会范式的概括,它的作用犹如“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些概念一样,是用来标识当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从而将它与另外一些社会形态区别开来。毋庸置疑,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或多或少的监控现象,但惟独当今社会可以被概括为“监控社会”,那是因为只有在当今社会监控才成为社会的主要特征,也只有在当代才“有一种无实体的监控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4]33。
在两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监控社会”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当下西方学术界监控研究、犯罪学研究的核心构成部分[5]179-194。学者们主要关注了“监控社会”的特征、产生的历史背景、监控对于隐私的侵害、监控在犯罪控制上的效果等问题。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此类研究都把监控看成是当代社会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6]61-76。这一视角当然无可厚非,因为不管是从监控的客观社会效果来看,还是从人们对监控的主观期待来看,监控都发挥着社会控制的功能。但是笔者认为仅仅从这一视角出发不能完整而准确地理解监控现象,也无法更好地解释监控社会不断扩张的原因。因为我们发现,诸多研究结果都显示,监控在犯罪控制问题上的效率是微乎其微的,监控在提升人们的安全感上的成效也是相当可疑的[7]115。假如监控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那么无论是从客观成效还是从主观感受方面,都无法解释监控社会不断扩张这一世界性现象。
如果说无处不在的监控设施构成了监控社会的硬件基础,那么弥漫在人心中的安全文化观念则构成了监控社会的软件基础,要完整地理解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监控社会,我们就必须补上对软件基础的认识这一课。因此笔者尝试提出另外一个观察监控社会的视角,即不把监控当成社会控制的手段,而是当成社会传播的媒介,作为媒介它创造和支撑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观念,即本文所概括的“安保主义”理念。这种理念一方面宣扬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使得人们对安全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渴望;另一方面,又设想了一种“透明社会”的安全乌托邦,使得人们对监控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笔者认为,通过这样一个观察视角的转换,我们不仅可以更深一步理解当今监控社会扩张的内在原因,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评估监控对于我们获取安全感的真实意义,以更理智而非盲目的态度对待监控。
二、 作为媒介的监控——监控社会的自我再生产
长期以来,人们(不管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学者、普通民众)都习惯性地把监控看成是一种社会管理与控制的手段,这一点本身并没有错,但它严重忽略了监控的另一层属性,而且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的属性,那就是监控的媒介属性。可以说,监控天然地具备媒介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收集、存储和传播信息的有效载体,在这一点上它与报纸、电视、网络、手机没有本质的差别。
下面这个现象就是有力的证明:随着监控设施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广泛使用,监控录像已经成为电视、网络新闻的重要新闻来源之一,以至于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监控新闻”的新名词。我们以“监控录像”为关键词,对百度新闻频道2016年3月1日至3月31日之间的新闻进行检索,可以发现在一个月之内新闻内容含有监控录像的新闻报道就有1 680篇之多。与这一现象相呼应的另一个现象是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我们以“监控录像”和“新闻报道”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期刊论文进行检索,我们发现内容涉及“监控录像”和新闻报道的文章竟有10 586篇之多,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相关学术成果呈爆炸式增长。
监控录像之所以在新闻报道中被广泛运用,以至于监控的媒介属性被不断挖掘、利用,其原因即在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监控录像与其他新闻来源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监控录像不仅覆盖内容广,而且剪辑方式巧妙,更重要的是它故事性非常强,进而增加了电视新闻的真实感和现场感[8]56,当然同时也增加了新闻的说服力[9]。
上述现象只是在经验层面证明了监控的媒介属性,我们还可以从逻辑层面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对于媒介本质的认识,麦克卢汉有过极为经典的定义,所谓媒介即是人体功能的外化延伸[10]。比如汽车是人类双脚功能的延伸,望远镜是人类眼睛功能的延伸,筷子是人类双手功能的延伸。按照这种思路,监控摄像头就是人类头脑功能体系的延伸,它既包含了视觉功能,还包含了大脑的存储分析功能,借助这种视觉与存储分析功能的外化延伸,人类可以更好地监视和控制社会生活。这就再度证明监控天生地就具有媒介属性。
当然,监控并非传统媒介,它是在信息技术革新和社会全面信息化进程中才得以出现的,因此它必然具备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介的基本特征。首先,监控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媒介。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人们一谈到监控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政府部门在背后操纵,事实上当今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只有一部分是政府部门建设和管理的,还有相当大部分是由半公共部门(比如小区)和纯粹私人建设和管理的。其次,监控是一种“自媒介”,监控摄像头并非像专业记者手中的摄像机是有意识地捕捉选取新闻画面,而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漫无目的地监视记录着特定区域的不特定对象,它的画面是技术设备自动产生的。最后,它还是一种集成化了的“媒介综合体”,不像以往的功能相对单一的传统媒介,监控作为一种媒介集合了图像自动抓取、自动识别、自动存储、自动分析等等庞大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把它称为“媒介综合体”。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大历史趋势,即伴随着信息化的日新月异,媒介与监控正在逐步实现融合,即“作为监控的媒介”与“作为媒介的监控”同时出现,或者说媒介承担着监控的功能,监控也承担着媒介的功能,这是一体两面。在这个大融合趋势下,人类不得不同时适应“媒介化生存”和“监控化生存”。也正是在这个大融合趋势下,监控的媒介属性会越来越突出,以监控录像为基本素材的新闻报道也会越来越普遍。
无处不在的监控作为无处不在的媒介,不仅是我们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它还构成了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背景,并且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而构筑起监控社会的软件基础。承认这一点,即意味着承认除了有资本和权力的因素在推动监控社会的扩张之外,监控自身也在推动自身的扩张,也就是说,当今时代的监控社会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再生产能力,其实现自我再生产的机制就是监控具备了媒介的功能,懂得了自我宣传、自我营销,从而塑造了一种适合监控社会扩张需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那么本文的任务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媒介的监控”塑造了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它又是如何塑造的呢?下文的论述将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
三、 安保主义的反面逻辑——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
如果从客观环境来看,我们所生活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安全的了,因为没有物质的匮乏,没有野兽的入侵,更没有炸弹的轰炸。但吊诡的是,当代人却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以至于有人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称为“不安全的时代”(insecure times)[11]1-3。显然,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并不是一种对客观环境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被放大了的主观感受。有关安全问题的讨论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缺乏明确的安全定义,以至于安全成为了一种难以界定的理想[12]200-214。同样,不安全感本身就是指人们对外在危险的主观认知,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扭曲(甚至是操纵)的东西。
那么,是什么在放大人们的不安全感呢?富里迪(Frank Furedi)认为政治家们正在有意识地操纵民众的不安全感以实现其政治目标,因为民众的不安可以换来国家的团结和政府的合法性[13]110-143。以下例子就是明证:对美国公民的调查显示,对恐怖袭击有着高度恐惧感的公民比那些恐惧感低的公民更加支持政府采取强硬的安全措施限制他们的自由和公民权利[14]28-46。还有学者认为企业(尤其是安防产业)也在有意放大民众的不安全感,因为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会导向一种新的消费,即对保护的消费[15]122,难怪有学者会惊呼监控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产业”[16]134-147。笔者认为政府和企业作为一种外部因素一定会对民众的不安全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从而促成监控社会的扩张,但是有一个内部因素同样不可忽略(事实上却经常被学者们所忽略),那就是监控本身也在放大民众的不安全感。
各项研究成果都表明媒体对犯罪的过度渲染是导致人们不安全感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7]755-785,因为媒体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暴力的、血腥的场面来提高节目的收视率,而这些暴力、血腥的场面并非是影视作品中的虚构画面,而是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的真实画面。有新闻传播学学者通过分析137篇运用监控视频的电视新闻报道发现,电视新闻运用的监控视频内容相对集中,均以暴力和犯罪事件为主,两者占监控视频的70%,而且这些视频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血腥的恶性事件[18]。监控视频所提供的资料就是最好的新闻素材,尤其是那些带有暴力情景的犯罪场面,更是被记者们认为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因为它们是犯罪事件的真实记录[19]305。被播放出来的监控录像营造了一种草木皆兵的危险氛围,民众经常接受这样一种负面的讯息,自然会对外部威胁十分敏感,甚至产生一种恐慌的情绪。值得一提的是,暴力恐怖分子经常借助监控摄像头来宣示他们的存在,营造一种恐怖气氛,从而达到他们的政治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监控并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恐怖袭击的发生,相反,它却无意中成了恐怖主义的帮凶。
当然,监控录像绝非仅仅以其暴力、血腥的画面放大了民众的不安全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当然也更隐蔽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这就是监控录像描绘了一幅“既可见又不可辨的他者”形象。可以说很多监控录像并不暴力,也不血腥,但是它们同样(甚至更甚)让观看者感觉到莫名的恐惧,因为有一些“既可见又不可辨的他者”环绕在你的周围。“他者”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焦虑的焦点[20]22,因为“他者”是不知其姓名、不知其背景、不知其意图,但是在价值观念上又与“我们”不同的“陌生人”,我们当然无法预知“他们”的行为,“他们”因而就是不安全感的总根源。而监控录像所记录下来的画面一方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不正常者、违法犯罪的人)和“我们”(遵纪守法的公民)同在,“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在告诉我们,“他们”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从表面上我们根本无法把“他们”从人群中辨识出来,只有警察和专业人士才具备这种能力。正因为监控录像告诉“我们”,“他们”是“可见”的,所以危险是可以被感知的,又因为监控录像告诉“我们”,“他们”就隐藏在“我们”身边,所以危险是无法被辨认,更无法被防控的。这意味着“我们”明知道危险的存在,却不知道危险在何方[21]121-133。一种只能被感知却无法被防控的危险,就是最令人不安的危险。所以说,正是监控录像所呈现的“既可见又不可辨的他者”成了当代人的梦靥,成了不安全感的源头。
必须立刻指出的是,放大民众内心的不安全感并非监控社会生产商或社会某个群体刻意为之的产物,而是监控技术本身蕴含的自然结果。任何技术都绝非客观中立,相反它们有一种自我证成、自我扩张的内在需要,就像武器的生产和扩张背后除了有武器生产商的推动之外,还有武器技术自身的逻辑在起作用。而且恰恰是技术自身蕴含的这种自我扩张逻辑,才是真正需要我们去警惕,也最需要我们去警惕的。
总而言之,这就是安保主义安全文化理念的反面逻辑:“作为媒介的监控”放大了民众的不安全感,从而催生了一种对于安全(进而对于监控)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渴望,监控社会正是在这一渴望的支撑下不断扩张开来的。
四、安保主义的正面逻辑——通过全面监控建构“最大安全社会”
虽然人类为不安全感深深困扰,但是它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作为生产推动力,推动当前“监控资本主义”[22]的快速发展;它还可以作为社会转型的推动力,推动当前“监控社会”的迅猛扩张。我们可以说,“最不安全时代”和“监控社会”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此必有彼,有彼必有此。而且,笔者还试图证明的重要一点在于,“作为媒介的监控”是这对孪生兄弟共同的幕后推手,它不但如前所述放大了民众的不安全感,而且还如下所述虚构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安全理念,即可以通过全面的监控来实现一个“最大安全社会”。
如果说现代社会为了因应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不平等而建构了一个“平等的乌托邦”,那么后现代社会则为了因应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而建构了一个“安全的乌托邦”,即所谓的“最大安全社会”(maximum security society)[23]159-175。这个乌托邦跟以往人类所建构的其他类型乌托邦不同,它并非是消除了一切罪恶的、完美无缺的最美好社会(这样的社会肯定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恰恰相反,“最大安全社会”中依然还是有偷盗、抢劫、强奸等罪恶存在,依然还是不完美的,但是“最大安全社会”却承诺了将所有这些罪恶都放置在监控摄像头前面,确保罪恶被监控摄像头“看见”(需要指出的是,监控摄像头的“看”是英文中的see,而不是look,see指称的是一种没有主观意图的“观看”,而look指称的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观察”),被“看见”就是在提供保护。
另外,还需确保罪恶被摄像头记录下来,被记录下来就是在提供证据。人们普遍认为监控摄像头所记录的画面就是事实,因而就可以成为法庭上的证据,进而摄像头就代表了社会公正的实现。因为据说监控录像是对视觉、知觉的简单校正,它是由机器运作的,没有人类意志牵扯其中,因此其产生的是一种“纯证据”(pure evidence)[24]136-137,似乎摄像头从来不会说谎“camera-doesn’t-lie”。事实当然远非如此,因为根本不存在完全客观中立的技术设备,因而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种“纯证据”。但是在“有图有真相”“眼见即事实”的主流观念支持下,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监控录像就等同于社会事实。这一点恰恰说明了,在“监控社会”里,不仅监控设施普遍化了,而且监控的文化与意识也已经普遍化了。
有了保护,有了证据,安全就有了保障,前者是为了事前预防犯罪的发生,后者是为了事后侦查犯罪的经过。这就是“最大安全社会”的安全逻辑:看见就是保护,录像就是证据。一个试图把所有犯罪行为都置于监控摄像头之下的社会,一个试图看见一切和记录一切犯罪行为的社会,可以被形象地称之为“透明社会”[25],监控社会的安全理念就是认为一个社会越是透明,这个社会就越是安全。这种理念是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理想一脉相承的,对于现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来说,黑暗即意味着罪恶与混乱,而光明则意味着善与秩序,所以要确保理性的光芒可以照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26]4,也就是要让整个现代社会按照理性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就可以消除罪恶与混乱。而通过监控实现的“最大安全社会”同样试图“去看到全部,知道全部,在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27]145,尽管这个光已经不再是指理性的光芒,而是指监控摄像头的电子光芒。如果说现代启蒙运动的美好理想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那么后现代居民们可能更愿意相信他们对“最大安全社会”的期待是有可能借助监控技术的不断改进而彻底实现的。这就是安保主义安全理念最重要的观念,即可以通过“监控方案”(surveillance solution)来解决社会治安管理问题[28]162。
安保主义安全文化理念的正面逻辑是:“作为媒介的监控”向民众虚构了一个“安全乌托邦”,即通过广泛使用监控摄像头,可以建立一个近乎透明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有效防止犯罪现象的发生,如果犯罪行为发生了也可以得到有效治理。这一文化理念促使人们非但可以接受和忍受被监控,而且还进一步喜欢上被监控、进而享受被监控,最终“爱上老大哥”[29]。一句话,它使得“监控社会”变得更加稳固了。
五、 结语——西西弗斯式的悲剧
综上所述,“作为媒介的监控”塑造了一种安保主义的安全理念,它一方面放大了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催生了对监控的渴望;另一方面又虚构了一个可以通过全面监控来实现的“安全乌托邦”,促使人们非但可以忍受被监控而且还进一步享受被监控。
如何评价这样一种安保主义的安全理念呢?毋庸置疑,这一理念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代人的安全关切,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人的安全焦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一理念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如果我们试图借助安保主义理念来确保自身的安全,恐怕其结局就是一场西西弗斯式的悲剧:每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看到前面的希望时,我们又总是陷入更深的绝望当中。
这首先是因为安保主义安全理念错误地评估和诊断了当代社会的安全症结。不安全感当然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但是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是不是极端不安全?这是一个需要当代人重新思考的问题,安保主义理念显然得为这种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承担起一定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弥漫在全社会的不安全感不仅仅来自对犯罪的恐惧,而且更是来自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不安全的恐惧,比如失业、贫穷等问题[30]79-101,后面这些问题是社会系统性的问题,而非局部性、技术性问题。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正确开出药方的前提条件。
其次,正因为安保主义理念对不安全病因的评估和诊断是错误的,所以它开出的药方也是不可靠的,甚至还会加重病情的发展。试图通过全面监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社会治安管理问题,进而确保民众的安全,这是注定治标不治本的。但是安保主义理念却促使人们对监控技术报以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人们把安全与监控等同起来,以为只要人们愿意付出一定的自由和隐私的代价,就可以换来安全感,其结果极有可能是“既不自由,也不安全”[31]。统计调查显示,在影响人们对待监控的态度的诸要素中,对于犯罪和恐怖袭击的恐惧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对于政府安全措施的评估正在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们通过走上街头,甚至组建政党等方式来反对监控的扩张也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比如德国海盗党 German Pirate Party已经成为德国第七大党)。反对国家安全措施的运动正在制度化,并且牵涉越来越多的反对政府监控的人群[32]。
最后,安保主义理念承诺的“最大安全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它让人们在安全问题上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犹太人有一句极富智慧的格言,一个东西越是完美,在它腐烂的时候就越是丑陋[33]58,“最大安全”的社会理想一旦破灭,恐怕会让人们感觉到更加的不安全。因此我们极有必要追问这样的问题,到底要“多安全才算安全”[34]?一旦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应该承认,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安全,所有的安全都是相对的。
承认安全是相对的,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直面和接受与人类历史相伴始终的相对不安全感,这就进而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和素质与不安全感共生共存。通过全面监控来建构“最大安全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一贯逻辑,即通过不断改造外部社会来实现人类的自由与幸福(包括安全),但是这注定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一个人越是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外面,他就越是感觉到不安全。与相对不安全感共生共存,就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虽然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与其对技术和外部社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如对自身德性的期待还是更加可靠的。
[1]Lyon D.. “Globalizing Surveilla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04(19):135-149.
[2] Murakami Wood D.,Webster CWR.“Living in Surveillance Societies: The Normalisation of Surveillance in Europe and the Threat of Britain’s Bad Example”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Research, 2009(2):259-273.
[3]Marx G. T.. “The Surveillance Society: The Threat of 1984-style Techniques”,The Futurist, 1985(6): 21-26.
[4] Lyon D..SurveillanceSociety.MonitoringEverydayLif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3.
[5]Wood. D.M.. “The ‘Surveillance Society’ Questions of History, Place and Cul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09(2): 179-194.
[6]Gandy. O. H.. “The Surveillance Socie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reaucratic Social Contro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9(3): 61-76.
[7]Gill M. & Spriggs. A..AssessingtheImpactofCCTV,HomeOfficeResearchStudy, London: Home Office Development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2005: 115.
[8]Jewkes Y..MediaandCrime, London:Sage, 2004: 56.
[9] 郭丽霞、霍福红: 《监控录像在我国电视新闻中的应用特点和价值》,载《传播与版权》 2014年第1期。
[10]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1] John Vail.“Insecure Times Conceptualising Insecurity and Security” ,J. Vail , J Wheelock and M. Hill( eds),InsecureTimesLivingwithInsecurityinContemporary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3.
[12] Lucia Zender. “The Pursuit of Security”, T. Hope & R. Sparks (eds),CrimeRiskandIn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00-214.
[13] 弗兰克·富里迪:《恐惧的政治》, 方军、吕静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 Davis, Darren W. and Brian D. Silver. “Civil Liberties vs. Security: Public Opin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America”,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4(1): 28-46.
[15] Paul Virilio.SpeedandPolitics:AnEssaysonDromology, New York: Columbia, 1986: 122.
[16]Germain S.. “A Prosperous ‘Business’: The success of CCTV through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Surveillance & Society, 2013 (1): 134-147.
[17]Chiricos T.K. Padgett and M. Gertz..“Fear, TV News, and the Reality of Crime”, Criminology, 2000 (3): 755-785.
[18] 王仁忠、李冰玉:《监控视频在电视新闻中的应用分析与思考》,载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2期。
[19]Reiner R..MediaMadeCriminality:theRepresentationofCrimeintheMassMedia,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minology Third Edition, eds M. Maguire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05.
[20]Lofland L.H..AWorldofStrangers:OrderandActioninUrbanPublicSpace, New York: Basic, 1973: 22.
[21] Inga Kroener. “Caught on Camera: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Video Surveillance in Relation to the London Undergound Bombings”,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05 (1): 121-133.
[22] Zuboff S..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 30(1).
[23]Lyon D..“The New Surveillance: Electronic Technologies and the Maximum Security Society” , Crime Law & Social Change, 1992(18): 159-175.
[24]Dovey J.. “Big Brother”,In G. Creeber(ed.),TheTelevisionGenreBookLondon,BFI Publishing, 2001: 136-137.
[25] 大卫·布里恩:《透明社会》, 萧美惠译,台北:先觉出版社1999年版。
[26] Robert C.. Bartlett.TheIdeaOfEnlightenment:APost-MortemStudy, Toronto Butt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4.
[27]Paul Virilio.“The Virilio Reader”,edited by Der Derian, James.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8: 145.
[28]Haggarty, K. D.. “Ten Thousand Times Larger’-Anticipating the Expansion of Surveillance”,B. Goold and D. Neyland(eds).NewDirectionsinSurveillanceandPrivacy, Cullompton. Willan Publishing. 2009: 162.
[29]Waugh I.. “Learn to love Big Brother”, Australian Personal Computer, 2005.
[30] Mary Fran & T..“Malone, Fear of Crime or Fear of Life Public Insecurities in Chile” ,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2003(1): 79-101.
[31] Robert Higgs .“Neither Liberty nor Safety: Fear, Ideology, and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Independent Institute, 2007.
[32] Christian Ludemann & Christina Schlepper.“The Role of Fear in the Surveillance State in Times of Terrorism: Explaining Attitudes towards New Governmental Security Measures”, S. Salzborn et al. (eds.),Methods,Theories,andEmpiricalApplicationsintheSocialSciences, DOI 10.1007/978-3-351-18898-1_32.
[33] (德)摩西·门德尔松:“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徐向东、卢华萍译,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4]Douglas M..RiskandBlame:EssaysinCultural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责任编辑 胡章成
Surveillance as Media and Securitism:On the Security Cultur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YANG Zi-fei
(HangzhouDianzi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The whole world is acceleratedly entering a total surveillance society. The surveillance as media has modeled a security culture called securitism, which enables the self reproduction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it has magnified ubiquitous insecurity, and then produced deep desire to surveilla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created a security utopia which seems to be fulfilled by total surveillance, as the result people can not only bear the surveillance but also enjoy surveillance. However, it is doomed to be a Sisyphus tragedy to build a maximum security society in a least secure era through total surveillance.
securitism; surveillance society; insecurity; safety utopia
杨子飞,哲学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副教授,浙江省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信息社会理论。
浙江省社科规划一般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大数据时代‘预测性监控’的社会负效应研究”(16JDGH1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平安中国建设中视频监控系统的‘负安全效应’防控研究”(16YJC840028)
2016-11-20
D631.43
A
1671-7023(2017)02-012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