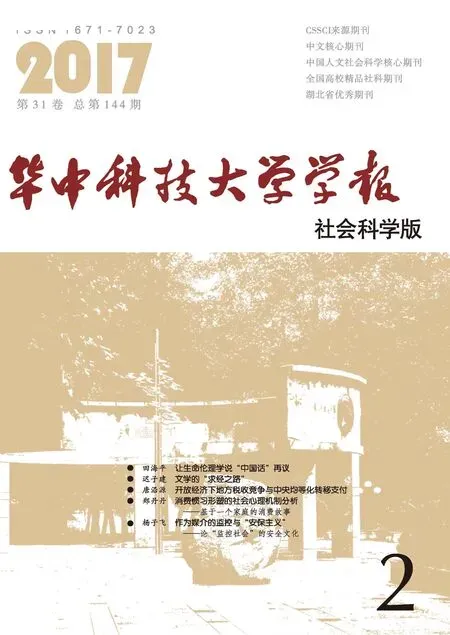秩序、人性与植物世界
——卢梭的“自然”谱系
杜雅,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秩序、人性与植物世界
——卢梭的“自然”谱系
杜雅,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自然”是卢梭思想的基石。秩序、人性与植物学,作为不同介质揭示“自然”,呈现从上至下、普遍到特殊的谱系。卢梭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斯多亚学派的道德秩序顺承于自然秩序的观念,自然首要地显现为同一于神意的秩序,又作为潜在的理性和道德的秩序在人类身上外化,因而,人性的自然之善合乎自然秩序,作为现实道德秩序遵从的逻辑前提,指向天性固有的自由观念。其次,卢梭溯及原初状态的自然人,从自然法原则说明自然之善,并认为社会化进程导致自然秩序被打破,人丧失其纯一及自然的自由。而植物学提供了一个与纯粹自然交谈的场所,卢梭得以认识自身,体察存在的自足。在其中,自然引导个体顺应自然秩序及天性,趋向道德的自由。
自然;秩序;人性;植物学
赫拉克利特《残篇》里谈论那一“喜欢隐藏”的自然,蕴涵并不显明自身的逻各斯,即恒常的、所有事物聚集或分离但始终遵循的中心。德里达主张卢梭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因其构建了一种以言语为自身、文字为替补的在场模式。在场是自足且自然的,卢梭将自然置于自身与替补的对立之中,艺术、技艺和习俗则作为自然的替补。当替补危险地充当自身在场,他退而将教育描述成替补的体系,力图以最自然的方式重建可能的自然大厦[1]145-212。德里达提供了认识卢梭自然观念的一种路径,并证明“自然”是构成卢梭全部思想的基石。事实上,“自然”使卢梭及其观念世界融贯为一,并呈现为从上至下、从普遍到特殊的谱系。秩序、人性与植物学,作为不同介质揭示“自然”。
一、自然秩序
于卢梭,自然首要地显现为秩序。如果说自然即卢梭全部观念的中心,秩序则是自然的首要属性。如Lester Crocker所总结的,卢梭的整体思想围绕一个核心:人扰乱了自然秩序。自然和宇宙出自上帝之手,作为理性且潜在的道德秩序;当人类开启对道德王国的经验,道德秩序在上帝之外呈现自身;而人最终打破了自然秩序[2] 247。
卢梭借《爱弥儿》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自述对自然秩序有所阐明。首先,自然或宇宙有序均匀的运行依赖一个固定法则,不在物质内部,而出自外在原因,如同使太阳运行、地球旋转的“那只转动它的手”,是自发的、自由的意志。进一步看,使宇宙按法则运动的不单是意志,更是一种生成秩序的智慧。人无法相信从死寂能生出有思考能力的生物,也无法想象万物不借助某个第一原因能保持秩序井然,“尽管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目的,我也能判断它的秩序”[3] 275,秩序显现在各个部分之间配合协作的关系,如同表壳之下所有齿轮为一个目的协同一致地转动。因而,从眼前所见的整体来判断,“我应该知道”并且“我感觉到了”统治世界的智慧意志确实存在。它有思想有能力,又自发运动,这一“推动宇宙并安排万物的存在,不管它是谁,我都称之为‘上帝’。其中包涵智慧、能力、意志和仁慈的观念。”[3]277宇宙的存在与我的存在一样都是我感觉的对象,从所及的经验世界推断,上帝存在。
如果上帝存在的推论基于对自然秩序的判断,那么《致伏尔泰的信》进一步说明,源出上帝的神意(Providence)作为对自然秩序的保证。“若上帝存在,他必完美;若他完美,也必明智、全能且公正”*卢梭在信中回应伏尔泰在1755年里斯本地震后所作的长诗。伏尔泰质疑莱布尼茨“神义论”和蒲柏代表的乐观主义,卢梭则认为不应由个别的恶怀疑整全的好。[4] 58,卢梭以此反驳伏尔泰的怀疑主义。在他看来,事物朝向那一保证宇宙及秩序完善的、普遍意义上“整全的好”(the whole good),“个别的恶”无从推翻“整全的好”,也无法证明“普遍的恶”的存在。于公民个体,自然秩序彰显的神意是其“良知”的源初推动,怀疑主义不亚于对灵魂的“暴力冲击”,因为同一于上帝的秩序,决定了灵魂应有的秩序。正如卢梭在《新爱洛伊丝》里让“朱莉”向上帝祈求:“我想要获得与您确立的自然秩序及其理性准则相吻合的一切”[5] 294,在此,自然秩序即合乎神意的秩序和理性的秩序,作为恒久有效的标准,遏制变动不居的冲动和激情。它主导宇宙运行,也规约人的意志。当观察和反思由上帝统辖的秩序中“我”的位置,自然秩序从上帝与“我”的关系中显现。
“我”与造物主,在柏拉图《蒂迈欧篇》表现为个体的理智灵魂与世界灵魂的关系。造物主实质是纯粹理念,个体灵魂试图脱离与肉体的交往,通过静观神圣之物重获关于善和形式的知识,与世界灵魂相互映照,在此“我”局限于灵魂的理智部分。而在亚里士多德,“不动的推动者”作为世界的“第一因和第一本原”,并非使物质世界从无到有的创造者,因而“世界对神的依赖间接且遥远,世界的秩序只是对神圣思想的一种反映或体现。正因为那个秩序构成里神的思想的可思维的内容,它也就构成了世界的可思维的结构。”[6]206-207有关神的观念,构成理性认识的对象。但人的伦理德性并不从自然而来,而从“习惯”中来,神圣智性的完美与俗世道德无涉。直至斯多亚学派开始构建神与人的密切关联。
斯多亚学派将物质和精神化二为一,统归于作为造物主的惟一的神。神被许以不同命名:逻各斯,宇宙的理性秩序或自然的理性法则。神不仅以理性法则掌管一切,也作为理性存在物栖居人世,神的善良意志理性化的呈现即“命运”,对立于“偶然”。斯多亚学派将个体以至人类族群的伦理实现与自然的理性法则统合起来,使自然法则成为行为的目的和德性的规范[7] 36。人要使行为合乎准则并获得幸福,先要有由理性把握的宇宙观念。塞涅卡就主张,明智的人的德性在于自我检省以做到正直谦逊,接纳由神统领的宇宙并归顺神意,模仿神的慈悲。因此斯多亚学派强调人的德性在于符合自然的生活,符合自然即符合理性、合于逻各斯。人自身的逻各斯相应于宇宙的逻各斯,使人天生寻求与自然的和谐。
卢梭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斯多亚学派的道德秩序顺承于自然秩序的观念,但“道德秩序”所指不同。斯多亚学派立足俗世伦理,道德秩序基于现实习俗和行为法则,而在卢梭,道德秩序尚未“下降”到日常的感性世界。如Asher Horowitz所言,道德秩序不是感性经验中的所有秩序,而是更高一级的秩序,即被卢梭称为“神性直觉”(divine instinct)之物所建构的[8]42,换言之,道德秩序溯至同一于神意的自然秩序,在人的自然本性与自然或宇宙的整全之间建立起“一致性”,形同斯多亚学派自然的理性法则与俗常伦理的一致性。关于一致性如何实现,斯多亚诉诸人的理性或逻各斯,卢梭则交由“良知”,从良知产生对道德秩序的直觉和理性判断。由此来看“出自上帝之手的都是好的”,即是说,任何物质存在都以最好的方式被置于与全体的关系之中,任何理智的有感觉的存在都以最好的方式作为其自身[4]58。 “最好的方式”基于神意朝向道德秩序的投射。所谓“好”,合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道德秩序。事物在物理秩序中呈现相对性,在道德秩序中却是绝对的。
自然秩序以潜在的理性和道德的秩序在人类身上外化和显明自身,因而卢梭所谓人自然的“善”与出自上帝的“好”相一致。“在所有作品中我已阐明一切道德的基本原则,人就自然而言是善的存在,热爱正义和秩序;人心中没有源始的恶,出于天性的行为始终正当。随人天性而来的只有一种情感,即‘自爱’(amour de soi),它本身无关善恶。”[9]170由此可见,第一,自然之善合于自然秩序,并不作为习俗层面的价值判断,而是道德秩序遵从的逻辑前提;第二,它先于人对社会化生存处境的反思,具有天然的自足性。第三,人与生俱来的只有自然的“自爱”,它尚未异变为“人为的自爱情感”(artificial self-love),即社会形态中引发虚荣或自尊的“自爱”(amour-propre)。
Arthur Melzer肯定自然之善为卢梭对现代人丧失身心和谐做出的古典式诊断,善即整全(unity),既属内在的,来自灵魂秩序的完好;又是外在的,不因欲望、激情和偏见导致与他人斗争,并天生怀有怜悯[10]16。Laurence Cooper 同样主张,自然之善在原初的自然人那里,体现为其自身形成有序的整全,同时是更大的整全之中有序运行的一部分[11]59-60。总之,自然之善顺应秩序,而秩序并非沉寂闭合的系统,而是力量消长以致平衡和谐的敞开的“生成”状态,故卢梭说,“善即对秩序的热爱,它生成秩序。正义亦是对秩序的热爱,它守护秩序。”[3]282“正义”源于良知,它保障秩序运行,而自然之善毋宁为天性的自发性建构,它生成并彰显秩序:就整全而言,每一有形存在物恰如其分地安置其中;就与自身的关系而言,每一有理性情感的存在物是其所是。“出自上帝之手的东西到人手里变坏”,换言之,人打破了自然秩序。这是由于社会形态中滋生的“自爱”,基于个体的相互依赖、利用和侵占,使每个人考虑自身的好处超过考虑他人。“自爱”作为虚荣或自尊的源泉,实质是自我主体对自身所是及他人地位的僭越,任何僭越都意味既有位置的失序,进而预示自然的隐匿。
二、人的本性
如前所述,自然之善不是其他,正是人合乎自然秩序的本性。“本性”源出自然的赋予,是事物是其所是的原因。这里,“自然”内在地含有衡量人类存在状态的根本尺度——人应成为其自身所是。因而,自然之善作为人类道德秩序的逻辑前提,不等同习俗美德之善;于上,自然之善顺应自然秩序;于下,它是人存在之自足自由的保证。卢梭从自然之善说明了人性对自然的揭示。
“谓之自然的(natural),不应从已被破坏的事物中探寻,而应转向就本性(Nature)而言是好的事物”[12]113, 卢梭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这句话作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题记。自然的,即固有正当的,必合乎自然法则。要证明“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规定,需先明了自然法则,或者说何谓自然正当。依照格劳秀斯的说法,自然正当有两个来源:或出自人的本性规定,或源于所有人、至少是最文明国家的人共有的观念。卢梭显然从人性本有引申自然正当。他将不平等之起源为何的问题转化为从普遍意义上还原人之自然本性的问题,即一个亘古常新的哲学议题:认识人自己。
从个体聚集到社会成型,伴随语言起源和理性的运用,自由意志和自我完善的能力(perfectibility)带领人类“进步”的同时却偏离了自然的引领,理智和偏见、善和恶蔓生繁盛,从而“人沦为他自身和自然的僭主”[12]141。卢梭以极为文学化的笔触描绘自然在人身上的隐却。如同神像克劳孔历经时间和海水风暴侵蚀,形似野兽而不再有神的风貌,人类经由社会的洗礼,因知识和谬误的累积、身体构造的改变和激情的不断作用,其内在的自然变得面目全非,不再依照既定法则,持守造物主赋予的堪称精妙的质朴纯一(simplicity)。灵魂中只剩畸形的激情,这激情自视为理性和智识,导致人被非本真的幻象左右。即,人之自然本性,如“神之所是”而非“野兽之所示”之于克劳孔,应为出自造物主之手时之所是,符合自然秩序的法则,尚未丧失天性原有的纯一。一方面,本性作为对人之应然的规定,逻辑上优先于任何政治社会形态。另一方面,要知晓人的本性及符合其自然构造的自然法,只能诉诸前社会状态的自然人*对此卢梭在笔记部分做了进一步解释。野蛮人自足宁静,不受自尊心搅扰,社会人则不可餍足,催生奢侈和财富,进而有了主人和奴隶的分别;人自身没有片刻喘息,其需求越是超出自然,坏的激情越发不可抑制。因虚荣自私的自爱而来的主体意识使其妄作宇宙的主人。详见Second Discourse, Notes, ix, p.199.[12]127。
卢梭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将人性固着于城邦进而做出“人就本性而言是政治性动物”的结论。于后者,政治性是人之自然朝向其目的的初始生成,而卢梭以为,政治性是人性进程的结果。
霍布斯也反对亚氏将个体聚集为城邦归于天性使然,而认为社会奠基于脱离自然状态之后人为达成的契约。他最先将“自然状态”的表述引入哲学传统。当个体都宣称保存自身的欲望和自由,其自然状态只能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充斥着匮乏、恐惧和残酷对立,缺乏公共权力保证人与人的共同同意,这种情境下,政治社会的产生成为逻辑必然。“在人的本性中,我们找到其斗争的三个主要原因,即竞争、差异和荣耀。竞争能决定控制权,身体差异决定安全与否,荣耀决定名声。一切人的普遍性情,即无休止的追逐力量的欲望,只有到生命终结才止歇。”[13]86-88霍布斯如此界定人的本性,因而在他这里,自然法作为“理性发现的诫命或一般法则”,“完全由一条公理构成:必须遵守协定。自然法被压缩为关于顺服的社会与治理契约的法律形态。”[14]77-78
卢梭肯定霍布斯看到了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弊端,即人们理所当然地宣布对其所需之物的拥有权,甚至病态地将自身想象为整个世界的惟一主人,他认为霍布斯与洛克、普芬道夫一样,并未触及纯粹的自然状态,“他们不断谈论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虚荣,这些观念是他们从社会那里拿来的,却被移植到自然状态中。他们说的是野蛮人,但描述的是政治人。”[12]132霍布斯视自然状态为矛盾的、人无法生存于其中的战争状态,是由于他将个体对权力和欲望无休止寻求的这一社会产物,错置于野蛮人自我保存的需求名下。
卢梭主张,前社会状态的野蛮人身上不存在恶,也不具有对善恶的反思;他们不做恶事,既不因为知识增长也不出于法律约束,而由于情感的平静及对恶的无知。其次,天生的怜悯削弱其自我保存的残酷和排他性,缓和对自身生存的热切,对同类遭受痛苦有着天然的憎恶[12] 151-152。由此推出属于自然人的自然法,有两条先于理性的原则,“一是对身体和自我生命保存的关切,二是出于天然地反感看到任何其他有感知的生物尤其是我们的同类遭受痛苦或消亡”[12]127。
至此,从这两条原则所见的是“自然之善”的具体表象,而要窥见自然之善的实质及其作为人的本性对“自然”的阐明,有必要从卢梭“人就其自然本性而言是好的,在社会中开始变坏”[15] 151-152及“自然使人幸福良善,社会则致其堕落”[16] 201的原则开始考察。自然与政治社会的对峙,常被作为卢梭哲学的显要观点。如何理解这里的“自然”?是认识这一矛盾的关键,也是澄清自然之善本质的关键。
事实上,自然与社会的对峙,在以下情形中可能成立:一是从历史维度论及自然,即溯至政治社会发端前,将“自然”直接等同于事实经验的、与人类习俗权威相对的“自然状态”。如Master在《卢梭的政治哲学》里所为,“卢梭的自然概念”一节从头至尾贯穿关于自然状态的讨论,“自然”作为纯粹自然状态的同义词,与公民社会的约定、与道德相对。然而,自然状态与自然实为两个概念。对自然的理解不应直接与历史意义上的“自然状态”画等号,进而将自然简单对立于社会形态。这里暂不赘述“自然状态”的复杂内涵,但须看到卢梭强调:“无法确切认识一个不再存在、或许从未存在过、可能将来也不会存在的状态,但又有必要拥有关于这一状态的确切概念,以便清楚地评判我们的现存状态”[12]125。溯及纯粹自然状态的目的,如他所言,与其说是揭示事物的真正起源,不如说为澄清事物的本性。既然本性在自然状态中“澄明”,故卢梭以自然状态为参照,反思自然之善何以在现存状态中“隐匿”。自然状态背后,存在一个更为根本的标准——自然,它彰显为秩序或尺度本身,进而促成自然之善。自然与社会相对立的第二种情形,就是单纯从人性层面界定“自然”,进而将自然之善有限地解释为人性的善好无辜。比如Master看到,自然之善在《论不平等》和《爱弥儿》中分别具有不同意义:于前者,它体现在原初自然状态中的人身上,是自由选择的、前道德的自然的好;于后者,它是卢梭试图通过教育在社会状态中的爱弥儿身上实现的善,显然是自我追加地,或者说至少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人习得的、道德的[17]212。但他的结论是,自然之善两种可能的呈现是卢梭个人对其内在融贯的思想做出的“危险让步”,换言之,Master认为自然之善的不同实现途径表明了这个概念内部本身存有分歧。然而,自然之善的内涵于卢梭并无歧义,问题症结在于Master对自然之善的理解。他仅将善界定为原初的自然人才有的无辜及其对恶的无知,善因此只限于单一的绝缘于世的个体,与不可见的、整全的自然秩序没有关联。而只要我们回顾《爱弥儿》中卢梭所说“善即对秩序的热爱,它生成秩序”,便可将对自然之善的理解拉回到更为恰切之处。
同样,尼采认定卢梭于人类自然的无辜与社会建制的腐败之间设置了危险、幼稚且不可调和的对立。如此,自然之善的意涵被简单化,表面看来与政治社会的人为规约相对。但正如Keith Pearson提到,尼采“没有考虑到卢梭关于社会建制的改革必须以我们内在道德感觉的改革为前提和基础的主张,认为他热切而幼稚地要求回到一种无辜的自然状态,而这是卢梭从未严肃提出的要求”[18]56。可以说,Pearson提及的“内在道德感觉”正是自然之善在社会状态下的寄居形式,自然之善所依循的“自然”,作为衡量存在状态的尺度,在政治社会形态中仍然有效。
康德洞悉表象,他阐明,卢梭《论不平等》中成问题的东西,在《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里都得到解决,卢梭思想中自然和道德之间的任何对立都能得到克服。如果我们把对立于“野蛮”的文化理解成“教育”,政治社会中被当做道德性物种的人,其发展便终结了自然与道德的冲突[19]67。原初状态里的自然之善在社会形态中泯没,或者说人的自然天性因社会进程而被遮蔽,就是康德所谓“《论不平等》中成问题的东西”,而他清楚地看到卢梭将对自然之善的期待置于教育或奠基于社会契约的文化进程上。
紧随康德的阐释路径,卡西尔对卢梭“自然之善”做了说明。自然之善不是感情的原初特征,而是人类意志的根本方向和根本命运;它并不倚靠某种同情的本能,而基于人类的自决能力[20] 93-94。即是说,自然之善的天性,跟感官本能无关,它蕴涵对秩序的热爱和某种向上的牵引力,“不用外在帮助就自发地将其自身提高到那自由的观念上”。
“自由的观念”,确切而言,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那里指向“自然的自由”(natural freedom),卢梭视之为源初意义上的自由,在已有道德意识的人身上,作为“道德的自由”(moral freedom)。自由是极少欲求与有限能力间的平衡,自足而不待于外物,或者说,自由是自然本性的内在升华。自然作为评判存在的尺度,自由是其核心。对此,施特劳斯的解释更为明朗。他看到,公民社会在卢梭那里必须被超越,但并不朝向已被他削弱和抽空的自然状态,而旨在历史上或曾生活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的特征,或称之为自然性的东西,即独立和自由。“自由就是善;自由,或者说成为一个人自己,就是成就善。不是理性而是自由成为了人的特质”[21] 284-285。施特劳斯所谓“自然性”,即人成其为自身的自由与自足,是自然之善超越公民社会或任何政治形态的自行展开。再次说明,自然在其作为生命内在尺度的意义上,相应于人的天性,与社会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相互取消的关系。
虽然卢梭指出原初自然人本性的不可复返,但自然之善并不是历史的、止步于原初状态的,而是能够在任一合乎自然秩序的存在状态中找到的特质。自然之善始终是对自然秩序的顺承,它显明自然以秩序和尺度规定人之所是,人从而得以依循天性固有的道德法则印证自身的自由。
三、植物世界
如果说卢梭对人性的追溯是一次“认识人自己”的实践,投身植物学毋宁是他直观自然,认识自身并体察自足存在的精神实验。
启蒙哲人霍尔巴赫以力学理论机械地拆解自然和观念世界,在卢梭看来,抽象而形式主义地看待自然并无法通达其内在生命。借用卡西勒之言,17世纪和18世纪的数学逻辑精神将自然变成单纯的机械装置,而卢梭再次发现自然的灵魂。他并不以自然作为外在的、为人的意志所用的对象,对“自然的灵魂”的观察,实为对自身存在意识的把握。通过植物学,他径直进入自然,不断回溯《孤独漫步者的遐思》开头抛出的问题:我是谁?卢梭宣告自己孑然一身——“在这世上不再有邻人、同胞和兄弟”——令他抽离对政治、社会和习俗权威的思考,决意关注自己,从他自身寻求慰藉、希望和宁静,在这样的状态中严肃、真诚地检省。卢梭这项自我认识的实验,如气象学家运用气压计测度天气状况一样精准,只是他检测的是自身灵魂[22]7。孤独的遐思时光将卢梭毫无阻滞地交还于他自身。“交还”,即面向自然的“回归”,“完全作为自己并以自己为目的”,由此卢梭才得以宣称“是自然所希望造就的那种人”[22]9。
对植物的观照与卢梭自身认识的呼应,首先出现在“第二次散步”。秋冬交际的自然景象混杂正值时日的繁茂与凋敝初现的踪迹,甜蜜又伤感的印象令卢梭联想自己不再年轻又尚未老迈的年龄。所幸他这件“造物主的作品”心怀善意、感知敏锐并能耐心应对外界谴责,这样的反思让他释怀。在从青年到成熟时期的回忆中,他重新欣喜地接纳了自己。“第七次散步”的主题则完全交给植物学。卢梭解释了对植物学这一“无用的研究”保持热情的原因,“它有助于自我认识,我在有生之年所要致力的正是这种对自己的认识”[22]58。他将植物比作地球的外衣,呈现于人充满生命力、情致和魅力的景象,也是世上惟一不会让他的眼与心厌倦的景象。遐思催生符合天性的直觉,让他从沮丧的观念中挣脱,平息想象,继而聚焦于周遭的自然事物,第一次充分细腻地体验到自然的奇观,在那之前他只耽于对自然庞然整一印象的冥想。
卢梭切身体会到,沉思的人具有愈敏感的灵魂,愈能将自身付予与周遭世界和谐圆融的狂喜之中,“他感到自身为一,一切具象悄然退却,他只意识并感受自身处于整全之中。”[22]59倘若为具体的表象世界所困无法通达这种体验,阻力之一来自他念侵扰内心,导致迟钝的自然感受力,之二则归咎于人们对植物王国的疏远,惯于从植物身上寻求药用价值。植物学于卢梭“无用”,在于它只作为纯粹的自然——自然从不说谎,也从不教导我们屈服于人类权威——因此他只面向自然本身,不致力获得知识或实用价值,采集标本也不为建造“药剂师的花园”。卢梭称亚当为第一位药剂师,因自人类亲近智慧之树,就已为心智的功利化转向埋下隐患。工具理性的进展使人将事物视为物质利益的载体,越寻求利益和效果,也就越漠然疏离于自然。植物学的第一大不幸,即从一出现便作为医学的分支。功利或虚荣掺杂于本应闲适自如进行的植物学研究,自然的美妙便消逝不在。
植物学之于卢梭,在Heinrich Meier看来,显露出哲学研究的基本倾向,换言之,卢梭在植物学里找到了哲学研究的本真意趣。不同于医学和药剂学的实践做法,植物学限于对自然本身展开观察,也不同于实用的理性思考,植物学营造了纯粹的沉思能提供的乐趣[23]97。真正的哲学规约人的理性,引导其认识内心同一于自然及其秩序的道德法则,其结果是朝向人本身的回归,这是卢梭早期在《论科学与文艺》中强调过的。理性运用的纯粹,从一方面证明了卢梭植物学的哲学化特征;Meier将回归天性的自由作为卢梭经由植物学认识自身存在的本质所在,可谓哲学化倾向的另一方面。遐思将卢梭置于具象的自然中,对植物学的观照则使他从作为现象世界的自然上升到与普遍意义的自然沟通,即天性与自然秩序的融合,只有顺应自然天性的规定,人才成其为自身。“当卢梭充分体现自身并实现特殊天性,他也就符合普遍意义上的自然。自然不‘愿意’看到他因献身于其他更伟大和更高级的存在而丧失自身。”[23]85Meier将“孤独漫步者”作为卢梭特殊天性的身份承载,因而,遵从自然的意愿,卢梭作为他自身达成与自然的和谐,既不否定也不消解自身于其中。由此,Meier将沉浸于植物学中的卢梭最大程度地阐释为哲学意义上的个体存在。
毋庸置疑,卢梭通过植物学纯粹的自然世界转向其自身,如Starobinski所言,在与植物学的亲密交道中,他转向内在,并引出他自己的本质存在(substance)。然而,对照卢梭与同样热衷认识自然的歌德,Starobinski似乎看到卢梭“转向内在”的局限。歌德尝试从自然可见的混乱表象里建构秩序,他的精神力量积极朝向外界发生作用,不停留于内在的自我慰藉。卢梭的植物学兴趣,则不具有歌德那种“行动的形式”,也没有将他与世界真正关联起来,因此,卢梭在植物学里找到抚慰内在的镇静剂,但其效果并不持续和彻底[24]235。
卢梭与自然的照面止于精神的“内在循环”,即是说“卢梭在自然中寻求的,是他的精神从前所供养的。自然的清白能填补他意识的虚空,而植物又是自然事物中最无辜的,作为自然纯粹性的象征净化卢梭的内在。无用的植物学不具外在目的,如果说它有用,则在于纯粹的内在目的:它恢复卢梭对其自身存在的把握,并使他过去关于幸福的回忆鲜活起来。”[24]236总之,植物学这项适于散漫孤独者的工作,似乎是卢梭对自身空虚和妄想的消化。Starobinski敏锐窥见卢梭的植物学兴趣与乐谱抄写的工作“异曲同工”:二者都不生成新事物,而只作为透明介质,复制现有的。植物学于卢梭,是精神的自我复述,并无其他意义。他沉浸于重复性的活动,是因为任何新的启动都可能作为“闯入者”,陷其于未知的危险和无力抵抗的境地。只有投身到这种活动——向内无害,不似理性活动的反思搅扰内心安宁;向外也无害,由于它不超越自身向外寻求某种目的——卢梭的焦虑才得以缓释。或言,面对植物学,卢梭无需做反思的努力,因为自然“直陈”自身,自我从中获得一个无障碍的世界,没有来自外在的投影。自然及人自身,都在内部谋求纯粹整一,无关他物。
植物学的确为卢梭提供了一个向内实现自身实存的天然场所,自足的精神实验使他表面上与现实世界割裂,这一点从《对话录》也能找到证明,卢梭坦诚他在对自然的沉思中找到了他所需的依恋感的补充,只有在努力与人交谈失败之后,他才转向与植物交谈。但是,我们应看到,卢梭将亲历自然作为一项普遍的适宜人们灵魂本性的活动,“在任何年纪,对自然的研究令肤浅消遣的趣味黯然无光,它平息激情的喧嚣,通过沉思最有价值的事物为灵魂带来滋养”[25]130,这里他对所有人说,将自然研究的意义归于对灵魂的教养,进而作为走出“洞穴”的精神助力。由此来看,植物世界不止供给卢梭求索自身整一存在的处所,它至少还揭示了自然于人本有的亲缘性,以及人们经验纯粹自然并重获有序灵魂的可能。重提Lester Crocker的总结,他认为在卢梭那里,人打破自然秩序并难以补救失序的现状,惟一的出路在于新秩序的建构,即理性和意志的而非本性的建构。那么,如何实现理性和意志的有序建构?终将立足个体,个体理性和意志的重塑离不开内在道德和精神法则的建立。而植物学或对自然的亲近和体察,恰好能成为使激情得到规训、灵魂内在秩序得以恢复的场域。这也是德里达所谓卢梭那里作为“替补”的自然的教育之旨归。
如果说植物世界开启的自然,作为隔绝人类权威和社会之恶的避难所,那么,自然与社会似乎再次陷入矛盾。然而,卢梭于植物学中感知存在的自足,与自然融洽甚至“如神衹般存在”,此时这位孤独遐思者,其本质是作为人而非社会公民。卢梭超然于社会之外体察自身与自然的整全,切身触及卡西尔谓之为“善”的自由观念,或者说朝向施特劳斯谓之的“自然性”,在此意义上他或许能称自己为源初自然秩序的“臣民”,因天性使然而为“善”。在这里,自然引导个体顺应自然秩序及人的天性,趋向道德的自由之实现。由此也看到,秩序、本性与植物学关联为一个整体,呈现从上至下、从普遍到特殊的谱系,阐释了卢梭的自然观念。
卢梭的“自然”谱系已揭示“自由”为自然之根柢。自然秩序与作为本性的自然之善,联结了自然与现代政治社会,秩序及依循其而生的自然之善,从自然神学和自然法的阐发为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道德自由的必要性提供充分佐证;植物学敞开的自然世界,则是使个体更为本真且体己的存在得以聚集于人自身。然而,由此看来,坚持回避形而上学哲学讨论的卢梭,并未全然避开形而上学的庇护。同时,他对自身存在的把握,因囿于固定的时空及对象,似乎难以从根本上超越“有待”之隅。
[1]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家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2] Lester Crocker. “Order and disorder in Rousseau’s social though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Vol. 94, No. 2, 1979.
[3]J. J. Rousseau.Emile:oronEducation,introduction,translation,andnotesbyAllanBloom, Basic books Press, 1979.
[4]J. J. Rousseau.LettertoVoltaire,inRousseauonPhilosophy,Morality,andReligion, Christopher Kelly ed.,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03.
[5]J. J. Rousseau, Julie, or the New Helois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 Vol.6, Roger D. Masters, Christopher Kelly ed., Philip Stewart and Jean Vaché trans.,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1997.
[6]克里斯托弗·希尔兹:《古代哲学》,聂敏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mile Bréhier.TheHellenisticandRomanAge, Wade Baskin tra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8]Asher Horowitz, Rousseau.Nature,and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9]J. J. Rousseau. “Letter to Beaumont”, inRousseauonPhilosophy,Morality,andReligion, Christopher Kelly ed.,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03.
[10]Arthur M. Melzer.TheNaturalGoodnessofMan,OntheSystemofRousseau’sThough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1]Laurence D. Cooper, Rousseau.NatureandtheProblemoftheGoodLife,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J. J.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or Second discourse”, inTheDiscourseandotherearlypoliticalwritings, V. Gourevitch ed. &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Hobbes.Leviath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5]J. J. Rousseau. “Letters to M. le President de Malesherbs”, inRousseauonPhilosophy,Morality,andReligion,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07.
[16]J. J. Rousseau, “Third dialogue”in Judge of Jean-Jacques: Dialogues, CW, Vol.1, Roger D. Masters, Christopher Kelly, Judith R. Bush?ed. & trans.,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1989, p.201
[17]马斯特:《卢梭的政治哲学》,胡兴建、黄涛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8]凯斯·安塞尔-皮尔逊:《尼采反卢梭——尼采的道德-政治思想研究》,宗成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19]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0]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王春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21]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22]J. J. Rousseau.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 CW, Vol. 8, 2000.
[23]迈尔:《论哲学生活的幸福——对卢梭系列遐想的思考两部曲》,陈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
[24]Jean Starobinski, Jean-Jacques Rousseau.TransparencyandObstruction, Arthur Goldhammer tra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25]J. J. Rousseau. “Botanical Writings, Elementary Letters on Botany”, Letter 1, CW, Vol. 8, 2000.
责任编辑 吴兰丽
Order, Human nature and Botany——The Genealogy of Nature in Rousseau
DU Ya
(DepartmentofPhilosoph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Nature is considered as the substratum of Rousseau’s thought. Order, human nature and botany illuminated ‘nature’ in different ways, representing a genealogy that was from divinity to secularity and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Rousseau, owing a view that the order of morality complies with the order of nature to Stoics to some extent, suggested that nature primarily presented itself as an order that was identical to Providence, and externalized over humanities as a potentially rational and moral order. Consequently, natural goodness of human beings, which served as a promise of moral order and conformed to the natural order, aimed to the idea of natural freedom. In further, Rousseau retrospected to original natural men in order to explain natural goodness. He thought that the socialization caused the order of nature disturbed, and then humans’ simplicity as well as natural freedom had been lost. However, botany provided a world where Rousseau could communicate with the pure nature, he examined himself and experienced the sufficiency of existence. Therefore, nature instructed individuals to follow its order and one’s naturalness, achieving to the moral freedom.
nature; order; human nature; Botany
杜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近代欧洲哲学。
2016-12-02
B565.21
A
1671-7023(2017)02-01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