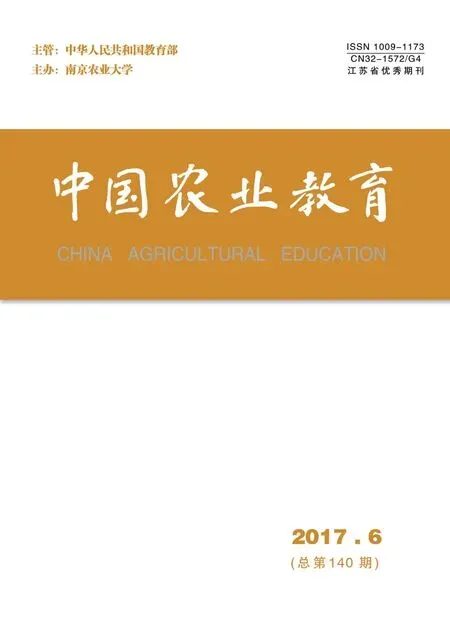“双一流”背景下农业史学科发展的挑战与前景展望
杨乙丹,樊志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 杨凌 712100)
农史学科是以各个历史时期农业科学与技术、农业活动与自然环境、农业制度安排与经济实绩、农业文化与人文素质的发展演变规律为核心研究对象,以培养为社会发展服务,具有较强解决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实际问题能力和独立从事农史研究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为目的的交叉边缘学科。农史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至今不足百年历史。
在经历长期的积淀和酝酿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农史学人在回顾农业史学阶段性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农史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1]、农史学科的价值和任务[2]、农史学科的主体意识培养和体制化建设[3]、农史学科结构完善和理论方法体系构筑[4]、观念的更新与农史学科发展[5-6]、现代化和全球化与农史研究的推进[7]等角度,廓清了农史学科发展的一些核心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农史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但社会的不断发展内在地要求农史学科要紧密跟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当前,弘扬祖国优秀文化、提高文化自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正方兴未艾,“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它们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鉴于此,本文在系统回顾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剖析农史学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学科体系发展、研究水平提升、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以及学科管理机制创新等方面,探讨我国农史学科的发展前景。
一、农业史学科的积淀与初步建制化
农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欧美国家始于1910年代,在中国则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5]。但我国农史学科却有着几千年的积淀。早在远古时代,伏羲氏养六畜和种五谷,神农尝百草和教民食五谷,黄帝播百谷,后稷教民稼穑等传说,已经昭示了我国农史学科丰厚的底蕴。先秦时期,重农思想的系统阐发、农家学派的活跃以及哲理化农学论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统农学的形成。继之,《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农书的接续出现①,一次次将我国经验农学推向新的高峰,同时也为农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世纪中后期,西方近代科学技术逐渐传入我国,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方农学著作的过程中,不免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试图在研读中国古农书的同时,探寻中国经验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的相通之处。其中,创办《农学报》和开办农务学堂的罗振玉,就是典型代表。当然,在移植西方实验农学的过程中,不顾国情、民情的生搬硬套和囫囵吞枣现象的确较为常见,一度出现“今农校教科书纯用东瀛译本,于本国农学言皆摈而不录”的局面。对此,清末民初学者高润生明确进行了批评,并在“以经义说农事,以农事证经义”的方法论指导下,提出了全面整理和继承古代农业遗产的方案和方法[8]。这些努力在将中国经验农学逐渐导入近代农学的同时,也使得农史研究初具学科形象,渐入科学范畴。
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革命”和随后的“社会史论战”,不断推动着中国经济史研究向纵深迈进,农史就被蕴含其中。与之同时,日益恶化的农村社会经济形势,也促使一些学者将研究视野转向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于是,农业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其中丁颖对水稻起源中国的论证,栾调甫和胡立初对《齐民要术》的整理研究等,具有先导性意义。另外,毛雝等人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陈其鹿的《农业经济史》、徐士圭的《中国田制史略》、尹良塋的《中国蚕业史》、李士豪的《中国渔业史》、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姚公振的《中国农村金融史》、陈安仁的《中国农业经济史》等著作,也纷纷涌现出来。并且,日益增多的农史论文也相映成辉,其中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尽管只出了6卷61期,但刊登的论文已经包括历代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农村组织、农民生活状况等内容。
经过长期的积淀,中国农业史学科的建制化被提上日程。1921年,金陵大学设立农业图书部,开始系统收藏中国农业古籍。1924年,万国鼎先生担任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后,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迈上新台阶,随后的20余年内,分类辑成《中国农史资料》456册,3700余万字[7]。1932年,金陵大学农经系在万国鼎教授主持下,创设了农史研究室。1933年,中国地政学会在萧铮和万国鼎的领衔下创办了《地政月刊》。此外,万国鼎先生还著有《中国田制史》,发表了系列农史研究论文,并翻译出版了格斯拉的《欧美农业史》,拓宽了中国农史学人的视野。所有这些,都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层面的农史机构建设和农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农史研究是以社会经济史为核心的,农业科技史、农学思想史等内容虽有所涉及,但显得十分薄弱。研究者更多的是在兴趣爱好或责任使命的驱使下进行的,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并且,尽管金陵大学的农科开设了农业经济史、国立政治大学开设了中国田制史等农史课程,但学科结构仍未体系化,科教队伍仍未真正建立,体制化的农史人才培养机制仍未构建。
二、专业性农史机构建设及其兴衰曲折
新中国成立伊始,农史研究在承继民国余脉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一些高校甚至成立了新的专门研究机构,如1952年西北农学院在辛树帜、石声汉的倡导下,组建了“古农学研究小组”,开始着手辑录、校释古农书的工作。但当时全国性的农史机构还未成形,农史研究仍呈“星星之火”的态势。
解放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就曾发出“整理研究祖国医学农学遗产,把它们发扬光大起来”的号召。1955年4月,农业部召开了“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决定积极、系统地整理研究和出版我国古农书和农史资料。会后,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双重领导,万国鼎先生任主任[6]。与之同时,西北农学院党委决定将学校原农史小组扩大,成立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1956年,研究室获农业部批准正式运行,石声汉先生任研究室主任。此外,北京农学院虽然没有成立专门的农史研究机构,但王毓瑚先生受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委托,开始系统编写《中国农学书录》,胡道静、张仲葛等先生也开展了相关农史资料的校注和研究工作。华南农业大学在梁家勉先生的主持下,于1955年创建了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1960年代,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农学院也成立了农业遗产研究室。
农史专门机构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农史学科的发展。其中,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1956年后的短短四年内,从全国4000多部古书中整理出了1540万字的农史资料,并从8000多部方志中摘抄了3600万字的农史资料[8]。同时,还出版了《陈旉农书校注》《补农书研究》《齐民要术校释》《四民月令辑释》《四时纂要校释》等,并编成出版了《中国农学史》,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农业科技史著作。在“文革”以前,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完成了《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便民图纂》《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24部骨干古农书的整理、校注、出版工作,同时还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绘制了《农书系统图》《中国古代重要农书内容演进图》[8],并出版了《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农书评介》《我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尤其是石声汉先生推出的英文版《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极大提升了我国农史学科的国际化水平及其在世界农史学科中的地位。北京农学院的王毓瑚先生则整理出版了《农圃便览》《农桑衣食撮要》《梭山农谱》《秦晋农言》《郡县农政》《区种十种》等。浙江农学院的农业遗产研究室,还于1965年创刊了《浙江农史研究集刊》,为农史的持续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除此之外,一些科研院所的学者还探讨了农业史领域的专门问题,如刘仙洲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谢成侠的《中国养马史》等。
“文革”期间,各地农史机构遭到了破坏,许多农史学人也在此期间作古,农史学科一度处于凋敝状态。其中,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被撤并到江苏省农科院,更名为农业技术史研究室[6];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经历被撤并的变动后,研究工作一度无法开展,直到1971年才逐渐恢复工作。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夕是我国农史学科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专门农史机构的设置吸纳了一批学人进入农史领域,农史学科的专业队伍逐渐建立。并且,井喷式的研究成果,也为学科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当时并没有组建全国性的组织或交流平台,各单位之间“各自为战”的态势较为明显。另一方面,农史研究还处于“摸清家底”的阶段,系统的专题研究刚刚起步。尤其是在人才培养方面,还缺乏学科专业的支撑,农史学科的青年学人,大多数是在兴趣爱好的驱使或者前人的感召下进入的,缺乏体制化的培养机制。
三、农业史学科体系构建与蓬勃发展
1979年春,农业部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郑州召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编写会议,被喻为“农史研究的春天”的到来。随后,农史学科体系逐渐得以构筑,农史学科进入到快速发展的轨道。
(一)农史机构的恢复与建设
1978年以后,各地已有的农史机构逐渐恢复开展工作,一些科研院所还趁势建立了新的农史研究机构。其中,华南农学院于1978年正式设立了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1980年该室又获批为农业部重点研究室;浙江农学院的农业遗产研究室恢复后更名为“农业科技史研究室”;河北农学院于1980年代专门设立了农史研究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于1994年成立了当代农史研究室;甘肃农业大学于2007年成立了农史与农耕文化研究所,等等。
在各科研院所设立农史研究机构的同时,全国性的和区域性的农史学会也逐渐宣告成立。1987年9月,中国农学会农业历史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农史学人终于有了全国性的合作交流平台。1993年2月,民政部更是批准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升格为国家一级学会。在此背景下,省级农业历史学会也相继在江苏、广东、山东等宣告成立。此外,在中国科技史学会体系下,还专门设立了农学史专业委员会,各省份成立的科技史学会,同样活跃着农史学人的身影。
(二)标志性成果叠涌与专业刊物创办
在恢复工作之后,农书的整理出版仍是农史学人的一大要务。于是,缪启愉的《四民月令辑释》《四时纂要校释》《齐民要术校释》《东鲁王氏农书译注》,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授时通考校注》《农桑辑要译注》,王毓瑚点校的《王祯农书》,以及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等等,纷纷得以面世。
在完成《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后,农史学界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攻克《中国农业通史》的编撰。在此过程中,杨向奎等人的《中国屯垦史》、游修龄组织编写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闵宗殿组织编撰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范楚玉和董恺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周昕的《中国农具发展史》、杨直民的《农学思想史》、曾雄生的《中国农学史》等标志性著作,纷纷涌现。
专业性农史期刊的创办,是这一时期农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1980年,梁家勉先生率先办起了十年动乱后第一份农史学术刊物《农史研究》(1990年停刊)。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筹委会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了《中国农史》,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主办了《农业考古》。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这些期刊的创办,不仅为农史学人提供了有效的沟通交流平台,也为农史学科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研究内容的廓清与学科体系的完善
与历史学科和农学学科相比,农业史是一个交叉学科。为了廓清农史学科的内涵,1980年代中期,一批农史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深入探索了农史学科的框架体系。其中,梁家勉先生主张在三级分类法的基础上,将中国农业史首先分为自然农学史、社会农学史、农业思想史以及农业文献,然后在自然农学史类下分生物史和非生物史两类,在社会农学史类下分农业政治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政策史、农业教育史。其中,生物史类下又可分为农动物史和农植物史,非生物史类下分土壤史和水利史。张波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应该从基础部分(外层)和专业部分(内层),构建农史学科层次体系。其中,基础部分包括相关的农学、文献、地理等学科知识,专业部分包括农史资料、农业历史和农史理论[4]。王思明先生在罗马尼亚农史学家尤金·米尔斯的基础上,将农业史按照综合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四类,划分了47个方向[6],基本上厘清了农史学科的具体研究方向。
在廓清农史研究的领域之后,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以及农业历史文献整理研究,就成为农史学科的核心方向或研究领域。直至今日,它们依然在各农史学科人才培养中具有积极的指导价值。
(四)理论方法体系的构建与研究视野的拓展
在明确农史研究面向之后,一些农史学人从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构建方面,明确了农史学科发展的关键基础问题。其中,农史研究理论体系包括由农史基本理论和农史具体理论构成的客观农史理论,由农史学科概论、农史研究法、农史体制理论构成的农史研究理论,由农史认识论、农史方法论和农史本体论构成的农史哲学[4]。当然,具体的理论运用,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条件加以选择。
在研究方法方面,传统的农史研究主要采用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以及古文字学等研究方法。但随着农史研究面向的扩展,交叉研究势所必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被列入农史研究的具体方法[6]。此外,比较研究法、计量研究法,尤其得到强调。
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明确,推动了农史研究视野的拓展。其一,考古学与农史深刻交融,成为农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中,史前农业遗址和古代农具的发掘研究,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辩,画砖、岩壁、墓葬中农史信息的采集与分析等,得到深入推进。其二,在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下,民族地区农业史与农业文化等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进而,区域和断代农业史,成为农史研究的一个核心方向。其三,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得到发展的同时,环境史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等,在农史研究领域得到充分吸纳。继之,农业灾害史成为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其四,在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成为农业领域的研究热点之后,农史学人不失时机地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农业伦理思想、精耕细作的经营思想、“地力常新壮”的可持续农业思想等,展开了深入研究,为现代农业发展提出了宝贵经验。第五,比较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使得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农业科技文化、农业社会经济史等领域成果,不断涌现。
(五)学科平台建设与对外交流的紧密
学科平台既是对学科发展成就的展示和肯定,也是推动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进入新世纪以来,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室,都在学科平台建设方面成绩突出。其中,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于2001年6月组建成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随后又相继获批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等,并筹建了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并且,该院的科学技术史专业还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西北农业大学的古农学研究室于1999年与西北林学院林业史研究室合并为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2008年获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组建为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16年12月获批农业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并拥有4000平方米的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创立了国内农业大学唯一的历史系,组建了跨院系的农业文化与乡村旅游、岭南生态史等研究中心。
日益强化的对外交流,也是农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展示。全国主要农史研究机构以农史学会年会为平台,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并开展了不定期的互相走访学习。与之同时,对外学术访问与合作交流越来越紧密。例如,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目前与世界十余所科研机构保持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其中,与英国雷丁大学合作建立的“世界农业起源与传播联合中心”,与美国普渡大学组建的联合研究中心,与日本相关高校合作共建“中日农业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等,将中国农史学界与世界农史学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六)专职队伍的扩大与农史人才的培养
1978年以前,全国主要农史机构的专职科教人员基本上停留在个位数的规模,其他农史学人则零星地分散在各科研院所。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机构的恢复发展,农史队伍超过了250人[8]。随后,这一数字一直呈递增的态势。目前,南农、西农和华南农大三家农史机构,常年保持30~80人的科研队伍。另外,中国科学院、全国农业展览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还保留规模不等的农史队伍。同时还有农史科教人员分散在不同的单位。
专职农史队伍的扩大,与专门农史人才的培养密不可分。1980年,梁家勉先生在华南农学院创设了第一个农史专业硕士点,主持制定了《农史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农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开始招收农业史专业研究生。随后,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也相继招收农业史研究生。1997年学科专业调整后,农业史硕士点转为科学技术史一级硕士点,各主要农史机构继续招收研究生。
在硕士生培养的过程中,农史博士生培养也得到大发展。1986年,南京农业大学获批农业史博士学位授权点(1997年变更为科学技术史一级博士点),正式招收农业史博士。2004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二级博士点下,培养农业史博士。2005年,华南农业大学自主设立了作物史二级学科博士点,招收作物起源与发展史、农业生态史方向的博士生。
除几家主要农史单位之外,南开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等,也或先或后地在环境史、科技史、中国史等学科下,招收农业史方向的硕士或博士生。尽管各单位农史研究生培养规模难以精确估算,但一些院校的统计数字还是能佐证农史人才培养和农史队伍的发展状况。例如,自1980年代初开始招收研究生至2017年,南京农业大学先后培养农史博士生263名、硕士生197名;西北农大先后培养农史博士生74名、硕士生219名。
四、“双一流”背景下农业史学科发展的困境与挑战
经过多年耕耘,农史学人不仅整理研究了祖国农业文化遗产,探索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也培养了大批农史专门人才,为农业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农史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在研究过程中,研究领域较为单一,偏重于农业技术史的研究,忽略技术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互动关系[6];研究方法和和研究手段陈旧,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史、经济史研究中的理论方法,在农史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将研究界定在远离现实的藩篱内,缺乏现世价值关怀;人才培养模式单一,难以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要求;教学模式较为陈旧,教学的前沿化、国际化和本土化水平有待提升;基础条件建设、学术交流互访、社会服务水平等,需要迈向新台阶,等等。事实上,上述问题已经被农史学人真切地认识到,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规避,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假以时日,农史学人一定能切实解决这些问题。
“双一流”战略的实施,为高校和学科专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但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尤其是边缘学科,受到的挑战更大,农史学科也不例外。
(一)学科点呈“断崖式”撤销
2016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下达2016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通报了全国25个省份的175所高校撤销576个学位点的情况。在被撤销的学位点中,科学技术史、专门史等学科十分显眼。其中,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和郑州大学在内的8所大学,被撤销科学技术史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前者曾有王毓瑚、董恺忱等农史大家先后耕耘60余年,培养出一批农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是中国农业史研究的重镇之一[9];后者以中原科技史,尤其是中原农业科技史为研究特色,在农史学界影响颇大。
为推动农史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科研院所还设置了相关的专业,以突破科技史专业招生规模的限制,但在这一轮学科调整中,它们也受到了影响。例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曾设置了专门史、科技哲学二级硕士点,这些专业同样培养农史方向的研究生,但2017年之后均不再有招生资格。
(二)招生规模急剧萎缩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集中打造世界一流学科成为各高校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核心策略。而入选一流学科不仅意味着在学科建设、资金保障、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照顾和倾斜,也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招生规模和机会。而作为交叉边缘学科,农史不可能成为重点支持的学科,各农林高校公布的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已经印证了这一点。这一局势对农史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带来的极大的挑战。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农史研究生招生规模近几年逐年下降,已经从之前年均10名左右的规模,萎缩至2018年的3人。
(三)政策瓶颈制约与保障条件的局限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农史与其他边缘学科一样,均面临队伍萎缩和保障条件有限的挑战。于是,被确定为一流学科的会得到充分的人财物保障,即使没有被确定为一流学科,各省和高校也推出了省级和校级一流学科建设的方案。但无论如何,农史学科都难以进入一流学科建设梯队,后续的发展保障必然会有限。
在目前培养农史研究生的高校,普遍实行以项目或科研经费为核心指标的导师审核制,对于那些没有经费的教师而言,即使有高级职称和长期的学术积累,也可能面临没有资格招收研究生的尴尬。而农史学科的交叉边缘属性,决定了农史学人在争取项目和科研经费方面困难重重。目前实施的研究生津贴制度,甚至会要求导师支付给研究生助研经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史研究生的培养。
(四)学科体系的断裂与领军人才培育的困局
农史学科是一个缺乏本科层次人才培养的学科,进入农史领域的研究生学科背景极为复杂。农史跨学科培养模式,需要有长期系统的培养体系方能确保人才质量。但目前除了南京农业大学科技史专业具有硕士和博士连续培养资格之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作为老牌的农史重镇目前仅有培养农史硕士的资格,其他农史人才培养单位也同样面临学科体系断裂的问题。
领军人才的规模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以后,农史学界有多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等。但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农史学界领军人才的培育空间将会受到很大的压缩,进而会影响农史学科的后续发展。
当然,目前农史学科发展的困局和挑战并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有些问题并非外部因素造成的,但无论如何,农史学人都要学会面对,并抓住机遇,突破今后发展的制约瓶颈。
五、农史学科发展的机遇与前景
尽管农史学科在发展过程中自身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双一流”建设对农史学科的后续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但总体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2011年10月,中共中央明确了“文化强国”理念,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必须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十九大报告在倡导“文化自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事实上,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已经为农史学科指明了攻坚方向、发展机遇和任务要求。为此,农史学人应在明确重任的同时,通过完善学科体系、提升学术气质、创新培养机制等途径,推动农史学科的持续发展。
(一)强化优秀传统农业文化的挖掘与价值阐发
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业文化的类型,其中,“敬天授时”的农业物候观、用养结合的土地利用观、“尽地力之教”的重农观、以民为本的国家治理理念、耕读传家的修身立命观、仁爱和睦的家庭观、“治田勤谨”的经营观、互利共生的和谐观、“富而好礼”的乡村建设思想等,不仅确保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也型塑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在以往农史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农史学人虽对传统农业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传统优秀农业文化对人们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借鉴、对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矫正等功能的挖掘和阐发,仍有待加强。
(二)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
传统农业强调天地人的内在统一,强调人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融合,注重人的幸福感的保持,具有深刻的生态内涵和深沉的伦理意蕴。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中华先民创造了原创性的农学思想理论体系、独具的农业技术体系和独特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留下了丰厚的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系统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传统农业遗产,意义深远。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可知、可感、可用的遗产,关乎到人们未来的生存和发展[10]。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相继开展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挖掘、保护和传承,仍是十分重大的课题,需要农史学人在研究机制创新、价值与内涵挖掘、新型保护和传承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
(三)推动新型高端农史人才培养机制建设
自1980年开始系统培养农史专门人才以来,各农史科研机构在人才培养方面一直呈各自为战的局面,培养方案的设计、培养计划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置等,基本上各行其是,优秀教学资源和平台的共享极为有限,限制了人才培养质量。为了适应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各农史机构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促进一流农史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成立“中国农史教育联盟”,订立教学资源与平台共享合作协议,通过互联网授课平台建设、学分互任、精品课程联合开发、联合培养等方式,打造我国新型高端农史人才培养机制和平台。另一方面,在通过学科培养体系和优势资源平台共享的同时,整合各方资源,共同加强基础建设,建设世界一流农史学科。
(四)提升农史科教水平和学术气质
在立足中国农业发展历史进程、总结我国农业历史的规律和经验的基础上,大力学习、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农史研究的前沿理论与方法,提高我国农史学科科学研究与创新能力,在重大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争取有所突破,渐次形成一批新的、具有特色的标志性成果,为中国农业发展中的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深入的分析和有益的历史借鉴,并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气派的学术气质,为建设世界一流农史学科注入独特的学术内涵。
在教学上,根据建设世界一流农史学科的要求,提升教学的前沿化、国际化、数字化水平,进一步改革和拓展教学模式,提升实践教学、联合教学的水平和质量。并且,要强化农史学科教材体系建设,围绕农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业历史文献等核心课程,建设能体现学科发展前沿、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中国话语的农史学科核心教材体系。
(五)创新学科管理机制
农史学科需要在明确世界一流农史学科定位的基础上,加强学科梯队优化,提升学科基地和平台的质量,夯实学科持续发展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要不断创新学科管理体制,突破目前单位制的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在各农史机构中构建自身的委员会系统,在组织重大科研攻关、审议学科发展规划、制定学术规范和学术评议标准等方面,实施专家委员会制,提升农史学科自我管理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
[注释]
①根据王毓湖先生在《中国农学目录》的考证,中国古代农书共有500多种,流传至今的有300多种,大致分为农业通论、农业气象和占候、耕作与农田水利、农具、大田作物、竹木和茶、虫害防治、园艺通论、蔬菜及野菜、果树、花卉、蚕桑、畜牧、水产等类别。
[1]张企曾.试论农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极其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J].河南农学院学报,1982(1):113-121.
[2]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1-3.
[3]张波,樊志民.论农史学科主体意识与体制化建设[J].农业考古,1990(2):144-152.
[4]张波.试论农史学科层次结构和理论方法体系[J].中国农史,1992(2):1-8.
[5]王思明.观念的更新与农史学科的发展[J].农业考古,1995(1):97-94.
[6]王思明.农史研究:回顾与展望[J].中国农史,2002(4):3-11.
[7]李根蟠,王小嘉.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古今农业,2003(3):70-85.
[8]张波.我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中国农史,1986(1):20-26.
[9]游修龄.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EB/OL].http://www.sohu.com/a/116701291_500712.
[10]李文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战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