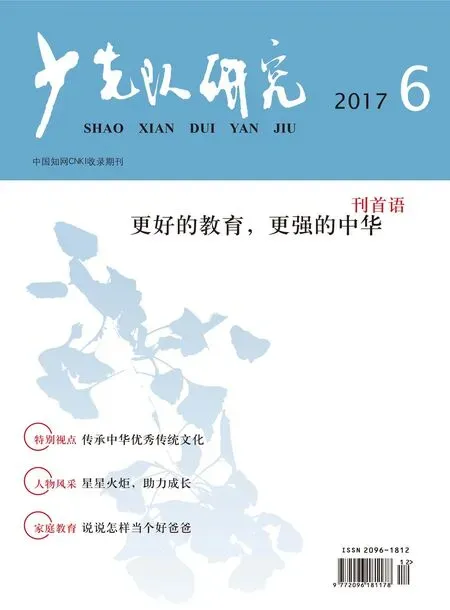儿童校外教育的空间意蕴
□ 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 华怡佼
按照198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界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这一年龄段的儿童也是我国校外教育的目标群体。根据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0—18岁的儿童约占我国总人口的20%左右,几乎每5个人中就有1个儿童。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否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教育在其中承担的责任是不可忽视的,学校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场所,历来得到社会的重视与关注。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差异的是校外教育的弱势状态,在一段时间内,校外教育甚至只是学校教育的附庸,成为学科培训或补习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校外教育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加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丰富学生课外及校外活动。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各种课外及校外活动。加强中小学校外活动场所建设”。
一、空间的概念与论述
相较于学校教育的制度化空间,校外教育的空间更为广阔、形式也更为多样。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陆士桢将校外教育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从广义上说,一切不属于学校教育的社会性教育都可以称之为校外教育。而从狭义上讲,按约定俗成的社会共识,我们把课外服务于少年儿童教育的组织、团体、机构、阵地等统称为校外教育”。本文所讨论的校外教育主要是狭义上的校外教育,“是指专门的校外教育机构对学生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而既然是教育活动,则必然是占据空间的,在哪里开展校外教育活动、如何开展校外教育活动,在不同的空间中蕴含着无限的可能,而从空间的角度来观照校外教育,也更符合儿童的认知,儿童在不同空间中的实践与经验、彼此间的人际互动,是校外教育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
空间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关系重大,空间场所塑造和影响着儿童的行为、健康、社交,乃至幸福感等多个方面,然而在儿童教育的相关研究中,空间很少被提及,更多的时候只是被设定为一个背景或简单化的名词,是一种静止的存在。然而儿童丰富多样的空间经验必然是在与空间的互动中形成的,感官的直接体验是儿童积累知识经验的基础。校外教育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决定了它是建立在开放的活动空间之上的,因此空间的安全性、友善性和开放性等特质,都会影响到校外教育开展的情况与效果。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活动场所的建设得到了政策和财政支持,“至2007年,在中西部地区23个省(区)共建设了一千多个场所,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大中城市及部分县区的校外活动场所网络”。不仅如此,校外教育的空间也在逐渐向外延伸,自然空间、文化空间,乃至社区邻里,都成为了校外教育的有效活动空间。田晓伟将教育研究中的空间观念划分为“容纳与盛载的空间观念和生产与建构的空间观念”,本文拟借鉴其思路,从这两个层面来分析校外教育空间——盛载的空间与生产的空间。
二、校外教育中的空间分析
1.盛载的空间——校外教育的物质基础
空间是对具体地点的抽象表述,是盛载自然与社会事件的容器,人类活动必然是在空间中进行的。校外教育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和活动阵地,其开展必然是占据空间的,无论是少年宫、教育实践基地或是户外的活动场所,都是校外教育得以开展的物质空间基础。盛载的空间设定了校外教育活动的基调,是否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是否对儿童友好且有吸引力,以及是否贴合活动的主题与内容,这些因素不但会影响到校外教育活动开展的综合实效,也会影响到儿童对于活动的体验与感受,体现的是儿童与空间的互动性。校外教育的空间应该是立足于儿童的,因此了解儿童对于空间的需求和喜好,值得我们成人和儿童共同探讨与思考,才能使儿童真正地从中受益。
在笔者参与校外教育的近十年时间中,与校外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化形影相随的是活动空间的拓展与延伸,从四面围墙的传统教室延伸至各种文化和自然场所。如美术校外教育,绘画的空间从课堂拓展至美术馆、博物馆乃至街道社区,在开放的空间中,儿童对艺术氛围和气息的感受直接而丰富,这与在传统教室中开展绘画活动是截然不同的体验。儿童在自然空间里活动的时间较之父母有了很大的减少,这既与城市的高密度发展相关,也受儿童本身可支配时间的限制。然而,自然空间提供给儿童的不仅有生物多样性的感知,更有丰富的感官刺激,这对儿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校外教育利用自身多元空间的优势,让儿童在自然空间中亲身体验、自然而然地激发其环境意识与情感,相比在课堂中开展间接的生态教育,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2.生产的空间——让儿童在开放的环境中建构自己的世界
校外教育广阔的空间与视野使儿童可以在开放式的环境中建构自己的世界,尊重儿童权利从一句简单的文本真正落地实践,这与校外教育多年来积极的倡导与探索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儿童而言,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者,而个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交往是这生产空间的重要方面。在活动过程中,儿童会自然而然地与他人产生互动,无论是言语交谈或是行为互动,都使彼此间产生联系,从而使儿童能更为投入学习与讨论中。就教师而言,他们不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在与儿童的交流互动中,引导儿童自发地去学习与思考,而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校外教育育人的独特性,即以学习者为中心,尊重人的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融多种学习内容于活动之中,让儿童完整地了解社会,品味生活,理解人生;集多种学习方式于一体,让学生在参与和体验中成长”。
盛载的空间展现的是空间的物质性,以及空间与个体间的互相影响与作用,而生产的空间描述的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彼此间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盛载空间的广度与深度决定了生产空间社会关系交杂与弥散的程度,空间在校外教育中已不再是静止的背景或简单的名词,而是“空间成为观察的角度、理解的向度和表述的维度”。空间在儿童的视角中从来不是简单的距离度量,儿童在体验中可以赋予空间无尽的想象与内涵,而儿童间支持性的互动与协同性的合作关系也为空间提供了更多生产与建构的意义。
三、探索校外教育空间的发展
1.依托社区资源,拓展校外教育空间
社区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空间,也是校外教育的重要空间,将校外教育的空间延伸到社区,对于促进儿童成长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一些国外的校外教育研究中,社区一直是儿童重要的校外教育空间。在日本,“作为少年儿童日常的生活空间, 社区与校外教育活动范围有着直接联系。对于少年儿童来说,最为熟悉的莫过于他们生活、活动的区域。 社区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环境, 蕴涵着丰富的教育资源”。社区是儿童开始与家庭之外的世界相遇的空间,社区的街道、图书馆、文化场所等都是校外教育盛载的空间,而社区区别于其他空间的重要特质是它能给予儿童温馨的归属感,虽然这种归属感在高密度的住宅群中有所减弱,但社区仍然使儿童感受到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盛载空间中,个体与空间之间的互动是有纽带基础与情感归属的,儿童也在与社区的互动中,进一步提升了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2.立足儿童视角,更新校外教育空间
社区空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适宜的场景、与社区儿童千丝万缕的纽带关系,更在于社区的生产空间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社区间的和睦感既来自于社区成员对于空间的熟悉,也来源于社区内的个体交往与相互支持,在社区内,成员间的关系平等友善,是儿童权利在校外教育中贯彻的重要催化剂。校外教育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儿童的权利,因此从儿童视角来审视社区空间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在国外的一些项目中,已经开始让儿童参与社区空间的探讨,新西兰但尼丁学校的儿童对于何为一个良好的社区就提出“一个良好的社区是你能感到安全并认识许多人、有很多空间的地方”。在这样的生产空间中,儿童对社区敏锐的洞察力、彼此间友爱信任的关系,使校外教育在社区中的开展更具有互动性与生命力。
3.把握发展大局,优化校外教育空间
校外教育区别于学校教育的独特性在于其广阔的活动空间、广泛的参与性与平等的互动关系,而这也是校外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儿童的教育和活动空间本身是不应有界限的,因为儿童对世界的探索是不存在边界的,从教室课堂到更为开放的文化空间、自然空间,乃至社区空间,点线面的物质空间承载的是儿童作为行动主体的体验与认知。校外教育的盛载空间为生产空间提供了物质性的基础,使儿童在空间中可以有更多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而生产空间对盛载空间的反哺体现在儿童通过自主的表达与实践,使从儿童视角来审视校外教育的空间成为可能,儿童是有能力的行为主体,在我们为儿童创设良好的校外教育空间时,应该多聆听儿童的声音与意见,立足儿童的视角来审视校外教育空间是否符合儿童的需求,是否儿童想要的良好空间。儿童在一些项目中参与校外教育空间的探讨已经开始实践,如“英国《卫报》出版了一份‘博物馆儿童宣言’,列举了20条建议,使博物馆变得更加儿童友好。建议包括‘咨询儿童’和‘不要假想儿童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等”。儿童在适宜性与支持性的校外教育空间中开展活动与学习,更有助于激发他们的主体意识,适宜性与支持性的衡量标尺并非来源于成人的观点,更多应立足于儿童的视角,去理解儿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而儿童也将在参与中获益良多,公民品质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都会将儿童引向更积极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