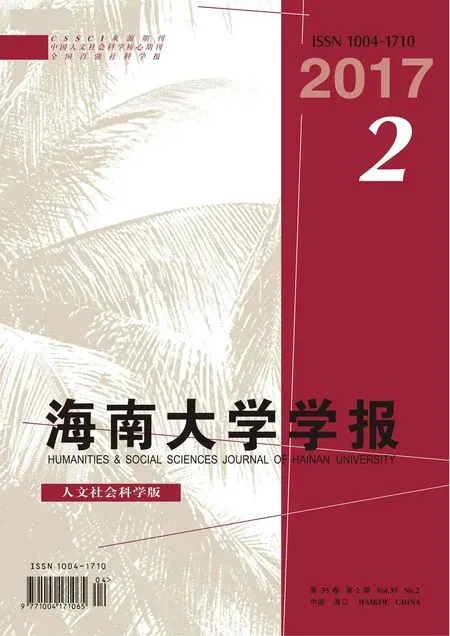德性伦理与智慧实践
——兼论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及其当代启示
陈鹤玲
(1.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2.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德性伦理与智慧实践
——兼论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及其当代启示
陈鹤玲1.2
(1.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2.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亚里士多德在对人性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爱智慧”的哲学真谛,探究了作为“政治动物”的“理性个体”何以成为城邦之德性个体的伦理问题。在亚氏看来,践履德性,施展实践智慧,唯有奉行“中道”,遏制人性本来的“不自制”。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以个体德性延展至城邦德性,既是研究“个体至善”的伦理学,又是研究“国家至善”的政治学,对构建当代公民社会具有重要价值指引。一方面,建构德性公民社会,需要培育有德性人格的社会公民,避免遮蔽灵魂、钳制人性的纯道德说教;另一方面,建构德性公民社会,需要构建一套由行政机制与立法机制共同组成的良好的国家运行机制。唯此,方能培育德性个体,构建德性社会。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智慧实践;道德哲学
在古希腊,哲学是一门“爱智慧”之学。如何“爱智慧”?在著述《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作为一种群居性社会个体,每个人都有求知的欲望。求知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获得智慧与幸福的手段。在《尼各马科伦理学》(Ethika Nikomachea)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求知与智慧的关系,他认为:智慧是无限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以人的理性之有限去洞察智慧之无限,是一种幸福的求知过程,其间,思辨构成了求知活动之核心内容。思辨既是爱智慧活动之本身,也是爱智者通达智慧之方式,它彰显了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理想人格与通达路径。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爱智慧”之学,即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它展开了古希腊的人性之辩,彰显了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的德性光芒。践行德性伦理,培育德性人格,不仅为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古希腊城邦之所需,更是当代公民社会之所必需。
一、人性与德性: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理论逻辑
(一)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通往德性的理论预设
“人性”即人之品性,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类的“本质差别属性”。“人性”分四维等级:区别于“非存在性宇宙”(即“彼岸世界”)乃人之“存在性”;区别于“一般无生命物质”乃人之“生命性”;区别于“低级‘活动性’动物”乃人之“社会性”; 区别于“其他‘思维性动物’”乃人之“精神性”。此人性之四维决定了人的“生命本能”“自我认同本能”“社会认同本能”及“解脱本能”,进而造就人性的健康、幸福、成功与智慧[1]。可见,“人性”关乎人的本质,是伦理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的理论基点。为建构自成一体的道德哲学理论体系,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研究预设了三个前提假设。
其一,研究人性首先要研究如何“爱智慧”(philosophy)。在古希腊,哲学乃“爱智慧”之学。据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著述《论自然》记载,在与弗里阿西亚或西库翁的僭主勒翁言说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首次运用“爱智慧”一词,以指代“生来寻求真理”之智者。毕达哥拉斯进一步提出,要把“爱智者”(philosophos)列入“自由人”之列,并将之与追求真理联系起来,以区别于那些“奴性的、生来追逐名利的猎手”。所以,在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那里,研究如何“爱智慧”就成了哲学研究的基本传统。而后,亚里士多德发扬并强化了这一哲学传统。在著述《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 作为一种群居性社会个体,每个人都有求知的欲望。求知本身不是目的,它是获得智慧与幸福的手段。德国符号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其著述《人论》中指出: 亚里士多德关于“爱智慧”命题的阐释昭示,“爱智慧”是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活动方式,它已构成人之本性的一种基本倾向;求知作为获取智慧的基本路径,它已嵌入到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思维方式、日常行为与社会实践中。人的认知包含感觉和记忆两个层次。感觉为一切生物所共有,它是生物的本体性存在;记忆为部分活动体所拥有,记忆生成经验,进而生成科学与技术。所以,“感觉—记忆—经验—技术”是人类认知的层级序列,反映了人类智慧不断提升的过程。区别于其他生物,人类的根本特性在于爱智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就是爱智慧,研究人性首先就要探究如何爱智慧[2]。
其二,研究人性要研究何以为“理性个体”(Rational)。理性(reason)源于古希腊语逻各斯(logos)一词,与“爱智慧”一道,理性概念同样出自赫拉克利特。在赫拉克利特看来,逻各斯乃天地万物运转之规律,它内置一种具有隐秘特质的智慧或理性,主宰着社会个体的思维认知与社会实践。据古希腊斯多葛(The Stoics)哲学学派,逻各斯即理性和本质,“理性是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3]。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O.N.Angola)曾言:物之“始基”在于“种子”,而认识“物”之“始基”在于理性,唯有理性才是揭示“物”的可靠工具[4]。亚里士多德在逻各斯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德性源于理性功能的卓越展示”[5]之著名论点。求知是“爱智慧”的理性活动,亚里士多德将富有求知意识的智者界定为“理性个体”(Rational),并将之作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进而将人的理性分成“手与智慧”和“语言与智慧”两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手与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手”是“爱智慧”之工具,并受“智慧”(即理性)规约,这就否定了阿那克萨戈拉(O.N.Angola)“因为有手,人类才有智慧”之观点。对于语言与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为各种动物所共有,“善辨是非”却为人类语言所独有。有了“手”,理性才能行使对人类实践的规约;有了“语言”,人类才有独特的智慧生成路径,理性才得以提升。所以,在亚氏那里,研究人性要探究个体“理性”,然而,亚里士多德研究理性,最终是要研究德性,这是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理论前提。
其三,研究人性要研究何为“政治动物”(Political animal)。“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命题。“作为共同体成员,人在本性上不能脱离城邦,否则,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就像荷马所指责的那种已成无族、无法、无家之人一样,宛如棋盘中的一粒孤子。”[6]7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已上升为政治学,亚里士多德也因此成了“政治学奠基者”。作为政治动物,人类不会像“蜜蜂等群居动物”一样,做一些“徒劳无益之事”。所以,人天生就是一种共同体,要过城邦生活,以追求幸福至善的生活。为追求“至善”,亚里士多德创造性地将德性、公民与政治融为一体。在《尼各马科伦理学》著述中,亚氏将德性分为伦理德性与智慧德性。伦理德性与人们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相关,是风俗习惯的人文表征;智慧德性通过人的社会实践生成并得以强化,一个乐于善待自身健康并善于利他之人拥有更大的智慧德性。如伯里克利(Pericles),不仅善于谋划自身,也为共同体之善做出谋局,充分展示了作为政治人的智慧德性[7]132。除公民外,政治家构成了城邦生活的另一主角。在著述《政治学》(卷四)中,亚里士多德将城邦职能界定为议事、审判及行政。城邦中参与此三者事务之公民有“演说家”和“行政者”,此两者为城邦政治活动家。城邦政治活动家要对议事和审判做出理性且明智的判断,以充分彰显其伦理德性和智慧德性。立法家是除行政者外的又一城邦政治活动家。对于立法家与城邦政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突破了古希腊关于“立法是一种创制而非实践的技艺”之传统观点,否定了“神谶立法”之说。“立法活动是城邦政治最高的实践”[7]126,这种实践不仅需要伦理德性,更需要智慧德性。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公民之于城邦好比水手之于船舶”,要船舶良性运转,水手们必须兼备德性并各司其职。所以,在《政治学》后两卷,亚里士多德指出,要建构至善城邦,除备有自然环境等“天赋优势”外,更要兼备培育德性素养的城邦法律和教育[6]255-301。
(二)德性与践履德性规约
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阐释了“爱智慧”(philosophy)的哲学真谛,探究了作为“政治动物”的“理性个体”(Rational)何以成为城邦之善者的伦理问题。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逻辑看,这已关乎到亚氏德性论之范畴。
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个体德性包含理性能力、非理性调适能力以及诸冲突调和与化解能力等三种能力。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一种朴素的自然主义德性论,具有形而上学的理论特质。事实上,自公元前6世纪泰勒斯(Thales)发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时候,古希腊自然主义的哲学传统就已经形成。于是,在此自然主义语境中,“德性与功能在含义上就具有内在一致性”[8]。何谓德性?“德性就是既使其承担德性的那个事物状态好,又使其承担德性的那个事物活动得更好。”[7]50可见,在古希腊那里,德性指向事物状态和事物特性两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也指向个体的本原与灵魂两个维度,而且尤指后者。有学者甚至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特指“灵魂的德性”,即“灵魂的功能发挥”[9]。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德性包括合逻各斯(logos)部分、不合逻各斯(Non-logos)部分以及两者之间之状态(Between the Both)。由此,人的灵魂实现能力分别对应为理性能力、反理性能力以及反理性又合理性能力(如柏拉图式的行为“激情”)[10]。于是,社会个体若要具有“充分德性”,就要求具备理性能力、非理性调适能力以及诸冲突调和与化解能力。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个体德性包含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非肉体的优秀乃灵魂之美好,德性( morality) 要接受理性的规约,方能避免“虽然很杰出,却也很无耻”的阿伽门农(Agamemnon)式道德异化(《荷马史诗》)。为此,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划分为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伦理德性包括实践智慧、勇敢、节制等基本内容,形成于社会风俗之中,具有历史的普遍性与承继性。作为社会个体,应该承继并发扬社会传统习俗,将社会个体纳入历史的文化传统,这是践行伦理德性的基础性要求;同时,我们又要在批判中继承,摈弃不合时宜的社会习俗,反对固守圣经式的道德狂妄,这是践行伦理德性的本质性体现。理智德性是对事物本源的通晓,可通过教化形成,通过“努斯”(Nous)和习惯获得[7]176。在亚氏看来,理智德性包括对不变事物的考察态度和对可变事物的考察态度两个方面,前者促成科学理论的系统化,后者促成实践技术的规范化。科学理论具有客观真理性;实践技术具有现实选择性,实践选择的明智与否为其基本特质。所以,明智是理智德性的重要品质,即“怎么样才能把手头上的事做得更恰当”,使其合乎科学理论、合乎人伦规范。可见,实践智慧是最高的德性,通过实践智慧,科学理论才能转化为实践技术,德性才能转化为实践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践履德性,施展实践智慧,唯有奉行“中道”(Mean),遏制人性本来的“不自制”(Incontrol)。
二、“中道”与不自制: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述《尼各马科伦理学》中阐述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个灵魂性命题:“伦理德性就是中道(mean)”。然而,什么是中道?如何确定一个中道?这是个很难定量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中道就是“既非过分,亦非不足”,要确定一个具体情境的“中道”有赖于人的实践智慧。通过实践智慧,即可解决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开篇之“何以为善,何以至善”的德性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促进社会至善、人类幸福的必然路径,它所关心的是与人类社会有关的公正与善,包含着对伦理学的哲学反思,即“用理性来支持对中道的选择”。理性是一种有教养的知觉,它能够在特定情境中对“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做出判定,并赋予我们一双“富于经验的眼睛”,以使我们看得更准确、更深远。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与德性互融互通:没有德性就不可能有理智德性,实践智慧就不可能拥有;同样,没有实践智慧就不可能践履善行,幸福就无法达成。所以,拥有实践智慧的前提是拥有德性,因为德性是“与品性相关联的那部分”。在苏格拉底看来,德性与生俱来而天然不可教,它是神赋的正确意见。与苏格拉底相左,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是后天习得的:习惯于做有德性之事,并非习惯使然,而是享受德行之过程,并从中得到快感;一个人通过做公正之事而变得公正,通过不断践履德性而至真至善。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习得理论,已涉及社会道德心理学,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重要基础。德性有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之分,两者伦理指向不同:伦理德性是“想得好”,理智德性是“做得好”。理智德性如何“做好”,有赖于伦理德性的引导,有赖于对“中道”路径的选择和对不自制行为的抑制。
关于“中道”。作为一种理性精神,中道就是恰到好处而不走极端。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是一种美德,社会个体偏离中道,其行为将足以败坏道德。因此,“不及与过度均为过恶的表现,适度乃德性之本真”[11]40。然而,如何确定“中道”却受评判者主客观状态的影响,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不容易”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对象本身的客观特质决定了取其中道具有现实的难度:处两极之中,端点分辨不易,两端相距茫茫,取两端之中位不易得。其二,对象本体的主观特质决定了取其中道具有理性上的不可控:“天生易发生之事,时常与中道相反。尤其是赏乐,虽然它本身并不是恶事或善事,但它却常使人认为是好事,因为它能够带给人以快乐,然而,由于快乐它又可能引人误入歧途,而不能取其中道”。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行中道不能仅凭感情而须具备相当的理性精神,要“依从理性,置理性为准则而行事”[6]275。其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中道本身的理论特质决定了“中道”只能靠拢,不能绝对。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概念内置绝对中道与相对中道。所谓绝对中道,是指与事物两极距离相等的点位,从数量上讲就是数学概念中的平均数;所谓相对中道,就是“不太多,也不太少”的位置,即“因人而异的适度状态”。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大多数情境下,绝对中道只是理论上的存在,所以人们要“准确地命中中间是极其困难的”。于是,对中道的把握只能是对相对中道的选择。事实上,绝对中道具有价值上的指引性,人们在践履德性时,可以不断“思量”,虽然不能穷尽,但可选择与其靠拢。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在过度与不及两个极端中,做到“两恶之间取其轻”。比如在怯懦与鲁莽之间,必须先克服怯懦而非鲁莽,因为怯懦离勇敢这一中道更远。当然,选择中道旨在促成个体行为通达至善,所以,对某一具体情境,要据时据势做出行为判断与选择,既要有适度“狂”与“狷”的体胖心态,又要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宽恕主张。
关于个体的“不自制”。个体德性的发挥需要由实践智慧予以支持。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为实践智慧之一翼,“个体自制”为其另一翼,因为“不自制将可能使德性与善遭到破产”,“中道就是适度(temperance),心中有度且能适之”。与“适度”相对应的是无度(intemperance),即“过于沉湎于快感”[12]1146。事实上,适度与无度之外还存有自制(selfcontrol)这一中间状态。自制者倡导适度,但有过度之欲望,他要有强大的心理以克制这种“过度之欲望”,使其行为有“度”;与自制者相反,不自制者(incontrol)非但具有“过度之欲望”,还不能克服,他是“心中有‘度’而不能自持”。所以,不自制者是弱者而并非恶者,因为他只是“不能自持”而非“自我放纵”。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自制者具有道德知识却存德性缺陷,即不具实践智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不自制者是“明知甜食有碍健康”却要“以吃甜食为乐”的人,它“说起话来像演员”[13]。不自制者虽然不是恶者,但为德性不健全者,在德性实践过程中,要规避“不自制”行为的生成,因为它与邪恶(evil)、兽性(beastliness)无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自制者按照欲望行动而不能“思量”(consider),完全忘却了德性品质。事实上,不自制是一种个体恶的品格,与个体理性相关,而无关欲望之客体。欲望之客体,比如甜食,就其自身而言,并无善恶之分。所以,将欲望客体看作是不自制的“罪魁祸首”是不恰当的。因为欲望客体能给人以“快感”,本身具有善的特质。欲望客体通过不自制者的行为将其“原本自在的善”衍生成了“自为的恶”,其根由在于不自制者的“欲望情感背叛了德性品质”,人们的贪求超出其生活所需的限度。所以,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违背“中道”之“过度”行为应该对“不自制”分担内源性责任[12]1146。所以,克服“不自制”,以通达智慧实践的彼岸,并非知识性问题而乃道德性范畴。
三、智慧实践与道德守望: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当代启示
从对人性的阐释到对德性的规约,从对“中道”与“不自制”概念的提出到对“实践智慧”的逻辑生成,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对其道德哲学的理论构建。何谓道德哲学?道德哲学亦即伦理学,是研究善与恶、对与错、职权与义务等关系的哲学分支。按照高国希的观点,从道德哲学层面看,道德有三个层次:首先,道德是一种智慧,需要习得方能成就个体素养;其次,道德是一种规范,需要遵守方能指引价值指向;最后,道德是一种信念,需要恪守方能体悟与持存[14]。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所指向的实践是一种道德实践,该实践以至善为导向,以幸福为目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既是研究“个体至善”的伦理学,又是研究“国家至善”的政治学。达成“个体至善”与“国家至善”的有机统一,需要社会个体具备实践智慧,践行个体德性,城邦社会需要具备善良法治,施展德性政治,培育德性公民。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对构建当代公民社会具有重要价值指引。
第一,培育有德性人格的社会公民。由上述,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是引导社会通达幸福彼岸的政治伦理学,培育德性个体为其伦理归旨。事实上,培育德性人格,不仅为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古希腊城邦之所需,更是当代公民社会所必需。根据李强的观点,德性教育至少应该涵摄个体人文精神、公民个性发展与道德人文主义三个方面的内容[15]。其一,培育德性人格必须培育个体人文精神。个体人文精神培育旨在确立一套做人的基本规范,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教育以及韦伯提出的唤醒人之“神性”的“卡理斯玛”教育就是以培育个体人文精神为宗旨的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个体人格。其二,培育德性人格必须促成公民个性发展。人文精神促成个体间的人格和谐,而个性发展则促成个体间的人格互动,以解决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问题,即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促成公民个性发展需要有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土壤。德国浪漫主义学派的洪堡教育以追求“美丽的灵魂”为导向,倡导个体发展,主张社会个体以自身方式完善自我,绽放着个性发展的德性光芒。洪堡将教育划分为bildung教育和schooling教育。Bildung教育将对人的素质培养界定为知识规范的获得、知识运用道德理念的培养以及关于社会知识的养成等方面。其三,培育德性人格必须促成道德人文主义的复兴。“个性”的发展只是“少数人”所为,要支撑起整个社会的德性天空,有赖于“城邦公共德性品质”,这就要求提倡道德人文主义,从社会环境出发加强对制度的改造,为培育德性公民提供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使社会道德教育成为一种合德性的灵魂教育,避免遮蔽灵魂、钳制人性的空洞乏力的纯道德说教。
第二,构建由行政机制与立法机制共同组成的国家运行机制。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城邦是社会个体天然的活动场域,“人天生不能脱离城邦,否则他将为一超人或为一鄙夫;为一神灵或为一禽兽”[6]10。作为社会共同体,城邦由个体、家庭、村社组成,离开了城邦之善,个体之善将无法达成。可见,政治性构成了城邦的根本属性。因为“一旦脱离了城邦良治,个体就会堕落成最邪恶、最残暴的动物”。为此,建构城邦良治,确保城邦社会为政公正,就成了城邦政治共同体的“一致意见”。首先,建构良治行政机制,保障城邦规则运行有序。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德性伦理是一种理想的“好人”状态,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完全至达,因为“自制”是相对的,“明知吸烟有害但仍坚持吸烟者”比比皆是。所以,个体灵魂时常是受遮蔽的,要去避这种“不自制”,需要通过个体间的德性交往来达成。要促成个体德性在共同体交往中互补互通,就必须具备良治行政机制,以制定公正的城邦规则,并促其运行有序。其次,建构公正立法机制,为城邦行政机制的良性运转提供校正。将立法纳入城邦的政治生活,是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重要特色。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立法是一种“神谶”的创制活动,与城邦公民无关,亚里士多德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城邦立法是一种属于智者的智慧实践,这一实践 “对城邦明智起主宰作用”[11]126,因为恰当的立法不仅能够规范共同体之个体行为,更能校正城邦行政机制的运转路径,使之不至于偏离德性轨道。“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正是这样一种中道的权衡。”[16]可见,建构公民社会,不仅要建构运行有效的国家行政机制,也要建构指向公正的国家立法机制。有了德性公民,有了良治政府,有了公正立法,德性社会共同体方能活力常在、容颜长青。
[1] 孙穆.启蒙文[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3:5-25.
[2] 易险峰.人性·德性·品性—兼评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J].求索,2012(5):168-169.
[3] 黄健,王东莉. 科学理性的人文反思[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27-30.
[4] 费洪喜,刘冠军. 理性:人的本质研究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J]. 齐鲁学刊,1998(1): 24-28.
[5]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形而上学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6.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 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2.
[9] 方德志.德性复兴与道德教育——兼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对德性伦理复兴的启示要求[J]. 伦理学研究,2010(3): 68-73.
[10]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6-169.
[11]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M].苗力田,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2]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M].Trans.by W. D. Ros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13] David Charles.Aristotle 's Philosophy of action[M].London:Duckworth, 1984:167.
[14] 高国希. 道德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26.
[15] 李强.大学通识教育:德性教育是教育的目标[N]. 南方都市报,2013-05-12(28).
[责任编辑:孙绍先]
Virtue Ethics and Wisdom Practice:Along with Aristotle’s Moral Philosophy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CHEN He-ling1, 2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Marxism School,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Aristotle demonstrates the philosophical essence of “loving wisdom” and explores the ethical issue that the rational individual as a political animal becomes the virtue individual of the polis. In Aristotle’s opinion, the practice of virtue and wisdom can only adhere to the “mean” to suppress the “intemperance” of human nature. Aristotle’s moral philosophy extends the virtue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city, which is not only the ethics on the “excellence of individual”, but also the politics on the “perfection of state”. It is of significant guidance of value to construct the contemporary civil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constructing the civil society with virtue involves cultivating the social citizens with the moral character while avoiding the purely moral preaching that hides the soul and restricts the human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involves building a set of good national operating mechanism that is composed of both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and legislative mechanism.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individual of morality be cultivated and the virtue society be constructed.
virtue ethics; wisdom practice; Aristotle's moral philosophy
2016-12-01
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青年项目(13CZZ019)
陈鹤玲(1976-),女,江苏盐城人,南京大学哲学系2009级博士研究生,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B502
A
1004-1710(2017)02-01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