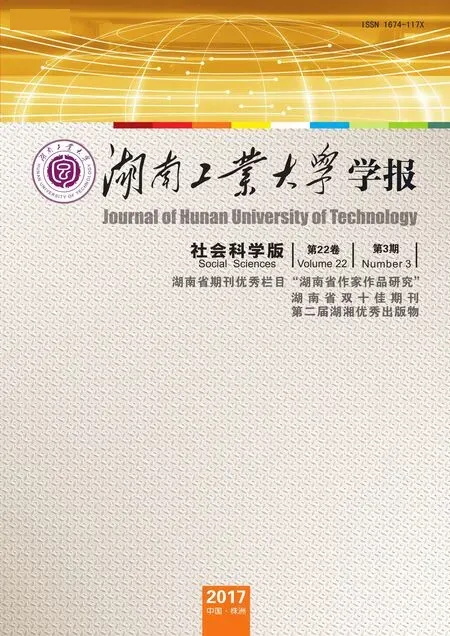《易经》欧洲早期传播史述
李伟荣,宗亚丽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易经》欧洲早期传播史述
李伟荣,宗亚丽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易经》早期译介者既有传教士如利玛窦、金尼阁和白晋等,也有非传教士人物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认为《易经》的六十四卦图类似于他所发现的算术二进制,尽管二者其实并不是一回事,但在传播目的和策略上却跟其他传教士一脉相承。《易经》在西方的早期传播,客观上影响和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开始在欧洲生根发芽。
《易经》;传教士;“适应政策”;“索隐派”
从16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传教士先后对《易经》展开研究。[1]19《易经》作为中国儒经之首便随着传教士的汉学西传而得以在西方世界传播。本文拟从历时角度来考察中西初识阶段《易经》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
一 揭橥西方易学传播的开端
海外的易学研究始于利玛窦(Matheo Ricci,1552—1610年)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年)。利玛窦在1594年刻印《四书》的拉丁文译本,该译本除中文原文、拉丁文译文外,还有必要注释。这部译作被寄回意大利,作为传教士日后到中国传教的参考。[1]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会士在中西交通史的影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学东渐”,将西方的科学著作传入中国,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二是“中学西传”,即将中国典籍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传入西方。
学术界一般认为,正是因为利玛窦用儒学来附会天主教义,所以孔子思想在16世纪末始得传入意大利。利玛窦是历史上有记载的西方最早读《易经》的人之一,也可能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接触《易经》的人。[2]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引用《周易·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3]以证明天主教的“天主”就是中国儒教崇拜的“上帝”。
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教,利玛窦采用了后来具有重要影响的适应政策;他还试图用中国典籍证明基督教的教义,从而调和中国典籍与基督教教义的矛盾。这种种做法对耶稣会会士在东方传教的垂范作用,无疑直接开启了传教士易学研究的先河。[4]他对中国经籍的这种方法和态度,首先就影响到了他的学生金尼阁。
金尼阁于1610年和1620年两次来华传教。在传教之余,悉心研究中国经籍,并将部分经籍译成拉丁文。在利玛窦所译《四书》的基础上,金尼阁翻译了“五经”,于1626年在杭州出版了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iblionSinense)。此书包含《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与《春秋经》,除拉丁文译文外,还附有注解。这部译作对后来耶稣会会士翻译《易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的传教士尤其是“索隐派”因为要在《易经》中寻找“上帝”的痕迹,不断研究和翻译《易经》。从这一意义而言,金尼阁可以说是揭橥了西方易学传播和研究的开端。[5]
利玛窦之后,声名卓著的汉学家以曾德昭(Alvarus de Semedo,1585—1658年)、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和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年)为主。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提出,《易经》(Yechim)是一部政治哲学或是治国方略之书。[6]卫匡国在其著作《中国上古史》中,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最早经书《易经》,其中包括阴阳的定义、太极八卦的演化过程;把“易”之义翻译成等同于“Philosophy”之义的拉丁文“Philosophantur”,并把《易经》与西方哲学相比,将伏羲比拟成毕达哥拉斯。[7]研究者认为,卫匡国在易学西传中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他第一次向西方指出伏羲是《易经》最早的作者;二是他初步介绍了《易经》的基本内容,并且第一次向欧洲公布了64卦图,从而使西方人对《易经》有了直观理解,这幅图比柏应理等人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所发表的64卦图早27年。[8]安文思也在著作中介绍过《易经》,中国人把它视为世上最深刻、最博学和神秘的书。[9]
欧洲的早期汉学研究大多出自耶稣会会士之手,他们的研究肇始于《尚书》和《易经》的翻译,他们将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译介传播到西方,中国文化和西方真正发生文化交流关系正始于此时。[10]34耶稣会会士的本意是通过引用中国典籍来附会其教义;同时,这又能证明在中国传教的可能性,从而获得教会上层人士的支持。我们要清楚的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在欧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耶稣会会士在中国之所以要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典籍对其传教的适应政策而言非常关键。以此为基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会士,创立了欧洲传统汉学的模式,即掌握多种语言文字,钻研中国文献经籍,进行文化比较研究,力图恢复历史原貌,以便于他们向中国人传教。[10]34耶稣会教士以《易经》和《论语》等儒家典籍为中心,展开了用欧洲语言(确切地说是拉丁文)翻译中国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工作。[11]25
二 “索隐派”与《易经》在法国的早期传播
“索隐派”或“索隐主义”(Figurism)指的是一种注疏(exegesis)方法,由白晋首创,受康熙帝的鼓励和资助。“索隐派”的方法是经由考据、索隐的方式企图从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在《易经》中寻找《圣经》的神谕、预言、教义以证明《易经》和基督教教义一致,其目的就是通过注释中国经典(主要是儒家和道家经典)而进入中国传教,主要代表人物有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年)和马若瑟(Joseph Prémare,1666—1736年)和傅圣泽(Jean Fran Qois Foucquet, 1665—1741年)等。[12]法国从17世纪起,就在汉学西传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巴黎从17世纪~20世纪初,一直是欧洲汉学的学术研究中心。1687年,《易经》的第一本西方译本(附刻在柏应理所编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正式在巴黎刊出。[13]1688年出版法文节译本《孔子的道德》,1689年又出版另一版法文节译本《孔子与中国道德》。其中,《孔子的道德》于1691年在英国出版英文节译本。目前在欧洲很多图书馆存有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可见这本书对孔子、孔子学说及《易经》在欧洲的传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不过,为了能在中国传教,并为“礼仪之争”进行辩护,柏应理把中国描写成完美无缺的文明先进的理想国家,值得模仿。正是因为这本书,欧洲人开始注意中国,从而在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柏应理在巴黎出版的《易经》拉丁文译本,与金尼阁在杭州印行的拉丁译本相去40年,这是第一本在西方世界出版的《易经》外语译本,因此柏应理也成为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14]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年)为比利时耶稣会会士,字信未,受到刚从中国传教回来的卫匡国之影响,也要求前往中国传教。与柏应理一起,殷铎泽、鲁日满和恩理格等,将《大学》《中庸》《论语》(缺《孟子》)译成拉丁文,书名为《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该书包括柏应理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献辞;导言;《孔子传》;《大学》《中庸》与《论语》译文等。书中“导言”部分有柏应理用拉丁文翻译的《易经》64卦和卦义,不过柏应理的译文用字冗长,例如,《易经·谦卦》的第二爻中的“六二,鸣谦贞吉”[14]6个字,译者却用多个省略号表示。
白晋是西方研究易学著作的先驱之一,在《易经》的西传史上,扮演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角色,在易学的西方传播中居功厥伟。柯兰霓和张西平都指出,对《易经》研究最深入的是白晋和他的“索隐派”。[7]康熙皇帝曾下旨让白晋研究《易经》,并将傅圣泽从江西调来与白晋一起研究《易经》。[15]白晋认为《易经》由伏羲所撰,是世界上最老的书籍。[16]白晋也因奉行“索隐主义”而名闻宗教界。不幸的是,“礼仪之争”时期“索隐主义”被禁止,其结果就是“索隐主义”的方法逐渐遭到废弃。
白晋1697年写于巴黎的一封信,第一次显示他对《易经》有浓厚兴趣。他在信中表示,尽管大部分耶稣会会士认为《易经》这本书充斥着迷信的东西,但他相信《易经》中存在中国哲学的合法原则——这些原则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7]据裴化行(Henri Bernard, 1897-1979年)的记述,回法国期间白晋曾于1697年在巴黎作了一次有关《易经》的专题演讲,白晋在演讲中说:
……虽然(我)这个主张不能被认为是我们耶稣会传教士的观点,这是因为大部分耶稣会会士至今认为《易经》这本书充斥着迷信的东西,其学说没有丝毫牢靠的基础……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再说,除了中国了解我们的宗教同他们那古代合理的哲学独创多么一致外(因为我承认其现代哲学不是完美的),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方法更能促使中国人的思想及心灵去理解我们神圣的宗教。所以我要着手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17]
创伤外用药有霜剂、粉剂、水剂几酊剂等几种类型,从功效上来划分主要有生长类及抗感染类,理想的创伤药物主要起到以下几种功效:不易被机体吸收,能够被迅速排出体外;明显的广谱抗菌作用;体液不会影响其疗效;药效能穿透焦痂进入痂下组织[2-3]。经过多项临床研究发现,烧伤外用药物中能起到以上所有特点的较少。
白晋既推崇《易经》,又认为《易经》义理与天主教教义一致,可以凭借这一著作打开中国人的思想并让他们理解天主教教义。在《康熙皇帝》一书中,白晋也说:“虽说康熙皇帝是个政治家,但他如果对天主教和儒教的一致性稍有怀疑,就决不会许可天主教的存在。”[18]换言之,只要能证明中国古经与天主教义的内容一致,就可以让康熙信仰天主教;康熙若能信仰天主教,那全中国都可以纳入天主教的版图。
在这种信念的推动下,白晋穷其一生都致力于在上古时代的中国典籍中寻找《圣经》教义。同时,作为一位数学家,白晋对易卦也颇感兴趣。[7]236白晋知道康熙皇帝喜好科学,便投其所好,用数学方法解释《易经》,再从《易经》中寻找天主。白晋企图通过揭示“数学中的神秘”,以证明中国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圣典——《易经》,其实与希腊、埃及犹太哲学中的神秘数学相呼应。白晋认为“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并认为“世上没有比研究那包含真理而又如此难解的《易经》更能显示中国人的心神是如何契合于基督教义了”。白晋这种传教方式显然是利玛窦“适应政策”的一种运用,带着无限浓烈热忱的宗教情怀作后盾。
白晋等之所以从中国经籍入手在中国传教,而且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士大夫对学经与传教之间关系的研究无疑直接启发了白晋等“索隐派”耶稣会会士。例如,夏大常就认为传教士应该熟读中国典籍,这样才能理解中国人的本性,才有可能成功地在中国传教。他指出:
若要免人妄证,须先明透中国本性之情;若要明透中国本性之情,须先博览中国之书籍。中国之书籍,即为中国之本性也,未有不读中国之书籍,而能识中国之本性者,亦未有不能识透中国之本性,而能阐扬超性之理于中国者。[19]
同时,他强调说,必须利用中国典籍才能更好地在中国士大夫中间传教。他说:
若对中国读书之人讲道解经,开口便要博引中国古书为证。若是能引中国书籍,出自何经,载在何典,他便低首下心,无不心悦诚服,若不详引中国书籍,辨析他心,纵有千言万语,他心不服,纵谈超性妙理,他心亦不能知,他或纵然当面奉承,背地尚加毁谤矣!必须多读中国书籍,方能开引人心矣![19]
傅圣泽和白晋一起抵达北京后,被分配至福建和江西传教。1711年(康熙五十年)被康熙召至北京,协助白晋进行《易经》的翻译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撰有《易经稿》。傅圣泽和白晋一样,相信在《易经》和《书经》等中国经典中,可以找到天主的启示。[14]
这些“索隐派”成员们为了从中国古籍中发掘天主教教义,努力钻研中国古籍和语言文字的作法,终于引来其他耶稣会教士的批评。这些耶稣会教士认为,“索隐派”所作的未免显得有些本末倒置,甚至太牵强附会。最后法国教会及罗马教廷对这些“索隐派”成员对中国经典的研究,尤其是鼓吹《易经》的做法感到反感,说他们是“着了《易经》的魔”,“索隐派”的《易经》研究于是被迫终止。虽然“索隐派”的《易经》研究画下了休止符,但是他们所撒播的种子,却使欧洲学人对《易经》的兴趣和喜好得以绵延不绝地发展。白晋及其“索隐派”对西方易学的传播和发展,亦可谓功不可没。
除白晋及“索隐派”外,尚有其他耶稣会教士对《易经》作了若干研究,如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年)、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年)、汤尚贤(Pierre de Tartre,1669—1724年)、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年)和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年)等。[20]
三 《易经》西传与莱布尼茨的“易学”数理研究
《易经》传入欧洲之初就在欧洲学界具有很高的声誉,关键在于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917年)所发明的二进制与《易经》之卦有着极为类似的关系,其中莱布尼茨又与白晋就《易经》多次通信,故而白晋与莱布尼茨在《易经》西传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与影响。关于白晋、莱布尼茨和《易经》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
莱布尼茨在1666年出版的著作《论组合术》(DeArteCombinatoria)中第一次提到了中国,当时他20岁。[21]109莱布尼茨很早就对中国的事物感兴趣,而且也熟悉中国的一些事物。自1687年开始,莱布尼茨积极地与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进行通信。最有名的要算他与当时在北京传教的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1638—1712年)和白晋间的通信。这些通信大部分被收录于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国近事》(NovissimaSinica)里。关于《易经》,莱布尼茨认为《易经》的卦图是古代的二进算术(binary arithmetic)。他曾与多位数学家和智者(intellectual)通信讨论相关问题,其中包括卡兹(Cesar Caze,1641—1720年)和坦泽尔(Wilhelm E. Tentzel,1659—1707年)等。[22]
莱布尼茨、白晋和《易经》的关系,其焦点就是他所发现的二进制是否受到了《易经》的启发。帕金斯(Franklin Perkins)的研究显示,莱布尼茨觉得自己发现的二进制可能有利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便于1697年和1701年分别给闵明我和白晋去信说明这一发现;白晋恰好也在研究《易经》,看到莱布尼茨的来信,觉得莱布尼茨信中所描述的二进制与他看到的64卦图非常类似,所以就将自己的看法寄回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得到确认后,便于1703年将自己的论文《二进制算术的阐释》(Explication de l’Arithmetique Binaire)[23]投给巴黎学院(Paris Academy)。
有学者认为白晋对《易经》的研究直接影响了莱布尼兹,他们二人从1701年开始在书信中讨论了伏羲、八卦及二进制的问题,白晋曾寄给莱布尼兹两幅“易图”:一幅是Segregation-table,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另一幅是Square and Circular Arrangement,即《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这幅图可能是从卫匡国那里得到的,而卫匡国的易图则可能是朱熹《周易本义》所录邵雍之卦图。莱布尼茨与白晋和《易经》的关系,其焦点就是他所发现的二进制是否受到了《易经》的启发。一般认为,首先是白晋将64卦图寄给莱布尼茨,然后莱布尼茨受到64卦图的影响发现了二进制。
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是否受《易经》的影响,并在20世纪初引发了一场公开争论,其始作俑者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年),他认为莱布尼茨二进制与《易经》有关。[24]随后激起很多讨论,例如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便反对韦利的这种说法,[25]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也支持伯希和的意见,[26]艾田蒲(Rene Etiemble,1909年—)也持类似观点。[27]这是反对的一方,这一方对国内的研究有着持久影响;另一方则认为《易经》,尤其是“八卦图”和“六十四卦图”对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具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代表有拉赫(Donald F. Lach,1917—2000年)、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1943年—)等。[28-31]
国内研究基本上也分两派,一派认为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受到了《易经》中卦图的启发,以孙小礼等为代表;而另一派则持否定意见,以陈乐民、胡阳和李长铎等为代表。
孙小礼最初认为《易经》的卦图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数表是一致的。[32]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孙小礼对自己关于《易经》卦图与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的关系进行了修正。她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莱布尼茨在1703年研究《易经》卦图之前已经发明了二进制算术。[33]
陈乐民认为,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有其数学基础的。而且,莱布尼茨在得到“八卦图”之前就已发明二进制,所以不能说他是受《易经》的启发而创造“二进制”。[34]与陈乐民持类似看法的还有胡阳和李长铎,在他们的著作《莱布尼兹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中,他们还制作了一份“莱布尼茨与伏羲八卦图历史年表”用来说明此类问题。[35]
韩琦则认为,这是“西学中源”说的一个新佐证。他认为白晋研究《易经》和莱布尼兹研究二进制是同时进行的,有关莱布尼兹二进制受到白晋的影响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过,他又肯定是白晋的《易经》研究促使了莱布尼兹把二进制和卦爻结合起来,可以作为“西学中源”的一个新佐证。
最近,有学者撰文说:“就数制而言,若说先天易具有二进制的优先权,于理勉强可通。就算术而言,若说先天易就是二进制算术,否定莱布尼茨的创造之功,实在牵强。此外,莱布尼茨还有功于二进制的传播与应用。”[36]这段话肯定了莱布尼茨对二进制的创造之功。不过,该文又试图调和这样两种极端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易经》对莱布尼茨创立二进制算术根本没有影响;另一种则否定了莱布尼茨的创造性贡献,认为《易经》或先天易才具有“优先权”。其目的无非是想说明,《易经》对莱布尼茨创立二进制算术确实起到了重要的影响。[36]
综上所述,传教士翻译《易经》等中国典籍,是希望从中国典籍中找到能使中国人迅速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正如利玛窦从中国典籍尤其是《易经》等典籍中证明出“天主与上帝特异以名”而已,这便为利玛窦所代表耶稣会传教士的“适应政策”和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莱布尼茨研究《易经》则主要因为他既为中国文化所吸引,进而呼吁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呼吁欧洲必须向中国学习、提倡中西方的优势互补;[21]114又由于《易经》的64卦图类似于他所发现的算术二进制。对于《易经》等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与影响,许倬云的评论非常公允。他认为包括莱布尼茨、伏尔泰(Voltaire)等在内的一些学者,从来华耶稣会教士寄往欧洲的报告中择取资讯,建构了理想化的东方,这是为抒发自己的理想而做出的郢书燕说。[37]我们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必须依据历史逻辑,还原事实真相,客观地认识《易经》等中国传统文化传入西方而促成的影响,既不能夸大而自诩自己为文化强国,也不能妄自菲薄而低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平心而论,《易经》在西方的早期传播,客观上影响和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开始在欧洲生根发芽。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经典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外部路径研究,因为在传播中,我们往往过于关注内部路径研究(即翻译研究),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外部路径研究。[38]
[1] 赖贵三.十七至十九世纪法国易学发展史略:上[J].巴黎视野,2011(15): 19.
[2] 林金水.《易经》传入西方史略[J].文史,1988(29): 367.
[3] 利玛窦.天主实义[M]//朱维铮,译.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2.
[4]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2.
[5] DEHAISNES C. Vie du Père Nicolas Trigaul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M]. Paris: Leipzig,1864: 217.
[6] 曾德昭.大中国志[M].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8.
[7] VON C. The First Encounter of the West with theYijing: Introduction to and Edition of Letters and Latin Translations by French Jesuits from the 18th Century[J]. Monumenta Serica, 2007(55): 235-236.
[8] 张西平.《易经》在西方的早期传播[J].中国文化研究,1998(4): 124.[9] 安文思.中国新史[M].何高济,李 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57.
[10] 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
[11] JENSEN L M.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12] LUNDBAEK K. Joseph de Prémare[M].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13.
[13] KNECHTGES D R. The Perils and Pleasures of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J].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004(1):123-149.
[14] 赖贵三.十七至十九世纪法国易学发展史略:下[J].巴黎视野,2011(16):21-24.
[15] 韩 琦.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J].汉学研究,1998(1):185-201.
[16] MUNGELLO D E.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M].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1985: 315.
[17] BERNARD H. Sages se Chinoise et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Essai sur Leurs Relations Historigues[M]. Paris: En Vente A La Procure de la Mission de Sienshien,1935:29.
[18] BOUVER J.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resent'e au Roy[M]. Paris: Robert & Nicolas Pepie, 1698: 41.
[19] 黄一农.被忽略的声音:介绍中国天主教徒对“礼仪问题”态度的文献[J].清华学报,1995(2):148.
[20] 李伟荣.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3.
[21] PERKINS F. Leibniz and China: A Commerce of Ligh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 ZACHER H.Die Hauptschriften zur Dyadik von G. W. Leibniz[M]. Frankfurt am Main: V.Klostermann, 1973:22.
[23] LEIBNIZ G W V. Explication de l’Arithmetique Binaire, Avec des Remarques sur son Utilite, et surce qu’elle donne le sens des Annciennes Figures Chinoises de Fohy[J]. Memoires de l'Academic Royale des Science, 1703(3):85.
[24] WALEY A. Leibniz and Fu His[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21(1):165-167.
[25] PELLIOT P. A Review on Arthur Waley’s “Leibniz and Fu Hsi”[J]. T’oung Pao, 1922(21): 90-91.
[26] NEEDHAM J. Addendum o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Binary Arithmetic of Leibnitz. in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 432.
[27] ETIEMBLE R. L’Europe Chinoise[M]. Paris: Gallimard, 1988:370.
[28] LACH D F. Leibniz and China[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5(4):436-455.
[29] MUNGELLO D E. Leibniz’s Interpretation of Neo-Confucianism[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71(1):3-22.
[30] RYAN J A. Leibniz’Binary System and Shao Yong’sYijing[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96(1):59-90.
[31]SWETZ F J. Leibniz, theYijing, and the Religious Conversion of the Chinese[J]. Mathematics Magazine, 2003(4):276-291.
[32] 孙小礼.莱布尼茨与中西文化交流[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12):7.
[33] 孙小礼.关于莱布尼茨的一个误传与他对中国易图的解释和猜想[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2): 52-54.
[34] 陈乐民.莱布尼茨与中国:兼及“儒学”与欧洲启蒙时期[J].开放时代,2000(5):16.
[35] 胡 阳,李长铎.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5.
[36] 朱新春,朱光耀.《易经》的“影响”与莱布尼茨的“优先权”[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5):26.
[37] 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M].北京:中华书局,2010:1.
[38] 李伟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部路径研究:兼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J].中国文化研究,2015(3):31-32.
责任编辑:李 珂
A Brief 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Spread of the Yijing in Europe
LI Weirong, ZONG Ya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The early translators of theYijingwere both missionaries, such as Matteo Ricci, Nicolas Trigault and Joachim Bouvet, and the non-missionaries such as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Leibniz holds that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of theYijingwere similar to the arithmetic binary, although the two were not all the same. The point is that his strategy in doing so came down from the same tradition as the missionaries. Fairly speaking, the early spread of theYijingin the West has objectively influenced and changed the Western view of the East, and thereafter Confucianism, with theYijingas the representative, has begun to take root in Europe.
theYijing; missionary; accomodation; Figurism
2017-04-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12BWW011);中国翻译研究院重点课题“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2016B12)
李伟荣(1973-),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西方易学、国际汉学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宗亚丽(1990-),女,河南兰考人,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B221; H159
A
1674-117X(2017)03-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