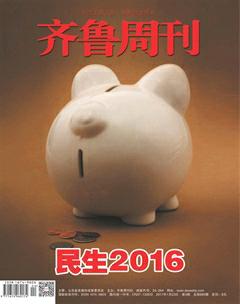无用之用和诗意栖居
吴永强
不谈狗血的出轨和离婚,不谈电影和小说对社会广度和深度的洞彻,不谈文人的价值和逝者的飘零,来,谈谈诗歌——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男欢女爱,没有七情六欲。过去的2016和已经开始的2017,可以如梅花落满南山,可以如一行白鹭上青天。
有人评价2015年是“微信诗歌元年”,以年初余秀华的爆红为标志。2016年,诗歌继续影响生活。以余秀华为例,这一年11月,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12月,又在国内获得纪录片学院奖最佳摄影奖。这部以余秀华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成为2016年度中国纪录片的代表作。
余秀华刚火的时候,人们将她和美国诗人迪金森并称,负面评价如火如荼。而今,以作品说话的她验证了一个诗人应该有的高度。
同样是诗歌,另一部纪录片《我的诗篇》,以六位打工诗人为拍摄者,记录了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叉车工乌鸟鸟、制衣厂女工邬霞、充鸭绒工吉克阿优、爆破工陈年喜、煤矿工老井、原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用诗歌抒发悲欣,吟詠爱情,呈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
当然,吴晓波担任总策划本身就具有超越诗歌的关注度。再加上罗振宇、梁文道、汪涵、吴小莉等的“加油打气”,这部纪录片成为过去一年的一个文化现象。
罗振宇说:“诗人如果无法从商业那里获得利益,那是诗人的无能……”这句话同样引发了争议,许多人撰文批判。诗人花脸说:“让商人谈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讽刺,理想和现实、完美和功利、出世和入世都会发生冲突。”
已逝诗人张枣说:“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作为人间最玄妙的“无用之用”,诗歌究竟带来了什么?其实,没有用处才是最大的用处,恰恰是这个越来越功利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闲适的土壤。
过去一年,我参加了大大小小很多诗歌活动,或为个人,或为工作。我问过很多诗人,为什么写诗。他们给出了很多答案,有的冠冕堂皇,有的戏谑笑之,我感到不满意,细想一下,确实都有道理。因为,写诗,根本就没什么原因。就像落满南山的梅花,和一生中后悔的事有什么關系呢?
诗歌继续拥抱时代,它不仅是微信公众号里的几个短句,不仅是睡前读的那一首诗,不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它还以细微的方式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有一天我躺在床上,两岁的儿子在客厅摆弄玩具,一个玩具里的童声传进我的耳朵:“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认识这首诗20多年了,唯有此时才被深深震颤,诗意栖居的静态中,千秋万里的江湖岁月倾泻而下,这是只有诗才有的情怀。
新年初,我收到远在昆明的花脸寄来的三副扑克,这不是简单的扑克,三副各不相同,分别是:2017诗年选、写给爱情的诗、写给孩子的诗,每一张扑克上印一首诗,每一副52首,相当于三本诗集。诗歌成为娱乐的载体,这是一种创意,谁说只有净手端坐才能读书?叼烟斜倚打扑克,同样是进入诗意的过程。
诗歌的边界不断扩展,其标志是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次活动上,我听到诗人孙磊说:“鲍勃·迪伦存在两个方向的给予。他给予了文学一个更大的场,他告诉我们文学不仅是语言的,即使不转化为语言,难道诗歌就不存在吗?”诗歌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别的许多形式,有什么关系呢,诗意本来就是随意的。
当然,呼声很高却没有获奖的阿多尼斯依旧堪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阿多尼斯多次来到中国,向我们展示一个叙利亚诗人对世界的看法——那个至今仍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度,苦难伴随,诗意也从未消失。
在济南,在北京,广袤大地上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城市,你都能遇到埋头上班低头写诗的人。如同你会遇到一个仰头看星空的人,一个低头乞讨的人,一个望着人潮发呆的人,一个躲在屋檐下落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