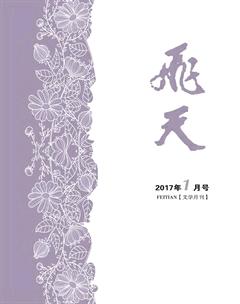散文二题
傅菲
粥
“今天不能喝水,不能吃任何东西。明天晚上可以喝点米汤。”医生一再嘱咐我。我噢噢地应和,点头。十二指肠出血,是该好好养养身子了。
第二天下午,我早早地用紫砂钵泡米,约一个小时,大火煮。小火文肉,大火煮粥。我捏一个瓷器大汤勺,一边煮一边搅,以免水花潽出来。米羹水白漾漾的,面上浮了一层泡泡,噗噗噗噗,浮上来又灭,灭了又浮。白汽在钵内沿卷来卷去,米翻上来沉下去,又翻上来。汤勺沿钵底转来转去搅动,米涌出水面,米边透明,米芯透白。羹水灰白,往中间翻卷,泡泡拥挤在钵中央,形成漩涡。潽起来的羹水成黏滴状。泡泡塌陷下去,消失,翻滚的水下沉,米完全胀开,米边耸起颗粒状的小圆角,像一朵冰晶花。边煮边添水,一勺勺地添。米香迫不及待地暴涨出来,连追喊打地扑人。米汤水稠黏黏的,我把盖子盖上。半个小时后打开钵盖,一锅白米粥熬好了。
粥熬好了,安安刚放学回家,嗷嗷待哺似的,说,我喝粥,吃咸鸭蛋!
食物可以排一个顺序的话,我会这样排:蜂蜜、粥、面疙瘩、面条、竹青白菜。其他无所谓。蜂蜜、粥、面疙瘩、面条,一年四季可以吃上,竹青白菜只有深冬可以吃,也只有上饶有(可能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从来没见过),圆竹的形状和颜色,甘甜、清爽,我不吃饭,吃一碗竹青白菜就满足了。蜂蜜在早起时,调两小勺,放进温开水里匀散,喝一大碗,一整天都是好心情。做面疙瘩,鸡蛋调进水里,把面粉完全调稠,黏糊状,撒半小勺盐花,再一勺一勺调进热汤里。汤料最好的是羊肉汤,可谁有那么奢侈,备着羊肉汤呢?还有一种汤料,并不逊色于羊肉汤,是螺旋藻。把茶油烧熟,加水,水沸,撮泡好的螺旋藻下锅,放二两活白虾一起煮,调面糊下去,熟了,撒一把葱花,盐、生抽和生菜叶最后下锅。白虾全身透红,起锅了。我一年到头都可以吃这样的主食。面条,我只吃清水面,一点油几粒盐即可,可以奢侈的话,再放几片生菜叶,若是当做盛宴来做,敲一个鸡蛋下去,和面条一起煮。
难得吃上的是一锅可口的白粥。高压锅或电饭煲煮出来的粥我不爱喝。米在高压锅或电饭煲里面,我们看不见,打开锅盖一看,米烂开,黏塌塌的,面上还起一层米羹泡——像一张美人脸,平白冒出疱疹。喝起来,阻滞的口感,唇感寡淡,到了胃部也是热感不足。我喜欢大锅粥和砂钵粥。小时候,家中吃口多,吃捞饭,饭坯捞上来,晾在竹箕里,剩下的米羹煮粥。劈柴巴掌宽、半米长,在灶膛噗噗噗的旺烧,滚动的火舌舔着锅底,米羹在锅里肆意翻滚,先是中间往四周翻,而后四周往锅中央聚——像丛林战,先扩散在四周埋伏,敌人来了,号角吹响,把敌人包扎在一个口袋里。锅沿有白白的一层白膜,这是米汤烫出来的黏膜,扯下来,长长一条,放进嘴巴,无踪无影地化了,微甜。这样煮出来的粥,是完全脱糖的,热量也久久不散,稠滑而不腻然,柔爽而不寡然。用大碗盛,托在掌心,沿碗边喝,不烫嘴,喝一碗,全身通畅。浮面的米汤,滚烫烫的,冲两个蛋羹,调小勺砂糖,是十分滋补的粥品,含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和低糖。浙江龙泉一带,中晚餐在饭前都要喝一碗米汤,以通肠胃。砂锅粥费时,谁还会把时间花在一碗粥上呢?用木炭煮砂锅粥,是上品。木炭烧透了,摆上砂锅,煮山泉水,沸了,添米,旺火熬。米羹渐渐稠时,放一个鸡蛋下去,一并煮。粥熟,蛋也熟了。蛋剥壳,烫手,滚圆滚圆,像一朵玉兰花。木炭的香味全进了粥和蛋里,有一股山野的气息。面对一砂钵粥,像似面对一座南方雨林。
用新出的晚粳米煮粥为上佳。粳米粒一般呈圆形或椭圆形,丰满肥厚,颜色蜡白,质地硬而又韧性,粘性油性较大,柔软可口,粥色奶白,营养丰富。
其实,吃一碗粥哪有这么讲究呢?用母亲的话说,叫穷讲究。以前上初中,住校,食堂早餐只提供粥。说是粥,倒不如说是米汤,端在手上,可以照见人影。一两粥正好是一蓝边碗。每次打早餐,同学叶云靠在饭窗,哀求大师傅:“多捞一些米上来,多捞一些米上来!”大师傅拿起饭勺,从底下捞上来,把不多的米粒倒进叶云的碗里。他食量大,上两节课,他便趴在桌上睡了,他实在饿不了。他吃得最多的一次,一餐喝了八蓝边碗。——他肚子胀得站不了,在操场的花坛上蹲了一个多小时。我二哥吃粥也是个很厉害的人。二哥和我说起早年去双河口砍柴的事。双河口离我家有二十多公里,是个大山区,他住在一个熟人家里。大清早空腹上山,砍两捆木柴下山,饿得腿都抬不动,他一餐喝一脸盆白粥。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一部饥饿史。也有连粥都没得喝的人家,早上,烧开一锅水,把田埂上挖来的野菜切碎,煮起来吃。常年吃,吃得全身浮肿。我还记得,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下午四点,生产队社员在李家大院里收听有线广播,哭声动天。有一个叫门槌的社员,广播还没结束,便趴在长凳上,喊:“粥,粥,我要喝粥!”门槌被生产队长叫人架出了院子。第二天,生产队开了批斗会,说他不爱领袖,拉到街上游街。门槌双手被一根绳子绑着,胸前挂一块纸牌,写着“畜生”,后背也挂一块纸牌,写着“打倒”。门槌从上街游到下街,打双赤脚,脸被人打得红肿。当晚,他便上吊死了。死后连个棺材也没人敢抬。门槌老婆求相邻的人,邻居连话也不敢和她多说。她又求生产队长。生产队长说,这是不爱领袖应有的下场,畜生死了还用棺材干什么?
也有不喝粥的人,嫌粥胀肚子,两泡尿撒撒,肚子又回了原形。光军的父亲每个早餐都吃油炒饭,把饭炒得硬硬的,沙子一样,吃起来硌牙。他吃上三大碗,边吃边喝开水。吃了油炒饭,他再重再累的活,也要干到脚踩到自己的头影子了才回家。做石匠的老春则吃面条。面是炒面,一个早餐吃一斤。村里有一个叫中顺的人,六十多岁,老篾匠,十几年前死了老婆,几个孩子常年在外打工。早上,骑一个电瓶车,沿街叫:“去镇里吃清汤呢,有去的,结个伴。”鎮离枫林有七里路,他天天去吃清汤。邻居正端着碗,窸窸窣窣吃粥。有邻居应答说,还是你中顺好,天天有清汤吃,柴火也不用点。中顺说,活到这个年纪了,清汤还舍不得吃一碗,那人还真没意思。中顺骑个电瓶车,嘟嘟嘟,去了。应答的邻居对着他的背影又说,连一碗粥都没人烧,还屌卵高兴得摇叮当。
我自小爱喝粥,尤其爱喝红薯粥、黄粟米粥。冬天,从地窖里拎出来的红薯,淀粉基本转化成了糖分,甜甜的、黏黏的。一碗红薯粥端在手上,薯香四溢。我三姑丈老说我:“你好养,一餐一个大红薯就解决问题,还吃得特别有味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了广东,才知道还有比红薯粥黄粟米粥更好喝的粥。广东喝一碗海鲜粥和喝一碗煲汤一样,都是日常中费劲心思的饮食大事。内地人大多不爱喝海鲜粥,嫌海鲜的腥味。我第一次喝便喜欢上了,那种鲜美和畅快,没办法不喜欢。
粥也称糜,是一种用稻米、小米或玉米等粮食煮成的稠糊的食物。李时珍《本草纲目》言:粥字像米在釜中相屬之形。《释名》云∶煮米为糜,使糜烂也。粥浊于糜,育育然也。浓曰粥,薄曰酏。粥有止消烦热的功效。所以,常见医生叮嘱患者:其他不要吃了,喝几天粥,把身体养好。粥养生。我有一个表哥,患结肠炎,肠道功能非常差,吃了两年多的药物都改善不了,一个老中医建议他喝粥。表哥喝了三年多的粥,彻底根治。这是表哥自己都没想到的。
不同的季节喝不同的粥品,不同的地域喝不同的粥品。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粥国,有菜粥,有海鲜粥,有白粥,有小米粥,有玉米粥,有肉粥,有八宝粥——不一而就。节令里,有寒食粥和腊八粥。饶北河流域,这两个节令都没有粥,但有年粥。除夕夜,年夜饭过后守岁。母亲便开始熬粥,熬满满一锅。到了子时,一家人便喝粥,喝了粥才上床睡觉。
今年五月中旬,纪录片编导刘海燕来横峰。海燕对我说,她已经三年没有吃米饭了。我说,那吃什么?她说吃杂粮粥。我知道吃杂粮对身体的好处。回到家,我买来黑豆、红豆、豇豆、花生、粟米、葡萄干、红枣、桂圆、银耳、绿豆,存放在一个大瓷缸里。我爱人说,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我说以后不吃饭了,吃杂粮。我爱人取笑我说,是不是发神经了?我常买来一些食材,自己琢磨半天,“发明研制”菜品或酱菜,却没有一次是成功的,最后都成为垃圾。我爱人也会这样想,这些杂粮也会不例外地进垃圾桶。
第一天的杂粮粥吃得很难受,口感和味道都不是我喜欢的,糙糙的,清汤寡水。连续喝了三天,慢慢适应了。上次回老家,我母亲说,你怎么瘦这么多,是不是身体有毛病了?我说,没有呀,我没觉得瘦。母亲说,还说没瘦,肚腩没了。我摸摸,真没了肚腩。前个星期去贵州,我到朋友的医院做了有关血液的所有检查,所有指标正常,体重减了八斤。五月中旬至今,我只吃了三碗米饭。吃杂粮粥这些时间,我明显感觉新陈代谢顺畅、精力充沛,对米饭没有想法。
粥只是用餐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小菜。饶北河流域,小菜有南瓜粿、豆豉、番薯豆豉、豆酱、剁椒、辣酱、花生米、霉豆腐、泡萝卜、泡椒、酸豆角、冬菜、泡刀豆、泡洋姜、腌蒜头、腌姜丝、腌萝卜丁、咸鸭蛋。当然,早餐也有炒菜,一般是炒豇豆、炒鱼干、炒豆干、炒榨菜、煎辣椒、炒梅干菜。这些菜品里,最难吃上的是上好的咸鸭蛋。鸭蛋须是河里放养的胡鸭或番鸭,腌藏的水是上年的雪水,用咸肉汁、八角、茴香、花椒、老姜做泡料,放在土缸里,泡上三个月。咸鸭蛋不要去煮,而是用干锅蒸,旺火蒸一刻钟即可,上锅后用冷水泡五分钟,切开吃,熟而不老。粥也配其它主食,如馒头、面包、花卷、小笼包。
每年,老家出晚梗米,我父亲会托人捎带一袋给我煮粥。我端着一碗热粥,似乎闻到了饶北河沿着灵山带来的植物气息、午后阵雨一阵一阵飘过山梁的清凉味道、疏朗田畴翻滚的稻香;似乎看到晨烟在村舍萦绕,白鹭在秧田里纷飞,阡陌上温暖地开着野花,乡邻在田垄里劳作。——这是一碗粥的精魄。
我们喝的每一碗粥,都有它来自母体的灵魂。周书云:黄帝始烹谷为粥。粥是一种与汉人相濡以沫的食物。它是我们食物中的配偶,也是食药合一的食物。
事实上,我们所需的生活十分简单,无需过于繁复冗杂,可以把生活的本源降低到一碗粥里,人间有味是清欢,而不是羊头狗肉。铅山县永平镇北彭溪桥边有“笪公祠”,祠内置石碑一座,名白菜碑,以奉祀事,以纪念万历年间江苏句容人笪继良任职铅山县令时造福百姓。碑铭“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假如,需我为这个时代立一个碑,我会在青石上雕刻一碗粥,碑铭“身在浮世,常尝粥味;人为赤子,当有粥品”。
门
一扇大门,究竟迎接了多少人?送走了多少人?我不知道。
一栋房子,无论它有多庞大,它只有一扇大门。大门是房子的脸部。饶北河边的房子,大多塀土房,坐南朝北,或坐西朝东,长四边形,中间大门进去,是厅堂,左右两边各有一间厢房,厅后叫后堂,左右两边叫偏房。这样的房子叫三家屋,四塀。也有六塀,或八塀,在厢房和偏房之间,修一条叫风弄的通道。也有大户人家的院屋,里外两栋,两边厢房相连,中间大天井,厅堂两个,前厅请客,后厅祭神。院屋和南方的祠堂差不多。一栋院屋,至少可以住四户人家,左右各开一条风弄。
大门都不能挑粪桶进出,人和六畜平等,污物避开大门而行。乡邻之间,无论有多大的仇恨,即使有杀父之仇,也不能把茅厕建在别人大门正前方——杀父之仇可以报,茅厕建在别人大门正前方,会引起全村人的公愤,也就失去立脚之地。大门是正前门,我们上门做客,即使身份再卑微、年龄多小,必须从大门进去,以表示体面光鲜。从侧门或后门进去,有些灰溜溜,做事谈话,不堂堂正正。不堂堂正正的人,受人鄙夷。门是一个家庭威严的地界。进门便是客,再好的邻居、再近的邻居、再仇怨的人,进了门都得摆椅子让座,若是吃饭时间,还要让桌,请邻居一起上桌。夏季昼长,下午会有一餐点心、烧面条、煮绿豆粥、蒸灯盏粿、搓饭麸粿,再苦的人家也有一碗葱花炒饭,进了门的人都要留一碗。
妇人吵架,都站在路边,或巷子,或洗衣埠头,拉起架势吵,吵个半天吵累了,坐一会儿继续吵,唾沫都吵没了,脸部抽筋,过个十天半个月,又和好了,有说有笑的。但不能在家里吵,没有谁坐在别人厅堂吵架的,会被人用棍子打出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实行计划生育,对违规生育又不缴纳罚款的人,政府派人把猪圈里肥猪拉出来杀,把谷仓里的谷畚出来卖,把屋顶捅烂,还炸房子,轰的一声,房子掀掉半边,但大门是要留着的。炸了大门会惹杀祸上身。
再穷的人家都有一扇厚实的大门。房子再烂,大门不能烂。大门的木板必是老木,杉木或苦槠,木头在家里陈放上十年,锯开,做门板。现在建房子,大门用料是镀铜的铝合金。铝合金门色彩鲜亮,易清洗,显得气派堂皇。十年八年后,铝合金氧化,烂得像一个患了白癜风的人。有钱的人买实木门,厚重。我建房子的时候,为做一扇什么样的大门,问了很多人,也征求我父亲的意见。父亲说,木门好,但不要实木门,实木门用不了几年会开裂。我表弟水根是个木匠,常年在顺德一带做实木家具,我问他,他说,自己买木头自己做,是最好的。实木门的门板是物理脱水,不是阴干的,时间长了会膨化,热胀冷缩很厉害,陈年老木不膨化,门板腐烂了也不開裂。可到哪里去买陈放了十几年的老木呢?一次,表哥兴泉来看我母亲。他开了锯板厂。我说我要陈年老木,做木门。表哥说,哪来这样的老木?不过还有比陈年老木更好的木料,用上一百年都不腐烂也不开裂。我说,这样的木料,谁买得起呀?不就是金丝楠木吗?或者红豆杉,是国家严控的。表哥笑了起来,说,地主也用不起呀,老房子拆下来的圆柱,锯开做门板,是好得不能再好了。过了一个多月,表哥来电话了,说,木料找到了,你来看看。两根圆柱,是老房子的中柱,四米来长,老杉木,木质还是浅黄色,手拍起来,嘣嘣嘣,像拍在绷紧的鼓面上。我说,要了,做三分厚的木门,上三道清漆,雨水不沾边。房子上大门那天,父亲用手一遍一遍地摸大门,还用力甩几下,说,这门好,厚重,拙朴,有村野大雅之气。我笑得像个裂开的核桃。
门,就是要把一个空间密闭起来,也是要把一个密闭空间打开。门是一个空间对另一个空间的防守与开放。门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栋房子有很多门,大门、后门、侧门、房间门、风弄门,还有院门。枫林没有院门,可能是山多地少,宅地不足吧。进山五里,我有一个舅公,即我母亲的舅舅,有院门。我还是十四五岁,进山。翻一座山,到山谷底,偷砍松树做柴火。我把松树扛到半山腰,被几个人追了上来。我扔下木头往山顶跑。饥饿,体力不支,我没跑多远,被几个六十来岁的人抓住了。一条猎狗,围着我汪汪汪狂叫,我吓得瘫软。我属狗,却十分怕狗。其中一个满脸胡茬的人问我,你是枫林人,还是洲村人?我说,枫林的。又问,你是谁家孩子?敢偷木头,这是犯法的!我说,傅家的。问我的人一下子语调温和起来,说,你是傅家第几个孩子?我说,第六个。“兰花的老六,都这么大了。”满脸胡茬的人说。我看看他,不知所措。我知道,我外婆出生在谷底叫坳头的小村子,但我从来没去过,我有三个外公,三外公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猎人,一把土铳震四方。满脸胡茬的人正是我三外公,怪不得他跑山路那么快,像头野猪。他看我饥饿得人都瘪了,带我去他家吃饭。这是我第一次去舅公家,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第一次看见了高大的院门。山边的房子临一条宽阔的山涧,涧水哗哗哗,冲击着巨大的涧石。土夯的院墙,有两米多高,瓦压在芦苇上,芦苇压紧墙垛。院门有三米多高,门轴是粗大的枫树兜切开的,门槛高过我膝盖,门板厚实,推开,门轴咿呀作响。院门上盖了一个蜂窝形状的大门垛,是厚木板上垒土砖的。开了院门,一个椭圆形的院子豁然开朗,柚子树、枣树、梨树、枇杷树,喷出了院墙。高大的院门,自有一种猎人的凛然之气,威武、强壮。再猛的野兽,也侵犯不了院中牲畜,伤害不了家人。
古代的财主或员外,有家丁护院。院侧有弄堂门,弄堂门之上有阁楼,阁楼有暗哨,能看见外边来人。晚上关了大门,客人从弄堂入院。护院睡阁楼,若是不义之徒入院,护院从阁楼跳下楼,以棍棒刀枪锤偷袭。大门也有讲究,两侧各有小门,门槛高且厚,普通客人从侧门入屋,贵胄之人才能跨大门。门口有两墩石狮子,憨态而威武。锁是大铜锁,锁侧有猫眼门孔,门外一览无余。也有门栓,是一根圆柱粗的原木,栓门,要两个人抬起来,穿进栓套。在枫林老式祠堂里,还可以看到。
车马盈门,是世俗中人所奢望的,多好,日日宾朋满座。
书香门第,多好的人家,诗书礼贤,是理想的家境。
名门世族,甲胄之后,三代出贵族,五代出世家,是个门阀。
相门出相,官是世袭的,种田人的子嗣想做官太难,读再多的书,不倚门傍户,难出头。
饶北河两岸贫瘠,有望族无世家。大多是撑门立户,席门蓬巷,筚门圭窦,沿门托钵,织楚成门,窄门窄户。穷人重子嗣,多生育,望芝麻开门,望鲤鱼跃龙门。门是命运的高度。越生育越贫苦。
乌衣门巷,户户捣衣,也是南方胜景。南方多河流,河流多支汊,支汊多水沟。水沟经过户户门前,有激越水声。雨夜,流水摇动铃铛,清脆悦耳。夜风轻轻地扑打门环,像个夜归人。门环是门的拉手,关门的时候,把门环拉起来,合紧门缝。门环也相当于叩门的手指,用手拉着门环,击门,铛——铛——铛——铛,轻轻叩,是对人的尊重。铛铛铛,铛铛铛,门环敲得急促又响亮,是遇上了急事,上门求助了。赤脚医生的门通常响起这样的敲门声,可能病号到门口了,也可能病号出不了门,急需上门急诊。门环铁质、圆形,和手镯的形态差不多,像门的耳朵。
间谍敲门是有暗号的。偷情的人敲门也有暗号。铛,铛铛。铛,铛铛。也有不小心敲门的人,敲出情人的节奏,闹出笑话。村里有一个赤脚老师,瘦小,踮起脚尖也没窗台高。赤脚老师爱偷情。村口有一个女裁缝,三十来岁,细腰圆臀,餐餐爱吃红烧肉,老公常年在外做油漆工。赤脚老师几次想和她相好,都没成功。一次夜里,赤脚老师敲窗户,窗户里的女裁缝问:“谁呀?”赤脚老师也不说话,拿起两张纸在窗外晃动。女裁缝看看,是两张十块头,说:“谁呀?要进来就来,晃什么?侧门又没上栓。”赤脚老师溜了进去,干柴烈火,烧了半夜。烧完了,赤脚老师也走了。女裁缝说,你晃在手上的钱呢?赤脚老师说,我又没钱,晃的是大前门烟纸。就这样,两人相好了。村口人杂,来往不方便,赤脚老师便说,我用门环敲门,三声长。铛——铛——铛女裁缝便天天盼着门环铛——铛——铛,像和尚盼着敲钟。赤脚老师也是个爱打麻将的人,常常打麻将忘记了去敲门。有一次,一个喝醉酒的人,口渴难耐,醉在女裁缝门前,手拉着门环,有气无力地铛——铛——铛。女裁缝半夜梦中听到敲门,知道是赤脚老师来了,急不可耐地开门,灯也不开,拉着醉汉往房间走,说,等了这么多天你才来,满嘴酒气,有酒气好,有酒就有力。醉汉见女裁缝这个样子,一下子酒醒了,但假装没醒,两个人折腾起来。折腾了半夜,完了,女裁缝开灯去洗身,发现床上的人是打铜修锁的老七。女裁缝说,你这个吃冤枉食的家伙,叫我怎么做人呢?老七说,我以后经常来吃冤枉食不就行了吗?你不能怨我。女裁缝扑哧笑了起来,说,你这样说还差不多,我便饶过你了。
天亮,门就要打开。这是人对生活的宣示。门打开,厅堂里有了人来,也有了人往。我们去耖田,去拔稗草,去收麦,去晒谷。我们去上学,去摆摊设铺,去走街串巷,去翻山越岭。我们去访亲问友,我们去拜师学艺。我们走出门,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去幽会亲爱的人。也有乡邻来坐,谈天气,谈恩怨。也有提亲的人来了,好茶好飯好笑脸相待。阉猪的人来了。割鸡卵的人来了。摇拨浪鼓的人来了。配牛种的人来了。郎中背一个褡裢来了。找酒喝的人来了。问路的人来了。挑担歇脚的人来人。躲债的人来了。回娘家的人来了。借钱的人来了。卖水桶的人来了。沿街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的人来了。收鸭毛鹅毛的人来了。
有每天都要来坐坐的人。有一年来三五次的人。有三五年来一次的人。有十几年来一次的人。有一生只来一次的人。有来了一次再也不来的人。有频繁来却突然不来的人。
有凌晨就来的人,这是报丧的人。有半夜突然来的人,是走投无门的人。
有吃饭时间来的人,是嘴馋的人。有喝上茶就不想走的人,是孤单的人。
有说完事就拔脚走路的人,是命苦的人。有吃了午饭等晚饭的人,是无处可去的人。有看了一眼就走的人,是失望的人。有看了一眼还想问的人,是留恋的人。有来了就痴痴呆呆的人,是有口难言的人。
一扇大门,把这些人迎接了进来。门,迎接了相熟的人,也迎接了不相熟的人。相熟的人,有的会变得日渐陌生。不相熟的人,有的成了知己。我们坐在门里,等待一个人来,等一天、等一年、等十年,却始终不来。我们也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我们也雪夜柴门闻犬吠。
新娘穿大红的衣服,盖着红稠盖头,在炮仗声声中、在唢呐欢快的曲调中,牵进了我们的大门,抱进了房门,成了我们的堂客,生儿育女,相守在一扇大门里,日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脸有了皱纹,乳房扁塌,双鬓斑白,儿女又顶门壮户了。
姑娘被舅舅抱出大门,抱上花轿远嫁。这扇大门,将在她一生的梦中拍打,关了又开,开了又关。
被抬出大门的人,却再也不会回来,去了一个没有门的地方。每一个人,最终都是从大门抬出去的,穿上干净的衣服,盖着白布,眼睛再也不会睁开。一扇大门,要抬出多少人,也是不知道的。
一扇久久锁着的门,里面一定有一个曾经长久居住的人,里面放着我们再也不忍目睹的物件。比如一本书,一把二胡。比如一件蓑衣,一顶笠帽。比如一双鞋,一袭外套。比如一只箱子,一个木匣。比如一封旧信,一支帽笔。我祖父故去之后,他住过的房间,很多年里我都不敢推开那扇门。门右边有一张床,还铺着草席、挂着蚊帐,竹椅子还靠在墙边,酒瓶里还有半瓶酒,鞋子里还塞着袜子,拐杖还斜放在门后。每次进那个房门,我都要站半天。当我们分离,人世间最温暖的东西,不是茶壶、不是锅、不是火炉、不是棉絮,而是恋人的唇,和亲人的遗物。当我们分离,人世间最寒冷的东西不是冰凌、不是灰烬、不是孤枕、不是残月,也是恋人的唇,和亲人的遗物。上帝不是关了一扇门,却开了一扇窗,而是先关了窗,再关门。所有的门窗都关了,我们被抬出了大门。
事实上,每一人,都有一扇属于自己的门。有人在门里,等待我们去敲门。我们也在门里,等待门环叩响。铛——铛——铛。
有些门,我们已经无法敲开。
松脂滴落。门外月光如海。温和的夜,想起这些,我心扉痛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