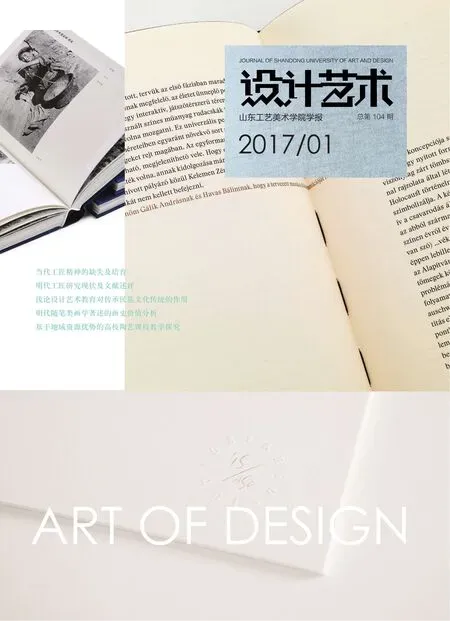明代随笔类画学著述的画史价值分析
耿明松
明代随笔类画学著述的画史价值分析
耿明松
明代出现了很多随笔体画学著述,如杨慎的《画品》、何良俊的《四有斋画论》、王世贞的《艺苑巵言》、屠隆的《画笺》、陈继儒的《妮古录》、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等,其中较多内容具有一定的画史价值,有的还体现了重要的画史观念,影响了之后的绘画史学发展。明代绘画史学的研究应关注此类著述。
明代;随笔类;画学著述;画史价值
明代许多随笔类画学著述虽然并不以画史体例或针对绘画这一单独门类进行阐述,但内容包含着重要的画史资料,对我国绘画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明代绘画史学需要关注这些著述。
杨慎的《画品》(有的称为《升庵画品》)由李调元抄辑所见杨慎各书而成,并非为杨氏生前自己所编。全书共48条,书名虽为“画品”,但全非品评体例,而是各种关于画论、画作、画家、画科、绘画材料、装裱等述评的杂汇,部分内容具有画史参照价值。
“托意”一条举例说明了中国古代绘画题材的寓意或讽喻功能。如认为曹髦画《卞庄刺虎图》,意指诛杀司马昭,说“宋雍秀才画草虫,每一物讥当时用事者,一蜗,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以比安石。”[1]“纪事”一条,以唐太宗和宋徽宗的例子说明绘画的记录或者再现功能。“山水”一条,提到张洵在昭觉寺画“三时山”于三壁,“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夕景。”[2]说明张洵已经开始有意识的描绘风景在不同时间段的各自风貌,可以媲美西方19世纪后半期印象派的色彩认知。
“人物”一条中谈到曹仲达、周昉、吴道子、王瓘等所画人物的不同特点,并对周昉画中“美人多肥”的原因是当时宫禁贵戚所尚之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是取自《楚辞》之意:“《楚辞》云‘丰肉微骨调以娱’又云‘丰肉微骨体便娟’,便是留佳丽之谱与画工也”,认为“肉不丰,是一生色髑髅,肉丰而骨不微,一田家新妇耳”[3],这一观点有别于画史常论。此条谈王瓘(字国器)时还提到了吴道子画作的不足,说“吴生画天女,颈领粗促,行步跛侧,又树石远近,不能相称。”当然,这种缺憾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并不能说是缺点。又说“国器舍而不取,废古人之短,成后人之长。”对绘画之法的继承和发展提出了正确的观点。
“马”一条中谈到赵光辅、韩干所画之马的不同特点,对赵光辅大加赞赏,认为“古今为番马者,胡环得其肉,东丹得其骨,光辅兼有之。至于戏风拽绳,啮草饮水,奔走立卧,嘶咬跑蹶,少壮老嫩,驽良疲钝……莫不精备。”[4]“薛稷”条记有“薛稷不特以书名,而画亦居神品。老杜所谓‘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是也。杜又有《薛少保画鹤》一篇,所谓‘薛公十一鹤,皆写青出真’是也。余谓‘陆探微作一笔画,实得张伯英《草书诀》,张僧繇点曳斫拂,实得卫夫人《笔阵图》诀,吴道子又受笔法于张长史。’(语出宋代葛立方的《韵语阳秋》,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卷二十四“书竹一法”条有引。)信书画用笔,同一三昧。薛稷书法雁行褚河南,而丹青之妙乃复如诗,当是书法三昧中流出也。”[5]较好地述记了中国书法与绘画的紧密关联与笔法上的同理。“试题”一条举例详述宋徽宗设立画院、考试画士之事;其他如《汉画》条、《张僧繇》条、《张湮》条、《薛稷》条、“杨补之”条、《桃源图》条、《拂林图》条、《春宵秘戏图》条、《青枫树图》条、《七贤过关图》条、《花竹》条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内容多抄摘前人,而且不注明出处,有的见于杨慎的《升庵集》、《丹铅总录》等,引据时需审慎。
何良俊的《四有斋画论》从《四有斋丛说》中摘出,约五十则,除了摘引、评说前代画书内容外,书中较多记录绘事、画家事迹、绘画作品等。如论述汉代绘于“车螯壳”上画作的特征,不同于晋、宋间顾、陆之笔,也认为各代画家风格不一样,“善鉴者可以望而知其年代之先后矣”[6]。记录自己所见所藏王维、顾恺之、吴道子之画,并述其特征,如记《女史箴图》为:“近又见顾砚山家《女史箴》,是顾虎头笔。单是人物,女人有三寸许长,皆有生气,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自然。所谓上之又上者欤,且绢素颜色如新,盖神物必有护持之者。”[7]末尾的解释似为玩笑之语。记述自家藏赵孟頫画“其《醉馗图》是临范长寿者,上有诗题,真可与唐人并驾,惜破损耳;其《天闲五马图》临李龙眠,真妙绝,精神完整,且是大轴,至宝也;又有《秋林曳杖图》,一人曳杖逍遥于茂树之下,其人胜韵出尘,真是其兴之所寄;有画《梅花》一幅,是学杨补之者,兼得梅之标格;其他如《大士像》二轴、《竹石》一轴,皆有神韵,非画工所能到也。”[8]这些对赵孟頫多幅画作的记述,具有较重要的画史参考价值;对历代书画书籍进行列述整理,是较早的绘画史学研究,并对人物画的古今变化与特点进行了谈论;以自己亲眼所见,对马远的画作进行评论,提出马远“长于人物”的新观点;比较元人之画与南宋院画,认为院体少韵,而元人画高于院画,并比较元四家之各自特点;比较元画家及沈周与宋画的特点,并述及古画单幅多、对轴少的特征;谈论柯九思、自藏倪云林绘画的特点;把白描分为两种,分别举例说明;山水分为数家(即荆关、董巨、李范、李唐),认为宗此数家为正脉,抑贬宋体(这里所谓的“正脉”之说,或许对以后南北宗论之说有影响);谈倪云林(通过倪的自题自云)的创作特征、创作方法和心理;评论及记叙晴川、汪肇、谢樗仙、王叔明等画作特征,以及画家事迹、作品流传等。此书后面各篇为评论体画史,评及者有曹云面、张梅岩、任水监、张可观、朱孔易、蒋子成、边景昭等,还有戴文进、沈周、唐寅等,分为名家、行家、利家品评;评及姚云东、周东林、陶云湖、文休承、王吉山、晴川等,并论各自特点等,这些内容都具有较高的画史参考价值。
王世贞的《艺苑巵言》以书、画、诗的相通性观点贯穿全史,谈论由古及今的各名家,并分科简述各家的特色,虽然简略,但具有一定的画史参照意义;其中对于人物、山水的流变、划分,较为精彩,可考察与“南北宗论”形成的联系;书中记录有部分画家事迹,可补画史所缺或不详,如明代周官、吴延孝、居节等。
莫是龙的《画说》虽然不是专史,但以画家的眼光评说各画家,论及各派特点,反而深刻,对画史具有参考价值。书中包含有关于“画分南北二宗”的观点。关于他与董其昌二人谁首先提出此观点多有争议,谢巍先生认为应该是莫是龙原创,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9]。
詹景凤所著《詹氏小辨》第四十一卷有《画旨》上下篇,其中下篇记述明代洪武至万历时的主要画家事迹、所擅特长,笔墨特点、作品高下等,具有断代画史的价值,值得重视。此篇还记有作者学画之事,自己的门人如丁云鹏等,也具有画史资料价值。
屠隆的《画笺》虽然是绘画杂论,但其中有关于古画、唐画、宋画、元画的概说,以及在临画、学画篇中论及个别画家,具有一定的画史参考价值。书中屠隆提出了“天趣”的品评观念。他在评述历代绘画时,多次以是否具有“天趣”作为褒贬的理由。如“唐画”条论及后人之画的不足时说“后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10];“元画”条中赞赏士大夫画“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观其曰写,而不曰画者,盖欲脱尽画工院气故耳。”[11]在赞赏元四家及赵孟頫、钱选等人时,也说“此真士气画也,虽宋人复起,亦甘心服其天趣。”[12]说明作者对“天趣”这一标准的推崇。
茅一相《绘妙》的内容与康伯父的《绘妙》第一部分相同,余绍宋先生认为是茅氏伪托之作,谢巍先生则认为是陶珽在辑《说郛续》时误将茅一相列于《绘妙》名下,不能定为茅氏有意伪托。
陈继儒的《妮古录》随手记录所见所闻以及读书中有关书画、碑帖、古玩器物之事,间或有鉴赏、评议。本书共四卷,书、画、帖、玉、瓷等混录,其中画事内容丰富,论述较细致,具有较高画史参考价值。第一,对画作进行较为专业的记录:如卷一记录吴镇(梅花道人)画《骷髅》一轴,详记其题文:“漏泄阳春,爹娘搬贩,至今未休,吐百种乡谈,千般扭拌,一生人我,几许机谋,有限光阴,无穷活计,汲汲忙忙,做马牛何时了。觉来枕上,试听更筹,古今多少风流,想蝇利蜗名谁到头?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回拜相,两度封侯。采菊篱边,种瓜圃内,都只到邙山一土丘。惺惺汉,皮囊扯破,便是骷髅。”[13]此内容对理解画作的深刻寓意具有重要作用。卷三有“余有李嵩《骷髅》团扇绢面,大骷髅提小骷髅戏一妇人。妇人抱乳之,下有货郎担,皆零星百物可爱。又有一方绢为休休道人大痴题。金坛王肯堂见而爱之,遂以赠去。”[14]对作品的内容、特征、归属流转做了详细记录。第二,对画作能做出品鉴:如卷一有“韩太史家有李伯时所画一人剔耳状,其屏障细山水皆学王维,后有子由东坡及王诜书,乃是晋卿暴得耳疾,故东坡作诗以嘲之,而龙眠绘此为图,此载在东坡集。徽宗题作《勘书图》,非也。《勘书图》旧传有顾虎头作,董广川极辨之,见画跋中可考。”[15]对传为《勘书图》的画作提出了见解。此卷对吴匏庵所题的《辋川图》提出了不同意见,“余观之,即未必果出右丞,然绢素极细,却是雪景,以浮粉着树上,潇洒清韵,应宋代临本,非后人可到也。”认为所传王维的《辋川图》不一定是原作,应为宋代临本。卷三有“《女史箴》,余见于吴门,向来谓是顾恺之,其实宋初笔,箴乃高宗书,非献之也。”[16]对《女史箴图》的年代提出看法。第三,对画家同仁绘事做出记录,可以考察当时画家、文人间的相互关系,对研究画史有帮助:如卷一有“董玄宰买龚氏江贯道《江山不尽图》,法董巨,是绢素……”[17]、“玄宰携示北苑一卷,谛审之,有二姝及鼓瑟吹笙者……”[18]卷二有“陆以宁谓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19]等与董其昌相关的十余条绘事记录等,可以考察董氏与当时文人、画家的交往,也可侧面参证画事的真实性。第四,对各类艺术珍玩(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工艺美术或艺术设计)一一记录,体现了我国艺术史学的综合性特点。如卷一记录“宣庙时,磁器及蟋蟀澄泥盆最为精绝。两宫火藏金流入铜中,熔而为炉,故后世伪造者迥不能及。”“余于项玄度家见官窑人面杯、哥窑一枝瓶、哥窑八角杯……”[20]卷三有“王敬美藏一玉觯,有把,长三寸,皆卧蚕纹,纯是青绿侵蚀,真奇宝也。敬美自题其斋曰宝觯,而余尝一再饮酒。”[21]等。第五,陈继儒另一书《眉公书画史》中很多内容与此书相同,疑是从此书中摘录而出,如卷一“阿瑛启,遁迹异乡……”条与《眉公书画史》相同,卷二“石田少时画……”条、“余见王右丞《山庄图》……”条与《眉公书画史》相同,“《鹊华秋色卷》……”条与《眉公书画史》相同,卷三“王齐翰《陆羽煎茶图》……”条与《眉公书画史》相同,卷四“王孟端俱喜作文写竹……”、“昆山王安道……”与《眉公书画史》相同等。总体而言,《妮古录》画事内容丰富,真实性较高,专业性较强,不仅有画史参考价值,而且若能仔细分类和考辨,可以辑为一本较专业的画学著述。
董其昌的《画旨》《画眼》《画禅室随笔》等书由他人辑录而成,虽然辑者因未能辨别是否为董其昌自著而误收入较多内容,但董氏所著内容中,部分具有一定的画史参考和补充价值。比如《画旨》中作者题写前代画作及题写自己画作的内容,《画眼》中对沈周、文徵明、王西园、顾正谊、莫是龙等人的记录等。《画禅室随笔》虽然不是专门的画史著作,但第二卷谈论绘画,分“画诀”“画源”“题自画”“评旧画”四个部分:“题自画”部分对自己所画作品进行题写,共41幅,题记自己作画之感想、缘由及画法,这对研究董其昌绘画有帮助;“评旧画”部分对前人的画作进行评述,具有史料价值。
其中“画源”部分有著名的“南北宗论”内容,以禅宗的南北二派划分画史南北宗的观点,对后代画史、画论、画法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后,大多数学者、画家接受董其昌关于山水画“南北宗”的二分法,并进一步发展到推崇南宗,贬抑北宗,或者在画史写作和画学理论上有意无意的用“南北宗”的观点阐释画家、画派、画法等,成为中国绘画史论研究中难以绕过的画史观念和方法。比如清代唐岱在《绘事发微》中提出正派正传的观点,主要意思是王维一派即南宗为画中贤圣;李思训一派即北派从宋李唐至明谢时臣为非正派,斥其“刻画工巧,金碧焜煌”“始失画家天趣”“究与古人背驰”,最后认为董其昌得正传,三王继之等。清代其他受“南北宗”明显影响的画学著述还有王昱的《东庄论画》、蒋骥的《读画纪闻》、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布颜图的《画学心法问答》、李修易的《小蓬莱阁画鉴》、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等。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编号:13YJC760018),系其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明]杨慎.画品·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815
[2]同[1],817
[3]同[2]
[4]同[2]
[5]同[1]
[6][明]何良俊.四有斋画论·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869
[7]同[6]
[8]同[6],871
[9]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363-367
[10][明]屠隆.画笺·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959
[11]同[10]
[12]同[6]
[13][明]陈继儒.妮古录·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1039
[14]同[13],1052
[15]同[13],1039
[16]同[13],1055
[17]同[13],1042
[18]同[13],1043
[19]同[13],1046
[20]同[13],1040
[21]同[13],1050
耿明松 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