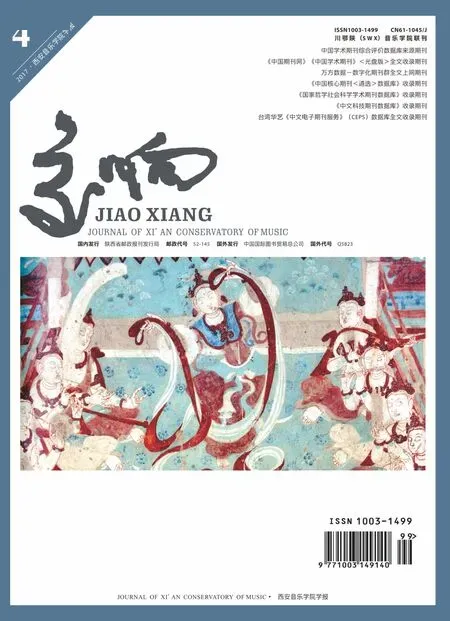我的导师高士杰教授
●祁宜婷
(西安音乐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一、初识先生
高士杰教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初识先生是在大学三年级的西方音乐史课堂,那是1993年,当时我还是管弦系小提琴演奏专业的学生,对西方音乐史和音乐学毫无认知,先生则是年逾花甲的音乐学资深教授。
从中学起我就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对学习的整体认知也和绝大多数音乐学院的学生相差无几。学习乐器演奏专业的我们始终认为,只有专业课才是最重要的核心课程。围绕核心的第一圈外围是如乐理、视唱练耳这样的基本乐科课和以作曲四大件为主的作曲理论课。像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这类课程距离核心则又远了一层,几乎是边缘状态,可以想见其不受学生重视的程度。西方音乐史开课之初,全班几乎都处在刚开学时的亢奋状态。好在那时候上课的人数少,一个班总共不过20来个同学,课堂倒不显得太混乱,但几乎没有什么人认真听课。这么过了一两周时间吧,课讲到了中世纪。
大约是因为早八点的课,我们班同学总是来不齐。就在那次略显冷清的课堂上,我第一次听到格里高利圣咏以及来自朗多尔米书中的一段对圣咏极富感染力的评价①。课间休息,我头一次郑重其事地到讲台上提问,顺便也认认真真地观察了一番这个从语气到表情都极温和谦逊、因此显得不太严厉、也不太有气场的西音史老师。
“你喜欢这个?”高老师显然对年轻人竟对古老的圣咏发生兴趣而感到惊讶,但他依然温和地告诉我课堂上听的是“复活节弥撒”中的一段。对复活节我自然一无所知,于是他又耐心解释了一下基督教的节日。虽然当时具体讲了些什么我早已忘记,但最后当先生告诉我可以借磁带给我复制时,真是令人大喜过望。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这门课,因为至少它还有那么点意思,而且也为了这门课的老师是如此谦和友善的一位长者。
二、优雅温良 君子风范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到后来为研究生考试做准备,高士杰先生的西方音乐史我前后总共听了四轮,有为表演专业的学生开的共同课,也有为音乐学学生开的专业课。其中为1993级音乐学开的课,只有一个学生,加上我这个旁听的,总共也就是两个学生。不过,据我观察,无论是为一个人还是十几人、几十人上课,也无论课堂环境对于一位老先生而言是不是足够友好,他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总是那么温和从容、谦逊有礼。在我与他接触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从未见过他发脾气或是显露任何极端情绪。给共同课的学生讲西方音乐史之类的史论课程,多半吃力不讨好。每当课堂秩序涣散、同学们不认真听讲的时候,先生就会停了讲述,抱臂肃立在讲台一边等我们安静下来,却并不疾言厉色地出言责备。有时候课堂上听到的作品不能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欣赏,一些同学会不礼貌地大声嘟囔“不好听,难听死了”,这时候他也不生气,只是温言相劝,要我们对音乐作品“要有耐心,不要浅尝辄止”。说到浅尝辄止时,他往往拖长了每个字的音值,使这个意思表达得尤为隆重。有时候,他还会在我们对作品感到困惑时安慰我们,“对作品、尤其是对深刻的作品的接受,往往不能一蹴而就”。这些特别的告诫于是烙印在了我心里。我曾经用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瓦格纳的音乐,并且时刻告诫自己不要因为偏见而放弃聆听20世纪实验性、先锋派的音乐,就是因为把老师一再叮嘱我们“不要浅尝辄止,不能一蹴而就”的话放在了心里。
记得前两年年事已高的先生还带研究生,并且几个年级的研究生加起来还不少的时候,有一次他罕见地提及自己的累,那是极难得的一次听到先生吐槽辛苦。我当时建议,不如趁着假期出去散散心,没想到先生转瞬便恢复了温和淡定的神态,微笑回应道,“这倒不必,累是累的,但心一直散着呢。”先生心态之平和雍容由此可见一斑。
我大学期间的小提琴专业老师是当时已退休的刘燕良教授,她与高老师年龄相近,虽平日接触不多,但认识时间久了印象也便深刻。刘老师总是对我说“高老师是谦谦君子”。我想,这是对先生品格的一种最简洁而又确当的评价了。当我考研放弃演奏专业而转投高先生师门研习西方音乐史的时候,刘燕良教授曾给予我最大程度的精神支持,这种支持和肯定一方面是出于对我个人选择的尊重,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她对高先生品格与学养的认同和敬重。
三、何为学问 言传身教
先生的谦逊和虚怀若谷也是有名的。先生自己爱问问题,他常说“学问学问,不仅要学,还要会问”。很多重要的学术场合请他发言,最后倒都变成了先生的提问时间。他的口头禅之一是,“这个我不太懂……”其实,凡听过他讲课的同学,谁不被他的渊博学识与严谨措辞所打动呢?在我印象中,直到2011年5月,已年过80高龄的先生还特地登上五号教学楼,到五楼的阶梯教室听北大刘小龙副教授讲座,还随身携带笔记本认真做笔记。
先生自己爱提问,也爱听学生提问。他的谦逊在对待学生提问方面也体现得尤为突出。无论多么肤浅的问题,他都微笑着听学生磕磕巴巴讲完,从未露出过鄙夷或不耐烦的神色,也绝不抢对方的话头,不代替学生把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说出来。我心里时常存着一个揣测,当初他愿意接收像我这么一个未经音乐学学术训练的表演专业本科生来考自己的研究生,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我爱提问吧。在本科阶段我经常无拘无束地在先生课堂上提问,但很多时候是不过脑子就脱口而出了。像这样冲口而出的问题常令对方摸不着头脑。每当此时,他总是耐心听我讲完,再把我话语中的关键词一一拎出来让我解释清楚。当我面对他温和的微笑时,急躁的情绪便会慢慢平复下来,等把自己话语里那些空洞的观点辨析清楚,我也大致找到了提问的思路和自己问题的关键点,一个相对明确的、有意义的问题就初步形成了。在与先生相处的数年中,我逐渐养成了无惧于提问并善待他人提问的态度,这也是先生教给我的最重要的学术态度之一。
先生上大课时板书不多,只是把几个关键词写在黑板上。若是发现我们对他讲到的某个概念面露狐疑,他也会特地写下来一两句话再详细解释给我们听。高先生上课一贯要用讲稿。我后来发现,讲稿上的文字都是他从相关文献上摘抄下来的。而先生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工整抄录下整段文字,是为了在课堂上引述各方观点时不致因主观印象模糊而曲解了原作者的用意。
每当先生拿起讲稿,我们就知道又会有一段精彩的宏论了。而当他抑扬顿挫、颇富节奏感地诵读完后,他也必定要反复申明,“刚才这段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某人在某本书里说的。”如果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先生书房里,那么这个过程还要再加入一个环节,那就是先生必定会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找到那段话,并且提醒我再看一看上下文。
我必须承认,刚进入西方音乐史课堂时的我完全不习惯这种讲述方式。不就是说一件事、表达一个观点吗?何苦搞得那么费事?究竟是何人评价舒伯特或者勃拉姆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某人是何方神圣……我觉得做这种说明既影响授课的连贯性,又浪费时间。但后来我逐渐开始适应先生的这种讲法,并且有意识地在笔记本上留下一栏空白以专门记录“这是某某在某本书里这么讲的”这个信息。长此以往,我逐渐认识到,一门课程并不是一本教材就可以撑起来的,背后有不计其数的学者和著作在支撑和不断丰富着它的知识体系和观念体系。
更重要的是,通过老师课堂上长年累月的申明“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像我这样没有受过音乐学本科学术训练的人,在写作研究生阶段的第一篇文章时,也都会不由自主地力求明确区分自己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并且通过注释告诉读者,我引述的某个观点来源于何处。“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某某在某本书里说过的”。通过聆听先生数轮的西方音乐史课程而养成的引证习惯,是先生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我的最可宝贵的学术表述方式和遵守学术规范的品性。
四、音乐史与史学,先生的开示
研究音乐而不囿于音乐学范畴、思考西方音乐史而不局限于西方音乐史知识体系,是先生对我影响至深的另一个方面,它极大地拓宽了我思考问题的门径。
我还记得,在考上研究生后上的第一节课里,先生曾问我有什么发展计划。当时我天真地回答说,要好好再看一遍音乐史,学习更多的知识。听到我的回答,先生并没有简单否定我的想法,而是要我去关注一下历史知识背后的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哲学?哲学思维与历史研究有什么关系?历史研究为何需要哲学的引导?历史哲学又是什么?于是,在先生指引下,我开始阅读《人心中的历史》、《历史的观念》等历史哲学书籍,以及冯友兰先生有关哲学方面的论述(当时还未接触到大名鼎鼎的冯氏《中国哲学简史》,读的是《冯友兰学记》)。对于历史研究背后的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并不仅仅为了“知”,而更多导向“求知”和“认识”,导向知识探索背后的方法和元理论问题,最终触及的是人对于历史的理解与阐释。在这些问题的推动下,短短的三年研究生阶段,我最终完成的学位论文才能立足于对音乐史学元理论的思索。虽然,这个阶段的思索远远谈不上成熟,但这种对于宏观理论的兴趣显然是受到先生思想影响的表征,亦是我拓展学术视野、启迪人生智慧的开端。
读过先生文章的人都了解他在研究西方音乐史时偏好从全局角度提出宏观性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思考基督教精神与西方音乐文化的关系②到对中西音乐关系的考量③,及至当下对人类音乐艺术的两种存在方式——混生与自足——的讨论,[1](P5-10)无不透露出他对于西方音乐史的关切从来就不局限于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更多地指向对中国当下音乐文化建设的现实思考。
先生生于1928年,他的人生中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多个阶段。历史的赓续变迁、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的起伏动荡对他的精神建构意义重大。多年受教于先生,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学术思索是充满了家国情怀的、极富现实人生温度的思索。他研究西方音乐及其历史,一方面是为着自己对音乐的挚爱之情以及求知求真的学术信念;另一方面也紧密联系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20世纪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名言),而“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现在反思过去”[2]。在20世纪90年代先生写作的一系列有关基督教与西方音乐关系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先生不仅对西方文化、西方基督教精神对西方音乐的深远影响有深刻的理解,而且也表现出他对西方文化精神对中国当下文化建设所起的作用有深切的关注。
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礼乐思想、礼乐建制及其影响深远的乐教传统对我们的音乐文化乃至文化族性都施加了无以伦比的影响。这一传统的辉煌灿烂、广博渊深自不待言,但也有值得今人冷静反思的一面。乐教传统强调了音乐对士人格的养成作用,使音乐在引人向善的德育功能方面被大力弘扬,但另一方面却削弱甚至遮蔽了音乐作为独立艺术的审美特性和科学的求真特性。西方音乐在近现代被引入中国后,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段,开拓了音乐的表现意义,开辟了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超越观念以及独立自足的西方艺术精神也极大地拓展了国人传统的音乐观念,更新了国人对于音乐艺术的认知和欣赏方式。20世纪中国对西乐的接纳和汲取,从音乐实践方式、乐理与创作理论,直至专业院校教育体制,均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卓尔不凡的海纳百川之精神。而中国音乐人在新世纪的世界乐坛上的卓越表现,更使得先生对中国音乐文化未来发展的“全面现代化和充分世界化”前景充满了乐观的期待。
五、心慕师风 高山仰止
在先生九十华诞即将来临之际写下上述文字并不是为了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以垂范后世、供人仰望。这样的写作是为先生所深恶的。我亦确信每个人都有其独特之处,每一代人亦有每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先生的独特品格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时代和环境的塑造,这其中既有帮助他实现投身音乐事业之梦想的时代契机,也有持续不断的现实困境对其人格的砥砺。先生的品格因而是无法复制的。同时,他为探究学问而投入的那种毫无功利色彩、纯然发自肺腑的热情是无法复制的;他由对这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的热诚关注而导致的宏观性的提问与论证方式也是无法复制的;也许,先生立论的宏观性视角和文章中某些表述方式在今人看来显得不那么客观中立、条分缕析,也不那么纯学术化,但其中却充满了自身宝贵的生命体验与思想热度,更渗透着他那个时代的学者对自身所处现实的深刻体认与反思。换言之,先生的学术研究绝不是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理论思辨,而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断寻求积极对话与思想交锋的成果。
最令人钦敬的是,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先生在长达数十年的思想历程中始终坚持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因为他坚信对马克思理论学说的理解必须建立在阅读马恩原典的基础上。也正是在这一经年累月的阅读思考过程中,他开始对始于20世纪中期、曾经在音乐理论界一统天下的认识论基础——以阶级分析的观点理解音乐作品——不懈地进行清理与反思。在最近几次与先生的交谈中,他多次提及自己刚入音乐学门墙之时因对阶级分析观点感到难以把握而深感焦虑和痛苦,而现在终于可以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精神的理解而与这种观念彻底决裂。先生提及此事时的感喟着实令人动容,要知道他本人是接受这种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种思想转变过程的孤独与艰辛可想而知,那并非是人人能够且愿意承受的。
在最近一次与先生的对话中,他向我提起康德作于其人生暮年的短文——《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1784),并引述康德的观点说,导致人的不成熟状态的原因,并非由于缺乏理性,“而是在无人指导之下缺乏勇气和决心来运用理性。因此,启蒙的口号是‘勇于智慧’,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着重号是先生谈话时特意强调的,非康德原文所有)。我相信,先生始终在用自己的人生践行康德的启蒙观念,也正是这种无惧于运用自身理性的坚定与坦然,造就了先生俯仰于天地间的独立人格。
人生有涯,而思无涯。在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高士杰教授九十华诞将临暨赴西音从事教研工作即满六十周年之际,祈愿他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以有涯之人生怡然享受思无涯之乐趣。
注 释:
①在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中,作者引用了罗曼 · 罗兰的一段话来评述圣咏,“……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充满沉思内省的艺术更感人肺腑了!尽管社会动荡,多灾多难,而这种甜美的音乐还是不顾一切的大放异彩。”此后我也常在自己的西方音乐史课堂向学生完整地朗读这段话。详见[法]朗多尔米著;祝少坤译《西方音乐史》第13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
②先生所写的系列文章择要列举如下:《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基督教精神与西方艺术音乐传统》、《基督教与西方音乐研究现状》等均收录于《理解·追问·反思——高士杰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此外还有发表于《交响》2009年第2期的《理性面对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基督宗教问题》等。
③这方面的文章择要列举三篇:《20世纪中国音乐道路论争的断想》、《从‘世界的文学’想到‘世界的音乐’》(此两文亦收录于《理解·追问·反思——高士杰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向西方乞灵——接着蔡忠德讲》(发表于《交响》2010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高士杰.在人类音乐文化的大视野中认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现状[J].交响,2017(1).
[2]引[加]卜正民著;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英文版序,x,[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评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