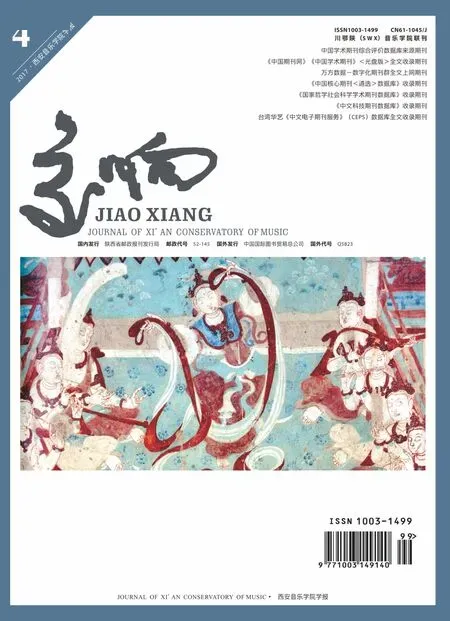“我想要自己活得明白”
——高士杰教授访谈
●高士杰 祁宜婷 王尚清
(西安音乐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第一次访谈时间:2017年7月22日,下午4:00-6:00
访谈地点:高士杰教授家书房
受访者:高士杰教授(下文简称“高”)
采访人:祁宜婷(下文简称“祁”)
现场录音及文字整理:王尚清
本次访谈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高先生退休之后始终萦绕于心的思考;二是有关基督教与西方音乐的话题;三是在谈话中涉及到的一些先生个人的学术经历。此三方面问题经由采访人与受访者事先磋商形成。谈话首先从高士杰先生近些年来思索的问题开始。
(开场白,高):今天我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还愿意和你们谈,是因为我完全退了以后,研究生也不带了,但脑子的确没休息,还一直在思考。并且也确实有些想法,想借此机会和你们交流交流。时间有限,我不能说的太琐碎。我想先从总的方面概括一下近些年来我所关注的最多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近些年来我思考最多的问题,总是离不开对我来说应该属于根本性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我工作中的老本行——西方音乐史问题;另一个就是关于我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也就是指导我思想的理论基础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曾说,我在工作中教了几十年的西方音乐史,如今退休了,绕了一大圈,最后在思想上又回到了原点。原点是什么?就是“西方音乐史”这五个字上。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西方音乐史”这五个字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西方音乐”,一个是“史”。但我自己在很长的时间中对这两个概念在理解上是幼稚和片面的,或直截了当地说是不正确的。基本上是停留在望文生义地把“西方音乐”理解为西方的音乐或西方人的音乐,把“史”仅仅理解为过去曾发生过的事。这样的认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得到启蒙,开始改变。
90年代初在北京举办过一次西方音乐史年会性质的会议(当时尚未成立西方音乐学会)。在那次会上推荐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另一本是刘昶的《人心中的历史》。会上还印发了几篇国内发表的有关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论文。其中包括杨燕迪的《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等。会后,我比较认真地读了书并开始重视史学方法论和历史哲学方面的学习与思考。在杨燕迪的那篇文章中,我第一次读到了关于对西方音乐界定的那句话,即西方音乐特指“艺术音乐”①。此后,关于历史哲学问题和艺术音乐问题就不断引起我的反复思考与学习,也陆续写过几篇文章。我最近在《交响》上发的那篇文章②,可以说就是我最近在有关艺术音乐问题上的新认识。这是第一个问题。
再说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在文艺领域出现过不少“左”的折腾。比如,直到现在,困扰我多年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包括音乐在内的文艺作家和作品去进行阶级分析,不断给作家和作品贴阶级标签。我根据自己对音乐和对其他文艺作品的感受,实在无法理解与接受。我酷爱音乐,聆听音乐至少也有七八十年了。我怎么也感受不到音乐的阶级属性。坚持音乐有阶级性的人,也从不告诉人们,他们是怎么从音乐作品中听到了阶级性的。
我虽然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多。但我是十分注意马、恩是如何讨论分析包括音乐在内的文艺作家和作品的。至今,我也未发现马、恩给文艺作家或作品进行阶级分析的一次实例。这绝非偶然,恐怕是有道理的。我体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科学学说,是建立在社会物质生产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上的分析。包括音乐艺术在内的文艺创作,一是精神生产并非物质生产;二是精神生产是文艺作家的个人创造,在创造过程中并不存在生产关系,怎么能进行阶级分析呢?
最近,我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开始部分,在强调文艺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时,习总书记举出了古今中外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整整一百位作家,其中也有不少作曲家。习总书记并没有给任何一位贴上阶级标签。这一点,与我读马、恩的有关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改革开放前,我们出现在文艺领域的各种“左”的折腾,其理论根据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来自前苏联。而苏联在文艺理论上的阶级分析,最初恐怕也是来自列宁吧。这些就是我关于第二个问题上的一些基本思路。
祁:您曾对基督教与西方音乐的关系问题很关注,能谈谈您当时的思路吗?
高:回忆起来,可以说大致有这样一些背景。我参加过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办的那次基督教与西方音乐的读书会。再有就是我在学习有关史学方法论的著作时,看到汤因比关于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分析。更直接促使我关注基督教与西方音乐的关系的重视,特别是前面提到的杨燕迪关于界定西方音乐那句话中,“艺术音乐”前面的那句定语,即“特指以基督教文明为基质发展起来的”那句话。促使我总想进一步了解基督教文化究竟怎样具体影响了西方音乐。
不过,我现在感到我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个很大的局限。我只关注到基督教在观念上或在意识形态上是怎样影响欧洲作曲家的创作。忽视了或者说未能从西方音乐在发生学上,基督教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祁:您可以再具体解释一下吗?
高: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只能简单地谈谈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脉络。我觉得教会负责音乐事务的神职人员,之所以能承担起艺术音乐生成的历史任务是不自觉的。倒很像社会学家郑也夫说的,“人类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教会音乐家们的职责在于规范和加工装饰圣咏的演唱,却在这个过程中催生了艺术音乐。
教会音乐家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副产品”,依我看,又是与基督教重视理性的传统分不开,起初我总觉得宗教信仰是一种非理性现象,是不能与理性结缘的。后来我读到一位华裔美国哲学家成中英的一篇演讲稿,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使我改变了看法。成中英说,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把宗教信仰看成大前提,然后加以理由化,说明化,所以有了神学”。这也就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我说这些,是想强调没有理性的参与,也就不可能有教会音乐家们对圣咏的理性加工,也就不会完成艺术音乐的历史性实现。要想搞清楚理性对艺术音乐的意义问题,我觉得还一定要很好地思考埃格布雷希特在《西方音乐》中的“反思之一:西方音乐”。在这个反思中,埃格布雷希特认为西方音乐历史“主导原则的中心观念……就是理性”。说到这里,我觉得你现在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实际上也涉及基督教和西方音乐的关系问题。
总之,这就是我现在对艺术音乐从发生学的视角,看基督教所起的历史作用的思考纲要。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祁:我认为圣咏是属于艺术音乐出现之前的……
高:对,是的。但如果没有那些教会音乐家们的工作,也就不会形成后来的艺术音乐。所以,正如尤德金在《欧洲中世纪音乐》中指出的:“作曲家开始把宗教音乐视为音乐材料,为了艺术的目的可以做理智的安排,而不是纯粹为了仪式的目的。”我觉得,经文歌就是从混生性艺术转向自足性艺术的一种过渡形式。
祁:可以再把这个过渡阶段提前一些。实际上从9世纪加洛林无名氏的理论家开始从希腊理论当中找一些依据去解释圣咏的时候,圣咏就已经不完全是一种只为仪式服务的功能性音乐了。可以说音乐实践每走一步,音乐理论就会跟上。
高:是,理论是跟上了,但是这样出来的产品依然是跟着教会的仪式活动混生在一起的。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音乐并没有记录下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音乐审美对象是圣咏吗?
祁:应该还不是。不过,现在已经有人研究当时的世俗音乐是怎么与教会音乐发生互动的。在仪式过程当中,有一些其实和仪式功能无关的因素,比如哈利路亚花唱。这样一种花唱更像是为了展现艺术的美感。
高:是审美的,但这是在仪式当中审美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不在仪式中唱,脱离仪式来专为审美的目的。比如,我要到音乐厅去听,不在教会仪式中听。也就是说,音乐是独立自足地存在,不依附于仪式,跟宗教仪式无关。我认为这才是艺术音乐。
祁:宗教与音乐的关系,确实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高:但谁都不能否认,自足性音乐的根源、起源是来自教堂音乐。
祁:是的。可以说自足性音乐是从教堂礼拜仪式中培育起来的。教会作曲家在有意识地培育,而音乐理论也在不断跟进,不断在走抽象化的道路。对中世纪音乐理论方面做研究的文章,会很清楚地告诉你,在歌唱过程当中,一个滑音的每一个音级是怎样被剥离和抽象出来,形成音高的概念。再被抽象成一组音型,而这种音型是按照规律来排列的,最后用音阶来表现它。这种规律可能是全、半音关系组成的一种音高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今天所谓的音阶。但这种东西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教会音乐家们辛苦归纳出来的音乐理论。
高:当时教会音乐家还有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就是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完备的、能再现乐音音响的记谱法。这个是了不起的成就。
祁:对,记谱法与调式体系是共同发展的。
高:所以说啊,中国古代不管怎么重视音乐,都没有形成一种完备的记谱法。历史上形成的那些记谱方式只能算作是一种演奏提示,它没有记录音乐音响本身。所以,我总是对这种说法抱有疑问,就是:中国古人之所以没有创造一个能再现音乐的记谱法,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尽管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审美是不愿意那么死板的,照着谱子演奏,但是你得有了这个谱子才能说我的演奏、欣赏是不完全按照谱子来做的。如果根本没有记谱,那这么说就没有根据。没有精准的、反映音乐音响本体的记谱法,就像人类没有文字那样,只有语言了,口头的历史那是史前史。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充其量也只能是社会音乐生活史。
祁:有了记谱法可以相对准确地去还原音乐音响。当然,教会音乐家发明记谱法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在传播过程中音乐不至于发生太大变化,为了各个教区的礼仪音乐尽可能达成一致。
高:那么别的宗教为什么没有创造出来记谱法呢?比如佛教、印度教,它们怎么没有发明出来精确的记谱法呢?
祁: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这与基督教是一个理性化程度非常高的体制性宗教有一定关系。
高:这个问题是一个还可以继续深入的点。基督教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宗教。他们在信仰上也争论过,是信了才能理解,还是理解了才能更好地去信仰问题。
祁:是的,在神学的层面上是如此。但不仅是在神学上,其实整个教会体制本身,包括教仪(宗教仪式)的制度化都是显著的特征,这是理性化程度很高的制度。而且西部的罗马教会表现得比东部希腊教会还要更明显。希腊正教并没有早于罗马教会形成一套系统的记谱法。
高:我对基督教与西方音乐关系的早期研究中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为什么会这样?
祁:这个问题就太大了,牵扯面也比较广。我只能大概说说从我阅读的一些文章中看到的西方人研究中世纪音乐的情况。西方音乐学界目前还是更偏向于从古文献实证的角度来做研究。他们当前在实物考证方面运用的技术非常高端,而这种利用特定技术研究音乐古文献的工作必须是由多人合作的团队来做,很少有单打独斗的研究。在国内从事这类研究之所以难出原创成果,一个原因就是你拿到的东西是被人研究过的,看不到原始资料。或者说,即使你看到原始资料,以现有的技术、能力与合作水平,很难达到西方学界那样的高度和水准。因为我们对音乐原始文献和档案的研究,这一块儿整个来说还处于极低的层次,甚至还没有建立这方面的意识。仅仅看一个二手文献就出成果了。而在西方做这样一个成果必须要有很多实际证据(一手资料)的支持。
祁:其实我还很想了解您那一代人的学习经历,肯定和我们这一辈的差异很大。您能讲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音乐学的?为什么要学音乐学?
高:我是1949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的,我经历了中央院建院的活动。49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北京艺专音乐系,还参加了天安门的开国大典。之后,就在当年的11月上旬,我们就乘卡车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到天津去,正式进入由几个单位合并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
我在49年以前没有正规学习过音乐。之前,我就一再说自己学音乐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不是客套话。先天不足是指我的家庭不是一个音乐世家,父兄没有从事过音乐这方面工作;后天失调是指49年我上大学才开始正规学习音乐。在这之前我喜欢音乐,除了中学的音乐课上学点音乐,也常到图书馆去借书看。也曾经到艺专去蹭课听。当时连大调、小调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有一天在艺专校园内碰到江文也骑车下班,我就上去问,“怎么知道一首曲子是大调还是小调?”江文也这个人倒真是没什么架子,我当时还不是艺专的学生。他听我问就停下车,用脚撑着地想了一想回答我说,“凭感觉”。
当时我是死心塌地的想学音乐,还去学了钢琴,弹到车尔尼849吧,然后就考了北京艺专音乐系。当时没有音乐学系,我考的是作曲专业。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念了6年,1955年才毕业,中间有一年去治淮——到安徽佛子岭修水库。
祁:然后您留校(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了三年,对吗?
高:毕业之后,来了很多苏联专家,吹拉弹唱的都有,包括教音乐史的康津斯基。我就在专家工作室工作了一段时间。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音乐学系。在我的请求下,被调到音乐学系,这就使我有机会参加康津斯基所开的西方音乐史课。从此,我走上了从事西方音乐史的工作道路。
我在前面提到的自己在音乐学习上的后天失调,主要是指在我学习和工作中,受到“左”的干扰,实在太多了。这些干扰让我浪费了不少时间,走了不少弯路。
祁:那您后来为什么又从中央音乐学院到西安来了?
高:那是服从国家需要。1956年我到中央院的音乐学系,1958年为了支援大西北随刘恒之带的一些人到了西安。来到学校(西安)以后,我是被分在基本乐科教研室,和作曲专业、视唱练耳专业在一起,后来才又成立了史论教研室。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了,在史论教研室的基础上,又成立了音乐学系。
祁:那大概是在1994年的时候了。我们学校在文革的时候也停过课吗?
高:当然停过课。
祁:但不是有工农兵学员吗?
高:那都是后来的事了。文化大革命头几年是停课闹革命。到了七几年的时候又复课闹革命。当时西安音院也跟美院合并了,成立了西安艺校。校名怎么称呼记不清了,当初我们调来的时候还不叫西安音乐学院,叫西安音乐专科学校。
祁:那您过来之后就在这边教授音乐史课程吗?
高:对。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康津斯基的班上,听课的学员,有很多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教音乐史的老师。到了1958年,康津斯基走了,又把这批人全部弄到中国音乐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组织大家集体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本来我是1958年被通知调到西安,但因为要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所以59年才到校报到。初到西安时既教西方音乐史,也教过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用的教材就是当时编写的油印本。
祁:那您觉得在恢复高考以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学校发生哪些改变,或者您在教学上有了哪些新的想法?
高:80年代之后,因为不再搞运动和搞思想改造,整个大环境就宽松多了。
此时天色已晚,虽先生谈兴正浓,亦毫无倦意,但毕竟还有晚饭等家务琐事需要操持,谈话至此只好戛然而止。我们与先生约定了第二次访谈的话题后,与先生一家依依惜别。
第二次访谈:2017年8月3日,下午4:30-6:00
地点:高士杰教授家书房
受访者:高士杰
采访人:祁宜婷
现场录音及文字整理:王尚清
此次与先生议论的主要话题是:请先生对正在音乐学之瀚海遨游的学子提一些建议。
祁:您对正在学习西方音乐史的同学有什么建议吗?
高:说到建议,我还真是有那么一点要说的。大概前几年吧,有一次接受崔兵老师和冯存凌老师的邀请给学生们做一个讲座,来听的人好像大都是研究生吧。原本我料想大家可能会七嘴八舌地有一些讨论,但令我特别意外的是,现场没有一个同学提哪怕一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作为一名音乐学系的学生,不管具体学什么专业,有一点要明确,你的前途不是演奏家、不是创作人员,你是来做学问的人。如何做好学问,如何得到学问,答案其实都已经在这两个字里面了,一就是学,二就是问。你只要学了、问了,你就能得到学问。学是接受信息,通过读书、上课学习知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有问题意识。问当然可以是向别人提问,请教别人,其实更多的时候,恐怕还是自己在学的同时,自己向自己提问,自己思考问题的答案。心里没一点问题,怎么做学问呢?而在提问题方面,我看现在的学生有些欠缺。康德说,启蒙“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是康德在200多年前说的话。我想,如果我们的同学们在学习中不善于发问,是不是反映了同学们在学习上还不善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还需要启蒙。
祁:高老师,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跟您学西方音乐史的,是您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那么到2015年您最后一个研究生毕业,您觉得学生的学习状态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
高:总体感觉是学生在学习上主动性不够。这个问题,我们当老师的也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启发学生们的自觉思考。最近,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一篇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钝写的文章,题目是《人类应该向历史学什么?》。文章中有些话十分让我动心,例如:某些史学家的史学研究起到了“为在人类过去与未来间搭设桥梁”的作用,指出“通向未来之路”和“帮我们开辟新思维”等等。看到这些话,我就想,我们的音乐史学教学与研究,难道只是讲讲音乐史上怎么断代,有过哪些名家名作之类的内容吗。想到这些,我深感我当年向学生讲的西方音乐课,实在太单薄而让我遗憾。所以,我们从事西方音乐史工作的人,是不是也应该问问,音乐工作者应该向音乐史学什么的问题。
另外,我从手机上也读了邓晓芒教授的一篇文章,谈他为什么研究康德。他说,因为他小的时候,“是生在一个不讲道理的文化环境里,所以就总想讲讲道理”。他还举了一段不讲道理的相声段子。所以我觉得邓晓芒研究康德,起初恐怕也是因为想从康德的思想中得到启蒙吧。我以前对启蒙还有点儿误解,我总觉得,启蒙就是别人告诉我们什么了,让我们有了新思维。其实到现在我才明白,康德所主张的启蒙,就是要自己动脑筋去追问、去回答、去解释你所面对的现实。
祁:您是指的康德的《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这篇文章吗?
高:对,就是这个。邓晓芒也在文中提到康德所说的话,你自己要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是那种不经别人引导而能够运用自己的知性能力,大致是这个意思。强调你要自己去思考,会思考,每个人都要自由地思考,这就是启蒙。那么我想我们学音乐学的,就要自己去想、去思考。就是在知道一般常识的基础上提问题,不再仅仅是你告诉我,我记住这么简单,而更要做到你告诉我了,我还要追问,它为什么这样?它的意义何在?等等。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好像不太注重培养人的爱提问的意识。邓晓芒小时候的生活促使他老想开开窍,问一问咋回事,怎么会这样?所以他就去研究康德,研究西方哲学去了,而且还很有成就。
祁:现在大学生主要是不太关注与自身无关的、外部的一些事情。
高:我们不说关注外部其他事情,仅就你自己立志要学习的专业,你总得关心吧?!关注、关心应该表现在哪儿?表现在“追问为什么”,就像康德所说的“这种现象何以可能”,你总得问一问吧?!所以我认为音乐学的学生应该要有“我要毕生做学问”的抱负,这不算好高骛远。
祁:当然不是,这是最起码的。尤其是我们学科积累的东西又那么丰厚,就算是使劲儿去做的话,也得磨很长时间才能出那么一点儿东西。
高:当然,所以如果你只是被动地在那里学习,效果就太差了。但你要是多发问,多问一问,然后再有自己的体会,那可能收获就会大一点儿。
苏格拉底说过:“未经过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你是搞音乐史的,你对有关音乐史的问题不加以思考,你觉得这样的人生值得过吗?
祁:不过,现在的学生可能与以前的学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他们有很多获取知识、信息的途径……
高:我先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学生有没有如饥似渴地要听音乐?这种劲儿有没有?我们上学的时候听音乐很难的,所以我们就跟乐迷一样,去听表演专业的学生考试。比如今天钢琴系考试,我们就坐在考场后头听,因为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听到古典音乐。
我当初学西方音乐史就是因为我爱听。我想着学了音乐史,我就会多知道一些经典作品啊,著名作曲家啊,他们是什么情况啊,或者是经典名作的分析啊,这样我的体会就更深了。
祁:因为以前那个时候能听到的东西很少。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有个录音磁带全班都在复制的样子。
高: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磁带录音机,才刚刚有了钢丝录音机。那也是很珍贵、很稀少的物件。
祁:现在不一样,获取资源的渠道特别多,所以学生选择的范围也很大,不只是追古典音乐。
高:但是你别忘了,西方音乐史讲的是艺术音乐的历史,听古典音乐是必须的。当然喜欢流行音乐没什么不好,那就换个专业,可以搞流行去。
还有刚有手提磁带录音机的时候,当时我们音乐学院的情况是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抢着听,因为“文革”刚刚过去,那十年的时间是不准听“大洋古”的。听说当时中央乐团有两个人,关在屋里头偷偷地听古典,外头有人敲门进来问“你们听什么呢”?两人早有准备,回答说,“我们在听列宁同志最喜欢的音乐”。
刚流行磁带录音机的时候,想买空白带都不好买,要托人买,买了好互相转录音乐。学校所有的人,包括刘大冬老师啊,包括咱们学校出来的、现在在世界上很有名的和慧都有这种强烈的愿望。我几乎每次去唱片室都能见到和慧在那儿如饥似渴地听音乐。可是后来大家这种劲儿不知怎么就越来越少了。我就总觉得现在的学生有点儿无所谓,可能现在是太方便了吧。
我还记得20世纪40年代,在北京想听音乐,我通常会去两个地方,一个是美国新闻处,另一个是英国新闻处。美国新闻处在北京南长街,它那儿每周某一个下午有唱片音乐欣赏会。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大的密纹唱片,我总到那儿去听。英国新闻处是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那个地方。所以,从前都是一有机会就去听音乐,但现在好像这种意识淡漠了。
祁:也许现在大家更愿意自己在家听吧。
高:那也好,听就好。就像学文学的,你不读点儿文学名著,有点儿说不过去。他们学美术的,都要出去到各个地方的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看经典作品。那么,学西方音乐史的,必定是要听经典的音乐作品的。
还有,我强调学问,一要学,二要问。问呢,不一定是要问别人,要问的对象往往就是自己,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上次我跟你说,我一直没有放弃思考,一直想着一些问题,其实我没有别的企图,我就是想让自己活个明白。为了这个,我一直没有放弃思考,没有停止自己问自己一些问题。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圣人说的话,我只是个老百姓,说大白话,我总想让自己活个明白而已。
第二次访谈结束时,先生特意强调,虽然自己退休有年,也早已不带研究生了,但还愿意思索一些问题。思索这些问题并不能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比如发论文评职称。而名利对于一位耄耋老人来说,也已是过眼云烟。思索不停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认识都是自己思索得出的结果”,就是为了“想要活得明白”,我为先生这样的人生直白而赞叹。
注 释:
①西方音乐史中的音乐概念主要指的是艺术音乐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的共识。但在中国大陆音乐学界,这一观点首次获得完整表述并激起较大反响是在杨燕迪的《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一文中,原文为“而‘西方音乐’在学界则是有共识的,即它特指以基督教文明为基质发展起来的‘艺术音乐’。”该文载《黄钟》1990年第1期。
②该文指的是:高士杰《在人类音乐文化的大视野中认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现状》,发表在《交响》2017年第3期。
——评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