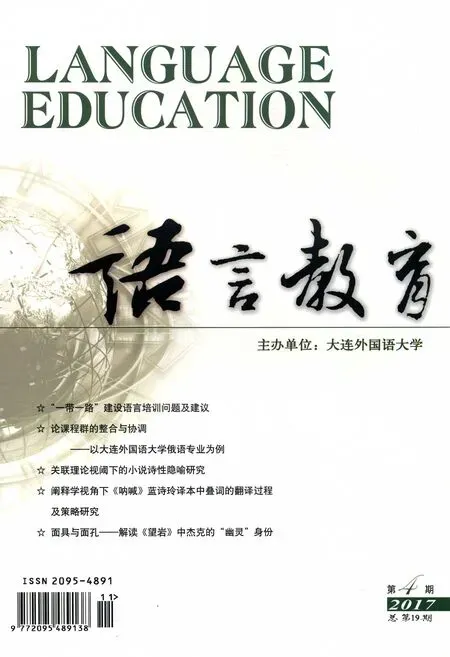刍议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
刁 洪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刍议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
刁 洪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不断自我更新研究方法和理念,是任何一门学科保持旺盛活力、适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当前,翻译实践呈现本地化、全球化、技术化、信息化和职业化等特征。相应地,翻译的定义和研究范式也在发生重构与裂变。在此背景下,“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似乎与翻译实践渐行渐远,在翻译过程、非文学翻译等领域显得无力。本文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几大“转向”,梳理了近年来翻译技术的重要进展,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范式提出了“技术转向”的概念,并阐述了翻译研究实现“技术转向”的必然性及应对策略。
翻译研究;翻译技术;研究范式;技术转向
1.引言
作为一个重要的术语,“转向”一词对当今翻译学者而言并不陌生。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2009)将其定义为:一种动态、明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的转换与革新。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是翻译研究“转向”的范例。本文中,笔者将提出并阐释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technological turn)”,以唤起学界对如下发展趋势的关切:技术正成为翻译研究的中心话题和重要手段。换言之,以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和计算机辅助翻译(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为代表的翻译技术研究已成为显学。而在跨学科研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与模式不断介入翻译研究,使其“科学性”不断提升。这显然预示着翻译研究范式的一场重大变革,值得译学界进行深刻的学科反思。
2.“文化转向”何去何从?
人类对翻译的思考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大量翻译家、哲学家、宗教领袖和作家对翻译进行了描述、评论和总结(Ferreira & Schwieter,2015:3)。但翻译学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20世纪上半叶开始,中西方学者才陆续展开翻译学的理论构想。我国的董秋斯(1951)①指“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原载于《翻译通报》1951年第二卷第四期,转引自《翻译论集》(修订本)(罗新璋、陈应年,2009)。先生明确提出了建立翻译学、建设翻译理论的主张;以维内(Vinay)、达贝尔内(Darbelnet)和奈达(Nida)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了翻译研究应当区别于传统语言学,跳出语言等值性(linguistic equivalence)的藩篱(Vinay & Darbelnet, 1958;Nida,1964)。1972年,荷兰学者霍姆斯(Holmes)在其“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建立翻译学的主张和规划。“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被称为“翻译学学派”的宣言书。此后,翻译学迅速发展,但始终拘泥于对比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维度。直到二十多年前,当翻译研究处于危机之境地和“语言的囚笼”中时,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菲尔(Lefevere)大胆地呼唤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这不仅使这门新崛起的学科走出困境,而且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王宁,2009:41)。从此,霸权(hegemony)、改写(rewriting)、操控(manipulation)、赞助人(patronage)、政治介入(political engagement)、意识形态(ideology)、暴力(violence)、性别(gender)、殖民(colonization)、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等概念被广泛引入,众多的西方理论学派,如解构主义学派(De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多元系统理论学派(Polysystem Translation Theory)、女性主义学派(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后殖民主义学派(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等都将翻译研究的视野指向文本之外,关注影响译者和翻译过程的社会文化因素。上述趋势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界,提升了其学科地位。其后,新的学术共同体日渐形成,从文化层面对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便渐次成为学术主流(傅勇林,2001)。
然而,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谢天振,2008:ii-vi),从而“毅然与文本内的讨论相决裂”(Bassnett,2001:12),丧失了对翻译实践的指导。因此,近年来“文化转向”招致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反诘甚至是批评。姜艳(2006)认为:“文化转向”过分强调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限制作用,试图否定传统翻译观和方法论,构成了对翻译本体论的消解。胡牧(2011)则指出:“‘文化转向’突破了语言研究的视域,但它没有强调文本从何处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缺乏对文本生产者、生产过程、产品的社会性方面的关注”。与“文化转向”紧密相关的文化翻译研究也饱受诟病。如蔡平(2005)指出:“文化翻译”这一提法本身就带来诸多困惑。Conway(2012)认为:文化翻译研究,特别是跨学科研究往往原地转圈,停滞不前。还有不少学者担心翻译研究有依附于文化研究的趋势。
综上所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陷入理论和现实的困境。学界出现了许多翻译研究回归现实世界的呼声。究其缘由,忽视文本物质性、脱离社会实践的泛文化倾向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卡西尔(2004:8)指出:所有文学作品都具有自然和物质属性,而创造这些作品的个人也具有自己的心灵存在和生命特性。所有这些都可以而且也必须置放于物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范畴中加以研究。否则,翻译研究会陷入泥潭。
3.“转向”抑或研究角度的不同?
进入新世纪,世界逐渐呈现出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各国家、民族、语言间的交流日益密切,翻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翻译研究发展速度空前,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更为宽广。国内外学者纷纷撰文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转向。经过梳理,笔者总结了以下新的转向:社会学转向(Pym,2001)、权力转向(Tymoczko &Gentzler,2002)、创造性转向(Loffredo &Perteghella,2006)、语用学转向(曾文雄,2007)、显性与隐性转向(徐剑,2007)、现实转向(黄德先杜小军,2008)、认知转向(刘军平,2008)、译者转向(夏维红 年丽丽,2013)、生态转向(陈月红,2015)和译创转向(Katan,2016)等。
然而,我们不得不对以上林林总总的“转向”表示质疑。它们是翻译研究“转向”还是翻译研究的不同角度?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厘清“转向”的定义和内涵。众所周知,“转向”一词译自英语“turn”。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对它的定义是:1. change in the direction;2. a sudden or unexpected change that makes a situation develop in a different way(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学术与辞书部,2010:1789)。而Collin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则将“turn”解释为:1. a change or reversal of direction or position;2. deviation or departure from a course or tendency(Hanks,1989:1564)。可见,“转向”一词主要指方向、趋势甚至是本质的重大改变。学科的转向则意味着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的转换与革新,它意味着彻底的改变,且“往往产生矛盾、混乱,导致抵触和激烈争辩”(Snell-Hornby,2009: 42)。斯内尔-霍恩比进而指出:研究方式、策略、材料的简单变化并非研究的转向(Snell-Hornby,2009: 42)。事实上,转向并不限于翻译学科,也是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如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文艺学的人类学转向等。至此,我们再来审视上文提到的各种翻译学转向,不难发现,它们并未带来翻译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的转换与革新,只不过是人们解释翻译现象的不同角度,这显然只属于研究视角的变化,而不是真正的研究转向。例如,“权力转向”首次出现在铁木志科与根茨勒合编的《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2002)一书中。在序言里,编者提出:翻译不仅是语言间的转换,一切翻译活动的背后都有权力在操纵,反之翻译又构建起特定的文化权力机构。权力因素已成为探讨翻译历史和翻译策略的中心话题,是推动翻译研究的真正动力。而“译者就与作家和政客一样,参与到了创建知识和打造社会这种权力行为中来了”(曾文雄,2007:xii)。诚然,权力因素是翻译研究的重要主题,但它仅仅是所有诸如意识形态、文化身份等主题中的一员,并未改变翻译学者的共有信念、基本理论和研究手段,且并未呈现雄踞译坛的趋势,因此连转向的前奏都算不得。再如陈月红(2015)在“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新视角——论汉诗英译中的生态翻译转向”中提出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生态转向”。她认为:通过生态翻译,中国传统的自然观被移植到美国现代诗歌中,且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以费诺罗萨(Fenollosa)和庞德(Pound)为开创者的美国生态诗歌。这些诗人们努力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东方有机自然观移植到西方,引领了中国古典诗歌生态翻译的走向,并对后来西方环保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陈月红,2015)。通读全文,笔者虽然了解“生态”这一实指概念对翻译的影响,却并未窥见古典诗歌翻译进行“生态转向”的方式与路径。
概之,多数转向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历史证据,而转向的泛滥归咎于部分学者对其实质的一知半解和对术语的机械套用。那么,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何以可能?
4.从翻译技术研究到翻译研究技术
2014年8月4至6日,国际翻译联盟(FIT)主办的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在德国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 Berlin)召开。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翻译工作者与术语学家的未来(Man vs. Machine-The Future of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and Terminologists)”,预示着翻译技术时代的来临,也凸显了翻译研究中技术的重要地位,为全球广大翻译学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契机。
翻译技术(translation technology)指“应用于人工翻译、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的不同类型的技术手段,包括文字处理软件(word processors)和电子资源(electronic resources)等计算机信息处理工具,语言库分析工具(corpusanalysis tools)和术语管理系统(terminology management systems)等专用翻译工具”(Bowker,2002:5)。翻译技术涵盖了计算机辅助翻译和机器翻译(Chan,2015:xxvii)。翻译技术的历史不长,但发展迅速。上世纪4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问世后,语言学家和计算机学家们开始尝试利用计算机进行字词和文本翻译。1954年,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Leon Dostert和IBM公司的Peter Sheridan利用IBM701计算机将俄语句子翻译成了英语。这被视为机器翻译的里程碑(Chan,2004:125)。同年,麻省理工学院(MIT)创立了第一本翻译技术研究杂志Mechanical Translation。到1965年,世界上多个国家介入了翻译技术研究,它们包括:美国、前苏联、英国、日本、法国、西德、意大利、前捷克斯洛伐克、前南斯拉夫、东德、墨西哥、匈牙利、加拿大、荷兰、罗马尼亚和比利时等(张政,2006:30)。然而,翻译技术研究在60年代后期遭遇挫折。1966年,美国语言自动化加工咨询委员会(ALPAC)在一份题为“语言与机器:翻译和语言学中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报告中指出:“机器翻译在可预见的未来前景渺茫”(ALPAC,1966:32)。至此,翻译技术研究热潮告一段落。而近二十年来,得益于计算机科学、计算机语言学、术语研究、多媒体、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快速发展,翻译技术也迎来了黄金发展期。Trados、Dj Vu、MemoQ、Trans Type、Yaxin等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Google Translate、Flitto、TryCan、Onesky等翻译平台,移动设备语言翻译软件等翻译技术产品大大提高了翻译效率,带来了诸多便利,因此它们在翻译公司和跨国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也受到了职业译员和普通用户的青睐。实际上,翻译技术在文学翻译中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毫不夸张地说,“技术无处不在”(张霄军 贺莺,2014)。与此同时,翻译技术研究正逐步占据翻译研究的中心位置,翻译过程研究(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译文质量评价(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译后编辑(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翻译管理(translation management)、云翻译(cloud translation)、翻译记忆(translation memory)、本地化/全球化(localization/globalization)、语音翻译(speech translation)、语义索引(meaning access index)、信息检索与文本挖掘(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text mining)、语言代码与语言标签(language code and language tag)、词性标注(part of speech tagging)、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计算词典编纂(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y)、在线翻译(online translation)等课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笔者通过Taylor &Francis数据库①该数据库收录了国际翻译学界数十种主要学术期刊,检索时间为2016年9月1日。定位至Perspectives和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两种期刊②这两种翻译学期刊并不以翻译技术研究为重心。,并以“translation technology”为主题词分别进行期刊站内检索。结果显示,前者以“translation technology”为主题的论文达253篇之多,而后者也有107篇。由曼彻斯特大学Mona Baker教授和伯明翰大学Gabriela Saldanha博士编著的《翻译学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第二版)(2009)收录的翻译技术类词条多达十余条,包含了“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CAT)”、“Machine translation”、“Think-aloud protocols”等,足见翻译技术研究的重要地位。2015年,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陈善伟教授编著的《翻译技术百科全书》(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该书分三部分,分别是“翻译技术一般性问题”、“翻译技术在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及“翻译技术专题研究”,各章节作者是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西班牙、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南非、日本等国家的著名翻译学者、语言学者和计算机学者。全书体系宏大、论证严密,集中展示了翻译技术研究的主要成果,也凸显了技术维度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和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包括王士元、钱多秀、刘洋等在内的多位作者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体现了华人在这一领域的优势。
与翻译技术研究快速发展相伴的是翻译研究技术的不断革新。在现代信息技术、神经学、心理学等不断介入的背景下,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实证性与综合性愈发突出,而创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模式层出不穷。语料库(corpus)、眼动追踪(eye-tracking)、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brain potential,简称ERP)、键盘记录(key-logging)和多元互证模式(triangulation)等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在翻译教学、翻译过程研究、译者认知心理研究、机器翻译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5.技术型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是“研究者运用具体研究方法时遵循的基本框架与理念”(孟春国 陈莉萍,2015),它代表了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等的总和(徐浩 侯建新,2009:2)。半个多世纪以来,翻译研究历经萌芽、形成、发展、高潮、低迷等阶段。期间,其研究范式发生了许多变化,经历了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多元范式等(刘性峰 王宏,2016)。当前,研究技术发展迅猛,传统研究范式受到巨大冲击,正发生“裂变与重构”(费伟,2016),传统的翻译研究者多囿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文化维度,进行案本研究,并未充分意识到全球化、信息化、商业化时代技术在翻译研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传统的翻译理论也很难描述和阐释新型的翻译活动。无论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全球范围内翻译研究范式正在并将持续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技术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5.1 语料库翻译研究
语料库翻译研究(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y)指:“在研究方法上以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为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对翻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的研究”(王克非黄立波,2007)。语料库的介入可以为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架起一座桥梁,促进翻译教学及译员培训中的描述性语言研究(Chan,2015:465),且使定量的翻译研究成为可能。Mona Baker(1993)的论文“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被视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滥觞之作,而她于1995年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可比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二十余年来,语料库翻译学经历了从研究途径到方法论,再到一种新研究范式的发展过程,取得了可观成绩(黄立波 王克非,2011)。语料库建设、译者风格、语言特征、翻译规范、术语研究、翻译教学、视听翻译和口译等研究领域不断取得进展。国际方面,John Benjamins出版社过去十年间出版的以“语料库翻译”为主题的专著达二十余本③该出版社以出版人文社科类,特别是语言研究类专著闻名,数据来源于John Benjamins出版社官网:https://www.benjamins.com/#hom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等专门期刊纷纷创立。国内方面,《语料库翻译学概论》(胡开宝,2011)、《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研究》(黄立波,2014)、《双语对应语料库与学生译者翻译能力研究》(朱玉彬,2015)等专著陆续问世。虽然国内还没有专门的语料库翻译学学术期刊,但相关研究论文与年俱增。笔者以“语料库”和“翻译”或“口译”为主题词,对CNKI全部期刊进行检索,共得到有效论文1548篇①检索时间为2016年9月3日,剔除了期刊目录、书讯、稿约等无效数据。,足见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程度。数据显示,王克非、胡开宝、李德凤、黄立波、戴光荣、刘泽权、胡显耀等学者的发文数量较多,论文引用率较高,是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的领军人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克非教授是国内语料库翻译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关于语料库研制、应用翻译研究等的多篇论文成为国内相关领域引用频次最高的文献。澳门大学的李德凤教授也颇有建树,他的多篇语料库翻译研究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等翻译研究顶级国际期刊。可以预见,语料库翻译学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其实证性和跨学科性将不断增强,多语种的多重复合对比模式将进一步发展。
5.2 跨学科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是以客观事实、经验观察和实验数据为基础的研究,研究者采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个案观察、收集数据和客观描述,分析现象、发现规律,从中归纳得出结论,从而实现研究目的(苗菊 刘艳春,2011)。实证研究的介入已证明是翻译学学科演进的重要里程碑,其意义在于揭示所有制约翻译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在于提高翻译研究的预见性(Toury,1995:221-222)。1986年,德国学者奎因斯(Krings)以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csson)和西蒙(Simon)创立的“有声思维法”(Think Aloud Protocol)进行了第一例个案翻译研究(“Was in den Kpfen von bersetzern vorgeht译者的大脑中发生了什么”)(Ferreira & Schwieter,2015:5)。上世纪末以来,翻译学与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的结合,为翻译研究开拓了全新视野。最近十年,翻译研究的“科学化”趋势愈加突出,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跨学科的实证研究范式已经建立。方法论方面,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合理性、应用性和局限性等得到广泛探讨,理论依据得到深入论述;研究技术上,采用了科学的技术软件,加强了实验生态环境的合理性、真实性,研究内容更能反映社会翻译实践。增加了获取内省数据的有效途径,确定了互补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提供了翻译过程量化的客观数据,尤其重要的是减少了实验对有声思维法的依赖,从而减少了对受试者的一定干扰和研究者的心理负担。翻译实证研究的主题已明确:通过描写研究翻译过程,从中认识译者的思维状态和操作策略,研究译者的认知能力和专业/职业技能,从而提出发展翻译教学、加强译者培训的建设性意见。因此,翻译能力的构成研究与翻译专业/职业技能研究已成为应用翻译研究的重点内容(苗菊 刘艳春,2011)。虽然国内的翻译实证研究发展较为滞后,但近年来也涌现出一批优秀学者。如范勇(2011,2012,2015)在新闻翻译和王文宇(2013,2014)在口译培训方面开展的实证研究就颇具开创性与示范性。
6.挑战与对策
随着全球化、商业化、技术化、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沟通方式和科学研究方式都在经历着变革。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大数据、云翻译等概念以及它们承载的翻译技术正猛烈地冲击着以人为主体的传统作坊式翻译,甚至翻译的定义也面临重构。而传统的翻译研究囿于文本的语言和文化维度,“已经落后于翻译活动的发展,传统的理论已无法解释、更不能指导当今的翻译实践”(廖七一,2015)。适应新的研究形势,不断革新研究方法,探索新的研究路径,是任何一门学科永葆青春的不竭动力,翻译研究亦不例外(喻锋平,2012)。翻译研究必须拓展其研究对象,更新其研究范式。正如上文指出,当前的翻译技术发展迅速,翻译研究技术也不断取得突破,推动了技术型研究范式的建立。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已经发生,并将持续深入。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催生了新的研究课题,也为研究者带来了更多挑战。
首先,需要重新定义翻译研究这个学科。范式的演进必将导致翻译“本质”认知的转变。我们不得不“老调重弹”,回答以下问题:什么是翻译?它更多的是一门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还是自然学科?2015年3月28-29日,《中国翻译》和《东方翻译》杂志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办了“何为翻译——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高层论坛,其主旨是重新审视当下翻译技术背景中的翻译,与会者围绕翻译的定义进行了深度、全方位的思考与讨论(傅敬民 谢莎,2015)。其次,需要对翻译实践及研究中的方法、概念、模式作出修正并进行理论化提升,并最终形成自身的“原发性”理论。正是由于翻译学理论上过度依赖其他学科,才导致它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性脆弱不堪。最为重要的是,翻译研究者应当转换思维、更新观念。恰如廖七一(2015)精当的概括:“翻译研究理应积极面对飞速发展的语言服务与跨文化交际现实,对译介的重大问题作出客观有效的描述与解释,而不是要求丰富多彩的译介活动服从传统或陈旧的翻译观念”。同时,翻译学者还应拓展视野与知识面,努力掌握新的研究手段与方法,关注现实生活、科技发展及社会需求。一味地拘泥于文学翻译,对非文学翻译、口译置之不理,必将落后于时代;一味地沉溺于书斋式的传统研究,对新概念、新技术、新范式充耳不闻,无异于作茧自缚。
最后必须指出,任何理论的构建,都是面向特定的社会素材,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完成,这一构建过程又必然受制于研究者的知识基础和志趣。翻译研究“技术转向”的构建亦然,它是技术时代的产物。然而,它并非否定和排斥翻译中的人文因素,而是人文与科技的共生共融。“技术转向”更不同于技术主义,前者是研究对象和范式的变革,而后者流于泛技术、唯技术的极端倾向,值得警惕。
7.结语
本研究首先回顾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阐释了其陷入理论和现实困境的缘由。接下来,笔者对新世纪伊始至今各种所谓的“转向”进行了分析与批评,指出它们并非真正的研究转向,而是不同的研究角度。接着,我们梳理了翻译技术研究和翻译研究技术的发展脉络,阐述了两种技术型研究范式,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翻译研究“技术转向”概念。我们认为,翻译研究“技术转向”的深入将为研究者带来更多研究课题和新的挑战。文末,笔者提供了应对“技术转向”的策略。而技术时代的翻译美学、翻译哲学、翻译伦理等更多问题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
本文提出翻译研究“技术转向”的概念,实为笔者不揣谫陋的大胆尝试,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1] ALPAC. 1966. Languages and Machines: Computers in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R]. Division of Behavioral Scienc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shington, DC.
[2] Baker, M. 1993.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A]. In Baker, M. Francis and E. Tognini-Bonelli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 Baker, M. & G. Saldanha. (eds.). 2009.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econd edi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4] Bassnett, S. 2001. Cultural Construction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5] Bowker, L. 2002.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Technology: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6] Chan, Sin-wai. 2004.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7] Chan, Sin-wai. (ed.). 2015.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8] Conway, K. 2012.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pproach to cultural translation [J]. Translation Studies, (3):264-279..
[9] Ferreira, A. & J. Schwieter (eds.). 2015. Psycho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Inquiries into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0] Hanks, P. 1989. Collin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Z]. London: Collins.
[11] Holmes, J. 1972.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A]. In Holmes, J. (ed.).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C].Philadelphia/Amsterdam and Atlanta: Rodopi.
[12] Katan, D. 2016. Translation at the cross-roads: Time for the transcreational turn? [J]. Perspectives, (3):365-381.
[13] Loffredo, E. & M. Perteghella. 2006. Translation and Creativity:Perspectives on Creativ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Continuum.
[14] Nida, E.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E. J. Brill.
[15] Pym, A. 2001. 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J].The Translator, (2):129-138.
[16] Snell-Hornby, M. 2009. What's in a turn? On fits, starts and writhings in recent translation studies [J]. Translation Studies,(1):41-51.
[17]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8] Tymoczko, M. & E. Gentzler. 2002. Translation and Power[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 Vinay, P. & J. Darbelnet. 1958.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cais et de L’anglais [M]. Paris: Didier.
[20] 蔡平.2005.“文化翻译”的困惑[J].外语教学,(6):75-78.
[21] 陈月红.2015.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新视角——论汉诗英译中的生态翻译转向[J].外语教学,(3):101-104.
[22] 恩斯特·卡西尔.2004.人文科学的逻辑[M].沉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3] 范勇.2011.美国主流媒体表达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显异策略——基于对2009 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实证研究[J].上海翻译,(1):65-69.
[24] 范勇.2012.美国主流媒体上的“中国英语”样本分析——基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2009-2010)的一项实证研究[J].中国翻译,(4):112-116.
[25] 范勇.2015.英语国家受众对中国当代政治宣传语官方英译文接受效果的实证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3):92-99.
[26] 费伟.2016.翻译研究的传承与创新——《翻译学研究方法论》评介[J].外国语言文学,(2):137-143.
[27] 傅敬民 谢莎.2015.翻译技术的发展与翻译教学[J].外语电化教学,(11):37-41.
[28] 傅勇林.2001.译学研究范式:转向、开拓与创新[J].中国翻译,(9):5-13.
[29] 胡开宝.2011.语料库翻译学概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30] 胡牧.2011.翻译研究:超越“文化转向”[J].江苏社会科学,(4):176-181.
[31] 黄德先 杜小军.2008.翻译研究的现实转向[J].上海翻译,(3):18-21.
[32] 黄立波.2014.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33] 黄立波 王克非.2011.语料库翻译学:课题与进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6):911-923,961.
[34] 姜艳.2006.论翻译的文化转向对翻译本体论的消解[J].上海翻译,(3):12-14.
[35] 廖七一.2015.范式的演进与翻译的界定[J].中国翻译,(3):16-17.
[36] 刘军平.2008.重构翻译研究的认知图景,开创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4):88-93.
[37] 刘性峰 王宏.2016.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嬗变、问题及对策[J].外语研究,(2):87-91.
[38] 罗新璋 陈应年编.2009.翻译论集(修订本)[C].北京:商务印书馆.
[39] 孟春国 陈莉萍.2015.走向多元融合的研究范式——中外应用语言学与外语教学期刊的载文分析[J].外语界,(1):2-11.
[40] 苗菊 刘艳春.2011.翻译实证研究——理论、方法与发展[J].中国外语,(6):92-97.
[4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学术与辞书部.2010.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四版)[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2] 王克非 黄立波.2007.语料库翻译学的几个术语[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6):101-105.
[43] 王宁.2009.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44] 王文宇 黄艳.2013.语块使用与口译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7):28-35.
[45] 王文宇 周丹丹.2014.口译笔记内容与口译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115-121.
[46] 夏维红 年丽丽.2013.译者现身:以德里达“延异”概念探讨翻译研究的译者转向[J].语言教育,(2):74-79.
[47] 谢天振.2008.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48] 徐浩 侯建新.2009.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9] 徐剑.2007.当代翻译研究的显性转向与隐性转向[J].云梦学刊,(1):139-141.
[50] 喻锋平.2012.国内外翻译研究转向及范式转换综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78-81.
[51] 曾文雄.2007.语用学翻译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52] 张霄军 贺莺.2014.翻译的技术转向——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侧记[J].中国翻译,(6):74-77.
[53] 张政.2006.计算机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54] 朱玉彬.2015.双语对应语料库与学生译者翻译能力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On the “Technological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onstant renewal of research method and concept is essential to the advancement and vitality of any academic subject.At present, translation practic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trend of localization, globalization , technic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Accordingly, the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paradigm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undergoing reconstruc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Against this complex backdrop, “cultural 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 becomes more and more problematic in that it cannot solve lots of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firstly summarizes the major tur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of all kinds,based on which the author further analyzes several newly developed research paradigm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ical turn”. Moreover, the necessity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technological turn”are discus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research paradigm; technological turn
H059
A
2095-4891(2017)04-0073-07
刁洪,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通讯地址:400067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19号 重庆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