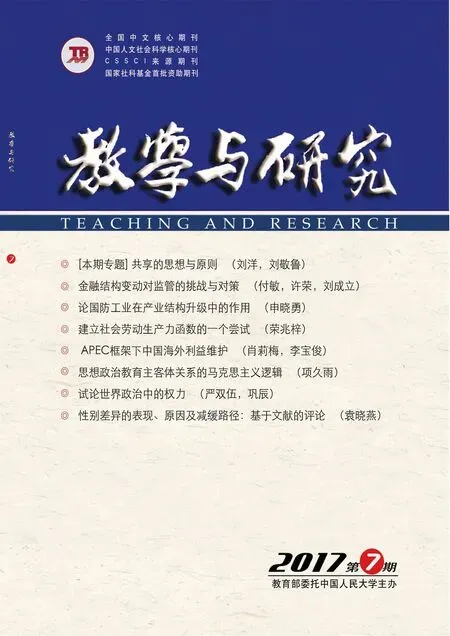命运与期望
——论蒂利希的“无产阶级处境”理论
命运与期望
——论蒂利希的“无产阶级处境”理论
于涛
蒂利希;“无产阶级处境”;新教原则;抗争与期望
蒂利希认为在现时代,几乎整个人类都陷入一种无产阶级式的焦虑不安的生存处境,即他所言的“无产阶级处境”之中。为了说明这一点,蒂利希综合多种理论资源,试图以新教原则的先知性批判作为克服这一扭曲状态的武器,以此来重塑人们对于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迎接未来无阶级社会的期望。
社会阶级的存在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既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深刻的理论问题,也是随着社会变化而不断变幻其表现形式的复杂的现实问题。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理论的兴起,一些西方学者就曾围绕着阶级的消逝与否和划分标准等展开了一场至今仍余波荡漾的争论。但从今天来看,这场争论似乎已经预示着阶级理论的衰微,在此之后,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研究社会分层结构的学术范式日益被边缘化,阶级叙事在社会话语空间中也逐渐被现代性批判所置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随着全球性的经济下行和两极分化、阶级分化乃至阶级固化的现象再次成为大多数人的基本日常生活体验,阶级理论才不仅仅是以一种学术传统的单纯姿态,更是作为人们审视当今时代的基本视角复归于网络和媒体的视野中。不过,阶级理论在以往的各种争论、解构和遗忘中早已凋零、面目模糊。于是,人们在阶级理论的“博物馆化”与阶级体验的日常化之间,既感受到了由于阶级分析缺失所导致的解释空白,也不乏对阶级所携带的对抗性因素的重重顾虑,而这就涉及本文借以展开和所要评析的核心问题,即“无产阶级处境”问题。
所谓“无产阶级处境”是德裔美籍宗教哲学家保罗·蒂利希在二战前后提出的一个理论,其在《社会主义抉择》(TheSocialistDecision, 1933)、《历史的诠释》(TheInterpretationofHistory, 1936)、《新教时代》(TheProtestantEra, 1956)、《政治期望》(PoliticalExpectation, 1971)等著作都进行了论述和阐释。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几乎在整体上已经陷入到了一种无产阶级式的生存状态,即所谓的“无产阶级处境”之中。对此,蒂利希结合自身独特的学术背景,融合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弊端展开了深度批判。他认为,帮助人类走出“无产阶级处境”的主体力量正是无产阶级自身,而分析这一历史进程的方法则是“新教原则”。
一、现实社会中的人类命运——“无产阶级处境”
保罗·蒂利希是20世纪前半叶著名的存在主义宗教哲学家,同时他也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学者。他早年对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他的社会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对他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他直接吸收了马克思的理论。其中,他提出的“无产阶级处境”理论就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语境中关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阶级,因而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片面的解放,而是意味着“人的解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分析和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任务,同时也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现实处境。如《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1](P279)工资不过是“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额数”;“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1](P280)“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1](P284)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丧失生产资料和自由地出卖劳动力是无产阶级的根本特征。在这个问题上,蒂利希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其成员以完全依赖的自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并且他们的社会命运完全取决于市场运作的境遇。这一定义的前提是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以完整地依赖市场的机遇”。[2](P164)
不过,蒂利希认为,这种建立在“经济还原主义”基础上的理解虽然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将始终有效,但也不能忽视资本主义在具体发展阶段上的具体情况。在蒂利希生活的那个时代,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启和战后全球经济的新一轮起飞,以及福利国家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推行,社会中专门依靠单纯出卖劳动力来获取生活资料的无产者正在大幅度减少,大量白领职业人员,如职业经理人和高新技术从业者等社会中间群体的涌现日益模糊着不同阶级之间的身份;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力量从阶级政党转向了技术资本,导致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淡化和个人身份来源的多元化,这与资本主义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呈现出来的“温和统治”、“匿名统治”、“非政治化倾向”相吻合,从而使传统的理论框架面临重重挑战。基于此,蒂利希没有像后来的一些理论家那样选择修正无产阶级的概念或划定标准,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思路,即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异化理论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转向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中,蒂利希以一位宗教哲学家和存在主义者的视角揭示了无产阶级似乎日趋消逝的表象下,无产阶级式的生存处境却愈发弥漫的现实。
蒂利希认为,作为描述当代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无产阶级处境”概念,就是构成早期无产阶级生存处境的那些基本特征,如动荡不安、俯首听命、精神紧张、空虚倦怠等,在现时代的四处延伸和弥漫。蒂利希将这些特征称之为“生存性焦虑”,使之几乎成为对整个人类生存图式的形象化表达,并把这种“生存性焦虑”归结为人类的原罪所导致的“存在的扭曲”。在蒂利希的理解中,人作为一种能反观自身的存在物,在进行对象化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具有创造性和自由性,另一方面又具有有限性和受动性。而在现代社会中,前者表现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实现的对自然的征服和物质财富的巨量增长,以至于把技术理性横行世界和上帝已死视为人类的福音;后者则表现为技术理性和资本逻辑对人的无所不在的统治,以至于沦入丧失自我的异化状态和空虚、无奈、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境地。因而人的存在的创造性、自由性的无限膨胀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受动性的深度“坍缩”是同构的。这种一体两面的存在特性构成了人类悲剧性命运的根源,也就是说,当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发生结构性扭曲时,人的存在事实上陷入“无产阶级处境”之中。[2](P164)这就是所谓“生存性焦虑”。对此,蒂利希在《社会主义中的人与社会》一文中曾指出:“在社会现实中,每个人的安全都被剥夺和践踏。而现在人们缺乏这种安全的原因就是我们当代人难以克服的灵魂焦虑和烦恼的力量在作祟。人们生活在有限中,那么在有限的自由中就存在着本质性焦虑。这种焦虑无法被克服,除非我们能够具有超越悲惨命运的无限意义。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的焦虑,它被认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焦虑并一直处于将被排除的恐惧之中,例如永久性失业带给人们的无意义感”。[3](P497)
在蒂利希看来,“生存性焦虑”就是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处境”的本质,它是由非存在的恐惧所带来的生命本体、道德本体和精神本体三个方面的焦虑构成。其中生命本体焦虑源于人对自身有限性存在的焦虑,道德本体焦虑源于人对罪恶和谴责的焦虑,精神本体焦虑源于人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三者同出而异名不仅直接体现出20世纪西方文化的深层危机,也戟指各色各样的经济危机、战争危机、生态危机等。这样,蒂利希就从本体论意义上的原罪说过渡到“生存性焦虑”的叙事逻辑,这虽然明显带有宗教语境的瑕疵,但他在这个语境中也感受到了“后阶级时代”人们心中的隐痛和人的存在的“无产阶级化”的现实。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上看,在以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为主导的历史时期,标准化流程、流水线作业、大规模生产虽然使人成为整个社会机器中一个零件,从而按照同质化逻辑异化为失去个性的抽象存在,但相对于经济的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这种异化尚且还在可以忍耐的范围之内,而当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刚刚走出经济困顿没多久,当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宣布历史终结时,无产阶级又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在新的经济和技术变革下再次败下阵来。此时的“无产阶级”一边行走于财富横流的世界,一边已经不得不从中产阶级的迷梦中醒来。一方面,担心失去目前的生活水准,恐惧经济困窘的污名化,害怕跌出时代发展的大潮;另一方面,面对技术理性的横行和资本逻辑的统治又缺乏实现个人价值的自信和勇气。这种充斥着焦虑、无力、混乱、茫然的处境与劳作在19世纪手工工场中的无产阶级相比,除了更加丰富的商品体验之外,似乎并无本质的区别和改变。
从蒂利希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无产阶级生存处境的描写是直接揭露无产阶级的异化处境,以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那么蒂利希对“无产阶级处境”的刻画则是用一种神学话语将“无产阶级处境”解释为人类原罪的现代遭遇,并从哲学上将其理解为一种脱离存在的人性“魔魅化”(demonic),即在历史中发生的人类自身本质从内在到外在的异化。[4](P80-102)其目的是为了剖析现代社会人们所普遍经历的这种生存性焦虑和困境,从而试图找到可以破解它的终极办法。为此,蒂利希运用新教原则对“无产阶级处境”进行批判,以期激发起人们对自身现实存在处境的反抗和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
二、新教原则对“无产阶级处境”的批判
蒂利希所提出的新教原则,就是在近代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在批判传统天主教时所形成的一种批判性、超越性原则。在蒂利希看来,新教原则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与深受宗教改革精神影响的德国古典主义传统融合的产物,它虽然继承了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但不像笛卡尔那样必须绕道上帝才能避免进行普遍怀疑的“我”陷入“唯我论”,而是通过扬弃实体性的上帝,只将其视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同样,新教原则也不同于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用现象隔绝了精神与存在,使精神与存在分离并使前者在事实上高于后者;而新教原则的实质则是“先知性批判”,即对包括宗教、权威、理性在内的一切现实和精神事物的终极批判。换句话说,新教原则本身并不是一个依赖宗教和理智力量的宗教观念,而是随着新教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不断完善化、系统化的“内在永恒性准则”;[2](P12)新教原则立足终极、诉诸实践,旨在通过对超自然的、神秘主义的、教条化的、“魔魅化”的信仰的反抗,使人们重新建立起对未来的期望。
蒂利希希望通过新教原则来超越一般宗教及其历史形式,从而使这一原则成为通行于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哲学尺度。他指出:“它(新教原则)通过超越一切文化形式而超越了它自身。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在这些形式之中,它是在这些形式中的一种活生生的、运动不息的力量;它就是以一种特定方式被设定在历史新教之中。……它包含了一种对任何抽象的相对性现实的人文和神圣的反抗……新教原则就是对包括自称‘新教’在内的一切宗教和文化现实的评判。”[2](P163)
从蒂利希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提出的新教原则试图把被设定在宗教中的终极维度引入现实,从而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将无限和有限的关系展现出来,凭借一种无限的存在性深度来审视一切现实,通过超越现实的有限性存在走向无限性存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教原则是对有限性在思想和行动上僭越无限性的反抗,在宗教上表现为“反对教会的独一性傲慢”,在社会中则体现为“反对世俗事物的神圣化”。[2](P163)因此,新教原则也可以被用来批判新教本身,因为在新教原则那里,新教只是基督教的一个发展阶段,同样也应该是接受新教原则批判的对象。如此一来,新教原则不断否定的批判性就与无产阶级的批判性达成了形式上的共识。关于无产阶级的批判性,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大量的相关论述,如“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身”;[1](P16)“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5](P272)“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6](P409)等等。在蒂利希看来,无产阶级把消灭阶级作为消灭自身的基础,这与新教原则对历史中的新教和对“无产阶级处境”的批判是一致的。基于这个理解,蒂利希并没有进而去分析无产阶级如何在新教原则的指导下克服“无产阶级处境”,而是从逻辑上把新教原则的批判性做了进一步延伸,使之达到对人的本质的整体论理解。一方面,蒂利希认为新教原则在宗教上继承了宗教改革对传统天主教的肉体精神二元论的批判,同时在哲学上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哲学关注超验世界与抽象人类的传统,主张将人的物质和精神、整体存在和具体体验统一起来,从现实的维度和存在的深度中去体察扭曲人类的生存处境。另一方面,蒂利希指出,新教原则明确反对那些具有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对人的个人主义理解。在他看来,尽管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个体从类的意义上讲都毫无例外地属于人类整体,但现代社会的普遍异化决定了每个特殊个体都无法把自身置于现实世界之外。当然,这并不是说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不能遗世独立,在自己的世界中获得自身存在的圆融和生命的价值,但个人主义对个体独立存在价值的崇尚以及对个体存在的差异化的鼓励往往只具有审美的意味,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容易造成思想的撕裂和社会的离析。因此,只关注自身的自由意志尚不能称为真正的、积极的自由意志,因为这种自由意志把个人从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中剥离出来,从而在本质上背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
通过对人的本质的整体理解和辩证解读,蒂利希使新教原则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要求达到了一致。他认为,作为“无产阶级处境”的主要体验者,无产阶级不仅代表着现实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较之其他阶级对自身的存在现实有着更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改变期望,因而是克服“无产阶级处境”的主体力量。
当然,从总体上看,蒂利希对人的理解并未达到马克思的高度。马克思将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并分别从自然存在物、类存在物、自由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维度对人的本质进行界定和说明。相比之下,蒂利希对人的存在主义式的理解就显得单薄得多;并且,蒂利希主要关注的是人在人格和精神层面上的扭曲及其扬弃,而马克思则将目光投注到现实的人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全面异化及其扬弃。因此,在理解无产阶级的处境和无产阶级解放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批判更为深刻。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谈到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时指出,这种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1](P14-15)
蒂利希注重从人的类特性层面,即从人的精神生活和信仰层面理解“无产阶级处境”并试图找到摆脱这一处境的突破点。这样一种思考使“无产阶级处境”这个概念更具有存在论的内涵,显示出他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度忧虑。这对于我们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处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哲学维度。但是,如果避开对造成“无产阶级处境”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现实批判,那么,这样一种思考依然会陷入有关人性异化的抽象议论,或者停留在“精神拯救”的空谈中。
三、人类的命运抗争与历史期望
蒂利希对“无产阶级处境”的颇费周章的论证乍一看不免使人心存疑窦,因为就他主要活跃的历史年代而言,即使不考虑无产阶级解放和左翼政治运动早已全球开花的历史背景,在1945年至1975年这一左翼知识分子主导西方思想界的“光荣三十年”,蒂利希对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变革主体的说明不仅相对滞后,并且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他的理论也显然不如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明了、尖锐、透彻,而是显得相当晦涩抽象。对于这种疑问,笔者认为应将蒂利希的“无产阶级处境”理论置于更广阔的时空之中,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穿过其宗教话语编织的神秘外衣,看到蒂利希思想的深沉之处。
从历史发展上看,自从无产阶级成为自为阶级,其在近两个多世纪的命运抗争中呈现出三种迥然不同的图式。第一种是跳出资本主义的周期律,亦即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挺进无阶级社会;第二种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发展红利中分一杯羹,跟随社会进入所谓“良性循环”:信心鼓舞→资本聚集→市场繁荣→政府收入增长→社会福利增加→就业充足→工资收入增长→消费能力和受教育水平提高→无产阶级中产化;第三种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下行时期率先利益受损,跟随社会进入所谓“恶性循环”:信心受挫→资本逃逸→市场萎缩→工作外流→岗位减少→收入降低→支出增加→消费停滞→债务缠身→中产阶级无产化和无产阶级赤贫化。其中,无产阶级的第一种命运图式在当代仅存在于极个别国家之中;第二种存在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个别历史时期,如前文提到的以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种则大范围地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如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蒂利希的理解,如果运用新教原则批判性地看待后二者,那么这二者的差别不过是为面包和房租而焦虑,还是为了牛肉和房贷而焦虑的形式差别。无产阶级的这两种命运并无实质的区别,因为不论是这二者中的哪一种,无产阶级面对资本、市场的波澜起伏而变动不居的命运和束手无策的处境都并没有实质改变,资本主义结构性的弊端也并无改变。
面对这种情况,依照新教原则,无产阶级如何改变自身命运?对此,蒂利希将目光转向了对期望的分析。蒂利希认为,期望是包含着认知与实践、蕴含着批判性和超越性的人的一种生存维度。一旦无产阶级形成改变自身命运的集体自觉和期望,无产阶级便会产生一种超越现实、实现期望的准宗教热情。在蒂利希看来,具有准宗教热情的期望是新教原则运用于理智层面的表现,如果这种期望无法唤起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感,无产阶级作为变革历史的主体就会被历史的辩证法所淘汰,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产生一种超越现实的历史性期望并同时感受到使命感的召唤,这就将意味着“一个具有完美理性的新世界时代”的开启。[2](P175-176)
但是,在对期望的进一步分析中,蒂利希紧接着又表现了自己的顾虑和不安:“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统一,即对即将来临的事物的期望和要求的统一,是一种概念的统一,同时也是一种具体的改造。当它意识到一切具体期望的不确定性,意识到将每一种具体实现与期望的无条件实现隔开的距离,所以它不会落入彻底的毁灭;而对一切目的的毫无批判性的具体期望,则必然伴随着这种毁灭”。[7](P50)
言下之意,蒂利希认为任何期望都存在着神圣与世俗、理想与现实、否定与肯定相并存的结构。否定意味着期望有一种否定和超越现实的理想维度,而肯定则有着将期望对象化为具体之物并占有该物的现实倾向。在蒂利希看来,期望和期望的对象化倾向是一对与同一和差异相关联的范畴,这就像社会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一样,社会主义理想的神圣性可以激发人们的牺牲精神和行动热情,而社会主义实践的世俗性在资本主义时代则有着被庸俗化和乌托邦化的可能,也就是有可能使致力于创造新社会、新生活和新人的历史性运动被矮化为对发达资本主义生活风格的普遍模仿。对此,一方面,蒂利希仍坚持自己对期望的判断,强调新教原则的批判精神对期望的重要性,强调要防止无产阶级将改变人类命运的期望简化为宗教意义上的天国救赎或世俗意义上的乌托邦幻想;另一方面,蒂利希通过对他的“第三条道路”思想的阐释,以折中主义的方式完成了对社会主义期望的神圣与世俗的合题。所谓“第三条道路”是蒂利希的另一重要思想,简而言之就是将宗教理想与制度设计相结合,走一条兼具宗教的终极关怀和人道主义关怀的社会主义道路。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蒂利希思想的矛盾、抽象和不彻底之处,就像黑格尔所言:“因为狂热所希求的是抽象的东西,而不是任何有组织的东西,所以一看到差别出现,就感到这种差别违反了自己的无规定性而加以摧毁”。[8](P15)蒂利希所理解的期望终究是彼岸的、隐喻意义上的精神力量,而不指此岸的、实践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却将其终极关怀的基础筑基于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他以反对期望的乌托邦化作为自己的理论旨归,自己却又在理论建构时陷入乌托邦的期望之中。
通过对蒂利希的“无产阶级处境”和新教原则等相关思想的考察,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蒂利希以其独特的学术背景、敏锐的洞察能力和浓厚的宗教情怀,使他在看待无产阶级问题、剖析“无产阶级处境”时表现出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批判力;但客观地讲,由于蒂利希拘泥于对多个学术领域和不同学术流派的“视界融合”,沉溺于“自造概念”和黑格尔式的概念演绎,使他陷入到封闭的逻辑和抽象的泥淖之中,最终只是切中了时代的脉搏,而无法为自己的人类情怀和宗教关怀提供社会性的承担。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Paul Tillich.The Protestant Era[M].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7.
[3] Paul Tillich.Man and Societyin Socialism[A]. Main Works Hauptwerke,vol.3,Writings in Soci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C]. Edited by Erdmann Sturm. 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 Evangelisches Verlagswerk GmbH,1998.
[4] Paul Tillich.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M].New York:C. Scribner S.ons.LTD,1936.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Paul Tillich. Political Expectation[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1.
[8]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责任编辑孔伟]
FateandExpectation——AStudyonthePaulTillich’sTheoryof“ProletariatSituation”
Yu Tao
(College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Paul Tillich;“proletariat situation”; protestant principle; expectations
Paul Tillich believes in the present age,almost the whole of human has been caught in a type of survival circumstance of proletarian anxiety, that is the “proletariat situation” he said.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Tillich integrates a variety of theoretical resources, trying to use the prophetic criticism of protestant principle as a weapon to overcome this distorted state and in order to reshape people’s expectations of overcoming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stepping into the classless society in the future.
于涛,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天津3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