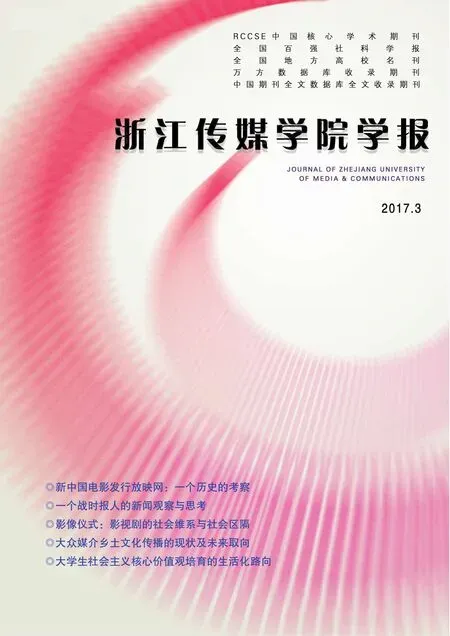一个战时报人的新闻观察与思考
——杜绍文《战时报学讲话》对战时新闻学的贡献
蔡 罕
一个战时报人的新闻观察与思考
——杜绍文《战时报学讲话》对战时新闻学的贡献
蔡 罕
文章分析了抗战时期《战时记者》主编杜绍文《战时报学讲话》一书对战时新闻学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1)探讨了战争与新闻学的关系,提出了“健全的新闻学”研究之构想;(2)论证了新闻是抗战的一种“新文器”,是制敌克胜的法宝;(3)呼吁制定新“新闻政策”,促成“一个民族一个意志一个舆论”的实践;(4)强调战时报人的职业操守,提出要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5)匡正战时新闻事业的缺失,揭示了抗战后我国报业的变化与发展;(6)分析了新闻的职能与特性,指明了“新闻纸”未来的发展方向。
杜绍文;《战时报学讲话》;战时新闻学
一、引 言
2015年7月2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了“抗战烽火中的复旦新闻人”座谈会,追忆“复旦新闻六君子”为中国抗战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受纪念的人物中,杜绍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杜绍文(1909-2003),广东澄海人。1927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曾留学任教,后在江苏镇江《苏报》《杭州民国日报》(1936年改名《东南日报》)任职。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随东南日报社迁至金华,任该报国际新闻版编辑,兼任“国际一周”专栏主任。1938年9月,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会刊《战时记者》创办,杜氏任主编。1940年1月,他离浙赴湘,任《湖南国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亲历了三次长沙会战。作为《战时记者》的第一任主编,杜绍文筚路蓝缕,为《战时记者》创办与如期刊出付出了心血。从创刊号(1938.9)开始至第二卷第5期(1940.1),他在每期刊首连续发表了《记者节与反侵略》等21篇文章,这些文章于1941年由战地图书出版社结集印行,取名《战时报学讲话》。拂去历史的封尘,当我们再次捧读此书时,我们不仅可以读出它远隔时空的学术价值,而且还能清晰地感受到抗战烽火中一代报人所跳动的时代脉搏,他们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对敌斗争的精神、抗战建国的爱国热情,以及他们的新闻理想。这里,笔者仅仅从新闻学的角度,谈谈杜绍文对抗战时期新闻事业的观察与思考,探究《战时报学讲话》对“战时新闻学”的贡献。
二、《战时报学讲话》对战时新闻学的贡献
所谓“战时新闻学”,是指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年代,我国新闻学界、业界的精英们对新闻事业所进行的“工具理性式”的思考与研究,“新闻救国”成为当时新闻研究的新方向,人们视新闻为武器,提出要开辟宣传与舆论战场,发挥新闻的“纸弹”效应;战时报人应该共赴国难,为捍卫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抗战烽火中应运而生的《战时报学讲话》,就是杜绍文针对抗战的形势发展与时局的需要,对战时新闻学与新闻事业所进行的专业思考与学理性的分析,这对于战时新闻学的建树与抗战新闻事业的指导均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战时报学讲话》的研读,笔者现将杜氏对战时新闻学的研究与贡献归结如下:
(一)探讨了战争与新闻学的关系,提出了“健全的新闻学”研究之构想
战争的环境下是否还能开展正常的新闻学研究,这是抗战开始后人们对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种学术前途的担忧。但是,杜氏却力排“战时不能研究学术”的悲观论调,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学术主张,他在《战争带来了健全的新闻学》等文章中,对战争与文化、战争与新闻学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论述。
首先,杜氏提出“战争是文化的肥料”的观点。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带有深厚的民族色彩。当战争爆发,外来的文化不断刺激着本国文化,势必会发生二者的斗争和交融。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好的文化将遭到淘汰,优秀的文化则得到继承与发扬。因此,战争有着“净化文化的作用”。它不但能“促进文化创造文化”,而且还可以“涤荡过去的陈腐文化,和淘汰不能适合环境要求的文化”。[1]正因如此,战争对于文化的发展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接着,杜氏批驳了“战时不能研究学术”的论调。许多历史事实证明,战时对文化的重视“尤甚于平时”。因此,“战时不惟不宜停止学术的研究,相反的,更须在炮声中,炸弹下,沙场上,地窖里,竞作各种学术的研究”。抗日一方面是“为维护我们锦绣的河山”,另一方面“即在维护我们珍贵的文化”。抗战的胜利,“即为中国文化的胜利”。“研究学术是一件不朽的事业,无论任何空间时间,其重要性永不会消失。”在杜氏看来,“前方的作战与后方的研究,有着同等的价值”。[1](18)
最后,杜氏提出“藉着战争的泥土,培养出一朵健全新闻学的奇葩,系新闻学者一件神圣的职责”。对于什么是“健全的新闻学”,杜氏在《新闻学能成立吗?》一文有过论述,他在分析了世界各国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后指出:当前世界的种种新闻理论,“均是有所偏颇,不能称为健全的体系”。“我们想象中的新闻学”,应包含下列几个因素:“它是综合的,集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于一炉;它是比较的,存优而去劣,留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它是前进的,不断自量的发展中,改进其品质,改善其内容与外观;它又是新颖的,站在时代的前锋,生生不息的新陈代谢着,做一切学问技术的先导者和模范者”。[2]笔者以为,杜氏“想象中的新闻学”,即是他理想中“健全的新闻学”。同时,杜氏就有效展开健全新闻学研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首先,“应运用国家力量,替有志于新闻学的人,设法解决其生活问题,让他们安心研究,然后根据这些研究的结果,再用政府的力量,推行于整个国家的任何角落”。除各大学设立新闻系外,国立中央研究院“宜加设一新闻学的研究所,招收新闻学的研究生”。其次,“新闻学论著的索引工作,须有一番广大、精深、详确的改造”。第三,要改变“交通不发达,教育不普及和经济不宽裕”的现状。此外,也要解决“政治的背景为之作梗”[1](20-21)的现象。
总之,“战争带来了健全的新闻学”的观点使我们看到了抗战时期一个新闻学者虔诚的专业理想。在“亡国论”甚嚣,“战时不能研究学术”的论调中,杜氏从战争对文化的净化作用出发,希望此次抗战能带来健全的且其学理“又须适于我们的国情”之新闻学,呼吁有志于献身新闻学的同志们,“要以加倍的努力,去实践这个合理的愿望!”[1](21)这无疑给当时的新闻界带来了一种坚持新闻学术研究的信心、勇气与希望,它赋予战时新闻学以智慧,给坚持抗战的新闻学者开启了光明的前景。
(二)论证了新闻是抗战的一种“新文器”,是制敌克胜的法宝
战时新闻学的一个重要而突出的观点是新闻“武器论”——新闻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一种战争工具。这种观点是新闻“工具论”在抗战时期的升级体现,它反映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新闻工作者以新闻宣传为武器,自觉地担负起“反侵略,谋自卫,求生存”的神圣职责,开辟抗战新战场的斗争气概。
首先,杜氏认为在现代战争中新闻(宣传)与经济、军事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现代战争已不是“军事上的单纯动作”,它需要经济、军事、宣传等方面的准备。在经济、军事、宣传三者之间,杜氏引用《孙子兵法》中“攻心为上”的观点,认为经济和军事固然是“战争中制胜的因素”,但是“其最后决胜工具,则有赖于报纸的宣传”。[3]在当时抗战的敌我力量对比上,我方“物质之准备不如人,军事之装备更不如人”,这就需要我方“以攻心的纸弹,俾济战场上子弹之穷”[3](51),充分使用“纸弹”的威力。这个“纸弹”就是报纸的宣传。杜氏认为,这颗“纸弹”之所以“力能挫暴”,其威力不在于火药和铅头,而是来自于“正义和事实”,“以正义制裁侵略,以事实揭破阴谋”。虽然敌人“在子弹上稍占便宜”,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在“纸弹方面”,他们“则大败特败”,[3](51)因为“全球爱好和平崇尚正义的人们,都站在我们这一边,援华反日的运动,更如火如荼普遍于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纸弹已经攻陷敌人的心房了”。[3](52)
其二,进一步充实了战时新闻学的“新文器”理论。在《新文器和新武器》一文中,杜氏首先提出并分析了“新文器”的威力不亚于“新武器”的观点。继而分析了新闻宣传这种“新文器”的结构,认为“新文器”由新闻事业、新闻记者、新闻教育等三个部分组成,“新闻事业系新文器的基干,新闻记者为运用新文器的兵员,而新闻教育,则是训练新闻记者的技术,使能制出一张力量较大之新闻纸,从而促进新闻事业的发达。”[4]从发挥战斗效用的角度来看,“新闻记者系新文器的战斗员,新闻教育系新文器的训练部,而新闻事业则一面系新文器的实习场所,一面又是新文器的作战疆场”。至于新闻政策,杜绍文则认为是“使用新文器的战略”。[4](64)最后,杜氏认为“新文器”可从“消极方面”与“积极方面”发挥其功效。消极方面,“为彻底摧毁敌对的势力”,可以“鼓吹有利于我的宣传”,“暴露敌人所有的弱点”,“争取第三者的对我同情,令进一步化同情为辅助”。积极方面,则可以“提高自己的信心,毅力和警觉性”;“瓦解敌方的内部”;“揭示我之必胜与敌之必败,助我之利与中立之害,使第三者无碍于我的中立,进至有助于我的帮忙。”[4](66)这些观点对于正确发挥战时新闻宣传的“纸弹”功效,均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其三,指出“纸弹”效应的发挥,“不重在消极的事后检查,而重在积极的事前推动”。为此,杜氏就如何“制造和应用这种纸弹”,提出了“宣传的原则要单纯,宣传的方法则要统一集中与普及”[3](52)的主张。“单纯、统一、集中、普及,系战时‘纸弹’的必要原料,缺乏这种原料,就减少了‘纸弹’的爆炸力和破坏力”。他还认为:“三十二条的抗战建国纲领,悉能吻合单纯、统一、集中、普及的宗旨,我们必须把纲领中的每一条,每一行,每一句,每一字,全部灌注到全国军民的脑海中,并以之诉于举世的列邦人士”。[3](53)
总之,杜氏之“新文器”理论对于正确理解新闻宣传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纸弹”的抗战威力均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呼吁制定新“新闻政策”,促成“一个民族一个意志一个舆论”的实践
所谓“新‘新闻政策’”,就是有别于平素的战时新闻政策。战时新闻是“统制”的新闻,一国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在思想方面,……以齐一的步伐,用统一的阵容,实施宣传的新方针”,[5]这就要求政府制定战时新闻政策,以指导战时的新闻工作。杜氏是新闻政策研究的专家,早在复旦求学时就致力于新闻政策的研究,其本科毕业论文《新闻政策》就对新闻政策的溯源、演变、价值、趋势等,作过颇为详尽的论述。1939年,他在《战时记者》首卷第4期上发表的《新“新闻政策”》一文,则是他对战时新闻政策的思考与研究。
在《新“新闻政策”》一文中,杜氏从人类新闻传播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自从有新闻传播就有“新闻政策”的观点,“新闻政策的运用,可以说系人类的一种本能”。从原始人类社会的图腾符号、“口头新闻”到“书写新闻”,再到“印刷新闻”,“新闻政策的表现方式或包含内容虽不同,而其发自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则亘万古而不变”。都是“一样的”“施行利己的宣传”,“一样的是有意无意间应用巧妙的新闻政策”。到了近代,新闻政策已变成“国策的一部”,“它以国策为政略战略,而以纸张、笔墨、广播、放映等工具为利器,从事于克敌制胜的思想战、言论战等战斗战役,而预期收获利己损敌的战果”。[5](57)所以,杜氏认为,要取得抗战的胜利,“除在军事上作机动的反攻,政治上作政略的进攻外”,必须要制订“新‘新闻政策’”,只有这样才适合当前抗战建国事业的“新需要”,“藉以创造一个光明开朗的新形势”。[5](54)
最后,杜氏指出新闻政策的最高目的,是缔成“一个民族,一个意志,一个舆论”。所谓“一个民族”,就是要爱护中华民族;“一个意志”,就是要增加战斗意志;“一个舆论”,就是要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6]这“三个一”即为“新闻政策具体的结晶”。[5](58)杜氏呼吁:当前,“我们正以全民族力量的总和,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周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三个指标,一方是最高度的升华,一方又是最低浅的要求;我们希望从这新“新闻政策”的确立,促成“一个民族一个意志一个舆论”的实践。[5](59)
总之,杜氏的《新“新闻政策”》一文,反映出一个战时报人对于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渴求,它在论证制定战时新闻政策合理性的同时,也提出了战时新闻政策实施的愿景——实现“一个民族一个意志一个舆论”的新闻实践。这也反映出战时报人从民族自由独立、抗战建国事业取得胜利的角度出发,自觉接受新闻“统制”,甘愿放弃新闻自由,实现舆论一律的良好愿望。
(四)强调战时报人的职业操守,提出要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在这场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血战中,要打赢新闻战、宣传战,战时报人的专业素质与职业操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杜氏对战时报人提出了要求与希望,对如何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首先,杜氏号召战时报人要“站在反侵略的第一线”,要担负起“反侵略,谋自卫,求生存”的神圣职责,成为“反侵略的急先锋”,[7]其“最低程度的神圣任务”是:第一,“确保胜利的信心”;第二,“倡导同胞的气节”;第三,“发扬正确的舆论”。[8]当前其“最低限度的工作”,在国内“须加速唤起全民族的反侵略意识,以驱除敌寇,做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在国际上,要宣示中国“不仅有反侵略的坚强决心,且有反侵略的庞大力量”,“把我国反侵略的狂暴的可歌可泣事实,用直接间接的方式,广为宣扬,使爱好和平崇尚正义的友邦,毅然决然地站在我们这一边”,并“加紧援华反日”。[9]
其二,要树立“民族至上国家第一的道德”。杜氏认为,“抗战伟业系目前的唯一真理,报人道德应以此真理为依据。这个真理的具体行为,是‘抗倭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于抗日’,‘集中力量、统一意志、整齐步伐、以争取最后的胜利’”[10]。
其三,要加强“自我扶助”和“自我教育”。杜氏指出:“‘自我扶助’和‘自我教育’,系我国战时报人的两大指标。达到这两个指标的最低水准,才能形成‘一个民族、一个意志、一个舆论’”[6](89)。
其四,要具有“四种精神”,负起六大任务。杜氏提出:“一个健全的报人,必须具备创造、服务、奋斗、牺牲等四种精神”。“报人是否能站在时代的浪头,或被时代的狂涛所冲灭,纯视能否创造、服务、奋斗、牺牲以为断”。[11]同时,还提出报人要英勇地负起“六大任务”:“一为报导的任务,二为宣传的任务,三为组织的任务,四为战斗的任务,五为创造的任务,六为改进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健全的报人”。[12]
新闻教育事关新闻人才的培养,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与能力与新闻教育密切相关。但是,上世纪30年代新闻教育在我国的历史至为简短,尚处起步阶段。对于当时新闻教育的状况,杜氏认为是失败的,而失败的症结“主要的为教育与社会不贯通,理论与实践不贯通,驯致学校自学校,报馆自报馆,学理自学理,事实自事实,格格不入,到处凿枘,互相排斥,互肆诋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学校所习的,不是社会所要的,理论所发挥的,又不是容易于实践的。我国社会机构的窳陋,新闻园地的荆棘,固使优秀的新闻人才,无法学以致用,但新闻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缺乏决心以开辟新风气,没有能力以开辟新环境,要为其中的主因。”[13]为此,杜氏呼吁:在这“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大时代里”,我国的新闻教育“尤不容其长此泄沓下去”,“应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弃其糟粕,采其精华,顾全事实,适应需求”。他希望“中央各有关系的机关”,“能够认识报纸是社会教育的利器,而报人则为制造报纸的动力,对此‘教育的教育’之新闻教育,能有中国本位化的一番新型建设”。“中国本位之新闻教育的重要原则,简言之,就是如何使教育与社会相贯通,如何令理论与实践相贯通而已”。[13](88)
从强调战时报人的职业操守,到提出要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从中反映出杜氏对战时新闻人才的重视。诚如杜氏所说“一个健全的报人,不是咄嗟之间可用人工制成的”,他“既须较常人有深一层的观察力鉴别力,又须较常人有进一步的活动力坚韧力,劳倍于人,乐薄于众,事居人前,功在众后”。对于这样人才的培养问题,杜氏在《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一文中引用了先辈戈公振先生的一席话:“……就学新闻教育,应以兴趣为前提,迨献身于新闻事业,尤应以人格为要件”[13](87)。这也就是说,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是要培养有人格的新闻人才,笔者以为,这应是杜氏所谓“健全报人”的固有之意。
(五)匡正战时新闻事业的缺失,揭示抗战后我国报业的变化与发展
“强化宣传则系把握胜利的阶梯”。作为《战时记者》主编,杜氏深知新闻宣传的时代意义与抗战作用,但他也看到了抗战以来宣传工作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着新闻纸这颗“纸弹”威力的发挥。正如杜氏在《战时记者》创刊号《记者节与反侵略》一文所说的,“我国过去反侵略的宣传,组织欠完善,工作欠紧张,联络欠密切,内容欠充实,手段欠敏巧,范围欠广泛,一切侦察、分析、统计、研究、归纳、诊断、策应、交际、分配等工作,类皆未能恰到好处。”[7]针对这些情况,杜氏多次撰文进行了批评指正。
首先,分析了当前报人环境的两大缺憾:第一,报界缺少中心的组织。第二,报人缺乏健全的训练。杜氏指出,抗战以来新闻界“缺乏中心的组织”,致使各地新闻宣传“各自为政,陷于盲动乱动的状态中”。同时,各地报馆、报人之间“问题从无讨论,意见难以磋商,深刻一致的见解,亦不易激发和蔚成了”。[8](1)而战时报人“缺少健全的训练”,“系我国战时新闻界的一大问题”。这种现象不解决,“则所谓正确报导,可以说付诸空谈”。[8](1)
第二,指出战时新闻的“四个显著的毛病”。一是公式化,“构成陈腐的‘抗战八股’,不易使人动听”;二是夸大化,“片面的夸大,非唯不能成事,反之,适足以偾事”;三是表面化,没有从“深入”下功夫;四是贫乏化,“不能满足战时人们(对抗战新闻)的饥渴”。[14]杜氏认为,一篇完好的新闻,光有“新闻价值”而没有“新闻技巧”是不行的。“新闻技巧的上乘,系令人有如‘置身事中’”;“中乘则使人近乎‘似观剧然’”;“下乘则只是‘人云亦云’,一点适如其会的作用都没有”。[14](31)要提高新闻的写作技巧,杜氏认为要向我国古代经典著作《水浒》《红楼梦》学习。
第三,分析了影响“纸弹”射程和威力的若干不利因素。杜氏对当时国内“汉奸敌探,多如牛毛,征兵募款,到处困难,腹地人民对于抗倭战争,尚多漠然视之”的现象深感焦虑,对“前线军队抗战民众逃亡”和“后方人民醉生梦死的麻木形态”痛心疾首。他认为产生这种“畸形状态”的主要原因是“过去报纸的不能使人人买得起,看得懂,和过去报纸的不能散布民间”,[3](52)而教育的不普及和宣传的不深入正是影响“纸弹”效应的原因。为此,杜氏提出:“我们应使报纸的文字,人人看得懂,报纸的价钱,人人买得起,看报买报的欲望,人人觉得需要”,实现“这三个最低线的要求”,则“系报人必须兑现的起码创造力”。[12](97)
与此同时,杜氏还深入分析抗战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新形势,揭示了抗战后我国报业的变化与发展。第一,报人“由聚居一处而散开各地”,“遍布了穷乡僻壤朔漠蛮荒”;第二,从前办报“非钱莫举”,现在则出现了“有人就有报”的现象,“人的价值远驾物的价值,人的意志可以克服物的困难”;第三,从前“服务人群与营利维持,固为新闻纸的生命线”,现在“惟主持正义和反抗侵略,尤在服务与营利之上”;第四,“新闻纸除报告、解释、分析、教育、组织、训练诸任务外,还有一个最基本最扼要的任务,那便是‘战斗’”;第五,战前“以纯商业性为号召的新闻纸,今后将不易立足”;第六,战后所出现的“流动性的新闻纸”,“不独在战时发挥其最大的效用,战后亦有其存在的必要”。杜氏认为:“一张流动的新闻纸,等于一座活的学校,费少而效宏,为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15]
总之,杜氏对抗战以来中国报业存在问题的分析,可谓切中要害,这对于纠正抗战新闻事业的缺失,改正抗战宣传工作的时弊,均有正确的指导作用。而杜氏所揭示的抗战以来中国新闻事业所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实则是对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新形势的概括与总结。抗战以来,报业由聚而散,由固定而流动,由“非钱莫举”的商业办报变为旨在“主持正义和反抗侵略”的宣传办报,这不仅反映出抗战的新闻事业有如星火燎原,发挥着战斗的威力,而且还决定着将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光明前途。
(六)分析了新闻的职能与特性,指明了新闻纸未来的发展方向
战时新闻学强调新闻学的“工具理性”。所以,从“一切服务于抗战”出发,杜氏认为,新闻学“系政治斗争和思想锻炼的主要工具,亦系社会改进和各项建设的无上利器,且兼有教育、组织、宣传、训练等功能”。[2](35)基于这种观念,杜氏对新闻纸的职能与特性都进行了新的思考与定位。
首先,杜氏将新闻的职能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两个部分。新闻的职能有两点:一为“供给敏确的新闻”,一为“代表真正的舆论”,但抗战的形势对新闻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新闻要成为“教育并组织读者的工具”,新闻纸“要分析新闻并提示新闻,指导读者一条光明途径”。[15](1)基于此,杜氏认为,“报告新闻和代表舆论两点,仅是新闻纸消极上的职能”,而“其积极上的效用,则为新闻纸的教育性及组织性”。“新闻纸为活的教育,……是一位‘无音的良师’”,“能激励读者意识,使其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组织成坚强的一群”。正因如此,“新闻纸的进步性,就要看其教育与组织的效率如何而定”。[15](2)
其二,在新闻纸的诸种特性中,杜氏特别强调其“国族化”之特征。新闻纸具有“有恒化”、“大众化”、“时代化”、“国族化”等特性。而能“反映国族利益的新闻纸,始不失其存在的真价值”。[15](2)
其三,提出要“创造新闻纸独特的个性”。杜氏认为,商品可以标准化,但是“新闻不能标准化”。“近来我国各处报纸,内容多属平凡”,就是“现阶段的我国报业”的“普遍的‘同病’”——“新闻的过于标准化”所造成的。要克服这种现象,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新闻不能标准化,而必须个性化”。[16]接着,杜氏就如何创造新闻纸“个性”的问题,提出了他的设想。杜氏认为,“读者为一张新闻纸所赖以存在的生命线”,“我们创造新闻纸的个性,便从读者的兴趣入手”,“将读者群细加分析”。“读者群的兴味即对象”,我们可以“迎合他们的意旨,以为立论编报的南针。而表现为适如其分的纸面,这是形态”。“对象和形态的总和,就是新闻纸的个性”。[16](83-84)当然,杜氏也指出:“新闻的个性,必须旨趣高尚,绝对不可为逢人之好,而自趋于卑鄙下游,诲淫诲盗的个性”,“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个性,第一要具崇高的报格,第二要有精彩的特色,第三要循合理的途径,第四要用正常的竞争,第五要尊重读者而不阿附读者,第六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笔者以为,“创造新闻纸独特的个性”可以作为杜氏“制造理想中的新闻纸”的一个注脚。抗战新闻是“统制”新闻,“统制”下的新闻,难免产生“地方报和都市报”的新闻来源“同出一流”、新闻内容“完全雷同”之弊端,难免会受到新闻“标准化”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杜氏探讨新闻纸独特个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他对“理想中的新闻纸”的一种寻觅,也反映着他试图为中国新闻纸的发展指出一条光明大道的思考与探索。正因如此,杜氏将“新闻学”定义成“研究制造理想中的新闻纸之学问”。[2](37)
三、结 语
上述所总结的六个方面,只是概括地说明了杜绍文《战时报学讲话》对战时新闻学的理论贡献,实际上,该著对战时新闻学还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由于不成体系而未加论述。比如《儿童该有自己的报纸》一文,就反映出杜氏对战时民众,尤其是儿童媒介素养培养的重视。作为上一世纪40年代初出版的一部新闻学论著,作者学术观念的先进性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许多人认为新闻学不够称“学”,顶多只是一种“术”时,杜氏就断定“新闻学不但是一门学问,且是一门综合的‘学’”,[2](35)并且认为新闻学“不是独立的科学”,它必须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地学等其他学术“作平行而不偏枯的研究”,[1](20)又如,杜氏对当时出现的广播、无线电报、电视、电影等“新媒体”持肯定的态度。在其主编的《战时记者》中,曾专门开辟“电枪与子弹”的特辑,介绍广播、无线电波、新闻电影在宣传功能上所带来的巨大效应。他还发表了《敌乎?友乎》一文,认为广播和电视这两种“新媒体”与报纸,存在着既竞争又统一的关系。报人“不特不能仇视这两种科学的新利器,相反的,必须引为亲挚的同伴”,[17]这样才能保证新闻的园地与日俱新。这些观点,即便从今天来看也是正确的、不落后的。
当然,限于时代,杜氏的某些新闻学观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杜氏将“新闻学”定义成“研究制造理想中的新闻纸之学问”,就反映着当时将“新闻学”等于“报学”的一种时代局限性;杜氏之“新文器”论,对新闻与宣传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有时是混淆着使用的;限于历史之局限,杜氏的新闻观是“三民主义”的新闻观。但是,将《战时报学讲话》一书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其主张“抗战救国”的新闻观无疑是进步的。
[1]杜绍文.战争带来了健全的新闻学[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15.
[2]杜绍文.新闻学能成立吗?[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38.
[3]杜绍文.论金铁与纸[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47.
[4]杜绍文.新文器与新武器[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65.
[5]杜绍文.新“新闻政策”[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54.
[6]杜绍文.一个民族 一个意志 一个舆论[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91.
[7]杜绍文.记者节与反侵略[J].战时记者,1938(1):1.
[8]杜绍文.战时报学讲话·前言[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2.
[9]杜绍文.记者节与反侵略[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110、111.
[10]杜绍文.报人道德论[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68、70.
[11]杜绍文.报人必备的四种精神[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11、14.
[12]杜绍文.英勇负起六大任务[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92.
[13]杜绍文.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86.
[14]杜绍文.一个比较的研究[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28-30.
[15]杜绍文.新中国的新闻纸[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7.
[16]杜绍文.创造新闻纸特征的个性[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82-83.
[17]杜绍文.敌乎?友乎?[A].战时报学讲话[C].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45.
[责任编辑:赵晓兰]
蔡罕,男,教授,历史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G219.2
:A
:1008-6552(2017)03-0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