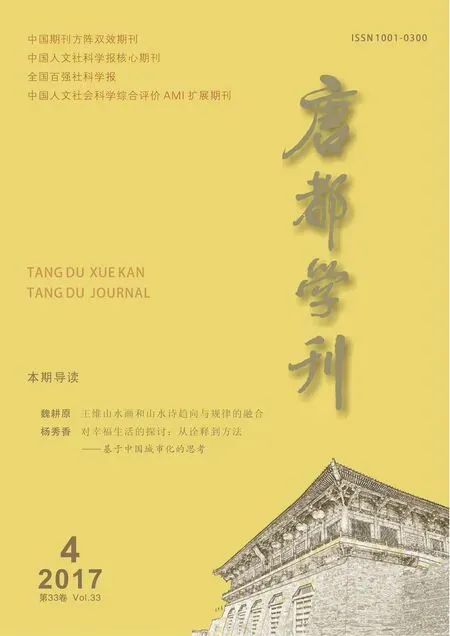拆解极端反差
——论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
马惠萍
(西安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65)
【文学艺术研究】
拆解极端反差
——论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
马惠萍
(西安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65)
莎士比亚以戏剧成就闻名于世,悲剧更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珍品。莎氏的悲剧艺术博大精深,绝非一篇文章、一部论著所能概括。但通过对《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雅典的泰门》《李尔王》三部悲剧的探讨,可以发掘莎氏悲剧艺术的一个重要侧面 :拆解极端反差。无论是泰特斯、泰门还是李尔王,都有一个从荣耀到屈辱的极大落差性的叙事建构,这个极端反差的设置以及莎氏对其的拆解于是成为莎氏悲剧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可以说,对于莎士比亚的悲剧而言,拆解极端反差已然构成其悲剧艺术的重要一面。
莎士比亚;拆解极端反差;悲剧艺术
莎士比亚无疑是西方文学史上最为璀璨的文学巨星之一,几百年来,他以持久的新鲜感一再刷新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人世的感知,对于生命的理解以及对于人性的探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真的会认为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都在莎士比亚身上,他的确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部部可以超越世俗、超越时间的文学经典。时至今日,我们当然不会再质疑莎士比亚所赐予文学的意义,我们也早已习惯性地使用莎士比亚自创的为数不少的英文词汇,但我们更应该了解的却是他的悲剧。
可能在莎士比亚之后,我们真的无法再去分辨何为悲剧,何为莎士比亚的悲剧;何为悲剧艺术,何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悲剧在莎士比亚的笔下,才真正成为一门深刻的艺术;我们因为常常以莎士比亚的悲剧为悲剧的范本,而不能将莎士比亚与悲剧断然分开。悲剧、喜剧、历史剧、传奇剧等都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所涉猎的领域,也只有像他那样伟大的戏剧天才才有可能在这些个戏剧门类取得如此斐然的成就,莎士比亚似乎样样精通,几乎没有艺术的死角。正如威武雄壮的喜马拉雅山系,有一个最高峰叫做珠穆朗玛峰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最高峰就是悲剧。
莎氏是悲剧艺术的个中高手,他也正是凭借着举世闻名的四大悲剧名扬于世。可以说,悲剧艺术是莎氏戏剧艺术中的精华,而就悲剧艺术而言,莎氏则表现出了其非凡的才能。在莎氏悲剧中,我们不仅能够欣赏到精彩的情节,还能感受到来自心灵的震动;不仅能够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还能感受到人物内在的不可遏制的行动缘由;不仅能够读到精彩无比的语言,还能感受到语言背后深广博大的对于人生之思考和对于存在之探察……莎氏的悲剧艺术无疑是丰富的,本文显然不能全部探讨。本文试图探讨的是莎氏悲剧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拆解极端反差。在我看来,拆解极端反差既是莎氏悲剧艺术的重要构成,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悲剧艺术的根基。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当可发现,几乎每一部莎氏的悲剧都有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反差叙事的设置,极端的反差诱导剧情不可思议地发展,人物也不可思议地活动,剧本于是总是处在一种紧张的叙事节奏之中,悲剧艺术的饱满时刻就此降临。有了极端的反差叙事的设置,莎氏紧跟其后还有对于这一极端反差的拆解;正可谓胆大者才可以走钢丝,艺术的高手敢于在一片绝境中开辟有力量的叙事。莎氏的悲剧艺术才因此引人入胜。
一、《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家与国的冲突
好人总是饱受折磨,坏人总是肆意妄为。这在该剧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莎士比亚有意将好与坏的对比极端化,以罗马新皇萨特尼纳斯、诡计多端而心狠手辣的新皇后塔摩拉为代表的坏人总是能够肆意为非作歹;以泰特斯和其25个先后为国捐躯的儿子为代表的好人则总是受尽磨难,并且不得上天的眷顾。莎氏几乎是在整个剧本中都在贯穿这样一条线索 :好人处处遭冤,坏人横行千里。如若不是泰特斯诚意推让国君的位置,罗马新皇很可能会按照民意给予这个为罗马常年征战的将军,民意正是如此。但泰特斯毫不犹豫地在凯旋之时将这份荣耀和王位都让给了萨特尼纳斯,因为在泰特斯心中,萨特尼纳斯是前皇的后裔,有着更为纯正的皇室血统。我们可以循此一步步来到这个剧本的核心 :家与国的冲突,或者说,家与国之间的某种极端反差的关系设置。
如果不是忠于国家,我们很难想象泰特斯何以能够容忍萨特尼纳斯的百般侮辱和欺压;如果不是抱着对这个国家无私的爱和忠诚,我们也无法设想泰特斯何以不在昏聩的国王的极端作为下揭竿而起。泰特斯生活的这个时代,罗马正渐渐变成了一个国王独裁专制的国家。然而,泰特斯虽然看清了这个邪恶时代,对此充满了愤怒和惋惜,却只想以怀旧的方式唤回从前的时代。泰特斯的悲剧大抵在此,面对一个不断向着专制发展的时代,他却要执意停留在前朝,停留在过去的时光之中。因此,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彻底的悲剧,是一个关于人与时间以及人与这个世界之间的悲剧,是无法解脱的悲剧。纵然泰特斯有赫赫战功,却也无法扭转乾坤。这个国家虽然还保留着过去的躯壳,却已然是另一个模样了,而泰特斯却幻想着能看到这个过去的躯壳内里依然驻扎着的过去的那个魂灵,那个忠君重民、国家与家庭心心相连的时代。
基于此,我们看到了最为激烈的剧本情节和最为伤痛的人生故事。从那个国家社稷之脊梁的位置上一步步跌落到女儿被割舌、奸污,儿子被通缉或杀掉,自己成为叛国贼,要听信艾伦的谎言自剁一只手去救赎儿子的下场,真可谓一时在天上,一时在地下。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国与家交互缠绕的故事。身为俘虏的塔摩拉哀求泰特斯善待自己被俘的孩子,并试图缓和泰特斯对敌对国俘虏的愤怒之情,但泰特斯坚决拒绝了她的请求,这无疑深深刺痛了塔摩拉的心。后来塔摩拉用计成为罗马的新后,她于是可以借着国妻的之名“光明正大”地行摧残泰特斯一家之实。所以,这个最反差的和最伤痛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母亲对于自己孩子极端爱护之心的发散,或者说是其对于杀子之仇的极端反映。这是两个家庭之间的故事,主角分别是塔摩拉和泰特斯。在这个叙事层面上,塔摩拉直接地是为自己的孩子复仇,间接地却也促成了其早日归国的愿望的实现 :削弱敌国最有战斗力的家族不啻于消灭敌国最重要的力量;泰特斯直接地是为了维护罗马极致的荣誉,间接地却也保留了家庭精华 :家规。在这里,家与国缠绕在一起,家庭故事一变而为国家故事,国家故事也是家庭故事的延续。因此,莎氏能够将家庭的切肤之痛写得真切,又能将国家的岌岌可危写得逼真。
以泰特斯的个性,我们一定不会想到他会复仇。他对这个国家如此的忠诚,为了国家他甘愿承受邪恶带给他的百般苦痛,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懦夫,一个国家或君主温顺的羔羊,从来不知道如何去反抗。拉维妮娅的悲惨遭遇不可谓不惨痛,但此时的泰特斯依然对国家抱有幻想,依然相信这不过是一帮恶人所为,于自己深爱的罗马无关;断手去救无辜蒙难的两个儿子这件事依然没能让泰特斯对国家失去信心,他依然期望国王能够履行诺言,放回他的两个儿子。莎氏悲剧中充满了泰特斯这种下场悲惨的英雄,他们不是无能为力,一旦他们觉醒,他们的一声吼叫就足以推翻一个世界!但他们的悲剧性也就在于他们的愚忠导致了他们总是思前想后,思想和行动滞后于那个荒谬的时代,只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存在下去。泰特斯的悲剧性就体现在他的觉醒来得如此缓慢、如此痛苦。直到那个狡诈多端的艾伦提着他的两个儿子的头和泰特斯的断手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泰特斯才真正对罗马死了心。是的,一个如此无视自己的功勋老将,一个如此糟践老人的罗马早已不是从前的罗马。实际上,它也的确不是了。如果说萨特尼纳斯与泰特斯之间的敌对关系还多少有同属于罗马君臣之间的微妙的不协调关系的影子,那么塔摩拉及其两个作恶多端的儿子以及艾伦则是完全敌对的力量,只不过以一种暂存的“同一”形式存在于罗马国境,他们与泰特斯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是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矛盾了。这剧本的艺术张力也就此生产。
极端反差的拆解虽然来得迟了一点,但足够长的叙事却使得剧本的叙事空间得到了很好的拉伸,也使得剧情能够一直牵动着读者的心 :泰特斯如此的愚忠,他的悲惨遭遇何时为终?他会不会反抗?他何时反抗,或者死去?莎士比亚看似用了一个极端老套的苦难叠加的方式去构建剧本,实则不断在诱惑我们的期待,又不断将之粉碎。这就是莎士比亚的过人之处。通过极端反差的叙事情境的设置,又对这一极端反差叙事的消解,剧本能够以其独特的方式经营悲剧艺术,使之产生更加惊心动魄的力量。《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因而令人难忘。
二、《雅典的泰门》 :荣与辱的对峙
与泰特斯一样,泰门也是国家的英雄和栋梁,但与泰特斯以“武功”著称不一样,乐善好施的泰门虽也在斯巴达和拜占庭两次战役中表现英勇,但其最赖以称著却还是其对于友情的极端看重以及在一颗善良之心的驱使下对朋友的慷慨无私。正像泰门在第一幕第二场对家中宴会中的朋友们所说 :“一切礼仪,都是为了文饰那些虚应故事的行为、言不由衷的欢迎、出尔反尔的殷勤而设立的;如果有真实的友谊,这些虚伪的形式就该一律摒弃。请坐吧;我的财产欢迎你们分享,甚于我欢迎我自己的财产。”[1]160从一颗真诚的、善良的心出发,泰门十分看重友情;为了呵护友情,甘愿想尽自己一切可能的办法为朋友分忧解难。试想,如果不遭变故,也就是说,如果泰门的钱财真的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其保障,他永世也不会认识到人情的冷漠和谄媚者的可耻;因为在慷慨多情的泰门真诚的世界里,所有虚假伪饰的友情及其表现形式——恭维话、假意的关心等——都是纯真友谊。人生的荣景也多少局限了泰门的视野,使得他总是倾向于用单纯善良的心态去认识、理解周围的人与事。
于是,他只能越发慷慨,因他无法识破这种所谓的真诚友谊的假象,他只能在受骗的轮回里越陷越深,直到被谄媚者——也就是那些所谓的朋友们,包括诗人、画师、商人、宝石匠、元老、贵族等雅典各色人等——榨干最后一分钱财、最后一滴血。莎士比亚惯用极端的叙事手法,几乎没用更多的语言,却已经悄然将剧情推向了一个高潮,推向了一个绝境 :泰门必然身陷绝境,他的乐善好施好比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总有末日穷途的那一天,这是确定无疑的。莎士比亚从一开始就将一种绝对的极端叙事放置在那里,我们见过乐善好施的,见过心肠善良的,见过为朋友慷慨解囊的,但我们面前的泰门依然让我们觉得他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更加极端了,更加极端的乐善好施,更加极端的心肠善良,更加极端的慷慨解囊。
借泰门最为忠心的、日后在泰门“众叛亲离”之时依然不离不弃的管家弗莱维斯之口,莎氏道出了泰门荣景的不堪重负以及剧本必然的黑暗走向 :
他所答应人家的,远超过他自己的资力,因此他口头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笔负债。[1]171
虽说泰门不认为是他自己在构建了这一场悲剧,但我们仍然可以说是泰门无意间助长了这一场悲剧的发生。泰门的乐善好施也不过是通过金钱去维系朋友的友谊而已,而那些所谓的朋友们也不过是看在金钱的份上,才愿意与他结交。当然,人与人的交往总会以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形式出现,正像人生之复杂多样一样,泰门显然也看到了多种多样的友谊,但不得不说,他看到的只是经过伪饰的友谊,是一种虚情假意。关于真与假的辩证一直是莎氏悲剧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在本剧中,泰门一直以来遭遇的不过是虚假的人生,事实证明,也只有虚假的人生才容易走向彻底的极端;但反过来想,这一切的根源除了周围那些狐朋狗友的卑鄙虚伪之外,泰门单纯善良的天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构建自己的悲剧。就像寄生虫与寄主的关系一样,泰门的朋友和泰门共同构成这一幅肮脏图画。在这个图画里,善良泯灭,真诚消失,虚伪当道。
“谁想得到,一个人行了太多的善事反而是最大的罪恶!谁再敢像他一般仁慈呢?”[1]213这依然是管家弗莱维斯的愤怒之言,其实这何尝不是泰门的肺腑之言。泰门终于走到了日暮途穷的一天,莎氏充满讽刺地展示了泰门在自己穷途末路之时向昔日好友借钱的过程,,这时的他实在不能忍受竟然分文都未借到的现实。十分愤怒的泰门终于认识到了人情的冷漠和人的虚伪。我相信在他决定用极端的方式去戏弄乃至侮辱、杀害他的那些昔日朋友之时,他已经想好了未来的归宿 :露宿海滨树林,然后悄悄死去。在人生危难的时候,泰门终于觉醒了,他领悟到人世不过是一场欺骗;但也就是在这种觉醒中,泰门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开始动摇。这是泰门的悲剧,当真诚的人遇到虚伪和欺诈也会变得如此可怕。
综观本剧,管家弗莱维斯和性情乖戾的哲学家艾帕马斯特犹如两道有力的闪电,不断驱除着弥漫于剧中的黑暗。在一片浑浊之中,他们是唯一清晰美丽的风景。在一片悦耳的谎言中,他们是唯一真诚的刺耳之音。弗莱维斯总算没有让人对雅典彻底失望,莎氏还留有人性复苏的可能性。早在剧本第一幕第二场,就在泰门说着慷慨的真心话却在被欺骗的时候,艾帕曼斯特就说过 :“人生的荣华不过是一场疯狂的胡闹”[1]160。莎士比亚在本剧中对极端反差的运用更为娴熟,其拆解之道也更为成功。正如布拉德雷所说 :“悲剧的根本力量是一种道义的法则。”我们真的是跟随着泰门上天入地,从荣到辱,仿佛真的经历了一遍人世。虽然这其中伤痕累累,但莎翁的悲剧艺术却在建构和拆解极端反差这一叙事的意义上获得了极大成功。
三、《李尔王》 :父与女的斗争
人们普遍公认,《李尔王》是莎士比亚最富有激情的一部戏,激情澎湃之处,常常如大江奔流,不知所终。也有论者认为,《李尔王》的悲剧成就当在《哈姆雷特》之上,莎士比亚在这部剧中塑造了一个个让人痛彻心扉的人物。他不给备受摧残的老李尔以任何真正的抚慰,却让人心底最后留有一丝温暖情谊。不管怎么说,《李尔王》是一部剧情人物丰富的悲剧,我们可以看到治理国家的艺术,看到争权夺势的战争,看到夫妻的反目,看到父女的复杂关系,看到这一切发生过程中冥冥的命运之手……这里有如天使一般圣洁的考狄利娅;也有最为丑陋狡诈的爱德蒙,莎氏剧本中最为作恶多端者,狠毒程度甚于摩尔人艾伦。不过,如果从对极端反差的氛围营造来说,那个最触目的事件却必然非父与女的争斗莫属。人生的荣与枯、国家的盛与衰、人性的善与恶,都在《李尔王》中得以揭示,其揭示的深度也很难企及,但本剧最有爆破力的那个点却在对于父女关系的表现上。李尔王与三个女儿的关系既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其现实气息甚至可以直穿无限的岁月来到当下,丝毫不显得过时;又具有极强的象征性,象征着人类非理性的黑暗势力的存在,且范围广大。
李尔贵为不列颠国王,但他又是一个父亲。在剧中,也正在对父亲这一身份的表现中,我们看到一种更加极端的反差,得到一种更加深刻的思考。身为国王的李尔最关心的问题是退位,因为退位意味着权力的失去,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痛莫大焉。然而对于李尔的子女而言,无论他在多高的位置上,他始终是一个父亲而已;国王的荣耀可以增添他的威望,但归根结底,他也只能在父亲的维度上期望更多的感情回报。这依然是一个国与家揪扯不清的话题,有心人当会发现这也是莎氏结构戏剧的一个重要方式。因此,我认为,本剧的国家故事更多是一个背景,或者叙事必要的配置,那些借由国家与家庭之间的联系而滋生出来的关涉家庭的点才是真正的主角。这个家庭故事的核心在于父女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父女之间的争斗。
就李尔的三个女儿来说,大女儿高纳里尔、二女儿里根是一种重复性或递进性的设置,她们属于一个类别,属于极端势力的一类。在这二人看来,老国王李尔不赶紧退位本身就是对自己身为子女权利的一种侵害,但其时李尔尚在位上,她们估摸了自己的力量与父亲的力量对比,认为自己没有多少有胜算才忍气吞声;等到老李尔决定退位的那一天,这两个女儿早已经急不可耐。极致的高调不过是极致的虚假的一种表现而已,对于高纳里尔、里根两姐妹来说,兴许是要摆脱老国王父亲的愿望过于强烈,以致她们才采取了那种最为直接、也最为赤裸裸的高调的宣誓方式。而其实,这一切不过是一场逢场作戏。对于李尔的三女儿来说,恋父情结却是本真的,但这种表达方式却恰恰为李尔王所不能接受。因此可以看出李尔王一辈子都是生活在一种虚伪的世界之中,也正是因为李尔不想看到那个可怕的真相的到来,他一直推迟退位,实在是不能接受甚至想象一下退位之后的凄凉。因此,在决定退位之时,老李尔事实上已经决定放弃在位时那些隆重的礼仪,他唯一的希望是三个女儿能够待自己如同以往。从国家的位置上走下来,李尔期望得到家庭的承认,这就是三个女儿对他全心全意的爱。
问题在于,李尔对女儿的父女之爱的预期与女儿愿意付于他的父女之爱形成极大的反差,这个反差一度让人不能接受。其实,从“爱的考验”开始,剧本已经呈现出一种反差叙事的建构。仅仅凭借分封国土之时李尔王的寥寥数语,就能看出他是怎样表达他的父女之爱的。
孩子们,在我还没有把我的政权、领土和国事的重任全部放弃以前,告诉我,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最爱我?我要看看谁最有孝心,最有贤德,我就给她最大的恩惠。[1]257
老李尔早就知道三个女儿的心迹,其实这些都是老李尔心中早已谋划好的事情;如果按照老李尔的设想,从老李尔在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的话音刚落,就迅速分封一北一南的领土给她们可以看出,小女儿考狄利娅将获得的其实是最为丰厚的领土,也是老李尔最想停留的养老地。而这些已经分封好的领地可以从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实现三方力量的均衡化,从而维持不列颠王国的长治久安。结果,莎士比亚给故事制造了一个断体,极端的反差效果就此产生。在莎士比亚的诸多悲剧中,这个极端反差叙事可能是最为悲剧性的、最为不可救赎的。
当高纳里尔、里根很快与父亲翻脸之时,我们读者都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觉得那会是必然的结果。但对于李尔王来说,那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创痛。这个反差叙事的核心在于父女双方对同一件感情的感知之差异上。高纳里尔、里根如果真的敬重父亲的话,她们也是敬重其地位,尤其是其国土,李尔从同样的话语中却感知到的是她们对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关爱与尊敬;考狄利娅,这个几乎完美无瑕的女儿不愿以愚蠢的谎言骗李尔,却也暴露了其不能体察父亲的喜好进而去迎合的个性特征。最好的父女之爱当是李尔与其三个女儿之间的充分融洽,或者说,是三个女儿之间个性的充分借鉴与互补。但这“不是‘睡意朦胧’间说干的事情,而是足以体现行动者性格特征的作为或不作为,即表现性格的行为。”[2]悲剧正是在这个方面果断地说不,由此造成绝对的断裂。正如斯托尔所说 :“恶棍是知识更大胆的和更放肆的命运之神”[3]。暴风雨这场戏以及围绕不列颠的国土争霸不可谓不血腥,甚至残忍,但这个剧本最后的发力点依然在于父女关系上。当李尔与高纳里尔、里根构成严重的冲突的时候,考狄利娅如同从天而降,扮演了拯救李尔王的角色;虽然最后仍难免死在李尔的怀里,将一种伦理的黑暗演示至尽头,但李尔与女儿考狄利娅终于在隔世的时空里达成和解和理解。而高纳里尔、里根也因为情事互相残杀,草草死去。随着李尔王因为考狄利娅的死去和这极端的伦理乱象而死,整个剧情瞬间充满了死亡的气息,黑色的伦理,死寂的世界,无望的国家。也许,莎士比亚在此拆解极端反差的方式过于极端,他实际上用一种更加极端的渲染反差的一方的方式去消解反差,这却使得他的悲剧艺术得以更大地提升。彻底地渲染黑暗的一方,实际上将反差更其反差了;但更其反差的最后,也就是反差的消解。这是最后的虚无,最后的黑暗,是《李尔王》掷给后人的沉重的绳索,这绳索至今仍在悲剧艺术的高地困扰着我们,困扰着后人。
四、结语 :拆解极端反差的艺术宝库
无论是《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家与国的冲突、《雅典的泰门》中荣与辱的对峙还是《李尔王》中父与女的争斗,我们都能看到那种压倒一切的极端反差叙事的滋长与丰盈。不能说极端反差是构成莎士比亚悲剧艺术的基石,但那确实使莎翁的悲剧艺术更加完美,以至成为其悲剧艺术的重要特点。可以说,极端反差的设置与拆解是莎翁悲剧中最吸引人的风景之一,是那些最为惊心动魄的剧情的灵魂。当然,以极端反差为魂灵的悲剧艺术需要作者本身有极高的文学天分和艺术才华,正可谓最高贵者最卑贱,最卑贱者最高贵,极端反差如若运用得当,其带来的艺术效果往往会出人意料。这是一个高难度的领域,涉猎其中需要勇气,更需要天分。莎士比亚从来不回避极端性的叙事建构,反差性的叙事设置更是其拿手好戏,不能说莎士比亚的每一部悲剧作品都以极端反差的叙事建构为根基,但我们却可以说莎士比亚的每一部悲剧作品都有极端反差的情节建构。它们或者偶一出现,或者频频露脸;或者点燃气氛,或者灌注灵魂;或者支撑叙事大厦,或者作为叙事材料之一种。值得一提的是,莎士比亚对极端反差叙事的建构和拆解手段之丰富、技巧之圆熟、方法之得当,都令人称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莎士比亚建立起了拆解极端反差悲剧艺术手段的宝库。我们后人除了用心去发现或探索这一宝库的奥妙之外,理当更加对其发扬光大,以使得悲剧艺术达至一个更高的程度,更加适应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1] 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雅典的泰门·李尔王[M].朱生豪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安·塞·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M].张国强,朱涌协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
[3] 斯托尔.莎士比亚的艺术与技巧[G]∥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39-140.
[责任编辑朱伟东]
DisassemblingtheExtremeContrasts——OnShakespeare’sTragicArt
MA Hui-ping
(SchoolofForeignStudies,Xi’anUniversity,Xi’an710065,China)
Shakespeare was world famous for hi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drama, tragic works were the masterpieces among his best dramas. Shakespeare’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tragic art can never be summarized in one paper or one book.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three tragic plays——TitusAndronicus,TimonofAthens,andKingLear,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ortant aspect of Shakespearean tragic art lies in disassembling the extreme contrasts. It can be easily seen that all the three protagonists have experienced from glory to disgrace, the narrations of extreme contrasts and Shakespeare’s disassemble are the most appealing parts. As for Shakespeare’s tragic art, it has become the highlights in his plays.
Shakespeare; disassemble extreme contrasts; tragic art
I561.073
:A
:1001-0300(2017)04-0096-06
2017-02-26
马惠萍,女,陕西西安人,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