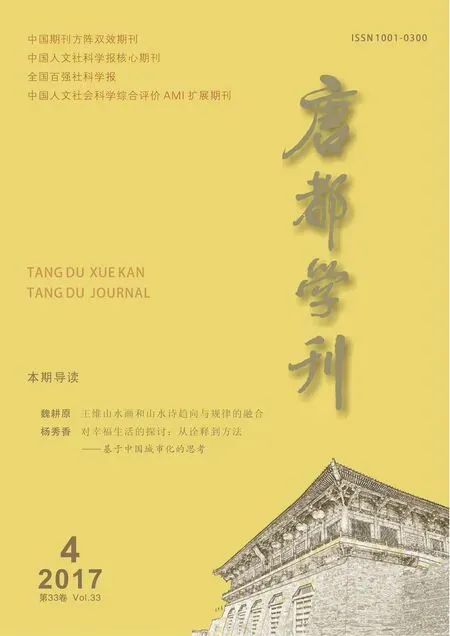对幸福生活的探讨:从诠释到方法
——基于中国城市化的思考
杨秀香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伦理学研究】
对幸福生活的探讨:从诠释到方法
——基于中国城市化的思考
杨秀香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幸福是人的生活目的,幸福同社会资源的分配有关。西方思想家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有一个从对幸福生活的诠释到实现方法的转向,这一转向是社会结构从传统的乡村转化为近现代城市在伦理学理论上的反映。幸福生活实现的方法严格地说是用来分配社会资源的公平的制度规则的建构方法的研究,城市社会是多元主体结构,必须要建构一个能够被多元主体共识为公平的资源分配的原则,才能被普遍地遵守,因而才能够使人们因得到自己应得的社会资源从而有条件追求更好生活而感到幸福。民众的幸福感由制度的公平效应决定了政府的合法性,政府的合法性又因为公平的制度而保证了民众的幸福,二者互为因果,这是幸福问题研究“方法转向”的价值所在。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社会的形成历史地提出了探讨幸福生活的方法问题。
幸福生活;幸福研究转向;中国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
幸福是人的生活目的,恩格斯在1847年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封信中说 :“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证明的……例如,每个人都追求幸福。”幸福意味着人能够利用应得的资源朝向理想目标追求的过程及目标实现的满足感,因此,幸福与社会资源的分配有关。不同的社会结构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不同。城市社会结构有别于乡村社会结构,现代城市社会结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差异更大,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必然不同。在西方,幸福生活或更好生活问题一直为思想家们所关注,但传统的乡村社会同城市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社会中的思想家关注的侧重点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多在对幸福进行诠释,后者则着力进行幸福生活实现的方法的探讨。分析西方思想家对幸福生活从诠释到方法研究的转变背后的逻辑,对正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中国而言或可作为一种醒示。
一
追求幸福生活前提性地要有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因此在思想家那里就必然会对此做出诠释,也必然会思考幸福实现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为人们提出实现幸福生活的方法措施,诠释和方法是构成思想家相关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缺一不可。但纵观西方伦理思想史,不难发现,在诠释和方法之间不同的思想家的关注度的确存在差异,大致可以说近现代的思想家比传统社会的思想家更重视方法的探讨,当代思想家尤其如此。
西方传统社会包括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两个时期,期间一些思想家或者从对人性的肯定方面将幸福作为人性的内涵,幸福实现的就是人性的实现;或者从对人性的否定方面将幸福推到来世,将幸福的实现归结为对人性原罪的救赎。二者的共性在于所谓“方法”(幸福实现)实质是对幸福的界定,是在诠释幸福的内涵,并不具有独立的理论意义。
古希腊思想家探讨幸福问题往往是从对人性的肯定方面进行的。经过早期的对世界本源思考的一些自然哲学思想家开始了对人自身的生活意义的思考,探讨人的行为的目的并将人生的目的归结为幸福。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都反映了这一思考。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固有本性是理性,理性的人以善为行为原则和标准,行为的目的是对善的追求,这是一种最佳的生存状态,所以苏格拉底向雅典公民提出“真正重要的是,不仅仅只是活着,而是要活得好”[1],即要“善生”,即幸福。为此人就要有关于善的知识,具备善的知识才会有善行、善生才会幸福。“没有人有意作恶或无意为善”“没有人有意追求邪恶的东西或者他认为是邪恶的东西”[2]70,人会作恶是因为没有关于善的知识。所以知识、美德、善生和幸福是一致的,最高的善就是幸福。知识、美德对善生、幸福实现有着条件或方法的价值,但就美德与善生、幸福的必然联系而言,美德就是幸福,其实质是以知识、美德界定幸福。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的特殊本质是有理性能力,“理性是一种分辨是非善恶并去善避恶的能力”[3]49。人按照理性指导去行为理性就成为德性。人出于德性追求一种最高的善即一种好的生活也就是幸福,幸福就是灵魂遵循理性的、合于伦理德性的活动[4]。最好的、最值得向往的生活方式则是有理性、有德性的人的思辨活动——“沉思”“是最高尚的幸福”[2]108。这是用理性、德性、“沉思”界定幸福。
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则往往从人性的否定方面看待幸福问题。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原罪说,人本是上帝的造物,但因祖先亚当、夏娃违背上帝意志偷吃禁果就堕落了,“罪就是人堕落之后的本性”[3]70,因此身体的欲望和世俗的幸福是魔鬼对人的引诱,是短暂的、没有价值的,只有来世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永恒的。只有按照上帝的意志、顺从神,依靠上帝的恩赐才能实现来世永恒的幸福,梯利概括说 :“亚当犯罪,人性受到腐蚀;他把罪恶传给子孙后代(原罪),唯有神圣的恩惠能够拯救他”。[2]230所以幸福就“在于获得上帝的接受”[5]。这是在用上帝的眷顾界定幸福。
无论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还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就其基本精神而言,都是将幸福视为人性的蕴含,只是因为对人性的规定不同导致幸福实现的方式各异,前者认为人按照智慧、理性行为就能够达到至善实现幸福,后者是说人必须通过赎罪,克服罪恶,回归善性,来世可以得到幸福,都是将实现幸福归结为人的意志。这与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将制度视为幸福实现的根本保证致力于有效的制度建立的方法的探讨明显不同。
康德的幸福观饱受批评。批评者认为他从预设的人的理性本性出发,认为理性人的行为仅仅遵循道德法则,与个人的“欲望和禀好”无关,也就同幸福无关,有德之人要得到幸福必须以人的意志自由、灵魂不死、上帝存在作为条件是信仰主义的;不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找到道德和幸福一致的可行的路径而简单地将其推到“彼岸世界”是“肤浅”的。但实际上当他承认人又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是一个“感性存在者”、一个“有需求的存在者”,不可避免地要受自然欲望的影响要追求幸福,而“幸福”包含着敏捷、健康、财富,幸福的匮乏则与贫穷相联系时,又认为物质财富的获取、利益的实现、个人意志自由等关系幸福实现的条件又必须有法权的保证,借助于法权幸福才能成为德性的报偿、有德之人才能得到幸福。为此他讨论了私人权利、公共权力,人们按照国家公共权力分配权利,他举例说政府可以采用征税、建立基金会的方式强制富人提供物资以帮助那些缺少必须生活资料的人。法律保证个人的财产权,人的幸福因为有个人财产的支持而成为现实可感、个人可以掌控或可以争取的东西具有了现实性;通过法律、制度体制的安排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进入了一个由法律、制度保障的目的王国,从而提出了人的幸福实现的现实途径[6]。这种对幸福实现方法的探讨使幸福实现既不抽象又不彼岸。
在近代英国的功利主义者边沁·密尔、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等思想家那里,这种对幸福实现方法的探讨已经成为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的思想家那里更是如此,以致哲学在向“政治哲学转向” :探讨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国家的制度如何才能是正义的、合乎所有人的利益的(合乎所有人利益的才是能够实现所有人幸福的)。罗尔斯的理论就是这一“政治哲学转向”的体现。
罗尔斯指出 :“正像一个人的幸福是由在不同时刻及时经验到的、构成个人生活的一系列满足形成的,社会的幸福也是由属于它的许多个人的欲望体系的满足构成的。个人的原则是要尽可能地推进他自己的福利,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体系,同样,社会的原则也是要尽可能地推进群体的福利,最大程度地实现包括它的所有成员的欲望的总的欲望体系”[7]21,因此他致力于具有正义价值的社会制度制定方式的探讨,希望通过制定出正义的社会制度合理“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7]5,社会制度要实现正义(公正)并成为普遍的规范前提是具有特殊价值观念的不同的权利主体能够形成价值共识,所以《正义论》之后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专门探讨了“重叠共识”的形成。
《正义论》及《政治自由主义》出版后引起的世界性的反响,说明探讨幸福实现方法问题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切。
二
对幸福生活探讨从诠释到方法的转变,是乡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分配社会资源模式的不同在伦理学理论上的反映。
城市古已有之,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但什么是城市、城市如何界定,至今没有一种定义能够被学界公认,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城市的复杂性。学者们对城市定义的不同在相当程度上与不同学科研究城市问题的角度不同有关。本文并不研究城市问题本身,因此不诉求对城市本质的界定,而是以城市社会结构作为分析的框架,研究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城市社会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的条件下,社会结构如何才能公平分配关系人的幸福生活的社会资源的伦理问题。所以,乡村社会结构与现代城市社会结构的差异是我们要分析的。
所谓社会结构“主要是一种社会资源、社会机会在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稳定性模式。”*关于社会结构的界定学术界颇有分歧,本文采用的是郑杭生等学者的观点,见郑杭生、李路路等著《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从历时态的视角乡村社会同城市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相继形成的两种社会结构。
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最早是村庄,城市是在村庄中发展起来的[8]9-20。据研究城市在旧-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从此开始了“古老的村庄文化”“逐步向新兴的城市‘文明’”的退让[8]32。但工业革命前的城市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之上,作为城市构成要素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无法容纳大规模的城市人口,直到工业革命时的1750年,“世界城市人口估计只有250万”[9],占总人口的3%,所以这一阶段就整个社会而言,城市被农村所支配,起着“第二位”的作用[10]67,是乡村社会。
乡村社会是传统的,其社会结构是一种总体性结构。总体性社会结构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单一的权力主体掌握着社会的所有资源并决定着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在乡村社会,社会资源掌握在国家、土地(传统社会在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的所有者地主、贵族手中,其他成员只能被动地接受分配的资源,对国家、地主、贵族有着依附关系,没有个人权利意识和诉求。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占总人口少数的“公民”(奴隶没有独立的人格)将自己与城邦国家融为一体,认为城邦国家就是自己的利益所在,服从城邦国家才是自己能够得到更好生活的保证,因此苏格拉底在被判处死刑后拒绝朋友安排的逃跑计划而甘愿受死,理由是他整个一生都享受城邦法律的保护,所以他有义务遵守法律,而遵守城邦法律忠于国家就是他所理解的更好的生活,是善生即幸福,哪怕为此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亚里士多德认为,贵族政治是最好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法律体现着社会上最好的公民的利益,社会的目的是使个体公民能够过一种有德性和幸福的生活,所以公民要遵守法律,要合法。而最好的公民又有理性、追求至善目的“为高贵的动机所推动,促进别人的福利,为祖国服务”[2]108。个人是生活的目的与国家是生活的目的二者是一致的,对公民个人而言,相信国家要使公民过幸福的生活,就是在相信国家能够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因而国家构成了公民幸福生活的当然的条件,公民只需向内探求修养自身、与外部生活相协调就可以达到幸福生活的目的。
工业革命后,机器大工业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吸纳到城市,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到195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达到了29.2%,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53%,成为世界局部城市社会,2008年世界城市化率达到50%,实现了全球城市化,“人类世界从此正式走进了普遍繁荣的城市时代”。
城市社会是现代的[10]67。与传统社会不同,城市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社会是一种多元社会结构,其根本特征是不同阶层各自拥有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形成了多元主体。按照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的观点,在人类文明发展之初起着社会秩序组织作用的祭司阶层,在古代城市发展中成为“新的城市秩序的主要组织者”,并且“牢固地掌握了物质世界的统治权”,而决定城市发展的是商人“从祭司的手中夺取经济控制权”这一体制性变革因素。所以从发生的角度看,城市从一开始就与商品交换、与商人对商品的所有权相关,从而决定着城市的居民与农村的农民相比有着更多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有着偏离统治权力的自由或自治,从而能够成为权力主体。到了中世纪,欧洲的一些主要城市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一些家族凭借着这些财富掌握了巨大的政治权力,“城市拥有最高权威,是所有政治决定制定的基础。”乔尔·科特金认为,这种状况显现的是“清晰的现代版的城市政治”[11]5。就是说在现代城市拥有财富、能够支配社会资源的阶级和阶层发展成了权力的主体。资产阶级革命使个人权利包括个人财产权成为法律权利;工业革命使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和专业化,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日益多样化,形成了多元主体的社会结构,各主体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都能够支配相应的社会资源,也就成为不同的权力主体。不同的权利主体和权力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城市社会必须要建构一个能够被多元主体共识为公平的资源分配的原则,唯有这种被共识为公平的分配原则才能够得到普遍的遵守,因而才能够使人们因得到自己应得的社会资源,从而有条件追求更好生活而感到幸福。
得到不同社会主体认同的公平观念,由此形成的得到普遍遵守的公平的制度规则决定社会成员的幸福观,并由此成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所谓合法性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包含民众对政府权威的承认和服从。显然,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必须建立在公平观念的共识性和体现公平观念的分配原则被普遍遵守的基础之上,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而一个以公平为基础的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民众幸福生活的基本保证。反过来说,民众的幸福决定着政府的合法性,民众的幸福感表达了对政府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认同,是对政府治理社会所依据的制度规则的认同,因而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同。民众的幸福感由制度的公平效应决定了政府的合法性,政府的合法性又因为公平的制度而保证了民众的幸福,二者互为因果。因此,就社会治理而言,如何才能够在多元主体中建构起公平的分配原则,即公平的分配原则的构建的方法问题就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被利奥塔等人表述为后现代的社会,城市社会的主体不仅多元对立,而且碎片化了,普遍性、一元性、同一性、确定性等遭到质疑,代之而起的是对特殊性、多元性、差异性和变异性等的肯定和崇尚,要协调特殊性、多元性、差异性,寻求共识性成为时代难题。所以,社会共识的形成就成为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着力研究的问题并因此决定了其研究的重要实际价值。
三
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社会的形成历史地提出了探讨幸福生活的方法问题。
所谓幸福生活实现的方法,严格地说是用来分配社会资源的公平的制度规则的建构方法的研究,旨在探讨公平的制度规则应如何建构,其目标、程序、目标实现的支持要素等。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并不构成问题,人们没有对其进行质疑的动机和可能,因为那时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总体性的社会,而且是特殊的总体性社会。其特殊性主要在于 :第一,分配上的高度平均主义,在资源所属高度集中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基于平均的公平感;第二,意识形态的统一性,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对民众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行为协调作用。二者相互作用,政府对资源的掌控和平均分配客观上形成了民众对政府的依赖感和认同感强化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又支持了政府对资源的掌控和分配,不仅消除了人们利益上的差异,而且也抑制了人们谋求特殊利益的冲动。所以规则的普遍性和规约的有效性,是这种特殊的总体性结构内在生成而无需建构。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一元发展为多元,成为一个多元社会。改革的目标是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转变必然要加快推进城市化。因为现代城市以工业的发展为基础,是“主要依靠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城市”[11]133,“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阶段,工业化体现经济内涵,城镇化体现空间内涵”,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普遍化形成市场经济,造就了普遍的市场主体,从而形成了多元的社会主体和价值的多元化,形成多元社会结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确定了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工作方针,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将新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明确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大大提高了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的17%左右到2015年的56.1%,一个多元的城市社会已经形成。
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必然对原有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形成冲击。一是市场与经济手段在资源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增大,二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后者使政府对资源的掌控失去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导致了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前者则带来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拉大,低收入或收入增长较慢的群体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导致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二者联系叠加的结果是更多的财富并没有使民众产生更大的幸福感,收入增长并没有使人们的同期平均幸福感同步增长甚或下降了,出现了“生活变好,感觉变糟”的情况,即所谓“幸福悖论”。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 Veenhoven教授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1~10标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4、2005、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7年的13 786元增长到2011年的21 810元,但幸福感却没有同步增长。《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3》中以在社会保障、福利政策、教育、医疗方面都占据“首都”优势的城市北京市为参照,对重庆、上海、郑州、天津、成都、广州6个城市进行调查,显示由从2007年到2011年相对剥夺感的平均值而得出的幸福感的情况为 :天津、郑州和重庆5年中相对北京有降低的趋势,上海和成都低于北京,只有广州最优,但其幸福感的增长速度小于同期北京的幸福感的增长[12],在这个意义上幸福悖论可以归结为人们的不公平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无法与城市原住居民享有同样的公共服务,在劳动就业、工资待遇、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这是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关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部署,目前全国已有30个省份取消了农业户口,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但真正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直以来,分配不公导致民众幸福感降低是一些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原因,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影响了政府的合法性,也影响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念,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极为不利。所以就社会治理而言,不仅要提出未来发展的愿景、蓝图、目标,而且要重视对获取幸福生活或更好生活的方法的研究。
第一,在观念层面,应以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成就说明改革开放的主张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以此增强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混合所有制等改革措施使社会成员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利益获得占有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着极大的不同,一些社会成员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往往因此产生了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这是一个把蛋糕做大还是把蛋糕分好孰先孰后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采取一些激励先把经济搞上去把蛋糕做大的措施是必要的,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共同富裕就成为财富分配的新目标,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也是改革开放的目的所在,改革开放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理念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明确这一点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引导多元社会主体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提高社会共识。
第二,在制度设置层面上,应通过沟通、对话、协商等方法使其能够体现多元利益主体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帕累托最优进而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自觉的遵守。沟通、对话就是在制度制定时让不同阶层、城市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充分表达自己的价值理念、利益诉求,协商就是这些特殊群体商量协调寻求一致的过程,在新制度制定中能够体现各方的最大利益达到多赢,对已有制度的改革应当是增加或保持相关主体的正当利益而不是相反(即帕累托最优),使不同的主体都能够在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坐标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的制度就会让人们自觉遵守。
第三,培育多元主体参与制度设计的支持性要素,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保障制度,保证共识形成的合理有效和持续发展。旨在形成共识的多元主体的沟通、对话、协商必须建立在平等尊重包容的基础上,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城市原住居民还是外来人口权利平等,要尊重他人说话的权利,要包容异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念;得到普遍遵守的制度规则必然能够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所以不同群体、不同类型的人对社会的公共资源要有分享意识;要有遵守作为社会合作条件的制度规则的理性态度。城市主体的平等观念、相互尊重、包容、分享、理性等合理素质要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多元主体沟通、对话、协商的保障制度,制度化了的多元主体的沟通、对话、协商机制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并促使社会共识的持续发展。
[1]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9.
[2] 梯利.西方哲学史 :上[M].葛利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3] 赵敦华.西方人学观念史[M].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5.
[4]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20.
[5] 布尔克.西方伦理学史[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65.
[6] 杨秀香.论康德幸福观的嬗变[J].哲学研究,2011(2):85-92.
[7] 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9] 新玉言.国外城镇化 :比较研究与经验启示[M].北京 :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 :2.
[10]赛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1]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王旭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牛文元.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3[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3 :117-120.
[责任编辑王银娥]
DiscussiononaHappyLifefromInterpretationtoMeasures——ACaseStudyofUrbanizationinChina
YANG Xiu-xiang
(SchoolofMarxism,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
Happiness, as people’s life goal,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Western thinkers’ study on it has experienced a diversion from its interpretation to its implementation of a happy life, which is the ethical reflection of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ountryside to the modern city. Strictly speaking, the method of realizing a happy life refers to the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institutional rules for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An urban society is a diversified subject structure, and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principle of fair resources allocation which can be recognized by multiple subjects, and which can be widely followed so as to make people feel happy because they can get their due social resources to pursue a better life. People’s sense of happiness determines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fair effect of the system, and also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is a guarantee for people’s happiness because of the fair system. Both of them are reciprocal causation, which is the value of the diversion of the study on the issue of happiness. Historically,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formation of a urban society put forward some methods of exploring a happy life.
a happy life; diversion of study on happiness; urbanization in China; urban social structure
B82-052
:A
:1001-0300(2017)04-0033-06
2017-03-2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公共伦理研究”(13BZX077)的阶段性成果
杨秀香,女,山东莱州人,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