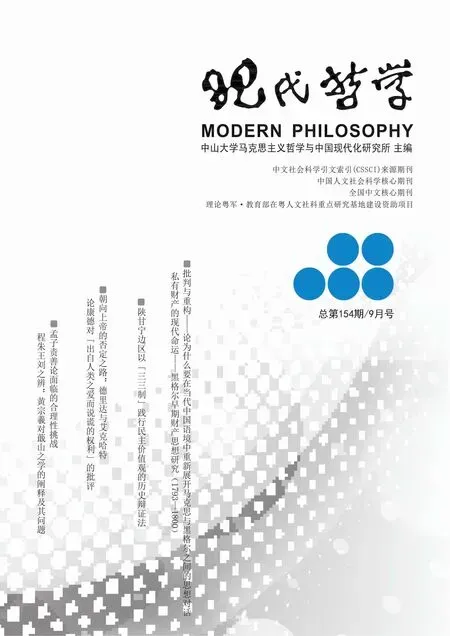“性体”与“情识”
——论张岱“情欲解放”与“道德严格”的两相并行
冯宁宁
“性体”与“情识”
——论张岱“情欲解放”与“道德严格”的两相并行
冯宁宁
张岱的思想继承了阳明心学的基本面貌,主张作为本体的“性”为无善无恶而又为至善,以“真情”为人之性灵,并在本体意义上把“性”与“情”两相同一。因此一方面,他既强调“情”的合理性,以此来张扬个体的独立自由,另一方面又强调“率性而中”,要求“情”的表现须合乎“性体”之本然。“情欲解放”与“道德严格”在张岱那里是可以两相并行的,而作为两者之间强大张力的内在制衡,则是“诚”。本文对张岱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刻剖析。
张岱;情欲解放;道德严格;性情;诚
张岱(1597-1684)*关于张岱卒年,史上有不同记载。清雍正《浙江通志》及清嘉庆《山阴县志》均载其“年六十九卒”;清乾隆《绍兴府志》载其七十九岁卒;邵廷采《思复堂文集》载其“年七十余卒”;温睿临《南疆逸史》及徐承礼《小腆纪传补遗》均载其年八十八卒;商盤《越风》载其“年九十三卒”。因201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清沈复粲抄本张岱著《琅嬛文集》,内有《万休师修大善塔》诗、《大善寺修塔功德圆满碑》文,可知张岱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尚在人世,是年八十八岁,可知张岱卒年最早应为1684年。至于“年九十三而卒”的记载,至今尚无明证。,浙江山阴人(今浙江绍兴),字宗子,号陶庵、蝶庵、蝶庵居士、古剑等,博通经史,长于为文,著作宏富。除大量小品美文以及史学著作以外,还有《四书遇》《明易》《大易用》等经学(理学)作品。然其论《易》二书久已散佚,唯《四书遇》独存,于1984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浙江图书馆于1934年购得原藏于江苏常熟周氏鸽峰草堂的《四书遇》未刊抄稿本,列为浙江图书馆甲级特藏稿本。198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朱宏达先生整理点校的《四书遇》,自此,张岱的理学作品才逐渐为人所知。。《四书遇》是张岱读四书的札记,亦是阐发其理学思想的主要作品。关于张岱的研究,学术界向来集中于文学、史学领域;随着《四书遇》的出版,其理学思想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与研究兴趣*目前,学界以张岱哲学思想及《四书遇》为研究主题的学术专著仅有台湾学者简瑞铨所著《张岱〈四书遇〉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一书。该书对《四书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包括其诠释方式、义理内涵、内容特色等方面,拓展了张岱思想研究的义阈。但是,该书比较注重张岱单个哲学观点的诠释,在各个观点之间的贯通上稍显缺乏,体系性不足。台湾学者邓克铭在《晚明四书说解研究》(台湾里仁书局,2013年)中的第五章,对张岱《四书遇》的注解特色进行分析,并对《四书遇》中的重要思想观念进行探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韩焕忠《佛教四书学》(人民出版社,2015年)一书,在第四章第三节探讨了张岱对四书的佛教解读,从三教合流的视角研究张岱的四书学观点。以张岱哲学思想及《四书遇》为研究中心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朱宏达的《张岱〈四书遇〉的发现及其价值》、台湾大学黄俊杰的《张岱对古典儒学的解释——以〈四书遇〉为中心》、张燕的《张岱与明代心学人物》、张夸的《以张岱为例浅析明末清初思想的变异》以及管技本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四书的心学视角——以张岱〈四书遇〉为个案的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15年)。这些论文主要侧重于剖析张岱对四书的解读,对张岱本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的探究则相对较少。。
张岱的理学思想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一方面,他坚持阳明哲学“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基本立场,又坚持对其后学在实践上流于玄虚放荡的批判;另一方面,他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吸纳程朱理学、蜀学等诸家之说,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完整观点,整体上因应了反思王学的时代潮流。综观张岱的一生,以明、清嬗代为转捩点,虽然其前期之放浪不羁与其后期之作为守节“遗民”,其行迹似乎判若二途,但若剖析其思想可以发现,其前后仍是“一以贯之”的。就其思想本身而言,原本就蕴含“情欲解放”与“道德严格”之间的独特张力,本文正以此为出发点来论述张岱的思想。
一、“性体无善无恶”与“性至善”
张岱的理学思想建立在关于“性”的认知之上。在他看来,性体是无善无恶的,性体超越于善恶之上,是不能用价值来评判的。《论语·雍也》“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一段,张岱释曰:
性体无善无恶,无背向,无取舍;离此离彼而卓尔独存,非中非边而魏然孤立。故曰“直”如千仞峭壁,非心思意识之所能攀跻。*[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0—161页。
依照张岱的观点,性体是“魏然孤立”的,没有背向、取舍,离彼离此,非中非边,它超越于一切心思意识,没有价值属性。也就是说,“性”是一个绝对理念,不能作为价值判断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他既批评孟子的性善论,也反对荀子的性恶论。
张岱对孟子性善说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孟子的以情言性上。他认为“孟子盖即情以论性也”,并引用张侗初之言,对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也”与孟子的性善说进行评论:
圣人说“性相近”,较孟子说“性善”觉浑融。盖圣人尚说习前之性,孟子却说习中之性。子思说天命之谓性,是在习前说,率性之谓道,则在习中矣。人生堕地才动,知觉便是习。知爱,知敬,都是习始也。试看父母未生前如何?*同上,第337页。
他认为孟子所说“性善”之性是“习中之性”,与孔子所说的“习前之性”并不一致,以“习中之性”所表达出的“情”来逆推“性善”是不成立的。他进一步反驳孟子对性善的论证:
孟子说性善,亦只说得情一边,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恻隐为仁之端,而举乍见孺子入井以验之,然今人乍见美色而心荡,乍见金银而心动,此亦非出于矫强,可俱谓之真心耶?*同上,第507页。
他认为孟子是从情之善的一面来论证性善,然而善只是“情”之一边,“情”亦有不善的另一边,荀子即是以“情”之恶来论证“性恶”的,所以,“荀子性恶之说,亦自有见,第不可以之立教万世耳”*同上,第118页。。二程与朱子均认为孟子“论性不论气”,即孟子只论天地之性(习前之性)而不论气质之性(习中之性)*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第197—202页。。张岱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恰与二程、朱子相反。张岱对孟子性善论的理解和批评,究其思想来源,应与王阳明有密切关系。王阳明曾就当时的“性”之争论,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说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
王阳明认为古人论性之所以各有异同,是因为对“性”的理解角度不同,“性”只是一个,从本体上讲,性是无善无恶的,但从发用、源头、流弊等方面说,又会有不同的结论。张岱亦认为性体是无善无恶的,他不仅以“只说得情一边”来批评孟子性善说,亦以“盲人摸象”之喻来批评其它性说为一偏之见,未见性之本质及全体*[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507页。。
这样看来,张岱实远承阳明之说,主张性体无善无恶。但是,无善无恶之性体却需要通过经验层面来展现自身,即所谓“从来本体,未有不见之作用者”*[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57页。。从先验层面来讲,人承天命之性,人之性与天之性通而为一,此即是道;从经验层面上讲,人率性而为,下学上达,即是与天道合一,“天命之性,天而人者也。合而言之,道也。率性之道,人而天者也”*同上,第21页。。正因如此,“性体无善无恶”同时是至善的。张岱引用张侗初之言曰:“元气虽含藏,故四时必备。圣性虽深静,故五德俱全。”*同上,第62页。圣性“五德俱全”,即是至善;而圣性与天道合一,故天命之性亦是至善的。
“性无善无恶”与“性至善”看似矛盾,但这恰恰是张岱性论的独特理论关照。“性体无善无恶”是一个属于先验范畴的本体论命题,性体是超越一切现象而绝对无待的。张岱一直强调性为“独体”,即“独者无对之称,有伦斯有对矣。观毛犹有伦,则知丝毫有对,终非独体”*同上,第67页。。性体“卓然孤立”而“无伦”,所以它不能施以经验的价值判断。但是,性体又必须通过经验层面来表现自身,若从经验角度来对它进行审视,性又是至善的。“无善无恶”与“至善”为一体两面的原因是:第一,“无善无恶”之性体,就其作为存在本体而言,它恰好代表了绝对价值本身,故为至善;第二,正因“无善无恶”之性体同时必为价值本体,是一切经验价值的照鉴者,故为至善。张岱继承阳明学派的基本观念,认为“心即性”(不过,张岱在使用“性”与“心”之概念时,往往在强调超越层面时使用“性”概念,在论与经验相关的问题时,则多使用“心”概念),并说:
人心原来至静,亦至动,如镜子随照随灭,故常照。若终日有个影子在镜上,便对面不受照矣。圣人之心惟无在,故无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同上,第12页。
事实上,王阳明早有“无善无恶,是为至善”之说。诚如董平所说:“作为最高价值理念的心本体,只有当它超越于任何相对价值,不落于善恶一边的时候,才可能如明镜之高悬,鉴察一切善恶美丑,才可能如规矩,虽规无圆而矩无方,但方圆自不能遁其形。”*董平:《王阳明四句教意蕴发微》,《宋明儒学与浙东学术》,贵阳:孔学堂书局,2016年,第164页。在这个意义上讲,“性”亦是至善。
二、“性”与“情”
“性”“情”关系的恰当处理构成张岱理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他认为“天命之性,天而人者也”,“率性之道,人而天者也”,那么人要归复于天道,就应当在日用伦常之中“率性”而为:“君子深造必以道。道者,率性者也。以道方自得,非由外铄,我固有之者也……”*[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468页。所谓“率性”,是以“性”的本来状态而将它表现出来,所以“率性”即是“诚”,是自我内在心灵与天命之性两相契合而无间隔,人的现实生活是可以通过“诚”来实现最高价值的:“诚即性也。诚至而性浑然全矣,有何不尽?尽性即是尽人性、尽物性也……无不有,乃无际之虚空。无不照,乃无尘之净境。此尽性之义也。”*同上,第50页。“诚至而性浑然全矣”,“诚”即是“中”“正”,“正心”“诚意”是一贯工夫。张岱说:
意者,心之动。其实心无离意之时,虽默坐眠梦都有觉在。所以说善澄水者,去垢不去波;善正心者,去妄不去意。先儒训诚以实,似也;不若《中庸》解“诚者,自成也”,有见成天不容伪之意。*同上,第10页。
“诚意”之功,非难非易。看得太易,恐认情识作本体,是袅爱子*此处“袅爱子”,疑为“枭爱子”之误。寒山有诗云:“贪人好聚财,恰如枭爱子。子大而食母,财多还害己。”可知枭有子大食母的自然特性,此处以“枭爱子”作喻,阐明“情”由“性”生,但“认情识作本体”,终会遮蔽本体。;看得太难,恐祛情识寻本体,是提灯觅火。此皆有志于“诚意”而卒失之。*[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4页。
可见,张岱是特别注重“心”与“意”、“本体”(性)与“情识”(情)之间关系的厘定的。“意”是“心”的发用,“心”无时无刻不在起“意”,因此所谓“正心”,并不是断绝意念,而只是要祛除妄念。心体之所发与心体本身不是一回事,但意既是心之所发,便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除去妄意、妄念,即是“正心”。在“性”与“情”的关系问题上,张岱也认为“情”是“性”的必然发用,“情”保证了“性”不沦为空寂,“情”的发而中节,即是“性”的应然表达,只有“过”或“不及”之情,才流于价值上的不善。他既肯定了“情”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强调不能离“情”而论“性”,又强调要谨慎对待“情”,不能以“情”为“性”。论述孟子性善论时,张岱指出: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孟子盖即情以论性也。贺瑒云:性之与情,犹水之与波,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盖即此意。李习之乃欲灭情以复性,亦异乎孟氏之旨矣。*同上,第507—508页。
照此看来,“性”“情”之本体实为同一,亦犹“水”“波”之体一不二。“即情以论性”固可能误入歧途,“灭情以复性”则必如缘木而求鱼。前者之过,或误将情识作为本体,则本体之性必为情识所掩;后者之误,则灭裂心身,本体必落虚玄。在张岱看来,“性”必藉“情”来呈现其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为“声色”辩护:
鹤鸣而子和,目与而心成。声色,亦化民所不废也,而本在焉,故曰“末”,不得尽说坏声色。*同上,第66页。
“情”为“性”之发,“性”为“情”之本,“声色”是情,“亦化民所不废”,故不当“尽说坏声色”,因离“声色”之情则“性”亦无由表达。在张岱看来,“真情”、“真性”恰恰是个体最宝贵的。“岱尝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明]张岱著、夏咸淳点校:《张岱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49页。理想人格原是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传统理学家认为需要尽行革除的“癖”与“疵”,在张岱看来却不仅具有其合理性,而且是个体性所需要彰显的,因为“深情”、“真气”正是“性(心)”的率真体现。显而易见,张岱其实是在心性学的架构之中为“情”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安置,从而充满了个体自由与解放的意味。
在这样一个具有情欲解放倾向的理论建构之下,张岱强烈批判虚伪、拘板的伪道学。他在注解《论语》“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时,尝说:
此皆圣人自然之德容,非相济之谓也。睟面盎背,着一毫妆点不得。故宋儒有学“恭而安”十五年不成者,亦大可笑事。几分“温”几分“厉”,自作秤量,觉圣人于此笑啼俱不敢矣,岂不板杀?*[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191页。
这种要求在“率性”前提之下而表达“真性”、“真气”的思想,体现在文学上便是其“独抒性灵”之说,而体现在史学上,则是秉笔直书,求真求实,不为世俗之见所裹挟,而直抒人物之精神气貌。但是,这并不表示张岱赞同所谓“任情恣性”,恰恰相反,为免于沦入隐怪狂者之流,他认为必须谨加“戒慎”、“恐惧”的修养工夫,要有所“忌惮”:
杨复所曰:“忌”字即“戒慎”二字,“惮”字即“恐惧”二字。“无忌惮”者,无“戒慎”、“恐惧”之心也。大抵异端只为大胆误了事。千古圣学,唯有小心而已。
冯具区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自以为“中庸”也。其“无忌惮”处,正是认“无忌惮”为“时中”耳。此小人不是小可,正是隐怪一流人。*同上,第23、24页。
这些观点表明,就张岱个人的思想倾向而言,他显然是推崇阳明学的,其思想路径也基本上属于阳明一系。他既希望能够给“情”找到一个合理张扬的空间,又希望能够将“情”严格地控制在“性”之所发的合理限度之内。正是在“性”、“情”的巨大张力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张岱对阳明后学之弊病保持着清醒反思,并试图将心性修养功夫落到实处的思想努力。
三、情欲解放与道德严格的并行
张岱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思想家。他既批判传统理学对人之“性灵”的桎梏,更抨击伪道学的虚伪。他主张“学贵自得”,要通过“学”来建立一个独立的精神主体。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严格的道德主义者,认为应当时刻检视自己的内心,以保证“情识”的表达能合乎“性”之本然。正是这种“性”“情”之间的内在理论紧张,导致张岱“情欲解放”与“道德严格”之间的两相并行。
在张岱那里,衡定道德的标准不能是人的外在表现。若以行为外观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道德水准,那么“世岂无衣冠尧禹,而行同桀跖者哉!”*[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73页。外观既不足恃,则评判标准只能是内在的“心”。只要“心”不受“习”“气”“私”的遮蔽,便能行于中道而廓然大公,则“率性”而出之“情”,即是“性”的体现。
董日铸曰:……率性而出,则为“中”、“和”,倚于气禀,则为南北。需从心体入微处辨别。
王道伯业,只在根本毫厘上差别。浮云太虚,功名便是道德,金屑着眼,功名只是功名。*同上,第32、112页。
“心体入微处”,即是“心”的自体状态,它既是行为的依据,又是道德评判的准则。但他同时强调,“心”虽具有超越性,却是极易为“习”所熏染的,因此功夫须在“习”上做,而“诚”之一字,则是全部功夫所应落实之处。他论曾子曰:
曾子一生得力止一“诚”字。“忠恕”是“诚”的表德。格豚鱼,贯金石,只有“诚”字担当得起。*同上,第125页。
曾子认“忠恕”为孔子“一贯之道”,而张岱认为“忠恕”只是“诚”的“表德”,显然“诚”是较“忠恕”更为内在的。在张岱那里,“诚”既是“性”,也是功夫,作为功夫的现实落实,即是“性”的经验体现,所以“人须要识得个诚体性体。无假之谓诚。有此诚,故性用不沦于空寂。无碍之谓性。有此性,故诚境不滞于思为”*同上,第50页。。诚之“无假”,即同一于“性体”,故“诚体”即是“性体”;现实行为的“无假”,即是“性”之用的现实体现,“故性用不沦于空寂”。可见,作为功夫的“诚”正是“无假”地体现“性体”(也是“诚体”)的根本方式。“性”是“情”之本,而“情”是“性”之用,两者皆以无假之诚为其终极规定,则“情欲解放”即是“道德严格”,两行不悖。
张岱的这一主张,显然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就其个人的思想倾向与生活实迹来看,他实际上更多地主张个性的自由解放,要以“性灵”来对治拘板,就需要为“情欲”安置一个合理空间;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阳明末流的工夫疏旷之病,以至于任性放诞,流于猖狂,所以又要以“小心”来对治猖狂,从而又必然需要“道德严格”。“情欲解放”与“道德严格”之间的内在张力,迫使他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寻得一个合理的制衡点,“诚”终于在他那里成为这一制衡的关键。在“率性”意义上的“诚”,既是无假之真情,则“解放”为应然;既须确保“情”必为真而非假,则“严格”为必然。“情欲”与“道德”的“解放”与“严格”之间,正因此而在“诚”的基础之上获得了并行的现实可能性。看似矛盾的两种倾向,经过张岱的合理措置,终究获得了统一。这一以“诚”为“性”、“情”间内在张力之制衡的思想,不仅在哲学上是有意义的,而且也可以解释张岱本人的生命轨迹,既有风流名士的洒脱不羁,又奉行着严格的道德主义。众所周知,其前后生命轨迹的转变,乃是以明清易代为其根本的转捩点的。
B248.99
A
1000-7660(2017)05-0148-05
冯宁宁,河南开封人,哲学博士,(杭州 310023)浙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