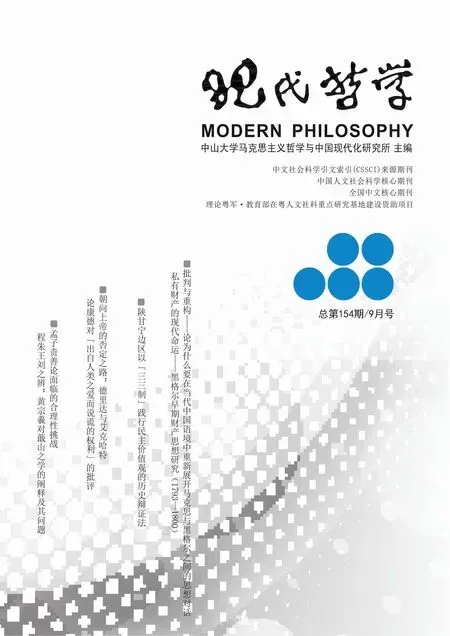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
张圆圆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
张圆圆
黄宗羲作为王门后学的一名得力干将,同时也是与王夫之、顾炎武齐名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他集“王门后学”与“明末启蒙思想家”的身份于一身,对明代阳明心学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定位,这一定位即“立心学为圣学”。在尊崇与维护阳明心学的基础上,黄宗羲不仅对阳明心学和释老之学做了区分,而且还努力为“王门四句教”辩难,试图从“心即理”的命题出发,划分儒释之界限;也试图通过重新理解“四句教”的涵义、置疑“四句教”的出处,以剔除“四句教”对阳明心学的负面影响。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不仅充分显示出其本人的学术好尚,同时也反映出其作为一名学术史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明代学术领域中阳明心学、程朱理学和释氏之学的论断和评价。
黄宗羲;阳明心学;定位;辩难
以往学界对黄宗羲的研究,多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其民本思想和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制度的批判,忽略了其作为一名理学家和学术史家,站在一定的学术立场对阳明心学做出的定位。黄宗羲是明末大儒刘宗周的学生,其本人又身处明清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出于对故国的怀念,黄宗羲对作为明代理学主流的阳明心学,有着极深的感情。在其师学的影响下,黄宗羲提出了“心气合一”“理性合一”的思想,他的气一元论思想,被刘述先先生表述为“内在的一元倾向”。作为心学传人,黄宗羲不仅致力于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与修正,而且在学术史研究领域,给予阳明心学极高的评价和定位。在其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中,黄宗羲用28卷的篇幅,记述、梳理、评价了王守仁心学及王门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同时,又根据王门后学所处的不同地理位置,将其划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六个派系,在《泰州学案》和《止修学案》中,对显著偏离心学的“泰州学派”和“止修学派”提出批评和指正,并在末卷第62卷设《蕺山学案》,以示其师刘宗周集阳明心学之大成和对心学的修正与总结。可以说,在黄宗羲的学术史观中,上承孟子之学、下至阳明心学的心学体系,始终是儒学发展的主线,是为圣之学,而阳明心学又是圣学的时代彰显。因此,黄宗羲在其著作中,用大量笔墨对心学做出了“圣学”的判断。然而,阳明心学自产生之时,便受到程朱理学的挑战,被质疑为“儒释杂糅”,而当时流传甚广的王门“四句教”又是引阳明心学入禅的一个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立心学为圣学”“为阳明学辨儒释”以及“为王门四句教辩难”等问题,阐释黄宗羲尊阳明心学、抑程朱理学与释氏之学的学术思想。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在结合黄宗羲理学思想的基础上,把研究视角投向“哲学史研究”领域。这样不仅区别于以往学界单向度地偏向于对黄宗羲心学思想的义理性研究,还能够为我们研究深入了解黄宗羲学术史观,提供有益的参考,更重要的是,也能够为现当代的阳明心学研究,提供一个特殊的思考路径。
一、立心学为圣学
黄宗羲认为,天下学术的发展遵循着“一本万殊”这样一条总的规律,即以儒家学说为天下学术之本,以儒学多元化发展而呈现的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学说为万殊之学,而在儒学范围内各种学说的共同发展中,“心学”一支是主线。在黄宗羲看来,阳明心学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悠久的历史渊源,其由先秦时期孟子的心性之学发展而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被赋予丰富的义理性阐释,而对于孟子之学,黄宗羲又将其评价为“千圣相传者心”的学问。所以,黄宗羲将阳明心学定位为圣学。
黄宗羲曾撰《孟子师说》(共七卷),这里“师”指明末大儒刘宗周。刘宗周是王门后学蕺山学派的创始人,也是黄宗羲、陈确和张履祥等人的授业老师。黄宗羲在《孟子师说》这部哲学著作中,借助阐释《孟子》章句的方式,记载了其师和黄宗羲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倾向。在《孟子师说》中,黄宗羲既肯定了孟子之学为“千圣相传”之学的历史地位,又高度评价了阳明心学对孟子之学的发展与延续。黄宗羲指出,“仁”是没有迹象的,孟子却能在“无迹象之中”,点明了“仁”存在的现实根据,即“仁义礼智”根源于人心,“仁”发端于人的“恻隐之心”,以及“人心”与生俱来的全部内容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清]黄宗羲著、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他还指出:“千圣相传者心也……禹、汤、文、武、周公五君子,其功业盖天地。孟子不言,单就一点忧勤惕虑之心之描出,所谓几希也。”*同上,第113页。他认为作为“仁”存在依据的“心”,是圣人们之所以为“圣人”的共通之处,孟子虽然没有“禹、汤、文、武、周公”这五位圣人的功业,但仅从孟子对“忧勤惕虑之心”的描述而言,孟子的贡献和历史地位足以能够达到这五位圣人的高度。
继对孟子之学的总结和高度评价,黄宗羲进一步阐述了阳明心学继孟子之学而来的观点。他说道:
“人皆可以为尧舜”一语,此孟子继往圣开后学一大节目。徐行尧服,人人能之,即人人可以为尧舜也,只在著察之间耳。后之儒者,将圣人看得烦难,或求之静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穷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见端倪,遂使千年之远,亿兆人之众,圣人绝响……自阳明之心学,人人可以认取圣脉。*同上,第144页。
在黄宗羲看来,孟子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语,点出了圣学的精要和为圣的功夫,而后世儒者却将成贤成圣看得繁琐,直到阳明出现才扭转了这一局面,王阳明打破宋儒所提倡的“静坐澄心”和“格物穷理”之旧规,指出了良知自在,延续了孟子的圣人之学,创立了阳明心学,点明了人们成贤成圣的实现路径,由此,阳明心学是圣脉相传的圣学。
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不止一次地称论阳明心学为圣学。例如,他在《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中记载陈献章的理学思想时指出,明初学术多不失程朱理学之矩矱,直至陈献章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点出了“静中养出端倪”,开启明代心学之端,“作圣之功”才至陈献章而始明,后至王阳明而始大。在黄宗羲看来,“白沙之学”与“阳明心学”两者一脉相承,皆是对孟子圣人之学的延续,由“白沙之学”至“阳明心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即圣学在明代由微到显的过程。又如,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黄宗羲立心学为圣学的思想,再次得以明确的表达。黄宗羲指出,明代以来的学术都是墨守先儒之成说,学者们未曾“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然而,阳明心学打破了学术领域这种僵化的格局,动摇了程朱理学独尊学术思想领域的地位,以可贵的学术自得和创新精神延续了古来之学脉,更重要的是,其提出了“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的观点,使道德先验与道德自律意识重新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继孟子之后又一次开启了人们的“作圣之路”*[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8页。,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明]王守仁撰,董平、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9页。。在黄宗羲看来,姚江之学恢复了已中断千百年之久的圣学之学脉,使儒家道统得以延续,因此为“作圣之学”。
二、为阳明学辨儒、释
黄宗羲以心学为儒学之大宗,以阳明心学为圣学这一学术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阳明心学在明代中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尽管如此,阳明心学自明初发端之际,其入禅倾向,就持续遭到程朱理学派的批判与指责;尤其到了明代中后期,在其传播、发展与流变中,王门后学之流弊日益凸显,由此,这种批判愈为强烈。明代初期,陈献章之学开心学之端,程朱理学派的胡居仁便批评陈献章“静中养出端倪”和“藏而后发”的思想为“将此道理来安排作弄,都不是顺其自然”*[清]黄宗羲著、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5页。,也指出陈献章虽然“窥见些道理本原”,但是却无格物穷理之渐进工夫,所以其思想只为“空见”*同上,第35页。。而对于陈献章之“物有尽而我无尽”之说,胡居仁则将其指责为“氏释见性之说”*同上,第39页。。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中记载道:“先生(胡居仁)必欲议白沙为禅,一编之中,三致意焉。”*同上,第30页。也就是说,胡居仁在论学中,已经将初具心学倾向的白沙之学划入禅学。罗钦顺则认为,王守仁之学以知觉为性,把知觉当作“良知”和“天理”。但是,在他看来,禅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知觉为性,不仅如此,禅学还把人的知觉和意识看作万物的根本,宣扬“心生万法”的思想,禅宗的这一特征与阳明心学的“心即理”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由此,一向极力批判释老之学的罗钦顺,也带有批判性地将阳明心学划入了禅学的范畴。明末斥心学为禅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顾炎武和王夫之。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说“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认为阳明心学为“阳儒阴释”的“诬圣之邪说”。这些对阳明心学入禅的批判,给阳明心学做了“外儒内释”的定性,与黄宗羲尊崇阳明心学为圣学的学术立场截然对立。基于此,黄宗羲从找寻阳明心学和禅学的差异着手,试图为阳明心学辨儒、释,以划分心学和释氏之学的界限。
黄宗羲指出,对于“心”的不同理解,是阳明心学和释氏之学的本质差别:阳明心学视“心”为“理”,而释氏之学视“心”为“知觉”。他说:
而或者以释氏本心之说,颇近于心学,不知儒释界限,只一理字。释氏于天地万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复讲,而只守此明觉;世儒则不恃此明觉,而求理于天地万物之间,所为绝异。然其归理于天地万物,归明觉于吾心,则一也。向外寻理,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总使合得本体上,已费转手,故沿门乞火与合眼见闇,相去不远。先生(阳明)点出心之所以为心,不在明觉,而在天理,金镜已坠而复收,遂使儒释疆界邈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睹也。*[清]黄宗羲著、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81页。
在黄宗羲看来,疑心学类禅者,在于其没有认识到儒释的界限在于一个“理”字,释氏之学不寻求万物之理,只把守知觉意识,而对心学持批判态度的“世儒”虽然“不恃此明觉”,但是却于心外求理,这在本质上与释氏“归明觉于心”是同一的。黄宗羲认为,王阳明指点出“心之所以为心”,不在于心有知觉,而在于“心即理”,即将“心”看作一切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根据。也就是说,在黄宗羲那里,阳明心学与释氏之学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对“心”的内容的不同理解上。
在《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中,黄宗羲又一次以“心即理”为着眼点,辨阳明心学非释氏之学。
今以理在天地万物者,谓之理一,将自心之主宰,以其不离形气,谓之分殊,无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视理在天地万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即理,则自不至为无星之秤,无界之尺矣。先生(杨时乔)欲辨儒、释,而视理与佛氏同,徒以见闻训诂之争胜,岂可得乎?阳明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释界限,而以禅宗归之,不几为佛氏所笑乎?*[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24页。
在黄宗羲看来,杨时乔分“心”与“理”为二,将“理”看作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存在,这一思想与释氏的“理在天地万物”的观点相同,皆属于“无星之秤”和“无界之尺”而不得要领。同时,黄宗羲批判了杨时乔欲辨儒释却拘泥于“见闻训诂”之争的错误路径,认为只有王阳明在“虚灵知觉”(“心”)之中,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才真正辨清了儒释之界限。进而,黄宗羲批判了归心学为释氏之学的儒者,指出其这种做法反而为佛氏所讥笑。
在《明儒学案》的《粤闽王门学案·行人薛中离先生侃》中,黄宗羲进一步以阳明心学中“心即理”的思想为切入点,区分了儒、释之差异。他说:
深于疑阳明者,以为理在天地万物,吾亦万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为己有。阳明以理在乎心,是遗弃天地万物,与释氏识心无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阳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万物之理具于一心,循此一心,即是循乎天地万物,若以理在天地万物而循之,是道能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释氏之所谓心,以无心为心,天地万物之变化,皆吾心之变化。譬之于水,释氏为横流之水,吾儒为原泉混混不舍昼夜之水也。*[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上册,第656—657页。
在这段话中,黄宗羲首先列举了“深疑阳明类禅”者的错误认识,即他们把理置于天地万物之中,以人为万物中之一物,分人与理为二,同时又认为王阳明合心与理为一的“心即理”的思想,与释氏唯心的思想相类似。其次,黄宗羲为阳明心学辩护,指出“深疑阳明类禅”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在于,没有理解到王阳明的“理在乎心”的思想是指天地万物的理都存在于“内心”,这种“理在乎心”的思想强调的是人作为道德主体,其道德与生俱来的先验性和将道德施之于事事物物的主体能动性,体现的恰恰是孔子所强调的“人能弘道”思想(而不是“道能弘人”),这样,黄宗羲从儒家经典《论语》中寻找理论依据,进一步确立了阳明心学的圣学地位。最后,黄宗羲分别对释氏之学和阳明心学做出了不同的比喻,将释学比作“横流之水”,将阳明心学比作“原泉混混不舍昼夜之水”,来表明两者的差异之处。黄宗羲不仅批判了“疑阳明类禅”者(宋儒)对阳明心学的错误理解,还指出了宋儒分心与理为二,混淆了儒学和释氏之学的界限。由此,在黄宗羲看来,不是心学类禅,而是宋儒类禅。黄宗羲认为,宋儒的“理在天地万物”的思想,是将理看成了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宋儒向心之外的万物寻理,在本质上与释氏只守此知觉之心而置理于心之外的做法大同小异,两者的不同不过是宋儒向外求理,而释氏不求理罢了。在此基础上,黄宗羲批评了程朱理学的“理”派生出“气”的近禅思想。释氏之学有“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寥寂,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之言,而宋儒提出了“理生气”的思想,这两者在黄宗羲看来,都是在“心”之外预设了一个先验的客观存在的派生世界万物的本源,在释氏那里,这一客观存在的本源是指“有物先天地”之“物”,在宋儒那里则指“理生气”之“理”,释氏的“物”和宋儒的“理”两者具有相同的逻辑和意义。黄宗羲认为,宋儒对理气关系的阐释,并没有对理学和释氏之学做出正确的区分,反而将两者等同起来,由此引来释氏的耻笑。在批判与指责宋儒的基础上,黄宗羲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阳明心学,认为阳明心学“心即理”的思想及时纠正了宋儒入禅之弊端,“遂使儒释疆界邈若山河”。由此可见,黄宗羲不仅为阳明心学辨儒释,划清了阳明心学和释氏之学的界限,而且还指出了程朱理学近禅的弊端。这样,黄宗羲不仅为立阳明心学为圣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进一步巩固了阳明心学的儒家正统地位。
三、为“王门四句”教辩难
“王门四句教”由王阳明晚年贵州龙场悟道时提出,其具体内容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对于这四句话哲学内涵的阐释,王门后学中产生了分歧,其中以王畿和钱德洪两人为著。王畿对“四句教”的理解被称作“四无说”。在他看来,“四句教”的第一句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既然“心体”为无善无恶,那么“心体”之“意”“知”“格物”也是无善无恶的。而钱德洪对“四句教”的理解被称作“四有说”,认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天命之性是至善的,因此心体是至善而无恶的。对于王畿和钱德洪的各抒己见,王阳明对两者进行了调和,折中地说道:“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以遗念矣。”*[明]王守仁撰,董平、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06页。王阳明指出“四无说”和“四有说”两种观点都成立:王畿的理解代表“上根人”而言,因为“上根人”能够顿悟出心体之无善无恶,无需循序渐进之工夫;而钱德洪的理解是针对“下根人”而言的,因为“下根人”只有通过“为善去恶”的功夫通过渐修的方式才能够体认本体。在王阳明看来,“四有说”和“四无说”各有长短,单纯地依靠“顿悟”或“渐修”都无法实现成圣之目标,“上根人”和“下根人”都应该结合“顿悟”与“互补”的方式,最终达到至善。所以,王阳明指出,“四句教”的第一句话是为了阐发“四无说”,意在强调“顿悟”的重要性,后三句话是为了阐发“四有说”,意在强调“渐修”的重要性。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促使了王门后学分划为“本体派”和“功夫派”,同时,其对“四无说”的认可,也遭致了程朱理学派的批判。很多人指责王门四句教中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属于释老之说,背离了传统儒家的“性善”思想。
黄宗羲毕生力斥释、老之学,且坚持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因而否认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的合理性。因为黄宗羲是阳明心学的尊崇者和维护者,所以他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并不是出自阳明之语,而认为这句话是由后人错会阳明之意而产生的。黄宗羲说道:
彼(错会阳明之意者)以无善无恶言性者,谓无善无恶斯为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无善之善,无乃断灭性种乎?彼在发用处求良知者,认已发作未发,教人在致知上着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远矣。得羲说而存之,而后知先生之无弊也。*[清]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上册,第179页。
也就是说,在黄宗羲看来,良知是至善的,而“错会阳明之意者”的错误之处在于以“无善无恶”界定“性”,以“无善无恶”为“至善”,以至于把“善”分解成“有善之善”和“无善之善”,这种做法无疑是“断灭”了“性”的根本,同时,他们(“错会阳明之意者”)在意念发动之处(“已发”)探求良知本体,只注重功夫,而没有真正停留于良知之处体认良知的本然状态,这种做法反而对“良知”是愈求愈远的,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违背了王阳明的性善思想。因此,在黄宗羲看来,“无善无恶”之说并非阳明之本意。
而对于王门“四句教”中“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句的内涵,黄宗羲自有其理解。他说道:
天泉问答“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体无善无恶是性,由是而发之为有善有恶之意,由是而有分别其善恶之知,由是而有为善去恶之格物。”层层自内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机,则良知已落后着,非不虑之本然,故邓定宇以为权论也。其实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恶,亦是有善念有恶念耳,两句只完得动静二字。*同上,第178页。
也就是说,在黄宗羲看来,心体之性为“至善”,并非人们对“四句教”的错误理解——以“心体无善无恶是性”。他认为,对王门“四句教”第一句的正确理解,应该为“心体之性”是一种“无善念无恶念”的“静”的本然状态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是最高的善;基于此,可以推衍出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旨在表达“心体”已发状态为“意”的“有善念”“有恶念”。以上黄宗羲对“四句教”的理解,对后人研究这一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现当代学者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在对“四句教”第一和第二句的理解中,将“心之本体”解释为“无有作好无有作恶”的超越之本心,将“心体”的发动理解为经验层面上的“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对黄宗羲辨王门“四句教”的延续与发展。
在为王门“四句教”辨难的过程中,黄宗羲不仅提出了“心体”为至善的观点,而且还就“四句教”的出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王门四句教的“无善无恶”一句,并非王阳明本人提出的,而是王畿伪造的。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具体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粤闽王门学案·行人薛中离先生侃》中,黄宗羲说道:
又其所疑者,在无善无恶之一言。考之《传习录》,因先生去花间草,阳明言“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盖言静为无善无恶,不言理为无善无恶,理即是善也……独《天泉证道记》有“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之语。夫心之体即理也,心体无间于动静,若心体无善无恶,则理是无善无恶,阳明不当但指其静时言之矣。释氏言无善无恶,正言无理也。善恶之名,从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恶得言无善无恶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证之,则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阳明也。*[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上册,第657页。
人们对“四句教”的质疑,往往在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薛中离去花间草,考证了一个事实,即王阳明说过“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之言:在王阳明那里,“理之静”是“无善无恶”的,而“气之动”则“有善有恶”,也就是说,“无善无恶”的侧重点在于“理之静”的“静”,而并非“理”,“理”是“心之体”、是至善的,贯穿于动静,而“四句教”中“无善无恶心之体”仅仅强调的是“以静言理”,并非王阳明本意。基于以上推论,黄宗羲得出“天泉证道”之言为王畿伪造,并非王阳明本人的真实思想。黄宗羲还说道:“当时之议阳明者,以此为大节目。岂知与阳明绝无干涉。呜呼!天泉证道,龙溪之累阳明多矣”*同上,第1379页。,进而划清了阳明心学与使阳明学备受争议的“王门四句教”两者之间的界限。
四、结 语
综上所述,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是以立心学为圣学为终极目标的。在他看来,阳明心学承接孟子之学而来,提出了“心即理”的思想,使人人具备了成贤成圣的可能。在尊崇阳明学的过程中,黄宗羲努力为阳明心学辨儒释,以“心即理”之命题,作为区分心学与释氏之学的主要标志,并将程朱理学之理本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与释氏之学等同划一。同时,在认同“王门四句教”使阳明学背上入禅嫌疑的基础上,黄宗羲先是对“四句教”中“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进行重新理解,然后又置疑“四句教”的出处,最后得出结论,即“王门四句教”并非出自王阳明,而是出自王畿伪造。黄宗羲围绕定位阳明心学的一系列学术思想和论断,不但充分显示出其本人的学术好尚,而且反映出其以主观学术见解为依据,对异己学说的学术偏见,也反映出黄宗羲作为明末阳明后学中的一名得力干将,对心学的修正,以及其作为一名学术史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明代学术领域中阳明心学、程朱理学和释氏之学的论断和评价。
B249.3
A
1000-7660(2017)05-0135-06
张圆圆,黑龙江同江人,哲学博士,(哈尔滨 150001)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习与探索》杂志社助理研究员。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专项项目“以《明儒学案》为中心的中国哲学视阈下的传统学术史思想研究”(14D062)
(责任编辑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