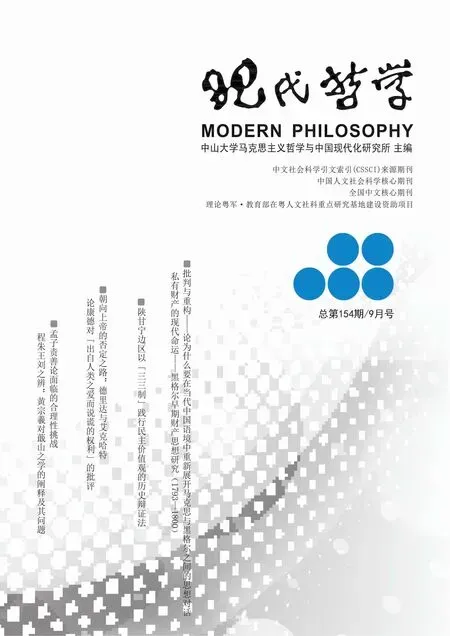程朱王刘之辨: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释及其问题
李训昌
程朱王刘之辨: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释及其问题
李训昌
程朱王刘之辨是明末清初学人论学的一大节目,黄宗羲作为心学主将之一,也参与其中。宗羲程朱王刘之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以阐发蕺山之学为主要目的:会通王刘,借阳明学以申师说;贬抑程朱,又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黄宗羲此论,虽在借古人之说以申己义,却也遮蔽了其师的甘泉渊源,使蕺山晚年对理学和心学、甘泉学与阳明学的综合,折入阳明心学一途。
朱子学;甘泉学;阳明学:蕺山学;程朱王刘之辨
“甘泉的哲学体系,是一个突破理学而又吸收理学,主张心学而又批评(陆王)心学的独特的心学综合体系。”*乔清举:《湛若水哲学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226页。其主要目的在于吸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长的同时,避开两家之短。在唐枢-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一系的甘泉后学中,唐枢、许孚远延续甘泉的思路,开始会通甘泉学与阳明学;刘宗周的诚意说“乃是沿着甘泉以及其师许孚远的思维路线,吸收阳明良知概念的部分内涵,而提出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心体概念,这个概念达到了纠正王学末流之流弊的目的,同时,也表明了湛学与王学的合流”*同上,第244页。。与刘宗周专注哲学体系的建构不同,黄宗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按师说对宋元明三代理学做了系统的梳理。因此,可以说甘泉学与阳明学的合流,是刘、黄师徒二人共同完成的。不过,刘宗周殁后,黄宗羲对师说的阐发却与程朱王刘之辨结合在一起。这既与明末对阳明学的反激与清初朱子学的复兴有关,也与整个时代精神从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的转化有关。黄宗羲会通王刘,借阳明学以申师说;贬抑程朱,又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这是黄宗羲在民间学者与官方学术两次程朱王刘之辨中,不得不采用的求全之法,其目的则在保全师说。只是黄宗羲主张阳明太过,对朱子学成见太深,反而遮蔽了其与其师的甘泉渊源,使蕺山对理学和心学、甘泉学与阳明学的综合,折入阳明心学一途。
一、《子刘子行状》:开始会通王刘
《子刘子行状》上下卷,又名《蕺山传》,是黄宗羲为补救刘汋、张履祥等人删改其师遗著的过失,而记述其师生平学行的纪传体史书,约成书于康熙四年上半年*张如安:《黄宗羲著作补考》,《古籍研究整理学刊》2001年第2期,第54页。。在《行状》中,宗羲只是说其师“中年专用慎独工夫。慎则敬,敬则诚”*[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0页。,那么,黄宗羲究竟是以慎独说还是以诚意说为蕺山最后宗旨的呢?在《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中,黄宗羲开篇即说:“先生之学在慎独。”*[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页。在《忠端刘念台先生宗周》中则谓:“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8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90页。按时间顺序来说,《行状》最早,《宗周》次之,《文集序》最晚,为黄宗羲晚年写定,当为最后定见。但是,从刘宗周的为学历程来看,他“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清]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因此,刘宗周的最后宗旨是诚意说而不是慎独说*东方朔:《刘宗周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那么,黄宗羲为什么要以慎独说为蕺山最后宗旨呢?
刘宗周26岁师事许孚远,直到37岁著《心论》才悟心外无理之说,于是有“甲寅悟心”之论。他早年不喜象山、阳明,此时也未接触陆王心学之书,而且其工夫克治省察与学问思辨并重,俨然程朱巨擘,不类阳明。其实,刘宗周接触阳明心学有一个过程,其对阳明学认识上的转变也有内外两方面的机缘。从过程上来说,自天启六年刘宗周读书韩山草堂,学朱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清]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82页。,一面“专用慎独之功”*同上,第82页。,一面“取有明诸儒文集、传记考订之”*同上,第82—83页。;越明年,著成《皇明道统录》,“自逊志、康斋外”,又推重“曹月川、胡静斋、陈克庵、蔡虚斋、王阳明、吕泾野六先生”*同上,第84—85页。;是故,“读《阳明文集》,始信之不疑”*同上,第85页。。如前所述,黄宗羲在《行状》中对蕺山宗旨的概括就出了问题。他的说法完全是抄自《蕺山刘子年谱》天启六年、七年条的按语,而这只是刘汋对其父在天启七年前为学的评论,而不是对其一生学问的总结。黄宗羲以此来论定师说宗旨,就抹杀了其师将其慎独说发展为诚意说的理论旨归。同时,这两年正是刘宗周对阳明学信之不移的阶段,也为黄宗羲会通师说和阳明心学埋下了伏笔。
刘宗周对阳明学的认识和态度“凡三变”,如黄宗羲说:“盖先生于新建之学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而新建之旨复显。”*[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254页。黄宗羲此论,也源自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崇祯十六年条的按语。与宗羲之说相较而言,刘汋明言刘宗周于阳明学“辨难不遗余力”的具体所指,即“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谓其言良知,以《孟子》合《大学》,专在念起念灭用工夫,而于知止一观全未勘入,失之粗且浅也”*[清]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147页。。天启七年,刘宗周之所以崇信阳明学为圣人之学,主要是因致良知之旨与其慎独说相类,俱为心学。但是,两人主张毕竟不同,所以刘宗周一方面指出阳明致良知在工夫与教法上的不足,如他说:
先生承绝学于辞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求学者支离眩骛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机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有之。*同上,第85页。
“所性之觉,曰良知”说明刘宗周与王阳明不同,不以良知为性体,而以良知为性体的发觉显露。这是刘宗周借鉴吸收阳明良知说,将其慎独说发展为诚意说的内在思想线索。另一方面,他还着手沟通其慎独说与阳明之致良知。崇祯二年,刘宗周著成《大学古记约义》,始以阳明“慎独即是致良知”*[明]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50页。的提法会通阳明学。崇祯四年,在《证人会约·书后》中,刘宗周则谓:“孔门约其旨,曰‘慎独’,而阳明先生曰:‘良知只是独知时’,可谓先后一揆。慎独一著,即是致良知。”*[明]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98页。因此,直到崇祯九年刘宗周59岁创立诚意说时,他一直在会通阳明之致良知与其慎独说。崇祯二年、四年,黄宗羲两次亲炙蕺山讲席,耳濡目染,受蕺山影响,即以慎独说为师门宗旨,以会通师说和阳明心学为毕生的学术努力。
刘宗周提出诚意说的外在机缘,源于崇祯四年与阳明后学陶奭龄在越城共举证人之会。初次讲会,刘、陶二人即产生分歧,使刘宗周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对慎独说与阳明致良知之旨的会通,另寻蹊径。崇祯九年,刘宗周在京师讲学,辑成《独证篇》,提出了“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也”*[清]刘汋:《刘子蕺山年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117页。的命题。自此,刘宗周“专举立诚之旨,即慎独姑置第二义矣”*同上,第118页。。为了从根本上救正阳明后学流入禅学的弊端,刘宗周的诚意说更强调以性规定心的思想。崇祯十一年,刘宗周编成《阳明传信录》三卷,对阳明学作了系统总结:一则从学则、宗旨、教法上捡择阳明之说,指出致良知之旨在工夫与教法上的不足;一则将阳明与阳明后学流入禅学的弊病区分开来,为阳明辩护,即“间尝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时时权实互用,后人不得其解,未免转增支离乎?”*[明]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页。在编纂《明儒学案》时,黄宗羲将《阳明传信录》前两卷收入,定为《姚江学案》,正可谓坚持了其师维护阳明的立场。不过,黄宗羲误以刘宗周之慎独说会通蕺山、阳明,不但有失其师综合理学与心学、甘泉学与阳明学的学术精神,而且有抹杀其师诚意说之哲学努力与贡献。同时,黄宗羲按师说特别是以性规定心的思想对阳明致良知的解读,集中在阳明“四句教”上;解读以后,黄宗羲已经很难在师说和阳明学之间做出区分。这是导致黄宗羲会通蕺山、阳明的内在思想线索。
二、《孟子师说》:转入贬抑程朱
《孟子师说》七卷,是黄宗羲以《孟子》章句形式阐发师说的哲学著作,约成稿于康熙八年。成稿后,黄宗羲又不断修改,故现行本有康熙八年以后的材料*郑宗义:《黄宗羲与陈确的思想因缘分析》,《汉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70—71页。。康熙六年,黄宗羲应万氏、董氏兄弟之邀,讲学甬上。黄宗羲初至鄞城,即以其师之《子刘子学言》《圣学宗要》授诸生,次至《人谱》《原旨》和《证学杂解》;越明年,乃讲授《四书》《五经》。至此,由黄宗羲主持的甬上证人书院,始由讲授蕺山之学转入阐发《四书》《五经》的经世致用之学。不过,黄宗羲讲《四书》即以师说为标准。在他看来,其师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于《论语》有《学案》,独于《孟子》无成书,亦无成说。他潜心师说有年,虽不能无所出入,但窃取师说而著成《孟子师说》七卷,“以俟知先生之学者纠其谬”*[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8页。。由此可见,黄宗羲在甬上讲《四书》,主要是以传播蕺山之学为目的,即“丁未,复举证人书院之会于越中,以申蕺山之绪”*[清]全祖望:《梨州先生神道碑文》,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页。。
职是之故,黄宗羲的《孟子师说》处处针对朱子的《孟子集注》也有顺理成章的一面,本无可厚非。如他说:“成说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8页。这说明他针对的是明代官定的《四书大全》,还有以之为标准的科举考试所造成的牢笼士人思想之弊,即“愤科举之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2册,第3页。。但是,《四书大全》又以朱子《四书集注》为蓝本,所以他说“屏去传注,独取遗经”*[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8页。,实质上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朱子。又如他在评介张邦奇时所说:“夫穷经者,穷其理也,世人之穷经,守一先生之言,未尝会通之以理,则所穷者一先生之言耳。”*[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545页。这里的“一先生”,根据上下文亦明指朱子。
但是,在《孟子师说》中,黄宗羲往往是先论述自己的观点,再引朱子之言以示批评,再冠以“羲以为”、“愚谓”的总结,最后引证宋明诸儒的语录以佐证其说。黄宗羲如此阐释《孟子》大义,就把对师说的阐发演绎为了对朱子的批评。如他对《浩然章》的解释:
朱子云:“配义与道,只是说气会来助道义,若轻易开口,胡使性气,却只助得客气,人才养得纯粹,便助从道义好处去。”羲以为养得纯粹,便是道义,何消更说助道义。朱子主张理气为二,所以累说有了道义,又要气来帮贴,方行得去,与孔子“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之言,似有径庭。*[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65页。
黄宗羲由养气工夫进而批评朱子的理气、心性二分,实涉及理气心性关系问题。其实,在此一问题上,刘、黄师徒二人的理气心性合一论俱导源于湛若水*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4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不过,刘宗周综合程朱陆王而进退之,对朱子阳明都有所批评、有所拨正,但他的态度比较平和,观点相对周正,如他说:
时谈禅者动援阳明而辟朱子,先生曰:“朱子以察识端倪为下手,终归涵养一路,何尝支离?阳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于去人欲存天理以为致良知之实功,何尝杂禅?”*[清]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124页。
刘宗周批评“援阳明而辟朱子”者,是为朱子辩诬,其慎独说即以批评调整朱子学为目的;批评援朱子而辟阳明者,则是为阳明辩诬,其诚意说即以批评调整阳明学为目的。从理论上来说,刘、黄师徒二人的理气心性一元论确有拨正朱子理气、心性易离为二的作用。但是,在心性关系上,刘宗周也批评阳明,其意、念之辨即是如此;而黄宗羲则置若罔闻,把问题都推给了朱子,主张太过,有所偏颇。其实,在《孟子师说》中,黄宗羲的很多观点都源自朱子,如《孟子师说》开卷第一句“天地以生物为心,仁也”*[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9页。,以仁为天地生物之心,本是朱子的思想,而黄宗羲却将其当做儒家学者的共识,不复再提与朱子的关系。因此,在《孟子师说》中,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发就由会通王刘转入明确贬抑程朱。
三、甬上证人书院与海昌讲学:借阳明学以申师说、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
黄宗羲会通蕺山阳明,贬抑程朱,既与其在甬上证人书院、海昌讲学时,弟子之间的学术分歧有关,也与清初康熙右文,尊朱贬王,编纂《明史》理学传的论辩有关。前者主要发生在民间学者之间,后者则涉及官方学术。在两次程朱王刘之辩中,黄宗羲的基本立场是借阳明学以申师说,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这是清初朱子学复兴之际,黄宗羲不得不采用的求全之法,其目的在于保全师说。
甬上本为阳明学重镇,刘宗周与陶奭龄在越城共举证人之会时,史孝复、王朝式等人已从阳明学的立场怀疑甚至反对宗周对阳明学的修正。至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讲学时,其弟子董允瑫、董允璘等又因素习阳明之学,认为蕺山“意为心之所存”不合阳明,作《刘子质疑》质诸黄宗羲。于是,黄宗羲作《答董吴仲论学书》:“余谓先师之意,即阳明之良知;先师之诚意,即阳明之致良知。阳明不曰良知是未发之中乎?又何疑于先师之言意非已发乎?”*[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67页。由此,黄宗羲认为:“欲全阳明宗旨,非先师之言意不可。”*同上,第149页。同时,邵廷采本为姚江书院韩孔当的学生,后问学黄宗羲,转而信服蕺山之学,即“致良知者主诚意,阳明而后,愿学蕺山”*邵廷采:《思复堂文集》,祝鸿杰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4页。。与此不同,陈锡嘏作为甬上证人书院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力主朱子的格物穷理说,与蕺山之学“独依回其间,恕人量己,卑之无甚高论。非敢过自沮弃,抑亦不能无疑于心也”*陈锡嘏:《陈母谢太君六十寿序》,《兼山堂集》卷四,转引自方祖猷《黄宗羲长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1页。。黄宗羲批评他说:“君从事于格物穷理之学,于人情事势物理上工夫不敢放过,而气禀羸弱……故阳明学之而致病,君学之而致死,皆为格物之说所误也。”*[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46页。陈锡嘏不改朱子格物穷理之说,黄宗羲认为他之死“虽其天性,亦其为学有以致之”*同上,第446页。。这无异于说朱子之学是死人之学,过于偏激。
甬上证人书院最严重的学术分歧,源自清初反理学的先驱潘平格。康熙八年,潘平格从昆山回慈溪老家,东至宁波,西至绍兴,宣传自己的求仁哲学。及至甬上,潘平格首先说服其慈溪老乡、黄宗羲弟子颜曰彬,引起不小波动。其时,万斯同馆于姜希辙家,并不在绍兴,至其回到绍兴,不但亲至慈溪“诘其说,有据”*李塨:《万季野小传》,《恕谷后集》卷六,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83页。,而且还将其书带回鄞城,始稍信潘平格之学。黄宗羲的另一弟子毛勍在观潘平格之书后说:
余少受业于南雷黄先生,学蕺山刘子之学。癸丑岁馆于宁城,因万季野得先生书数帙,一见而嗜之。同志者皆非余,余信之益笃。*毛勍:《潘先生传》,《潘子求仁录辑要》,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页。
毛勍虽“未亲受业于其人,而私淑之,求其全稿,守而弗失”*毛勍:《序》,《潘子求仁录辑要》,第2页。。郑性则赞誉潘平格之学,“真可谓表里无间而终始一贯者矣”*郑性:《序》,《潘子求仁录辑要》,第3页。。至此,潘平格的求仁之学在甬上证人书院引起轩然大波,几至分裂,致使黄宗羲不得不出面主持大局。黄宗羲移书姜希辙、万斯同,批评指责潘平格之学,《与姜定庵书》《与友人论学书》即因此而作。概而言之,潘平格作为反理学的先驱,指责“朱子道,陆子禅”,认为“朱羽陆释”,将宋明七百余年之理学一概否定。黄宗羲则为维护一代理学之传,从“灭气”、“灭心”、“灭体”三个方面对潘氏之学作了批评,认为“用微有此三弊,故其放而为淫诐之辞,有无故而自为张皇者,有矫诬先儒之意而就己议论者”*[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54页。。黄宗羲此时心里反倒清楚,潘平格的批评迁延开去,其师可能被一并划为“一群僧道”。因此,在《与友人论学书》中,黄宗羲表面上是在为朱子、阳明等宋明诸儒辩护,实质上他的反驳处处以师说为标准,处处是在维护师说。这是其老辣世故的一面。不过,黄宗羲措辞严厉,指责潘平格为“兔园老生”,其学为“祖师禅”、“名母之学”,则反激过甚,已超出学术讨论之范围。万斯同虽被黄宗羲之激烈态度所压服,但心里怏怏不快,谢曰:“请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李塨:《万季野小传》,《恕谷后集》卷六,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3页。及至晚年,在李塨影响下,万斯同才发觉潘氏之学的不足,转而倾向颜李学派。后来,全祖望批评黄宗羲一生不脱党人习气,盖因此而发。
在面对清初反理学思潮时,黄宗羲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平章朱、王,为朱子、阳明辩诬,继而为传播蕺山之学张本。这一立场与他在参与官方的程朱王刘之辩时,借朱子之言以维护蕺山、阳明相同。不过,与其师维护朱子、阳明的态度相比,黄宗羲之说甚有差距。又如:
余讲学海昌,每拈《四书》或《五经》作讲义,令司讲宣读,读毕,辩难蜂起,大抵场屋之论,与世抹杀。余曰:“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谓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是也。”*[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4页。
黄宗羲对朱子的批评,一定程度上与清廷将朱子学定为官学有关;其反对朱子与反对科举,又与其不事清廷的遗民思想有内在联系。但是,这也与其天性有关,即“余平生颇喜读书,一见讲章,便尔头痛”*同上,第44页。。这里,黄宗羲说“朱子所谓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是借朱子之口以封攻诋者之口舌,实质上还是在维护师说。即如在史馆立理学传的问题上,黄宗羲的《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表面上是在融合程朱陆王,对朱子的态度有所缓和,其实是借之以维护蕺山、阳明。于此,他实有难言之隐,是其为维护蕺山、阳明而不得不在策略上的调整。此时,在民间学者与官方学术的双重压力下,黄宗羲已无法正面回应人们对心学特别是阳明学和蕺山学的的批评。
四、《明儒学案》:会众合一的蕺山之学
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除以师说为标准论定明代诸儒外,还积极维护阳明。这无论是从《明儒学案》的篇章结构还是从其对诸儒的评介上来说,都是有目共睹的。从《明儒学案序》出发,有一种观点认为黄宗羲综合朱子、阳明,主张一本万殊、学贵自得,是会通程朱陆王而为一。其实,他说的“会众以合一”的“一”具体所指是蕺山之学。他说:
士生千载之下,不能会众以合一,山谷而之川,川以达于海,犹可谓之穷经乎?自科举之学兴,以一先生之言为标准,毫秒摘抉,于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经大法,反置之不道。童习自守,等于面墙。*同上,第417页。
黄宗羲此说,除反对清廷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外,还反对以宗旨强附门墙、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争,即“尝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同上,第645—646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为真”*[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7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页。。又如黄宗羲在《恽仲昇文集序》中说:
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心,其书数卷可尽也,其学终朝可毕也。虽然,其所假托者朱子也,盍将朱子之书一一读之乎?夫朱子之教,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故曰:“若能读书,就中却有商量。”又曰:“且教学者看文字撞来撞去,将来自有撞着处。”亦思其所谓商量者何物也?撞着者何物也?要知非肤论瞽言可以当之矣。数百年来,儒者各以所长,暴于当世,奈何假托朱子者,取其得朱子之商量撞着者,概指之为异学而抹杀之乎?*[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页。
黄宗羲借朱子之语来讲学贵自得的精神,其主要目的是为其阐发师说张本,这是黄宗羲一以贯之的态度和方法。所以对他来说,最切实的自得之学,即是蕺山之学。因此,在编纂《明儒学案》时,黄宗羲一方面恪守师说,评介诸儒,即“间有发明,一本之先师,非敢有所增损其间”*[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4页。;另一方面,则体会诸儒之得力处,约之一二字为其宗旨,即: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之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同上,第5页。
对黄宗羲而言,其得力处在蕺山之学;对诸儒而言,则“是其人之得力处”;两者之间,黄宗羲约之在我,保持了适当张力,所以其《明儒学案》超出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峰《理学宗传》之上,成为后人研治宋明理学的津梁。有一种观点认为蕺山之学是明代理学的殿军,因此,黄宗羲以师说为标准,溯明而元而宋,逐一论定宋元明诸儒,也有其相当的合理性。
对蕺山之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891页。的期愿;在《孟子师说》中,他则假《乾》卦《彖辞》贞下起元之说,以道自任,甚是担当,即:
吴草庐曰:“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鲁邹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余以为不然。尧舜其元也,汤其亨也,文王其利也,孔孟其贞也。若以后贤论,周程其元也,朱陆其亨也,姚江其利也,蕺山其贞也,孰为贞下之元乎?*[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66页。
受康熙右文的影响,康熙十九年以后,黄宗羲开始承认清廷的合法性。但是,举目四望,昔日的学友悉数陨落,弟子后进也开始凋零,胡翰十二运交入大壮的希望业已破灭,担续蕺山之学的只有他孑然一人。所以,他说“孰为贞下之元乎”的心情是复杂的,梨洲末命,不棺而葬,只是期于速朽而已!不过,事与愿违,贞下起元的不是其所属愿的蕺山之学,而是浙东经史之学。
综合来看,刘宗周的最后宗旨当为诚意说。刘宗周在甘泉学的立场上综合程朱陆王而进退之,不偏袒一方,为宋元明三代理学之大成。惜乎,黄宗羲颠沛一生,亲炙蕺山时,又志在举业,未能注意师说宗旨的调整,虽然基本坚持了其师的思想纲领*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而力主会通蕺山阳明、贬抑程朱,不但有失其师综合理学和心学的学术精神,而且,“仅以阳明学之目光看其师之学。其编著《明儒学案》,于蕺山之甘泉渊源,更不复提起,遂遮蔽后人耳目,竟不知蕺山学术之自来,宗羲之误甚矣!”*乔清举:《湛若水哲学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233页。这是使用黄宗羲《明儒学案》时,必须注意的两个问题。
B249.3
A
1000-7660(2017)05-0141-07
李训昌,山东淄博人,哲学博士,(重庆 400100)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重庆 401331)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一般基金项目“清初河南理学研究及文献整理”(15BZX047);中国博士后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孟子师说》:刘宗周、黄宗羲的孟子学研究”(2016M592626)
(责任编辑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