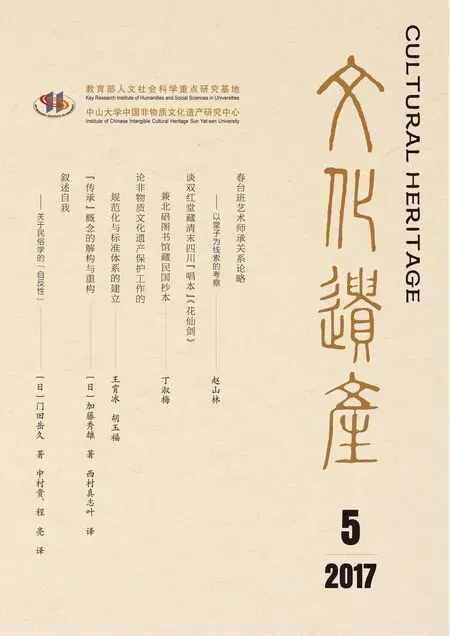“传承”概念的解构与重构*
[日]加藤秀雄著 [日]西村真志叶译
“传承”概念的解构与重构*
[日]加藤秀雄著 [日]西村真志叶译
自柳田国男在《民间传承论》中界定其研究对象为“民间传承”以来,日本民俗学围绕“传承”概念,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从田野看传承”或“由传承思考田野”,认为应努力把握田野里传承的实际面貌,借此显示出一种民俗学能够进行独到的调查研究之可能性;二是对传承概念的批判,主张不可以继续拘泥于其所蕴含“同一性/连续性”规范,仅仅探究具有“传承”性质的事象,否则今后的民俗学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传承”概念被“冻结”,背后存在着基层文化论和民族性理论的影响,这种传承观将有可能由行为论之传承理论逐渐得以“解冻”。民俗学有必要把握“生活世界中的传承”的实际情况,重新返回到田野,返回到生活世界,重构传承概念。
传承 田野 行为理论 后历史
序 言
近年来,日本民俗学围绕“传承”概念,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认为传承概念在认识民俗学的对象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民俗学应该探讨一种方法,以激发出该概念蕴藏在其中的潜能;另一种则指出,传承概念规定了新旧文化的同一性和连续性,正因为这种概念规定的存在,传承概念才难以适应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象,因此民俗学应该寻找另一种新的田野调查和研究的方式。
尽管如此,这两种立场却又站在同一个研究前提之上,即:二者均把传承视为一种实体概念,认为田野中应该存在某种等同于传承的现象或行为。我们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对于文化、历史表象中被隐藏的建构性和权力性问题的批判性讨论之后,既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那么,面对这两种立场赖以成立的前提,仍有必要以怀疑的目光去重新审视其存在论意义或认识论意义上的基础。比如,当小池淳一梳理传承概念所蕴含的问题和可能性时,就谈到了“用来审问历史叙事主体的诸如历史学批判、传统的创造等新视角”,他还据此把传承与“历史”问题相连接在一起,显示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假如我们重新检讨结构主义者对民俗学所做的批判内容,就可以发现他们批评的论点其实都来自于传承概念本身所隐藏的问题。
回过头来,村井纪、川村湊等人批判民俗学曾经给予殖民主义以支持(村井2004/1992;川村1996),他们的批判确实为二战结束以前的日本民俗学与思想家柳田国男的历史评价带来了冲击,甚至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转折点,然而,由这些批判引起的讨论并没有波及到实际的田野调查和记录中被隐藏的问题。直到岩竹美加子指出美国民俗学的研究实践所蕴含的政治性问题之后(岩竹編訳1996),日本民俗学中才逐渐出现了诸如民俗主义、文化财保护部门的思想背景分析等成果(岩本1998;2003)。其中,菊池晓在人类学“文字文化休克”的影响之下,极其详细地描绘出了奥能登地区的“Aenokoto”仪式得以“创造”的过程。长期以来,民俗学视“Aenokoto”仪式为一种能够启示田神与祖先神之间的连续性的重要对象,而菊池恰恰指出了该仪式在其形成过程中把宫廷祭祀与民间仪式、或者把天皇与常民联系在一起,甚至吸收了柳田国男的个人见解(菊池2001)。可以说,过去民俗学者把田野中的民俗传承视为某种自明性的存在,而菊池的研究从根本上对此提出了质疑。
那么,所谓传承是否就是只能令民俗学家看不清现实的一副墨镜?在传承概念的批判者们看来,只有卸掉这副墨镜才能拓展民俗学的研究领域。然而,假如他们加以批判的对象本身有误,又会怎么样呢?换言之,如果传承概念在它刚出现时根本就不具有今天成为批判对象的概念规定,那么批判者们还继续他们的批判吗?
这个疑问便是本文的基点。下面,我们将梳理民俗学界有关传承概念的讨论,努力指出这一概念至今没有失去有效性。为此,我们借鉴以下两种研究成果作为关键的资源:一是柳田国男《传承论》,此文关注了传承的变容,据此描绘出了“没有文字化的历史=史外史”;二则是近年来试从独到的观点对传承概念进行重新定位的历史哲学的相关成果。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确认一下传承概念在最近的日本民俗学界是如何被界定的。
一、围绕传承而形成的两种立场(一)从田野看传承,由传承思考田野
自从柳田国男在《民间传承论》(1934)中界定其研究对象为“民间传承”以来(柳田1990/1934),传承作为田野中被采集的民俗事象本身或者显示出传承性质的某些东西而广泛被接受,随之,对民俗学的对象认识产生了不少影响。同一时期,折口信夫也提出了“民俗=民俗传承”的观点,并进行了独到的分类(折口1967/1934),*请参见《日本文学大辞典》(1934)“民俗学”一项。折口提出来的传承分类包括周期传承、阶级传承、造形传承、行为传承以及语言传承等5种。本文将避免称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为“民俗”,而统一称之为“传承”(引文不限于此)。为的是将传承作为主要分析概念来分析对象的研究与基于其它目的意识的研究区别开来。我之所以强调传承一词,是因为希望明确一些传承概念的批判者所忽略的问题。我以为民俗学应该保持一种可能性,来在叙述田野生活及其历史的民俗志的实践层面继续运用传承概念。这一分类工作后来还影响到了国学院大学出版的《日本民俗研究大观》(1990)的整体结构。此外,和歌森太郎在其《日本民俗概说》(1947)中,对传承做了不同于柳田的分类(和歌森1981/1947:18),后来在《日本民俗事典》(1972)的“民间传承”一项里又发表了与折口相一致的看法(和歌森1972)。和歌森的分类包括“经济人的生活传承”、“社会人的生活传承”以及“文化人的生活传承”,所谓《日本民俗学讲座》就是在此分类法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民俗学的各种集成大系或讲座系列都依据有关传承的分类作为编辑基础,由此可知,民俗学的研究领域本身就是由传承概念来被规定的。然而,只要民俗学家们站在元素论的立场上来搜集、记录田野中的传承事象,与之密切相关的地域特征亦即“地域性”就会被除去。这一问题由山口麻太郎较早地提了出来(山口1974/1939),二战后的日本民俗学也因而对地域性、使传承得以“延续”的传承母体给予了极大关注(福田1982)。尽管如此,所谓地域民俗学也罢,基于地域民俗学的传承母体论也罢,其实都建立在传承概念的基础之上,因此与民俗学的传统形态即“从田野看传承”或“由传承思考田野”,差距并不大。
地域民俗学和传承母体论盛行于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而至今还有不少研究者努力去把握传承的实际面貌。
比如,最近田中宣一试从神、人、自然之间的动态关系中把握传承(田中2009:122-140),还据此讨论了目前的资料操作方法以既成分类为基础,今后能否从另外一种角度去认识对象。又如,真野俊和从“民俗始终都在变化”这一命题出发,认为“世上确实存在一种不同辈分之间的信息传达方式,叫做传承的这种传法方式应该具有极大的社会文化意义”,至于其效果和规范能力,视之为“民俗学应该解决的课题”(真野2009:92-96)。*尽管如此,根据真野的传承观看,传承并非是始终自立存在于田野,它不过是跨世代传达文化的手段之一,我们应该在与其它手段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理解。也就是说,“民俗学再怎么关心传承或看重其意义,只有其中的相对位置才能成为民俗学的对象”(真野2009:104)。尽管真野承认,对他所提倡的“homo-folklolicas/民俗人”来说,传承不过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可选项”之一,而且“研究者所要记述的人类世界里,每个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远远多于他们依托传承来可以处理的问题,传承作为研究者描述和分析的唯一工具显然是不足的”(真野2009:86),但对于把握田野中传承的实际面貌,真野仍然肯定其重要性,认为民俗学的主要课题就是“记录人们在各个生活场景里,根据怎样一种判断与价值观念,来继承和创造什么样的知识和技术”(真野2009:86)。
最能体现“从田野看传承”或“由传承思考田野”这一民俗学立场的人物,应该是新谷尚纪。新谷认为民俗学是“始终把历史的变迁论、传承论与地理的地域差异论、地域性论等放在其研究范围内的学问”,“以此为起点生产出新的理论或概念才是最重要的”(新谷2011:19)。他在最近的研究中,以有关全国墓制、葬制、道祖神的传承研究实践为例,站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上显示出了一种以传承资料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新谷2011:201-212)。值得注意的是,新谷并没有把柳田的比较研究法与为反对比较研究法而诞生的地域民俗学对立起来,也没有把生活的变化与传承对立起来,而努力摸索一种能够把二者相“并含”的视角,这便是其论述的特点所在。可以说,这一特点主要来自新谷对传承的基本认识,即:“传承是动态的,礼仪结构也罢,组织结构也罢,都不是作为一种固定样就如永远不变的拷贝一般传承下来的”(新谷2004:98)。
上面,我对继承和发展“从田野看传承”或“由传承思考田野”这一民俗学立场的近期研究成果做了简介。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者努力去把握田野中传承的实际面貌,借此显示出一种民俗学能够进行独到的调查研究之可能性。
而目前,除了这种研究立场,学界还存在另一种研究立场与之形成对立,认为民俗学之所以无法适应多样化的社会事像,难以视之为研究对象,就是因为其方法论受到了传承概念的限制。下面,我们对持后一种立场的研究者所提出的批判内容加以整理,进而阐释一下传承概念所蕴含的问题。
(二)对传承概念的批判
前川智子在确认“一直以来民俗学者视民间传承和传承概念为一种可突出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差异性之概念”的基础上(前川2009:31),参考渡边欣雄对“传承”概念的批判,写出了如下一段话:
渡边欣雄对过去民俗学有关传承、传承人、民间传承的定义产生了怀疑。渡边并不认为某一特定的传承人传承下来的内容是永恒不变的,而把传承内容作为一种民俗知识来展开论述。(中略)在渡边指出的几点中,笔者希望强调以下一点:被命名为传承的概念,在现实社会中却未必意味着不同辈分之间的知识传达,被传达的知识本身时刻都在变化。
另外,现代社会里,一般都用数字化手段来传达信息,口头传达只限于特殊场合,如教育系统中的学校教育现场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民俗学者开始关注一些以文字为媒介传达信息的案例。关心信息化社会的古家信平探讨的“书承”概念便是一个例子。
利用传统概念去把握我们周围的现代社会整体,这实在是困难的。(前川2009:31)
这里,我们将前川的这一段论述简括为4点:
1.既成的传承概念把从古到今的“不变性”包含在其中;
2.现代社会里,某一事象即使被视为传承,也未必意味着不同辈分之间信息传达,其知识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3.现代的信息化社会里,口头传承被局限在教育现场等场合,当界定传承概念时应该考虑以文字为媒介的信息传达。
4.仅有传承概念,难以把握现代社会的整体。
其中,第一点如实地体现了前川对传承的看法,并成为了她从第二点到第四点展开论述的前提。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真野俊和曾经做过同样的讨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真野留下的影响(真野2009:92,103)。值得关注的是第四点。的确,如果传承指的就是从古到今丝毫不变的某些东西在不同辈分之间的传达,或者指这样被传承的内容,那么,我们难以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抽取传承作为研究对象。即使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象里找到时间轴上的“同一性/连续性”,其中难免掺入了观察者任意性的理论操作。
根据这一段论述,前川指出了“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传承概念的局限性”,并从中看出了导致“民俗学夕阳”的原因(前川2009:31-32)。关于所说的“传承概念的局限性”,岛村恭则也持有同样的见解。
岛村在其著作《关于“生活方法”的民俗志》(2010)中指出,当他在阐释福冈县福冈市的朝鲜移民后裔群体的实际生活时,传承概念并没有发挥出明显的效果:
在我的田野中,相等于传承的行为或者可以称为传承的事象不是不存在。我通过当地人生活中的各种事象,或者在他们与前辈之间,确实看到了某种传达、继承的关系。(中略)尽管存在这种情况,这些事象并不是“自然地”、“无条件地”传承下来的,而是只因为人们实践“生活方法”时选择,所以才得以存在的。而且,“生活方法”的实践中,还出现了不同于传承的事象,或者某些异质的事象从别处移植到其实践之中
面对这种实践,如果我们只关注传承,进行偏重于传承的记录或考察,那么当地的生活能否充分地被描述出来?显然是不可能的。要是只关注传承,我们无法描述当地的生活(島村2010:301)。
书中,岛村如此指出了“传承概念的局限性”。此外,他在解释传承事像之所以能够从田野中被发现,是因为“当事人在生活上选择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还强调了不是关注“传承”而是关注“生活方法”的民俗志实践所具有的可能性,即:“要把传统民俗学的传承观重新定位到相对位置上来,从而不拘于传承这一框架而把握实际生活”(島村2010:302-303)。对于岛村的研究,门田岳久认为,“他批判了传统民俗学把记述对象局限在所谓‘民俗事象’或‘传承’的‘民俗志’写作,他的目光已经超过了由诸如宗族、节日、信仰、生业此类的固定项目编成的‘民俗志’范围”(門田2011:90)。门田实际上指出了学界开始出现研究视角的转移,有些人从不同于传统民俗学的角度,不再按照“传承”的分类进行研究。
前川也罢,岛村也罢,他们都主张我们不可以继续拘泥于传承概念所蕴含的从过去(上位辈分)到现在(下位辈分)的“同一性/连续性”规范,仅仅探究具有“传承”性质的事象,否则今后的民俗学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其实,早在1980年代后半期,已有人对传承概念“同一性/连续性”的历时性规范提出过质疑*福田亚细男认为“所谓民俗指超越时代而存在的、社会组织成员以一种规制力让其他成员保持的事象”,并说道“如果称这种社会为传承母体,所有民俗都具有其传承母体”(福田1982:6)。大月隆宽则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面对某一社会组织,对于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进行历时性考察,这种研究模式即使考虑它出现在功能结构主义成为主流以前,还是难免过于封闭,缺乏动态视角。而且,使用‘传承母体’一词来理所当然地接受历时性的‘传承’,尽管可以保证‘现在’的‘民俗调查’——按照福田的意见来说是‘田野调查’——在方法论上的正当性,却自然把一个问题悬置在一边:该‘传承’经过怎样的径路达到了现在?”(大月1986:51)。据大月,“使用‘传承母体’一词来企图‘常民’本义的复权”,这种目的“只不过酝酿了对‘传承’或‘传统’等其它词汇指示的文化历时连续性的盲信”(大月1986:52)。。与之稍微不同的是,前川和岛村并没有把批判的矛尖指向传承母体论赖以成立的传承概念,而指向基层文化论、民族性理论(島村2010:303-306),因为在新旧文化的“同一性/连续性”乃至“不变性”被编入到“传承”概念的过程中,正是基层文化论和民族性理论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再说,地域民俗学和传承母体论本该是为了批判民族性理论而诞生的,但二者在传承的认识上却袭用了“同一性/连续性”规范,至今人们使用的传承一词仍然包含着从古至今的“同一性/连续性”规范*比如,工学者畑村洋太郎在其著作《技术的传达方式》(2006)中说道:“‘传承’一词包含的印象是,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东西一如既往地世代沿袭”(畑村2006:4)。。
本文第三节还将谈到,后来民俗学对传承母体论进行了批判,还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对传承概念进行了再检讨。即使如此,今天还有研究者要批判传承概念,这意味着民俗学至今没有能够摆脱过去的概念规范。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民俗学在研究对象和田野的选择方面心甘情愿地要遵守学科传统。借用门田的话来说,那就是“由诸如宗族、节日、信仰、生业此类的固定项目编成的‘民俗志’范围”。我以为,除非每个民俗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有意识地去警惕、解体这些研究对象的自明性,传承概念所蕴含的“同一性/连续性”规范是不断再生产的。岛村之所以选择二战后成立的朝鲜移民后裔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正是为了打破这一旧框架。面对这些批判,我只希望提出一个疑问:前川、岛村等人所批判的传承概念,它与研究者对对象的认识方式共同形成了某种套匣式结构,似乎就是二战后的民俗学叙事空间中得以形的“作为宾语的传承”,而在现实的田野中是否存在另外一种传承呢?
的确,如果我们采用一种由时间轴上的“同一性/连续性”所规定的传承概念作为分析视角,那么,只有很少一部分才能成为田野作业的调研对象。不过,我们也许还可以先把这种分析视角悬置在一边,从“何谓生活世界上的传承”这一问题开始讨论。“生活世界上的传承”作为一种分析视角,不是要从形形色色的人类行为或现象中仅仅抽取具有传承性的一部分,而是要换种姿势,对于日常生活场景中所有事象的过去与现在进行比较和讨论。我们通过“生活世界上的传承”能够看到的,不是事象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同一性/连续性”,而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性”将会浮现在我们眼前。
为了创设新的讨论平台,首先有必要阐释前川、岛村等人所批判的传承概念究竟为什么带有了“同一性/连续性”规范。对此,我们将围绕二战刚结束不久的日本民俗学及民族学领域盛行一时的基层文化论与民族性理论来做一些思考,然后再指出这种传承概念本来就是脱离于“生活世界上的传承”的。
二、被“冻结”的传承与作为行为理论承论(一)传承的“冻结”
传承内容本该具有一种“游隙”*“游隙”指民俗文化本来具有的变化之余地。据鲍辛格说,“上辈人的民间传承”中老一套的固定因素还是很少,由于“游隙”的存在,其它部分都可以自由改变,其游戏性也得到了保证(バウジンガー2001/1961:191-192)。来适应时代变化而变化,但也会出现一些违背这种本性而内容被固定化的情况,鲍辛格称之为“道具性冻结/requisiterstarrung”(バウジンガー2001/1961:185-192)。鲍辛格具体谈到了民间故事的“冻结”案例:
我们在口头传承仍保持生命力的地方,往往会看到它接近于周围环境或时代的情况。鲁兹·罗里克(Lutz Rohrich)就是收集了众多这一类个案。在他收集的故事当中,主人公不但会坐飞机,还会看报纸,也有鬼魂设下炸弹的,至于勇敢的裁缝店的儿子将泼撒“煤油”烧死凶熊,夫人们则涂上了指甲油(鲍辛格2001/1961:186)。
在此,飞机、报纸、炸弹、煤油等可以代表科技技术的母题成为了故事的“道具”,鲍辛格由此阐释了口头传承“接近于周围环境或时代”而存在。除了口头传承,所有传承都是如此*除了故事,鲍辛格还提到了民俗工艺品的“道具”,如用来再现圣经中某一场景的服装装饰等(バウジンガー2001/1961:188)。。但这些逐渐被“努力维持历史形态的意志(Historisierung)”所“冻结”。作为故事“冻结”的例子,鲍辛格说到了巴登-符腾堡州的文化局所属的“故事讲述家”:“她的拿手剧目超过300种,跨越65个国家,而她不是随心所欲地讲述这些故事,其讲述活动近乎于朗诵了。她的故事没有母题的置换,也没有修辞上的改进,进而不可能接近于现代”(バウジンガー2001/1961:187)*鲍辛格的传承观似乎集中体现在以下一段:“如今,我们被要求尽可能地纯粹且一如既往地享受那些传承下来的种种形态,而过去,有一种意志作为抗拒于传统所具有的持续力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它每当进入新的时代都要改变传统”(バウジンガー2001/1961:189)。。
那么,存在于这种“冻结”背后的“努力维持历史形态的意志”究竟为何产生,至今发挥出什么影响?鲍辛格列举了多种可能的原因,如人们深受19世纪浪漫主义影响的眼光,又如纳粹德国有关“民众(Volk)”的观点(鲍辛格2001/1961:1-7)等,但最大的关键还是在于民俗学家对民俗世界的视角。为了说明这一点,鲍辛格从约瑟夫·杜宁戈(Josef Dünninger)的著作《民俗世界与历史世界》中引用了如下一段话:
常民性(Volkstum)具有一种不同于历史的根本法则。常民性是无时间的永恒性,在自然的历年推移中实现自我,其内容一成不变。这是从原始阶段就已经被规定的特征,它只有在空间里才得以展现,与时间是互不相干的。*原文为Josef Dünninger,Volkswelt und geschichtliche Welt. Berlin-Leipzig-Essen 1937; vgl. Insbes. S.21-31.由鲍辛格的引用及其翻译(河野真译)见(バウジンガー2001/1961:21)。
至于这兼容恒常性与不变性的“常民性”如何被链接于日尔曼民族、亚利安人的“民族性”和“国民性”等问题,可以详见河野真的相关研究(河野2005),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日本民俗学中也曾经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传承作为核心概念逐渐确立了其地位。
(二)另一种传承论与国民、民族的表象
从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1934)问世6年后的1940年,有一位哲学家发表了另外一种传承论,那就是务台理作撰写的《表现与论理》(1940)。该书收录了与传承概念密切相关的两篇论文《传承的文化》和《乡土文化与教育》(務台1940:140-174,188-211)*“传承文化”和“乡土文化与教育”均初见于1938年,在此,把《表现与论理》出版的1940年作为务台传承论的发表时间进行定位。除此之外,务台还在《作为种社会的质量契机的传承文化》(1939)等论著中发表过他自己的传承论(務台2000/1939:287-296)。。文中,务台将传承作为素材,对民族、国民精神的“主体/基体”或者“原型=基层文化”展开了论述。据务台,民俗学的传承研究有两种:“一是不论有无形态,将视所有传承文化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对传承的形态及其存在方式进行类型研究”,“二是尽管承认其研究意义,却不会简单地断定那就是人类的文化财,而视之为存在于其背后的民族、国家的所有物”(務台1940:147)。关于后一种立场,务台还做了如下一段描述:
传承具有极为突出的特殊性,始终都在主动地表现出背后的集体生活。由于这种集体生活从来都是特殊的存在,因而该集体就具备了固有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不外乎就是传承文化的主体。(中略)我们应该把传承理解为一种构成国家基层的民族性、国民性的问题。亦即,必须将其解释为其中蕴含着民族精神、国民精神之原型的东西(務台1940:150)。
经过如上整理,务台便把讨论的焦点挪移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上来展开批判,对此我不打算说太多。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重要的就是以下一点,即:有一种要从传承内容看出“民族精神、国民精神之原型”的志向性,在二战以前的民俗学内部已经存在*在此,务台考虑的恐怕是创立于1932年的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的研究者们所追求的研究。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是为了抑止“学生学徒左倾”并“阐明我国国体、国民精神的原理,发扬国民文化”而成立的文部省直辖机关单位,诸如和歌森太郎、堀一郎、萩原龙夫等民俗学家也在此工作过。。这种志向性从二战后的民俗学的基层文化论继承而来,它使得日本人“民族性的阐明”成为民俗学的主要研究目的之一。关于其具体过程,岩本通弥在《战后民俗学的认识论变迁与基层文化》(2006)中做了详细的考证工作(岩本2006:71-76)。文中,岩本围绕传承概念指出“在视传承为共同体之仪礼(sitte)的集体类型理论上面,通过与风俗、流行之间的比较,又出现了视‘民俗’为不变之物的认识。尤其在1970年代以后,这种认识深受传承母体论或地域民俗学的影响而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岩本2006:71,74)。
前面已经介绍过,岛村在其著作中对民俗学的研究目的即“民族性的阐明”进行了批判(島村2009:303-306)。如果我们重新检讨民族性理论的主要内容,那么可以发现它与传承的“冻结”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下面将引用《日本民俗大系2》(1958)所收录的和歌森太郎著《从与历史学的关系谈起》中的一段话:
民间传承,伴随着日本人的历史,贯穿于不同时代,长期维系了下来。它与盛行一时的流行是不同的。(中略)民间传承从上一个世代到下一个世代,时间轴上纵向移动。民间传承亦可谓民俗(和歌森1958:219)。
和歌森给民间传承下定义,说道:以“日本人”为主体,“伴随着日本人的历史,贯穿于不同时代,长期维系了下来”的东西。他认为“考察民俗的由来和意义,可以令人触及到日本人自身的思考方式、其生活态度的框架等”,甚至认为“应该说占据日本人多数的民间百姓之生活,才是真正的日本式生活。追溯到这种生活的渊源,我们可以触及可谓日本人特性的某些东西”(和歌森1958:219)。
关于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樱井德太郎则写道:
日本民俗学的学术目标在于,通过日本民族古来度过的传承生活,或者通过他们正在经营的传承生活,来追求日本民族的Ethnos乃至常民性/Volkstum(桜井1957:113)。
以上讨论,其实袭用了石田英一郎有关民俗学学科性质的发言内容(石田1950)。关敬吾则参照德国民俗学的情况,据此进行了批判:“据说德国民俗学家曾经跪在神圣化的民族灵魂面前,结果妨碍了作为科学的民俗学的正常发展”(関1958:154)*有趣的是,这一批判见于收录和歌森讨论的《日本民俗学大系》第二卷,明确了关敬吾不同于和歌森、樱井等人的学术立场。。关敬吾把批判的矛尖指向了当时的民族学和民俗学从“民俗(民族)文化”中寻找普遍性和不变性的潮流整体,当时这种潮流与传承概念都是需要民俗学家仔细检讨和验证的,但日本民俗学家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结果,这一时期形成的诸如“民间传承·传承生活”=“日本人·日本民族贯穿于不同时代长期维系了下来的东西”此类的认识,使得传承概念包容时间轴上的“同一性/连续性”规范。
后来,民族性理论在民族集体(ethnicity)理论的上下文中受到了本质主义批判,至今已经很少有研究者选择“日本·日本民族”作为传承的主语来使用。然而,人们曾经给出的定义即“传承=日本人·日本民族贯穿于不同时代长期维系了下来的东西”,这仍然“遗留”在传承的概念内涵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批判传承概念的研究者,恰恰持有这种传承观,这也是最近由传承概念引起的争议中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对于民俗学来说,传承概念还是一直被冻结至今的。
我在前面讲过,面对这种情况,除了毫不怀疑地接受“被冻结的传承概念”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去关注和讨论“生活世界中的传承”,亦即对现实中的田野和人们而言的传承。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下有关传承的存在方式的田野研究,借此思考不同于“被冻结的传承”的“合乎实际的传承”究竟是什么。
(三)行为理论的传承理论
据《日本民俗大辞典》(2000),所谓传承是指“文化在时间轴上的移动,它与文化在空间上的移动(传播)形成对立,广义上包括上位世代讲述的语言、动作行为以及下位世代通过视觉和听觉而继承下来的行为”(平山2002)。此文的文责在平山和彦,在此之前,平山早在1992年发表的《传承与惯习的论理》(1992)中提出过“传承=行为”的定义(平山1992:29-32)。据及川高说,“这种行为主义或者现象学方式的(对传承的——笔者)把握方式,使得民俗分析更进一步地接近于传承人的现实性”(及川2010:6)。由于平川参照了本文前面介绍过的务台、和歌森等人的观点,他的传承理论依然把持续性、反复性以及类型性视为重要条件(平川1992:29-57),也没有顾及到传承的动态性。尽管如此,正如及川所指出,平川开拓了从“个人间的行为”这一微观角度讨论传承问题的可能性。
从此以后,关注传承人“行为”的研究,较集中地出现在民俗艺能研究之中。比如小林康正,他以千叶县松户市的“三匹狮子舞”或广岛县安艺郡仓桥町室尾的“三弦”之女性传承为例,讨论了其动态过程,并主张了传承研究中的“行为者的复权”(小林1995:219-220)。又如大石泰夫选择最近在静冈县南伊豆町子浦得以复兴的“木偶三番曳”等作为例子,阐明了通过行为传承下来的艺能内容是动态的,决不是静态的(大石2007)。小林和大石的研究具有一种共同的视角,他们都认为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行为传承下来的技术或表现内容始终处于动态状态之中。这种关注个人行为并据此归纳性地阐释传承内容的研究,我暂且称之为“行为论之传承理论”(加藤2010:85)。行为论之传承理论似乎受到了萊夫和温格“合法的边缘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概念的影响,为了探讨传承论之传承理论的内容,不妨先介绍一下此概念的涵义:
“合法的边缘参与”远远超过信任新手的学习过程,它是一种人与实践之间的互惠关系。这意味着实践共同体中的学习者并非在静态的语境中转移到全面参与状态。实践本身处于动态之中。活动、与活动有关的人们之参与、他们的知识以及他们对将来的展望,这些都是相互依赖、彼此构成的,因此变化才是实践共同体及其活动最根本的特点(レイヴ、ウェンガー1993/1991:104)。
如果我们把萊夫和温格所谓“学习”换为“传承”,便可以理解行为论之传承理论赖以成立的传承概念是把“变化”视为其本质性特点的。正如上述,采用重视变化的视角而进行研究,这对冻结已久的传承概念而言,仿佛就是可“解冻”的处方药,今后民俗学视“生活世界的传承”为对象时能够提供一种基本的立足点*我在本文第一节里谈过,传承概念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同一性/连续性”规定至今没有消除。小林的先驱性研究成果发表于1990年代,而这10多年来其概念规定之所以没有更新,是因为人们尚未把行为论性传承论阐明的“变化”视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性质。也就是说,如今学界存在两种立场,一种是如小林一般认为传承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另一种则认为在其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同一性/连续性”的才是传承。我以为,今后随着立足于行为论性传承论的个案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后一种学术立场必趋衰落。到了一定阶段,我们再不会对“传统不易变化”这样一种看法加以批判,因为这种批判本身没有什么意思了。。
当然,行为论之传承理论不是完美无缺的。行为论之传承理论的缺点,就是它对民俗学的初衷即要叙述“未被写下的历史”及其效果的问题意识稍微薄弱一些。一方面,行为论之传承理论成功地阐释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行为中的微妙差异,从而把过去的静态的传承观刷新了一遍;另一方面,行为论之传承理论所阐明的传承的变异性,它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我们也许需要开拓一种思路,以根据传承的变化来阐释特定的主题、特定的田野的过去与现在。检讨传承的性质,当然是围绕传承概念的问题体系中最关键的题目,然而我们必须要避免把检讨传承的性质视为唯一的目的,否则传承概念所蕴含的可能性就会遭到消减。
追溯其源头,传承发生变化,这在传承概念刚出现时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自明性前提,而且,这种变化导致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差异”正是在叙说“未被写下的历史”时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重新回到柳田的《民间传承论》确认这一点,然后再把目光转移到历史哲学领域的传承理论上来。柳田在《民间传承论》中所做的讨论可以在这些历史哲学领域的最近成果中进一步地发展,我们将据此对传承概念的现时性意义做一些讨论。
三、传承概念蕴含在其中的可能性(一)作为“后历史”的《民间传承论》
前面,我们已经确认了传承概念被“冻结”的背后存在着基层文化论和民族性理论的影响,并指出了这种传承观将有可能由行为论之传承理论逐渐得以“解冻”。视传承为静态的“不易变化的东西”,这种观点主要在二战后民俗学的学术潮流中得以形成,而传承概念原来是丝毫没有这种规定的*平山和彦指出,汉语中本来没有“传承”一词,它是简略“传达继承”而成的新造日语单词(平山1992:23)。柳田之所以采用此词,为的是避免使用“情实缠绵”的“传统”(柳田1990/1934:256-257)。由此可知,柳田面对那令人想起从过去的“连续性”的“传统”概念,仍然思考如何强调其变化的一面。因而,《民间传承论》要把蕴含连续性的传统概念刷新一遍,代之提出了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轴上不断变化的传承概念。。《民间传承论》的以下几段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万叶集》表现的日本人就是原本的日本人,这种想法失之过急,因为达到奈良时代的文化样式之前显然经过了巨大变化。奈良时代之后,也应该一次一次地度过了变化阶段。如今的日本人特性论视之为静止不动的东西,是错误的(柳田1990/1934:291)。
可见,柳田并没有认为传承的内容是凝固而不动的,他甚至明确反对有些人据此谈论民族性或国民性。他认为“相信固有事物的存在,或者相信事物具有普遍性,这种想法本身受到了进化论的污染”,并提醒人们注意关注其变化(柳田1990/1934:315)。而二战后的民俗学却为这一概念赋予了完全相反的意义,对此我们不再赘言,这里只确认一点,即:今天有关传承概念的批判,与柳田的传承观无关。既然如此,我们应该重新梳理《民间传承论》的传承概念,并挖掘其可能性。当然,对于柳田自己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依从传承资料描绘出“未被写下的历史”。他对当时的文献史学提出了以下批判,指出了所谓“历史”应有的可能性及其重大缺陷:
可以说,史官一开始就有意地选择历史的一部分当是无历史。即使到了纸笔容易入手的今天依然如此,有关农民百姓的记录,要不是他们在荒年的饥饿状态,就是农民起义。就如常民大众的平素生活这一般的东西,既很下贱又平凡得不引人注目,就是没有记录价值的。于是,长期以来没有人发现常民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而一直误以为会永远地持续下去。(中略)我们不满足于仅仅由史官选定历史。正是在今天的历史置之不顾的那一部分里,我们渴望知晓的历史亦即我所谓史外史才会存在。(中略)探究民间传承这一学问可谓是为了弥补历史的这种缺陷而必然兴起的学问(柳田1990/1934:304-305)。
柳田的学术目标是要阐明历史家所忽略的“常民大众的平素生活之历史”即“史外史”,他在别处称之为“后历史”(柳田1990/1934:309)。为了阐明这一史外史,传承的变化在方法论上就成为了关键因素。因为,我们无法对静止不变的存在描述其历史,正因为事物发生变化,在与过去之间产生“差异”,历史叙述才成为可能。
柳田从不同时空间得以传承的田野资料中读出“差异”,试图通过“差异”的比较和检讨,描述“未被写下的历史”。至于“被写下的历史”中被隐藏的“未被写下的历史”所具有的可能性,最近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在所有这些观点中,传承成为了关键概念之一。下面,我对历史哲学方面的有关讨论加以整理,以此确认传承概念蕴含的现时性意义。
(二)历史哲学视野中的传承
有关传承概念的讨论,并不是民俗学及其邻近学科的专利,柳田所谓史外史仍是如此。在与民俗学几乎无关的领域里,人们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进行了十分有意义的探讨。从这些非民俗学者有关传承的讨论中,民俗学可以获得有意义的视角,以便对传承概念做出建设性的再建构。这里,我将参照哲学家野家启一的《叙事哲学》(2005)和鹿岛徹《作为可能性的历史》(2006)*这里引用的野家著作是岩波书店于1999年出版的增补改订版。旧版的本书题目为《叙事哲学——柳田国男与历史的发现》。,对于书中被讨论的传承概念在现代社会里所具有的可能性做一些检讨。首先,我引用鹿岛的一段话作为开场白:
个人在生活着,是否已有某种历史插入于其中起作用?个人周围的一切当然拥有多少缘由,而除了这种自明的事实之外,日常场面的个别行为本身即个人作为个人的行为举动本身,是否就是因历史才成为可能?(鹿島2006:177)。
民俗学要从日常的生活世界中看出“历史”,这与鹿岛的问题视角十分相近。作为使“日常场面的个别行为”成为可能的东西,鹿岛关注到了海德格尔的“传承(überlieferung)”*请参见《存在与时间》(1994/1927)第二篇第五章“时间性与历史性”(ハイデガー1994/1927)。。海德格尔的“传承”概念中,个人自觉地牵涉到过去的事象,同时能够使之变化、变奏。按照哲学解释学的说法,这种传承作用可以称之为“反复=夺回(Wiederholung,Répétition)”。“夺回”不是指对前人行为的简单“重复”,而是指现代人要跨时代地实现那些“前人应该能够实行却未完成的东西”的一种作用(鹿島2006:26-27)。如果我们参考这一定义来重新检讨民俗学的传承概念,那么导致变化和差异的原因就会显得更加明确。如果说传承是人们在现在时段里对“过去的可能性”所做的“夺回”,那么可以说“本该实现的可能性”在现在时段的实现则导致了差异的形成。
除了“夺回”之外,鹿岛还列举了传承的重要侧面,包括对历史事象的“调查探求”和“记录痕迹”。据鹿岛,二者均蕴含着一种潜力,以此面对作为支配性语言而得以流通的“正史”之过去,并与其压抑和遗忘进行抗拒(鹿島2006:214)。也就是说,传承不仅仅意味着传达文化事象,它同时还具有另外一种重要功能,即“夺回”被压抑的、被遗忘的过去,进而要求正史对其历史叙说做出修正。
鹿岛的传承论与历史家依据文献资料描述的历史格格不入,而与以传承为基点去摸索“未被写下的历史”叙述的柳田思想之间发生了强烈的亲和性。鹿岛和柳田之间的共同点可以说是他们都要阐明对于生活世界或个人而言的“过去”所具有的现时性意义。与之相关,野家启一曾对民俗学写出了如下评语:
经验拥有一种超出瞬间性体验的时间广度,既然如此,现时的经验必然地背负着对过去的经验所解释的历史(中略)。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就是在常民的生活形式中,对历史经验里如此凝聚的时间厚度进行测量。这才是我们称他的工作为“生活世界的解释学”之缘由(野家2005:90)。
野家是站在现象学的立场说这几段话的,他与鹿岛同样,其前提性认识便是人类的“现时体验”因“对过去的经验所做的解释”而成立。野家把民俗学的研究领域设定为“生活世界”,这仍是他给予民俗学的评价中值得我们聆听的一点。野家、鹿岛等人之所以强调“生活世界中的传承”所具有的意义,是因为他们假定近现代社会里“对人的存在本身而言的传承”这一问题驱逐到边缘。野家和鹿岛讨论这个假设时,都参照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逝世前最后一篇作品《论历史概念》(1940)。《论历史概念》的“命题Ⅳ”中,见如下几段话:
危机不仅使传统(Tradition)的内容面临危机,同时还威胁到了传统的传承人。对于两者而言,危机是相同的,即:将支持统治阶级,成为其阵营的工具。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做出一种尝试,努力去把它从压制传统=传承作用(überlieferung)的体制顺应主义之手中重新夺回来。*《历史哲学命题》的日语翻译收入于《本雅明历史哲学命题精读》(2000)、《本雅明·选集1》(1995)等,鹿岛参照的便是后者(ベンヤミン1995:649)。本雅明所谓“危机”无疑就是要压制、忘却传承功能的近现代性社会状态。鹿岛参照《巴黎拱廊街》(1982)指出,本雅明所谓“历史概念”指的就是一种“根源历史(Urgeschichte)”,它先行于作为近代“大叙事”的人类发展史,或者先行于国民国家以传统为中心讲述的“由来故事”而形成(鹿島2006:223)。这种根源的历史并非是由历史家所能写下来的,而是从任何生活世界中可以看到的“历史”的行为,即“传承”。关于柳田和本雅明在问题意识上的相似,可以参考野家的如下分析:
对于柳田而言,搜集故事传说并不是单纯的怀古爱好。通过叙事传承的挖掘,柳田要与“近代”所强迫人们的“历史意识的断绝”相抗拒,同时他试图显现出叙事行为的潜力,进而使得本雅明所谓“经验的传播能力”或“交换经验的能力”得以复兴。(野家2005:95)
本雅明所谓“经验的传播能力”或“交换经验的能力”不外乎就是传承。当柳田和本雅明面临一个叫做近代的时代状态时,这两位思想家都注意到了“生活世界中的传承”,各自探讨了对“史外史”或者对“根源历史”的记述方式。他们的尝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不局限在思想史方面。无论是基于传承被叙述的史外史,还是“夺回”过去这一功能对正史所产生的效果,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在这个叫做历史的大叙事早已瓦解的现代社会里应该探究的重要课题。
上面,我借用近年来历史哲学家所做的讨论,并对野家称为“生活世界的解释学”的柳田民俗学及其传承论所具有的现实性意义进行了检讨。柳田视之为对象的“生活世界中的传承”,始终/已经“理所当然”地存在于我们周围。站在柳田传承论的立场看,“生活世界中的传承”可以说等同于人们平时不会留意到的自然地“进入视野里的东西”、“听见的东西”或者“心灵的活动”。当然,这种“理所当然”又是多种多样的,因时因地而异。而传承正是作为了解其多样性(=差异)的材料而存在,人们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作为“生活世界的解释学”的民俗学就会开始其生命历程。
结 语
本文对今人有关传承概念的讨论加以整理和参照,首先确认了其中存在两种相反的立场。通过一番整理发现,传承概念至今还包含了时间轴上的“同一性/连续性”规定,这种规定以“被冻结”的状态残留到今天。面对这种情况,我先把凝固而不变的传承概念悬置在一边,指出了民俗学有必要把握“生活世界中的传承”的实际情况。本文第二节,作为后面讨论的前提,借用鲍辛格“工具性冻结”之说,在与基层文化论、民族性论之间的关系中,对时间轴上的“同一性/连续性”规定被编入到传承概念中的原因进行了一些分析。结果我们看到了民族性论尤其对传承概念的冻结产生了极大影响。今后,行为性传承论的出现和发展,这种固定化了的传承概念将会逐渐解构。
本文第三节,根据柳田《民间传承论》的内容确认了传承概念本来不含有这种“同一性/连续性”规定,并讨论了重新挖掘其可能性的重要性。一直以来,柳田从千变万化的传承内容中看出细微的差异,并以此为起点,努力去理解“未被写下的历史”。他的研究态度让我们强烈地意识到现在社会的“生活世界中的传承”所具有的意义。接着,我们确认,关于这种传承概念蕴含在其中的现时性意义给予做出更多讨论的是历史哲学,而不是民俗学。历史哲学家们所讨论的传承论或者他们对“历史”的目光,与柳田民俗学之间保持着很高的亲和性。
作为结论,我最后要强调一点,即:我们不应该自明性地接受学术讨论中得以形成的传承观,而有必要重新返回到田野,返回到生活世界,来重构传承概念。就如我们在本文第三节中确认的那样,柳田的《民间传承论》本来就是为了开拓历史的可能性而提示出来的“后历史”。自从宣布“历史的终结”之后,至今经过了20年之久*参见法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福山在考虑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与随后的冷战体制的终结的基础上,认为“欧美的自由民主主义”即历史的终点。只不过,这里被宣布结束的,就是社会主体思想的进步史观,而不是人类平时经营的生活世界的“历史”(フクヤマ1992)。。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面对围绕“历史”而形成的这种情况,民俗学作为后历史,可以留下贡献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石田英一郎 1950『民族学の基本問題』北隆館。
岩竹美加子(編訳) 1996『民俗学の政治性—アメリカ民俗学100年目の省察から』未来社。
岩本通弥 1998「民俗学と「民俗文化財」とのあいだ—文化財保護法における『民俗』をめぐる問題点」『國學院雑誌』99(11)。
岩本通弥 2003「フォークロリズムと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現代日本の文化政策と連続性の希求」『日本民俗学』236。
岩本通弥 2006「戦後民俗学の認識論的変質と基層文化論—柳田葬制論の解釈を事例にして」『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132。
及川 高 2010「来たるべき日の民俗学—ルーチン·フィードバック·スケール」『現代民俗学研究』2。
大石泰夫 2007『芸能の〈伝承現場〉論—若者たちの民俗的学びの共同体』ひつじ書房。
大月隆寛 1986「常民·民俗·伝承—開かれた民俗学へ向けての理論的考察」『常民文化』9。
折口信夫 1967(1934)「民間伝承」『折口信夫全集25』中央公論社。
鹿島 徹 2006『可能性としての歴史—越境する物語り理論』岩波書店。
加藤秀雄 2010「役割交替と〈伝承〉概念の相関性—主婦権と当屋の「ワタシ」儀礼周辺から」『常民文化』33。
門田岳久 2011「生の全体的記述は可能か—空間·文脈·民族誌」『現代民俗学研究』3。
川村 湊 1996『「大東亜民俗学」の虚実』講談社。
菊地 暁 2001『柳田國男と民俗学の近代—奥能登のアエノコトの二十世紀』吉川弘文館。
河野 眞 2005『ドイツ民俗学とナチズム』創土社。
小池淳一 2000「伝承」『新しい民俗学へ』せりか書房。
小林康正 1995「伝承の解剖学—その二重性をめぐって」『身体の構築学』ひつじ書房。
桜井徳太郎 1957「日本史研究との関連」『日本民俗学』4(2)。
島村恭則 2010『〈生きる方法〉の民俗誌—朝鮮系住民集住地域の民俗学的研究』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
新谷尚紀 2004『柳田民俗学の継承と発展—その視点と方法』吉川弘文館。
新谷尚紀 2011『民俗学とは何か—柳田·折口·渋沢に学び直す』吉川弘文館72。
伝承概念の脱/再構築のために(加藤)。
真野俊和 2009『日本民俗学原論—人文学のためのレッスン』吉川弘文館。
関 敬吾 1958「日本民俗学の歴史」『日本民俗学大系2』 平凡社。
田中宣一 2009「『伝承』の全体像理解に向けて」『日本常民文化紀要』27。
野家啓一 2005『物語の哲学』岩波書店。
ハイデガー,マルティン 1994(1927)『存在と時間』筑摩書房。
バウジンガー,ヘルマン 2001(1961)「科学技術世界のなかの民俗文化」『文明21別冊』。
畑村洋太郎 2006『技術の伝え方』講談社。
平山和彦 1992『伝承と慣習の論理』吉川弘文館。
平山和彦 2000「伝承」『日本民俗大辞典』吉川弘文館。
福田アジオ 1982『日本村落の民俗的構造』弘文堂。
フクヤマ,フランシス 1992『歴史の終わり』三笠書房。
ベンヤミン,ヴァルター 1995(1940)「歴史の概念について」『ベンヤミン·コレクション1』筑摩書房。
前川智子 2009「民俗学の差異化に関する一考察—他領域との対話を通して」『現代民俗学研究』1。
務台理作 1940『表現と論理』弘文堂。
務台理作 2000(1939)「社会存在論」『社会存在の論理』燈影社。
村井 紀 2004(1992)『南島イデオロギーの発生—柳田國男と植民地主義』岩波書店。
柳田國男 1990(1934)「民間伝承論」『柳田國男全集28』筑摩書房。
山口麻太郎 1974(1939)「民俗資料と村の性格」『山口麻太郎著作集3』佼成出版社。
レイヴ,ジーン、ウェンガー,エティエンヌ· 1993(1991)『状況に埋め込まれた学習—正統的周辺参加』産業図書。
和歌森太郎 1958「歴史学との関係から」『日本民俗学研究大系2』平凡社。
和歌森太郎 1972「民間伝承」『日本民俗事典』弘文堂。
和歌森太郎 1981(1947)「日本民俗学概説」『和歌森太郎著作集9』弘文堂。
渡辺欣雄 1990『民俗知識論の課題—沖縄の知識人類学』凱風社。
[责任编辑]刘晓春
加藤秀雄(1983-),男,日本人,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研究员;西村真志叶(1977-),女,日本国鸟取县米子市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居日本。
K890
A
1674-0890(2017)05-063-11
* 本文日文原题为《伝承概念の脱/再構築のために》,发表于《現代民俗学研究》第4号,2012年5月。本刊已获作者授权中文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