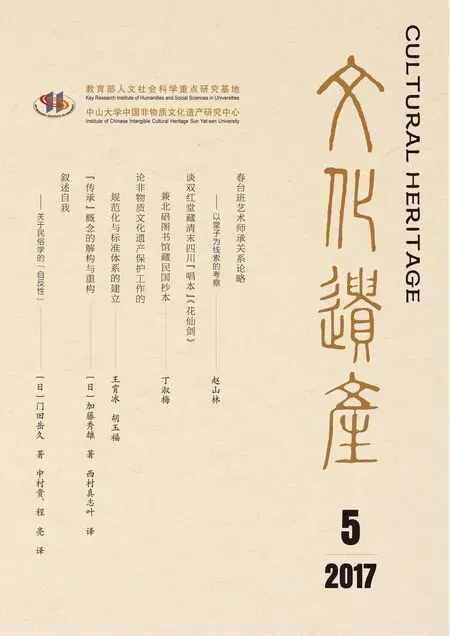以龙求雨:从传说、巫术到习俗*
徐金龙 王梓薇 刘中兴
以龙求雨:从传说、巫术到习俗*
徐金龙 王梓薇 刘中兴
中国自古农业立国,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雨水对于古代先民的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对降雨没有科学的认识,古代先民多将这种自然现象归结于某种神秘力量,各类求雨巫术和传说应运而生,并逐渐流传发展成为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本文从民间关于龙行雨的传说故事出发,探讨古代求雨巫术之一——以龙求雨现象的发轫渊源和发展情况,分析龙和雨之间的联系,针对不同地区流传的传说特点进行比较和归纳,并说明龙作为雨神的文化内涵和现存状况。
龙行雨 求雨巫术 民俗活动
龙作为十二生肖中唯一一个非现实存在的神兽,在民间信仰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龙以操控者或掌权者的象征,逐渐渗透到政治、文化、宗教、民俗等诸多领域,受到人们的供奉和崇拜。并且,龙作为动物神,更多的同雨联系起来,从上古传说到民间故事,从民间巫术到宗教习俗,龙形象从单一的影响降雨的神兽逐渐发展为能够兴云布雨的神明,人们祭拜龙神,并以民俗活动的形式将求雨仪式传承下来。以龙求雨的民俗活动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南北方龙降雨的故事类型及差异
由于地缘因素的先决条件,农业成为我国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并且由于没有人工降雨的科技支撑,自然降雨便成为了广大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我国地域广袤,跨纬度大,数个气候区并存,形成了南北方气候差异大、降水分布不均的局面。北方降雨量少,水系不发达,所以农作物生产基本以一年一熟为主,粮食产量低;江南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地表河流密布,引水便利,农作物一年可两熟甚至三熟。尽管产量可观,但所出产的粮食不仅要供应江南密集的人口,还要向北方等缺粮地区供应,商品粮供不应求,所以,自然降雨对于南北农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而龙作为民间信仰中的雨神,祭祀龙神也就成为了民间巫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为“龙降雨”类型神话传说提供了土壤。
民间传说这种文学类型因为其口述传承方式的不稳定、传承人不具体的特点,导致民间文学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轶失严重,这对于文学界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对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界便掀起了搜集整理民间传说的热潮,以活跃于第一批热潮的、在1955年4月创刊的《民间文学》为领路,20世纪80年代后各地区又掀起了地方民间文学搜集热潮,创办在江南地区的如江苏的《乡土报》(1980)、浙江的《山海经》(1981)、福建的《故事林》(1984)、湖南的《楚风》(1981)、四川的《巴蜀风》(1989)等。这些杂志将本来散落在民间的故事搜集起来,并从古至今、分门别类地安排在每一期杂志中,这给相关内容的查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其中收录的一部分关于龙的传说,大多也都与降雨有关。例如1962年第3期的《民间文学》收录的一则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县的传说,讲述了一个老龙随意行雨给百姓带来灾难,老龙的儿子小金龙继承父亲封地后使当地风调雨顺,百姓给小金龙祭礼却不给老龙。因此小金龙遭到了老龙的嫉妒并被老龙在天上追打,百姓看见小金龙要吃亏,便仿照小金龙和老龙的样子制作了两条一模一样的小金龙和老龙在地上舞动追打,不同的是小金龙占上风。老龙看到地上自己的败相后,便吓得落荒而逃的故事。该故事的语言充满了方言特色,并且情节细腻生动,表达了人们对龙王降雨的爱戴之情。
除上述杂志收录的传说外,全国各地区涉及到龙行雨的民间传说也极为丰富。北方地区的龙传说多与民俗或节日活动有关,内容和类型较为单一;江南地区的龙传说相比北方而言要丰富得多,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人类女性生出龙孩为百姓降雨型、龙神违背天帝意愿私自降雨型、百姓向龙神祈雨型、龙王与术士打赌降雨时间型。
第一个类型,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的“百叶龙”传说为代表,讲述了一个苕溪岸边的夫妻生了一条小龙,夫妻俩怕族人容不下小龙便把小龙放进荷花池里养,后来小龙被老族长发现后被砍掉了尾巴,摇身一变变成荷花龙将老族长吓死了,最后每逢苕溪两岸干旱都会回来降云播雨,百姓也为了纪念小龙,便年年春节用彩布做成荷花瓣的样子制成百叶龙表示庆贺的故事。与此类似的还有丽水市松阳县的“龙母娘娘”传说和嘉兴市海盐县的“分龙会”传说,这两则传说还涉及到女子因吃下某种神物而产下龙孩,龙孩为报答恩情或造福百姓而雨露人间的情节。故事用人母龙子的方式来表明龙与人的亲近和不可分离,用龙子的知恩图报行为表示对龙行雨的深切企盼,也表现了民间对龙神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第二个类型,以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的“玉柱龙”传说为代表,讲述了一个玉帝不准龙神在仙都降雨,然而玉柱龙可怜当地百姓依然屡次私自降雨,后来受到玉帝责罚化成石峰,石峰上的泉水继续滋润着百姓,玉柱龙和玉柱峰都深受百姓爱戴的故事。与此类似的还有嘉兴市海盐县的“龙潭”传说和“分龙会”传说、杭州市建德县的“接龙灯”传说、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的“老龙窝与黎龙河”传说、福建省厦门市的“五龙屿”传说,讲述的都是关于龙神私自降雨被天帝责罚却受百姓爱戴的故事,可见龙神在人们心中,或者说是人们理想化的,大多都是体恤民情、敢于反抗的公正无私、勇于牺牲的形象。
第三个类型,以湖南省吉首市苗族的“看龙场”传说为代表,讲述了某年大旱,百姓举行献祭烧香、打鼓放鞭的仪式到谭边向老龙求雨并且应验成真,后来沿袭下这一习俗的故事。与此类似的还有福建省福安市的“分龙节”传说,都对求雨的仪式和细节有一定的表现,表明民间以龙求雨已形成了仪式化的活动,龙的地位已经不仅仅是为人们降下甘霖的神兽,更是可与其他神仙平起平坐的龙王,要受百姓香火和供奉。
第四个类型,以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的“魏征斩龙”传说为代表,讲述的是泾河龙王与术士袁天罡打赌降雨时辰,袁天罡算中后,泾河龙王为了赌赢私自改了行雨的雨量和时辰,被天帝发现要被砍头,托梦向唐太宗求情,却还是被魏征斩首的故事。这一情节已被明代文学家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收录,如今已为大家耳熟能详,并且与此类似的还有湖南省吉首市凤凰县的“玩龙灯的兴起”传说,与“魏征斩龙”如出一辙,只是人物换成了金钩老龙和鬼谷子。这时的民间传说视角从神转向人,更加关注人类本身,在流传的故事中加入了人类智慧胜过神明、神明反而在某些时刻还有求于人类的情节,可见人们对龙王的感情已不仅仅是崇敬,也多了一些调侃,龙神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更加饱满,更近于人性。
北方地区的龙传说较江南地区而言稍简单,异文较少,同一个类型或几乎相同的传说在北方各地均有流传。此类传说以风俗传说“二月二,龙抬头”为代表,在中原及关中地区各省份均有广泛流传,讲述的都是龙王违背天帝的旨意为干旱的人间私自降雨,天帝大怒将龙王压在山下,并下旨对太白金星说除非等金豆开花,否则永世不得将龙王释放。由于没有龙王降雨,民间再度陷入旱灾的苦境,百姓知道天帝下的旨后,便在二月二的那天家家炒包谷变成爆米花晾在院子里,太白金星往民间一看以为是金豆开花,便放了龙王给民间降下甘霖。百姓为了纪念龙王,便每年二月二都家家炒爆米花以庆祝或企盼龙王降雨换来好收成的故事。这一故事类型应属于江南地区“龙传说”的第二种类型,但因北方的此类传说都有类似“金豆开花”的情节所以单独提出。
同样以二月二作为时间节点,还有一个类型分支,以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的“抽龙筋”传说为代表,并插入了牛郎织女传说的情节。讲述的是民间久日无雨,织女知道是龙王偷懒忘记降雨,便组织民妇在二月二这一天给织机的织线打蜡,这一举动实际上就是“抽龙筋”,龙王浑身被抽的疼痛便起来为民间降雨。降雨之后龙王觉得百姓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一定是有天神下凡泄密,便查出了织女私自下凡并向王母娘娘告状,王母得知后便让织女重返天宫,将牛郎和织女拆散了的故事。“抽龙筋”的故事在中原地区流传较广,并与民俗活动关系密切。
对比北方地区“龙传说”的情节和江南地区“龙传说”的情节,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南北方“龙传说”都涉及到民间大旱、龙王降雨的情节,但北方“雨龙”多偏向于人们为解决旱情请求或迫使龙王降下甘霖,而南方“雨龙”相较于北方“雨龙”则多出了一部分关于龙王降雨过多或惹怒龙王发生洪涝灾害的情节。这一细微差别的出现反映出南北方的气候差异,北方大部分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且离海较远,降雨多集中在夏季,且雨量不均,春秋冬多干燥,所以农田经常出现干旱的现象;而南方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东面朝海,春秋雨量十分可观,并且降雨大量集中于夏季,加上地表水系发达,地形多丘陵,洪涝灾害的爆发率较之北方高出十几倍。因此,南方地区的龙传说相较于北方龙传说所不同的关于龙王发怒而洪水暴涨的情节,正是南北方气候差异造成的。
二、龙作为民间求雨对象的历史流变
我国古代的先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主要靠两种途径进行农业灌溉:一是修建水利工程,接引江河湖水;二是靠雨水的浇灌。古代先民知道江河的来源,却不懂得过云致雨的原理,于是便认为降雨是由某种动物将水从江河中带到天上再降下来的过程,于是便出现了崇拜这种可以致雨的动物的现象。
关于龙的起源,学界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尚未有定论,比较有名的有两种。一种是部族征战图腾交换的说法:在早期原始社会,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图腾,而我们祖先部族的图腾是蛇。部族南征北战,每战胜一个部族便从其图腾上选取一个部位放到自己的图腾上,这样,我们祖先部族战胜了许多部族,于是我们的图腾就成为了一条拥有马的脸、鹿的角、鱼的鳞、鹰的爪等许多其他动物特征的蛇,即后来的中国龙;另一种是神化某种具有特殊本领的动物的说法,这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更为可信一些。
从龙的字形来看,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龙显然是一个象形字。学者何新从龙的字形上对龙形象进行总结:“龙是一种具有四足的爬行动物;这种爬行类可能有角,有鳞,颈部有鬣(像野猪),有长尾;真实的龙,应是一种凶猛的动物,有巨口獠牙;人们畏惧龙,因此在这个字的头上标记‘辛’,以示镇服。”*何新:《龙:神话与真相》,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何新认为,从古生物化石来看,符合上述特点的“类龙”生物以鳄类最为相似,并且此类动物有从气压变化预知晴雨的生物本能,每当下雨之前,鳄类常作怒吼,有“其声如雷,闻之可占雨”之说。所以,早期龙形象的形成,应该与人们对鳄类可以预知天气对特殊本能表示崇拜有关。虽然能够预知晴雨的动物不止鳄类一种,蛙类、蛇类以及其他一些动物也有此种本能(后来的求雨仪式也有用这些动物作为施法或供奉对象的),但鳄类从外形上而言,比其他动物凶猛得多,发出的类似雷霆怒吼的叫声令人震颤,并且由于早期先民居住条件差,武器不发达,被鳄类攻击致死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鳄类比起其他几种身形较小的动物,更容易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为了符合神明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人们开始鳄类的形象加以美化和改造,使之更具备神灵的形象特点,最后逐渐发展成龙的形象。
最早记载龙掌管雨事的文献是已出土的甲骨文卜辞:“其乍(作)龙于凡田,又(有)雨。”*《安明》1218,吉成名:《中国崇龙习俗》,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十人又五□□龙□田,又(有)雨。”*《佚》219,吉成名:《中国崇龙习俗》。等;“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陈成:《山海经译著》(大荒北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山海经》中的这一段关于“应龙畜水”的情节涉及到的“应龙”这种神兽可以致雨的神力,体现了人们对于“雨龙”的认知,可见龙在先秦已和雨水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先秦时期,龙的形象一直保持着原始自然崇拜的色彩,民间对龙的概念也仅仅停留在龙是一种可以致雨的神兽上;而到了汉代,龙的形象则发展得更为完备,云、雨、龙已在民间信仰中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个完整体系,王充在《论衡》中提到:
雷雨时至,龙多登云。云龙相应,龙乘云雨而行……龙闻雷声则起,起而云至,云至而龙乘之。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汉)王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但从汉代开始,佛教如星星之火传入中土,并开始宣传的龙王概念,如《德华经》的八大龙王和《华严经》的十一大龙王,逐渐改变了龙神在人们心中的单一的神兽形象。为了适应佛教文化的龙王,汉代兴起的道教塑造出了五方龙王的雨神形象:除东、西、南、北四方龙王外,还有中央黄帝龙王。此时,这种自然的本土龙开始出现人格化的趋势,体型似蛇的巨大神兽开始向人的形象过渡,除了从外观上给龙穿上了人的衣服,还具备了用语言同人交流的能力,并且地位也从凡间之物逐渐向神明靠拢。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到了宋代(1108年),宋徽宗正式将民间信仰中的龙神册封为“龙王”,使得“龙王”的地位在官方和民间都得以最终确立,并且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政府和民间都逐渐开始兴建各种以龙为尊的“龙王庙”,供官方和民间供奉祈福。这些庙宇后来成为了举行求雨仪式的主要场所,龙王作为行云布雨的神仙形象也逐渐出现在各种民俗活动或民间文学中,“雨龙”的形象最终确定下来。
关于求雨,早在商代就有一种被称为“珑”的用来求雨的玉石,《说文》对此解释:“珑,祷旱玉,龙文。从玉,从龙。”意思就是,“珑”是一种在旱情爆发时用来祈祷降雨的玉石,上面绘有龙形图案。这说明商代早在就已经出现简单的、以龙作为请求对象的求雨仪式。在古人的祈雨仪式中,雩礼是求雨祭祀活动的主要方式。“雩”是一种求雨的舞蹈,在商代已成为惯例,是一种感化雨神的行为,殷墟卜辞里有大量“乎舞,有从雨?”、“今日奏舞,有从雨?”的记载*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并且裘锡圭先生认为,在整个求雨活动中,除舞蹈外,常常会使用龙形道具作为辅助或感化对象,但先秦的求雨活动更重视舞蹈和呼号所起的作用,龙可能只作为辅助工具出现。对早期求雨仪式有文字说明的还有《神农求雨书》,虽是后人所作,有掺杂后代的求雨方式的可能,但这种求雨方式的一部分在上古时代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绎史》(卷四)引,何星亮:《中国自然崇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汉代初期,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对求雨仪式的细节有着十分详尽的阐述,与《神农求雨书》十分类似。
春旱求雨……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乡,其间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求雨……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乡,其间相去七尺。……季夏祷山陵以助之……以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长二丈五尺,于南方。皆南乡,其间相去五尺……秋暴巫尪至九日……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乡,其间相去九尺……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乡,其间相去六尺……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汉)董仲舒著,曾振宇注说:《春秋繁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里的求雨仪式较为复杂,出现了“土龙求雨法”,还形成了针对时节方位的不同旱情进行不同的求雨仪式的局面,求雨仪式的标准化、制度化在这里得以初步体现。
隋代的求雨仪式也以建造土龙的方式来求雨为主,这种祈雨方法也同样为后代所沿袭:
隋制雩坛,国南十三里……孟夏龙则见雩……皇帝御素服、避正殿、减膳、撤乐或露坐听政,百官断伞、扇,令家人造土龙。雨澍,则命有司报州县。*杨静荣、刘志雄:《龙之源》,《文献通考》(卷七十七),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版。
此时,求雨仪式逐渐从民间走向官方,皇帝也作为求雨仪式的执行者被纳入仪式中。这种巫祝仪式逐渐获得朝廷的重视,龙和雨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到了唐代,除了沿袭隋朝的土龙祈雨方式,又出现了画龙祈雨法,冯绍正、曹不兴都是当时画龙的高手:
绍正乃先于西壁画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唐)郑处海:《明室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除以上使用龙形道具进行求雨之外,还有使用蜥蜴或蛇来求雨的,古人认为龙和蜥蜴、蛇等爬行动物同属一种,用蜥蜴作为龙的替身来求雨是民间信仰的一种具象化的寄托。据《宋史·礼志四》所载,宋神宗于熙宁十年(1077年)颁布“蜥蜴求雨法”,让各坊巷捕捉蜥蜴十只置于水瓮中,并在瓮中放入混杂树叶若干,挑选28名10到13岁的男童,分成两班,着青衣涂青色,轮番用柳枝蘸水散洒,昼夜不停,还要围着水瓮高喊:“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除蜥蜴外,也有用蛇作为求雨对象或道具的,形式类似。“蜥蜴求雨法”这种巫术仪式,按弗雷泽的理论属于交感巫术中的顺势巫术,顺势巫术也叫模拟巫术,就是利用“偶像”对达到目的的过程进行模拟,运用“相似率”的原理,模拟之后能达到相同的目的。也就是说,龙可致雨,但龙作为神物不可随意差遣,故捕捉与龙形象类似的动物进行降雨过程的模拟——洒水,以达到龙行雨的目的。
唐宋以后,随着佛教和道教的发展,龙王的形象渐入人心,龙王庙开始广泛的建立起来,各种求雨仪式开始以龙王庙为依托举行。同历代相似,宋代的土龙祈雨法也是靠建造土龙来祈雨,但不同的是,宋代废除了巫觋,使得后来的官方祭祀求雨和民间的巫术求雨逐渐分离,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也是我们上文提到的宗教与巫术的分离。元代的官方求雨时不行大礼,只是请僧人做法,但巫术祈雨仍在民间广为流行,并延续至明清乃至近代。
明清时期民间流传的求雨仪式各地虽有不同,但大致都有一个类似的程序。百姓看黄历或请术士算吉日到当地的龙王庙或城隍庙举行仪式,仪式当天百姓奉上牲礼供龙王享用,并有专门的巫者表演求雨的歌舞,表演人员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也有搭戏台给龙王爷唱戏的。百姓则在一旁跪地嚎啕或祈祷,有的甚至磕头磕出了血。若是龙王“应验”降雨,则百姓还会挑选吉日到龙王庙还愿,感谢龙王普降甘霖,若是龙王“不应验”,百姓还会继续做祭礼或巫事继续祈求龙王慈悲,直到降雨。然而龙王“不应验”的情况较多,如清代湖北长阳人彭秋潭在江西担任知县的20年间,经常遇见巫师祭雨不验的情况,于是针对吉水县五龙寺写了一首《不雨叹》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乞雨乞雨龙不与,五龙五龙奈何许!
得毋只能数米盐,端然不解为霖雨。
从数师巫与鬼谋,醉舞婆娑张两眸。
唱赞阇黎热欲死,冠巾道士拜不休。
皇天仁爱无终极,必然一阵苏民力。
刲刀割豕享鬼龙,庙神醉饱夸功德。*杨发兴等:《彭秋潭诗注》,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版。
有时,同求雨仪式并存的还有“止雨仪式”,一般在降雨过多给生产生活带来不便时举行,两者都是通过龙王塑像或龙神的象征物来进行。
中国人擅长袭击天庭的法术。当需要下雨时,他们用纸或木头制作一条巨龙来象征雨神,并列队带它到处转游。但如果没有雨水降落,这条假龙就被诅咒和被撕碎。在另外的场合,他们恫吓和鞭打这位雨神,如果他还不降下雨来,他们有时就公开废黜他的神位。另一方面,如果所求的雨水降临则发出诏令将它晋升到更高的地位。1888年4月广东的清朝官吏们祈求龙王爷停止没完没了的瓢泼大雨,当它竟然对他们的祷告充耳不闻时,他们便将它的塑像镇压起来整整五天。这取得了有益的效果:雨停了。于是龙王爷也恢复了自由。前一些年,旱灾降临,这位龙王爷又被套上锁链牵到它的神庙的院子当中暴晒了好几天,为的是让它自己也去感受一下缺少雨水的苦楚。*[英]詹姆斯·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意识的引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龙王行雨的巫术仪式是无效的且没有任何依据的,每当发生旱灾或雨水过多时,更多的人选择求助于人工降雨和人工驱雨的科技手段来达到目的。虽然巫术求雨逐渐被时代所淘汰,但关于祥龙的节日活动在今天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三、当代“以龙求雨”活动的发展状况——以浙江省为例
求雨作为一种祭祀活动,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中国已沿袭了几千年,虽形式不同,但人民对风调雨顺的年景、丰衣足食的生活企盼是不变的。雨水对人民来说不仅仅意味着丰收的庄稼,更是拥有美好生活的好兆头。所以,随着巫觋活动的日益消亡,求雨仪式也渐渐从祭祀龙神逐渐发展成通过开展关于龙的活动来庆祝节日,龙也渐渐从雨神逐渐变成吉祥的代表,有关龙的特色活动也逐渐被各地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钟敬文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各地龙传说的比例我们可以了解到,浙江关于龙的传说数量相较其他地区十分突出,比起其他地区的散落在风物或动物传说中的龙传说,浙江的龙传说是单独列出的,这凸显出浙江对龙的重视和崇拜。
关于龙行雨,浙江有“分龙日”一说:
吴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不知其何据。前此夏雨时行,雨之所及必广,自分龙后,则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四),陈文华等《浙江民俗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
所言之意就是“分龙日”前后降雨量不一,之前雨量甚广,之后便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分布不均。“古人以为龙主水,而盛夏常有‘夏雨隔牛背’的现象,是因为龙的上司在分龙日这天开始,命令下属各自分头行雨,以便‘察而治之’的缘故。”*朱元桂:《分龙日和水龙会》,《山海经》,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1995年第3期。
在绍兴,以往存在于传说中的“分龙日”逐渐具有现实意义,并衍生出一种消防组织,即水龙会。龙会的成员叫龙兵(消防队员),由村里的青壮年担任。每当发生火灾时,负责司锣的龙兵便马上拿起铜锣,沿着村庄边跑边敲,其他龙兵们听到锣声便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奔向水龙间,按照各自的分工拿起工具赶去救火。水龙会每年还会在“分龙日”这天举行较龙活动,这是当地一项十分有特色的消防演习活动。这一天,每个村的龙会会进行较龙,即村坊之间龙会的比赛较量,龙兵们会穿上胸背绘有会名的无袖号衣(每个龙会颜色统一)在广宁桥附近举行浇龙(喷水)比赛,龙兵们各自划起龙舟聚集到会场,迅速将消防工具陈列完毕后,龙兵们便手握消防管进行喷水,较龙的水柱以远近取胜。
而以龙为主题的节日活动,大多以“龙灯”、“舞龙”、“龙舟”等形式为主。如杭州市寿昌县(今建德县)的灯节,所制的观赏灯主要为龙形:
元宵、自初八、九日至十六日止。以布罩竹,画鳞甲为龙形,长可数丈,灯燃其中,宛转戏舞,曰‘龙灯’……十五、十六放灯三夜,新年娱乐,颇为美观。*《民国寿昌县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又如武义县的桥灯(板龙灯)活动,最能体现本区灯会特色。“桥灯由龙头和灯桥两部分组成,龙头以竹篾扎成神龙形状,外裱绵纸,措以彩色龙鳞、云彩等,制作极为精工。灯桥由各农户自行制作,灯下托一长约六尺木板,其两头各凿一孔,用以前后连锁接灯。板上没有灯架,每板二支,套于灯架上的是灯壳,灯壳表面糊以绵纸,绵纸上绘有各种花鸟虫草、亭台楼阁等图案,壳里置有蜡烛。灯桥多的有数百桥,视村户多少而定。元宵前后夜晚,桥灯出迎郊野的山冈、田埂、溪流、池塘等地,以红色瘟神,并祁风调雨顺,成熟丰稔。桥灯每到一村,该村须派代表到村口迎接。迎桥灯活动到高潮时,在开阔处狂奔乱舞,拼命拉扯,俗称‘冲灯’或‘拉灯’,以拉龙头落地为大吉。落地即及地,讨及第之谐音,游毕,各户灯桥扛回其家。龙头饰纸及竹篾扯掉并点火焚烧,称‘送龙上天’,龙头上的各色彩灯则分送村中新婚夫妇,俗称送丁,以谓受此者能早生贵子。”*陈文华等:《浙江民俗史》。
永嘉县的春节、元宵舞龙活动与武义县的类似,但龙的种类更为丰富,有首饰龙、狮子龙、滚龙、板凳龙、虾扣弹龙与大龙等。正月初六龙灯上殿,初七、初八便开始“接龙灯”的活动:“常一座屋里的大堂上,集中七八张八仙桌,各户供上福礼祭品。有的摆米塑的戏曲人物、瓜果与小禽等,节俭一些的也有糖糕。随着鞭炮齐鸣,当舞龙的一行人到来,主家、主妇点香跪地迎拜,用稻草燃于地上,人从火焰上跨过,叫‘燃红’。并将迎龙至厅堂,主妇们抢着往龙头口中换红烛,以示吉祥。灯师走到香案前坐定,鼓手打起参龙鼓,灯师唱参龙歌。”*姚周辉、潘一钢:《永嘉传统风俗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浙江地区的舞龙活动多在元宵节前后开展,所舞之龙虽在外观上稍有差距,但总体构造基本相同,龙头用竹篾编制,龙身则是由很多节构成,每一节由村中的各户制作,一户一节,每节上均点有一只灯。现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舞龙活动有:湖州市长兴县的“百叶龙”、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一带的河上龙灯胜会、衢州市衢江区上方镇玳堰村的上方节节龙、苍南县云岩乡鲸头村的太平龙迎新春、三门县花桥镇的板龙(花桥龙灯)、龙游县湖镇镇大路村毛岭头自然村的龙舞(滚花龙)、安吉县梅溪镇上舍村的灯舞(上舍化龙灯)、开化县农村的龙舞(开化香火草龙)等十几项有关舞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除舞龙之外,还有数项关于龙舟竞渡的表演。这些活动的历史渊源大部分与祈雨有关,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于活动娱乐性的要求,求雨舞龙活动除了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之外,更越来越多的作为吉祥的代表出现在各类民俗活动中。
真正以求雨为目的的祭祀龙王活动,留存至今的还有名为“翻龙泉”的道教求雨仪式表演。由于保护力度不够,再加上民众对求雨仪式有效性的质疑,“翻龙泉”活动正趋于消亡。该表演的法师如今或已去世,或年事已高不能表演。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民间信仰的历史证明,“翻龙泉”仪式的文化内涵在民俗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故其消亡已引起当地各部门的重视。经过莲都区非遗保护中心、碧湖文化广电中心站、联城文化广电中心站和樊寿康、陈真理等老艺人的挖掘、整理、包装、申报,“翻龙泉”表演被浙江省设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于2010年列入丽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时在丽水学院建立了传承教学基地,列入该院体育课教程,并于同年7月17日,丽水市(处州)将中断五六十年的“翻龙泉”表演重现人世,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古老图腾和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的象征,已被中华儿女崇拜了几千年。虽然以龙求雨并无科学依据,但始终寄托着人们对富足生活的美好心愿。从传说、巫术到习俗,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华夏民族的象征,已逐渐渗透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中。龙虽然是虚幻的,但人们对风调雨顺、幸福安乐的生活企盼是真实的。求雨舞龙活动虽不能直接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但活动的举行却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也让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抱有新的希望。
[责任编辑]蒋明智
徐金龙(1979-),男,湖北罗田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硕士生导师;王梓薇(1993-),女,吉林吉林市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刘中兴(1981-),男,湖北随州人,华中师范大学社科处问津文化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湖北 武汉,430079)
* 本文系2017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人文社科类)自由探索项目“‘动漫+民间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后民族化策略研究”(项目编号:CCNU17A06037)阶段性研究成果;本项目成果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编号:201706775023)。
K890
A
1674-0890(2017)05-13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