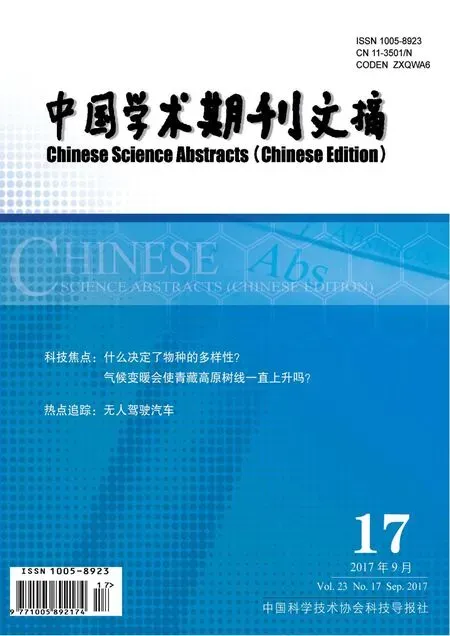什么决定了物种的多样性?
葛 颂
什么决定了物种的多样性?
葛 颂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长期进化的结果,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具有巨大的直接和间接价值,包括直接利用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表现在生命系统的各个组织水平,主要体现在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几个层次上。通常。物种多样性(species diversity)是指一定区域内物种的总和及其变化,包括物种组合的状况(区系)、起源、演化、分布格局和维持机制等。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水平上的表现,是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当谈及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时,就已经涉及物种多样性。因为物种是构成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是遗传多样性的主要载体。
作为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物种是人类文明和社会持续发展所依赖、需要重点保护的资源。理解过去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因素还可以帮助预测生物多样性的未来及其变化趋势。因此,了解并阐明“什么决定了物种多样性”兼具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也是其被列为125个科学前沿问题的原因所在。面对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科学家们甚至公众都会提出成千上万个问题,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什么决定了物种的多样性?
1 物种概念和物种分类
1.1 什么是物种?
当试图回答什么决定了物种多样性这一命题时,往往要涉及“什么是物种”这一基本问题。可以说,生物学家使用最多、但未必意识到的一个概念就是“物种”(species),因为任何一位生物学家都在和一个有名称的生物打交道,不管这个名称是科学名还是俗名。另外,物种概念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是划分物种的依据,而物种划分的结果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多方面。然而,在生物学中,没有哪个概念能像物种概念那样引起如此之多的争议。早在20世纪40年代,Camp和Gilly就提出,要创立一门学科来研究和建立一个自然而又明确的生物学单位和命名系统,使其能客观地反映生物类群的界限、变异性、亲缘关系和动态结构,然而其后的几十年研究并未得出理想的生物学单位,也没能为物种确定一个明确的概念和生物学准则。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物种概念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争论到哲学的高度。已有几十种不同的物种概念被先后提出,但到底如何定义物种迄今仍没有形成共识。其原因大致有3个方面:专业视角的局限,对物种形成或进化过程认识的不足,以及理论定义与分类实践之间的不协调。前两个原因涉及对生物分类和进化的研究,最后一个原因则与物种概念在实践应用上的可操作性有关,因为大多数生物学家把物种看做是一个可操作的单元。
迄今,比较常见的物种概念有“形态学种”“生物学种”“系统发生种”“进化种”和“生态种”等。尽管这些物种定义都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性,但任何一个物种定义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普遍适用于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大自然,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换言之,任何一个“物种”定义都不能满足类似物种概念所涉及的所有内涵。因此,早在20世纪就有学者提出了可操作的物种概念,如形态—地理学物种概念,即以形态学和地理学为标准来定义物种。还有学者认为,可以同时接受多个物种概念,用于描述处于不同分化阶段的物种。最近,洪德元比较全面地回顾了较为流行的几个物种概念,结合自身对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Andr.)类群的长期研究,提出了“形态-生物学物种概念”,作为一种可操作的物种概念,是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尽管如此,依然很难指望在短期内科学家会在物种概念上达成一致,但这并不妨碍“物种”在实际应用中所具备的功能和具有的价值。
1.2 物种的发现、描述和科学分类
面对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人类所要完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现和描述生命世界的所有物种并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即分类学研究。分类学(taxonomy)是最古老的一门学科,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第一步。分类学研究可大致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α和ω阶段。前者主要涉及野外调查和采集以及随后室内标本鉴定、命名和归类,而后者则涉及对类群更为全面的遗传学、细胞学和生态学等实验研究,进而建立科学、具有预期性的分类系统。
然而,分类学这门最古老、最基础而又最包罗万象的学科也是争论最多、最令人误解和遭到诽谤的一门学科。因为分类学理论和实际操作带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如前述不同学者对物种概念有不同理解,研究不同生物类群、甚至研究同一类群的不同分类学家,对物种划分和确定的原则和程序,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在具体类群的分类处理中就出现了所谓的“归并派”(lumpers)和“细分派”(splitters)。正如Davis和Heywood曾声称的,分类学具有科学和艺术的双重属性。
其实,除了科学的分类,人类在发现和描述物种方面做得也远不够。这表现在全球分类学研究在类群上和地域上的极度不均衡。相比而言,全球植物和脊椎动物的物种数目已大致确定,而对于微生物、昆虫等类群以及海洋生物来说,还有大量物种有待发现。从地域上看,发达国家分类学研究的α阶段已基本完成,大量研究已进入ω阶段。但大多数非发达国家,分类学基本的α阶段还远未完成,这些国家往往地处生物多样性极高的区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经费投入不够、标本采集不足、分类学人才缺乏、研究水平较低,造成许多类群的划分和处理存在问题。最近,Goodwin等人评估了来自21个国家、40个标本馆的4500份非洲豆蔻属(Aframomum)标本名称的准确性,结果发现,至少有58%的标本被错误地命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龙脑香科和番薯属(Ipomoea)标本中。进一步对全球标本的统计发现,虽然1970年以后标本采集量增加了1倍多,但超过50%的热带植物标本可能存在命名上的错误。由此可见,对分类学研究较为深入的植物类群尚且如此,对其他研究更为欠缺的类群,科学上的未知就更多了。简言之,物种的发掘、描述和科学分类仍然任重而道远。此外,与物种发现和分类密切相关的一项重要研究就是系统发生重建(phylogenetic reconstruction),即探讨并构建生物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一个客观反映类群进化(亲缘)关系的系统发生树是科学的物种分类以及分类体系建立的基础。
近20年,随着DNA测序技术的发展,分子生物学数据已广泛运用到类群鉴定、物种形成和系统发生重建等不同方面。在分类学中采用DNA分子技术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DNA条形码的出现及其普及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当前针对分类学中如何正确而有效地利用海量分子(基因组)数据仍存在很大争议,但这一发展方向依然不可阻挡。
1.3 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物种?
这一命题似乎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但却与本文密切相关。如果无法知道某个类群、某个地域乃至整个地球上物种的准确数目,要阐明决定物种多样性的原因自然困难重重。但遗憾的是,迄今学术界不仅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物种数目,连物种数目的估测值都达不成共识。以研究较为清楚的植物类群为例,物种数目的估计就差别很大,少到25万种,多到42万种。对研究极为欠缺的微生物类群来说,物种数目的确定和分类就更困难了,因为其具有遗传变异大、无性生殖和横向基因转移等许多干扰物种分类的特性。
物种不确定的原因,除了前述物种定义的不确定和分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外,估计物种数目的方法不同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例如,Mora等人根据物种分布曲线及其建立的模型,估计地球上的生物种类约为870万种;但Grassle和Maciolek根据物种-面积关联的方法估计地球深海海床上就有1千万个物种,而Erwin根据动植物类群间的相关,估计仅在热带地区就有3千万种节肢动物。尽管如此,一个基本共识是,迄今在科学上被描述或定名的物种大概在150~175万种;而地球上与人类共栖共存的物种约有1300~1400万种。
讨论估算物种数目的原理和方法已超出本文的主题范围,有关的研究及其进展可参阅有关文献。尽管迄今对地球上到底存在多少个物种还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这并不影响探讨和阐明决定物种多样性高低的因素,因为物种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
2 物种形成和物种灭绝
与自然界任何事物都有生有灭一样,物种多样性的总量也取决于生与死这一大自然的规律。物种的“生”就是物种形成(speciation),是一个物种群体(population)体系在各种进化力量作用下发生分化,从而形成两个或多个不同物种的过程,也即新种产生的过程。而物种的“死”就是物种灭绝(extinction),即一个物种的所有成员全部死亡。物种灭绝既是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也是决定性的,由生物演化规律所决定的。
2.1 物种多样性的源头——物种形成
物种形成是生物进化的重要步骤,物种形成最重要的结果在于不同物种经历了独立的分化过程,并且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演化趋势和命运。在整个生命之树上,每一个分支点都标志着一次物种形成事件,即物种的一分为二,因此物种形成意味着多样性的起源。由于生殖上的隔离,不同物种得以进行独立的、分歧式的演化,最终获得标志着属、科、目等高阶元分类群的差异性特征。因此,物种形成又是连接宏观(高阶元分类群)进化和微观(种群内部和种群之间)进化的桥梁。
物种形成过程中有些步骤发生得很快,可以被直接研究,但整个过程通常很漫长,以至于科学家通过一代甚至几代都无法观察到。反过来看,物种形成往往又太快以至于不能完整地记录到化石中,即使理想的化石记录也不能说明物种形成的某些遗传过程,人们对这些过程仍然所知甚少,尤其是难以形成化石的生物。因此,物种形成是让生物学家始终困惑不解的一个难题,早在100多年前就被达尔文称之为“谜中之谜”。
物种形成彻底完成所需时间是不一致的。某些物种形成模式(多倍化和重组物种形成)所需时间要短于其他模式(尤其是那些带来不亲和性的中性等位基因突变和遗传漂变促成的物种形成)。对某些生物类群来说,物种形成可能平均需要200~300万年,而在其他情况下,物种形成所需时间会长得多或短得多。最典型的快速物种形成就是适应辐射,即指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尺度内产生大量新物种。例如,在夏威夷群岛定居下来的动植物并不多,但很多定居下来的物种都发生了适应辐射。Carson和Kaneshiro的研究表明,夏威夷群岛存在超过800种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其数目比世界其他所有地方加起来的果蝇物种还要多。同为菊科的夏威夷银剑菊(silversword)(隶属3个近缘属Argyuroxiphium,Dubautia,Wilkesia)所分布的生境从裸露的火山岩一直到潮湿的树林,生活型包括灌木、藤本、乔木和匍匐状,表现出巨大的表型多样性。生活在非洲东部大湖地区(Great Lakes)的丽鱼(cichlid fish,Cichlidae)也是经历了适应辐射的类群,在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区就有超过200种丽鱼,在马拉维湖(Lake Malawi)区丽鱼的种数则超过500种,甚至达到1000种。
当前,对物种形成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群体遗传学家为主的学者,侧重对物种形成机制的研究;二是以古生物学家为主的学者则侧重对物种形成时间尺度的研究。物种形成研究的重点涉及物种形成的方式、速率、遗传基础以及影响因素。近年来,许多学者利用微生物繁殖快、人工控制容易、基因组测序和遗传操作简便等特点,开展物种形成式样和机制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突破。毫无疑问,这些不同方面的研究为理解物种以及物种的保护和科学利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2.2 物种多样性的波动——物种灭绝
化石记录表明,自地球上有生命以来,数以亿计的物种发生了进化。然而地球也并非简单地不断被越来越多的物种塞满;相反,物种形成的过程总是与另一种相反的过程——物种灭绝相平衡。据古生物学家推算,自生命产生后的漫长年代里,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物种中,有99%已经灭绝。
从物种消失的规模上看,有两种程度不同的灭绝:一种是大量类群的灭绝,被称为大灭绝或集群灭绝(mass extinction);另一种为正常的灭绝或称为本底灭绝(background extinction)。如果从灭绝的原因上分,也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与环境灾变有关,包括地球气候的突然变化、小行星以巨大的能量撞击地球以及大陆板块之间的碰撞等。这些灾变导致大批物种(如恐龙)的灭绝。大批物种灭绝之后常会伴随着几百万年的物种形成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成千上万的新物种又会产生,往往通过上述的适应辐射的方式。灭绝的第二种原因通常不易察觉,可能是每个物种都会面临的一种挑战,从气候到各种其他物理因素,以及来自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在此过程中,某个物种的生存环境可能会逐渐受到破坏直至其无法生存下去,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前述的本底灭绝,即在大批灭绝之外的物种丧失。
历史上的大灭绝事件主要有5次,分别发生于奥陶纪、泥盆纪、二叠纪、三叠纪和白垩纪末期。也许最后这一次(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最为出名,一方面是因为包括恐龙在内的许多陆地动植物的消亡发生在这一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一种解释灭绝的原因很吸引眼球:来自外太空的一颗小行星或大慧星撞击地球,从而导致不能飞行的恐龙灭绝。但真正最剧烈的大灭绝发生在二叠纪末期,海洋动物中54%的科、84%的属、80%~90%的种均在此期间消失;陆地上的植物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及曾经占据主导的两栖类和兽孔目爬行动物也让位于新出现的兽孔类(包括哺乳类的祖先)和双颞类(包括恐龙的祖先)。
达尔文曾说,现存的和灭绝了的所有物种构成了一个宏伟的“生命之树”,其上紧密相邻的细枝代表着最近才从共同祖先衍生出来的现生物种,而来自不同枝杈的类群则代表着从更为久远的共同祖先演化而来的后裔。与探讨物种形成一样,对灭绝原因的探讨似乎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有关各个地质历史时期主要生物大类群的灭绝情况,以及对灭绝原因的各种解释和假说已有专门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3 决定物种多样性的因素
谈到物种多样性,自然会发现许多生命世界中有趣的问题,当然也是科学上充满吸引力又富有挑战的命题。从生物类群上看,为什么类群之间物种数目差别如此之大?例如,动物的节肢动物门超过100万个物种,而棘头动物门却只有约1150个物种;被子植物的兰科,物种数目超过23000种,但裸子植物的银杏纲却只有1个种。从地理区域的角度分析,为什么在高纬度地区的物种数目总是要少于低纬度地区?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为什么物种数目在生物演化历程中会忽高忽低不断变化?地球上能承载多少物种,已经达到了极限了吗?…。尽管三言两语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可以影响物种的多样性及其分布,迄今也有不少研究专题探讨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和理论,这里仅针对决定物种多样性的几个关键因素进行介绍。
3.1 生命演化的历史因素
如前所述,从演化历史的宏观尺度上看,物种多样性总量受两个相互对立的力量(即物种形成和灭绝)所影响。当回溯到约35亿年前生命的伊始,地球上仅存类似细菌的细胞,到如今面对具有不同特征、在自然界扮演不同角色、数以千万计的物种。关键因素是物种多样性变化的速率,即单位时间内类群生成(或物种形成)速率和灭绝速率之差。迄今,已有许多研究探讨物种多样性变化速率这一命题,并利用类似于种群增长模型的方法来描述物种多样性的变化,但这类模型往往过于简单化,其推算准确性无法保证,因为外部环境和生物内部的各种因素都会影响物种形成和灭绝的速率,进而影响物种多样化的速率。期间一些假说也被不断提出。例如,“多样性依赖(diversitydependent)假说”认为,如果某个类群在某个时间节点多样性很高,那么其随后灭绝的速率也会很高;反过来,灭绝速率提高后,下一个阶段该类群中新生成类群的速率又会提高。Van Valen则提出了“红皇后假说(Red Queen hypothesis)”,认为生物类群是以近似恒定的速率在灭绝,因为它们无法和相抗衡的其他种类一样快速进化。因此,任何一个类群都类似“红皇后”,必须尽可能快地进化以避免灭绝(被淘汰)。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证据表明,灭绝速率较高的阶段过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新类群的迅速产生。这大概是由于之前占据相似生态位物种的灭绝释放了大量空间和生态位的缘故。新分化类群有时通过直接竞争来替代其他类群;但在更多情况下,只有原先的优势类群灭绝之后,新类群才能取而代之。晚白垩纪恐龙的灭绝和被子植物的大爆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2 地域和气候的因素
回顾全球生物区系分区(provinciality)的历史就会发现,世界动植物的区系分区是逐渐细化的。自中生代起始,生物类群存在着一种由全球性分布不断区域化的趋势,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当今全球生物多样性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和大陆板块的分裂、漂移以及环境多样性的上升密切相关,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地理区域和环境类型能容纳的动植物物种在数目上有如此之大的差别。
物种多样性的地理式样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纬度多样性梯度(latitudinal diversity gradient),即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海洋中,物种以及更高阶元分类群(如属或科等)的数目均随分布纬度的增高而下降。尤其是在热带地区,大多数陆地动物和植物类群的多样性都远高于热带以外的地区。对此解释已有不少,包括归因于生态学因素,还有“多样化速率假说”(diversification rate hypothesis)以及“时间和地域假说”(time and area hypothesis)等。
气候变化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更为直接,包括宏观地质尺度(如前所述)以及微观(短期)尺度,涉及大气环流和洋流以及季节变化等。气候变化不仅加快了物种灭绝的速率,同时还会改变生物栖息地以及植被类型,导致其中生物类群的进一步改变。
其实,地域因素和气候因素是无法分割的。例如,光照、温度和生长期从两极向赤道逐渐递增,使得植物的生长离赤道越近越适宜,植物的丰富度也从高海拔到低海拔有递增的趋势,从而出现物种以致整个生物多样性在低纬度的赤道地区最高(如热带低地的雨林),在两极地区最低(如南北极植被)。然而这种看似简单的规律也会被气流、洋流及山区或岛屿等主要地貌特征所改变,从而造成显著的地理差异。本研究组曾对中国特有植物的分布式样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利用物种及其分布资料确定了中国20个特有植物分布中心,发现包括横断山在内的多个特有植物中心既是古老物种的保存地也是新物种形成的摇篮,反映了这些地区特殊的地质和气候历史。
3.3 生物特性的因素
生物类群各自具有的一些生物学特性对其自身物种形成或灭绝的速率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特性会造成谱系间多样化速率的不同以及面对环境变化在适应能力上出现差异。但是,想要明确找到引起某一谱系类群快速分化的具体特性是很困难的,因为类群中的某一特性和许多其他特性相关联。例如,被子植物的分化程度高于裸子植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有明显不同的特性,如被子植物具有吸引动物传粉者的花。但是,无法排除可能导致类群快速分化的其他特性。例如,被子植物的种子受到子房的保护,因双受精而形成了三倍体胚乳,从而为种子胚提供了养分等。
类群的适应和扩散能力是最重要的生物学特性之一。物种的适应首先和其遗传变异水平、生殖方式以及迁移能力有关。物种的生态位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物种只有在环境条件允许其种群生长速率大于或等于零时才能存留,这些条件可以是温度、水分以及其他可利用的资源,所谓“基础生态位”(fundamental ecological niche)。另外,某个或某些性状可能是物种适应环境必不可少的。例如,在两种雨林中生存的果蝇物种中没有检测到与耐受干燥相关的遗传差异,这可能就是阻碍其向更干燥生境扩散的遗传因素。
物种间的相互作用也是物种生存或灭绝的关键因素。一个谱系中物种数目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其他相关物种数目的变化,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具有寄生和共生关系的类群中。例如,热带雨林比温带森林有更多植食性的昆虫,因为热带雨林有更多种类的植物,从而促进昆虫向不同方向特化以促进对植物的利用。Janz等人挑选成对的蝴蝶姐妹种进行研究,发现其幼虫在食用植物种类上存在差异。在22对组合的18对中,寄主植物多样性高的类群其自身物种数目也较多,符合植物分化有助于昆虫物种形成和分化的预期。种间关系中的合作(cooperation)、互惠(reciprocity)、互利共生(mutualism)和利他行为(altruism)等各种关系都是一些特殊的生物学因素。
来自理论和实验的证据表明,遗传学因素与物种的灭绝有密切关系,物种通常在遗传学因素和环境因素(偶然性事件、环境灾害)的共同作用下趋于衰退并走向灭绝。影响类群的分布历史、物种形成速率以及散布能力等各种生物学因素都将影响物种的生与死,从而影响物种多样性的水平。
3.4 人为因素
当今全球范围内物种大批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类的膨胀带来的后果。生境的破坏、捕猎、疾病的传播和有害动植物的扩散都对生物(物种)多样性产生了严重影响。而且,人类活动导致物种灭绝正在几百年甚至几十年这样的尺度上发生,以至于现有类群无法在短期内靠适应环境并通过物种形成来取代丧失的物种。根据化石记录推算,在农业刚出现的1万年时间里,平均每10年消失一个植物种;到最近的100年里,平均每10年消失近100个植物种。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叶,物种灭绝的速度不断加快,若以平均每10年5%这一保守的灭绝速度推算,今后平均每10年将有近1500种植物消失,而且还没包括大量未被发现和命名的物种(尤其在热带地区)。这种人类活动带来物种灭绝的加剧常被称为“第六次大灭绝”(sixth mass extinction)。
另一种未必都意识到的人为因素就是对物种的认识和研究,包括物种概念和定义、物种的发现和分类等(如前所述),分类学研究的欠缺会从不同角度带来对物种多样性认识的偏差甚至错误。由于物种多样性主要是依据已有的文献记载和馆藏的标本记录汇集而成,试想即使有一天人们能够对地球上所有生物类群进行深入的分类学研究,但当研究不同类群、甚至研究相同类群的分类学家无法统一划分物种标准时,仍无法对物种有正确的认识。准确而权威的植物物种名录对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决策和研究都至关重要,也是保护生物学研究所依赖的最重要的数据来源。因此,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变化管控的基础上,加强生物资源的本底调查和基础性的生物编目工作以及不同层级上的分类学和进化研究是不容忽视的方面,尤其在生物资源丰富而科学研究又比较薄弱的国家和地区。♦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
(摘自《科学通报》2017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