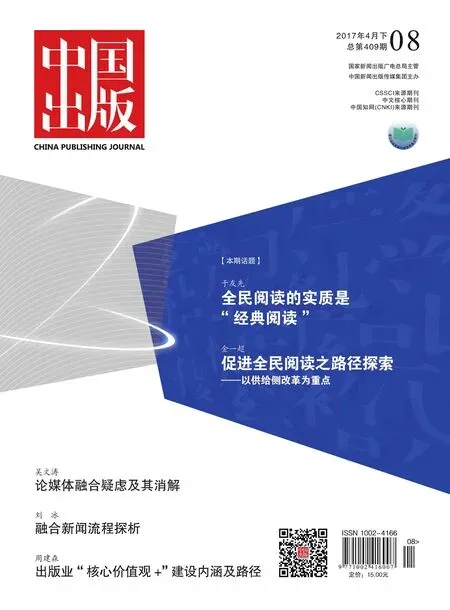典籍文化数字衍生品翻译出版发展策略*
□文│陈 柯
中国典籍文化以其丰富想象力和故事性,给数字开发带来更大的创新空间。在全新的运作模式下,典籍文化衍生产品应运而生,多方合作、共同开发,从世界视野的高度,对民族文化和历史再挖掘、再创作,让译语读者同中国文学典籍产生感性关联,开启个性化的文化消费新模式。面对时代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府顺势而上,提出了“文化数字化”发展理念,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包括在文化资源、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各环节实现全面数字化。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借助高新技术数字化手段,以翻译出版为桥梁和纽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传播,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一、概念厘定和历史进程
典籍文化数字衍生品,是指基于原作的创作精神和特点,经过再加工、再创作、再设计形成的既有艺术价值,又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1]伴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一向被认为“曲高和寡”的典籍文化以全新的方式冲击着我们的民族意识,由此带来的是典籍文化衍生产业的迅猛崛起。
较之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对典籍文化数字衍生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翻译出版起步较晚,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将具有美国价值观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各种动漫、手游、影视作品,在获取巨大商业利润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输出赢得全球话语权。2000年以后,国内市场开始关注典籍文化数字衍生产品的设计发展和海外布局。2003年以前,尚属典籍文化数字衍生产品翻译出版和海外发行的探索阶段。2004年,经历英国“多媒体革命”洗礼的上海,积极计划回应数字化潮流,经翻译加工整理的典籍文化电子版读物和由此产生在线数字终端产品首次亮相市场,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和现代作品源本和多语译本悄然出现在各大网站以供中外读者下载阅读。2006年进入发展阶段,以数字媒体为载体,实现典籍文本、图片、音频、视频交互联动,开发出的各类数字应用软件,通过APP、移动应用、数字交互平台、社交媒体,与读者互动,译语受众可以超越书面语言读中国典籍,品先贤人生哲理。2008年是衍生品发展的井喷阶段,以典籍文化作品人物形象、文本图片、影视资料为模型,设计的艺术作品出现在博物馆、艺术馆、电影院、书店乃至主题公园,出版业、印刷业、娱乐业、游戏业共同关注数字科技对典籍文化作品对外传播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数字化发展趋势的营销策略。[2]当海外需求增加,典籍文化数字衍生产品商业价值将能否被进一步挖掘,产业链各环节的运作与配合至关重要。
二、市场现状和存在问题
大数据和云计算不仅拓展和改造出版业原有的融资和营销模式,而且重构了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组织和生产方式,典籍文化数字衍生品产业迅速进入发展爆发期,在强大消费需求特别是海外需求的推动下,商业运作有望短期内实现良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传播方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内容为王时代的结束,相反,内容资源是影响典籍文化数字衍生品海外布局和对外传播的关键因素,其翻译出版直接关系产品的价值导向和社会效果。
1.市场现状:出版发行渠道极大拓展
典籍文化数字衍生品翻译出版和海外推广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种是国内出版社和国外技术平台开发商携手合作,实现内容资源和技术产业整合,共同创作衍生产品;另一种是由专门从事设计开发的开发商,结合译语受众的需求,以典籍文化出版物中的人物形象、文本图片、历史文化为模型,用销售国所能接受的形象重新构建,创作开发的衍生产品。[3]
这些年,中国典籍文化出版翻译发行渠道较之过去有了较大拓展:一是创新海外运营合作模式,鼓励外来投资,通过合作出版、版权输出等方式缩短出版周期,突显典籍文化创意产业对外输出的跨国经营形态。伴随着中国政要出国访问,典籍文化数字出版物和具有现实题材的中国元素影视作品,已译成该国语言,作为国礼送出,生动形象、设计新颖的典籍文化衍生品,以大众化和形象化的交流媒介出现,亲切又易引起共鸣,更能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输出中国价值观。二是不断创新衍生品出版形式,多角度开发典籍文学作品,开创包括影视、动漫、主题园区、玩具等在内的多种形式,“借船出海”推动典籍文化走出去。如来自法国Pumpkin Studio的动漫作品《庄周梦蝶》,是用中国经典元素水墨画风,全新演绎其文化因素和哲学思考,融合中西动态立体化现代风格合成的动漫短片,获得了不少好评,当年入围昂西动画节官方精选。腾讯动漫趁热打铁,出了《庄子》系列漫画书和动漫线上作品,在法国点击下载率名列前茅,连其动漫人物的游戏玩具也销量颇佳,超越中国传统动漫形象玩具喜羊羊与蓝猫。三是重视译语读者的反馈意见,提供多样化的阅读方式,让译语读者超越书面语言,走进中国文化典籍世界。互联网平台的“战国志”动漫网游提供四种语言,借助三维虚拟技术让译语受众走入先秦,体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代,开展一场虚拟辩论,与圣贤结友,与古人对话。同时,可以通过阅读平台的点击率、下载率、收视率获得最新信息,通过多样化措施开展读者调查,鼓励读者评论,及时有效获得反馈信息,实现“分众化”服务,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爱好分类选择所需阅读的内容。
2.主要问题:创意品牌不足,缺乏监管统筹
典籍文化数字衍生品创造出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无法估量,但在国内尚属于小众产业,缺乏统一监管与领导,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出版发行缺乏创新,导致“中国制造”的典籍数字化衍生品在欧美国家随处可见,遗憾的是,创意和品牌都不属于中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对外推广团队意识不足,典籍文化衍生品出版翻译缺乏完整产业链。《火影忍者》等国外动漫衍生品选择在我国加工,完全展示我们制作方面的实力;我们缺乏关键的原创形象想象力和后期产品销售力。典籍文化衍生品的翻译出版,不能靠个别出版商、经销商单打独斗闯出一片蓝天,亟待重新整合。
对外传播区域定位方向不明,区域辐射传播效应不佳。在西方国家,道家哲学易为接受,无论是《道德经》所提到的辩证哲学、“无为政府”和“自由平等”思想,都与现代西方哲学不谋而合;而在东南亚国家,儒家哲学中庸之道的处事为人法则与其历史文化背景、道德价值理念相得益彰。典籍文化作品如果本身拥有良好读者基础,由其设计创作的衍生品自然也不乏原始粉丝,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典籍文化衍生品产业的回报率。而目前典籍文化数字衍生品翻译出版,不分传播区域,不考虑目的国家语言,定位模糊,无法满足不同区域的差异需求。
实战人才后备力量不足,人才系统选拔与培训机制不完善。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中国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专业人才数量不足130万人,而同期美国是3900万人,欧盟是3000万人。[4]复合型高端人才缺乏和低端人才过剩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才市场的尴尬。事实上,我国各类典籍文化衍生作品交流网站上频频出现创意人气王,但多是业余爱好者,未成团队且缺乏进一步培训,缺乏相关版权保护知识,无法为整个典籍文化衍生品产业提供智力支持。这类人才的培养单靠院校是无法完成的,而专门培养选拔文化创意人才培训机构少之又少。
三、发展策略
典籍文化数字衍生品翻译出版,带来的不仅是文化传播形式的改变,更会影响到译语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乃至审美体验。数字化衍生产品翻译出版,压缩了典籍文化和译语读者的时空距离,但因定位模糊、人才匮乏和监管不力,尚未形成成熟的产业链,当务之急是完善监管措施,多维分层管控风险。[5]
1.依托体系建设,打造翻译出版团队
政府扶植、企业资助和私人捐助相结合,实现典籍文化数字衍生品翻译出版资金来源多元化,依托体系建设,打造一流翻译出版团队,建立成熟的衍生品孵化和发展生态。典籍文化数字衍生品翻译出版周期长,投入大,脑力劳动付出多,协同性要求高,但一旦完成初期的数据库建设,后期盈利空间和无形效应就不是用钱所能估量的。大型出版社和技术平台须强强联合,有序扩大并健全市场化产业链形成机制,增加智力投入,提高管理效率。形成出版商、技术商、发行商、销售商一体化市场理念,弱化中间运营成本,用规范化、市场化体系团队逐步替代分散、无序的零散出版企业,实现出版社与衍生品企业无缝对接,将典籍文化作品原创、制作、衍生产品销售团队融为一体,形成完整的衍生品孵化和发展生态。2010年,电影《孔子》以2500个拷贝的特大发行规模创造中国影史之最,其多语种翻译水平可圈可点,直接拉动了孔夫子网的点击率,连当年以孔子数字图像设计的邮票都卖得异常火爆。第二年,动画片《孔子》就在法国戛纳第48届电视节上被评为最佳动漫作品,当年孔子学院总部、中国孔子基金会、深圳崇德影视传媒携手联合,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一部由动漫《孔子》改编的多语互动式有声学习教材及相关读物在第六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上正式亮相,马上引起现场与会者的极大兴趣,这可谓典籍文化数字化衍生品从翻译出版到海外推广强强联合的经典范例。[6]
2.重核心传播价值,拓展增值服务空间
文化典籍文辞深奥难懂,笔调深僻茫昧,但其数字化衍生品可以做到深入浅出、流畅精炼。将优秀的文学作品重新设计开发,以跨媒体、跨平台的方式挖掘其商业价值,大众关联度和用户匹配度是拓展海外市场必须考虑的因素。在法国,最受欢迎的中国哲学典籍数字化衍生品是《三国演义》的动漫和网游作品,言语简单,却富有东方哲理。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维珍书店,于丹《〈论语〉心得》已登上畅销榜,这是因为法国人对宣传说教式出版物不感兴趣,他们喜欢幽默风趣、以小寓大、互动性强的读物。在意大利,源自《易经》思想的工艺品、篆刻作品随处可见,正是由于这些数字产品的衍生物,意大利人对充满神秘特色的中华文化无限憧憬,“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通过网上书城、在线书店推出3D书籍《中国印章篆刻艺术》获得成功。[7]新版图书《论语系列》携其电影作品联手作战,版权迅速输出到韩国、马来西亚、日本、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版权累计输出13种,是“图书+影视作品”联合版权输出的新突破。[8]这些哲学典籍数字化作品翻译出版的10年间,正是中国对外开放深入推进的10年,尊重自然、相互克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成为全民共识;公正法治社会、自由平等权利,也成为社会认可的核心价值观;自强不息、民族复兴、互利共赢与兼济天下的“中国梦”,更是中国在改革发展新时期对外交流的哲学智慧和历史担当。
3.完善版权保护,提高数字版权技术防护措施
犯法成本太低,而维权成本却过高,这是数字化产品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
对此,我们既不能“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也不能三缄其口、保持沉默,态度暧昧。在版权保护上,一方面需要加强立法,细化数字衍生品的定义,完善侵权与非侵权的界限;同时,建立起从版权信息到违法处理,再至版权维护的长效工作机制,实施技术、行政、司法、社会四位一体的维权机制。另一方面建立起数字衍生品翻译出版、创作改编、设计使用的监控和管理体系,团结行业力量,共同推动版权保护的国际化工作,提高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建立有效的版权争端解决机制。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