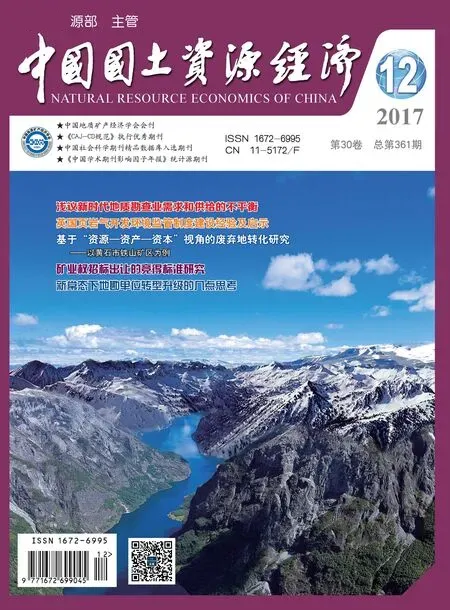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
■ 李梦洋/李欣腾
(东华理工大学测绘工程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
■ 李梦洋/李欣腾
(东华理工大学测绘工程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加新型城镇化不是城市规模的简单扩张,重点在于要把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放在第一位。如何真正实现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成为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影响市民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的退出因素有:(1)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承载力不足;(2)宅基地退出后的保障性风险;(3)黏附社会功能的户籍制度阻碍;(4)补偿方式单一。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建议:(1)推进住房保障政策,增强市民化能力;(2)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农民后顾之忧;(3)明确宅基地权属,确认和保护农民利益;(4)加大户籍改革力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5)制定多样化的补偿方式,合理设计利益分配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
0 引言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宅基地闲置、废弃和低效率利用等现象愈加严重,而经济发展用地的需求量却越来越大,造成了农村土地大量闲置和城市建设用地严重紧缺的冲突,土地集约化利用的程度较低[1]。这一现状使得我国在耕地保护上的压力与日俱增,阻碍了加快实施城镇化发展的步伐。宅基地利用不合理的问题,也引起了政府的足够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央一号文件(2017年)强调要不断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国家“十三五”规划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单列一篇,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基础性指导,体现了对农村转移人口的高度重视;新发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对探索农村宅基地退出也提出了要求;总而言之,无论是从农村土地整治的角度出发,还是有关宅基地制度的改革方面,以及在不断强调的城乡统筹发展要求,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退出的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对宅基地退出做了广泛的研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①宅基地退出的意义。杨保勤等认为,宅基地使用权的退出机制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要之举,合理的退出机制有利于调整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激发农村经济活力[2]。②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徐玉婷等在研究中发现,宅基地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以及退出机制的缺失大大阻碍了宅基地退出的推进[3]。③宅基地退出的实践模式。黄晓兰等和刘双良都认为,宅基地置换模式应趋向多元化,比如置换资金或住房等[4-5]。④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机制。邢姝媛认为,应充分考虑农户的意愿,在与加快城市发展相协调的条件下建立多元化的补偿形式和标准[6]。
然而,对宅基地退出的研究中也存在局限性,现有的研究大多只对其某一方面进行了探讨,能够系统完整地提出宅基地退出机制的研究不多,而且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也并不充分。鉴于此,笔者将侧重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基点,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提出宅基地退出的合理机制。
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解析
要把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概念,全面了解该类人口的内涵是首要工作,但有关农业转移人口内涵方面可供参考的研究并不多。国内学者对其定义各有不同,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部分学者从广义视角出发,将农业转移人口理解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以及由农业脱离出来转移到非农业的人口;同时也有学者直接将其等同于农民工这一概念。然而,在城镇化背景下衍生的这类特殊群体,将其笼统地概括为“农民工”显然过于狭隘。结合当下社会现实情况,农业转移人口可以划分为两大类:①仅实现了地域空间上的转移但户籍并没有发生迁移的农业人口;②已实现了户籍的改变但难以适应自身角色转变,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的小部分城镇居民。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是一个过程,即农业转移人口已有城镇户籍并完全融入城镇社会的过程,更是一个结果,即农业转移人口已经适应了自身的角色转变,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显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的理解和界定需要更加全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身份的转变,即户籍的改变;二是综合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在价值观、文化水平、社交能力等综合素质上有了显著的能力积累和提升,在城市中可以顺利地生活并实现自我价值的突破;三是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保障,享有平等的各项权利、公共服务和保障;四是生活水平和行为方式的转变,诸如教育、就业、薪资等生活水平在各方面都大大提高,已经逐渐适应并养成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五是具有社会认同感,社会地位不再被边缘化,逐步被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组织、公益团体所认同和接受,慢慢适应了自身在新环境中所处的角色,并对进入的城市产生了归属感。
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内在关系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口就业结构的转型。我国的城镇化应兼具“广度”和“深度”,现今城镇化发展的速度虽快却忽略了转化的“深度”,需要有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在当下城镇化的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大多数只是单纯在地域空间上的转移,工作性质发生转变的同时并没有获得同等的市民待遇,没有同步实现户籍身份的转换、综合素质的提升、生活水平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认同感的提升。因而,较于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比率太低。
较为缓慢的市民化步伐带来了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的问题,尤其住房问题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与此同时,截至2016年11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达69095万m2,平均每月销售面积仅12348万m2。可见我国城镇房地产库存量很大,面临着巨大的去库存压力。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盘活地产库存量需要大力鼓励进城农民在城镇买房置业,因而把握好农村宅基地退出这一环节,帮助农民有序退出显得尤为关键。
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近几年来农户的非农收入比重逐步增加,部分农户的收入日益提高,土地不再是唯一的生存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7]。有些收入稳定在城市已经生活了一定年限的农户甚至已经在城镇购买了住房,逐渐产生了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另外,有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稳定,但其对农村宅基地基本政策的认知总体情况并不乐观[8],这部分农户即便让土地闲置也不愿意退出,造成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缓解城乡建设用地的矛盾。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而要化解我国城镇化发展遇到的困境,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高效性,都离不开建立健全的农村转移人口宅基地使用权退出机制。
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量劳动力储备留在农村,使农业转移人口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这是中国城市化滞后且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因此,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农村人口有效转移的重要环节是要构建一种鼓励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农地经营、退出农村的新型机制。
3 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影响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因素
3.1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承载力不足
市民化作为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内容,应兼具外在资格和内在素质的同时变换,但实现内在的变换涉及到农户自身的诸多特征因素,与外在资格的变换相比显得尤为困难。对于普遍的农户而言,年龄、受教育水平、非农收入水平、家庭状况等因素无疑影响着他们能否在城市顺利生活。农业转移人口承载城市素质的市民化能力较弱,他们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在城市中完全融入社会、人力、物质等城镇资本,因而其主动退出的意愿也不强,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宅基地退出的进程。
3.2 宅基地退出后的保障性风险
目前,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还未成熟,农民将宅基地视为自己的固有财产和基本保障,这也成为制约农户主动退出的主导因素。尽管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工对宅基地的依赖程度较于以往有了明显降低,但是替代宅基地保障功能的机制还未完全形成,并不能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户将宅基地视为自己的一条“后路”不愿意退出,造成农村宅基地出现了闲置、荒废等现象。因此,宅基地退出后的保障性风险也是宅基地退出的重要影响因素。
3.3 黏附社会功能的户籍制度阻碍
当前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城镇化的步伐,户籍制度普遍黏附着差别化的权利配置功能,尤其在住房、医疗与养老保障等方面最为凸显。在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这样的二元户籍制度下,产生了两种群体在享有公共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上的本质差别,严重制约着农村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向资产功能的转化。受户籍的限制,农业转移人口仍然无法享受相应的权益保障,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尚能生活却无法真正融入的地方,这也导致了农业转移人口主动退出宅基地的积极性不高。
3.4 补偿方式单一
宅基地退出的补偿与农户的利益息息相关,不基于实际情况的补偿机制往往会使农户的利益受到损害。将宅基地视为自己的主要财产的农户,他们会对宅基地退出带来的成本、收益进行评估,补偿机制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退出意愿。退出后所能带来的收益若与农户自我评估的收益一致,则不仅会大大提高尚在观望的农户退出的积极性,而且会引致其他农户更大的退地需求。现在许多地方单一的经济补偿机制没有充分考虑农户的意愿,补偿标准也达不到农户心里的预期,不利于宅基地退出的推进。
4 构建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建议
4.1 推进住房保障政策,增强市民化能力
农业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而国家推出的公共租赁住房在一定程度也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了在城市生存扎根的愿望。因此,对在城市生活已久达到一定年限的农户,若自愿主动退出宅基地的可以给予包括城市住房保障或者购房补助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由此推进宅基地退出与住房保障政策相衔接。对于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来说,也只有解决了宅基地退出后的居住问题,逐步被纳入到城市的住房保障体系中,实现从有房可居到安居乐业的根本转变,才有可能提高其自愿退出宅基地的积极性。
4.2 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而是要为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体系,发展适合的产业,为农民搭建进城就业创业的平台和充满活力的就业环境,从而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激发其创业热情。对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更是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变。
4.3 明确宅基地权属,确认和保护农民利益
明确宅基地的产权属性是降低宅基地退出交易成本的关键,而且明晰产权是建立产权、行为激励与经济行为之间有效联系的内在保证。要健全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办法和相关规章制度,在落实宅基地登记颁证工作的同时,还应从法律层面阐明农村宅基地的产权,包括明确产权主体、产权收益。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原则,明确宅基地的所有权归属与产能范围,为农民实现退出宅基地提供相关法律保障和行之有效的办法。
4.4 加大户籍改革力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在推行宅基地退出的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徘徊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因此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必要。户籍制度作为与宅基地联动的改革,首先要在两者间构建恰当的衔接和转换机制,并对户籍制度进行制度构造与功能分配,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不同情况协调户籍附加的保障机制,从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4.5 制定多样化的补偿方式,合理设计利益分配机制
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机制应该在遵循合法性、平衡性、多样性以及适度性等原则下,针对宅基地区位、规模等的不同情况进行多元化的设计,可借鉴试行择业补偿安置、税费优惠、作价入股等多种方式来满足农民的不同需求。与此同时,在维护农民权利与意愿的前提下,保证农村宅基地溢价分配利益均衡,确保退出农户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5 结语
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分析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因素,由此探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建立。从宏观层面上看,宅基地使用权的退出必须首先建立进城农民住房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为市民化提供基础建设的保障。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宅基地使用权退出路径的选择要具有现实可行性。具体来讲,宅基地退出机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程序上的规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退出需要不断规划操作的流程,按照城乡统筹的基本要求,建立健全“两种产权,一个市场,统一管理”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体系,这样才能保证退出的标准化建设,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二是需要建立合理的制度路径,尤其是对补偿制度的设计,一定要赋予农民多样化选择的权利,并根据各地区不同情况实行对应有效的补偿模式。比如苏州的“等价置换”政策,浙江的“指标置换”政策,天津市“宅基地换房”政策等。三是辅助路径即配套措施的实施。新型城镇化中有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在农民退出宅基地后,对退出宅基地的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应当尽快构建起来。在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同时,配套的诸如户籍制度也需要联动改革,并注重将农村承包地与城镇权益保障相挂钩,真正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而保证农村宅基地有序退出。
[1] 卢向虎,杨延梅,蒋宗杰.农村宅基地土地整理的再思考[J].农村经济,2011,10(6):6-27.
[2] 杨保勤,陈景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退出的现实风险、法治理念和路径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15(10):78-82.
[3] 徐玉婷,黄贤金.经济新常态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J].中国土地,2015(9):18-21.
[4] 黄晓兰,桂军,韩军.宅基地退出须“退之有道”:成都市两镇农村宅基地退出的探索实践[J].中国土地,2015(1):10-12.
[5] 刘双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与退出机制[J].重庆社会科学,2010(6):25-29.
[6] 邢姝媛.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建立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1):115-119.
[7] 吕文静.论我国新型城镇化、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保障[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4(1):57-61.
[8] 刘静,陈美球.农户对宅基地基本政策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6(11):63-67.
A Research on Rural Homestead Quit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Farmers Citizenization
LI Mengyang , LI Xinteng
(Faculty of Geomatics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angxi Nanchang 330013)
New urbanization is not a simple expansion of city sizes, should focus on the rights of former farmers who are granted urban residency. It is an urgent task to achieve real urbanization and push forward farmers become urban resident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rural homestead quit in the farmers’ citizenization are: (1) insuf fi cient bearing capacity for farmers becoming urban citizens ;( 2) indemni fi catory risks for farmers after rural homestead quit; (3) the obstacl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which has social functions; (4) the ways of compensation are few. Suggestions for rural homestead quit mechanism are as follow: (1) pushing ahead government-subsidized housing to strengthen farmers’ capability to become urban citizens; (2)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social insurance to solve the troubles for farmers in the future;(3) clearly determining the rights of rural homestead to clarify and protect farmers’ interests;(4)stepping up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o break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5) making various compensation plans to reasonably design the mechanism of interests distribution.
rural population transferring; citizenization; rural homestead quit; mechanism
F301.2;F062.1
A
1672-6995(2017)12-0034-04
2017-05-23;
2017-05-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土地整理中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行为分析及管控措施研究”(41261041)
李梦洋(1993—),女,湖北省孝感市人,东华理工大学测绘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土地利用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