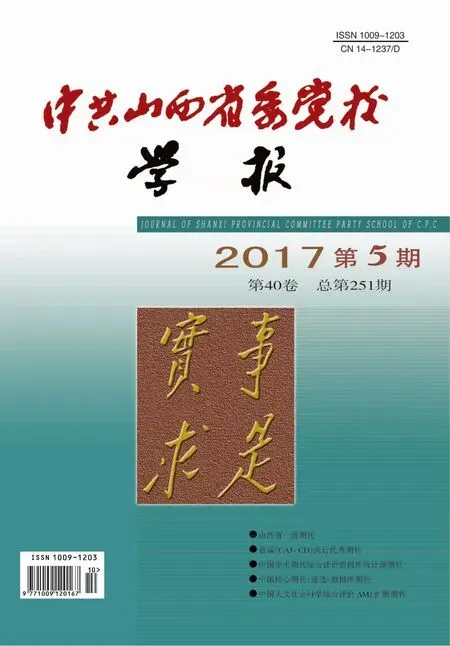伦理学视域下薛瑄廉政伦理思想研究
薛勇民,柴旭达
(1.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太原 030006;2.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太原 030006)
伦理学视域下薛瑄廉政伦理思想研究
薛勇民1,2,柴旭达2
(1.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太原 030006;2.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太原 030006)
薛瑄是明代程朱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河东学派的开创者,在儒家道德理想、理学心性工夫的影响下,平生为官二十余载,历经患难沉浮而不易仁义公正之节。薛瑄在入仕为官的道德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基于理学的廉政伦理思想和为政道德修养,突出体现为:以“视民如伤”的仁爱之心作为施政治理的道德情感,表现出“以公守法、以仁行法”“为政通下情为急”的爱民思想;以“清心省事”的主敬无欲、廉洁明理作为处己待人的道德自律;以“是非毁誉皆所不恤”的坦荡泰然作为达至公平正大的道德境界。
儒家;为政;道德;仁爱;自律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谥文清,明山西河津南薛里(今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既是位朱学巨擎、理学大师,又是位杰出的政治家、清官廉吏,因正直刚毅被誉为“明初真儒铁汉公”。如果把思想史与政治史中的薛瑄相比照,不难看出,儒家的道德追求是薛瑄廉洁从政的思想根源,而克己奉公的为政实践,亦加深了薛瑄对“视民如伤”之情与“清心省事”工夫的理解与体认。薛瑄的理学思想与廉政实践,是知行相即、互相推动的。因此,将薛瑄的从政历程与理学思想相结合,是考察其为政观的可行路径。
薛瑄之学“居敬以立本,穷理以达用”〔1〕1083,“强调躬行践履和人伦日用工夫,注重上学下达”〔2〕。薛瑄秉承儒家的道德实践,认为“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此居官之七要也”〔3〕1541。其中,以正立心属非人伦实践的内容,律己反省、居官以廉兼涉非人伦实践与人伦实践,而事君、事长、接物、待下、处事等,则属于人伦实践。这样的为政修养,讲求由诚意正心到应事接物,由非人伦实践走向人伦实践,内外相即,修齐治平。薛瑄就是在“视民如伤”仁爱本性的体认过程与“清心省事”主敬无欲的修养过程中,表现出“以公守法、以仁行法”“为政通下情为急”的爱民思想及“见理明而不妄取”“不接异色人”的廉政伦理实践。
一、“视民如伤”的道德情感
任何一种道德判断、伦理行为,都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前提。在薛瑄看来,最值得关注的应是人的伦理道德行为背后的心理根源,即“‘视民如伤’,当铭诸心”〔3〕1532的爱民之情。这种情感是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同理心的推广,也是薛瑄秉公执法、为民辨冤、廉洁从政的精神动力。
薛瑄引用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修身之要〔4〕,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仁者之事,即王者之事。”〔3〕1551认为“正义明道”而不计较外在功利得失,才是符合儒家理想追求的“仁者”的做法。“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这种“爱”是基于人主观上对于人的类的认同、认为自己与他人的情感欲求必定相近,进而以恻隐之心行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以求达到己与人、内与外的协调共进。薛瑄“视民如伤”的警诫即是这种“仁爱”的体现,其“爱民”思想,追寻的不是在“爱民”行为中获得利他与个人物质利益的统一,而是欲从其中全善自身的道德价值,达到精神性的自我实现与内在超越。
就字面意思来看,“视民如伤”可作两种解读:一种是指待百姓要像对待自身的伤痛般看重,另一种是指待百姓要像其有伤病般照拂。虽然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薛瑄对后者的体会应尤为深切,这与其所居官职的工作职能有关。自宣德三年(40岁)至天顺元年(69岁),薛瑄先后供职于都察院与大理寺,长期接触官吏的监察、举劾与刑案的监督、审理工作,更是多见刑狱讼案的冤假错判,所以,“视民如伤”的薛瑄看重秉公执法,以“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为“作官持己三要”〔3〕1543。
(一)以公守法,以仁行法
薛瑄将“法”与“天道、天讨”联系起来,言:“法者,天讨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3〕1536“天之道,公而已,圣人法天为治,一出於天道之公。”〔3〕1548
理学家讲求“推天道以明人事”,认为人世运行的关系秩序有自然界的必然法则作根据。所谓“天道之公”,是理学“天理”的内容。“天理”作为程朱之学最为重要的范畴,有物理、性理、义理等不同意涵,“天道之公”所表示的为“义理”,也就是处理社会人伦关系的道德原则乃至法律规范。在薛瑄看来,“公正”是世界合理运行的内在要求,法是惩恶扬善的天道的体现,所以执法者应当“以公守之”。
而在行法上,薛瑄则是从“卖法”的否定角度言:“夫法,所以治奸顽也……若纳贿而纵释奸顽,则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3〕1537执法的目的在于惩奸罚恶,执法者求贿就意味着包庇、纵容奸顽,从而致使良善者所受之冤无从伸张,助长犯法者气焰,败坏风纪。正因“卖法求贿”必将导致“害民”,故以“仁爱”立心、不忍百姓蒙冤受难的薛瑄强调“以仁行之”。
如果逻辑地加以分析,“以公守之”与“以仁行之”二者则关涉薛瑄的公正执法之依据是自然法则还是精神感受、是客观还是主观的问题。就其后者而言,“仁行”本于“视民如伤”的爱民情怀。“惟孝友于兄弟,为为政之本”〔1〕1091,“以仁行之”的情感发端处是亲亲、敬长之情,但所谓“仁行”并不止于此,“推己及人”才是其最为核心的关切,要求把对亲人的爱推及到天地万物中,直至通往“无他”的境地。
至于“以公守之”,薛瑄将“公守”的依据归于“天讨”“天道之公”,而这种流行于天地的规范应当如何把握?其回答是通过人的实证活动“即物穷理”,“如是之久,则塞者开,蔽者明,理虽在物,而吾心之理则与之潜会而无不通”〔1〕1067。在薛瑄看来,虽然研究世间的一切事物是不可能的,但对于自己所能接触到的事物,不论表里精粗,都循序渐进、精心一意地去探究。薛瑄相信,工夫用到,则人的鄙陋之见将得开明,积久日深,则内心性理与物中天理终将会通,人方能够达到由末而知本、见万物为一理的境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潜会而无不通”的理论是存在一定困惑的。因为天理在“末”的表现上,具有如前文所言的“物理”“义理”等不同意涵,所谓“潜会而无不通”,指的是吾心之“义理”与自然“物理”的会通,但作为主体判断的“义理”与源于客体的“物理”的性质不同。“义理”的内容属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关注“应当与否”的问题;而对“物理”的判断则是描述性的,关注“其所是”的问题。薛瑄所接之“物”与其所寻之“义”之间,即事物是然样态的事实判断与义理应然准则的价值判断之间,存在逻辑鸿沟。实际上,这种由“是然”到“应然”的逻辑迁跃,在求“豁然贯通”的朱子那里便存在了,构成了一个理学的理论困难,为阳明心学所非难。
其实,理学关于自然法则与人事准则间有必然联系的理论预设,是含着信仰成分的、对传统“天人关系”认识范式的继承。从《周易》籍由物事而寓吉凶——《易传》对《周易》卦爻辞生效前提的道德诠释——《中庸》的道心人心之论——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先儒所挺立的便是人伦与天地的相通性。所以,“天人相通”在理学家这里更近乎于信仰而非逻辑问题,即相信天人之间具备共通一致性,宇宙中存在以“善”为根本内容的客观普遍的“天理”。虽然“天理”的内容在具体万物上表现不同,但“理一分殊”,薛瑄认为万千众理在根本上是出于普遍的“一”,物理、人性都只是这个“一”的不同发见,故物我可以在“理”的角度上达到统一。可以说,这种“共通一致”其实并不依托经验认知,从理论旨趣上看,薛瑄希望为学者用心去感悟、体证外与内、物与我的共通性,天人沟通,而这种沟通在逻辑上究竟何以可能的问题,则在一种冥证体验的活动中被淹没了。
(二)为政通下情为急
但是,并不能因为薛瑄乃至理学逾越了“是然”与“应然”的距离、重体验而不重逻辑,就否认其道德哲学的价值。虽然断定物事中有义理的理论预设值得商榷,但是认为法乃“天讨”的薛瑄,在执法时以“仁”作为精神驱动力,以恻隐良善之心作为出发点的路径,是值得肯定的。
在为官的具体实践中,薛瑄言:“为政以爱人为本,”〔3〕1534“为政通下情为急,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3〕1540薛瑄为政观中,不论是官对民的“爱”,还是百姓相应回以的“亲”,其旨趣都在于一种官民之间发自内心、和谐自然的情感上。薛瑄所希望的百姓对执政者的敬并非出于惧怕权威,而是心悦诚服。民心向背是天下得治的关键因素,为官者以爱亲之心体察民情,关切百姓,则民心将至,否则便有祸端滋起却全然不知之危。关切“通下情”的薛瑄,在任上平反了诸多冤案,据《行实录》载,薛瑄为积年蒙冤的人昭雪,“人皆称快,其他平反多类此,不能悉记”〔5〕1615。
可见,薛瑄是将爱民情感动机下的“公正”追求应用到了执法之中,使得仁爱之心、天道之公、律法之正三者,在为政实践中彼此连贯,协调一致。薛瑄崇尚居仁由义、以德待人以及“通下情”、“以仁行法”等都显示其儒家济世理想与爱民之心分不开。薛瑄的伦理实践、执法行为,是一种理性上力图符合天理、感性上追求顺乎本心的理性与感性的统一。
二、“清心省事”的道德自律
“清心省事”是“视民如伤”的薛瑄在居官为政中的自律修持。薛瑄处己时的“主敬无欲”以及“廉而不妄取”“不接异色人”的为政观,都与此四字有关。
“清心省事”语出西晋荀勖的“省事不如清心”〔6〕,其“省事”指略宥细苛,精抑文案,简政放权;“清心”是指为官者心思清静,政令统一,还民以宁。“清心”与“省事”在荀勖这里是有高下之别的、相分的施政治理之策。而薛瑄则将二者统一于“守身”工夫,言“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3〕1537,其意趣在于主体,即居官者自身。
薛瑄言:“临政持己,内外一於恭敬,则动静无违,人欲消而天理明矣。”〔3〕1536在他看来,为官持己不论是在面对众人、处理政务时,还是独居于寝、愝息事宁时,都应注意保持内心恭敬的状态,而不可有丝毫的傲慢、疏忽之心。这就表明,薛瑄的居官修养是以其理学的“主敬”工夫为根基的。有学者曾对“主敬”的意涵作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7〕138,认为狭义的“主敬”专就喜怒哀惧等情感未发状态而言,可对应上述薛瑄所言之“内”“静”;而广义的“主敬”则兼存于未发和已发两种状态之中,涵盖“外”“动”。由此来看,作为与理学“主敬”相一贯的工夫,薛瑄居官的“清心省事”亦有“内、静”与“外、动”两个方面的意旨。
(一)主敬无欲
“清心省事”是指情感未发时内里心性的用敬涵养。
唐虞时代留下的儒家“十六字心传”,表达出人心险危难测、道心微妙难明的观点。朱熹解释情感未发时“一”的工夫为“守其本心之正”〔8〕,即保持一种戒慎、恐惧的敬畏心。薛瑄据此理路将持敬作为砭切人心纷扰之患的良方〔1〕1051。
“清心省事”要求人在情感未发时集中注意力于内,时刻保持审慎恭敬的知觉状态,警觉、谨畏地收敛身心,而非肆意放纵致使本性蒙蔽。从情感体验上来看,这是一种对于不受思虑牵扰、适净安定的心理状态的保持,最终将通往“无欲”之境。薛瑄曾言:“心如镜,敬如磨镜。镜才磨,则尘垢去而光彩发;心才敬,则人欲消而天理明。”〔1〕1155通过以主敬涵养的工夫对心性加以打磨,人才能够内心安顿而有所止、心境清明而不昏蔽,私欲止息,人所禀赋的本然善性彰显,“斯得太极之妙”〔1〕1125。
需要指出的是,当这种个人内圣、清心无欲的心性修养理念即重天理义节而轻感性享受的观点,被作为一种普适的道德伦理原则应用到义利取舍时,面对所谓“无欲”的主张,人在直观上往往容易感到道德压抑。面对宋明理学的“存理去欲”在20世纪遭受的猛烈批判,一些学者在义理、历史的层面为理学作了正名,认为这种批判与批判者对理学表述本义的不明晰、对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不了解有关,在高涨的批判热情下存在着对历史哲学的曲解〔7〕1。
对于薛瑄的“清心省事”,应当注意的是,“清心”的持守不是要人扼杀自然天性地去画地为牢、自缚枷锁,“无欲”之时人的内心状态也并非如槁木死灰般枯寂空无。理学讲求生机的修养工夫的枝叶,需要以恻隐羞恶等为内容的人心善端作根,“无欲”状态下所揭示、呈现的“天理”,定要以鲜活的人性为内核,“‘活泼泼地’,仁之发也”〔1〕1077。如此,才能把解放人于习气欲望的理学工夫同背离儒家人本精神的禁欲主义区别开来。正如“清心省事,为官切要,且有无限之乐”〔3〕1547所显示的,在这样的一种修养中,薛瑄并非要让人万念俱灭,而是通过消减人的过分欲望的方式,促使人对内心本性体悟的加强。随着道德境界的提升,薛瑄体会到了一种“孔颜乐处”式的超越了感性享受的精神愉悦。
(二)廉洁自律
“清心省事”实际上指向思虑萌动后应事接物的取舍决断。不论是朱熹还是薛瑄,所倡导的“主敬”并非只是适用于情感产生之前,“持敬”贯通着未发已发之始终。薛瑄的“居敬时敬以存此理,穷理时敬以察此理”〔1〕1083,就是将“敬”作为兼涉存心与穷理、静与动、内与外的修养方法。针对应事的“清心省事”,就要求省去不必要的扰乱心志、牵绕情感的人事接触,纵使需要接人处事,也要主敬庄严,注意在应事的动态中保持内心的澄定与安宁。
当薛瑄将“清心省事”内里的居敬无欲的精神体验与应事时恭敬严肃的知觉状态相结合,并贯彻到为官从政上,便形成了具有理学主敬工夫特点的“廉政”实践。
薛瑄并不反对人最基本的感性诉求,认为衣食等物质条件对于人颐养生息、保障生存不可或缺,但与此同时更应强调:“衣食取足者,天理之公;过为华侈者,人欲之私,君子谨之。”〔1〕1132也就是说,物质供给只要能满足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即可,人若执著于此而追求华贵、希望向人炫耀,则会人欲滋生而天理难存。在薛瑄看来,用衣食物质来满足人生存的基本需求,是符合天理的,而追逐奢靡则就是私欲在作祟了。显然,对于崇尚“君子”人格的薛瑄而言,“利”并非旨趣所在。
除了“衣食享乐”外,薛瑄还谈及掌公权、行赏罚的为官者定然要面对的“取、与”问题,认为“取、与是一大节,其义不可不明”〔3〕1538,获得与给予都应合乎“义”的原则,而执著于华贵的居官者,往往易悖于“义”。所以薛瑄言:“锦衣玉食,古人谓‘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当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时即侈用无节……可以为贪侈之戒。”〔3〕1541
所谓“惟辟可以有此”,语出箕子“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尚书·洪范》),意思是“主威权、行赏罚与享美食”的行为,君王可而人臣不可。如果臣子揽威专断、滥用职权、贪图享乐,则会导致官吏上下倾侧不正、流于邪僻,民众也不会再安守本分,最终社会风气败坏,遗祸于家国。儒家一贯重视“礼”,讲君君、臣臣的仪节法度,认为君当统摄全局、经世治国,臣应匡扶社稷、恪尽职守。君臣各尽其责、各司其事,这既是“礼义”的要求,亦是政治秩序平稳运行的需要。
显然,关于“惟辟”的表述,实质上是以君主专制的等级制为基础的,被孔子称“仁”的箕子如此,薛瑄亦然。值得注意的是,薛瑄虽然未能、亦不可能对其时的君主特权提出质疑,但能将“惟辟可以”的合理性构建在君之“功”而非既有权威上,暗含着对人君行王道的希冀。至于官吏人臣,正如箕子的意见般,薛瑄不主张居官者逐利,对于因一时得志而奢侈无度、锦衣浮华的官吏,颇为不屑,以之为贪侈之戒。
薛瑄依据“廉”的动机,将“世之廉者”的境界分作三类〔3〕1542:一为“见理明而不妄取”,即前文所讲的“清心省事”、主敬到“人欲消而天理明”的境界。薛瑄认为符合此标准的居官者乃廉之上者,“无所为而然”,廉洁的品行是自然而发而非刻意造作,在这样一种境界中,人无需特意确立廉洁的主观动机,其本性即是天理,顺性而为即合乎道德,“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二是“尚名节而不苟取”。此等境界低于前者,其“不苟取”并非人顺乎本性天理的自然举动,而是存在行为约束力,这个约束力就是对“名节”的向往,虽然这样的不屑于取、“不苟取”需要借助人为的主观把握,但能崇尚名节,也属正直自守、洁身自好的“狷介之士”。三乃“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此清廉,则是基于制度的约束下,人保全自身利益的功利考量,在此层次中,私欲是在理性的权衡利弊后被刻意压制,人尚不能做到“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9〕。所以与前两者相较,“斯又为次也”。薛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3〕1542
薛瑄以动机划分了“廉”的境界,相应地,也以此批驳“取不义之财,欲为子孙计”〔3〕1023的行为。这种贪赃昧法与以满足身体感官享受为动机者不同,出于父之爱子的情感,是“亲亲”之情的一种不合宜的心理、精神欲求。前文提到自然的亲亲之情与同理心构成了儒家“仁爱”原则的情感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将一切爱亲的情感都归于仁善。薛瑄认为,包括爱亲之情在内的一切情感都需讲求“致中和”,这里的“‘中’是性情恰好的道理……存於心而不偏不倚,发於情而无过不及”〔1〕1231。所以人的情感若能适度,则符合天地流行的“道”,反之则如为子孙而昧法者的爱子之情一般,失却了“中”的原则,偏离了人的本然善性而沦为人欲之私。所以,在薛瑄看来,相较于为后人留身外之财,传授有可求之道的德业学术才是正途。
(三)不接异色人
除了主敬无欲与廉洁自律外,“不接异色人”〔3〕1533是“清心省事”在应事取舍上的一个具体要求,即疏绝巫祝尼媪、不久留匠艺之人、不与“假文辞字画以媒进”者款洽。薛瑄要求居官者疏远、断绝同事鬼神者、僧尼的联系,既是对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态度的延伸,更是出于两宋理学一贯的排抑佛老的立场。这种对佛老的拒斥主要是在政治伦理的角度上,认为佛老之说“举人伦而外之”〔1〕1029,背离人世的君臣父子伦常,其“偏於空寂”的修行导致人远离社会生活,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担当相左,故薛瑄视佛老之流为道学的主要对立面而加以批判。至于“匠艺之人”与“文辞字画”,虽不似佛老有系统的异于儒家的理论主张,但就效果而言,也容易改变接触者的见地意志,或令人“堕其术中”,对为政而言并无裨益,故也当审查疏节,减少瓜葛。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清心省事”要求人对所思所务有把控,但薛瑄反对为官者据此而不作为。“为官者切不可厌烦恶事,苟视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务省事。’则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3〕1543。也就是说,当“清心省事”的修养遇到了为政职责所须,纵是恶事,也要全力投入而不可推辞。
质言之,薛瑄的“清心省事”是以理学主敬工夫为基础,以追寻天理、仁爱本性为目的,以不妨碍居官者职责履行为前提,以剔除无关于修身养性、为政履职的内心杂念与人事接触为手段,是贯穿居官者情感动机、思维念虑及应事接物全过程的为政修养。
三、“是非毁誉皆所不恤”的道德境界
如果说“视民如伤”是薛瑄为政方略的情感根据,“清心省事”是薛瑄身居官位的律己自持,那么“是非毁誉皆所不恤”就是薛瑄无私奉公的境界觉悟了。
薛瑄言:“为政当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毁誉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誉悦,则失公正之体,非君子之道也。”〔3〕1536意思是为政应当正大光明、没有偏私,以公正作为行事的指导原则而不必在意外界评价。“是非毁誉皆所不恤”是面向外界的肯定、赞誉与非议、毁谤的正反两个方面。对于正的方面,“方为一事,即欲人知,浅之尤者”〔3〕1539,薛瑄批评行事即希望别人知晓、赞扬的贪功者十分浅薄,所以人应当自信自守,不能为别人的称赞奉承而愉悦;在反的方面,人也不应因外界的侮辱轻慢而“为之加沮”〔3〕1532。
薛瑄之所以能“不恤”,是因心中早已“有主”,“有主则中虚,虚谓心中无物也。有主则中实,实谓有理也”〔1〕1075。“中虚”、“无物”即前文所言的人欲消,信念不会被喜怒哀惧爱恶欲所动摇;“中实”、“有理”即天理明,循着性理以求“性天通”。显然,薛瑄的“不恤”与“视民如伤”的仁爱心切及“清心省事”的主敬修养分不开。其“不恤”不仅限于外界的是非评议,亦包含自身的贫贱富贵、甚至祸福死生。对此,可结合薛瑄的为政事迹来看。
宣德三年至七年,薛瑄奉命监察湖广银场,对于为政物质所得,作诗道:“赢得归囊一物空。”〔10〕对于居官而两袖清风,薛瑄非但不为之忧,反倒以之为荣。正统八年,乱政宦官王振之侄欲纳一去世武官的遗妾,遭武官之妻以服丧期未满之由反对,妾遂诬告其毒杀武官,经都察院严刑拷问,武官之妻受冤认罪。薛瑄及同僚为其申辩而触怒王振,振遂命人诬薛瑄刻意量刑过轻、受贿,导致其获罪下狱,以死论处。可以看出,讲求“公平正大”的薛瑄所面对的官场生态并不清明,存在着势力庞大、以权谋私的官僚团体,但他坚持“君子惟义是守,命有所不恤也”〔1〕1153,为民辩冤甘愿舍生取义,不为危难所动。在狱中,薛瑄仍镇定自若,读《易》不辍,不移大丈夫“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刚正气节。除了自身的笃定外,薛瑄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追求亦感召着门人子孙。在其值生死危难之际,薛瑄之子三人上奏,恳请以二人发配充军、一人替父就死为条件,挽回薛瑄性命〔11〕。虽未得明英宗允准,但如此敬孝之情,舍身之义,令人侧目。最终,“将决,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归田里”〔5〕1620。
薛瑄言:“君子行义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3〕1546认为君子应立于中道,存心知性,行其所当行,坦荡立命于天地间,而安危荣辱则被视作“死生命也”〔5〕1614,泰然以待。这里“命”的意涵不全是批判者眼中的儒家宿命论,不论孔孟还是薛瑄,都认为事情的发展除了人的主观因素外,还存在着不为意志转移的客观条件在起作用,欲完全控制事情发展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所以,如《孟子·尽心上》的“求在我者求则得之”与“求在外者得之有命”的论述所示,在行义俟命的儒士眼中,即使仅从事功获得的可靠性层面看,利益得失也不值得成为修身处事关注的范畴,故薛瑄认为当用功处在于“复其性”〔1〕1202,即努力通过心性修养,超越人欲物累而回归人的仁义礼智的本性,做好自己。
距放归六年后,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遭外族俘、王振被杀,薛瑄才受诏诣京。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薛瑄曾因秉公执法而遭难,但此次还朝亦分毫不坠其志。景泰四年,大理寺卿草场失火,本是因饥民抢夺了富人的粮食后焚其屋,但奉命严查的太子太保王文因贪功故,以谋叛罪名羁押了饥民数百人,群臣畏惧其势而不敢申辩,惟有薛瑄首先上书力陈饥民之冤。王文不悦道:“薛某旧性不改,当有以报之。”薛瑄听闻后笑言:“辩冤获咎,死何憾焉,”遂“辩之愈力。”〔5〕1616可以看出,在“是非毁誉皆所不恤”的薛瑄的价值评判体系中,以仁义公正为内容的道德价值甚至比自身的生命价值更为重要。
四、结语
《论语·子罕》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薛瑄作为一位实践之儒,其居官为政的“视民如伤”出于“仁”,“清心省事”的疏绝欲杂堪称“知”,“是非毁誉皆所不恤”可谓“勇”,文能继绝学以传道学之志,行可处危难而守君子之节。其为政奉行的“事合义,虽大不惧;不合义,虽小当谨”〔3〕1544的原则,既讲谨慎敬畏,又勇于担当,纵受祸患之害,只要所为合乎仁义公正,也坚持本心、矢志不渝,这正是道德信念所赋予人的精神力量。
但是,薛瑄理学思想毕竟产生于明代初期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在代表当时儒学较高水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诸如其所看重的君臣关系于当今而言已不再适用;在讲人“修身俟命”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却仍然带有一定的宿命论色彩;以及存在中国哲学普遍具有的“重了悟而不重论证”〔12〕的特点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扬弃”的态度对待薛瑄及其思想。
无论如何,薛瑄重视内心情感体验,基于人性诠释道德,又基于道德诠释存在,以一种将主体透射客体、以主体收摄客体的路径,最终希望达到人天相“通”。尤其是他对于内心情感的尊重以及通过伦理原则改善人之行为的理性主义路径,以实现作为人最高价值的道德价值为目的,于今而言都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遗憾的是,当前,人们常常停留于关切内心情感体验,而不甚明晰其所以然和当中蕴含的道德价值,结果则大量出现了为成全内心欲望而沉醉名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不良现象。不仅如此,“现在的人总以为道德是来束缚人的,所以就讨厌道德、讨厌宋明理学家,因为理学家的道德意识太强。其实,道德并不是来拘束人的,道德是来开放人、来成全人的”〔13〕。回顾前贤,思考和探析薛瑄的廉政伦理思想及其理学根基,无疑对于倡导政治伦理文化研究、实现道德理想人格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
〔1〕薛 瑄.薛瑄全集·读书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常裕.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
〔3〕薛 瑄.薛瑄全集·从政名言〔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1990.
〔4〕朱 熹.朱子全书·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587.
〔5〕薛 瑄.薛瑄全集·行实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2560.
〔7〕陈 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4.
〔9〕程 颢,程 颐.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1:263.
〔10〕薛 瑄.薛瑄全集·文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504.
〔11〕许嘉璐,等.明史〔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5745.
〔1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9.
〔13〕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70.
责任编辑 文 丁
B825
A
1009-1203(2017)05-0095-06
2017-08-06
薛勇民(1964-),男,山西万荣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山西行政学院副院长,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与道德哲学。柴旭达(1992-),男,山西河津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规范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