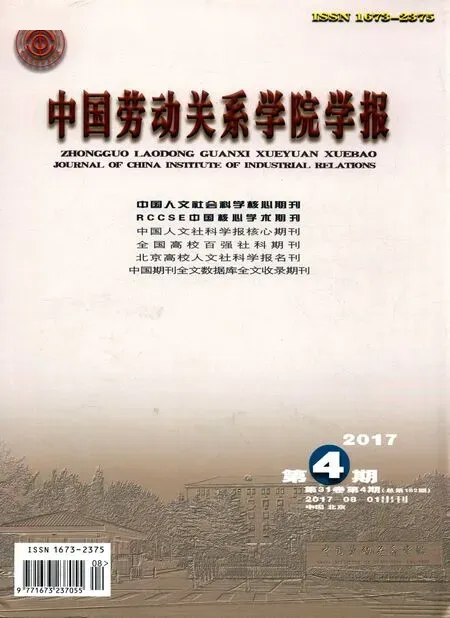劳动关系视角的职场欺负研究*—— 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付美云,孟繁强
(1.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法政学系,天津 300270;2.南开大学 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350)
劳动关系视角的职场欺负研究*
—— 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付美云1,孟繁强2
(1.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法政学系,天津 300270;2.南开大学 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350)
传统基于功能主义范式的职场欺负研究往往以社会心理学为主要研究视角,将职场欺负看作是个体之间的人际问题,关注于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的诱发作用,忽视了组织变革、雇佣制度等组织和劳动关系层面的因素对职场欺负的影响,因而现有的干预政策和措施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而基于批判管理范式和后现代主义范式的劳动关系视角认为,存在“欺负型组织”,制度性权力和组织外显的控制途径对职场欺负行为有诱发作用,并且雇主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干预意愿对现有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有重要影响。这一视角运用跨学科、情景分析的方法揭示了新型劳动关系下职场欺负的产生机制,为进一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减少职场欺负的发生,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架构。
职场欺负;劳动关系;研究范式
职场欺负是职场中权力强势方对弱势方较长期地实施的一种负向行为,常见的欺负形式包括贬低某人的工作价值,戏弄嘲讽或孤立排斥某人等等[1]。早期关于职场欺负的研究较多出现在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领域的文献中,以社会心理学和人权关注作为主要的研究取向,采用的是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关注于测量受欺负者的个性特征及其身心健康受到的影响,进而呼吁雇主和组织通过制定明确的反欺负政策、开展相关教育和培训等手段进行干预和治疗[2]。然而已有研究表明,这些干预政策和措施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3]。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措施往往将职场欺负看作是员工个人层面的问题,忽视了组织变革、社会化过程以及雇佣制度等组织和劳动关系层面的因素对职场欺负的影响,也忽视了雇主和组织的干预意愿。
伴随着过去30年里工作与职场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例如,组织结构扁平化、职能和工作外包等),职场关系以“雇佣条件的个性化、员工的工作安全性逐渐减弱”为主要特征。为了更好地揭示新型劳动关系下职场欺负的产生机制,进而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减少其发生率,需要进一步转变研究范式,通过跨学科的、情境分析的方法对职场欺负问题加以研究[4]。比如,我国学者近来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研究指出,虽然职场欺负在中国普遍存在,但家族主义导致的潜规则盛行,权威主义导致的以强凌弱、明哲保身和麻木不仁,使得职场欺负被组织和个人普遍地漠视,缺乏比较有效的处理职场欺凌的部门和程序[5]。
一、传统研究范式的回顾与新研究范式的提出
(一)基于功能主义范式的职场欺负研究现状
受校园欺负研究的延伸影响以及对员工身心健康和工作生活质量的关注,有关职场欺负现象的研究最早源于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随后扩展至德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乃至世界各国。关于职场欺负的研究大多采用功能主义范式,以社会心理学和人权关注作为主要的研究取向。
在职场欺负的界定上,虽然目前对于职场欺负的概念界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强调了职场欺负的人际特征,认为职场欺负是职场中权力不均衡的个体之间发生的一种持续且重复的人际行为,对受欺负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消极影响。例如,Einarsen(2000)将职场欺负定义为,向一个或多个员工实施的重复且故意的负性行为(例如,贬低某人的工作价值,戏弄嘲讽或孤立排斥某人),并影响了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和工作绩效[1]。Skogstad等人(2011)认为,员工在职场中受到重复的、持续较长时间的欺负行为的困扰,但他(她)却很难对这些消极行为进行反抗[6]。我国学者李永鑫等人(2011)也指出,职场欺负是员工持续且重复遭受的难以反抗的负性行为,这些负性行为来自一人或多人[7]。
在对职场欺负的诱因进行解释时,功能主义范式下传统心理学视角的研究主要以人本主义为研究取向,侧重于将职场欺负作为工作压力和人际冲突升级的结果,关注于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等因素对于职场欺负的诱发作用。在受欺负者个性特征方面,过度焦虑和沮丧等人格特征与受欺负有关[8]。然而,受欺负者可能兼有焦虑和攻击的反应模式。在工作特征方面,角色冲突[9], 工作要求模糊[10],工作缺乏安全感[11]等工作特征与职场欺负有关。然而,Hauge, Skogstad和Einarsen(2009)通过对挪威受欺负对象的追踪研究并未发现角色压力对后续受欺负经历有影响,而之前的受欺负的经历却反过来影响了受欺负者后续感知到的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角色负担[12]。由此可见,个性特征和工作特征因素对于职场欺负的诱发作用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目前关于职场欺负干预措施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从工作特征设计、群体氛围营造等方面入手,通过减少工作压力和人际冲突来降低职场欺负的发生率。常见的组织干预措施主要有技术投入和社会经济投入两个方面。其中,技术投入包括组织结构变革、工作角色的重新界定、工作的重新设计与分析等等;社会经济投入包括制定明确的反欺负政策和有效的欺负投诉处理程序、强调彼此尊重与合作的价值观、开展相关教育和培训、提供咨询和员工援助服务、进行有关职场欺负氛围的调查等[13][14][15]。然后来自各方面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干预措施有时不仅没有改善甚至可能加剧职场欺负[2][3]。因为职场欺负可能是嵌入组织系统的一种系统性存在,现有基于功能主义的干预措施无法彻底改变这一局面。也就是说,职场欺负可能源自于其存在的组织——“欺负型组织”。
(二)欺负型组织的存在与研究范式转换
欺负型组织(bullying organization)是指职场欺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是以人的特征变化而变化,只要存在组织就可能存在职场欺负现象。因为组织存在的首要特征就是存在权力、阶层、角色和规范等,并且权力、阶层、角色和规范本身也是动态变化的。因此,职场欺负本身存在于整个组织中,并不仅局限于“实施欺负者和受欺负者”个体层面。
首先,职场欺负是组织控制的必要手段。Jenkins等人(2012)通过对24位被指控为职场欺负实施者的管理人员进行的访谈调查表明,许多管理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危害性的,并且辩称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合法的绩效管理行为[16]。在有些组织/机构(需要通过军事化管理、团队协作、提供应急服务、高压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不固定、需要特殊技能),可能需要通过职场欺负行为(尤其是口头的辱骂行为),来塑造员工的坚韧性,进而使员工达成组织设定的绩效目标[17]。例如,在护士、警察、军队以及建筑行业中,职场欺负被当作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或习俗,是一些职场新人必经的阶段和仪式,是组织控制其员工的一种手段[18][19]。
其次,从组织政治角度,受欺负者有时是那些业绩突出或在组织政治斗争中战败的一方。他们由于破坏了所在群体内的规范,经常挑战其同事和上级主管的自尊,从而被置于孤立无助的境地[20]。尤其当组织的晋升政策不明确时,职场欺负常被作为一种组织政治行为[21]。从这一角度来看,职场欺负行为被看作是一种管理手段,而非消极行为[22]。
“欺负型组织”的前提下职场欺负的研究范式不能是单纯的心理学研究,而应该转向批判管理范式和后现代主义范式。在这一转变中,职场欺负的对象关系从“欺负者和受欺负者”的关系,转向“欺负行为和组织体系”的关系上,研究方法也逐渐转向社会建构和情境分析。
传统以心理学为主导、强调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对职场欺负现象进行研究时,大多采用操作化的定义对当事人进行测量。由于在数据收集上很难获得来自实施者方面的解释数据,也缺乏来自第三方数据的证实作为客观标准,因而研究更多地依赖于受欺负者的主观感知,忽略了情景角度和第三方角度,导致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不深入细致[23]。近来一些研究则通过社会建构的方法(例如,话语分析、历史文献和典型案例分析等)揭示了情景因素(例如,组织文化、雇佣安排以及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于员工界定职场欺负概念的影响:职场欺负已超越个体行为,被员工用来表达其对工作体验[24]和劳动关系[25]不满意的一种方式。
二、新研究范式对职场欺负诱因的解释——制度性权力和组织控制途径
欺负型组织的存在,强调个体与组织互动、雇员与雇主双方劳动关系的视角对职场欺负行为进行分析,关注于组织特征(例如,组织结构、制度性权力以及组织文化与氛围、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实践等)对职场欺负的影响。为此,批判管理范式和后现代主义范式分别从制度性权力和组织控制途径的角度揭示了职场欺负的诱因。
(一)批判管理范式下制度性权力对职场欺负的诱发作用
与功能主义研究范式不同,批判管理范式主要侧重于从更广泛的制度性权力问题(Issues of Power within Institutions)来分析欺负实施者和受欺负者之间的权力不均衡性,因此受欺负者自然地会接受实施者的权力地位(即服从权威、逆来顺受),而职场欺负则被看作是维护秩序、权威和纪律的需要,在社会大众和受欺负者看来甚至是正常的情景。批判管理范式视角下,职场欺负有两种体现:
首先,作为组织权力体系维系的基础,职场欺负“被合理化”,这意味着个体所采纳的信念体系是由规则制定阶层构建的,秩序、权威和纪律是必要的[26]。在批判管理范式看来,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结构理论就是职场欺负产生的根源,其强调组织中去人性化的、理性冷淡的人际关系(关心生产而不关心人),当组织中这一关系盛行时,员工往往很少顾及同事或下属的感受。
其次,职场欺负逐渐演变为一种“组织惯例”。组织结构、高层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组织文化和氛围等组织因素对职场欺负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职场欺负是建立在当事人双方权力不均衡基础上的,组织的相关管理制度和组织文化如果缺乏对权力强势方有效的监督控制和对权力弱势方有力的社会支持,对职场欺负采取放任自流的容忍甚至是纵容态度,那么可能会导致进一步助长权力强势方的威风,使其认为欺负是组织允许甚至期望的[17],还会进一步使处于权力弱势方的受欺负对象感到习得性无助,认为群体成员已对欺负达成共识(即欺负是符合群体规范和组织文化的)、自己被欺负是注定的,从而使职场欺负得以持续重复发生。
综上所述,批判管理范式将职场欺负视为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Ideological Hegemony),强调职场欺负是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反映,因此改善职场欺负就要颠覆这一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
(二)后现代主义范式下组织外显控制途径对职场欺负的诱发作用
与批判管理范式一样,后现代主义范式也关注对管理的批判,但是它更倾向于对外显的组织控制途径的研究。在功能主义范式所推崇的、让员工和管理者均受益的高绩效工作系统,在后现代主义范式看来却是工作激化(work intensification)的温床。Foucault(1997)强调“人这一主题在被置入生产关系的同时,也会被置入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27],因此高工作绩效系统强化了对员工努力的控制,将高工作绩效放置于员工身心健康和工作-家庭平衡之上,由此增加了员工的工作压力和同事的监督,进而为引发欺负行为提供了环境诱因[20]。后现代主义范式下,职场欺负有两种体现:
首先,职场欺负本身是组织权力的传递链条,因此在某一职位上的人既可能是职场欺负的实施者,也可能是受害者。正如Foucault(1997)提到的,权力是以网络形式运作的,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处于服从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27]。职场欺负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角色是有内在逻辑的,即他受欺负程度越严重,实施欺负的程度就越严重。即受欺负者并不总是以“受气包”的形象出现,还存在一些“挑衅型”受欺负者(provocative victims)。他们是那些对职场欺负行为作出积极反应的受害人,既是实施者同时又是受害人,兼有焦虑和攻击的反应模式[28]。
其次,管理实践通过简单的权力运用就可以加剧职场欺负现象。后现代主义范式将诸如会计、绩效考核和操作手册等管理手段作为加强组织内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而个体时刻受到权力的监管,在职场中员工的行为和工作总是受到管理当局的监视。Liefooghe和Davey(2001)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分别对英国一家电信公司呼叫中心的员工和一家银行的员工进行了焦点群体访谈,并通过话语分析发现,职场欺负以去个性化的方式被员工感知,两家公司的员工都把欺负归因于组织,将组织整体作为欺负实施者而不是某一个体,以此作为他们尝试对其认为不合法或有问题的日常组织管理实践进行挑战和反抗的一种武器[29]。根据组织实施的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未达到绩效标准就会受到处罚,这一事实使员工体验到遭受了组织欺负。为此,他们声称,组织对员工实施的权力和控制的过程,尽管没有采取具体的方式,却是一种对员工的欺负。因此职场欺负并不受实施者和受欺负者的个体特征直接驱动,而是源于管理角色要求,人格正常甚至没有经过新角色要求训练的人,也会非常极端地表现出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相一致的行为方式,甚至会欺负他人,这一点在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范式强调让员工从严苛的组织控制中解放出来,而非强调工作绩效。对管理者的启示是组织控制会导致员工之间的疏离。例如,对于学者们曾一度困惑的职场欺负为何在护士职业中较为盛行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范式对此的解释是公共部门医疗体系的机构改革增加了官僚主义,进而加大了管理控制的力度。而管理控制力度的增加、严密的监管和惩处手段,使得有经验的高级护士通过职场欺负来强化规则和权力[30]。
三、劳动关系视角的职场欺负:一种研究范式转换下的社会建构
伴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过去30年里经历的重大工作与职场变革,组织的结构趋于扁平化、许多职能和工作被外包出去,职场关系以“雇佣条件的个性化、员工的工作安全性逐渐减弱”为主要特征。这些变化被看作是导致员工产生与压力相关的一系列疾病的根源,它们与职场欺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为此,近几年来,一些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者开始从劳动关系管理的视角进一步审视这一现象[31][32]。这一视角将整个组织看作是职场欺负的实施者,从社会学层面来解释职场欺负现象,强调工作环境、组织文化和社会化过程对职场欺负的影响。这恰恰符合上述批判管理范式和后现代主义范式的主张。
(一)劳动关系视角对职场欺负的深层次解读
事实上,已有一些学者采用上述研究范式的观点,运用社会建构的方法,从劳动关系的角度,对职场欺负的组织诱因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Hodson, Roscigno和Lopez(2006)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在对有关组织生命周期的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组织凝聚力低(秩序混乱)是诱发职场欺负的组织基础。组织凝聚力又可通过透明度、责任和能力三方面来衡量。高凝聚力的组织中,欺负是不必要且不被允许的;而组织混乱和权力滥用则为职场欺负的猖獗提供了温床。人际互动中的弱势者可能会在混乱无序的组织环境中被放大,即使相对强权者也可能成为受欺负者[33]。
Ironside和Seifert(2003)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指出,职场欺负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一种对员工进行日常管理控制的典型做法[34]。职场欺负的基础——雇主和雇员双方权力的不平等,来源于二者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地位:一方面,雇员作为劳动力的卖方,在数量上远超过作为劳动力买方的雇主,即属于买方主导;另一方面,失业带给雇员的损失远大于劳动力短缺对于雇主的影响。由此可见,需要从更深层次的劳动关系角度对职场欺负进行解读。
(二)劳动关系视角下的职场欺负干预
对职场欺负现有政策和实践干预效果的质疑,使得人们不得不考虑管理层、工会、工人和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立场和态度:一方面,在一些职场欺负事件中,管理者本身就是职场欺负的实施者,高层管理当局很难让这些管理者将反欺负的政策和措施贯彻执行下去;另一方面,高层管理当局往往不愿意由工会出面通过集体挑战的方式胁迫其解决问题,更愿意通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来处理欺负案件。而人力资源部门则常打着“强调员工参与”的口号,让员工独自面对欺负事件。正如Hutchinson(2012)所说,职场欺负不仅是个体间行为的产物,更是涉及工作、组织和雇佣关系在内的一个复杂问题,需要雇主、政府、工会等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到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以干预和减少欺负的行动[35]。目前各种干预措施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之所以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措施往往强调的是个体层面,而忽略了组织、雇佣关系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这些措施实施的前提假设是:雇主和组织有意愿和能力对职场欺负行为进行干预。
然而,在经济不景气的宏观形势下,雇主和组织面临激烈的竞争和高绩效的压力,为了实现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雇主和组织需要维护高绩效的工作系统。而对于那些擅长使用政治技能的领导者而言,职场欺负可被作为一种管理绩效低下员工的战略手段,通过员工的优胜劣汰,有助于达成对领导者和组织预期的绩效目标[31]。为此,雇主和组织会对其干预职场欺负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权衡,进而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决策。从劳资关系的视角来看,影响雇主和组织做出上述决策的因素可归纳为:
首先,对高绩效的关注。Lewis和Rayner(2003)指出,由于一些直线管理者本身就是职场欺负的实施者,组织高层管理当局很难让这些管理者将反欺负政策贯彻执行下去,强制实施的话可能会致使其管理权威受到质疑而最终使组织损失一名在业绩方面表现优秀的管理者[36]。
其次,员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Beale和Hoel(2011)指出,当劳动力市场上稀缺的高技能、熟练工人遭受职场欺负时,雇主和组织往往会进行积极干预,以获得员工的高承诺和高留职率;而对于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易被获得和替代的低技能员工遭受职场欺负时,雇主和组织往往希望通过职场欺负使其尽快离职,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因而可能会无视甚至鼓励欺负[37]。
再次,劳动关系的处理模式。Hoel和Beale(2006)指出,在英国,组织管理当局更愿意通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强调员工参与的建言机制和申诉流程来处理职场欺负问题,而不是以工会等集体挑战的方式胁迫其解决[32]。
最后,政府角色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Beale和Hoel(2010)通过对英国和瑞典两国企业在处理职场欺负问题上的做法进行比较得出,职场欺负在瑞典并未引起企业的重视可能与职场欺负带来的员工缺勤、提前退休等成本是由政府买单、企业缺乏相应的财务动机有关。同时,瑞典有明确的针对职场欺负的法律,因而企业更愿意将干预职场欺负看作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31]。
四、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对职场欺负的干预作用及其角色障碍
劳动关系视角下的职场欺负研究,往往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作为职场欺负干预措施的主要实施者。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人力资源部门在干预欺负方面,并未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源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定位。
(一)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干预作用的质疑
Salin(2008)以荷兰市政部门人力资源经理为调查对象,探讨了他们对于各类职场欺负干预措施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数量情况[3]。结果表明,人力资源经理最常采用的干预措施是书面的反欺负政策和提供与欺负相关的信息,而且政策的实施特别强调管理者和直接上级的作用。而从调查对象提供的书面反欺负政策规定可以看出,各类组织的反欺负政策规定几乎如出一辙,并非根据各组织自身需要和实际情况进行量身制定,而且不论是对于受欺负者还是各部门的管理者而言,人力资源部门很少提供具体支持和建议。受欺负者经常被建议直接与其直线上级进行沟通,人力资源管理者也常将这类人员管理问题下放到各部门的直接管理者去处理。然而已有研究表明,直线管理者往往正是欺负行为的实施者[33]。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这一做法无形中鼓励了放任型领导,并进一步强化了受欺负者的习得性无助感。
Cowan(2012)也指出,受欺负者常会抱怨人力资源专业人员的不作为,甚至在他们向人力资源部门寻求帮助后,情况变得更糟了。一些受欺者报告称,在向人力资源部门申诉受欺经历后,感觉受到了恶意中伤(二次受欺体验)。一些人力资源部门人员由于未获得他人信息的证实,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仅凭过去经验直觉进行判断,往往对欺负情景进行错误归因,将欺负归因于受欺者本身,认为受欺负者往往是出于对他人行为的误解而感到受到了欺负,进而对受欺者给予不公正的批评[38]。
(二)干预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障碍
Lewis和Rayner(2003)通过批判性的文献回顾指出,过去20年来,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在英国各类组织中的发展使得职场欺负被允许甚至被间接鼓励[36]。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为了维护雇主利益,使其免于与职场欺负相关的法律制裁,通常不会公开、公平地处理职场欺负问题。而工会组织的缺失(或被边缘化)以及员工在参与管理中微弱的话语权,使得员工只能独自应对职场欺负或以换工作的方式寻求自我解决。
事实上,人力资源部门对于职场欺负行为的干预意愿主要取决于其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组织战略伙伴的角色使得人力资源部门将职场欺负看作是帮助组织保持生产力的一种竞争行为而非恶意欺负;同样,行政管理专家的角色也使得人力资源部门关注于更宏观的组织流程与结果,而将职场欺负看作是直线管理者应处理的问题,除非这一问题影响到整个组织。这样就使得人力资源部门可能对早期较轻微程度的欺负行为采取置之不理或观望态度。
当欺负的实施者是直线管理者时,人力资源部门人员认为职场欺负事件是烫手山芋,会威胁到他们与直线管理者的关系,因而他们往往优先考虑和维系自身与直线管理者的业务合作关系,宁愿牺牲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不把直线管理者的行为标签为欺负行为,而是自然而然地不信任员工对职场欺负所进行的申诉;相应地,员工将人力资源部门对待欺负问题的这种不作为看作是人力资源部门对直线管理者实施欺负的否定或是与实施者的同流合污,是职场欺负消极影响的延伸,进而降低对反欺负政策的预期以及对人力资源部门的信任。Harrington, Warren和Rayner(2013)通过对英国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者的话语分析也表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者常将员工投诉的管理者欺负行为看作是管理者进行合法的绩效管理行为,宁愿以牺牲员工拥护为代价来维护组织利益[39]。
五、研究趋势与展望
(一)研究范式的扩展
批判管理范式关注去人性化的、冷淡的职场关系对职场欺负行为的诱发作用,将职场欺负看作是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权力关系的反映,是组织维护其秩序、权威和纪律的一种手段。后现代主义范式则关注权力、控制和监视,将职场欺负看作是组织实施控制的一种形式。在这两个研究范式下,职场欺负已超越个体层面,扩展至更广泛的组织层面乃至组织之外的宏观环境层面。为此,一个符合伦理的、公正的组织对于抑制职场欺负的发生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对职场欺负的研究需要考察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对职场欺负的诱导作用以及受欺负者对这一作用如何应对。
(二)跨学科、跨层次的研究
跨学科方面,如同骚扰问题一样,职场欺负问题不仅是一个涉及个体心理健康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法律、管理、社会领域的问题,为此需要从多个视角加以分析,并从多方介入的角度(雇主、工会、政府、志愿型组织/第三方调解机构等)加以应对。
跨层次方面,可以考虑从宏观层面,加强国家文化、制度惯例等对组织形态、进而对职场欺负的影响。比如,Beale和Hoel(2010)从政府角色、立法框架以及组织所采用的员工关系处理模式等方面,对比了瑞典与英国对待职场欺负问题的不同做法[31]。英国有专门的政府部门通过设立基金项目的方式鼓励工会和雇主参与职场欺负问题的处理,但对职场欺负问题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法律框架;而瑞典有专门的法律框架对职场欺负问题进行干预,并且员工缺勤、提前退休等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大多由政府买单,组织缺乏财务动机来干预职场欺负,管理层也往往不愿出面介入员工工作冲突。
未来也可从中观层面,探讨行业与组织性质的影响,目前基于劳动关系视角的职场欺负研究大多以公共部门的机构改革为背景,着重探讨了公共部门权力等级分明、监督控制严格的官僚制组织形态对于职场欺负的诱发作用,未来可更多考虑不同行业、甚至是非政府组织的职场欺负现象。从劳动关系的角度看待职场欺负问题,可以整合个体行为、权力关系、规章制度、职业健康、多样化员工管理等因素在识别雇佣和工作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更有助于从政策制定和实施层面促进对职场欺负问题的干预。
(三)人力资源管理角色的转变
由前文论述可知,人力资源部门在处理职场欺负问题时的出发点往往以组织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而不是雇员福祉。要想使人力资源部门成为干预欺负的重要力量,需要首先明确组织管理当局对于欺负的立场和态度。以往研究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往往没有独立的价值取向,唯一的价值取向就是为雇主服务,未来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将增加独立的价值取向,干预职场欺负进而促进员工心理安全本身就是人力资源管理独立的价值主张,这也应该成为人力资源职业化和独立性的着眼点。
比如,在儿童欺负处理上的教训表明,如果在处理方式上忽略了对员工隐私的保护,可能会对受欺负者造成“二次伤害”。因为让其他人知晓了自己的受欺负经历会让受欺负者感到更加敏感和羞耻。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一些研究建议,最初对欺负的关注最好是通过其他渠道,而不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渠道。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是与雇主相关的、结构化的、系统的和战略导向的,其出发点之一就是减少雇主企业的用工风险。这一职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其公正性。为此,一些大型的组织可考虑雇佣受过专业培训的调解员对职场欺负问题进行干预和应对。
(四)企业管理哲学的转变
从职场欺负的研究范式转变趋势来看,改变职场欺负的关键在于“人类民主精神向现代企业渗透”。在普拉哈拉德《管理的未来》中,他提到了一个创新型企业“戈尔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人人倡导“自然领导”的体系,员工用脚投票、自由公司时间安排,领导者的权力不是理所应当的,自然在这样的企业中,就不存在“欺负型组织”的特征。而在互联网社会的今天,企业范式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行业发展历程来看,要构建能迎接未来的企业形态,就是建立一个适合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一个能够真正尊重、激发和赞赏人类创造性、激情和勇气的新型管理模式。
[1]EINARSEN S. Harassment and bullying at work: A review of the scandinavian approach [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0, 5: 379-401.
[2]KHAN A & KHAN R.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workplace bullying.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rainning, 2012, 44(2): 85-89.
[3]SALIN D. The prevention of workplace bullying as a ques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easures adopted and underlying organizational factors [J]. Scand. J. Mgmt. 2008, 24: 221-231.
[4]HOEL H & BEALE D. Workplace bullying,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towards a contextualiz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6, 44(2): 239-262.
[5]郭靖,张碧红,黄绿香,等. 职场欺凌的中国文化背景分析:基于深度访谈的探索性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2): 302-307.
[6]SKOGSTAD A, TORSHEIM T, EINARSEN S & HAUGE L J. Test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hypothesis of bullying on a group level of analysis: Psychosocial factors as precursors of observed workplace bullying [J]. Applied Psychology, 2011, 60(3): 475-495.
[7]李永鑫,聂光辉, 李艺敏,王明辉 & 赵国祥.工作场所欺负的内容结构与测量 [J]. 心理科学, 2011,34(5): 1201-1208.
[8]ZAPF D. Organizational work group related and personal causes of mobbing/bullying at work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1999, 20: 70-85.
[9]HAUGE L J, SKOGSTAD A & EINARSEN S.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al predictors of workplace bullying: Why do perpetrators engage in the bullying of others? [J]. Work & Stress, 2009, 23(4): 349-358.
[10]VARTIA M. The sources of bullying: Psychological work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J].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96, 5: 203-214.
[11]DE CUYPER N, BAILLIEN E & DE WIITE H. Job insecurity, perceived employability and target’s and perpetrators’ experiences of workplace bullying [J]. Work and Stress, 2009, 23(3): 206-224.
[12]HAUGE L J, SKOGSTAD A & EINARSEN S. The relative impact of workplace bullying as a social stressor at work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0, 51: 426-433.
[13]CILLIERS F. A systems psychodynamic description of organisational bullying experiences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2011, 38(2): 44-55.
[14]GAETANO M. Bullying: A view from the corporate world [J].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Association, 3(2): 52-57.
[15]MEGLICH-SESPICO P, FALEY R H & KNAPP D E. Relief and redress for targets of workplace bullying [J]. Employ Respons Rights, 2007, 19: 31-43.
[16]JENKINS M F, ZAPF D, WINEFIELD H & SARRIS A. Bullying allegations from the accused bully's perspective [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23(4): 489-501.
[17]HUTCHINSION M, WILKES L, JACKSON D & VICKERS M H. Integrating individual, work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esting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bullying in the nursing workplace [J]. Journal of Nursing Management, 2010, 18:173-181.
[18]MILLER H & RAYNER C.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bullying behaviors in a strong occupational culture: Bullying in a U.K. police service [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12, 37(3): 347-375.
[19]MCCORMACK D, DJURKOVIC N & CASIMIR G. Workplace bullying: the experiences of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pprentices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3, 10: 1744-1764.
[20]SALIN D. Ways of explaining workplace bullying: a review of enabling, motivating, and precipitating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in the work environment [J]. Human Relations, 2003, 56: 1213-1232.
[21]ALEV KATRINLI, GULEM ATABAY, CANGARLI B G, et al.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of bullying behaviors as 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tactics [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0.
[22]ALEXANDER M, MACLAREN A, O’GORMAN K & TAHERI B. He just didn’t seem to understand the banter: Bullying or simply establishing social cohesion?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5): 1245-1255.
[23]TRACY S J, LUTGEN-SANDVIK P & ALBERTS J K. Nightmares, demons, and slaves: Exploring the painful metaphors of workplace bullying [J].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6, 20: 148-185.
[24]MCCARTHY P. Workplace bullying: A postmodern experience. In: Einarsen S, Hoel H, Zapf D, et al. (eds) Bullying and Emotional Abuse in the Workplac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231-244).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03.
[25]LIEFOOGHE A P D & DAVEY K M. Employee accounts of bullying. In: Einarsen S, Hoel H, Zapf D, et al. (eds) Bullying and Emotional Abuse in the Workplac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03. pp. 219-230.
[26]BURRELL G & MORGAN G. Sociological paradigms and organisational analysis. London, England: Heinemen Education Books, 1979.
[27]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997.
[28]MATTHIESEN S B & EINARSEN S. Perpetrators and targetsof bullying at work: Role stres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J]. Violence and Victims, 2007, 22(6): 735-753.
[29]LIEFOOGHE A P D & DAVEY K M. Accounts of workplace bullying: The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1, 10(4): 375-392.
[30]HUTCHINSON M VICKERS M H, JACKSON D & WILKES L. Workplace bullying in nursing: Towards a more critical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J]. Nursing Inquiry, 2006, 13: 118-126.
[31]BEEALE D & HOEL H. Workplace bullying,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for management in Britain and Sweden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0, 16(2): 101-118.
[32]HOEL H & BEALE D. Workplace bullying, psychological per spective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towards a contextualized and int erdisciplinary approach [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6, 44(2): 239-262.
[33]HODSON R, ROSCIGNO V J & LOPEZ S H. Chaos and the abuse of power: Workplace bullying in organizational and interactional context [J]. Work and Occupations, 2006, 33: 382-416.
[34]IRONSIDE M & SEIFERT R. ‘Tackling bullying in the workplace: the collective dimension’. In S EINARSEN, H HOEL, D ZAPF and C L COOPER (eds.), Bullying and Emotional Abuse in the Workplac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M]. London/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2003.
[35]HUTCHINSON M. Rethink workplace bullying as an employment relations problem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2, 54(5): 637-652.
[36]LEWIS D & RAYNER C. Bullying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 In: Einarsen S, Hoel H, ZapfD, et al. (eds) Bullying and Emotional Abuse in the Workplac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370-382).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03.
[37]BEALE D & HOEL H. Workplace bullying and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Exploring questions of prevention, control and context [J].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2011, 25(1): 5-18.
[38]COWAN R L. It's complicated: Defining workplace bullying from the human resource professional's perspective [J].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2, 26(3): 377-403.
[39]HARRINGTON S, WARREN S & RAYNER 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responses to workplace bullying: Cycles of symbolic violence [J]. Organization: The Critic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015, 22(3): II (679).
Research on Workplace Bullying Based on Labor Relations: A Transformation of Paradigms
FU Meiyun1; Meng Fanqiang2
( 1.NanKai University BinHai College, Tianjin 300270, China; 2.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
Based on the functionalist paradigm,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es understood workplace bullying as an interpersonal issue between two or more employe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a number of studies conducted on the individual and job antecedents of bullying, ignoring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employment system and other factors of organizations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Consequently,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measures adopted to intervene bullying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either the prevention or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critical management theory paradigm and post modernist paradig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ment relations emphasizes the existence of ‘bullying organization’, and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and managerial control of employees as the important antecedents of bullying. So the intervention initiatives of employers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department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of workplace bullying. This perspective applies a contextualiz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reveal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workplace bullying under new labor relations, and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and implying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reduce workplace bullying.
workplace bullying; employment relations; paradigms
F246
A
1673-2375(2017)04-0050-09
[责任编辑:苏 清]
2016-11-2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12BSHO57);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TJGL13-005)的研究成果。
付美云(1980—),女,河北张家口人,博士,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法政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孟繁强(1980—),男,辽宁瓦房店人,博士,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人力资源管理、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