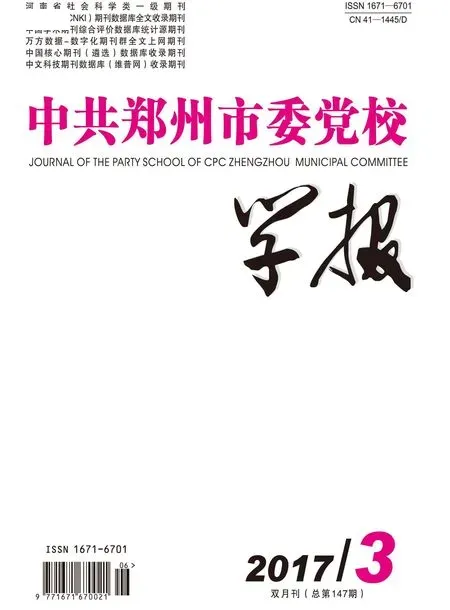论明清“性灵”思想对沈复《浮生六记》的影响
李巧玲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8)
论明清“性灵”思想对沈复《浮生六记》的影响
李巧玲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8)
“性灵”思想在晚明时期曾经对中国文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到了清代中期,“性灵”思想又一度恢复了勃勃生机,在江南一带影响甚广,而生活于乾嘉时期的江南文人沈复也难免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明清“性灵”思想对沈复《浮生六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保持真实的情性、自由抒发对生活的欲望、表现出独特的创造性三个方面。
明清“性灵”思想;沈复;《浮生六记》;影响
“性灵”一词,其实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就被一些文人所用,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1]到了唐代,也有“陶冶性灵存底物,自诗改罢自长吟”的诗句。这些时候的“性灵”一词,其意义大概是指人的本性中的性情。到了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时期,“性灵”一词重新被人们所重视,它的内涵也比南北朝时期更加丰富。晚明时期公安派的重要领袖袁宏道曾在《叙小修诗》中称其弟之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袁宏道的这些评论之词,表现了其“性灵”思想的主要内容。今天看来,大抵可这样总结:“要求诗不托于理,不托于闻见知识,而发之于真实的情性,要求诗自由地抒发人的生活欲望;要求诗表现出个人的独特创造。”[2]这样的内涵显然与南北朝时期的“性灵”意义是有区别的。而到了清代中期,辞官归隐的袁枚在小仓山下的随园过着广交四方名流的名士生活,他也标举“性灵说”,使晚明公安派提出的“性灵说”在清初衰退后再一次恢复了勃勃生机。袁宏道和袁枚提出的“性灵说”虽然主要是针对诗歌创作的,但一经提出后它不仅影响了许多文人的诗歌创作,而且在文章创作方面也同样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性灵说”不仅使袁枚创作了《祭妹文》《所好轩记》《随园记》等优美感人、盛传不衰的文章,而且也带动了江南一带许多才子文人的创作热情。例如生活于清朝乾嘉时期的非主流江南文人沈复,就受“性灵”思想影响颇深,从沈复创作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中,我们不难看出“性灵”思想的频频闪现。
一、保持真实的情性
保持人性的纯真自然是“性灵”思想首要的特点,沈复在此基础上创作的《浮生六记》也因为含有作者真实的情性而深深感染着读者的心。例如在卷一《闺房记乐》中描写陈芸的相貌和作者对陈芸的一见钟情:“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余年一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3]。
两段文字中前者描写了芸的秀丽和缠绵之态,但也对其“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表达了一种遗憾。而后者描写了对芸的一见钟情,可仍流露出“窃恐其福泽不深”的一种担忧,前文中明显的遗憾和后文中由衷的担忧都是作者真实的性情流露。作者不似前代文人描写对女子的爱慕那样只写出女子的美丽,而是并不掩饰她的不佳之处,更不掩饰自己对其薄相的担忧。这样的描写更让人感受到芸的那种真实自然的美和作者的用情之深。同样具有真实情性的描写也体现于卷一中,叙述作者对妓女憨园的私爱之心。
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将挈芸游虎丘,闲憨忽至,曰:“余亦有虎丘之游。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因请吾母先行,期于虎丘半塘相晤。拉余至冷香寓,见冷香已半老,有女名憨园,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款接间,颇知文墨。有妹文园尚雏。
余此时初无痴想,且念一杯之叙,非寒士所能酬,而既入个中,私心忐忑,强为酬答。
因私谓闲憨曰:“余贫士也,子以尤物玩我乎?”
闲憨笑曰:“非也。今日有友人邀憨园答我,席主为尊客拉去,我代客转邀客。毋烦他虑也。”余始释然[4]。
从上述文字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妓女憨园的私爱之心。诚然,在当时的年代中,像作者这样的衣冠子弟除了正室妻子外,宠爱姬妾是很平常之事,但问题是,作者上述文字是在其卷一《闺房记乐》中出现的,而这部分内容则主要是描写夫妻间恩爱情感的,这似乎破坏了作者爱情专一的高大形象。但试想之,作者的这些描写其实正是其真实情性的自然流露。他对妻子芸并非爱恋不深,而是在见到美而韵的女子时一种真实的性情流露,俗语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处于男子有权拥有三妻四妾的封建时代,作者对貌美的妓女存有私爱之心也很正常。作者能在此处写出这些内容,更可见他毫不遮掩自己情性的一面。尽管按今天的情感标准来看,这些描写似乎有损他痴情的形象,也多少会令渴望男子情感专一的女性失望,但笔者认为,真实的卑下还是比高尚的虚伪要高尚。另外,其妻芸因失欢翁姑,颠沛流离,抑郁而死之后,在吴俗的鬼魂回煞之期,卷三《坎坷记愁》中这样描述:
余冀魂归一见,姑漫应之。同乡张禹门谏余曰:“因邪入邪,宜信其有。勿尝试也。”
余曰:“所以不避而待之者,正信其有也。”
张曰:“回煞犯煞,不利生人。夫人即或魂归,业已阴阳有间,窃恐欲见者无形可接,应避者反犯其锋耳。”
时余痴心不昧,强对曰:“死生有命。君果关切,伴我何如?”
张曰:“我当于门外守之。君有异见,一呼即入可也。”
余乃张灯入室,见铺设宛然,而音容已杳,不禁心伤泪涌……
此时心舂股栗,欲呼守者进观;而转念柔魂弱魄,恐为盛阳所逼,悄呼芸名而祝之,满室寂然,一无所见。既而烛焰复明,不复腾起矣。出告禹门,服余胆壮,不知余实一时情痴耳[5]。
上述文字描述中,作者对其妻芸娘那份刻骨铭心的爱恋令人潸然泪下,这是一种情真意切的断肠之恋,而不似有些文人在其悼亡诗词中对其妻那种矫揉造作的怀念。但作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凡人,尽管情痴而欲见其妻魂魄,但也有胆怯的一面,如“此时心舂股栗,欲呼守者进观;而转念柔魂弱魄,恐为盛阳所逼,悄呼芸名而祝之……”读至此处,我们决不会低视作者之胆怯,反愈见其情痴和真实的人性光芒,从而产生钦敬和感动之情。
二、自由抒发对生活的欲望
肯定并自由地抒发人的生活欲望也是“性灵”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如此新鲜又真实的生活情感和欲望在《浮生六记》中也屡见不鲜。如卷一《闺房记乐》中作者这样描述婚后夫妻小别,对妻子的依恋之情:
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
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
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
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6]。
上述文字详尽描述了作为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子对新婚妻子的爱恋之情。而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更多是描写妇女对分别丈夫的思念、爱恋之情,极少有男子在作品中大胆地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更何况像作者这样自由地抒发、细腻地描写男子对妻子的那份依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前所未有。尽管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描写男子爱慕美丽妓女的作品,但极少见到男子对妻子思念爱恋的描写,即使有,要么轻描淡写,要么闪烁其词,像这样诚挚而具体地表达男子思念之情的描写亦实属新鲜之作。又如在卷四《浪游记快》中我们仍可看到这样自由抒发生活欲望的描述:
卧床外瞩,即睹洪涛,枕畔潮声如鸣金鼓。一夜,忽见数十里外有红灯,大如栲栳,浮于海中,又见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实初曰:“此处起现神灯神火,不久又将涨出沙田矣。”揖山兴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事竣,十月始归[7]。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考场得意无疑是令许多男子最心驰神往的,而上述描写作者无拘无束的乡野之游,则充分表现出作者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同时也隐含了作者对功名仕途的兴味索然。卷二《闲情记趣》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余素爱客,小酌必行令。芸善不费之烹庖,瓜蔬鱼虾,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同人知余贫,每出杖头钱,作竟日叙。余又好洁,地无纤尘,且无拘束,不嫌放纵。
时有杨补凡名昌绪,善人物写真;袁少迂名沛,工山水;王星澜名岩,工花卉翎毛;爱萧爽楼幽雅,皆携画具来,余则从之学画。写草篆,镌图章,加以润笔,交芸备茶酒供客。终日品诗论画而已……
芸则拔钗沽酒,不动声色,良辰美景,不放轻过……
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8]。
这样的描写无疑表达了作者对闲适生活的怀念之情。爱妻相伴,友朋长谈,清茗一杯,可惜,红颜知己已香消玉殒,朋友也风流云散,不堪回首又留恋之极,怀念之情渗透纸背。
三、表现出独特的创造性
“性灵”思想中要求文章表现出个人的独特创造。而《浮生六记》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的读者阅而忘疲,很大程度上也都缘于作者的独特创造。此文中最突出的则是主要内容和布局。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极少写夫妻间感情的,而作者不但真实、生动地写出了与其妻芸之间二十三年的鸿案相庄之情,而且勇敢地把《闺房记乐》卷置于卷首,这在当时那个压抑人性、热衷科举的主流社会中的确是离经叛道之举。而后面三卷虽主要记述作者生活中的情趣、坎坷、浪游,但仍会充满着芸的影子,无处不洋溢着作者对芸的深深爱恋。而这样一部以夫妻深情和日常琐事为主要内容,又多以白描之笔真实、生动、细腻地记述之的自传性作品,真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稀有之作。也难怪林语堂先生从旧书堆中把它淘出来后,称其中的芸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另外,《浮生六记》的语言更是为人欣赏。俞平伯在《重刊浮生六记序》中赞美其语言“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作者又多以白描笔法,真实、细腻、生动地描述这些琐细之事,娓娓道来之中自有感人之处,看似平淡无奇,实则独有一翻雅韵。
那么,“性灵”思想为什么对沈复《浮生六记》影响如此之深呢?笔者认为以下的影响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首先,沈复生活于清朝中期的乾嘉盛世,此时,清初的遗民思潮渐趋低谷,而江南一带随着商品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日趋壮大的市民阶层就有了更多对文化的渴望,他们更喜欢贴近现实人生、表现个人生活真实情感的文学作品[9],在这样的趋势下,晚明时期盛极一时而清初又跌入低谷的“性灵”思想恢复生机就顺理成章。此时的“性灵”思想倡导者袁枚又弃官归隐至江南,与许多名士交游唱和,终于使“性灵”思想在当时的江南一带深入许多文人的内心并影响于他们的文学创作。其次,与作者自身的独特个性有关。作者多情重诺,爽直不羁,不愿为礼法所缚,不喜谈仕宦八股,而喜欢自由、闲适、充满情趣的平实生活。这样的性格一定会迷恋充满人性的“性灵”思想,而摒弃矫揉造作的假道学思想。因此,由如此个性的作者所创作的《浮生六记》无疑会深受“性灵”思想的影响。
[1][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89-90.
[2]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284.
[3][4][5][6][7][8]沈复.浮生六记[M].愈平伯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14,35,3-4,58,21-24.
[9]韩进康.无奈的追寻——清代文人心理透视[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216.
[责任编辑 张敬燕]
I207.41
A
1671-6701(2017)03-0102-03
2017-04-20
李巧玲(1978— ),女,河南南阳人,硕士,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