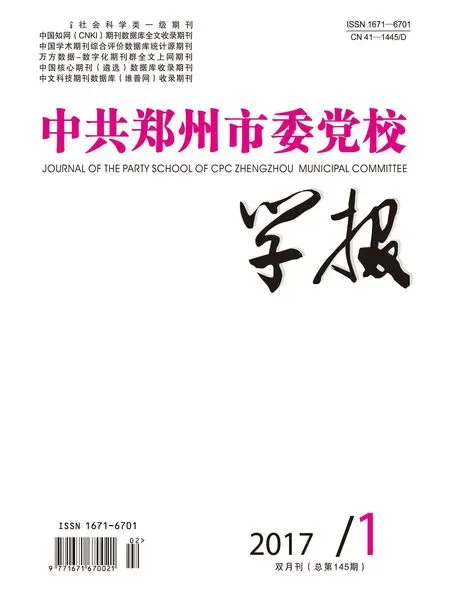网络群体性事件之舆情引导相关研究评析
殷辂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网络群体性事件之舆情引导相关研究评析
殷辂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和社会风险叠加后的特殊现象,虽然是一个新问题,但已经成为研究热点。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场域、生成模式及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网络舆情引导是网络治理的重要内容,其发挥着疏通壅塞、彰显公道、凸显社会的重要作用。政府在网络舆情引导中虽然需要发挥主导作用,但它与民众不是主客体关系,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只要除去附着在事件上的私意、私利、情绪,事件的是非曲直就会显现,网络舆情就不会出现变异。
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舆情引导
网络空间的兴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话语权结构、话语方式以及舆论形态。与此同时,我国进入风险社会,突发事件频发已成为“常态”。突发事件及相关的矛盾、问题必然会呈现在网络中,这种呈现不可能是直观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与风险社会叠加后的一个特殊问题,虽然具有群体性事件的一般特点,但无论是形成原因、社会影响还是舆情变化都相对复杂许多。学术界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多方位、多学科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对其进行梳理和辨析,对完善网络舆情治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界定
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在我国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最初是集体上访、游行示威、围攻政府机关、堵路请愿等聚众行为的统称。2004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在该文件中群体性事件虽然被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基于其行为方式的破坏性,又将群体性事件与非法聚集、围堵、串联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表述从维护秩序和稳定的角度出发,强调了事件对公共秩序的危害,并没有触及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在提出之时尽管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局限性,但一旦成为约定俗成的表述,其内在含义也发生了变化。目前学术界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有以下几个维度。
1.将网络群体性事件视为危及社会稳定的负面存在。这种观点延续了公安政法部门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将网络群体性事件视为利用网络实现非法、或非正常聚集的扰乱社会秩序的集群事件。揭萍和熊美宝在其合著的文章中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中人’群体,为了共同利益,利用网络进行串联和组织公开干扰网中网外秩序,干扰网络正常运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乃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集群事件。”[1]他们将网络群体性事件视为网上利益群体的有意识的串联活动,强调事件干扰网络运行,危害社会稳定。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葛琳、杨久华等。他们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其本质是一种集群行为。与揭萍和熊美宝稍有不同的是,葛琳区分了一般和严重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认为:“严重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会对网络内外秩序产生干扰,甚至危及社会稳定。”[2]杨久华在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模式的论文中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它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乃至可能或已经发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暴力事件。”[3]这种界定与揭萍、熊美宝相似,强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串联性、组织性,将网络群体性事件视为群体性事件在网络时代的表现形式。
2.将网络群体性事件视为风险社会、转型社会中的维权现象。邵道生在《正确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一文中,批评了一些地方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错误思维方式。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不是去治‘根’,而是去治‘表’;不是将事件的主体看成是‘公民’‘良民’,而是将其看成是‘刁民’‘乱民’;不是将事件主体看成是‘权益受损的受害者’,而是将其看成是‘公共安全的破坏者’。”[4]他还认为,如果说突发性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的话,那么始作俑者不是事件的主体,而是严重损害弱势群体权益的少数当权者。单光鼐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虽然很多事件都由网络舆论引发,但不能过度地进行政治化解读,“每个群体性事件都有他们的诉求,但目前主要还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5]。若夸大其敌对性,就会制造出本来不存在的敌人。张爱军在此基础上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界定为“公民基于利益表达的集体行动”,认为群体性事件只是过渡性概念,其实质是维权,将其“改称群体性维权事件有利于解决公民与现政权的矛盾、维护宪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顺应时代潮流”[6]。张爱军还批评了将群体性事件分类的做法,认为这淡化了问题的本质。
3.以中性的立场认识网络群体性事件。持此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不能一概地将网络群体性事件视为负面存在,也不能一概地将其视为正面的东西。裘伟廷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反社会性质,是一种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存在;广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并不是反社会的活动,而是被社会情绪支配的社会集体行为,是一种中性的社会现象[7]。虽然狭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倒逼真相、监督权力、缓和社会矛盾方面有积极意义,但是以狭义和广义去界定网络群体性事件,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杜骏飞给出了一个更全面的定义:“网络群体事件的本质是网民群体围绕某一主题、基于不同目的,以网络聚集的方式制造社会舆论、促发社会行动的传播过程。它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受组织的,可能是有序、健康的,也可能是无序、不健康甚至是非法的。”[8]杜骏飞的定义突出了舆论聚焦和网络聚集,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否有组织、是否合法应该从具体的事件中去判断。于建嵘不主张对群体性事件做预设的一般性判断,他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9]据此,他将中国群体性事件划分为四种类别,即“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社会泄愤事件”[10]。维权性抗争事件虽然所占比例较大,但它只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类。就像不能将群体性事件一概地判定为“闹事”一样,也不能完全将它视为维权。童星、张海波从有无组织、有无直接的利益诉求两个维度将群体性事件分为四个类别:“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11]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场域、生成模式和形成原因
1.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网络传播的关联性。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传播造成的还是现实问题在网络中的反映,学术界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从网络助燃的角度界定网络群体性事件,将其界定为由网络引发、传播直至演变为有一定规模的现实的群体性事件。第二,将网络群体性事件概括为非现实的、网络环境中的群体性事件。将网络群体性事件视为产生、爆发并消失于网络舆情意义上的群体事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传播行为。网络群体在共同关注的事件、主题之下聚集,以制造大众舆论的方式引发群体行动,这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第三,将网络群体性事件视为网上、网下相互作用的结果,网络中的公共话题演变为现实问题,或现实问题在网上放大和聚集。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一样,学术界对于其发生的场域也从单一的角度向多元类型化转变。网络群体性事件是虚拟世界的现象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在研究初期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随着认识的深化,场域问题被生成模式问题取代。也就是说,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由网络舆论引起,还是由现实矛盾引起,只有在具体的事件中才能得到确认。但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网络传播相关联,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
2.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模式。杨久华研究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模式,认为:“我国网络群体事件发生模式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网络舆论引发模式、由网络谣言而恶化成失控模式、利益受损群体网络发动模式以及境内外敌对分子发起模式。”[12]在这里,网络舆论、网络谣言引发模式成为类型之一,现实利益受损群体以及敌对分子引发模式成为与其相对的类型。这种划分虽然避免了单一化的问题,但却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一,网络舆论和网络谣言为什么会产生?难道是网络制造出来的?第二,利益受损群体与敌对分子发动,能否与网络发动并列?这种划分在逻辑上没有解决现实与网络的关系。与杨久华的生成模式不同,何国平从动员模式角度研究网络群体事件的产生,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存在四种动员模式,即“焦点型动员模式、诱发型动员模式、泄愤型动员模式、公关型动员模式”。何国平分别分析了四种类型的特点:“焦点型动员模式中的焦点涉及三公部门的公信力,主要是‘涉腐’‘涉官’‘涉警’等问题;诱发型动员模式是由小问题引发的大事件;泄愤型动员模式主要是由‘义愤’激起,情绪性宣泄、讨伐是其主要表现;公关型动员模式是指人或机构为自身利益,通过网络推手、意见领袖或专业性的策划机构人为制造舆论,引发网络聚焦。”[13]这种区分逻辑层次分明,但把“动员”视为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就模糊了事件产生的社会性原因。网络群体性事件存在发动者,但动员并非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绝大部分诉求、事项、话题即使存在动员者也不能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社会动员理论只能描述事件的类型,但并不能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模式上,孙晓晖提出了与产生过程相应的四种类型:“个人问题社会化、社会矛盾网络化、网络舆论扩大化、舆情蔓延危机化。”[14]这种描述性概括是有意义的,但同样不能将其视为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
3.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原因。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原因和机理问题上,王扩建做了一般性概括:“网络特性的外在诱因、求实追责的内在机理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本质特性引发了网络群体性事件。”[15]互联网的特性是传播迅速、覆盖面广,并且具有交互性、虚拟性、盲从性,事件很容易被聚焦放大,舆论也容易激化。同时,民众对事实真相的探究欲越来越强,但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网络群体性事件必然会频繁出现。高抗分析了个体事件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机理:“第一,发生了具有特殊性的个体事件;第二,命运的共同依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第三,去个性化、群体激化等群体心理机制;第四,公共权力机关的应对失当。”[16]高抗的分析较为全面,他认为特殊的事件在特定的环境下被点燃,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机理。但是,高抗的分析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将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群体性事件区别开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独特性体现在何处?群体性激化、去个性化等心理机制并非网络环境造成的,而是群体环境下的问题,将其作为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实际上,网络中的群体性聚集与现实中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网络环境中虽然存在舆论激化现象,但这绝非简单的去个性化或群体激化,而是现实问题在网络中的反映。网络群体与现实中的群体并不完全一样,不存在直接的、面对面的情绪感染过程。网络中的舆论激化则是社会性激化,网络只是起到了聚焦作用。没有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单纯的网络氛围不可能聚集人群且产生群体性事件。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引导
1.网络舆情的概念界定。网络舆情在字面上可以表述为网络上的舆情,但这种表述却没有实质性意义,因为舆情并不是由网络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事件+网络”,是网络新闻事件产生的模式,但并不能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的内涵。网络舆情的概念界定存在不同的视角,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将网络舆情界定为民众在网络空间内表达“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17]。第二,将网络舆情视为网民“对某一‘焦点’‘热点’问题所表现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的情况”[18]。第三,将网络舆情看成是民众在网络空间围绕特定社会事项“对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态度”[19]。以上几个定义虽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在以下两个方面是一致的:网络舆情虽然发生在网络空间,但并非是虚拟的;网络舆情是一种公众情绪或意见的集合,而不是单个人的情绪表达。在引发网络舆情的刺激源问题上,研究者的观点存在不同:第一,将中介性社会事项视为群体自己关心的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第二,将刺激源看成是互联网上传播的“焦点”“热点”问题;第三,将公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社会事项作为舆情的刺激源。以上几种界定虽然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第一,没有将引发社会情绪、产生社会心理的背景因素考虑进去。网络舆情并非是特定事项在网络中的直观反映,事件背后的情绪、心理倾向都会借助于事件而释放。因此,网络舆情实际上是社会背景、事件、网络这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第二,忽视了中介性社会事项的独特性。并非所有事件都能引发网络舆情,只有具有爆炸力、刺激性和象征意义的公共事项才能引起舆论聚焦,并且这种公共事项并不仅仅与公权力有关。同时,在特殊的事件背后是问题的普遍性,没有后者,不会产生持续性的舆情。第三,对“网络舆情”的属性定位不清晰。将网络舆情表述为“情绪、态度的总和”或“倾向性的共同意见”,并没有触及舆情的社会属性。实际上,社会情绪、倾向、态度并非先验的存在物,而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就是说,它们并非来自一般性的价值判断,而是与现实矛盾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个体或局部的现象不足以形成集体倾向和心理,只有在社会环境持续性地刺激下,才会形成共同的情绪和态度。
2.网络舆情的引导行为。关于网络舆情的引导,学术界在基本问题上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舆情是民众的心声,是一个自然展现的过程,不存在引导问题,也不应该刻意引导。引导的本质就是控制,刻意的引导不但不会让人接受,反而会产生新的问题。互联网正处在发展阶段,控制或限制网络不利于网络的繁荣。在现实中缺乏制度化的诉求表达平台,在传统媒体中也缺乏舆论自由表达的空间,民意难以进入决策和裁判之中,如果限制或控制网络的表达,社会矛盾与公共情绪就无法释放。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网络舆情不但需要引导,还需要强化政府在引导中的主体作用。他们认为,网络舆情的产生、传播虽然具备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但并不一定代表大多数,网络舆情存在流言、谣言和情绪性因素,同时,敌对势力和网络炒手会误导舆论,如果不加以引导,必然会产生混乱。这两种观点虽然看似对立,其实也存在共同之处,即预设了引导者和被引导者,将舆情引导视为人的引导。实际上,舆情引导是舆论共同体的共同行为,这个共同体既包含政府,也包含民众,引导的目的是彰显事件本来的是非曲直,防止事件的变异。
3.网络舆情的引导方法。在舆情引导方法和策略方面,许蓉佳提出“完善社会管理、加强舆情监测和主流媒体作用、控制网络议题设置、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建立网评队伍”等具体对策[20]。苑丰分析了地方政府应对网络事件的策略,将其概括为“公关管控”:“目的是尽快消除网络负面影响,维护自身形象,本质上是迫于压力型体制的刚性约束。通过‘信息封锁’对互联网媒介生态形成的政府治理挑战的一种短视回应,其危害在于矛盾积聚与消解权威。”[21]他提出政府应对网络事件应从“管控”转变为“沟通引导”。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机制、高效的矛盾排查调处机制,是应对网络事件的关键所在。陈月生将网络舆情分为常态舆情和非常态舆情。常态舆情是指普通或相对稳定的舆情,而非常态舆情是指突发的、表现强烈的、处于不稳定状态下的舆情。他认为,网络舆情的引导也应该作出这种区分。常态的舆情疏导应“贯穿于日常工作之中,与政府的思想政治工作、矛盾调解工作、社情民意汇集反映工作、各种宣传教育活动等形成相互依赖互相配合的工作机制”,而非常态的舆情疏导,主要体现在特殊事件或突发事件的应对之中,应“通过疏理、疏通,使其分散和分流,在最短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内使激烈的冲突状态获得理性导向,使人们对待社会的态度和行为不是由冲动和情感支配”[22]。网络舆情需要引导,但绝非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运用舆论操纵人们的意识,引导人们的意
向,从而控制人们的行为,使他们按照社会管理者制定的路线、方针、规章从事社会活动的传播行为”[23]。这种观点是灌输论的延续,没有摆脱阶级斗争的思维窠臼。社会管理者与民众并非对立的群体,也不应该有自身的私利,所谓操纵人们的意识,其本质是将政府与民众割裂开来。舆情引导是善治范畴内的问题,不是通过操纵言论而去除壅塞、彰显公道。而是只要除去附着在事件上的私意、私利和预设立场,事件本来的是非曲直就会显现,舆情就会自然畅通。因此,舆情引导其本质是一个理性互动的过程。政府在舆情引导中虽然要发挥主导作用,但它与民众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而是相互监督、共同治理,有共同的责任将变异的舆情矫正过来。目前,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引导上存在着理念不清、囿于技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没有将舆情的引导置于社会治理范畴之内,驾驭、管控思维没有消除。舆情引导其实是多元主体的共同行为,政府部门既是主体也是客体,规范政府行为,防止政府形象被少数官员劫持,这是舆情引导的关键所在。然而,在现实中,政府主导、社会共治的理念并没有确立。第二,将舆情视为力量较量的结果,预先定调、强势灌输,不但不能正确引导舆情,反而使其产生新的变异。第三,将舆情的引导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脱离真相、是非而论技巧,造成手段与目的割裂。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的引导,其前提应该是中立不倚、无偏无私,而不是抱着先入之见控制和操纵人们的思想行为。相信民众的良知和理性,在沟通中形成共识,彰显事件本来的是非曲直,应该是舆情引导的出发点。只有确立了正确的理念,才会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将舆情引导至正确的方向。
[1]揭萍,熊美保.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J].江西社会科学,2007,(9).
[2]葛林.网络舆论与网络群体性事件[J].新闻爱好者,2008,(9).
[3]杨久华.当前我国网络群体事件发生的模式、趋势及其防范策略[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9,(3).
[4]邵道生.正确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J].社会科学报,2009,(2).
[5]单光鼐.当前群体性事件新特点和应对之道[J].时事报道,2009,(11).
[6]张爱军.群体性事件概念之名实辨析[J].社会科学论坛,2010,(13).
[7]裘伟廷.网络群体性事件初探[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3).
[8]杜骏飞.网络群体事件的类型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9,(7).
[9][10]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4,45.
[11]童星,张海波.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J].学术界,2008,(2).
[12]杨久华.试论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模式、原因及其防范[J].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
[13]何国平.网络群体事件的动员模式及其舆论引导[J].思想与政治工作研究,2009,(9).
[14]孙晓晖.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执政公信力的流失及其防范[J].理论与改革,2010,(4).
[15]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特性、成因及对策[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5).
[16]高抗.试论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演变机理[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5).
[17]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3.
[18]周如俊,王天琪.网络舆情: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J].思想理论教育,2005,(11).
[19]纪红,马小洁.论网络舆情的搜集、分析和引导[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20]许蓉佳.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舆情引导[J].唯实,2010,(7).
[21]苑丰.从“公关管控”走向舆情引导[J].理论与改革,2012,(3).
[22]陈月生.试论舆情疏导的理论内涵及其现实性[J].社科纵横,2007,(9).
[23]彭祝斌,邓崛峰.科学建构舆论引导机制[J].湖南大学学报,2010,(2).
[责任编辑 游玉华]
G206.3
A
1671-6701(2017)01-0060-05
2016-11-06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BSH35)、2013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2013BZZ009)阶段性成果
殷 辂(1964— ),男,河南舞阳人,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