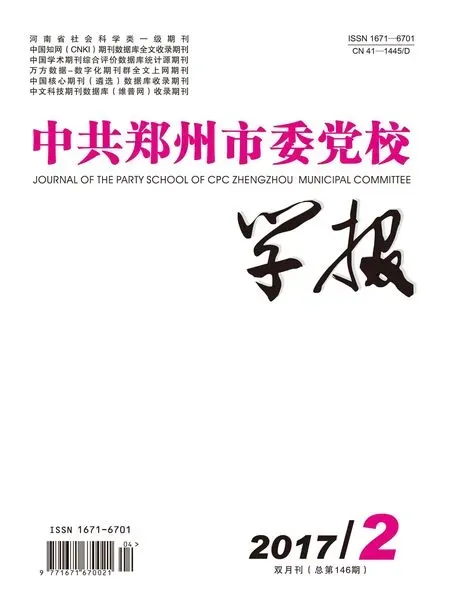刑法中“角色”的概念与意涵
陈文昊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刑法中“角色”的概念与意涵
陈文昊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刑法中的“角色”以一般人作为视角,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概念。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行为人的角色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介入因素的场合,他人对于角色的不履行会导致因果关系的阻断;在先前行为人对于结果发生存在回避义务的场合,介入因素不会导致因果关系的阻断。从不作为犯理论到规范论,角色在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定角色意味着行为人要承担更高的义务,因此法秩序在过失犯的认定中赋予行为人更高的期待。
角色;规范;过失犯
一、刑法中“角色”的内涵
在规范论的视域中,刑法保障的是那些忠诚于法的市民,即法律上人格体的角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行为人的缺陷表明他是无能力的时候,就可以对其免责”[1]。可以说,角色是规范的化身,它是指社会规范具体地指向行为人的载体,通过规范保障社会的同一性以维护规范的效力[2]。对此,雅各布斯教授认为,法秩序的命令不是“不得造成利益侵害”,而必须是“不得破坏你作为忠诚法律的市民角色”[3]。在笔者看来,刑法中的“角色”概念具有以下特点。
(一)刑法中的“角色”与社会预期相关联,是客观的、一般人视角的及应然层面的
存在论视域下对于个人形象塑造往往与行为人自身的能力休戚相关,可以说是主观的、行为人视角的、实然层面的,这就与规范论视域下的行为人形象产生了本质上的差异。对此,何庆仁教授举例进行阐明:报刊亭主人明知一篇报道上记载有国家机密仍然将该报刊卖给他人,司炉工明知自己送到锅炉里的煤污染成分超标仍然将煤送进锅炉。报刊亭主的角色就是将报刊卖给他人,司炉工的任务就是送煤进锅炉,二人没有义务去知道和检验自己所卖和所送东西的性质;即使知道报道上有国家机密和煤污染成分超标的事实,也没有必要破坏自己的角色[4]。
(二)刑法中的“角色”和“身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在本质上身份犯理论的构建是以“角色”概念作为基础的
德日刑法相关理论认为,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是与义务违反紧密相连的。对此,德国学者纳格勒(Nagler)认为,只有对法秩序所指向的、邀请特定集团服从的特定人才可以课以义务,因此就规范而言,并不是针对全体国民发出的。木村龟二教授也指出,在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场合,违反了法秩序所划定的特定身份所具有的特别义务,才能成为使犯罪成立的契机[5]。由此可见,作为身份犯制度得以构建的基石,社会期待以及特定注意义务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从这一点来讲,身份犯制度与刑法中“角色”的概念休戚相关。
(三)“角色”是由规范延伸出的产物,要求每个人按照法秩序的期待生活,不得僭越雷池
对此,雅各布斯教授指出,规范并非是用来指导活动的,而是把活动解释为属于抑或不属于某一秩序,当规范被认可,秩序就稳定了,这需要通过将偏离性活动贬低为边缘性的东西[6]。从这个角度来说,刑法中的“角色”不限于法秩序对于特定职业、身份具备者的合理期待,相反,每一个公民的生活都会受到法秩序所发出的要求的约束。例如,看到人行横道人们就可以放心地过马路,看到红色信号灯人们就毫不犹豫地停止前行[7]。
在笔者看来,刑法中“角色”的认定在很多方面对于犯罪论体系的构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刑法中“角色”的概念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不作为制度的构建、过失犯的认定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因果关系的认定与“角色”
(一)“角色”影响介入因素的判断
2009年5月31日18时45分,李五元驾驶摩托车载妻子上路,邓伟雄驾驶中型普通货车从后面超车,货车的右前侧与李五元左手臂相碰,摩托车倒地后,摩托车的尾部被货车的右后轮碾压,造成李召、李五元受伤,李召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治疗过程中,接受伤者的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存在医疗过失,并且向李五元等人赔偿15万元。
本案中,在既定因果流程的基础之上介入了医院的医疗事故,这就导致了在对结果能否归责于原行为人这一问题的判断上疑窦丛生。不同于一般的介入因素问题,医生对伤者不予救治的行为涉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医院对自身“角色”的违背。毫无疑问,社会一般人对于医院的期待是“救死扶伤”,这也就赋予了医院对于病人以及伤者予以救助的社会义务。例如,行为人将被害人打成重伤,被害人被他人送到医院救助,但是医生对伤者不予救助,放任其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论者认为,医生不对伤者予以救助,实际上是放任危险的自然现实化,因此,不能将结果归责于原行为人。但是,从规范的视角出发,这样的结论并不妥当。因为就医生不救治的行为而言,已然违背了社会对于医生“角色”的期待,从而阻断了原行为人与结果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医院存在重大医疗过失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不得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归责于原行为人。
例如,行为人A驾车将被害人撞成重伤,而后打B的出租车欲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救助,途中A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逃跑,B见状也害怕承担责任,将被害人弃置在路边导致其死亡。在本案中,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应当归责于B而非A,原因在于,司机这一角色决定了B具有将被害人运送至医院的、社会所期待的义务,B对于角色义务的违背决定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A。其实,从规范意义上来看,A将被害人送到B的出租车上与将被害人送到医院没有本质上的差别;B没有将被害人遗弃于路边的行为与医生不对伤者进行救治的行为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因此,对于本案,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只能归责于B,A只能成立交通肇事罪的逃逸情节,不对“致人死亡”承担责任;B成立故意杀人罪或遗弃罪。
(二)“角色”影响归责类型的选择
与存在论意义上的归责体系不同,义务犯中特殊的结果归责构造是通过义务这一规范因素进行补足的[8]。在作为犯的场合,异常的介入因素之所以会打断先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非是因为异常的因素使得因果流程发生了重大的偏离,支配流程被更强的支配力打断。但是在义务犯的场合,因为本身不存在因果流程的支配,就不会存在介入因素对支配流程的打断,义务犯为基于义务不履行的原因而承担责任[9]。正如何庆仁教授指出的,“不得伤害他人”的义务总是以行为人通过一定的媒介给他人造成伤害为标志;与之相反,义务犯中的义务与先行的组织化行为无关,是直接从外部强加给行为人的要求,期间不需要任何人、事、物的先决性条件,换言之,积极义务是一种无媒介的义务[10]。正是基于这一特点,义务犯本身不会因为介入因素而被切断与结果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在行为人具有特定社会角色的场合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此,张明楷教授指出,被害人虽然介入了不适当的行为并造成了结果,但如果该行为是依照处于优势地位的被告人的指示而实施的,应当将结果归责于被告人[11]。例如,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行为人违反枪支管理规定,私自出租、出借枪支给第三人,第三人用于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对于该结果应承担责任。从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三款将“造成严重后果”作为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之一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之所以将第三人的犯罪行为归责于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行为人,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依法配备公务用枪者这一角色就决定了对其适用义务型归责。除此以外,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丢失枪支不报罪、第一百八十七条的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等,都属于以义务为核心的结果归责类型[12]。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义务型归责”案件。2012年,被告人刘某某任企业职工退休审批领导小组成员,在工作中,黄某某主持行政审批股的日常工作,主要负责全县参保职工的退休审批,刘某某主要负责行政审批股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黄某某、刘某某作为企业职工退休审批领导小组成员,均要参加审批领导小组会议。由于二人在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对资料的审查把关不严,工作流于形式,导致沙湾煤业公司职工陈某某等14人办理假工伤提前退休手续,骗取国家社保基金124万余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案中,虽然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介入了他人严重的犯罪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本身具有“退休审批领导小组成员”这一角色,第三人的介入因素并不能阻断对行为人的归责。
因此,无论是作为先前行为还是介入因素,行为人对于自身特定“角色”的违反都会成为影响因果关系判断的重要因素,这尤其体现在偏重于规范意义的归责进程中。
三、不作为犯与“角色”
刑法中的“角色”概念与不作为犯理论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不作为犯对于作为义务来源困境中的不断求索最终催生了“义务犯”理论的诞生;另一方面,不作为犯与义务犯分别立足于存在论与规范论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进行理论构建。可以认为,在现今的刑法理论中,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标准尚未完全被弃之不用,但与此同时,规范意义上的义务犯理论对于传统理论的渗透与改造也不能视而不见。在这中间,“角色”概念在整个体系大厦的构建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存在论的视域之下,作为的义务来源发生了从形式到实质的过渡。形式的义务来源理论认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业或业务上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四类[13]。实质的作为来源理论认为作为的义务来源包括:对结果原因具有支配的情形、对法益脆弱性具有支配的情形、对危险源具有支配的情形[14]。
而在规范论者看来,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不具有实际意义,重要的是支配犯与义务犯的划界。根据雅各布斯的看法,支配犯是由于对组织领域有管辖的所有人,组织了一个犯罪。在组织领域内,基本的组织行为就是犯罪支配;与支配犯不同,义务犯是基于制度管辖的犯罪,因而具有一身专属性。
可以发现,从形式的作为义务来源分类到实质的义务来源分类,从存在意义上的不作为犯理论到规范意义上的义务犯理论,对于行为人“角色”概念的刻画正逐渐得到重视。例如,在形式的义务来源理论的框架之下,对于义务承担者与他人的关系似乎是在一个平面上进行考察的,“角色”的概念在当中无法得到体现。实质的义务来源理论开始强调行为人之所以有作为义务,是因为具有支配力,这就开始强调行为人特殊于他人的社会角色。规范论索性舍弃了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划分,强调义务犯的概念,强调行为人所处“角色”对于犯罪性质的重要影响。
事实上,传统的不作为犯理论强调作为义务、强调作为可能性,无非旨在表明不作为犯的成立需要行为人具有高于他人的优越地位,这一点在行为人具有特定角色的场合显得尤为明显。例如,根据我国的通说理论,不同于德国刑法理论,紧密生活共同体的义务不足以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15]。因此,如果作为导游的行为人与被害人签订合同去风景区漂流,在漂流筏转弯时,被害人跌入河中,行为人不具有救助的义务。这是因为,行为人的导游角色并没有赋予其特定的救助义务,或者说,相对于被害人来说,行为人在社会角色上不存在任何可以救助他人的优势地位。因此,即使此时的行为人是游泳高手,法秩序也不能因此赋予他救助被害人的义务。相反,如果游泳教练教授学员游泳的过程中,学员不慎溺水,作为游泳教练的行为人就具有救助义务。由此可见,刑法中“角色”的概念对于认定不作为犯是否成立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案件。2014年7月13日晚,驾校学员冯广新、潘某及赵某请教练员高树虎喝酒。当天23时43分,冯广新酒后无证驾驶高树虎的车,高树虎坐在副驾驶,潘某、赵某坐在后排。冯广新与小型普通客车尾随相撞,导致潘某死亡。对于本案法院指出:“受害人潘某等人作为学员请教练员高树虎吃饭、喝酒,与高树虎的教练员身份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驾校应对该事故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在笔者看来,这一立场还是十分中肯的,至少可以说,作为教练的高树虎对于被害人的死亡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应当成立相应的不作为犯罪。毫无疑问,高树虎没有达到社会一般公众对于“驾校教练”的角色预期,他不仅在学员尚未取得驾照的情况下纵容学员酒后驾车,而且将自己的车提供给学员驾驶,对于结果发生当然负有一定的责任。另外,现实中也出现过驾校学员在教练失职的情况下驾车不慎发生事故的案件[16],法院在对学员定罪的考量中必须十分慎重,因为其中教练对于角色义务的违反使得行为人的责任减轻。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也规定: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造成交通事故的,由教练员承担责任。
因此,存在论对作为、不作为进行区分,而规范论开始关注支配犯与义务犯的对立,舍弃了作为与不作为形式上的区分。即使在现今的刑法理论体系中也难以完全摒弃存在论的基本立场,但“角色”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规范论对于传统不作为犯理论体系的渗透与侵入。
四、过失犯的成立与“角色”
如前所述,刑法中的“角色”是一个客观的、一般人视角的、应然层面的概念,这就决定了“角色”一词的构造与新过失论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新过失论的产生背景是日本昭和30年到昭和40年间,随着汽车的普及,业务过失致死的数量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限制处罚范围,日本刑法学界在对过失进行界定的过程中开始在结果预见可能性之外加入了结果回避可能性的因素。对此,Welzel教授指出,“行为人由于不注意使得自己的汽车与他人相撞,对于过失而言,本质性的特征不是结果无价值,而是疏忽了社会生活上所必要的注意的行为无价值”[17],正是基于这一点,新过失论也被称为“基准行为说”[18]。
对此,野村稔教授指出,“结果回避义务是为了回避结果发生而采取外部的具体措施的义务”[19]。山口厚教授也认为,“行为的实施本身是无法禁止的,行为人以进行使行为的危险性减少的操作为前提来实施行为,成为了结果回避义务的内容”[20]。新过失论的提出对于过失结构的改造十分明显,它在旧过失论以行为人视角判断过失的标准之上加入了客观标准。
按照旧过失论,因为开车的人对于造成交通事故、人员伤亡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直接认定行为人存在过失。但是,倘若如此,就不当扩大了过失犯的成立范围。因此,新过失论在过失犯的认定过程中,不仅考察预见可能性的问题,还要考察社会对于行为人特定角色的期待。例如,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将交通肇事罪的主体限定为车辆的驾驶者。因此,从理论上说,行为人也可以成立交通肇事罪。但问题在于,在本罪的认定过程中,法秩序对车辆驾驶者和行人要求的注意义务是完全不同的。1999年,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行人横穿马路不走人行横道线,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机动车无违章,行人负全部责任。这一办法出台之时,引发了社会的热议,被称为“撞了白撞”条款。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引发反对的社会舆论,本质上是因为法秩序对于司机这一角色赋予的注意义务理应更高。
以最近热议的两个案件“追小偷致死案”和“雷洋案”为例。前者的案情是,福建省漳浦县一名黄姓男子因发现小偷后穷追不舍,导致小偷摔倒在地死亡,被漳浦县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起诉至法院。检察院指出,雨天路滑人尽皆知,追赶并拉扯他人有可能致其摔倒受伤也是常人都能预见的,行为人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21]。后者的案情是,2016年5月7日晚,派出所时任副所长邢某某带领民警孔某、辅警周某、保安员孙某某、张某某等人在抓嫖过程中因雷某试图逃跑,对其实施了用手臂围圈颈部,膝盖压制颈部、面部,摁压四肢、掌掴面部等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检察院对于被告人做出了不起诉决定[22]。
在笔者看来,两个案件虽然都是过失致人死亡的案件,但是在定性上应当有所区别。“追小偷致死案”中,行为人的角色是一般的公民。在法秩序的期待中,公民追捕小偷,尤其是为了追回自己财产的情况下,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但考虑到行为主体的角色,这种注意义务不应过高。相反,对于“雷洋案”,行为人具有警察这一特定的角色。法秩序完全可以合理期待,“警察”这一角色受到过专业训练,在执行公务的同时承担着保护对方人身安全的义务。因此,可以对于这一类特殊角色的主体课以比一般人更高的注意义务。正是因为这一点,刑法理论中对于职务行为与正当防卫两种违法阻却事由,在要求上做了一定的区分:对于公民实施正当防卫所采取的手段,法律不做任何要求,但是警察的职务行为,必须符合严格的必要性和比例性要求[23]。毫无疑问,这种差别的产生根本上还是因为“警察”这一特定角色的因素。
五、法秩序期待能力的发挥与“角色”
“角色”概念的设立表明,法秩序为法律生活中的各种典型状况设定了明确的标准,并且设置了一个平均的能力。如果行为人没有达到平均标准的要求,就会被归责。问题在于,如果行为人的个体能力高于一般标准,是否要求其要发挥出全部的能力呢?例如,一个生物系的大学生,作为临时的餐馆服务员,当他端着一盘异域菜品,发现一株有毒植物,但不动声色地端给客人,能否归责于他呢?答案是,一种特别的知识,不属于角色,不属于构造人格体的物质,因此,没有必要为了避免损害调动这种能力。因为人格体都是按照“当为”而非“能够”展开的[24]。再如,一名出租车司机,即使不小心洞悉了乘客的犯罪计划而继续运送的,也不因此构成犯罪。因为他的行为是符合社会状态的,即使他成为一种利益侵害的原因[25]。
纯粹规范论按照一般预防的社会需要来确定罪责,而不考虑行为人个体的能力[26]。因此,贯穿于一般人标准始终的正是公民对法的忠诚义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实在法规范的社会之中,我们要忠诚于社会,要信赖刑法,要善待刑罚。因为这种忠诚、信赖和善待正是我们存在着的一种证明;没有这种忠诚、信赖和善待就证明我们自身无能力存在[27]。这正是规范论对于如何应对风险社会的答案。
[1]吴情树.京特·雅科布斯的刑法思想介评[C].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法论丛[A].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71.
[2][4]何庆仁.特别认知者的刑法归责[J].中外法学,2015,(4).
[3][25][德]雅科布斯.刑法保护什么:法益还是规范适用[J].王世洲译.比较法研究,2004,(1).
[5][日]木村龟二.法学词典[M].顾肖荣等译.上海:上海翻译公司,1991.130.
[6][24][德]京特·雅各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M].冯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6,89.
[7]冯军.刑法的规范化诠释[J].法商研究,2005,(6).
[8][12]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4,135.
[9]陈文昊.假定因果关系与合义务的择一举动辩正[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6).
[10]何庆仁.义务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91.
[11][2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91,233.
[1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7-68.
[14][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9-91.
[15]周光权.刑法总论(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0.
[16]谢磊.驾校女学员疑错踩油门撞死男学员 教练不在车内[EB/OL].http://news.xinhuanet.com/ local/2013-06/05/c_124814857.htm,2013-06-05/2017-01-01.
[17][日]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49.
[18][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M].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29.
[19][日]野村稔.刑法总论[M].全理其,何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80.
[20][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第2版)[M].付立庆,刘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1.
[21]小偷致其身亡被诉,司法勿违背常理[EB/O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14/15004574_0. shtml,2016-11-14/2017-01-01.
[22]北京检方对雷洋案五名涉案警务人员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EB/OL].http://www.jiemian.com/ article/1034667.html,2016-12-25/2017-01-01.
[26][德]罗克辛.构建刑法体系的思考[J].蔡桂生译.中外法学,2010,(1).
[27]冯军.刑法的规范化诠释[J].法商研究,2005,(6).
[责任编辑 张彦华]
D914
A
1671-6701(2017)02-0059-05
2017-02-10
陈文昊(1992— ),男,江苏镇江人,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