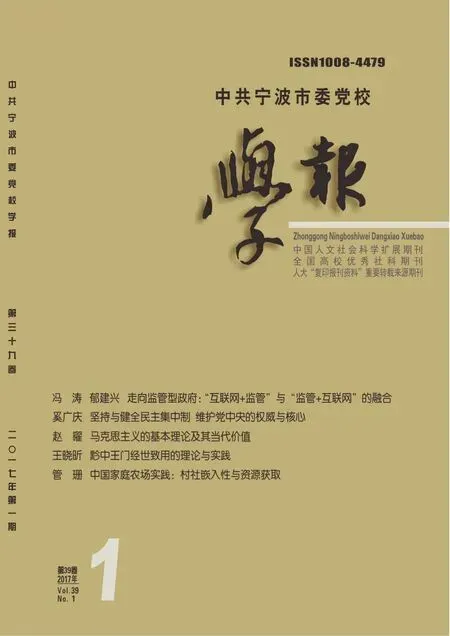黔中王门经世致用的理论与实践
王晓昕
(贵阳学院,贵州贵阳550005)
黔中王门经世致用的理论与实践
王晓昕
(贵阳学院,贵州贵阳550005)
在黔中王学的思想系统中,经世致用的理论颇具创造性,其集中表现于治世、治人、治教、治政及治心等方面,而尤其以治心为要道。孙应鳌提出了“以用世为本”的七项主张,成为其治教、治人、治心的典范之作而鼓动当时。以马廷锡、李渭、孙应鳌等“理学三先生”为代表的黔中王学的经世之实践,推动了黔中在嘉、隆、万年间掀起了一浪又一浪讲会高潮,形成了黔中王学五大重镇,遂与中原王学诸门的繁荣景象构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黔中王门;经世致用;理论实践
黔中王门诸子不仅继承和发挥先师阳明的心性之学,且对先生心性之学的致用与践行也多有阐发和亲履。在王阳明本人的思想系统中,其经世致用思想已十分丰富。从一定意义上讲,阳明的经世致用的心学思想,亦同时具有实学的性质。当初为了修正和纠偏,阳明针对程朱理学之流行而导致的“记诵词章之习”盛行的弊端而提出了一系列经世致用的思想。阳明认为,致良知与声色货利等人的物质欲望密不可分,主张考虑利害和人情以务求公私两便而提出了“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工”的思想;他肯定功利和事功,把格致诚正之说落到实处,提出了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的“体究践履,实地用功”的实学思想;他还提倡和肯定“居官临民,务在济事及物”,尤其是倡导“亲民”的治世理路,使他真正成为一位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文治武功皆备的全能大儒。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黔中诸子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黔中王门经世致用的理论
孙应鳌不仅是发挥先师阳明心性之学的大师,他对先师阳明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因子,同样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及发扬。他的经世致用之学亦可称之为地地道道的实学,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主张“行著习察,存心致知”;二是强调“励勤”;三是强调“善政不如善教”,教则以孝为先;四是提倡“革浮靡之习,振笃实之风”;五是重视“名至实归”;六是宣扬“养民之义”;七是主张“能用事为本”、“处则为名儒,出则为名臣”。
1.行著习察,存心致知
孙应鳌在《四书近语卷六》中,就如何致良知,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行不著,习不察,是不存心致知耳。”当然,他的这一经世致用思想的提出决非偶然,而是具有现实的针对性。阳明殁后,其后学各派分流,有的逾渐空疏,大讲现成良知,大言空手缚鲛龙,使先生的实实在在之“致良知”学说被凭空肢解,导致本体与功夫的决裂。孙应鳌敏锐地感觉到了当下的这一严重弊病,敏锐地察觉到有些人虽口口声声言及先生的“致良知”,实际上却完全不在行动上付诸“行”与“察”,实际上是“不存心”致良知,这样的学问实际上成了无意义的口耳之学。口耳之学导致名与实的分裂,导致本体与功夫的断裂。孙应鳌主张学问要与人伦日常之用结合起来,他说:“农夫尽力于田亩,工人尽力于()市,商贾尽力于道途。身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不能者瓦解,彼所以自食,道故然也。”农夫、工人、商贾之所以各有其名,全在于他们的“各尽其力”,各施其道,所以“道故然也”。他讲“体用合一”,“用”就是百姓伦常之日用,“用”在于民。“致良知”也好,“知行合一”也好,“慎独”也罢,其“用”皆不离于百姓伦常,不离民用。孙应鳌接着说:“大舜知矣,好问好察,惟在其用中于民。可见知者,知其所行耳。行之真切处,便是知也。”[1]他认为大舜的“知”、大舜的“问”与“察”、大舜的“行”,都是“用中于民”,才是“行之真切处”,才“便是知”。孙应鳌特别指出,知行合一之道实质上就是常行日用之道,这无疑又是他在理论上作出的又一贡献,他说:
故知行合一,而慎独之功尽,便无时无处不与此道合一,就是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学,既不外于日用,又不滞于日用,不离不囿,然后与道为一矣。[2]
可见,中庸之道即日常行之道。[3]
可见圣贤学问,只在人伦日用上做,外此皆非吾之学也。[4]
这样一来,他既克服了王学末流空疏之弊害,又恢复了传统儒家与先师阳明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他强调一定要将“行”、“察”、“日用”与实施“致良知”、“知行合一”、“慎独”等紧紧结合起来,否则就是“不存心致知”。孙应鳌垢病当下时弊,可谓一针见血。
2.“励勤”
“励勤”、“勤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也是阳明学说的重要旨归。当年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后,为弘其道,在修文建龙冈书院教育学生,提出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其中“勤学”就是极重要一条。孙应鳌在陕西教谕,在清平筑书院,时时倡导勤勉,反对疏懒。他主张:
勤则不匮,不匮则日光;不勤则惰,惰则日堕。
在对待学习问题上,他把“勤”和“速”对应起来,认为“为学莫善于能勤,莫不善于欲速”,认为“速与勤反,惟不能勤,故欲速”。
古之人自强不息,终日乾乾,修学砺行,缉熙光明,是以德崇业广,令闻垂诸无穷。[5]
“日光”即日日光明,喻示为有美好的前途。孙应鳌把勤与日光对应起来,把不勤与日堕联系起来,虽其中不无功利性之因素,且亦不失为经世之用。但他的“勤”的说法又非完全的功利性质,他反对“欲速”,“欲速则不达”,因为速是勤的对立面。凡速者,皆是不能勤,所以欲速。在他看来,勤学非一朝人日之功,务必“终日乾乾”,做到事事磨练,时时磨练。修学砺行,才有光明的前景,方能“德崇业广,令闻垂诸无穷”。
3.“善政不如善教”,教则以孝为先
孙应鳌以为,如要“道千乘之国”,总是见以仁心而行仁政,实千古王道之本也。孔子行仁政的几条要律,一为“敬事”,则此心不敢忽信,则此心不敢欺;二为“节用”,则此心不敢侈肆;三为“爱人”,则此心不敢残忍;四为“使时”,则此心不敢劳伤乎人。孙应鳌在每一条中都贯穿一个“心”的要诀,此心又只一个“敬”字,却又都该贯通了。故曰:“敬者,帝王相传之心法也。”[6]把心体之学运用于施仁政,运用于经世致用之业,是孙应鳌思想的一大特色。他同时看到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善政不如善教”的主张。其云:
“弟子入孝出弟”一节,便是蒙以养正圣功也。今日之弟子,即他日之人才。凡国家兴替、治道隆污,皆由于此。古人教弟子先孝弟,今人教弟子先学文,古今人才所以相去之远。[7]
而教育的最先行,则是“孝”的教育。人言百善孝为先,在孙应鳌看来,百教也以孝为先,今天的青少年,是将来的人才,国家兴替、治道隆污,皆由于此。孙应鳌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尤有重要之意义,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应鳌说“古人教弟子先孝弟,今人教弟子先学文”。孙应鳌实际上探讨了在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先后关系问题,他批评了当时教育上的轻德重文风气,他显然是主张德育为先,德育中,又主张以孝为先。
4.革浮靡之习,振笃实之风
其实,明中后期社会风气之浮靡,阳明先生早有察觉,他曾经把对程朱的盲目推崇、繁琐解读、空谈义理、不求创新的僵化教条学风和所谓“记诵词章之习”视为比杨、墨、释老更甚的大患。在《传习录》中,阳明痛切之:“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静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词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8]应鳌完全站在传统儒家与阳明心学的立场,视“记诵词章之习”等同于杨、墨、老、释,皆为“浮靡之习”,主张敦行儒家的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应鳌在《教秦绪言》中颇有针对性地说:“革浮靡之习,振笃实之风,务敦尚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不许务口耳之学。”[9]他提出的振笃实之风,是“崇正学”、“迪正道”,是着着实实地去行孝、行弟、行忠、有信、施礼、行义、行廉、有耻(“行己有耻”)。《教秦绪言》是他在教喻陕西时给学子门留下的训文,他开宗明义地要求学生“不许务口耳之学”,所以他的实学精神很早就已在内心有所挺立,并且主张学以致用,为天下、国家任事。他认为:“夫其养之使可用,用之以所素养,则士之以根本责效者,出而任天下国家事,斯为其术,与唐虞敷三代宾兴何异?”然而当时风气则导人于误而丢弃了根本:“今讲习诵读,但以拘挛于训诂;崇尚磨砺,尽皆胶滞乎占毕。以其词章争妍、取怜,无所不至。术陋心迷,罔自振拔。是国家期待本高且重,顾自处于卑且轻。”其导致的结果便是“所谓正学、正道,弃而费省;笃实之风,浸微浸灭;浮靡之习,浸明浸昌。”[10]在提倡正学、正道,主张笃实之风的同时,他还倡言:“机械变诈,君子所耻邪也;德慧术智,君子之所贵正也。”[11]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未来治理国家的君子,自然应视德行与学术不端为耻辱,故人品(德慧)与学术(术智)都要走正学、行正道,这才是作为君子所最为看重(贵)的。
5.“名”与“实”
孙应鳌的“实学”讨论了“位”与“名”、“名”与“实”的关系。他分析道:“位与名,是学者一生事业所在。非学则无以立乎其位,非实则无以彰乎其名。故君子求在我者,有其学、无其位,可也;有其位,无其学,患莫大矣;有其实,无其名,可也;有其名,无其实,患莫大矣。”[12]在其看来,位与学相对应,名与实相对应,彼此之间,他更看重学与实。因为在他看来,有学而无位,可以;有位而无学,则患莫大焉。有实而无名,可以;有名而无实,患莫大焉。他这种重实轻名,重学轻位的精神,实乃秉之于先是阳明,也是其注重实际、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
6.“事上之敬”于“养民之义”
孙应鳌的经世致用思想反映在于“民”的对待上,强调对“民”要发自内心,讲究一个“敬”和“义”,而不是虚以委蛇。在《四书近语卷三》中,应鳌表明了这样一种如孔孟一般的亲民态度,他说“圣人经世宰物,只是一‘义’字。”又强调一个“敬”字。他说:“事上不敬,则行己之恭为虚文;使民不义,则养民之惠为姑息。”应该说,这是一种颇具辩证思维的态度。很好地把握了度的原则,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理解。因为在他看来:“然行己恭,则事上之敬非容悦之私;养民惠,则使民之义无厉己之怨。”这完全与孔门儒道相吻合。“君子之道四,固又未始不相因也。夫子在齐,与晏平仲处者八年,平仲沮夫子尼谿之封,而夫子犹称其与人久交之善,可见圣人无我之量真同天地。”[13]事民若无“敬”,所谓事民也就是“不存心”;使民若不讲究“义”,一味宽纵,又会适得其反,走到反面,就成了姑息养奸,反倒违背了当初惠民养民的初衷。应鳌对《论语》“敬事而信,使民以时”章的诠解,真有其独出之处。这样做的又一个好处就是“务民义,远鬼神”。能够“专务民义”,就能够“去了一切免祸求福之心”[14]。
7.“能用世为本”——“处则为名儒,出则为名臣”
孙应鳌提出的经世致用理论,都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他在居官理政之时,特别强调将为学与为政统一起来,做到学以致用。他在陕西任教喻时,曾语重心长地教导学生说:“士穷居不能通五常、三王之道,审当今之要务,察安危之术,不能预有此术,徒规时好,窃取荣名,异日者仕而任官效职,苟抱尺寸,应给仓卒。是人也,其出入不远矣。本道愿诸生矢为志其学,以能用世为本。”[15]“以能用事为本”,孙应鳌把学习的目的视之为“能用事”,且将“能用事”上升到了“本”的高度。“能用事”,方能“辨黑白于掌上”,方能为“治天下之大器”,方能“处则为名儒,出则为名臣”。他在专“讲治”一条中提醒人:“一一观诸要难,而辨黑白于掌上,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是以处则为名儒,出则为名臣,视苟抱尺寸,应给仓卒者,九霄之上,九地之下矣。夫历途于远以言有车,涉津以言有航。‘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此之谓也。”[16]“处乐”与“出为”,是阳明心学系统中较早产生的思想,他在龙场悟道后,即有了这一思想[17]。孙应鳌则将这一思想发展为“处则为名儒,出则为名臣”,不仅厘清了“处”与“出”、“名”与“实”的关系,更是包涵了深刻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孙应鳌的这一系列经世致用思想,在他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在王学末流大谈性命而流于空疏的当下,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他的这些经世致用思想完全可以视为他对黔中王门在思想上的特殊贡献,也是与其他王门后学相比较而言的独特之处。
孙应鳌于陕西任提学副使期间(明嘉靖四十年辛酉(公元1561年),时应鳌35岁),写下其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教秦绪言》(又名《谕官师诸生檄文》),文中提出十六条训示(略),是其经世致用思想在他的教育教学理论中的重要反应。经世致用之学,就是实学,黔中王学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马廷锡和李渭,在这方面也有重要论述。马廷锡著《警愚录》,提倡实事实功,反对愚读死书;李渭著《先行录》,更是提倡先行其言、行在言先,反对只说不做,只知不行。
二、黔中王门经世致用的实践
经世致用不仅表现在诸多黔中王门学者的思想中,更是体现在他们的行为实践中。在明代中后期,作为农业社会的中国,在偏于一隅的黔中腹地,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乃是从事教育实践活动,这也是黔中王门学者们最为重要的经世致用的实际内容及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落实。在这方面,先师阳明堪称典范。
阳明悟道后所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传道,即传其所悟之道。他立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书院,施行教育。龙冈书院不仅是他在贵州所创办的第一所书院,也是他一生中所开办的第一所书院。他给龙冈书院立下校训,作《教条示龙场诸生》,提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教谕四条。接着他又受席书之邀,主讲于贵阳文明书院,始提出他的“知行合一”的学说。这时候,他的学生已达二三百人之众,开始形成他一生中第一个具备规模的弟子群。
王阳明在贵州不仅完成了他的思想创设,他还作出了大量经世致用之事功业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实践活动,就是从事于教育。在贵州设乡试考点,是阳明及其弟子们在教育上的一项重要努力。贵州是明代开国以来最早设立的第十三个省,贵州教育的一个短板,是直到正德年间,尚未设立乡试考点。贵州的学子欲参加乡试,须不远千里远赴云南,且名额分配极少。王阳明于黔中开教化以来,学子数量大增,若纷纷远赴滇国赶考,实在苦不堪言,为此王阳明和他的学生们,曾几番上书,请益增设贵州考点事宜。表明阳明及其后学对贵州教育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
黔中王门后学经世致用的事功实践运用于教育事业的又一突出贡献,是兴办书院和大力开展讲学活动。黔中与阳明直接关联有三所书院:一是龙场悟道后亲自创办和主持了龙冈书院,二是受席书之邀主讲于贵阳文明书院,三是离黔时讲学于镇远青龙洞紫阳书院。这不仅是明代贵州文化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由此揭开了黔中王门书院讲学运动的序幕。一百年间,贵州书院由最初屈指可数的几所,迅速增加到40多所,即每两三年左右增加一所,这是贵州史上书院讲学运动最为兴盛的时期,从此中原儒学大规模进入贵州,黔中王门举阳明心学旗帜,与其他王门学派形成遥相呼应之势,书院遂成为黔中王门与其他王门学派思想互动的重要场所。
由于阳明先生亲履之教育实践的带动,在近百年时间内,贵州先后出现了三次讲学高潮,形成了五大王学重镇。
第一次讲学高潮是由阳明在龙冈和贵阳所掀起的,阳明在黔虽不足三年,却由悟道、证道、体道、弘道而开启书院讲学活动,在为贵州播下阳明心学种子的同时,掀开了持续百年的书院讲学活动之序幕,影响了黔省的学风与民风。他在其《教条示龙场诸生》、《龙场诸生问答》等重要教育理论著作中明确提出:“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急!”龙冈书院“立志、勤学、责善、改过”可喻为四大院训,遂成为黔省书院讲学之范例。
第二次讲学高潮产生于嘉靖二十年前后,以阳明的亲炙弟子、楚中学派代表人物蒋信的到来为其标志。蒋信莅黔提学副使,复修阳明书院,举办正学书院,诸生闻风就学,不仅传播阳明心学,更是培养了大批黔中弟子,黔中王门的三位代表人物孙应鳌、马廷锡、李渭都是他的学生。加入此阶段讲学运动的还有许多王门后学名宿,如江右的徐樾、浙中的王杏、赵锦等等。孙应鳌就曾亲聆徐樾教诲,举乡试第一。蒋信讲学的盛况,“一如当年文成”。马廷锡亦曾两次拜蒋信为师,深受蒋信思想影响。
第三次讲学运动高潮形成产生于嘉靖三十五年前后,经隆庆而延续至万历年,以马廷锡返乡于贵阳城南渔矶旁建栖云亭,开讲授徒三十年为其标志。马廷锡在渔矶深入研究阳明心学的同时,还招徒授课,培养了许多王门弟子,使简陋狭小的栖云亭成为当时贵阳讲学活动的中心。渔矶湾位于贵阳城南南明河左岸,马廷锡讲学时,渔矶湾呈现出茂林修竹、渔舟唱晚、风景清幽的优美景象。当时各地许多王门后学知名学者纷至沓来,聚集观摩和参与讲学活动。嘉靖三十五年(1556),江右学人王绍元借巡抚黔省之机,亲赴渔矶观学,耳闻目睹、心领神会于马廷锡的演讲风采与致思心得,深为感动,思此地处西南边陲,尚有马氏这样的高明学者,实为难得。绍元见栖云亭狭小破败,遂建渔矶书院于原址,扩大了规模,增设主静堂、栖云精舍于其中,延马廷锡主讲书院。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绍元又上疏,称廷锡“妙契圣贤之经旨,默坐沉心,远宗伊、洛之渊源”而举荐于朝。对于绍元的推荐,廷锡有志于学,不为所动。又得四方学者,争先恐后负笈请业。有提学万士和、按察使冯成能、巡抚阮文中、布政使蔡文等,相继延请廷锡主讲贵阳文明、正学两书院。隆庆四年(1570),阳明弟子浙中学人冯成能见文明、正学两书院地址狭窄,年久失修,遂于城东新择一地,别建阳明祠,名曰“正学堂”,延马廷锡主讲其中。马廷锡贵阳讲学,前来求学者众,不仅有黔地本省的,也有不少外埠求学者;不仅有下层市民,还有相当部分地方官员。正所谓“讲诲不倦,兴起成就者甚众,成能(指按察使冯成能)复时时来会,听者常数百人。”[18]由于马廷锡的努力,贵阳复现当年阳明主讲龙冈、文明书院,蒋信主讲桃冈精舍之盛况,诚如清学者莫友芝感叹云,廷锡掀起的第三次讲学高潮,“盖阳明、道林后仅见”!
黔中王门的经世致用的事功实践,更进一步表现为王学五大重镇的形成。
由于阳明于黔中大倡书院讲学之风,历经黔中王门四代一百年(1508~1608)的大力弘扬,不仅阳明心学在贵州得以广泛传播,贵州教育文化事业也更是得以长足发展。万历年间,泰州学者罗近溪游龙场,江右王门名宿、东林党领袖邹元标谪戍都匀卫,形成了泰州、江右两大王门著名学者与黔中王门“理学三先生”同现黔省的盛况,加快了彼此间思想互动的进程。学者们相互论学,兴建书院,培育人才,阳明心学覆盖全省,黔中王门达到极盛,黔中文化教育事业也开出新的局面,出现了以贵阳、修文(龙场)、清平、思南、都匀五大王学重镇为中心的书院讲学运动,成就贵州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又一盛举。
修文(龙场)堪称第一重镇。阳明悟道之地的龙场,被视为阳明心学始基之地。嘉靖8年(1529),阳明殁后,黔中弟子和士民走祭龙场,遂使龙冈书院香火不绝终年。嘉靖18年(1539),楚中蒋信提学贵州,龙冈书院乃重修,祠田增置。嘉靖30年(1551),谢东山(时任提学副使)重修“王文成公祠”。嘉靖31年(1552),刘大直(时任贵州巡抚)赴龙场拜谒阳明遗像。嘉靖32年(1553),赵锦(时任贵州巡抚)重建龙冈书院,王阳明的黔中亲炙弟子陈文学作《何陋轩歌》。“龙冈书院”和阳明祠的薪火相传,不仅凝聚了黔中本土学者的学术向心力,同时促进了黔中王门与其他王门学派的学术交流和思想联系。修文(龙场)遂成为黔中王学第一文化重镇。
贵阳是黔中王门至为重要的文化中心,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省的精英与学子。以文明、正学、阳明三大书院为依托,黔中学人开展持续多年的讲学活动。嘉靖14年(1535),阳明私淑弟子、浙中王门王杏巡按贵州,在黔中两位同为阳明亲炙弟子的陈文学与汤哻的提议下,于城东白云庵旧址修建了阳明祠(又名阳明书院)。嘉靖18年(1539),楚中王门蒋信道林提学贵州副使,修葺阳明、文明书院,并新建“正学书院”,大力弘扬心学。尤其是马廷锡归来故里,于“栖云亭”及阳明、文明、正学三书院大兴会讲,逾30载之久,倡导私人讲学之风,直契阳明心学宗旨。隆庆5年(1571),提学万士和延请马廷锡讲学修葺一新的阳明书院,其辞云:“惟先生颜似冰壶,形如野鹤。弃荣名而修性命,脱凡近以游高明……庶几明公为众领袖,务使多士范我驰驱。”[19]至此,明代心学讲学运动在贵州,达到了“盖自阳明、道林后仅见”的又一高潮。此时的廷锡“距桃冈归里时,又三十余年”矣,贵阳书院讲学活动的同时,大批黔中王门后学弟子涌现,如汤哻的子、孙、曾孙三代,“在明三世,皆能世其家”。马廷锡及其子、孙三辈均也有功于阳明心学。贵阳汤、马两氏,堪称贵阳阳明心学世家。
第三个重镇是孙应鳌的出生地凯里清平卫(今名炉山镇)。万历五年(1577),应鳌因病告归,与蒋信的另一亲传弟子蒋见岳主讲“平旦草堂”、“学孔书院”、“山甫书院”,传播文化,在此俨然开拓出一方天地,使“远近求学者接踵而至,盛极一时”,“远近问学者履盈户”。著名的孙应鳌弟子、陕西三原人温纯,更留连于此地“沐教廿年”。万历年间,“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提学贵州,乃亲晤孙应鳌于“山甫书院”。江右王门巨儒邹元标谪戊都匀时,也专程造访,“首访李渭、孙应鳌,所至讲学必称两先生”。清平时乃苗夷之地,孙应鳌与他的弟子蒋见岳、温纯在清平的书院讲学活动,开创了以阳明文化教化苗疆之先河。据统计,明清两代,清平中进士者19人,中举者86人。清平遂成为明清两代苗疆人文荟萃之地、黔中王学之重镇。
再就是位于黔东北的思南。因有李渭晚年讲学二十载,开边地苗夷一方学风而得名。《嘉靖思南府、县志》载云:“回翔郡邑盖有廿载”,“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排释老,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习俗一归于正”[20],“远近问学者以千计”。李渭培养了王门黔东北弟子群体:李渭三子(李廷谦、李廷言、李廷鼎)、思南三罗(罗国贤、罗廷贤、罗明贤)、冉宗孔、胡学礼、萧重望、田惟安、熊时宪、安岱、李宗尧,以及江西赖嘉谟、徐云从等。他们继承李渭之业,著书立说,传教一方,如:冉宗孔“阐扬正学,继李渭而起”[21]。江西赖嘉谟“好学不倦,日夜与门人相切,后数年归,成进士,历官四川左参政”。江西徐云从“闻郡人李同野兴学黔中,负笈远从,终身不忘”。“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李渭思南讲学还波及印江、务川、铜仁等邻近府县,多地学风蔚然兴起,使王学对边远少数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
都匀作为第五个黔中王学重镇,与江右名宿邹元标和泰州学者赵大洲的到来有关。嘉靖29年(1550),泰州学派名宿赵大洲因与权相严嵩不和,被贬荔波教谕有年。稍后,广西著名学者、刑部主事张翀谪戍都匀,于都匀龙山建“龙山道院”、“鹤楼书院”,一意宣讲阳明之学[22]。万历5年(1577),江右王门巨子、东林党著名领袖邹元标因获罪张居正而谪戍都匀。元标居匀六载(1577~1583),筑茅屋讲舍以为“讲学草堂”,聚徒而讲授,黔南弟子遂云集门下。“日惟讲明王守仁良知之学”,“与匀士共相切劘”,“问学者何啻百数”。郭子章云:“阳明之学,成于龙场,尔瞻之学,定于都匀。”以都匀为中心的黔南民族地区深受影响,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黔中王门后学,如都匀“三先生”(陈尚象,余显凤、吴铤)、都匀陆氏兄弟(陆从龙、陆德龙)、麻哈艾氏兄弟(艾友芝、艾友兰、艾友芸)等。其中,陈尚象中进士,因力言建储事,削籍归,于是在都匀接续讲学20余年(1592~1613),“惟以兴起学术为事”,“不负所学,不愧师门也已”。余显凤从邹元标最久,“所得尤深”,“州人讲正学,有科名,并自巩县(余显凤)起”。吴铤于邹元标离开都匀后,也“毅然以师道自任”。为表彰邹元标的传教之功,众弟子建都匀“南皋书院”。至此,黔中王门“经世致用”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明清时期黔南民族地区文化的兴起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亦为贵州全省的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
[2]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
[3]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
[4]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三。
[5]孙应鳌:《教秦绪言》。
[6]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
[7]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
[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第230~231页。
[9]孙应鳌:《孙应鳌文集》第320~321页。
[10]孙应鳌《教秦绪言》,《孙应鳌文集》第321页。
[11]孙应鳌:《四书近语》卷六。
[12]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三》,《孙应鳌文集》第203页。
[13]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三》,《孙应鳌文集》第208页。
[14]同上,第218页。
[15]孙应鳌:《教秦绪言》,《孙应鳌文集》第331~332页。
[16]同上,第332页。
[17]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年(1508)即作有《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一文,其中有“君子之道,出与处而已。其出也有所为,其处也有所乐”一语,是其在心学理论构建初期,经世致用思想的较早流露。见《王文成公全书》第999~100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6月版,王晓昕等点校。
[18]冯成能:《重建阳明书院会记》,载《万历贵州通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郭子章:《黔记》卷四十五《乡贤列传二·理学传》
[20]《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思南县编办2002年3月。
[21]李渭:《婺川县迁学记》。见万历《贵州通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2]有学者戏言,黔中文化乃为贬谪文化,其云虽属一番史实,然既不入耳,亦不准确。确切地说,黔中文化受大量中原被贬士人的影响和参与,不乏积极之因素,然从整体上讲,黔中文化自有其独立鲜明之特色。
责任编辑:郭美星
B248.99
A
1008-4479(2017)01-0039-07
2016-12-12
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黔中王门及其思想研究”(10BZX035)的阶段性成果。
王晓昕,贵阳学院教授,贵州省阳明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