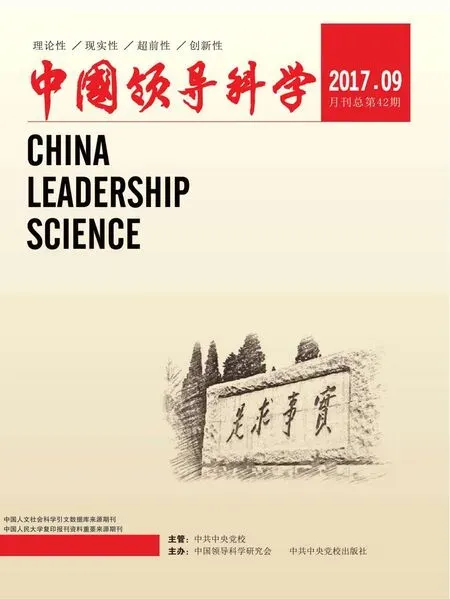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批判
◎张 竑
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批判
◎张 竑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侵扰和干涉,企图动摇我国人民的信念。本文通过分析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的非历史来源、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自身的逻辑错误和西方自由主义自身的不合理性三个角度,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观点进行批判。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性批判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利用各种媒介渠道,不断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侵扰和干涉,企图用思想武器动摇我国人民的信念,阻挠我国的发展。他们的这些做法,体现了文化霸权主义和话语霸权主义,根源于冷战思维的残余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固执。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和驳斥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观点,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和神圣使命。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观点进行批判。
一、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的非历史来源
西方自由主义号称个人自由的“普遍性”来自何处?西方学者的答案通常是给出一种先验的回答或者逻辑的假定。比如“天赋人权说”、“神意说”、“人性说”、“理性说”、“先验说”、“经验传统说”等等,以“天赋人权说”为例来进行理论反驳,其他假说的性质可与此类似。今天距离“天赋人权说”提出已有200多年,当我们冷静地审视这套理论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不仅实践效果有明显的局限性,而且理论本身也有明显的脆弱性。
从实践的角度看,“天赋人权说”仅在法国和美国取得了效果: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理想设计是通过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封建制并建立了共和国;美国的杰弗逊把“天赋人权”写进《独立宣言》。在英国,霍布斯和洛克的相关理论不是事前的启蒙,恰恰相反,是事后的总结。当19世纪的戴雪以及20世纪的哈耶克在分析英格兰法治的时候,二人都认为英国的法治是源于英国人的民族本性,而并非源于启蒙学者的思想。在德国,几乎从未真正信仰过“天赋人权说”。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几百年奋斗历程中,“天赋人权”仅仅是政治理想的口号。
从理论的角度看,“天赋人权说”自19世纪开始就一直饱受抨击。因为这种假说根本就是凭空而造出的,没有历史和哲学的根源。被黑格尔视为“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积极狂热”,被边沁称之为“修辞上的胡闹”,被梅因称之为“纯粹理论的信条”,终被马克思用唯物史观进行了批判和取代。马克思认为,权利并非每个人生而有之,是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决定了权利的内容和范围。肯尼迪的法律政治学揭示了“天赋人权说”的内在矛盾性,即人们永远都在利己与利他、个人与社群之间无所适从,而“天赋人权说”并没有给人们肯定和明确的价值判断。欧洲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人类永远是在权力和训诫下挣扎,“天赋人权说”只不过是以文明的压迫代替了野蛮的压迫。
可见,“天赋人权说”具有非历史性,人权不是天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是由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必须让位于新的生产关系时,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使人们头脑中产生了对于人权这个概念新的意识、新的理解和新的规定,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新的意识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借口是“天”赋予了这种人权的规定性,凭借这一学说妄图冲破旧势力对生产力发展的阻挠。同样,“神意说”、“人性说”、“理性说”也是如此,都是凭空捏造一个非历史性的学说来试图解释历史、冲破障碍。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在人的头脑中重新定义了人们对人权的理解,由于这种理解不是在一个人或一代人之中完成的,而是具有历史继承性动态地发生着改变,所以人们以为这种意识是在头脑中先验存在着的,于是康德提出了“先验论”,其实恰恰相反,先验的错觉来源于人们经验的不断改变。哈耶克的“经验传统”说认为“个人自由”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由传统演化、逐渐形成的。但他所说的传统,只是指近百年的现代社会发展传统,并不是指从人类一开始就存在至今的传统。
西方学者的众多答案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历史性,仅仅依靠主观的臆断或抽象的想象,企图赋予自由主义“普遍性”一个合法的来源,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唯心史观的表现。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仅是西方物质生产活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暂时性产物,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条件的社会或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非要说是普遍性的话那也仅是有限度的普遍性,而不是所有社会或国家都普遍适用或者同时适用的。西方自由主义“普遍性”的来源,如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观念所说的那样:“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二、西方自由主义“普遍性”的逻辑错误
西方的自由主义突出强调个人具有选择的权利,属于个人的私人事务。比如,有关信仰、情感、性爱、婚姻、嗜好、兴趣、思想、学说等等方面,“不强加于人”是基本原则,无论是以国家、政府、社会、团体、舆论、宗教的名义都不可以强加于人。[2]这正是西方所谓“自由”的要义所在。按照这种逻辑,西方自由主义应该允许反对自由主义的其他主义、信仰、思想和学说的发表和发展的权利,这才能体现出自由主义的“自由”要义,而政治家、政府、法律一般不能干预这种自由。那为什么西方国家热衷于对我国人民的自由选择指手画脚呢?这不正说明他们所谓的自由主义根本就不自由吗?
西方自由主义者以我国人民的选择是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为借口,质疑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他们认为我国人民是被中国共产党强迫做出自己选择的,以救世主的心态来对待中国人民,并以此借口来干涉我国内政,甚至颠覆我国的政权。这种强盗逻辑不是现在就有的,早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就已存在了。西方以臆想和偏见为基础,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捏造我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伪现状,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为悬设,赋予西方以“神圣使命”来解救中国人民,打造所谓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系。这是明显的强盗逻辑。他们不以事实为根据,不以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为根据,仅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不择手段地丑化中国共产党、丑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其心何其毒也。
西方的做法有两方面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是带有冷战思维的残余,心底里仇视社会主义中国、敌视社会主义阵营,以不消灭社会主义就会被社会主义所消灭这种僵化固执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没有辩证地看到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现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每个国家、各国人民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力,人民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和政治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不容他国干涉和阻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家间交往的底线原则。
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忌惮中国的高速发展,忌惮中国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凝聚力。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以为中国强大起来就会像西方国家尤其是像美国那样,搞极权主义和霸权主义,他们不了解中国人民的处世原则与中国所特有的发展理念。与西方传统游猎民族的处世原则和生存理念截然不同,发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西方以征服、掠夺为原则,中华民族以和睦、安居为原则,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人更能理解为什么西方人骨子里会对中国有如此强盗逻辑。
三、西方自由主义自身的不合理性导致其不具有“普遍性”
西方学者在用自由主义的“普遍性”指责我国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谓的自由主义自身具有不合理性。在北美和西欧,自由主义的充分发展实际上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西方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突出表现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积极地或者消极地参与政治选举活动,这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多数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于政治活动非常消极甚至干脆不参与。普通民众对政治很冷淡,多以娱乐节目的心态看待政治选举活动,所以总统、议员的得票率常常极低。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冷淡态度导致民主选举活动被各种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所操控,带来的结果是对大多数人的不利。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就是典型事例,选举结果出来后,美国的中产阶级(现今美国人数最多的阶级)椎心泣血,整个精英阶层大跌眼镜,这就是典型被操控的结果,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力量必然导致资本与政治的结合,只有这样,资本才能获得更大的力量,获取更多的收益;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并不是好事,资本的力量越强大,民众的力量越弱小。以致于出现西方“倡导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似乎反而使大多数人可能在政治上处于无能为力的不自由状态。”[3]
西方自由主义在文化精神领域,突出表现为社会变成了个人原子化的社会,即人与人之间日益孤立分离,人际冷漠、人情淡薄、精神空虚、心理躁动。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发现自己的人生没有目的、身处的世界没有意义、生活没有价值,于是吸毒、暴力和性放纵泛滥成灾;西方的“新闻自由”提倡多元和多样,但实际上变成了在媒体的控制下的不自由,多元和多样变成了一元化和同质化;西方自由主义提倡启蒙精神,事实上变成了愚民精神;西方自由主义倡导理性至上,现如今理性变成了反理性的有效工具,个体的自由自主被异化、被商品化,变成了对个人从心灵到生活全方位的枷锁和奴役。
正是因为西方自由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弱点和缺陷,导致如今各种宗教的复兴,西方学者和民众开始反思和质疑这种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一个自身不合理的理论却要把它“普遍化”,就意味着故意把有众多弱点和缺陷的自由主义硬说成是普遍的真理。他们硬要把不合理的“真理”强塞给中国,非要中国尝尝这种歪理的苦果,背后的居心,不正是唯恐中国不乱的阴谋吗?
面对西方国家以自由主义“普遍性”为代表的伪真理输出活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高度警醒,积极运用理论武器和现实依据批判这种伪真理、伪命题,自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促进人民群众对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辨别力的提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7页。
[2][3]李泽厚:《哲学纲要》,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1页;第32页。
责任编辑:王鹏凯
D091
A
2095―7270(2017)09―0039―03
(本文作者: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机关党委宣传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