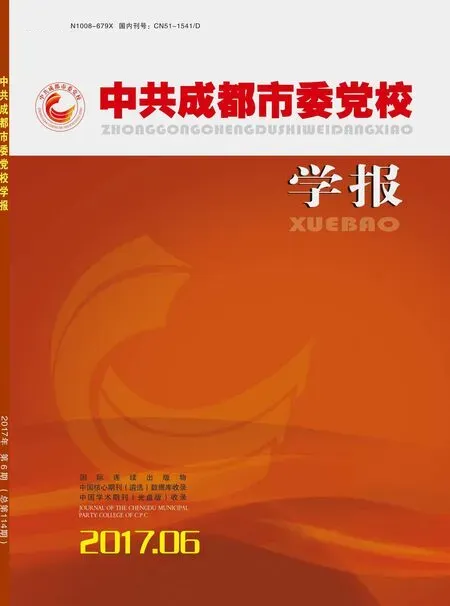新政治生态下领导干部的心理边界问题探讨
■
人们对边界问题的关注首先是基于组织管理的结构架构与功能设计,从边界的属性认识,边界划分表现为一种规则和规定的物理界限,实质上体现了组织内部间的控制关系;从群间关系和社会特征理论认识,个体在依附组织时,会对组织产生较强的同一性意识[1],并因而对组织产生高度认同,这种认同构成了群间比较的社会边界,在人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情绪情感及个性差异等方面产生影响,最终归结于个体理解和把握外部关系距离和秩序遵守的心理边界。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寻求一种组织内外和成员之间的分类和比较时,心理边界作为人的心理因素介入于组织管理和组织变革中,必然产生信念、态度、感受和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和界限,形成个体独特的心理属性。当前新政治生态带来了工作环境和工作要求的大变化,领导方式方法与惯用路径也大相径庭,基于目的动机、权利与义务、责任的感知和价值比较,都会促使领导干部表现出不同的心理边界,并进而形成新的领导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新政治生态催生了新的心理边界,表明领导干部一种新的心理控制体系的环境适应,是否能应和领导工作的积极主动性还是趋于心理防御和保守,这必将最终影响领导效能的发挥,因此研究领导干部心理边界的动态变化性,是与领导干部的信念、工作精神状态和行为密切相关,反映的是个人心理位置调整和时代要求。
一、领导干部心理边界构成的独特心理属性
心理边界作为人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是个体与组织内外环境交互影响中心理区分、行为控制的自我表现。领导干部由于其独特的社会角色扮演,其心理边界无论从个体方面还是从群体类分上认识,都表现出独有的心理属性。
(一)政治社会化取向明显
政治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不能脱离开社会关系而存在,同样的,人也不能脱离开一定的政治关系而存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总是与特定的政治关系相关联,确立特定的政治价值判断标准,扮演一定的社会政治角色,表达各种政治观点,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态度并付诸于政治行为之中,这些都是一个人政治社会化的演进过程。心理边界一方面反映出这种社会化的结果,一方面又作为一种控制界限对人的政治社会化取向产生影响,因此人的心理边界的确立包含政治社会化的内容。但由于人所处的情景及人际比较时选取的维度不同,通过自我分类建立起的人际、群际间感情和价值意义的区分及认同感不同[2]。相比较一般社会人,领导干部更重视自身政治社会化中的角色扮演,政治认知更强,政治信念更突出,对外部政治环境变化和政治评价更敏感,而建立于政治信念、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基础上的政治性格又决定和影响着政治行为方式,这一切成为领导干部心理边界建立的前提和出发点,也使领导干部的心理边界更带有政治化色彩。虽然人们更期望归依于高声望、高社会地位的群体原型并自觉遵循群体规范,以此达到对自我积极评价、增强自尊和社会影响,但领导干部自我概念的确立和自我分类可能更多从政治情景出发,而不仅限于一般社会人的认知模式、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惯势的范围界限。新政治生态实际上带来的是政治社会化的环境变化,作为一种开放系统,个体自组织与环境之间虽然存在着边界划分,但更需要与这种政治环境保持动态的联系,领导干部作为自组织系统,其原来固有的心理边界因环境变化适时做出调整和重新构建,在凸显政治社会化时将会更多因应时代政治的要求,从自我定位和新的价值观、信念确立达成新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归类。
(二)权力动机突出
权力动机理论指出,人们有一种影响和控制他人的愿望和驱动力,这构成了人的权力动机,无论是主动谋求权力还是害怕失去权力,权力动机的本质都在于强化对秩序的遵守和控制功能。从对边界的属性认识,边界具有限制和授权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确定不能做什么,一方面又确定能够做什么,既表现为一种规则和制度,又体现为一种对秩序遵循的社会关系,心理边界无形中是在人的意识、情感、价值判断以及行为倾向等心理活动中生成的的判断标准,本质上展现的是一种控制和调整功能。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竭力谋求更高领导职位或“组织中的权力”是诸多领导行为的出发点,也是一种领导工作价值取向,权力所表现出的限制和授权功能恰恰又成为确定这种领导价值的边界标准,高权力能够带来更强、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既体现了领导价值,同时也反映出领导心理边界。为满足个人私利,或更加追求个人化权力;为满足才干、人格、地位、声望等对他人的影响,或更加追求一种社会化权力[3]。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旧有政治生态影响下,追求权力既是一种行为动力,又变成了工作绩效的评判标准。通常情况下,权力需要与领导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几乎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有高权力需要的动机追求,他们希望通过控制环境和他人来展示自己的优越感和影响力,而这种权力动机也成为领导干部心理边界的构成要素和独有心理属性,权力追求和获得成为最重要的领导价值取向,权力的心理界限成为激发领导行为动力源泉的标准线。新政治生态下,虽然政治环境和权力运行机制已经发生变化,但权力作为政治环境构成部分,如何看待当前的权力影响,如何使用权力来体现领导价值,是作为政治主体的每一个领导干部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新旧政治生态不同,领导干部对待权力的心理界限理应不同,领导干部实现领导价值的权力动机追求是不能忽视的,但过分把权力追求作为领导行为的至高目标和标准也是与新政治生态环境格格不入的。
(三)成就感取向强烈
获得成功和感到有能力的愿望既是一种人格完善过程,也是影响人的行为活动的驱动力,高成就需求者总喜欢设立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并愿意为实现目标而付出积极努力,在伴有兴奋、惊讶、好奇与探索等情感体验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这构成了自我概念的基础,亦成为心理边界建立的前提条件。自我越是能够赢得社会赞许而不断寻求个人成就突破,个人越是能够通过成就提升而不断强化自我概念,从而达到更高程度的自我肯定,从心理边界确立起高成就满足感的自我。相对于社会其他人群看重经济地位的物质自我,领导干部更期望通过“政绩”追求优越与完美,更加关注如名誉、地位、控制与成就等精神上的自我,不仅内心存在强烈的成就体验和积极主观评价,而且期望社会他人评价与自身知觉相一致。由于领导干部拥有权力和社会支配的权威性影响,在名誉、地位及控制上表现出更高的优越感,在成就感上表现出更高的社会期望,由此在心理边界划分上,也更看重个人成就的社会评价和认可问题,成就感成为领导干部心理边界确立的突出心理属性。新政治生态下,政治环境变化催生了领导“政绩”新的内涵,领导干部要积极有所“为”,才能实现个人价值和成就感,但“有为”不是“政治秀”和做表面文章,领导干部应敢于担当,真正从社会发展需要去做,才能够树立起正确的成就观,才能确立起客观、正向的心理边界。
(四)权威感取向敏感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个体关系和组织维系离不开各种权威的影响,从传统家长制向法理型转变,人们习惯于接受权威和服从权威,在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种秩序关系。心理边界作为人的一种心理防线,是使自身与别人保持一种恰当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表现为对秩序的遵守和从对方赢得尊重,因此距离和秩序构成了心理边界的主要形式。基于信任、自主性和互赖性的心理倾向需要权威的影响[4],人的心理边界的建立和维护也需要权威的支撑,只是由于每个人支配和控制别人倾向的强弱不同,而使这种权威感存在着个体差异。通过对别人“发号施令”,对别人施加影响,从而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获得某种权威。高权威者不仅希望依靠权力增强自己的权威性,而且希望依靠出色的成绩获取权威,所以当权威影响由法理和规制向个人能力、才干、经验和人格等要素转变时,人们更愿意自觉接受魅力型的权威。对于中国人而言,无论是从家庭环境或是在某种组织制度背景下,人们总是表现出一种权威敏感和权威依赖,习惯于权威影响下的辈分、年龄、职位及权力等级别划分,由此形成一种无条件的权威崇拜,而权威无形中在人际和群际关系中树起了一堵“围墙”,在物理距离上表现出明显的上下关系之分,在情感距离表现为上下等级的命令与服从,这自然在制度规范和心理影响上确立了一种边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权威感在确定人际秩序关系上比其他社会类群都更加重要,无论从传统观念还是从当代权力运作机制上认识,权威感所带来的地位、名誉、声望和控制的心理优势就是凸显的领导者心理边界,权威树立既是一种权力、等级的外显,同时也是心理边界标准划分。看重等级,重视名誉,计较规范遵守,敏感于他人的意见、褒贬和批评,这种在周围所划定的权威心理边界较一般人更加凸显和敏感,是不能碰及和破坏的,领导干部也更愿意通过权威心理边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体现秩序关系,获得下属尊重。
二、新政治生态下领导干部的心理边界构成
人的心理结构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心理边界作为人心理结构的外在“隔离带”也会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领导干部的心理边界更容易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新政治生态下,领导干部心理边界构成必然会随着这种政治生态变化而加以改变。
(一)领导干部自我概念构成了人的心理边界的基石
自我概念来自于自我观念、自我意象、自我意识及自我评价,通过自我概念的界定,人们能够确定“我是谁”及与他人的差别,无论对自我是否客观、准确的知觉判断和主观评价,自我概念的确立就如同一种“边界划定”使人与人之间保持了一种稳定的秩序化关系,表现在人知、情、意的心理边界区别上,因此一个人自我概念的界定越明确,越能建立清晰的心理界限感。无论早期的自我理论还是后现代研究,自我概念的建立都是取自于个体对自身特点的主观知觉和评价,而从个体期望获得尊重出发,这种评价大多取向于对自我的更多肯定,所以自我概念的建立更带有主观性。在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各因素影响下,人们往往更多关注精神自我,诸如身份、地位、名誉、成就等成为自我概念构成最重要的内容,从而也成为个人心理边界划定的主要依据和标准,个体差异和社会分类往往取决于这种标准。人本主义重视自我实现中的理想自我,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通过“自我卷入”,人们更希望通过“公我”赢得“有意义他人”的评价,实现对“私我”的肯定,所以个体主义的“自足性自我”是与这个时代主流相背逆的,强调个人控制和排他性的自我概念虽然使心理边界可能更加清晰坚实,但没有包容、缺乏责任的价值取向,只能使自我封闭和走向狭隘[5]。通常情况下,领导干部自我概念构成更重视来自于身份、地位、名誉、权威控制等方面的优越感,并由这种优越感而产生能力、自我效能的中心主义。新政治生态强调制度、规范和责任,确立什么样的自我概念,这既是一个领导价值问题,也是一个自我定位问题,如何看待政绩与能力,如何看待利益与权力,这是确立领导干部自我概念的实质,也是划定领导干部心理边界的焦点。一些干部把突出形象政绩看作是自身能力使然,把权威服从看作自我肯定,把利益诱惑看作成就回报,脱离群众和工作实际;在权力面前往往不能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在利益面前往往迷失自我,所导致的往往是自我概念模糊、心理边界不清。
(二)角色认同成为领导干部心理边界划定的载体
从社会心理学理解,角色存在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人的社会地位、身份不同,与之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就不同,从而决定了一个人社会角色不同。角色认同既是一种角色期待,也是一种角色定位,其实质就是对于一个人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社会期望。受制于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角色认同更多体现出对角色的基本规范的遵循,只有按照此规范去做,才能满足对自身角色规定一致性的社会期望,因此角色认同具有制约、控制和规范个体行为的规范功能,能够使得个体更好的与他人区别开来[6]。从这方面认识,无形中角色认同在社会互动关系中划起了一定的边界,凡是角色越明确并符合社会期望,越能得到社会认可,个人越能准确地把握好自己的角色,明确自身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反之,角色混乱将导致这种权利与义务界限混乱,从而导致心理边界混乱,心理边界混乱反过来会加重角色混乱甚至导致角色冲突。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角色认同首先体现在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认同,这既是领导干部应遵循的角色规范,也是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心理边界。“角色模糊”、“角色偏移”及“角色错位”表面上是一种角色意识缺失,实质上是由于个人对与自己特定身份相一致的权力、义务的认知偏差造成的,领导干部没有责任感、使命感,就是突破了自己应有的角色规范要求,“公权力”变“私权利就是突破了党性原则和政治觉悟的心理低线,把自己混同为一般社会人。新政治生态下,领导干部要明晰自己的心理界限,就需要保持个人与社会在自我角色期望上的一致性,特别需要强化党员的角色意识,通过党性修养和以身作则,达到领导干部角色的高度认同。
(三)人格要素构成了心理边界的指向性
人格作为因应和调节外部环境的人的身心系统,首先是具有激发和唤起个体内在力量的动力特点,个体应对一定情景刺激时行为反应的度不同,表明在动力特点上存在着人格差异性;而从人的心理倾向性上看,人格在人的认知、情绪、意志、价值取向及态度等方面也表现出个体差异的心理特征。当一个人的人格不断融进社会文化因素时,会在人的生理、心理及具有社会意义的内在特征上形成完整、统一的人格结构,所以人格构建既离不开一定个人特质的作用,也离不开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心理边界的形成恰恰受制于这种人格特质的差异性影响。人格特质不同,表现在人的知、情、意等方面的心理特征不同,而反映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的心理界限就不同。研究发现,一些人格特质成为心理边界建立的指标,如自尊心强的人相对于自尊心弱的人更不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他们不会为获得积极的评价而一味取悦别人;相反,他们总是注重与别人保持适当的情感距离,心理边界是明晰的;如高自我监控者对环境变化更能表现出高的敏感性和强的适应性,性情和态度表达更具有心理尺度感,不同情境采取不同行为,心理边界清楚。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人格要素既表现出领导能力、领导性格方面的差异,更表现出人性化的道德尺度把握,这也构成了领导干部心理边界划定的标准。同样的工作,是否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优良的品德和高尚情操,是否能亲民爱民、公平廉政、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这些都体现出领导干部人格中的道德尺度问题,而这也成为领导干部心理边界划定的重要标准。新政治生态带来领导环境的变化,环境塑造人格,领导干部不能因人格差异性而无视政治环境变化的新要求;相反的,更应该通过强化自我监控、提升人格素养来凝聚人心,发挥人格的正能量。
(四)分类和社会比较构成心理边界的运行机制
从群体角度认识心理边界,人们总习惯于人际、群际间的分类和比较,以此使个体与他人区别开来,通过保持人际间的距离,维护一种控制功能和秩序关系的存在。当人们试图把自己归类为某个群体时,总是寻求与内群体原型更多的相似性;而当人们试图把自己与某个群体相区分开时,总是寻求与外群体更多的差异性。群体压力和群体规范使得一个人可能在群体里更多采取他人取向,如顺从他人、关注规范、重视名誉;而通过与外群体的积极区分,能够获得更多自尊体验和优越感。心理边界建立来自于这种关系互动的分类和比较,并由心理边界的界定反过来不断强化这种分类和比较。领导干部对内群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来自于领导者身份、地位、名誉、权利等社会表征的差别并由此带来的尊重体验和优越感,这使得领导干部愿意与外群体进行积极的区分并凌驾于一般人之上,所形成的心理边界更趋于封闭而显示出它的不可渗透性。事实上新政治生态所带来的从政环境的变化是体现为政风、党风、民风的改变,它要求领导干部要有更多的责任担当而不是一眼看着权利,要求遵循党内的制度、规矩、纪律而不是与群众隔离于组织之外,融进组织这个内群体但不是高高在上,理应在心理边界确立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三、新政治生态下领导干部心理边界的构建路径
每个人都有心理边界,它决定了一个人在与环境互动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个体差异和环境变化决定了一个人心理边界的动态变化,新政治生态带来的是领导干部从政环境的变化,也必然带来自身心理边界的变化,重塑心理边界是因应环境变化的需要。
(一)领导干部要增强“边界意识”
边界意识实际上就是规则意识,人没有边界意识,社会就会处于无序状态;为官者如果没有边界意识,就会越界与社会与市场争权争利,催生各种腐败[7]。增强“边界意识”,首要的是面对规则要有敬畏之心,只有敬畏百姓、敬畏组织、敬畏国家法纪,才能把握好政治方向、确立政治立场。但仅有敬畏之心还不够,要使自己言论、行动与领导工作的要求相一致,还需要强化规矩意识,行为上要遵规矩、守纪律,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才能真正做到心里有“界”和有“戒”。
(二)从人际心理边界评估中把握好心理边界的度
拥有权利和支配优势使得领导干部每天面临各种诱惑和复杂关系的处理,要坚持党性和把守好政治关,就必须把握好心理边界的“度“,要有高的人际敏感度和人际洞察力,既不做边界感弱的人,往往把自我与环境混为一团,也不做心理边界极强的人,排斥或拒绝一切,保持人际距离、留有个人空间领域,“度”的把握关键在于把党性原则与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有机结合起来,无论面对怎样的关系处理,都不能突破党性原则的边界。
(三)由正确对待自我到加强自爱
一个自我界限清晰的人永远知道自己的责任权利范围,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正确对待自我就是如何客观、正确的看待权力和责任的问题。权力如同“多棱镜”,能放大人的优点、掩盖人的缺点,使自我迷失;权力又如同“变焦镜”,权力扩张和利益可诱惑性往往使人忘乎所以,混淆自我与他人界线,混淆公与私界限。尽责用权,权力与责任应是对等的,有权必有责;领导干部正确对待自我,首要的是认清身上的责任而不是关心权力大小,从责任出发而不是从权力出发,才能把握好关系分寸、做事分寸,做到心理有“边”有“界”。因此,领导干部在权力和责任面前应保持一颗“谦虚”的心,学会自爱。
(四)领导干部应构建健康的人格
人格是构成心理边界的重要要素,健康的人格既不是施以绝对的控制,也不是无条件的服从和权威依赖,独立的人格体现高的自尊,而自尊程度越高,也表明一个人的心理边界就越清晰和稳定。构成领导干部人格的自尊不应来自权威崇拜和权威依赖,而应看真正为社会做了什么,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越大,赢得的社会尊重越高,获得的人格自尊感越强。所以,健康的人格归根到底来自于人的道德取向,领导干部只有不断提升高尚的人格魅力,才能凝聚人心;只有不断加强学习和道德修养,才能构建健康人格,形成健康的心理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