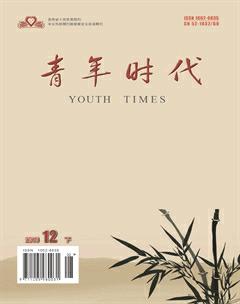试论电影《燕尾蝶》的主题现代性
黄菲蒂+陈相
摘 要:影片《燕尾蝶》的现代性主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隐含其中的日本民族文化属性,一为包裹着西方现代思潮的现代文化反思。文章着力从对这两方面的发掘与解读作品,从文化角度阐释作品主题。
关键词:主题;现代性;民族文化
一、日本民族文化属性的影像化呈现
电影总是带有某一民族文化符号特征的,日本电影的民族文化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电影大师传承下来的。新出道的导演在向前辈致敬的同时也在模仿着前辈的创作理念,这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也是一种创作上的学习和更新。日本新电影的转折大约在1989年,北野武的导演处女作《凶暴的男人》可看作是一个代表作品。此后,一系列成就较高的电影有竹中直人的《无能的人》、周防正行的《谈谈情,跳跳舞》,直到1997年北野武的《花火》将日本新电影运动推向高峰,该影片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认可。
在这样的背景下,岩井俊二开始以自己的电影语言记录日本青年人的生存状态。 “任何一个年代都不会没有描写青春和年轻人的作品,这类电影的内容、风格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变化的,它最敏锐的捕捉着时代的气息反映着时代的气氛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存状态”。[1]电影所关切的正是现时社会人生所迫切需要被重视的问题,这与其他文学艺术的现实关怀是一致的,立足于民族文化,寻找问题的由来和解答,是这一时期日本电影导演共同的艺术追求。
日本孤立大洋之中,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繁。在紧张而压抑的环境里,日本人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从日本传统的武士道文化来看,日本人的性格有很极端的一面,坚忍、顽强、尚武、决绝、残酷、冷漠等成为性格中相生又相悖的特点;然而他们文化里也有“雪月花时最怀友”这中温和的茶道文化,温和、宁静、简洁、深挚,寂然,对心灵的关怀细致入微。概况起来就是有论者说的“菊花与刀”二者的结合。岩井俊二的电影也根植于这样一种极端而又温情的文化之中。《燕尾蝶》中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大都市“元都”,元都可看成是东京边缘一面的放大,虚构的故事里充满着极大的现实感,或者说导演在有意淡化某些客观的真实,是未来创造更加纯粹的本质真实,在现实里创造着人生和人性的寓言,这样的故事总是充满着扣人心弦的感染力。故事讲述的是在某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住着一群为生存而抗争的人,从对这群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中能够感受到导演是怀着极大的同情,甚至尊重来讲述他们的故事的,他们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有着善良的一面,但他们的生存方式又是极端的甚至充满罪恶的,出卖肉体、吸毒、造假钞,可谓无恶不作。是什么样的现实让他们生存如此艰难不堪,他们的心灵世界经历过怎样的挣扎和痛苦,在这样极端的矛盾之下所展现出来的灵魂状态,反而是更加真实,也更能引人深思的。在残酷和人性堕落的背后,并不是意味着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或者说他们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来找寻人性的一种美好。固力果用她微弱的力量保护了失去母亲没有任何依靠的凤蝶,当她在人群之中唱着《南海姑娘》,所有人静静的听着的时候,观众看到的是柔软而真诚的人性之善。当再次面对生活时,这样的幸福感会让人愿意怀抱着希望,微笑着去面对生活,尽管生活那样艰难,尽管灵魂的美好可能只是那一刻的闪现。这与日本文化里两种极端的特点是相符合的。
此外,《燕尾蝶》中对情感和欲望的表达都印下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特征。“日本人倾向于承认人类自然的欲望和感情,而且坦诚直率,不借重伦理的伪饰。日本人不认为欲望和情感有损于人的道德品格,而感官的享乐和人生情爱的体味也不必然是道德堕落的情由”。[2]《燕尾蝶》中对这样的一种天性也是肯定的,甚至将对金钱的执着看做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执着而非罪恶,毕竟每一个人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每一个人都至少要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或许给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们提示了一种更轻松也更合乎情理的生存态度,为自己争取正当的生存资源是合理的,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内心,并在此基础之上来确认自己的生存价值。只是,当一个个体的价值不是用精神的高度,灵魂的净度来衡量,而是用金钱和情欲的满足来确认时,人性里高尚的道德情操被挤压殆尽,这多少是有些悲哀的。
二、影像世界中的现代文化属性
“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它产生于基督教的中世纪”。[3]当波德莱尔说现代性就在于对现时、对现时之现实性的一种独特感觉时,他是对的,而且不仅仅是在美学上。在波德莱尔看来,这种感觉不可能通过模仿古代大师们学到,人们只能靠自己去获得,靠自己感觉的敏锐性去捕捉。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不是相对于古代而言的现代,而是指示这一种最趋近于时代的文化特质,现代性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传统文化相互渗透。新电影的现代性一方面是指电影主题聚焦于现实题材,用以反映现实,结果则体现对现实的关怀,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对特定文化区域文化类型的指涉。
二战之后,日本曾受到美国长时间的占领,其经济、文化、思想意识也因此受到美国价值观的直接影响,日本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受到极大冲击,人们对此丧失了信心,并因此变得迷惑而抵触。国民的价值取向从对国家、天皇的忠诚和信任转向了企业等获得现实物质的场所,从禁欲主义走向了肯定物质欲望和性意识的解放。这样的转变必然导致人心动荡,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危险的,思想意识领域的工作者们意识到并警惕着这些情形的出现,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电影必然成为电影工作者发声的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思考未来的电影提供了发展机遇。日本电影在这段时间迎来了一段繁荣的时期,黑泽明、沟口健二等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就是这时间的代表人物。这段时期的日本电影既融入了西欧的现代思潮,也有着对日本本民族文化的深刻依恋和反思。如黑泽明的《七武士》、《影子武士》、《用心棒》、《姿三四郎》等一系列电影,有对大义“武士忠义”的歌颂,也有对平凡的“小子精神”的赞扬。导演们不断对现实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提出警示,用影视语言诠释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渴望。他们的影片中即便有西方文化的渗入,但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更多的是根植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寻找立足点。这对日本电影本土性的保持和发展极为重要。
岩井俊二创作《燕尾蝶》,耗资六百万美元,中日美多方合作参与制作,这不但是因为影片中涉及到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群,更是对破除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等种种界限,寻求相互合作,互相融合的一次文化尝试。当我们面临一种生存的、精神的困境时,我们总是寻求突破的出口,我们希望在交流中获得答案。我们将自身置身于不幸之中,大概会更容易对与自己有着相同困境的人产生同情,人心的体察来自于境遇的体会,我们与你同在,一切都会理解。隔膜或许是因为即使同在一个空间,却彼此思想情感不通。我们关注精神状态,才会明辨是非,在物质的漩涡挣扎得太久,身心都会麻木冷漠。所以,导演在这里是怀着最大的真诚来创作的,这不仅是一部电影的发生过程,也是一个导演寻求精神道路的努力。
故事的发生地“元都”既是虚构的也是现实的,出离于东京却也源自于东京。生活在东京这样一个整齐规律的地方,忙碌现实的都市人,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浅层的平面化的生活也难以诞生故事,生命也在萎缩。而“元都”为故事的发生提供了变数,或者只是将现实生活中原本就存在的这样一种变数借由“元都”这一媒介由边缘地带转置于众人的视角之下,让观众有机会去注视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或有意或无意而被忽视的处于边缘地带的人。对边缘人的关注是影片表达底层社会关怀的一个角度,也是我们进入生活粗粝本身的一个窗口。
岩井俊二为考察都市人的生存状态曾前往亚洲各地去考察,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还有中国内地各处,最终在上海他看到了浓烈而真实的人间烟火气息的存在,这与日本人生活的过度规律化模式化截然不同。人们在户外洗菜做饭,一边忙碌家务一边聊天,饭菜飘香、笑语交融,公共的生活空间令人愉快轻松。他感慨日本人精神的贫瘠,虽然他们物质生活更加充裕,却缺少了这样的生活气息。元都人对金钱的执着导演认为是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这似乎已经不仅是金钱的诱惑,而是体现为一种对命运和环境的抗争与不从,绝境中的人总是会拥有巨大的生命能量,不管是什么,只要能让人为之努力,这个过程就是对自我的肯定。当然,金钱毕竟不是精神层面的救赎,欲望的满足总是伴随着空洞的幻灭感,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原本追逐金钱本是以此为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在追寻的过程之中,金钱不知不觉已经被我们当成了梦想本身,我们在企图控制物质的过程中,居然毫无意识的被物质牢牢控制,然而这样的事实竟难以为人所察觉。职场中拼搏的都市人,希望努力工作来实现自我,又总是成为工作的奴隶,金钱的附庸。他们追求自由,却越来越失去自由。这种迷惑和困顿是让人沮丧而忧郁的。
在《燕尾蝶》中,岩井俊二让从世界各地带着不同的肤色、语言的人来到这欲望的金钱“故乡”挣扎沉沦,在这里有的人的欲望被满足了,然后带着创伤的灵魂从这里离开,也有最终也一无所获客死异乡的追梦人。不论是实现了金钱梦顺利回到故土的,还是留在这片充满罪恶的土地上继续挣扎的,又或者已经客死异乡的人们,其生存的价值从未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确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日本电影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动荡、经济萧条,人民也生活在不安之中。社会环境的激烈变化会引发个人意识的转变,丧失、孤独、迷茫这样的颓废精神特征烙印在日本人身上。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电影特征是感官刺激的成分和浓重的影像风格出现。但是即便在这样的颓废的环境之下,岩井俊二始终坚持着他唯美清新的镜语风格,并且坚持高度的艺术责任感,因而总是能够赢得观众的认可。岩井俊二的电影里面带有明显的日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痕迹,而且日本民族文化极端的共同心理特征或有意无意的在他的电影中显现。
参考文献:
[1]晏妮<走出低谷,再见昔日的辉煌--九十年代日本电影>[J].电影艺术,1998,(2):26.
[2]彭修银<东方美学>[M].人民出版社,2008:26.
[3]土居健郎著,阎小妹译<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商务印书馆,200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