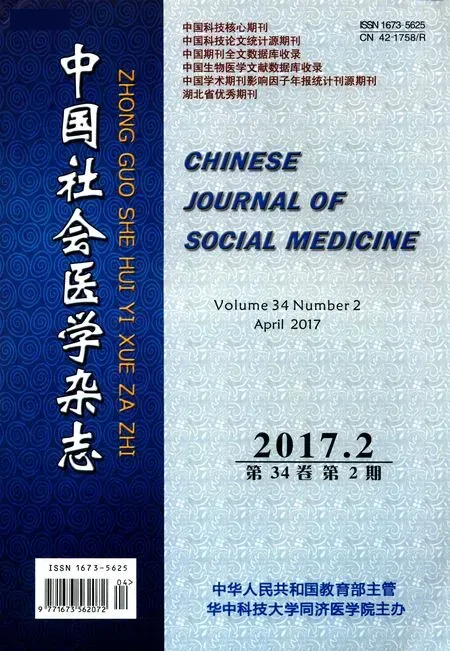生物技术时代安乐死研究的新趋向
刘刚
·理论研究·
生物技术时代安乐死研究的新趋向
刘刚
当前安乐死的研究实现了从隐问题向显问题的转变,随着大量安乐死案例的出现,对其进行理论的思考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安乐死问题的复杂性使得科技、政治和法律等参与其中共同解决“安乐死难题”,而从道德伦理角度的思考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安乐死的研究不仅在于探究死亡中的相关概念、范畴等,更是希望通过对临终患者死亡状态的探究,引导人们正视死亡和死亡之前的生命。
安乐死; 隐问题; 伦理; 道德
生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生命科学的进步,开拓出这一时代急需讨论的一些重大议题,如妇女堕胎权与未出生婴儿生命权之间的冲突,绝症患者选择“安乐死”以保持人格尊严的权利与医生宣誓遵守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之间的冲突,人类改变其他物种的基因从而重构生物演化路径的权利与生态环境的“自然权利”之间的冲突等[1]。在这些议题中涉及到生命的安乐死问题已成为医学、生命伦理学等学科讨论的焦点。安乐死(euthanasia)原是个希腊词,由eu(好)和thanatos(死亡)两部分组成,因此,这个词的直接意思就是好的死亡。其对象主要是指患有不治之症,并在当前医疗技术条件下无法治愈的患者,经过医生和病人双方同意后进行,为减轻痛苦而进行的提前死亡。随着人们对生命科学的关注以及大量相关案例的报道,安乐死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在新的技术环境下,正在转变成“安乐死命题”。围绕着安乐死命题首先出现的是和社会有广泛联系的案例;其次,患者安乐死的最终实现,意味着在医生、患者、家人和社会之间,就这个患者的生命问题达成了一种共识。
1 安乐死现象的出现与发展
1986年我国陕西省汉中市出现了第1例安乐死案例,以后陆续出现了类似“李燕事情”等案例。而在西方国家,安乐死案例出现的更早,近代以来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的卡伦·昆兰案、英国的普雷蒂之死等。大量案例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使得关于死亡的讨论从过去的隐晦、不可说等逐渐转向公开,与此同时,在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每年申请安乐死的人多达上万,但真正被实施的人大约只有约3 500人。在美国,尽管安乐死没有合法化,但每年被实施安乐死的人多达上百人。可以看出,安乐死正在由过去的隐问题变为显问题,这就意味着它和现存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的关系更加密切。此时的安乐死问题,就变成了“安乐死命题”而存在。
安乐死由隐问题逐渐转变为显问题的过程即是哲学的思辨之路,也是普通民众认同的过程。就哲学思辨而言,有详细记载的开始源于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办法;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
中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2]在其著作《乌托邦》中,将安乐死理解为“好死”与“善终”的意思,“当在无法治愈的疾病之外又增加了残酷的折磨时,法官和牧师出现在患者面前,并规劝他,试图让他明白他已经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生命的所有幸福和意义……既然生活已变成纯粹的磨难,那就不应该质疑接受死亡,也不应该对自己或在他人帮助下得到身心的解脱产生怀疑。”
马丁·海德格尔[3]通过对存在与时间中的实存分析,将死亡诠释为:“人是面向死亡的存有,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此在这种可能性中完完全全以它的在世为本旨。”这可以理解为人人终必死亡。正因为人人都要死亡,所以我们要反向而行,那就是生存。二战的到来,使安乐死的发展走入了另一个维度,而这种维度是安乐死本身所不能蕴含的。二战之后,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人们的视野由对二战的反思转向了对自我和生命的关注。
大量案例的涌现,引起了理论学家的兴趣。Ross[4]对末期患者精神状态的五阶段模型;安乐死中滑坡理论的应用[5],托马斯·香农[6]对安乐死类型的划分,从安养院的成立到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的安乐死组织,均表明安乐死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小,由过去的哲学和医学的范畴,扩大到了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等领域。在当前新一轮的生命科学发展中,安乐死必将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
2 由安乐死产生的三大命题
安乐死的存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死亡,同时还涉及到死亡的主体人和死亡的环境。并由此引出了安乐死存在的三大命题。
2.1 安乐死的科学技术命题
安乐死的实现是运用科技成果诊断安乐死对象的状况、帮助其死亡的过程。在美国著名的“特丽案件”中,医生用电子设备检测特丽脑部产生意识的区域有没有活动,试图通过扫描脑血流量等手段反映病人脑部活动变化,但试验结果到底如何却不清楚。进食管的使用成为维持特丽生命的主要渠道,因此,围绕着能否拔出进食管和什么时候拔出,出现了很多的争论。传统医学是以希波克拉底宣言为基础建立的,主张和强调救死扶伤;而现代医学则是在日内瓦宣言的框架中存在,认为医生的职责除了救人外,还可以加入让患者“好死”的内容,这两种宣言之间的差别,成了对待安乐死态度不同的一个方面。按照亚里士多德[7]的观点,科学的重要功能是解释,科学解释就是从有关某种事实的知识过渡到关于这种事实原因的知识。因此,在涉及到安乐死的科学命题时,需要更多的去追问选择安乐死的原因。从贝尔纳[8]大科学的角度来看:“科学可以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系统,一种维持和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在安乐死的发展中,是否也需要一种建制,使其偏向于程序化的方式,也就是建构起赞成和反对安乐死的两种体系。
2.2 安乐死的法律命题
特丽案引发了诸多法律争论,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患者死亡的权利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是患者本人还是监护人;当患者不能表达自己意愿时,患者的丈夫和父母是否有权利替患者做出决定。作为患者父母的仅仅是血缘关系还是具有法律的抚养义务。监护人的权利是得到法律保护的,这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权利,必须符合当事者的利益和要求。
安乐死的法律命题主要指向了其合法化的问题,并出现了合法化和非法两种主要的倾向。安乐死合法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依法保护实施安乐死的人,同时还要避免出现因为安乐死而导致的犯罪行为。因此,安乐死的法律命题就集中在是否能够保证病人享有选择或不选择死亡的权利,并且将其作为一项基本的权利,这其中涉及到生存权、自由权、选择权和尊严权等。
2.3 安乐死的政治命题
“特丽”案发生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前期,很多人都会将这件事情与选举联系起来,认为由此引发的“生命文化”讨论将成为国会中期选举的中心议题。共和党反对拔除特丽的进食管,而民主党一些议员明确反对国会通过相关法案干预。民主党作为一个团体采取了与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合作”的态度,置身于讨论之外。但对一些选民来说,他们认为生死问题是个高于一切的问题,他们关心在没有外人的干预,特丽·夏沃将会死于饥饿和脱水的情况是否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所以当安乐死的问题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时,作为人类契约组合体的政治就会进行干预,形成了安乐死与政治发展并进的道路。
作为政治维度的安乐死,包含着政治家和广大民众的两种态度,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的。美国的选民会根据政治家的立场决定自己选票的投向,因此,政治家反过来就要依据选民的想法决定自己的立场。在这个案例中,美国的大多数选民支持拔掉特丽的进食管。民意调查显示,70%的被调查者认为国会不该多管闲事,在美国的两党中,共和党反对拔掉进食管,而保守党内部则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要么沉默,要么追风。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政治的存在不是纯粹的,安乐死的政治命题,和现实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3 安乐死研究中的伦理道德价值
从古希腊起,安乐死一直困扰着人们,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死的掌控和干预能力越来越强,使得死亡问题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这种模糊不仅仅体现在安乐死的定义和分类上,更体现在涉及到安乐死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上。在伦理利己主义者看来,只要自杀或安乐死的行为是利己的,就可以实施。而康德义务论道德哲学认为,人不能仅仅被当作手段,而是目的本身。这种不同伦理观念的冲突,在安乐死的研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通常情况下,做出一个道德判断需要考虑4个因素,即行为的动机、行为本身、行为的后果和行为者的品质。在安乐死这个范例中,安乐死的行为动机存在着善和恶两方面,安乐死本身是一个合道德和合伦理与非道德和非伦理之间的争论,安乐死的结果是患者无痛的还是痛苦的死,而涉及到的行为者包括患者、医务人员、家属和社会的其他存在。我国早期研究安乐死的学者胡佩诚[9]从代价-收益的角度反思了一个生命痛苦活着的意义,并指出“为维持一个苟延残喘的生命而遭受的苦痛和折磨在无情地增加,而病人自己享有的以及任何方式给予他的裨益却在无情地减少,随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而受益变得越来越少,人们可能怀疑,所有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
有关安乐死的道德争论,主要涉及两类性质的问题:第一类,安乐死对人类而言在道德、伦理和法律上是否可行。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和形而上,涉及到基本的道德原则、法学理论、宗教原理、哲学思辨等,如人的权利、自由、人的生命起源等。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安乐死是可行的,那么我们可以接受自愿且自我实行的死亡吗?这个问题属于实践层面,主要是医学的领域,涉及医学伦理学的问题。
安乐死的伦理和道德争论,其真正的原因是各种观念背后所依据的基本道德原则的差异,这些差异的本质是对生命的态度和意义认识的不同。源自于宗教的传统,带有着神圣的色彩,将保护生命作为首要的原则。而世俗的观念,则将死亡与生联系在一起,看作是一个过程,有始有终。美国学者罗丝说,“死亡如同生一样,是人类存在、成长及发展的一部分,其意义可以说就是成长的最后阶段,你是什么,以及你所作为的一切,都在你的死亡中达到了最高潮[10]。”
4 安乐死研究的社会意义
黑尔[11]认为,人们赞许或者谴责任何的事物“总是为了引导各种选择,亦即我们自己的或他人的、现在的或将来的各种选择。”在安乐死研究中,不仅要探明安乐死中的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说明安乐死作为死亡的一种方式的合理性和可实施性。把安乐死由一个医学和伦理学命题转变成为一个社会的命题的目的在于希望引导人们去正视死亡,进而正视死亡之前的生命。
在安乐死研究中,生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说的分歧已经成为影响安乐死发展的重要因素。生命神圣论对于死亡的阻止,成为反对安乐死的核心议题,范隆指出:“死亡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当死亡被否认时就可能是更大的问题。”生命质量说对于质量的强调,使判断死亡的标准出现了很大的模糊性,引起了人们对于生命的很多争论。古老的拉丁格言曾说过:“生命中最确定的事情是我们都会死亡,最不确定的则是死亡何时降临[12]。”
在生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说之间,是否存在着转义,将成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命题。美国学者凯瑟林克提出,在生命质量说和生命神圣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生命神圣原则在维护生命方面并不如经常宣称的那么绝对和僵硬;同时,生命质量的概念也不仅仅与相对价值和主观价值相联系,两者之间可以互相协调和补充,如生命神圣原则的尊重,其中就包含对生命质量说的关心[13]。
美国学者格罗沃则希望用生命品质来取代生命神圣的概念,他认为人的生命神圣论有3个推论:有意识、活着或成为人。人是本质上有价值的,但只有“值得活”才能作为这三者的共同基础,而这值得活就是生命的品质,进而,只有具有了人的生命的品质,人的生命才是值得活的。
这种生命质量和生命神圣之间的转义,是对生死问题的一次全新的认识,打破了传统生死二元对立的局面。在现代生物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对于生命不同维度的认识,也是个人在实现自我权利过程中自主性因素得到最大化的体现。人们研究安乐死,不仅仅是为了把握几个概念,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伦理学家麦金泰尔[14]所说:“理解一个概念,把握表达这个概念的词的含义,至少应了解支配着这些词使用的规则,从而把握这个概念在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1] 汪丁丁.生物技术时代的伦理学[J].技术创新,2002(1):23-23.
[2]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程孟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93.
[3]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305.
[4] Ross EK.On Death and Dying[M].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7.82-83.
[5] 杰拉尔德·德沃金,弗雷.RG,西塞拉·博克.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M].翟晓梅,邱仁宗,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6] 托马斯·香农.生命伦理学导论[M].肖巍,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97.
[7]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16.
[8] 贝尔纳 JD.历史上的科学[M].伍况甫,彭家礼,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6.
[9] 胡佩诚.生命与安乐死[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3.26.
[10] 冯泸祥.中西生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0.
[11] 黑尔.道德语言[M].万俊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5.
[12] 莫特玛·阿德勒.西方思想宝库[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16.
[13] 张桂华.西方道德哲学九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16.
[14] 麦金泰尔 A.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4.
New Trend of Euthanasia Researches in the Era of Biotechnology
LIU Gang.
School of Marxism,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
Currently,researches regarding euthanasia have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implicit question to explicit one.With large amounts of cases of euthanasia,now it is possible to make theoretical thinks on this topic.Meanwhile,the complexity of euthanasia requests the involvement and cooperation of technology to solve regarding problem,politics and law and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and ethics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requisite for solving this problem.The researches of euthanasia are not limited to discussion about concepts and domains,but also intend to lead people to face up to death and life before death through exploration of the status of patients near the end of life.
Euthanasia; Implicit problem; Ethics; Moral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171)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1
R-052
A
10.3969/j.issn.1673-5625.2017.02.001
2016-04-24)(本文编辑 熊月琳)